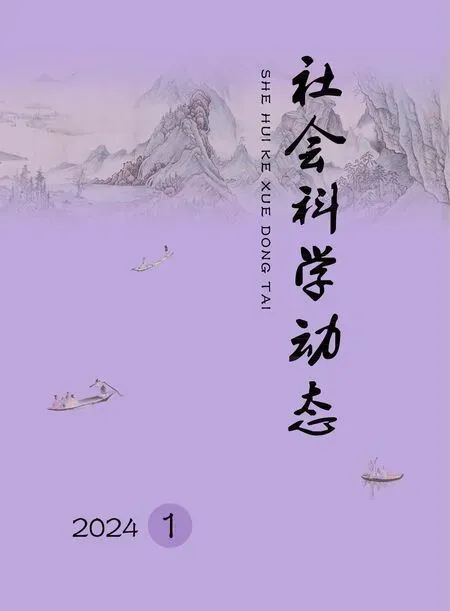跑单帮:商业、人口流动和战争时代松动的社会关系
朱天啸
“跑单帮”一词,指单人随身少量货物至异地贩卖的商业活动。在交通欠发达的年代,不同地区之间的物价有差异,正是为了赚取这中间的价格差而产生了跑单帮。该词首先出现在上海一带,并在20 世纪40 年代成为热门话题。在近年的民国史研究中偶有涉及。有研究认为,跑单帮是沦陷区普通民众因生活物资匮乏不得已而从事的走私活动。在抗战后期,上海的户口米制度无法向市民提供足够的生活所需,使得黑市米粮成为必要的补充。而黑市米粮正是单帮商民所提供。①当时的报纸认为在抗战末期,跑单帮的现象极其兴盛,对上海的食物供应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又如一些学者研究抗战时期的浙江经济,发现跑单帮带动了战时新的商业路线。②商贩将上海、杭州货物带到浙江省富阳县场口镇进行交易,其中大量货物输往后方。③跑单帮被这些学者视为一种经济现象。
笔者想要探讨的话题是战争时代社会关系的松动,以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战争时代人口流动增加,不仅仅是因为当兵参军,或者逃避战火。跑单帮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方式。从事跑单帮的人并不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但他们在两地之间来往十分活跃,这是一种不太受到关注的人口流动现象。关于战时的人口流动,学界多关注抗战时期人口西迁④,及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影响。⑤不过,“迁移”与“流动”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思考,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一个连续的时段。这一时段内的社会环境持续动荡,因而跑单帮在20 世纪4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中保持了相当大的热度。
一、争取粮食的斗争
跑单帮在抗战期间兴起时,社会舆论多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上海地方史研究者认为,“跑单帮大都以个人经营为主,但为了预防沿途遭人抢劫,这些个人商贩又多人结帮同行,到目的地后再分散活动,故被叫作跑单帮”⑥。商贩需要穿过日军封锁线并躲避检查,本身是社会治理的违禁行为,因此在上海的社会舆论中,跑单帮类似一种都市传说。一位生活在上海租界区的居民回忆,自己在抗战时期年纪尚小,因此对战争的苦难没有切身的体会,但他有两项记忆深刻的战争回忆:一是“有时听说谁谁谁跑单帮背米,被日本赤佬用刺刀捅死了”,二是听说从虹口过来的居民愤愤不平,因为在外白渡桥要向日军鞠躬行礼。⑦二者均为听说而非亲见,但是跑单帮的传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这是战时出现的一种奇观。
跑单帮在兴起之初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亲历者多处于社会下层。他们面临许多困难,诸如工作条件的不稳定、失业、收入减少,以及粮食来源锐减等。这些都是战争对生活秩序的冲击,是社会关系松动的主要表现。因为缺少稳定的收入,上海的工薪阶层开始跑单帮。申新一厂的工人耿阿红回忆:1937 年10 月,申新一厂被日军轰炸而停工。耿阿红带领一家六口人逃回江阴老家。1938 年交通恢复,耿阿红返回上海,在安达纱厂工作,工资六角一天,不够全家人的日常开销。这一时期物价开始上涨,但工资水平保持不变,耿阿红决定放弃工厂的工作,转而贩卖蔬菜。不久他开始跑单帮贩米,直至抗战结束。在他的印象里,跑单帮贩米的都是失业工人。⑧
乡间农民受到战乱影响,也会选择跑单帮来维持收入。1945 年的上海《杂志》月刊曾刊载张金寿的《北行杂记》一文。张金寿从苏州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前往北京。在车上他与一个跑单帮的山东农民交谈得知,这个农民从济南乘火车到天津去买面粉,然后带回济南销售。该农民自家有耕地,但是可能受到战乱的影响而无法耕种,而且即便耕种有一点收成,他也会面临苛捐杂税。因此他索性将田地闲置,靠跑单帮赚钱谋生。⑨
也有居民回忆,跑单帮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家庭增加食物来源。月份牌画师唐铭生抗战时期在五洲大药房画广告,工作不稳定,收入很低。日军占领上海后,所有居民排队购买劣质的户口米。而唐家小孩多,户口米不够全家人所需。唐铭生之子唐荣智回忆,孩童时期的自己曾与母亲一起到青浦县朱家角跑单帮买米,以增加全家人的口粮。在回上海的船上,唐荣智坐在米袋上以躲避日军检查,他的母亲则在夹层背心里藏有另一些大米;在途中,他曾目睹日军在检查时抢走别的乘客的米。⑩母子二人一同行动,大概是为了彼此掩护躲过检查。在耿阿红与唐荣智的例子中,跑单帮是一种个人应对困难生活的策略。
通过跑单帮来补贴家用在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北京跑单帮的商贩早期多乘火车往来于北京、张家口之间。最先从事此种营生的人,多居住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一带,是铁路职工的家属或街坊。北京在1942 年之后实行粮食配给,粮店供应质量低劣的“混合面”。张家口的粮食供应较北京充足,但工业品较为短缺。他们在北京购买一些纸烟、土布一类物资,到当时的察哈尔首府张家口脱手,再购买粮食、肉类回到北京。但是后来日军检查变得越来越严格,平绥线火车在南口站、康庄站停留时间变长,很难躲开检查。跑单帮于是转移到其他检查不严的路线上,例如石家庄和奉天等。⑪日军的检查使得跑单帮的活动需要不时更换路线,跑单帮的商贩因此扩大了他们的活动区域。
二、特殊的商业模式
交通运输路线被战争破坏后,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受阻,但仍然需要以一种替代性的方式进行,跑单帮因而承担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上海作为工业中心,为全国生产销售大量的轻工业产品。抗战开始后,日军在沦陷区设置层层封锁线,力图切断上海与后方特别是重庆的经济联系。这样一来,大宗商品批发无法进行。《上海商业史》认为,跑单帮是战时一种特殊的批发运销方式,跑单帮的商贩在上海购买少量日用百货,然后冒险穿越层层封锁线到达后方,一人独立完成运销全过程。粮食等农产品从郊区流入上海同样要经过这种“化整为零”的运输过程。跑单帮不仅是一种生活策略,更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模式。⑫
跑单帮所贩卖的商品种类很多,并且根据市场需求而出现各种变化。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内的丝织厂原料较为紧张。浙江海宁出产生丝,又临近上海,虽然地处游击区,仍有农民小规模地收购生丝,然后带上火车去上海贩卖。贩卖生丝的人增多,就被敌伪注意而受到阻拦。跑单帮的商贩因此将少量生丝缠在身上或藏在衣服里面,带到上海。除生丝外,海宁所产的小湖羊皮在1940 年后一度颇为畅销,据称香港市场的需求量很大,采购者到上海的租界来收购。跑单帮的商贩转而经营此种羊皮,但是1941 年12 月香港沦陷之后,羊皮无法在香港转口国外,销路中断。⑬
抗战期间的长江沿线,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既有日军、汪伪政权和土匪,也有各个派系的抗日武装。这些政治军事势力的共存,使得交通运输系统更为复杂而且危险。跑单帮的存在是对这种战时社会状况的适应,因此日军和伪政权都无法完全禁止,但是跑单帮的过程惊险不断。据耿阿红回忆,日军沿“清乡区”筑有一道竹篱笆,并规定任何人不得进入距离竹篱二里的范围内,一旦被发现,日军则会向穿越者开枪。贩米者为穿越禁区而产生分工:一种人将米从竹篱里面拿出,获利最多;第二种人在外面拿到米再带到上海租界外围地区;第三种人将米拿到租界内叫卖。后两种人只有微薄的利润,但相对安全,第一种人获利较多,但是穿越禁区非常危险。耿阿红回忆,“禁戒线内,被日军枪杀的人极多,有的被缚在篱笆上,活活戳死”⑭,贩米所冒的风险极大。有一次是深夜在井亭头,贩米者有上千人,贩米者向伪军行贿后,趁日军调岗期间穿越竹篱。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引起日军注意并开枪,人群四散,三人死亡。与耿阿红同行贩米的邻居顾洪友,颈下中弹,两人爬过三条河浜,最终幸免。⑮暴力发生的地点往往是远离城市中心的偏远地区,封锁线成为跑单帮过程中的难关。即使如此,商贩仍然想尽办法,试图穿越封锁线。
跑单帮不可避免地要躲过种种检查,行贿成为常见的手段之一,这也是战时社会特别是沦陷区社会风气败坏的一种表现。行贿并不能消除跑单帮所面临的风险,商贩张泰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张泰在南京购买西药(奎宁与针剂),然后往江北的“匪区”贩运。他在下关火车站经受检查,在居住证下塞钞票,向车站的警察行贿,然后才得以通过。不料在下关车站通往江边的路上,他又遇到检查,因此再次行贿而且不断哀求,才得以放行,但少量货物被扣下。到达江边后,他需要找到愿意合作的船主帮忙渡江,因此又需要花钱。为躲避检查,渡江在下半夜进行。靠近北岸后,船主避开码头,不靠岸。跑单帮的商贩们在江滩内就下船,只身淌过冬天的江水上岸,之后继续行夜路,天明时在一家小店里歇息。他在店里听人议论,昨夜在江北某地一群商贩被人告密并被抓。张泰最终到达六合县城外的“匪区”,完成一次买卖。⑯单帮客除了多次花钱行贿来通过检查,也要承受可能被抓捕的精神压力。
抗日武装如新四军在苏中一带活动,也需要通过跑单帮来获得物资,其运输过程同样经过类似的步骤。1942 年9 月间,新四军采购一批医疗仪器和卫生玻璃器材,因为难以小规模带出上海,新四军的采购人员在海门县青龙港一带寻求帮助。当地一位单帮领头人褚四姐,经常帮助新四军运输物资,她建议事先买通码头管理处处长和稽查处处长。打点完毕,新四军的采购人员得以随船通关。褚四姐日后被揭发而被日军逮捕受刑,但她没有出卖新四军的情报,最终被营救。但是海门县青龙港也因此备受怀疑,新四军不得不另找其他的运输路线。⑰跑单帮需要多次实地试验某一路线的可行性,在战争期间,任何路线都不可能万无一失。
跑单帮也会遇到交通事故和伤亡。钱财与伤亡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社会的各种流言蜚语。《万象》杂志在1944 年曾刊文分析跑单帮的兴起,该文认为1940 年3 月发生在宁波镇海口的景升轮倾覆事件,使跑单帮这一现象进入大众视野。景升轮搭载大批旅客,他们大多在上海与宁波之间活动。由于当时乘客过多,景升轮发生倾覆,导致许多旅客丧生。事故发生后,有传言称,搜救者在落水行李中发现各种隐藏的钱财。景升轮上的许多乘客其实是在跑单帮,他们隐匿钱财的方法由于事故而意外泄漏。在这一事故之后,各地日益严格检查旅客的行李。灾难事故背后的隐情,使得社会大众知晓了跑单帮的存在。⑱
又如1944 年在无锡附近的官渎里与正仪车站之间曾发生列车相撞事故,伤亡者很多也是跑单帮的商贩,他们活跃在沪宁铁路一线。无锡本地文人曾写诗描述单帮的活跃:“大包小裹负累累,粉米鱼肉随意挈……上车下车涌如潮,满坑满谷路阻塞。”列车相撞后,“货物浸淫血渍中,抛残金饰无人拾”。诗人同情死者,点评单帮客之死,称“君等若为国家死,雄鬼声名应赫赫。奈何骈死荒山道,不过鸿毛同一掷”⑲。无锡同样是跑单帮活跃的地区,商贩竞相逐利而落的可悲结局,在社会中引发复杂的观感。社会舆论一方面认为这是战时畸形社会的一种表现,商贩多为生活所迫而操此业;另一方面,舆论批评跑单帮的活动扰乱了经济秩序,没有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
除了交通路线的紊乱,传统的银行汇兑业务也被战争干扰。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都有各自的货币,商贩为了跨越这几个区域,就需要想方法携带现金而不被发现。当时各种纸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都在贬值,职业商贩因而青睐黄金来保值,他们为了携带黄金而想出各种方法。例如,1942 年上海的文具商人汤蒂因去重庆跑单帮,卖完货后返回上海时,她化装成难民步行穿越湖北一带的封锁线。为了携带现金而不被察觉,汤蒂因煞费苦心。她先将2000 元美钞卷紧塞进空牙膏筒中,又将法币换成30 两黄金,打成细长条,塞进油纸雨伞的伞柄中。这些黄金也用来支付旅店和船票之类的花销,黄金是在不同区域之间通用的货币。⑳又如,原商务印书馆编辑赵克毅回忆,他在抗战后期(1944 年)随家人旅行途中曾遇到一群跑单帮的商贩。赵家人在湖南省桃源县住店,打听如何穿越封锁线,其中一个商贩答应带赵家人穿越封锁线。该商贩私下里说,他所携带的木盆、肥皂等货物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木盆上的厚实铁箍其实是黄金所制,但外表涂有黑漆加以掩饰。该商贩其实是在穿越封锁线,倒卖黄金。㉑黄金在各地价值也有差异,商贩可以从中赚取差价。黄金作为货币开始悄悄流通,也是沦陷区人心动荡的一种表现。
三、作为“第二职业”的跑单帮
抗日战争结束后,市面曾一度平静。但随着国共内战的扩大,跑单帮再次进入一个新高潮,并发展出一些新形式。这一时期没有日军的封锁线,商贩在各地穿梭往来较为安全。但是交通工具的承载量有限,使得旅行活动较为艰难。陶希圣在回忆录中写到,1948 年末“南京与上海之间,跑单帮的小商人、搬家避难的军公人员把车站拥挤得水泄不通,火车拥挤得上下无门,旅客们只有跳窗户”㉒。在这一时期跑单帮的人多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失业者,种种原因使他们生活困难,他们操持旧业已难以维生。跑单帮因而成为他们的“第二职业”,商业行为和糊口谋生之间的区别逐渐变得模糊。
这一时期,往返于大陆与港台之间的跑单帮者最受人瞩目,甚至被人称为跑单帮中的高级形式。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上海与香港、台湾之间的交通得到恢复。随着战事演变,上海的有产阶级逐渐向香港靠近,资本和工厂不断从上海迁往香港。初到香港,这些上海人一时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上海和香港之间跑单帮。商贩们将香港市面上容易携带的奢侈品如金笔、名表、化妆品之类的商品带到上海销售。与上文提到的贩卖粮食、日用品不同,这些人所贩卖的商品表明他们来自一个更优越的社会阶层。他们颇具资本,举止阔绰,经常占据飞机、轮船上的高级座位,并非一般失业阶层或穷苦百姓。到了战争末期,上海海关盘查甚严,并且打击奢侈品消费。一些往返于上海、香港之间的商贩因而改变线路,转走台湾。40 年代后期的台湾,制造业尚未发展,因而此类奢侈品畅销一时,售价甚至高出上海。乘飞机往来于大陆和港台之间的商贩,被认为是跑单帮的人当中获利最多的,社会舆论为之侧目。㉓
台湾在1945 年光复之后,与大陆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多。《西方日报》记者在1947 年登上一艘前往台湾的轮船,发现统舱与甲板上睡满了跑单帮的生意人。其中一人向记者说,台湾几乎缺少一切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该商人说纺织品在台湾可卖出较高的价钱,但是前往台湾的海轮班次较少,一票难求。赴台一次的开销可以花掉一半的利润,而且渡海的旅途颠簸,十分辛苦。一个月跑两次台湾所赚的钱,可以在上海买三担米,一家三口,仅够吃住而已。㉔台湾经济在日本殖民时期,以生产大米、蔗糖等农产品为主,制造业不发达。日本在战败之后,一片萧条,无法顾及台湾,所以上海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兴起,上海的轻工业品不断输往台湾。
解放战争期间已经没有日军的封锁线和检查,但是伴随国统区、解放区界线的演变,有一些跑单帮的农民来往于国统区、解放区之间,使平静的乡间发生一些变化。静海车站是津浦铁路上的三等小站,昔日乘客稀少,但是随着沧县在1947 年被解放军攻克,津浦线铁路被切断,静海站成为天津以南的终点站。有记者发现,静海站挤满了跑单帮的人,他们多是从青县、沧县一带过来的难民,从乡下携带少许农产品,乘火车到天津城里贩卖,再在天津带些杂货回到乡下。他们已经放弃耕作自己的薄田,靠跑单帮谋生。在返回家乡时,他们可能也会遇到盘查,跑单帮的行为会被认为是走私,所以这种营生并不安稳。这些难民对自己的营生毫无好感,痛恨战争打乱了他们的生活。㉕
在解放战争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跑单帮,在国统区俨然成为一景。其中跑单帮的军人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多是抗战胜利后退伍的,因为退伍后无业而开始跑单帮,当时的报纸社会版常见此类人的身影。《苏州明报》载,湖南籍军官李春华,曾在某通信班担任班长。李春华于1947 年9 月间负伤退伍,与他同时退伍的还有家住苏州的另外一名通信班成员。退伍后,两人共同在京沪线(今沪宁线)、津浦线跑单帮,据说收入尚可,李春华把家眷也接到苏州,租房居住。㉖苏州一带是跑单帮的活跃地带,李春华跑单帮的想法或许是受到苏州同僚的启发,两人可能在退伍时就做好了一同跑单帮的打算。跑单帮的军人在火车上常常身着全套制服,以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常常依仗自己的身份不买票,并拒绝补票。铁路部门对此类人十分头痛。㉗直至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出台对策,禁止身穿军队制服者跑单帮,认为这种行为有辱军人荣誉。淞沪警备司令部在1948 年12 月11 日发布命令,禁止退役军人穿着军装跑单帮。现役军人身着军装跑单帮者,自12 月17 日起,一经发现,“一律将其军服剥下”,24 日以后再有发现者,还将没收其货物。㉘该命令并未完全禁止退役军人跑单帮,这可能表现了官方默许的态度。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在火车上跑单帮的退伍军人越来越多,战事从北方扩大到南方,跑单帮的退伍军人也随之从北向南流动。《老照片》杂志曾刊载一位原国民党军官王宗贤所写的个人历史,其中涉及到他跑单帮的经历。1948 年济南解放,王宗贤离开济南到徐州,他在徐州看到很多人跑单帮,于是加入其中,他先是在徐州与南京之间活动,从徐州带粮食、肉类去南京贩卖,后来徐州战事紧张,他改到南京、上海一线活动。南京解放,他又在上海与衡阳之间活动,生意越做越差。衡阳解放后生意变得更加困难,最终不得不返回山东原籍。㉙国统区的规模不断缩小,王宗贤跑单帮的范围也随之南移,一直到无法继续为止。
时局动荡,撤退的不只军队,还有国统区的公务员。1949 年淮海战役后,江北地区的地方政府相继遣散了其工作人员。他们多数聚集在南京一带,依靠政府发放的一点遣散费度日。南京的《每日晚报》报道,为了生活,这些失业公务员不得不在市场上做各式小生意,养活一家老小。本钱少的人在南京的新街口、大行宫、建康路一带倒卖银圆,而本钱较为丰厚者,则在上海、芜湖一带跑单帮。据说他们贩卖所得也能抵上基层公务员的薪水,但做小商贩让他们感到难堪。㉚战争尚未结束,没有人能过上稳定的生活,跑单帮虽然能弥补一些收入,但是面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下降,公务员的心情十分复杂,备感焦虑。
战争同样使得学生流离失所,出现了流亡学生群体,也导致部分失去生活来源的学生以跑单帮维生。解放战争时期学潮频发,学生群体时常借助媒体发表意见。《新闻天地》杂志在1949 年登载一名跑单帮学生的自述,向读者倾诉苦衷。该文称,社会上很多人对流亡学生跑单帮的行为予以批评,但是他们确实有困难之处。这名学生来自郑州,郑州解放后,他们的学校南迁至江西吉安的青原山。因为生活经费不足,这些学生凑集一点本钱,推举几人外出做些小生意,希望以此来添补衣食。他们在浙江衢州、江西樟树一带收集鸡蛋、鸭蛋、竹笋一类农产,乘火车或汽车带到杭州、上海出售。为节省开支,他们往往不愿购买车票,选择坐在长途公交车的车顶;在乘火车时,他们不愿缴纳运货费,被铁路乘警发现后,又与乘警诉苦,最终不得不添补一些运费。该文作者称,跑单帮十分辛苦且收入微薄,交通费用会抵消他们的贩卖所得,所以才经常逃票。他们过去都是富家子弟、闺阁小姐,像逃票这种并不光彩的行为,实在是因为万不得已。当时全国学生都在抗议物价上涨,他们不可能等到任何政府的救济,只能通过跑单帮来自救。该文希望社会能了解他们的困难,让他们在苦难中生存下去。㉛
四、跑单帮的妇女:生活压力下的性别关系
战争时期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外出谋生。妇女加入跑单帮的行列,引发了社会关注,成为战时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许多妇女往往负责家庭内的饮食,如上文所述,妇女为了筹集粮食可能会加入到跑单帮的行列中,她们与男性一样活跃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万象》杂志曾刊文认为单帮客中约30%是女性,而且战时乘交通工具出行的妇女人数较战前大大增加。㉜当时的大众媒体对这些妇女十分好奇,有些人注意到跑单帮的妇女经验丰富,灵活老练,与大众想象中艰苦谋生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1948 年,《茶话》杂志某作者在京沪线(即沪宁线)列车上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带了一篮虾到上海。这位姑娘家里开鱼行,她经常乘火车往上海带货,把虾交给上海的鱼行,当日去当日回,有时一趟能赚二三百万(解放后币值改革,一万等于一元),有时则赔钱。由于经常乘车,她似乎很熟悉车上的其他人。车上有年轻男性与她调情玩闹,她反唇相讥,不以为意。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里,这位姑娘灵活周旋,业务熟练,给该文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㉝
这些妇女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她们的社会关系。很多人认识铁路警察或者茶房(搬运工),这给她们提供了诸多方便。《茶话》杂志的一位作者在火车上听到一位跑单帮的少妇阿四妹在与相识的乘警闲聊:乘警说阿四妹现在(1948 年)应该不如之前抗战期间贩米赚得多;阿四妹回应着说,过去众人还在第一道检查台排队等待时,她已经出了车站;乘警则说,阿四妹交情好。言下之意,阿四妹可能认识车站的工作人员,可以躲开检查,因此比众人独得先机,跑单帮的成果丰硕。阿四妹显得与众人十分熟络,她在列车快要到站时,将车门打开,探出半个身子,迎风微笑。站台上候车的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阿四妹则对人群致意,俨然是该站的一位名人。㉞想必她也曾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其他人提供过方便,因此得到如此爱戴。跑单帮的群众相互熟识,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团体。社会关系网发达的妇女跑单帮很有优势,在自己的社会阶层中左右逢源,并且相当享受这种奇特的自由感。
妇女在公共空间的活跃也意味着战时家庭关系的某种变化。妇女外出跑单帮,说明夫妻关系有可能出现了裂痕,比如妻子不能得到丈夫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自谋生路,因而跑单帮。例如1946 年苏州的一起离婚案,勾画了跑单帮的妇女所处的家庭关系。本案中夫妻均为苏州本地人,男方是医师,抗战开始后,男方前往大后方行医,对留在苏州的妻子不闻不问,男方更在大后方行医时与另一护士结婚。女方因此依靠跑单帮生活,并于跑单帮的过程中结识其他男性并同居。抗战结束后,男方返回苏州,发现婚姻实际已经破裂,故向法院申请离婚。㉟类似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学者倪万英在上海的司法档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件。例如,1946 年一位木匠控诉妻子及其情夫“妨害婚姻”。该木匠的妻子早于1941 年就因夫妻感情不睦而逃走。逃走后与跑单帮时认识的情夫同居并另有子女。她逃走的原因是:跑单帮时自己的货物被没收了,回到家之后夫妻二人因此争吵,丈夫不让妻子吃饭,并扬言让她去改嫁。最终丈夫撤诉,二人正式离婚。㊱在这两个例子中,女方都是因为男方不提供经济上的供养而外出谋生。当然也有男方跑单帮时出轨,以及妻子趁丈夫外出跑单帮时出轨的案例。㊲在地方小报和法律档案中的婚外情事件里,跑单帮时常成为婚外情发生一个要素。这意味着战时的经济压力对家庭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也是社会关系松动的一种表现。
五、小结
跑单帮的盛行,反映了长期的战争对我国国内贸易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跑单帮的商贩增多,说明正常的贸易受到了阻碍。在战争环境下,商业活动的规模被迫收缩,以一种个体化的方式继续进行。货物、资金和运输都依赖个人只身完成,一个人等同于一个商号。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资交流,因此能够以隐蔽的方式得以存续。这是跑单帮兴起的社会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商业活动不再仅由专业人士完成,任何受生计所迫,懂得门路的个人都可以尝试。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善于此道,从中牟利,这当中风险很大。资本主义商业提供了一种“自由”,使得个人不再依附于原有的社会关系当中,而进入一种风险与机会共存的处境。史学界多强调20 世纪40 年代官僚资本主义在社会上层的扩张。笔者认为,跑单帮是社会中下层人民创造出的市场交易活动,是战争刺激出的投机行为。
从中我们也能看出一些战时人口流动的特点。在以往研究中,由政府机构牵头实施的人口迁移受到较多的关注,例如迁都重庆,高校和企业内迁等。这些活动与军队的转移密切相关。跑单帮则是自社会底层兴起的现象,并以秘密的方式穿越沦陷区、国统区的界限。它并不是人口从一地流动到另一地的单次行动,而更多的是在两地之间反复进行。这也提示我们,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存在许多不易觉察到的联系。从某种角度说,跑单帮的人最终并未离开故乡,但是他们频繁旅行,他们的活动与战争有着微妙的联系。
社会关系的松动是跑单帮兴起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持续的战争。战争造成的社会压力,使得社会中旧有的社会关系无法维持下去。沦陷区、国统区的社会秩序,确实在战争的压力下不断松动甚至崩坏。可以说,战争造就了大量原子化的个人,他们试图重新组织社会关系以自救。跑单帮的个人背景各异,但是很多从事此业者并非职业的商贩。他们可以是失业的公务员、退伍军人、流亡学生、家庭主妇等等。他们跑单帮是因为受战争的影响,旧日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够再支持他们的生活。跑单帮并不只是横向、平行的人口流动,战争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生计,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下滑。这意味着更多人进入社会下层,尽管可能是暂时的。社会阶层下滑使得他们带有各种焦虑、愤怒或是嘲讽的感情。跑单帮是一种临时的生存策略,应对战争期间特殊的现实,并且象征了一种对时局的不满和抗议。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