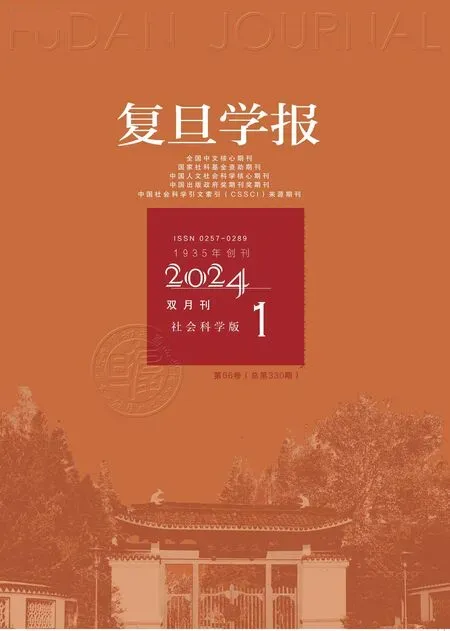从功德报偿到“汉家尧后”:刘邦置立巫官与两汉天命论的变迁
尉雯琪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一、 问题所在:刘邦祭祖、神权统一与抚慰诸侯
“汉家尧后”是关涉两汉政治的重要命题。王莽宣扬刘汉祖尧,以舜后自居,借此求图禅让,刘秀以降的东汉诸帝,则号称“汉承尧运,历数久长”,将它转化成了巩固政权正当性的手段。《汉书》更于《高帝纪》文末铺陈汉家祖系,称刘邦上承刘累、远祧唐尧,并强调他早在即位之初,即已根据家族迁徙轨迹,置立秦、晋、梁、荆四地巫官,所谓“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可见汉为尧后,“岂不信哉”。(1)班固:《高帝纪下》,《汉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1~82页。
顾颉刚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现代学者,他不信从《汉书》的说法,驳诘有二:其一,《左传》曾经窜乱,并非信史,《高帝纪》据此立论,固为无稽;其二,在以国别命名的四巫之外,尚有九天巫、河巫与南山巫,何以判定四地巫官乃为祭祖,而九天诸巫“就和汉的先人不发生关系了呢”?(2)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05~507页。顾文以《左传》为伪,当今多数学者已不能接受,但他的第二则诘问,仍使“刘邦祭祖”说难以作答。
刘邦置立诸巫,事在高帝六年,《封禅书》所载甚详:
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3)司马迁:《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8~1379页。《汉书》文字稍异,见《郊祀志上》,《汉书》卷二十五上,第1210~1211页。
细绎此段文字,可知与四巫关系最为紧密的乃是九天巫,五者“皆以岁时祠宫中”,河巫与南山巫则逊之不及。
除四地巫官与九天巫在《封禅书》中一体合论外,祭祖之说仍存在两点疑问:第一,若依“汉家尧后”,刘邦祖先曾先后居于晋、秦、梁、楚四地。这不仅是家族迁徙的轨迹,也照应着祖宗世代的早晚,刘邦置立巫官,既为崇祖隆祀,不应轻忽疏慢,为何《高帝纪》在赞语中随意变乱,称秦、晋、梁、荆?而在撰作时代更早、也理应更多保存了资料原貌的《封禅书》中,又以梁、晋、秦、荆为序?
第二,刘邦为祭祖设立巫官,丰地先世为何祠以荆巫,而非楚巫?诸巫之置在高帝六年,刘邦封刘交为楚王、刘贾为荆王,其区别荆楚,使分治淮河西东,正在同年春正月。(4)《楚元王传》,《汉书》卷三十六,第1922页。刘交是高祖亲弟,刘贾仅为“诸刘”,(5)《荆燕世家》,《史记》卷五十一,第1993页。《汉书》稍有异说,见《荆燕吴传》,《汉书》卷三十五,第1899页。刘邦以荆巫祭祖,淆乱亲疏,不合情理。
李祖德支持“刘邦祭祖”说,他对荆巫问题的解释是:史载刘邦“立濞于沛”,既然他改荆为吴,封刘濞吴王,则其原籍沛,正在荆国的域内。(6)李祖德:《刘邦祭祖考——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不过,李祖德对“立濞于沛”存有误读,如颜师古所说,这是刘邦于沛地立刘濞为王之意。(7)《荆燕吴传》,《汉书》卷三十五,第1903页。史载刘濞受封的过程是: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刘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为吴王,国除。(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53页。
可见刘濞既领刘贾故国,沛便“国除”,并非荆域。况楚都彭城,沛不应越山隔水,受荆国遥领。(9)沛的地位特殊,或许曾为中央直管。可参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马孟龙:《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室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
由于“刘邦祭祖”说存在诸多问题,学者便努力另作新解。李零认为,刘邦是有意“整齐六国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各种巫祠)”。(10)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0页。既如此,为何刘邦却漏掉了巫风大盛的燕、齐?
杨华的观点与李零类似,认为刘邦在长安宫中置立诸巫,人为划定分属职掌,存有“神权统一”之意。至于燕、齐未得置巫的缘故,他提供了两种推测:其一是梁近齐鲁,梁巫可能已经掌握齐鲁巫术;其二,其时追求巫术的实用,方士的地域身份并不重要。(11)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杨华的观点是,“汉家尧后”之说虽属可疑,但刘邦置巫,确是根据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可是,梁地近鲁,并不近齐,齐、鲁有别,梁巫恐难以熟习齐巫的术法。且以燕、齐巫风之盛,为何术法却对刘邦而言缺少实用?
李炳海则认为,刘邦征召异地巫师,是为了与秦巫共同参与朝廷祭祀。择取晋、梁、荆,是由于这三处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均为要害,故通过置立巫官,体现对三处诸侯王的倚重。(12)李炳海:《汉初异地群巫参与朝廷祭祀的政治文化意蕴——〈史记〉相关篇目的对读》,《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但晋、梁、荆在刘邦初年何以成为要害之最,以及在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下,征召地位低下的巫师进京,(13)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27~48页。为何能够体现对诸侯王倚重,其间似有逻辑缺环。
综合学界目前看法,尽管已有顾颉刚的批驳在前,赞同刘邦置巫与家族源流有关的论述仍为多见。但当学者具体讨论“汉家尧后”问题时,却极少信从《高帝纪》的赞语,不以刘邦为“汉家尧后”的首倡,(14)相关讨论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84页。其间的矛盾与含混,正说明学者面对巫官问题时的困扰:既不以汉初已有“汉家尧后”为然,又尚未在祭祖说之外为刘邦置巫觅得合理解释。
二、 军行载巫:战争中的巫术需求
《封禅书》在叙载四巫之前,有一段重要文字,提供了关键线索: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治枌榆社、立蚩尤祠,及置立四地巫官,皆在高帝六年,这一时间节点应予瞩目。秦楚汉间战事连绵,刘邦于五年春正月称帝,五月即下诏使兵罢归家,责令诸吏善待军功高爵。六年冬十月,又与功臣剖符,大封王侯。巫官之置与此时序相接,理应放在“天下已定”,以战功定封赏的政治背景下进行讨论。
同时,史书对刘邦重视枌榆社与蚩尤祠的缘故也有明确交代:
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15)《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第1378页。又见《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50页。
而《左传》记载:
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16)《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34页。
刘邦出身布衣,可“祓社衅鼓”的古礼,亦是他初起兵时所行之事。《左传》所谓“祝”,与巫关系密切,往往连称。(17)较新的材料有清华简《程寤》、北大秦简《祓除》。李零亦有讨论。参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册,北京:中西书局,2010年,第136~137页;田天:《北大秦简〈祓除〉初识》,《简帛》(第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3~48页;李零:《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下),《中国方术续考》,第58~59页。《仪礼》称:“巫止于庙门外,祝代之”。(18)《仪礼注疏》卷三十七,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1页。而《说文》亦曰:“巫,祝也”。(19)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53页。则刘邦在“祓社衅鼓”之后,以巫代祝,军行以从,使其为战事服务,也合情理。
刘邦祠礼枌榆、蚩尤,显然是为了敬谢神灵对他战事顺利、卒建帝业的护佑,其论功行赏所及,固未限于王侯军卒,亦已将神灵包囊其内。则他所置诸巫,是否也属于对鬼神的酬答?
由于材料缺乏,秦末军队用巫的细节史无明文,但仍可窥蠡大概。首先是两条时代虽晚,但具有较强说明性的史料:
(武帝朝)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20)《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第1402页。
(赤眉时)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21)范晔:《刘玄刘盆子列传》,《后汉书》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79页。
这是汉时军中有巫活跃的明确例证。武帝曾使巫诅军,(22)参王子今:《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赤眉则多山东亡命,其以齐巫祷祠,兵卒籍贯与巫者术法的地域正乃相合。
其次,新见材料对秦汉占卜吉凶、祛鬼禳疾的巫术信仰颇有展现,结合传世文献,可以推测巫者在兵战中的具体作为:
1.祭奠阵亡士卒,使其得受祭飨;镇伏受戮敌兵,使其不能为厉。
时人认为“兵死者”(23)参陆德富:《说“兵死者”》,《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未得善终,有亏天年,不能享受通常的祭奠,有武夷神司掌其事。(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5~110页。《庄子》亦称:“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资。”(25)王先谦:《德充符》,《庄子集解》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2页。“翣”并非旧注所云“武饰之具”,参王龙正、倪爱武、张方涛:《周代丧葬礼器铜翣考》,《考古》2006年第9期。而《国殇》之祭,在汉人王逸看来,即是对“死于国事者”的群祀。(26)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页。参[美]夏德安著,陈松长译:《战国时代兵死者的祷辞》,《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42页。至于敌方“兵死者”,更为淫厉,将以作祟。《左传》载,文子即将晋戍三百卒,视作可以复仇作恶的厉鬼。(27)《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七“襄公二十六年”,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19页。若要驱除厉鬼,则需巫者行法,《淮南子》所谓“战兵死之鬼憎神巫”,汉人高诱即称“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杀之”。(28)刘安编,何宁撰:《说林训》,《淮南子集释》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98页。
刘邦麾下野死乌食,魂魄无依的士卒不可计数,攻战之时,除临阵歼敌,往往又有屠城之举,依照时人的信仰,敌我两方的“兵死者”,均需托赖巫者施行术法。
2. 治疗伤病,祷除疾疫。
巫术是当时疗疾的重要手段,这首先与医疗资源的匮乏有关。据《论衡》记载,社会上流传的病方如称“已验尝试”,则“人争刻写,以为珍秘”。(29)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6页。迟至东汉末年,祝恬受公车征,病于邺、汲,两地往来辐辏,并非边乡僻壤,仍有“困无医师”的忧苦。(30)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8~339页。验方与良医难求,可见一斑。(31)参杨勇:《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分与地位》,《新史学》1995年第1期。而且巫医关系紧密,《说文》即谓“医”曰:“古者巫彭初作医。”(32)许慎:《说文解字》,第490页。秦汉间人也普遍相信,病痛本由鬼神作祟,需以巫术祓除。秦简有“占病祟除”之法,(33)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汉帛书《五十二病方》也多祝由巫术。(34)可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出土医方中的祝由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1~268页。当秦始皇出游道病时,曾使蒙毅“还祷山川”。(35)《蒙恬列传》,《史记》卷八十八,第2567页。汉武帝病于鼎湖,同样“巫医无所不致”。(36)《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第1388页。至东汉,王充仍称当时民风为“病作卜祟”。(37)王充著,黄晖撰:《祀义篇》,《论衡校释》卷二十五,第1047页。可见巫医虽然渐已分途,但以巫术疗疾的传统依然深厚。(38)参林富士:《试论汉代的巫术医疗法及其观念基础——“汉代疾病研究”之一》,《史原》1987年第16期;金仕起:《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新史学》1995年第1期;杨勇:《从出土文献再论战国秦汉时期的巫、医关系》,《简帛研究》2019年第2期。
因此,虽然刘邦军中或许已效秦制,设有医官,(39)参彭卫:《秦汉时期医制述论》,《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2期。但辗转征战之间,药石针砭不便,巫术则相对简易,它的假托鬼神又受时人信笃,普通兵卒对巫者提供的精神慰藉是颇为依赖的。《墨子》论迎敌,认为需“举巫、医卜有所”。(40)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迎敌祠》,《墨子间诂》卷十五,第574页。这自然是理想状况,但战国以降随军有巫,应是实情。
此外,盟誓与辟兵亦需巫者行法。据侯马盟书,盟誓之语要靠“巫觋祝史”说释于“皇君之所”。(41)参朱凤瀚:《侯马盟书之内容与年代考略》,《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01~511页。刘邦征战中,受降与约盟的仪式也应有赖巫者的施为。至于辟兵,又有“蟾蜍五月中杀涂五兵,入军阵而不伤”的传说,则知汉人相信存在取蟾蜍血以辟兵的巫术。(42)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88页。而战国有“兵避太岁”戈,秦简有“矢兵不入于身”之法,(4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汉墓见“弓矢毋敢来”神祇图,(44)参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辟兵图》《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3~212页。也可见辟兵巫术在实战中确有流行。
总之,在时人心中,战争取胜,除了方略得宜、将士用命,顺奉阴阳、托赖鬼神也必不可少。行伍中的祭祀与疗疾离不开巫者的服务,而刘邦要将散乱之众,组织为行旅之师,使他们离故土、冒白刃,在爵禄诱劝之外,于军中存置巫者,使出身社会下层的兵卒心理有所寄托、情感得以慰藉,也至为关键。且其时巫风盛行,巫者于征战辗转之间易于求得。《逸周书》称“乡立巫医”,(45)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晁错谏文帝,也以“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作为安抚民情之法,(46)《爰盎晁错传》,《汉书》卷四十九,第2288页。《盐铁论》描述其时社会,更曰“街巷有巫,闾里有祝”。(47)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2页。史载秦汉战争中胜方每下一城,往往收其兵卒军械,那么刘邦同时将当地灵巫载以军行,使不同籍贯的军士皆能获得符合他们地域信仰的酬神驱鬼之法,应是符合历史情境的。
要进一步验证刘邦置巫与战争有关的推论,则需继续考察,他亡秦破楚,一路收附的兵卒来源,是否与《封禅书》所载梁、晋、秦、荆一一相合?
三、 兵卒来源:梁、晋、秦、荆、胡
关于刘邦军中兵卒来源,李开元和陈苏镇曾有细致考述。(48)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47~179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43、50~57页。以前人丰硕成果为基础,对照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梁、晋、秦、荆,以行文之便,可将刘邦的征战历程暂分四个节点,进行梳理:
1. 起兵至高阳(梁)
刘邦初起,沛子弟随从征战,他又于砀收兵六千,从项梁处请得五千军士。此后西行至栗,“夺”刚武侯军四千人,在高阳又获郦商四千卒,在入战秦关之前,刘邦军队已经迅速壮大。(49)《秦楚之际月表》,《史记》卷十六,第766页;《高帝纪上》,《汉书》卷一上,第17页;《樊郦滕灌列传》,《史记》卷九十五,第2660页。李开元的看法是,此时刘邦军力包括沛兵三千、砀兵万余(六千砀兵、四千郦商兵)、楚兵万余(五千项梁兵、四千刚武侯兵),余为散卒。此时刘邦军队的核心,是砀、泗旧楚国人士。(50)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61页。陈苏镇认为,此时刘邦部下真正楚人不会超过一万三千,至于丰兵、郦商兵,则属魏人势力。(51)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43页。两人所论,除陈苏镇明确指出刘邦应于丰地得兵数千外,仍有两点区别:其一,李开元计入项梁五千卒,认为皆是楚人,陈苏镇默认不在计内;其二,李开元认为,刘邦于薛所得将军陈武二千五百卒,是项梁五千兵的一部分,陈苏镇则于此无论。那么,刘邦的军卒结构究竟如何?其时刘邦以楚为号,麾下兵士的巫术信仰,应以楚俗视之吗?
刘邦此时部卒,包含丰、沛子弟与六千砀兵、四千郦商军并无疑义,问题在于陈武薛卒、项梁楚卒与刚武侯栗卒三者。《史记》载录陈武的侯功,称:
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52)《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07页。《汉书》所载略同,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第556页。
这段文字的史源是汉廷档案,记叙存有义例,可以推而求之。其中有两处需要关注:其一,陈武是以将军的身份“起薛”。由“二岁十月入汉”逆推,(53)此处“岁”表示积年,参陈侃理:《如何定位秦代——两汉正统关的形成与确立》,《史学月刊》2022年第2期。可知陈武起兵在秦二世元年七月,刘邦反秦则迟至同年九月,当陈武“起”薛之时,刘邦尚在山野泽中,其将焉附?可知“起”与“从起”不同,后者是指附从刘邦征战,前者仅是起事反秦之谓;其二,陈武的侯功注明了“二岁十月”一段时间长度,意指陈武自行起兵,经两年十月之后,才彻底归附刘邦。类似的用例又有两处,张说“属魏豹,一岁五月,以执盾入汉”(54)《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592页。《史记》作“属魏豹,二岁五月”,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46页。;陈婴“属楚项梁……四岁,项羽死,属汉”(55)《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第527页。,都通过对某一时段的强调,表明某人归附刘邦的时间。因此,史籍称陈武率二千五百人起薛,只是为了载录他反秦的行迹,这部分兵士并未在当时就归入刘邦的麾下。
至于刘邦至薛,从项梁处所请五千卒,李开元认为“功臣表”有郭蒙诸人从起于薛,可见刘邦确已将其收归己有。但其间论证,似或未足。“功臣表”见八人与薛有关,其中将军陈武已如前论,丁复是越将、革朱是越连敖,将此三人排除,所余五人从起薛地之时共有四种身份:户卫、连敖、卒、舍人。(5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第554、616、555、563、579、583、590页;《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04页。除连敖尚属中低级军吏外,(57)参陈颖飞:《连敖小考——楚职官变迁之一例》,《出土文献》(第五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86~91页。余皆职阶微末,以此论证刘邦获得了项梁军卒,有所不宜:其一,项梁五千兵由十位五大夫将统领,是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战国之时,无论秦、楚,五大夫皆是高爵。《战国策》载陈轸谏阻楚王赐杜赫五大夫,理由即是“得赵而王无加焉”。(58)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3~504页。刘邦军中功侯者,诸将公认曹参第一。曹参起沛为中涓,辗转战于胡陵、方与、薛、丰,始迁七大夫。又经连番征杀,攻爰戚及亢父先登,才为五大夫。项梁所遣十位五大夫将,秩级颇高,其下部将亦应有职有爵,“功臣表”载从起于薛者,身份不合;其二,五千军卒数目非寡,项梁为了广树六国为党,此时曾立韩成为韩王,使其率千余人西略韩地。项梁立一王,尚仅予千人之数,若说将五千兵赠予初出茅庐又无甚知交的刘邦不再收回,也实在过于慷慨。刘邦请兵,是因为攻丰不克,项梁予五千之众,应是助他速胜夺城的一时权宜,并非彻底的军力划拨。刘邦得砀兵六千,攻秦破楚一路率随,“功臣表”即载从起于砀者十四人,他得项梁五千卒约在同时,表中所见从起于薛、疑为楚卒者,却只有五人,这也令人生疑。
除向项梁请兵外,刘邦至薛,非只一次。二世二年十一月,刘邦取得过薛地的控制权(59)《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12页;《曹相国世家》,《史记》卷五十四,第2021页。,当项梁谋立楚怀王时,他也曾再次应召往薛。“功臣表”所见从起薛者,更可能是其中某次归附的散卒。至于项梁的五千卒,应已璧还,时机可能早在他受召至薛,或从项梁征战之间,也可能迟在项梁殁后,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时,此时他剥夺了刘邦的五千军众,改易以砀郡之封。总之,揆以情实,刘邦请得的五千之众,在克丰之后是难以长久保全的。
关于刚武侯的四千卒,史载刘邦“夺”于栗地:
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60)《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57~358页。
刚武侯其人,史籍只此一见。陈苏镇的观点是,史笔既然称“夺”,刚武侯应为楚将,刘邦此时受怀王命,西向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故能夺兵。(61)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42~43页。问题在于,无论依据怀王的号令本身,还是考虑群雄并起的实际,刘邦所能“收”的其实仅是失伍散卒,何能得成建制的四千部众?且刘邦新封武安侯,与刚武侯爵号等侔,或为陈王余部、或为项梁旧属的刚武侯,只因收卒之命,便能将士卒拱手让人吗?
刘邦所受怀王号令,并不只是收散卒一项,怀王还委他为砀郡长、使将砀郡兵。此前刘邦曾收砀兵六千,两倍于沛子弟,但远不足一郡之兵。因此怀王所谓将砀郡兵,不止是对他已获六千砀兵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而是明确授予砀郡兵权。栗属砀郡,刘邦能够成功夺军,应赖于是。
可见刘邦此时兵源主要有丰沛子弟、砀栗之兵及郦商之军,不应计入陈武和项梁的士卒。丰与砀栗,皆为梁地,郦商兵士,亦是梁人。丰是故梁所徙,一度随雍齿归魏。史载刘邦祭祷枌榆,所用宜为梁巫。沛则为故宋,辗转楚魏之间。春申君曾游说秦王,称秦如攻楚,魏将趁机出兵,“故宋必尽”。(62)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第241页。可见宋偃王亡国后,沛虽属楚,魏仍虎视眈眈。此后约五十年,秦军伐楚,沛终入秦。虽然沛人在秦末张立楚帜,但神鬼巫俗的变更,与政权认同相比,是远为滞缓的。沛于楚国,僻在北疆,却紧邻梁魏,丰、沛交往又十分密切,当刘邦起兵之初万事匆简,既祠丰地枌榆,很可能军中已载梁巫,沛中子弟以为祭祷,也属顺理成章。至于砀,高帝五年刘邦以魏故地封彭越为梁王,其封域即是故秦砀郡。(63)《高帝纪下》,《汉书》卷一下,第51页;《地理志下》,《汉书》卷二十八下,第1636页。而郦商军卒四千,乃自高阳东西略人所得,史书又称为陈留兵,(64)《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58页。陈留、高阳皆在魏故都大梁近东,(65)据《二年律令》陈留应属河南郡,可参马孟龙的研究。不过陈留近大梁,是魏名城,即使在当时已归河南郡,未在彭越梁国境内,也并不影响巫祀观念。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以巫祀术法的传统论,这些都应属梁。
2. 破秦与伐楚(晋、秦)
刘邦过高阳后,先遇张良引兵襄助,又得南阳卒,复折西南,与梅合兵北进,入至霸上。当他为汉王就国时,“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不久东向出关,“劫五诸侯兵”,受彭越三万人降,但彭城大败,十余万卒皆入睢水。萧何因此“发关中老弱未傅”诣军,韩信亦收兵,汉军终于复振。此后刘邦平定秦地,得韩信所下赵、代精兵,与楚军战于成皋,兵败逃遁,驰夺张耳、韩信军。(66)《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58~364、371~375页;《高帝纪下》,《汉书》卷一下,第19~22页;《留侯世家》,《史记》卷五十五,第2036~2037页;《魏豹彭越列传》,《史记》卷九十,第2592页;《淮阴侯列传》,《史记》卷九十二,第2614页。这一阶段刘邦军力大增,具体情形较为复杂。其兵卒增补之途有二,其一是彻底归附,受其统辖,其二则属诸侯合兵,协同作战。考虑到汉初诸侯国具有相当自主权的政治现实,讨论高帝六年巫官之置,是不宜将诸侯合兵计算在内的。
将诸侯的合兵之助排除,刘邦此时实际增补的军卒,首先来自南阳。刘邦入秦之前,曾约降南阳守,“引其甲卒与之西”。南阳是大郡,宛为大郡之都。因此刘邦兵围南阳之时,虽然军威已壮,但陈恢仍称他如若强攻,死伤必众,可见实力不容小觑。(72)《高帝本纪》,《史记》卷八,第359~360页。而刘邦既受宛降,余城亦下,则他引兵俱西者,可能已有万余。南阳由故楚入韩,后并为秦郡,六十余年间,秦“徙天下不轨之民”,于是民俗“上气力”,“藏匿难制御”。(73)《地理志下》,《汉书》卷二十八下,第1654页。秦徙罪于此,竟达到能够影响民俗的程度,可证迁徙人数必不在少,巫祀信仰已颇为驳杂。(74)秦始皇亦徙天下豪富入咸阳,但这一政策的施行,距离反秦事起不过十余年,这批移民在秦亡之后也基本散归故乡,因此刘邦后来统率的关中卒仍以故秦为主。南阳情形则有不同,自昭襄王徙不轨之民,至秦末已逾六十年。参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67页。
南阳兵后,汉军多补晋、秦之卒。汉二年三月,刘邦号称要“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为义帝复仇。这于当时,自然仅是宣传的口号,但在他出师东向,与项羽争雄的过程中,的确对秦兵与晋卒越来越多倚重。刘邦征发秦卒,始于初至霸上的“稍征关中兵以自益”。不过,他十月至霸上,十二月项羽即携诸侯军至,其征发秦卒至多不过两月,数量应当有限。刘邦徙封汉中,甲卒歌思东归,(75)《高帝本纪》,《史记》卷八,第370、364、367页。可知此时军士仍以关东为主。
刘邦军中第一次成规模地补入秦卒,应在还定三秦之后。塞王、翟王曾是秦将,后降项羽,得王秦地,他们控制秦兵的能力应当颇强。(76)参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89 页。刘邦出关征讨项羽,两人相随,他们既是故将,又为故王,麾下秦卒,应与俱从。“功臣表”中,有五人其时从起秦地,(77)《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35、943、947、968、973页。很可能即是诸王旧部。汉二年二月,刘邦诏使“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78)《高帝纪上》,《汉书》卷一上,第33页。这亦是此时汉军颇有秦人的反映。
不过,刘邦三月渡河,四月即于彭城惨败,塞王、翟王复降项羽,刘邦仅与数十骑脱身遁去。他后续军力补充,复赖两途:其一由韩信主导,收拢溃散败卒;其二是萧何五月悉发“关中老弱未傅”。六月刘邦亦还栎阳,史称“关中卒益出”。(79)《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72页。“功臣表”中,也可见四位秦将,此时从刘邦出关征战。(80)分别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32、937、956、969页。但是,萧何五月尚仅征得老弱,刘邦次月入关,恐亦无太多丁壮可用。且同月尚需“兴关中卒乘边塞”,时又值“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81)《高帝纪上》,《汉书》卷一上,第38页。关中饥馑惨况如斯,又需分兵乘守边塞,此时追随刘邦东向的秦卒数量,应当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与汉军补入“关中卒”约略同时,刘邦亦得“三河士”。所谓三河,即河东、河内与河南。首先是河南的情况。汉二年冬十月,刘邦受降河南王,置其地为郡。河南王或许未随刘邦战楚彭城,(82)辛德勇:《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第112~120、127页。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南兵卒未出。其时陈余要求汉杀张耳,刘邦为求赵兵之助,遂“求人类张耳者斩之”,(83)《张耳陈余列传》,《史记》卷八十九,第2582页。可见他出关战楚,颇有兵力需求。既然河南已降,亦置郡县,将兵使从是自然之理。(84)崔建华注意到“功臣表”载南安侯以河南将军汉王三年降于晋阳。他推测刘邦彭城败后,诸侯皆叛,“河南将军”亦是叛将,故在汉王三年二次归降。这是合理的推测,这位河南将军很可能是在刘邦置郡太原时复降的。参崔建华:《楚汉战争中的“五诸侯”再讨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至于河南王瑕丘申阳并未亲身从军,很可能是因为他原本仅为张耳嬖臣,威望有限,且瑕丘在薛,申阳与河南兵士渊源尚浅,刘邦故能驱使如意,无需他做驾驭。河南郡即故秦三川,(85)河南郡即项羽所封河南王的疆土,参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楚汉诸侯疆域新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与河东、上党、颍川相接,伊水上游东周与故韩分界交错,其俗属晋,应当不误。
其次是河内。汉二年三月,刘邦虏殷王,置河内郡。殷王从军彭城,竟至战死,相随甲士,应已归属刘邦。殷于战国属魏,入秦七十余年后,反秦事起。如前所述,这样的时间长度,虽然或能影响百姓对政权的认同,但不足更革鬼神信仰,使其改作秦俗。
最后是河东。在汉二年与三年间,刘邦虏魏豹,三分其地,置郡为河东、太原、上党。(86)《史记》系于汉三年,《汉书》则记为汉二年九月。《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72页;《高帝纪上》,《汉书》卷一上,第39页。“功臣表”载蔡寅、缯贺此时初从,即是刘邦这一时期补入故魏兵卒的佐证。(87)《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11、917页。河东久属魏地,太原属赵,上党为韩,它们皆是可以上溯至春秋之世的晋国旧地。虽然已为三分,但文字相近,风俗不远。《汉书·地理志》亦称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孙”,汉廷将其一并视为难治。(88)《地理志下》,《汉书》卷二十八下,第1656页。因此,刘邦所置三郡,军卒皆为三晋甲士,以晋巫为之祷祀,固为所宜。
三河是故晋,巫俗应与前述梁地有别。梁惠王远徙大梁为新都,至刘邦反秦,已历百五十年。大梁本为宋地,宋俗重巫鬼,惠王携民东徙,与当地土著交往融合,又时撄齐、楚兵锋,祠法应已改易旧貌,颇受浸染。刘邦置巫,并立梁、晋,即为此故。
其后,汉军仍有秦、晋兵卒陆续补入。刘邦多次失军亡众,他能够重振旗鼓,除了有赖萧何征伐关中军士,(89)《萧相国世家》,《史记》卷五十三,第2015~2016页。也与韩信麾下晋卒大有干系。早在韩信破魏下代之时,刘邦即已收其精兵,备战荥阳。魏是魏豹封国,已见前述。代为故赵,迟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入秦,距陈胜起事,不过十余年。韩信行定赵地,曾不断发兵诣汉。尤其成皋败后,刘邦驰夺张耳、韩信之军,终使兵士复振。(90)《淮阴侯列传》,《史记》卷九十二,第2614、2619页;《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74页。此时韩信军中有三万是当初刘邦分兵所予,余皆新收晋卒,可能还包括巨鹿战中,陈余、张敖所收常山、代兵数万。“功臣表”载此时从起赵、代者,即有五人可考。(91)“谔千秋于汉王三年以谒者初从,受封涿郡安平”,据此推测,或许亦是赵代之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26、933~934、939、940、945、948页。秦楚之际,常山、代一度与赵分立,但战国时皆为赵地。赵国在这一区域的经营,自迁都邯郸算起,至为王翦所灭,已百六十年。
因此,汉军这一时期补入甲卒以秦晋为多。刘邦大量征用晋卒的时间较为明确,在汉二年、三年之间;而秦卒,虽早自汉元年即已稍征,但由于关中大饥、分兵乘塞,迟至四年兵乃益出。这样算来,刘邦收附三晋甲士,尤其是使他们立有勋绩、足叙功劳的时间,较秦中子弟更早。刘邦置立巫官,《封禅书》载序晋、秦,即应与他先得晋卒用命,而秦兵后显劳绩有关。
3. 垓下之战(荆)
汉四年刘邦大胜楚军,韩信破齐,亦败楚将龙且。汉五年刘贾围寿春,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刘邦与诸将大会垓下,项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惊楚人之多,误以为汉军已得楚地。(92)《项羽本纪》,《史记》卷七,第333页。史念海认为四面楚歌是汉军诡计,陈苏镇指出,此时韩信麾下有俘自龙且军的大量楚人,灌婴也已降下彭城,垓下汉军多楚,不足为怪。(93)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57页。
垓下会时,汉军“楚”卒的确不少,来源大致有四:其一,刘邦于汜水击曹咎军卒半渡,尽得“金玉货赂”,亦应收虏残卒。只是史无明文,未知其详。(94)《高祖本纪》,《史记》卷八,第375页。其二,韩信击齐,大破龙且,楚卒皆降,此后兵分为三,除自将主力、赴会垓下外,又使灌婴下淮南,曹参平齐地。龙且士卒从至垓下者,不知其数,其籍贯的详情,也不易深考。
其三,九江楚兵,亦至垓下。当项羽分封之时,九江原属黥布,汉四年,黥布将兵数千降汉。(95)《黥布列传》,《史记》卷九十一,第2602~2603页。汉五年,楚大司马周殷降,佐刘贾“举九江,迎英布兵,皆会垓下”。此后刘邦又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共击临江王,以其地为郡县。(96)《荆燕吴传》卷三十五《汉书》,第1900页。可见,“举”九江兵者,是周殷与刘贾,黥布率兵乃自外来。在垓下与临江两场战事中,九江兵士统属未变,仍由刘邦麾下的将军——刘贾率领。虽然九江是淮南王黥布的国土,但九江卒此时仍非诸侯的部下。至于九江卒的数量,应当颇众,随何为刘邦游说黥布时,即称其遣兵四千助楚,过于寡少,是臣下的不智之举。
其四是灌婴所降兵卒。汉四年,灌婴由鲁北南渡淮河,降城邑、收士卒,至于广陵,(97)《樊郦滕灌列传》,《史记》卷九十五,第2670页。这已大致相当于汉六年刘贾荆国所辖东阳郡的范围。(98)东阳郡的郡城范围,可参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9页。灌婴南征楚地,虽受韩信分兵,但在垓下战时,乃以御史大夫受诏击楚。(99)《樊郦滕灌列传》,《史记》卷九十五,第2671页。灌婴既为汉廷官吏,此时又尚无荆王,所降东阳兵卒,自然并非诸侯的甲士,而是刘邦的直属。
综合上述,刘邦麾下楚兵来源有四,其中九江与东阳的情形较为明确。这两部劲旅亲历楚汉决战,都来自淮南故楚旧地,城郭相连、巫俗相近,东阳即在刘贾荆国域内,刘邦于汉六年置巫曰“荆”,因此情理固宜。此外据“功臣表”,“荆令尹”灵常于汉五年初从刘邦,随战钟离眜、利几有功,这亦可佐证荆兵在刘邦后期的征战中有所贡献。(100)《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66页;《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第610页。
而燕、齐巫风虽盛,附从刘邦亡秦破楚的劳绩却有限,且自有统属,建制独立。汉四年八月,也即距离垓下决战仅四月之时,“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101)《高帝纪上》,《汉书》卷一上,第46页。其以北貉与燕人并举,又曰“助汉”,隐含燕王与刘邦敌国相匹之意。“功臣表”所见昭涉掉尾即“以燕相从击籍”。(102)《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64页。至于齐兵,虽或于垓下有功,但韩信时为齐王,他们随从而至,是诸侯的行旅,非刘邦的军伍。刘邦实际掌控这支军队,应迟至楚汉事毕,夺军韩信之后。“功臣表”所见韩信旧部齐将,随从刘邦取得战功,即已在诸巫置毕的高帝七年。(103)《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第591、619页。
经过以上梳理,可见梁、晋、秦、荆四巫之置,与丰之枌榆社、长安之蚩尤祠相类,皆是由于刘邦亡秦破楚的征战。九天巫即胡巫,(104)参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98页。《封禅书》将其与四巫同叙,应与楼烦兵士加入楚汉战局有关。楼烦是晋北之戎,赵武灵王拓边,(105)《匈奴列传》,《史记》卷一百十,第2883、2885页。遂入雁门郡。(106)《地理志下》,《汉书》卷二十八下,第1621页。高帝六年,韩王徙都马邑,马邑尚在楼烦之北。则楼烦虽然曾是胡戎旧地,但在秦汉之际,早已属于近边的中国。因此,长于骑射的楼烦兵士,出现在秦末战中,并不为奇。史载刘邦军中楼烦善骑射者,即曾出阵应对楚军的挑战。(107)《项羽本纪》,《史记》卷七,第328页。丁复亦为“楼烦将入汉”,《史记》《汉书》所载稍异,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卷十八,第904页;《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书》卷十六,第554页。以楼烦为代表的边地兵卒,风俗信仰自然与梁、晋、秦、荆有别,他们的祠祀祝祷,有赖九天胡巫。
总之,《封禅书》所载高帝六年诸巫之置条理井然,可大致划为四组:其一是枌榆社、蚩尤祠,它们与刘邦举事时的祠祷有关;其二是梁、晋、秦、荆与九天巫,刘邦起兵以来,军中陆续补入的士卒,正与这五处相合。不同籍贯的士卒信俗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巫者术法亦有区别,刘邦以五地巫者为五处兵源服务,他在称帝之后置立诸巫,既是对巫官劳绩的颁赏,也是对神灵助佑的酬答;第三、四组分别是临晋河巫与南山巫。秦并天下,祠礼名山大川十八,中有临晋在内。(108)《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第1371~1372页。问题是,为什么刘邦独将临晋择出?汉二年,刘邦初出秦关,便是从临晋渡河。出关东向,通常的做法是取道武关或函谷。但刘邦遣将迎亲,曾于武关受阻,河南王“迎楚河上”,(109)《项羽本纪》,《史记》卷七,第316页。也使他对函谷关存有疑虑,反而是经由临晋,可以直达魏豹的封国。魏豹是故魏公子,被项羽徙王河东。(110)《魏豹彭越列传》,《史记》卷九十,第2590页。他由故国膏腴远迁至此,与刘邦被迫入汉中的境况相似,在刘邦出关之前,两人很可能已有联络。如是,则刘邦率军渡过临晋险滩之时,水中风波的顺逆与魏豹反楚的诚伪皆未可知,他兵行险着,取天下后,宜谢神灵。《左传》载子玉在城濮战前,也曾梦见河伯索取琼弁玉缨。(111)《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僖公二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63页。至于南山巫,《封禅书》称“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112)《封禅书》,《史记》卷二十八,第1379页。秦二世自杀于望夷宫,赵高葬其于宜春苑,为何却在南山设祠,又为何以“秦中”称之,不能详知,暂以阙疑。
四、 申说天命:功德报偿与“汉家尧后”
刘邦于高帝五年得天下,次年即兴立巫祠,报劳苦、酬神灵。他在这一时期的诸种行事,亦以与群臣论定功绩、分封王侯为要,其恩待优赏也及于罢归故里的众多兵士。在高帝十二年的诏书中,刘邦因此自称,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可谓无负。刘邦的“无负”天下,是指他论功计赏无所遗漏、公平允当,使随从征战的将士,大者王、次者侯,余者皆得世世复。当他未允帝位之时,诸侯上疏,亦以功臣皆得受地食邑为由劝进。可见将功德报偿作为得享天命的证凭,不止是刘邦的惬心之言,也合乎当时的政治情势。高帝六年诸巫之置,即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时至东汉,刘秀同样以武力平服天下,也曾封功爵、颁策勋,号称有中兴二十八将、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在他称帝之前,诸将几番劝进,最终将他打动,表示“吾将思之”的,是耿纯的谏言。耿纯称,天下士大夫追随辗转,计望无非爵禄,一旦攀附不成,则将四散而去。(113)《光武帝纪上》,《后汉书》卷一上,第21页。所论直截恳切,并无讳饰,功德报偿的观念,仍在政治实际运作层面,发挥深潜影响,是刘秀此时无需否认、也无可辩驳的朴素逻辑。
不过,刘秀虽为布衣奋起,但乐于自号宗室绍绪,他因此有意宣扬“汉家尧后”之说,以证明自己终践帝祚的名正言顺。当其诏许封禅之时,即称得承鸿业,乃为“帝尧善及子孙之余赏”。(114)《祭祀上》,《后汉书》志七,第3164页。不过,此时以“汉家尧后”论证刘汉天命,犹有滞碍。刘秀曾有意祀尧,杜林上疏反对,刘秀最终接受了他“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的说法。(115)《杜林传》,《后汉书》卷二十七,第937页。刘秀既从其议,可知“汉家尧后”尚未能够成为朝廷自证天命的关键一环。
光武之后,明章继轨,仍有意以“汉家尧后”自为表彰。史书记明帝生而不凡,其异象便是“有似于尧”。(116)《显宗孝明帝纪》,《后汉书》卷二,第95页。只是杜林当初所谓“民不晓信”的障碍没有完全消除,章帝朝贾逵上疏,仍以“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来说明《左传》的优长。(117)《贾逵传》,《后汉书》卷三十六,第1237页。尽管时移世易,东汉朝廷于“汉家尧后”更为重视,挑战此说的政治风险也与日俱增,但由此可以看出,朝廷欲使“汉家尧后”更为凿凿有据的需求,仍然存在。
贾逵上疏,在章帝建初元年,《汉书》草成,亦是建初中事。《汉书》追溯汉初史迹,将九天巫从刘邦所置群巫中割裂出来,裁出梁、晋、秦、荆四者,因其与刘向所论汉家先世的迁徙轨迹大略相合,故将其作为“汉家尧后”的证明,系于“开宗明义”的《高帝纪》赞语之中。联系明章两朝的时势,《汉书》乃有深意存焉。在《典引篇》中,班固的阐释更为充分,他称:尧禅舜、舜禅禹,因此尧堪称孕育虞夏;稷、契广立事功,商汤、周武是他们的后裔,故而尧又为陶冶殷周。可见四代圣王的鸿业,其实全都导源于尧。尧据有“元首”之功,于是上天论功报德、善及子孙,将使刘汉昭明祖德,万嗣不绝。(118)《班彪列传下》,《后汉书》卷四十下,第1376、1380页。班固这重逻辑,基于帝王之祚必有“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的论断,(119)《叙传上》,《汉书》卷一百上,第4208页。也在实质上与刘邦、刘秀酬答劳苦、奖励勋绩的观念一脉相承。尽管功德报偿的朴素逻辑日趋沉潜,“汉家尧后”解释的成立,其实依然与之相关。
从秦汉之际到两汉之交,帝业成就的理据由笼统含混的“天命”变得清晰具体,在这一过程中,“汉家尧后”的地位日显关键。两汉同以武力奠定基业,也都遵循功德报偿的政治规则,依据从征之人的劳苦功勋,安置官爵、分配利益,但对于天命,刘邦无心申说,光武诸帝则有意缘饰——尽管实现统治的底色并未改易,但涂抹已经更为堂皇。刘邦出于功德报偿的观念,在长安宫中置立的群巫,也正因如此,被《汉书》改造成了“汉家尧后”的“岂不信哉”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