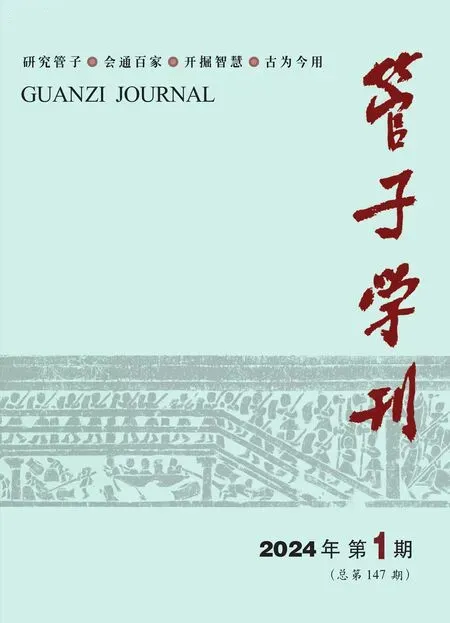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马卓文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
西周以来“以德承命”“以德配天”的观念构成早期儒家所面对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给儒家学者带来了认同障碍与解释困境,他们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因此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倾向于从“时”与“命”的角度揭示儒家“德位”观的新发展(1)参见晁福林:《“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39-47页;王中江:《孔子的生活体验、德福观及道德自律——从郭店简〈穷达以时〉及其相关文献来考察》,《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第50-57页;王光松:《先秦儒家的德、位关系思考——以孔子“有德无位”为线索所作的观念史考察》,《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40-43页;姚裕瑞:《道德与命运:从早期〈诗〉学的线索看儒家德命观的演变》,《管子学刊》2020年第4期,第25-34页。。在相关讨论中,孟子的说法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仍然有学者注意到孟子对“德位”观的论述。王光松敏锐地发现孟子之说与《穷达以时》的区别:二者虽然都以“天”作为得位与否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子的阐释中,“天”是意志主宰者,《穷达以时》篇所谓“天”则指“时”,没有意志主宰色彩。不过,王氏认为天意是神秘的,“有主宰功能的天缺乏德性或德性特点不明显”(2)王光松:《先秦儒家的德、位关系思考——以孔子“有德无位”为线索所作的观念史考察》,《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42页。,这一点还需商榷。李若晖联系孟子的人性思想指出,孟子倡导“修其天爵而人爵随之”,在此意义上,“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3)李若晖:《“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05页。。李氏的判断是准确的,然而在论述时却并未提及孟子讨论“德位”问题的背景——关于圣人之事的叙述与解释。王博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指出,在孟子思想中,从天子以至于人间秩序中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们都应当德位相应(4)王博:《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61页。。
笔者注意到,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首先,孟子对德位关系的讨论是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展开的,而孟子的圣人叙事遵循着强烈的“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这也就意味着历史上圣人参与政治的不同形态必然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其次,孟子继承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以天命和民心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权威来源,超越偶然性的时运因素。本文将从孟子的道统观念出发,在与“时命”观的比较中进一步分析孟子的“德位”思想,并揭明其在孔子之后对“德位一致”观念的重新建构。
一、圣人与道统
孟子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这一说法代表了孟子塑造与诠释圣人的根本旨趣。他认为,圣人具有同一的内在本质,只是由于历史境遇与人伦角色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方式。现实的差异性并不影响圣人之内在同一性;相反,通过“易地皆然”的阐释,孟子证明了圣人之间的传承与一贯。
为了彰显“圣人一道”,孟子构建了系统化的儒道传承谱系,将自尧舜以来的儒家圣人列于前后相继的统绪中。我们引用后来的“道统”概念称呼它,则需要对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澄清。所谓“道”,是对儒家文明的总称,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层面,对人与社会运行原理的根本认识、价值观念、制度设施与实际政治功业都是其中应有之义。所谓“统”,《说文解字》云“统,纪也”(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5页。,二者的本义都与线丝有关,因此可以说,“统”表达了一种“承继性和连续性”(7)景海峰:《儒家学统的重建》,蔡方鹿主编:《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滕文公下》第九章中有一段极其恢弘的描写,社会历史呈现为“一治一乱”的循环式发展,治与乱交替出现,圣人于其中发挥拯救世道、扭转局面的关键性作用(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176-178页。。孟子特别划分出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洪水之祸与尧舜禹之治;第二,殷纣之乱与武王革命;第三,礼坏乐崩与孔子作《春秋》。我们注意到,“世衰”与“道微”总是一起出现,圣人与圣人之“道”对社会历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人对圣人之“道”的背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需要一代代圣人在衰微之际力挽狂澜,传承与弘扬圣“道”。尧、舜、武王、周公、孔子便是这样的圣人。
在《尽心下》第三十八章中,孟子以一种非常整齐的形式将圣人置于“道”的传承链条之上,构建了由尧舜至汤、由汤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的道统序列(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408页。。在这三段大的历史间隔内,分别又有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知圣人之“道”。因为,孟子在别的地方明确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1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269页。,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此六人也可以称为圣人。这一传承序列正表明“圣人一道”,此“道”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悠久流长。
不同于后世韩愈将圣“道”传承区分为“其事行”之治统与“其说长”之学统(11)《原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页。,孟子的道统具有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所传的只是“道”本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将脱离政治。儒家思想承自尧舜,是关于社会人生的恰当表述,也是王道政治的权威解说。因此,掌握王道理论的儒家学者虽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却以更加独立的方式成为对君主公卿的指导与约束力量。
如同荀子所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12)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8页。。圣人对“道”的稽守,绝不是固执一成不变的规矩准则,而是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以适合特定之时的具体之道恰当行事。正因如此,从现实表现来看,儒家圣贤“千举万变”,实际上则是一贯之“道”依据时势的不同呈现。朱熹有言:
故尧舜与贤,而禹与子,汤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杀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说诸侯以行王道,皆未尝同也,又何害其相传之一道?(1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25页。
在朱熹看来,孔子作《春秋》、孟子说诸侯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行为“异行而同情”(14)赵金刚:《常道与变易的困境——朱熹论“汤武革命”》,《河北学刊》2016年第4期,第37页。,都是对“道”的把握。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前代圣人之行的列举,着重于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转移这一方面:尧舜传于贤德之人,禹传于子,汤武革命而得天下。
无论是应然地看还是历史地看,关于圣人的讨论多与政治权力紧密关联起来(15)如陈来认为,在殷周之际的思想变革中,“以德承命”“以德配天”的观念通过西周统治者的阐释与强化,成为非常强势的思想传统;郑开认为,圣人作为人极,具备最高超的智慧和最完满的德性,也应当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61-181页;郑开:《试论儒家思想语境中的“无为”》,王博主编:《哲学门》(第三十五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1页。。因此,获得与传承权力也被视为圣人之“道”的重要表现之一。历史上,圣人权力转移方式的实然差异与孔子不得其位的信念冲击,成为儒家学派不得不面对的公案。包括孟子在内的众多儒家学者都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回应,而《穷达以时》与《荀子·宥坐》等文献中的“时命”观念最具有代表性。
二、德位分合与孔子有德无位
“以德承命”的观念经过西周统治者的阐释与强化,成为前诸子时代强有力的思想传统。《尚书·康诰》陈述文王之德,认为文王具有“克明德慎罚”的功德,这些功德“闻于上帝”,天帝赞美其德,因此降天命于周(1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9-360页。。周公将文王的政治美德与受天大命建立因果联系,在这种思想传统下,有德与受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必然性,“上天通过监视和诫命的方式给予人事祸福以强制干预,因此有德之人理应获得政治上的地位、身份和与之相应的俸禄”(17)姚裕瑞:《道德与命运:从早期〈诗〉学的线索看儒家德命观的演变》,《管子学刊》2020年第4期,第25页。。《中庸》以孔子之名曰: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1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5页。
“德”与“尊”(即“位”)分属伦理与政治两个领域,前者的“极点”是圣人,后者的“极点”是天子。虽然指向不同的领域,但“德”与“位”可以结合,“大德者必受命”的必然性肯定就是对早期文献《尚书》《诗经》中“德位一致”观念的延续。历史上,舜为代表的上古圣人的确实现了“德位合一”。这一信念在东周时期开始面临挑战,随着礼乐秩序的崩坏,德位不一致的情况大量涌现,对传统“德位”观造成冲击,孔子“有德无位”的事实更是给儒家学者带来了认同障碍与解释困境。孔子本来对于自己继承道与德而救济乱世有坚定的信念,其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但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的政治理想不断受挫,即“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20)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84页。。跟随他的子路不由发出疑问:“君子亦有穷乎?”(2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论语注疏》,第207页。
孔子“厄于陈蔡”的经历太具有冲击性,以至于后来在《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说苑·杂言》,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中都记载了孔子受困之时与弟子关于“时”与“命”的讨论。在《荀子·宥坐》(2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6-527页。的记述中,子路从“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的传统受命论信念出发,对孔子“累德”但却无位、无福的处境产生困惑。孔子根据历史上比干、关龙逢、子胥的遭遇,否定了“以知者为必用”“以忠哲为必用”“以谏者为必用”的信念,切断了“德”与“位”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与必然性关联,得出“德命未必一致”的新论断,“具有美德或追求美德的人,他不一定就能得到相应的好的社会回报,他甚至还有可能遭到不幸”(23)王中江:《孔子的生活体验、德福观及道德自律——从郭店简〈穷达以时〉及其相关文献来考察》,《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第52页。。接下来,孔子以“时”的观念对有德无位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成为德(“贤不肖”)之外另一种影响得位与否的因素。而对有德之君子来说,“时”更加直接地决定了他的遭遇,即使是“博学深谋”之人,如果“不遇时”,也终究不能得到与他自身之德相匹配的职位与福禄。
《说文解字》云:“时,四时也。”(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302页。《逸周书·周月解》曰:“凡四时成岁,春夏秋冬。”(25)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谷梁传》曰:“四时具而后为年。”(26)柯劭忞:《春秋谷梁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7页。可以看出,“时”的最初含义主要是体现为时间运转的自然节律的变化,因而有“天时”“时制”之说。后来,“时”又引申出时运之意,强调在具体的时间、时候下人所面临的外部处境。荀子曰:“遇不遇者,时也。”“遇不遇”的说法在《穷达以时》中有很详细的举例说明:
舜耕于历山,陶埏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繇衣枲盖,冒绖蒙巾,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吕望为臧棘津,战监门来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举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遇不遇,天也。(27)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在以上所举例子中,“遇”的意义比较确定,均指遇到知人善任的在位者,被赏识而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也就是说,在有关“德位”的讨论中,“时”为时遇、时运之意,具体表现为能否获得在位者的赏识与举荐。儒家学者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时运之遇或不遇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出于“天”的意志(“遇不遇,天也”),既不由人的主观努力支配,也超出人的认知范畴。
《穷达以时》与《荀子·宥坐》都否定了“德位一致”的必然性,认为偶然性之“时”现实地决定着人的显达与困厄(“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28)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86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士人君子就只能随波逐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首先,儒家学者将道德与时运分为两个领域,《穷达以时》言“有天有人,天人有分”(29)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86页。;《荀子·宥坐》指出,君子应当致力于“材”“人”这些自己可以把握的方面,致力于自我修养,而对于“时”“命”这些人所不能知的方面,君子的明智态度是“俟时”——等待合适的时机(30)《荀子·宥坐》:“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7页。。其次,儒家学者将道德从得位的纠缠中解放出来,德行修养超越了现实境遇而自有其崇高本质。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获取福报的手段”(31)姚裕瑞:《道德与命运:从早期〈诗〉学的线索看儒家德命观的演变》,《管子学刊》2020年第4期,第33页。;《荀子·宥坐》言“君子之学,非为通也”(3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7页。。因此,人也不会因为外在时运的幸与不幸放弃自身道德的如一,所谓“穷达以时,德行一也”(3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86页。。在这样的观念下,儒家学者号召人们,无论境遇如何都应当“敦于反己”,通过道德自律与自足把握自身,主动地超越外在之“时”对人的限制。
以上说法固然振奋士人君子道德修养之自主意识。但是,以偶然性的时遇、时运否定德位之间的必然关联,实际上撤销了根据德而赐予福的天命的确定性(34)参见王光松:《先秦儒家的德、位关系思考——以孔子“有德无位”为线索所作德观念史考察》,《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47页。,也撤销了天命“赏善伐淫”观念背后天人共同遵守的某种稳定的价值体系。笔者认为,这对“圣人一道”的道统阐释带来一系列困难。第一,将一切不可知的、人力不可及的因素统统归之于时遇与运命,“这确实有其模糊性和消极性的一面”(35)李加武:《荀子“禅让”观释义》,《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85页。,使得“道”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大打折扣:既然人世的变迁更大程度上由不可知晓、不可把握的“时命”主宰,那么儒家宣扬的“道”对于社会的秩序建构来说就不再具有纲领性的意义。第二,如《荀子·宥坐》所言:“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36)王先谦:《荀子集解》,第527页。以偶然性的时遇作为得位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很容易导出一个结论:即使是无德或者德行不那么优越的人,如果他足够幸运,也可以得位、得福。这样就削弱了西周以来权力合法性论证中德行的重要性,也使得历史上圣王的道德优越性受到质疑。第三,在上一条的基础上,撤销了圣人之道德与精神的内在一贯性,使得道统的序列不能维系,而变成没有内核的偶然性的罗列而已。
孟子在阐释圣人、建构道统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面对圣人之间权力转移方式的差异与得位与否的根本不同,他必须要对德与位的关系进行某种相对确定性的说明,以证明圣人的内在一致性及圣人之“道”的普遍性与客观性。
三、天、人与权力合法性
孟子在《万章上》中引用孔子之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3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259页。所谓“其义一”,一方面表明,圣人不同的权力转移方式背后有同一之“道”的支撑;另一方面表明,在圣人的时代,获得天子之位是可以用理义来解释的,同时也是人的理性、道德可以把握的。在“德位”问题中,孟子聚焦于四种具有代表性和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一,尧舜相代;二,禹不传贤而传于子;三,孔子不得其位;四,汤武革命。
尧舜相代的故事被先秦诸子广泛称颂。尧的权位由异姓之贤者继承,舜因道德优越获得天子之位,尧舜二人的美德与王权相配合而更加熠熠生辉。当时流行的说法认为尧舜禅让(38)《荀子·正论》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可见此种说法的流行与影响。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1页。,《尚书》《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及《子羔》《容成氏》等出土文献都提到了“禅让”,而以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解释最为清楚明白(39)参见李加武:《荀子“禅让”观释义》,《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83页。,其对禅让作了清晰的界定:“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40)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96页。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禅让’,‘贤德’是权力让与者和继承者双方都需要具备的”(41)王中江:《〈唐虞之道〉与王权转移的多重因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3页。。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前代君王将权位授予后代君王,完成禅让过程。
然而,孟子与荀子纷纷反对尧舜禅让的说法(42)《孟子·万章上》中,当万章询问“尧以天下与舜”的事情时,孟子明确回答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正论》一篇中对于“尧、舜擅让”的世俗之说展开了详细的批评,从“天子无敌,无谁与让;死而有传,无所谓让;天子无老衰”三个方面反对禅让之说。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256页;牟宗三:《名家与荀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55页。。对于这一现象,徐复观指出,“儒家认为天下不是天子或人君私人之可以‘取’或‘与’”(43)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他引述孟子言“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4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116、256页。;又引述荀子言“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有擅国,无擅天下,古今一也”(45)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1、336页。。徐复观认为,这些说法表明:“天子之对于天下,不是私人‘所有权’的关系,所以天下不是个人之所得而取或所得而与。”(4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290-291页。徐氏的观察可谓精确。在《唐虞之道》描述的禅让过程中,天子之位的转让似乎只是“上德”与“下贤”两个个体之间的事情,孟、荀极力反对这种权力转移方式具有合法性。
《万章上》第五章中,当孟子弟子万章询问“尧以天下与舜”的事情时,孟子明确地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并且指出尧舜相代是“天与之”的结果,王者之位的归属只能由天所决定(4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256-257页。。如果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分析,这里的天当为“主宰之天”,而《穷达以时》中的天则为“运命之天”(4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5页。。天作为神圣的主宰者观看、监视人类世界的活动,通过“行与事”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意志,决定天命与权位的归属。孟子所理解的天之“行与事”,主要体现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在这里,百姓的反响体现了天命,民众的选择即为天的选择(49)刘蒙露:《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及其内在关系——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10期,第17页。。也就是说,“主宰之天”的意志并非不可捉摸,而是有明确的道德内涵,百姓所希冀的仁爱正义就是天所看重的。因此,“主宰之天”在价值上其实与“义理之天”(5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第365页。一致。这样一种“民意论的天命论”(5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185页。,承自西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观念,孟子在本章结尾引用《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语,正可以说明其思想来源。
万章又询问“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之事,当时有说法认为禹不传贤而传于子是德行下降的表现。这种观点在秦汉之时依然存在,其表现就是当时关于“家天下”与“官天下”的激烈讨论(52)参见王中江:《〈唐虞之道〉与王权转移的多重因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4页。。孟子认为,无论传贤还是传子都取决于天命,只有天及天所代表的民的意志才能决定王权的合法归属。在《万章上》第六章的描述中,与禹所举荐的益相比,百姓更亲爱、服从禹的儿子启(5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258页。。因此,启之获得权位并非父亲私意传授,而同样是天与民的意志所决定。总而言之,孟子以“天与之,民与之”的说法解释尧与舜、禹与启之间的权力转移,为王位之获得与否设定了一种确定化、道德化的评判机制,从而重新建立起德位之间的必然关联。同时,主宰之天的至上性与神圣性,以及民意对伦理秩序的推崇,恰恰反过来证明了尧、舜、禹等圣人崇高的道德与伟大的功业。
那么,孔子之不得其位是否意味着孔子之德还不能令天与民满意?对于“私淑”孔子的孟子来说,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圣人的权力转移过程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位的君主向天举荐可堪重任的贤德之人,如“昔者尧荐舜于天”“昔者舜荐禹于天”“禹荐益于天”。根据《万章上》的相关文献材料,“荐之于天”与“暴之于民”并列,具体体现为“使之主祭”“使之主事”。《尚书·尧典》记载,尧询问四岳是否有可以接续帝位之贤人,四岳举荐庶人舜,称其有大孝之德,尧因此让舜处理政事,以考察他的德行(5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尚书正义》,第45-46页。。《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舜协助尧举元恺、流四凶,使国家安定、百姓和谐(5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7-584页。。在这些文献中,舜即位而为天子之前就已经被尧赏识而拥有政治职位,可以开展政治行为,与孟子“使之主祭”“使之主事”的说法若合符节。由此可见,“荐”的实质就是:在位的君主经过考察选择贤德之人,使其执掌一定的政事,包括侧重于神圣事务的对祖先天神的祭祀和侧重于现实事务的对臣子百姓的管理。天与民观看并体验作为君主候选的贤德之人的政治实践,从而决定是否赋予其天子之位。舜、禹都通过了这一考验,得到天与民的赞同;而禹本来推举的益并未得到百姓归附,人们更加爱戴禹的儿子启,因此益没有获得天命。这样一种“荐”的环节,与《穷达以时》所说的“遇”非常相似,成为孟子“德位”观中受命与否的偶然性因素的唯一来源,也是孔子有大德而无大位的合理解释。
孟子在《万章上》第六章(5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259页。中又区分了“匹夫而有天下”与“继世而有天下”两种类型,“匹夫而有天下”的条件有两个:大德与天子之荐。孔子之德可以与舜、禹相提并论,但因为不被在位之君主举荐,就没有被天与民考察的机会,因此也没能获得天命之王位。因此说,孟子在努力调和德位的应然一致性与历史的实然无序性之间的张力。在孟子这里,与权力转移有关的天为主宰之天,天意并不是神秘不可测的,其与民意相表里,具有明确的道德内涵。真正具有偶然性的是人的因素:在现实世界中,在位的君主可能是贤者,也可能是凡俗之人;可能会举荐有德之人,也可能会忽视而背弃他们。
孟子特别维护天命之权威性,“天子之大位乃天与之,绝非私相授受之范围”(57)王博:《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62页。。天命一旦确立,就不可随意更改,汤、武取代桀、纣而有天下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并且也依然要符合非常严苛的条件。《易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5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从天、人两个维度肯定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这也是先秦儒家一贯的看法。《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5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53页。
孟子不认为汤、武“弑君”,因为被其诛杀的桀、纣已经彻底违背了“君”的实质,他们“贼仁”“贼义”,不可以“君”视之,不过“一夫”而已。朱熹特别阐发“一夫”的含义:“一夫,言众叛亲离,不复以为君也。”(6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页。从朱熹的说法可以看出,“君”的实质并非权位或强力,而是民心及民心所体现的天命。《荀子·正论》载“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从这一定义来看,桀、纣显然不能够称为王,所以“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弒君”(6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24页。。
孟子坚持“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即是从天意和民心的角度阐释汤武革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6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198页。桀、纣贼仁、贼义,他们的治理戕害百姓,因此丧失了民心,同时也意味着丧失了天命,朱熹言“盖人心离而天命改久矣”(63)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30页。。与之相对,汤、武道德高尚,治理清明,百姓自愿归附于他们(“民之归仁”)。在《梁惠王下》第十一章的记载中,孟子生动地描述了人们对仁义之君的敬爱:天下之人都视汤为君主,热切企盼汤的到来以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所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6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第57页。。由此可见,汤、武真正获得了民心。天通过民意向背显现自己的意志,剥夺桀、纣之位而赋予汤、武天命,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得到证明与确立。
结语
孟子虽然也历经了历史上无序的事件(65)张小稳:《〈孟子〉学术史》,济南:济南出版社,2023年,第11-30页。,但他并不承认德位相分的合理性,而是“期望以理想的秩序纠正现实世界无序的状态”(66)王博:《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62页。。《万章上》集中收录了孟子对圣人之事的叙述与解释。他试图证明“圣人一道”,以构建道统、彰显儒家思想的至高地位与传承谱系,而历史上圣人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也成为“道”的呈现形态之一。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以“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他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实际上,“德位一致”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推断:大德之人必定得天下,得天下之人必定具备大德。相比于为后世君子树立某种内圣外王的承诺,孟子的问题意识似乎更聚焦于为儒家圣人作某种辩护。他关于德位关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澄清世人对尧舜、禹、汤武、孔子的误解而展开的。在孟子采用的“天与之,人与之”的释论模式中,天的神圣性、权威性以及民心的伦理意涵,证实了圣人之德的卓越。进一步而言,孟子证明了圣人之间具有一贯的内在本质,从而确立儒家之“道”的稳定性、普遍性与传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