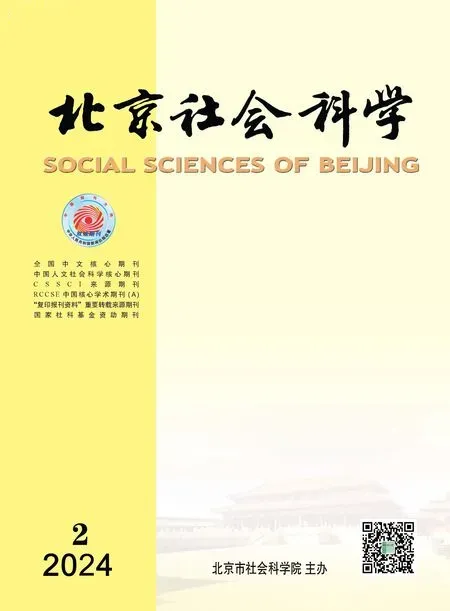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
——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李天慧 张润枝
一、引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近年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思想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学者研究的聚焦点,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对它进行研究时,学界往往只重视探讨它是什么,如论证它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却忽视研究马克思关于它不是什么的回应,如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研究中,并没有研究马克思关于它不是形而上学方法的回应。事实上,自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的导言中明确提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却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质疑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那么,针对质疑,马克思是如何回应的?鉴于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其不仅关系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定性,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阐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而且关系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科学性。
据此,本文尝试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进行解答,希望有助于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拓展性研究。
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
通过文本研读可知,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指出,研究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研究方法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初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是从一些具体的现实的前提开始。在马克思之前,这种方法一直被推崇,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被认为是正确的方法。但马克思指出,这种研究方法看似正确,但其实是错误的,是经不起严格验证的。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探索国家为例,他们要对一个国家进行探索时往往会从人口开始,因为他们认为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是最现实、最具体的,从人口开始便能抽象出国家,最后建构经济学体系。马克思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为的最具体最现实的人口其实并不是现实具体的,因为人口本身就得依存于其他的要素,没有其他要素的支撑,人口也就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人口的现实具体性是有前提的,是依赖于一些前提性概念或者说因素支撑的,如果缺乏对这些因素的分析,那么人口也就不再是具体的、现实的了,它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已。正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1]。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从人口开始,只能得出一些混沌不清的表象,如果沿用这种方法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那将陷入恶循环论证。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否认从具体到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所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那些生动的整体开始,一步一步分离出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并使这些抽象的一般关系上升为各种经济体系。
第二种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开创的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具体来说,这种方法就是从已经科学地抽象出来的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逐步呈现其抽象背后的具体,使具体再呈现出来。马克思指出,这种方法才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因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也就是说,具体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统一与自身的规定性综合表明,其不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果。仔细分析马克思的话不难发现,其研究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显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马克思又对其进行了质的区分。黑格尔从抽象出发,是为了说明抽象的自我运动过程,他从抽象引出的具体并不是真实的具体的自身形成过程,而是精神上的具体的再现。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具体不是真实的具体,而是从抽象、从绝对精神外化出来的,由此形成的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但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只是一种用思维来把握具体的过程,具体本身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是真实的,不是观念、精神的产物。对此,马克思举交换价值的例子进行说明:交换价值首先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现实的经济范畴存在,但作为一个具体、现实的范畴,对它的把握又是以它和现实的生产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交换价值作为范畴是直接等同于现实的生产行为的,世界就是从这种范畴运动中产生出来的。
尽管马克思不仅从理论层面讲明其研究方法的“抽象”范畴与黑格尔的“抽象”范畴有着质的区别,而且还举例论证二者具有质的不同。但马克思从抽象范畴开始,特别是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商品”开始,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经济运动规律,仍然引起了人们各种不理解,乃至质疑。这些不理解主要源于马克思从商品这种最常见的现象出发,引出了其中内含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反过来说,人们对马克思从商品进行分析产生各种不理解,也正源于人们不懂得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3]那么,商品的神秘性体现在哪里呢?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性就在于,商品把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变成物的性质,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成物的关系。也就是说,商品所呈现的只是其所表现的物的性质,把其真实的社会性质给遮蔽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明显超越了他在1844年所形成的“异化”认识。显然,马克思实现这个超越得益于他的研究方法。在1844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直接面向经济事实,从经济事实出发的,他甚至否定斯密、李嘉图“非人的”抽象方法,因为那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定的,并没有认识到其值得改造或者说利用的价值。但在创作《资本论》时,马克思不仅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还为其辩证法进行辩护,认为只要去除它的唯心主义外壳,把它颠倒过来,就可以利用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能够发现商品的神秘性质与他此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不无相关。但也正是缘于此,一些对他的研究方法理解不到位的人开始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责备,质疑他的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三、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质疑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经问世就震动了整个世界,无产阶级为之欢呼,而资产阶级则想方设法极力攻击。这不仅是因为《资本论》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而且还在于其宣布共产主义必然来临。资产阶级最开始的攻击表现为对它的沉默不理,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使《资本论》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随着《资本论》销售越来越火爆,“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4]。并且,《资本论》已经开始在欧洲多个国家受到热捧,从德文一版到德文二版,再到俄文版和法文版,《资本论》已经成为国际性读物。此外,《资本论》也日益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对此,恩格斯指出,《资本论》的理论、观点已经越来越得到世界各个国家无产阶级的认同,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同样也认同了《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无产阶级的存在状况,认为那就是自己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资本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起到唤醒无产阶级的作用,使无产阶级通过《资本论》的启蒙认识到自己与资本的对立,自己的异化存在和非人存在等状况。对此,资产阶级改变策略,他们开始找各种借口攻击《资本论》。在这些攻击中,尤其以质疑其研究方法最为突出,他们质疑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并认为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质疑有以下两个。
质疑一:法国评论家叶·瓦·德·罗别尔提在《实证哲学。评论》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指责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他“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5]。对于叶·瓦·德·罗别尔提的责备,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季别尔教授在《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中指出,马克思的方法是英国学派的演绎法,这种演绎法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也有其不足和缺陷,但这些优越性和缺陷并非马克思的方法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用这种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家都会存在的。尽管季别尔教授给出的回应并非十分准确,但也间接地反击了关于马克思研究方法是唯心性质的形而上学方法的质疑。
质疑二:德国评论家质疑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法,指责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黑格尔式的诡辩,是形而上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例如,伊·伊·考夫曼在1872年5月号的《欧洲通报》上专门就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发表意见,指责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实在论,但叙述方法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伊·伊·考夫曼指出:“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6]但他的文章却又自相矛盾,在引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不是唯心方法而是实在论并具有唯物主义基础后,又把马克思的方法描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所看重的是从现象中发现规律。不可否认,在这点上,伊·伊·考夫曼对马克思的认识是到位的,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现象的真正旨趣,即马克思研究的目的在于把藏匿在现象中的资本主义规律、本质和异化关系公诸于众,批判其剥削性质,从现象到规律的揭示,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运行规律直接呈现出来,以至表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但他说马克思只看重揭示规律的实现,而忽视从一种现有秩序的必然性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是否被人们所认识或所相信,显然又是错的。此外,伊·伊·考夫曼还指出,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运动不是思维的运动,相反,思维、意识是受社会运动的规律所支配的,精神的东西是第二位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史的发展过程。在此,伊·伊·考夫曼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是准确的,因为他抓住了唯物史观的本质,但他并没有在确认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后意识到人的意识、意志和意图等精神维度的重要性。
对于伊·伊·考夫曼的评论,马克思指出,伊·伊·考夫曼对他的研究方法的分析有准确的一面,但伊·伊·考夫曼把他的叙述方法指责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是不恰当的。并且,在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进行评论时,伊·伊·考夫曼自己也自相矛盾起来,一方面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提出指责,质疑其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辩证法,另一方面又对这种辩证法抱有好感,肯定式的去描述这种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及其手稿并不是思辨哲学式的哲学自言,而是要向天下昭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秘密,唤醒无产阶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目的除了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运动规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让无产阶级知道自己的处境,认清资本主义的本真面貌,进而完成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马克思是否真的形而上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什么会使人容易产生误解或者说不易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真实情形又是怎样的?是否属于德国的辩证法?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有什么区别?只有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指责实现有力的回应。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本真要义
事实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会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质疑并攻击,首要原因在于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产阶级辩护,而责备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们攻击《资本论》的原因并不在于其经济原理部分,而在于它所诉求的目的上,即揭穿资本主义的生产秘密,指出资本的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唤醒无产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攻击不在于经济学的解读上,而在于它所反映的政治属性上。因为马克思正是要借助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7]的揭示,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己要通过革命使自己从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一生使命就在于探索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穿资本主义现实的种种丑恶现象以实现对无产阶级的唤醒,使无产阶级真正意识到自己才是社会生产的真正主人,应当以自由人的身份平等地参与劳动。这也是马克思屡次被驱逐、被诽谤和被诅咒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这是《资本论》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意蕴的重要体现之一。
除了上述政治因素外,《资本论》的研究方法被质疑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原因,还在于其分析方法不容易理解。这是马克思自己所承认的。马克思在法文版序言和跋中就指出,《资本论》不容易读懂,特别是前面的开篇三章,因为他所运用的方法与其他人的不一样,“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8]。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资本论》前三章是最难理解的,这三章实际上包含了《资本论》的所有基本命题。在阿尔都塞看来,《资本论》前三章使马克思又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取代了的哲学框架中去。基于此,阿尔都塞提出在读《资本论》时应该抛弃开篇三章,直接进入第二部分[9]。这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分成意识形态时期和科学时期,并用科学时期来否定意识形态时期的做法所造成的错误认识。但《资本论》的展开是从抽象开始也是事实,即它是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进行演绎的。因此,前三章从抽象的范畴开始是进入整部作品的必然通道,但也正是这部分,使得《资本论》显然不是一部平庸的经济学著作。美国学者詹姆逊指出:“同时,对别的许多人来说,开篇三章实际上包含了《资本论》的所有基本命题,因而是走入整部作品的必然通道。”[10]如果抛弃《资本论》的开篇三章,那么《资本论》将失去最具有哲学味的部分,这部分也正是突出马克思《资本论》的真正价值所在的部分。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容易使人一开始就产生困难,这也是人们责备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的原因之一。
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质疑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还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常地和黑格尔“暧昧”起来。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美国学者莱文曾指出:“黑格尔从1837年开始驻留马克思心中,即他撰写论黑格尔的诗《黑格尔。讽刺短诗》这个日子,直到他1883年去世。”[11]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曾对黑格尔进行过三次系统的批判。第一次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都是建构在唯理论之上,属于唯心史观。第二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黑格尔的唯心异化劳动论为着力点系统地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及其三位一体的思辨哲学体系。第三次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部分。但在创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反常地提及黑格尔,甚至为黑格尔辩护,还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这种吊诡,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此时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一步指责他的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事实上,马克思自己曾说过,他在创作《资本论》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重新认识,甚至要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马克思指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12]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德国知识界都对黑格尔进行批判,把他当作死狗来对待,这是不对的。因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还存在着合理的内核,即辩证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虽然被黑格尔放在体系里,造成神秘化,但这并不影响黑格尔是第一个对辩证法进行全面阐释的哲学家。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似乎又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范畴演进的形式上,而且经济范畴本身也带有黑格尔色彩。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时期重新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不是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要在思维体系上重建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前面提到的对黑格尔的三次批判,可以说是他自己没有真正读懂黑格尔的哲学造成的。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曾表明自己当时是严重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他那时并没有形成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深刻认识,而黑格尔的法哲学本身却是基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反思而建构起来的。只有经过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时期重又提起黑格尔,并要求使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神秘体系中挣脱出来,把它颠倒过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想把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特质呈现出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
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尽管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与后者的研究方法截然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自己的辩证法并不像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是属于神秘的、思辨的、形而上的,具有神秘形式包围着的,他自己的辩证法是没有神秘形式的。马克思说:“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3]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表明,在思维过程方面,他与黑格尔也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绝对精神的思维观念是第一性的,世界万物都从它那里来,由它所外化出来。也就是说,思维过程就是观念的外化过程,从绝对观念出发,外化出一切规律和外部事物,最后又回归到观念本身。而在马克思那里,精神性的东西只是外物映射给人们的意识,人们按照这个意识来认识外物,也就是说,观点是第二性的,它由物质而来。这表明,尽管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从抽象开始的,但并不能因此指责它是形而上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具有唯物主义特质,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方法截然相反。
事实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出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自觉,即从这种分析方法出发,透过资本演绎的理解揭示其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4]这就是说,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的体现。
五、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质疑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方法的回应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本真要义表明其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内在特质。梳理研究学界忽视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质疑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回应,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如何科学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讨论。出于其研究方法晦涩、抽象的考虑,有学者建议在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时跳过集中论述研究方法的部分,如阿尔都塞建议初读《资本论》时跳过前三章。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5]事实上,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晦涩、抽象,但其科学特质并不难理解,马克思明确指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科学理解其研究方法的特质,便能把握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批判资本以及要求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使命,而这是实现科学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关键。也就是说,科学理解其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研读《资本论》其及手稿。
第二,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定位《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学科性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基于这种研究方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实现了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到经济运行规律的抽象概述,成功揭开商品的神秘面纱,揭穿物与物背后的社会关系,批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哲学自觉的展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哲学自觉表明,《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仅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著作,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观点。可见,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定位《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学科性质,把握《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特质。
第三,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拓展性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特质表明,它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的研究方法。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视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为《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域,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关于资本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基于哲学方法视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则为《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宽广的哲学研究域,对于深入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此外,作为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又为《资本论》及其手稿提供了跨学科的开阔研究空间,有助于深入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拓展性研究。
第四,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有助于保持对当前资本主义的警醒,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不可否认,当前资本主义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调整生产结构、劳资关系与分配关系等途径缓和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造成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赤裸裸的、血淋淋的剥削敌对关系。当前,资本主义正是以此制造资本主义不再需要批判的假象,并提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过时等错误论断。对此,为了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不难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从根上实现质的改变,依然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质言之,资本主义经济根基并没有改变,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此外,资本的贪婪和剥削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资本主义通过实行福利制度和保障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工人的劳动创造与获得报偿依然严重不匹配,工人阶级无时无刻不被资本控制和剥削。总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
六、结语
总的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随着近年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思想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的本真要义也得到了科学把握,表明它就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但在对它进行研究时,学界往往忽视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的质疑,没有研究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梳理研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质疑的回应,科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在当下深入推进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科学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有助于科学定位《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学科性质,有助于深入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拓展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