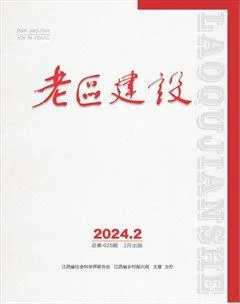空间价值凸显: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的新形态
宋文娅
摘 要: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文化惠民工程,已在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民文化知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建设初期对空间的忽视为农家书屋后续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学界和农家书屋的管理者都注意到了空间的价值,逐渐从在空间中提供服务转向利用空间为农民提供服务。农家书屋的选址、阅读场景营造、阅读空间功能创设等问题得到重视,通过收集和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家书屋转型升级的案例,分析探索空间在农家书屋后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空间;农家书屋;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544(2024)02-0075-08
一、引言
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文化惠民工程。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文明办等八部委联合出台了《“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要求在“十一五”期间建成20万个“农家书屋”,到2015年实现全国行政村的基本覆盖。截至2012年8月,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60万个,配送图书9亿余册,报刊5亿余份,电子音像制品1亿余张,影视放映设备和图书设施60余万套,提前三年完成了“农家书屋村村有”的建设目标。“农家书屋”工程是一项惠及民生的重大工程,取得的显著成效具体体现在:改善了城乡文化信息资源不平等的现状,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带去科技信息、实用养殖种植技术等,提升了农民的技能和文化水平,为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建设初期,重资源配置轻空间利用,在选址、空间布局等方面都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为农家书屋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要求“推进农家书屋延伸服务和提质增效”。2019年2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提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统领,树立问题导向、立足整改提升、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始,学界和农家书屋的管理者都注意到了场所的价值,从在空间中提供服务转向利用空间为农民提供服务。农家书屋的选址、阅读场景营造、阅读空间功能创设等问题得到重视,涌现出新疆伊犁“马背图书馆”、浙江安吉“余村印象青年图书馆”、福建泉州“永安村农家书屋”等许多由空间推动农村阅读服务的创新案例,为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二、农家书屋建设初期重资源配置轻空间利用带来的问题
从2005年农家书屋的试点启用到2012年提前3年实现农家书屋全覆盖,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视。这期间,国家及各级政府对农家书屋的政策支持以及设施设备、图书、资金等资源的投入都比较完善周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业务指导方面,连续发布《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编发《农家书屋管理员》指导用书,创办期刊《农家书屋》,开通中国农家书屋网;二是在经费投入方面,出台《农家书屋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财政按照每个农家书屋2万元的配置标准,给予中西部地区补助资金用于出版物购置等,给予东部地区奖励资金用于管理人员培训等;三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每个农家书屋配备的图书不少于1500册,品种不少于500种,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
然而建设初期,与空间相关的政策和研究却鲜少出现,已出台的建设标准和验收标准中,也没有对场所选址、阅读环境创设、阅读空间功能布局等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在空间建设方面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这种重资源配置轻空间利用的模式为农家书屋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
第一,场所选址不合理造成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据学者陈含章统计,建设初期农家书屋选址90%在村委会,5%在农村文化活动中心,3%在农户家,1%在学校,1%在其他。[1]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家书屋都设在村委会,而村委会是行政办公场所,与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有所区别,许多村委会设置了农家书屋但农民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村委会阅读。另外,选址没有考虑距离对农民参与阅读意愿的重要影响。一项农民参与农家书屋阅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到农家书屋的步行耗时每延长1分钟,农民到场阅读的参与意愿就降低0.007个单位。[2]这些都造成了书屋资源未被充分利用。
第二,空间定位守旧,与乡村发展不协调[3]。农家书屋多是以传统的学习空间模式建设的,布局多采用“书架+书+书桌椅”,空间功能较为单一。随着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的推进,一些农家书屋配置了网络和数字化设备,却也因为操作困难、使用不便等问题被闲置,严重影响了村民参与阅读的意愿。
三、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对农家书屋空间价值的关注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空间生产正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和农家书屋的管理者都注意到了空间的价值。
学术研究的视角从农家书屋资源配置、读者需求等逐渐拓展到对空间的关注,农家书屋的选址、阅读场景营造、阅读空间功能创设等问题得到关注。韩晗[4]以农村工业遗产改造更新为视角,指出目前农村工业遗产体量庞大,被开发利用程度较低,认为可以将农村工业遗产加以改造利用,使之成为兼具公益属性与商业属性的公共阅读空间。金晶[5]闡述了农村公共阅读空间在促进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分析当前农村公共阅读空间创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乡村社会生活在地性表达、乡村场域在地性营造、使用主体需求关怀的农村公共阅读空间设计原则与路径。陈赓、周若依[6]基于对中部3省27个行政村的田野调查,从空间生产、空间参与、空间获得三个维度指出农村公共阅读空间的弱化,并分析了原因,提出空间构建的优化建议。
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重视和支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及了空间的价值:“探索古村落古居民利用新途径”;支持有条件的乡村依托古遗址、历史建筑、古民居等历史文化资源,建设陈列展示场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深化农家书屋延伸服务的通知》中提出“优化网点布局”的要求,推动农家书屋向农民居住密集、活动集中的地方延伸,创新地列举了农家书屋延伸场所,包括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养老院、祠堂、书店、商店、电商服务点等。2019年,中宣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要求“调动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解决好农家书屋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新形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经历了由均等化阅读场所向综合化服务中心、个性化阅读空间的转变。各地从场所的延伸、释放空间自身的生产力、空间功能多元化创设等方面发力,利用空间价值对农家书屋建设、使用和服务开展创新,为农家书屋可持续性发展注入了活力。
(一)场所的延伸
在建设期,90%的农家书屋设在村委会,然而村委会所在地并不是村民集散地,农家书屋的选址如果在村民密集度程度低的位置就会造成使用、管理的不便,设施使用率较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解决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农家书屋创新网点布局,提升服务“可及性”。
在新疆、青海等边远牧区创立“马背书屋”。由于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新疆伊犁新源县坎苏镇阔克托别村农家书屋采取马背运输的办法,将党建、法律、养殖等内容的图书送到牧民手中,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2018年,青海省和祁连县图书馆共同建设的“马背流动图书馆”点燃了牧民对知识的渴望之光。在五年的时间里,“马背书屋”走出了原有的20万亩草场,将服务扩大到周边的村镇,成为当地牧民乡村振兴路上获取先进农牧业知识的“文化粮仓”。
广西、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创立海上“渔家书屋”,服务渔民的阅读需求。广西钦州钦南区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把农家书屋服务延伸到北部湾海域。按照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2018年底前,在北海、防城港、钦州建设完成10个以上北部湾海上渔家书屋。为了让公共文化设施惠及渔民,钦南区打造了2个码头文化站,将其作为固定渔家书屋,又借用6艘客运船只,作为流动的“北部湾海上渔家书屋”,在码头文化站和6艘客运船只上都挂牌“北部湾海上渔家书屋”。渔家书屋配置了300—1200册不等的书籍、音像制品以及书架等借阅设备,方便渔民的阅读与学习。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燕子山派出所联合区县图书馆,创新地把“渔家书屋”设在“海上警务室”内,以点单式的服务,将渔民所需的图书送上渔船、送入书屋,并定期更新轮换,为渔民提供免费借阅服务,帮助渔民实现了与图书的“零距离”。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用“行走的书箱”带活乡村阅读。该市构建“平度市图书馆—镇图书馆分馆—农家书屋”三级联动服务体系,在18个镇(街、开发区)图书馆分馆设立“行走的书箱”驿站,用于领读人培训和图书补给。为每个书箱都配备“领读人”,负责图书管理、交流指导、意见反馈等,精准化满足村民的阅读需求。为确保公共阅读全覆盖,采用特色化“行走”聚焦群众特殊性,如对种植养殖农户,将书箱配送到田间地头、养殖场点;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残障人士等,将书箱配送入户。截至2023年,“行走的书箱”已走进平度市220个村庄、30所乡村学校,累计图书借阅量超过50万册。有效激发了乡村阅读热情,打通了乡村阅读“最后一公里”。
(二)释放空间自身的生产力
空间生产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对在空间中的生产应该转向对空间生产的关注,空间的生产不再仅仅是社会空间的生产,更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文化设施中,场所建筑物的外观、材料和用途等,都能从各自的使用功能中抽象出来,传递文化价值。而在文旅融合的当下,文化场所与自然环境、空间功能的综合呈现,除了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还能服务于乡村旅游,为农民增收创造价值。
浙江安吉“余村印象”图书馆是由一处已经废弃的水泥厂房改造而成的,项目改造以“保用结合”为原则,最大限度地对原有场景进行了还原和重塑。外部空间融入乡土自然环境,田埂路和农作物种植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内部建筑物保留了原有的体量和开窗记忆,原有的两堵墙体改造成从底层延伸至顶层的观景书墙,与书架结合的楼梯是村民、新青年、游客聚集的复合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阅读、交流、聚會和演绎等活动。建筑物的开放空间打造成为图书馆的乡村展厅,新建的下沉式广场联结了原水泥厂建筑地下层,成为了一个融合休闲、聚会和表演于一体的多功能使用场所。现在,“余村印象”已经成为推动余村文化交流与社区凝聚、培养青年人才、激发创业创新的复合空间。像“余村印象”图书馆这样由农村工业遗产转向阅读空间带来的现实价值值得关注。据统计,我国目前可利用的农村工业遗产建筑有400万栋,通过空间改造和场景转型,以场所提供的优质乡村阅读空间来激发乡村阅读文化需求、助力生态乡村产业发展,体现了空间生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任何文化事项脱离了特定场域,文化意义就不能生成,文化内涵也无法表达。[7]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家书屋在升级更新中更加注重阅读场所的在地性表达。江苏扬州“渔家书房”位于邵伯湖畔的“国家级最美渔村”沿湖渔村,“渔家书房”在阅读场景的营造上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当地渔家特色。书房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所有的木料都涂有和渔船一样的桐油,室内灯饰仿造小船样式,除了书,还陈列了渔船、渔网以及当地渔民使用过的生活和劳动用品,在阅读环境中沉浸式地展现了渔家文化生活。浙江余杭小强公益书屋位于素有“中国毛竹第一村”美誉的百丈镇半山村,书屋隐于千亩竹林间,以半山“竹”为特色,毛竹将内部空间划分为多功能区域,天花板以毛竹吊顶,空间中的用具随处可见毛竹制品,在阅读空间中展示了当地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文旅融合背景下,农家书屋不仅可以服务于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提升游客的乡村旅游体验,为村民带来经济价值。黑龙江省同江市赫哲族民族特色浓郁,为了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该地将农家书屋资源整合转变成民宿图书角,游客入住民宿可以在图书角阅读,通过图书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民宿+书屋”这一模式丰富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带动了当地游客人数的增长。农家书屋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着力点。
(三)阅读空间功能多元化融合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前,农家书屋大多数按照传统的“学习空间”模式创设,空间功能单一,很难适应数字化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需求。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会出台《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探索以县域为整体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2019年,中宣部等十部委印发《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要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统领,将农家书屋纳入精神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体系中,探索农家书屋的空间功能创新与融合。福建省泉州市永安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为契机,改造农家书屋,提升村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以前,农家书屋只有借阅功能,农民参与意愿不高、书籍使用效率低。改造以后,该村开辟了“周末课堂”,招募社工、志愿者为当地儿童提供公益辅导,放映儿童电影,定期开展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成为乡村儿童的“社会学校”;永安村农家书屋还是当地“学习强国”线下体验中心,通过书籍、影像等形式推动农村党员群众思想理论学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山东省把农家书屋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乡村阅读与文明实践活动深度融合。探索“党建+阅读推广”模式,让农家书屋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理论宣讲平台;以场所创新农家书屋使用功能,“农家书屋+复兴少年宫”,既解决农村孩子“双减”政策下的课后托管问题,也让农家书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农家书屋+孔子学堂”,在书屋里,农民群众诵读国学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农家书屋+流动大集”,开在书屋里的图书集市创新的形式让农村儿童趣玩阅读、亲近阅读。
浙江省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作为全省农村地区的基层文化平台,是传承乡土记忆、构建农民群众精神家园的重要场所。嘉兴市“礼堂书屋”就是依托乡村文化礼堂,打破传统阅读空间,以“书屋+”融合模式构建新型乡村阅读空间的创新服务成果。[8]礼堂书屋是多功能复合空间,在空间布局上重视人与建筑的互动关系,充分考虑阅读服务需求对动线进行合理规划,做到空间分区即相对独立又互联互通。在空间打造上,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与村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邻里中心、乡村景区服务中心等相结合;在空间功能上,融入未成年人实践体验、居家养老服务、基层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廉政建设、法制宣传、乡贤文化等内容;礼堂书屋还注重对本土文化的展示,除了图书资源中提供与地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外,在空间布局、室内装饰、陈列等方面也都能体现本土文化特点、地方文化传承的元素。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初衷就是为了弥合城乡文化差距,促进城乡文化权利均等化。但是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数字阅读空间正在兴起,城乡数字信息素养能力的差距造成了新的信息鸿沟。为此,国家提出了开展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提高农家书屋数字化服务水平的要求,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空间建设路径。西藏墨脱的“莲花书屋”是西藏首个智慧农家书屋,书屋可实现扫码自助开门、自助借还等功能。读者只需要注册个人账号就能通过智能手机自助借还、查询及续借。书屋内除了纸质图书,还拥有海量的数字资源。此外,农家书屋将作为佛山市联合图书馆分馆与广东省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在“广东粤读通”上实现读者数据互通,共享佛山市图书馆的所有数字资源。湖北省共建成数字农家书屋2万多个,实现了数字农家书屋村级全覆盖,数字农家书屋“书香荆楚”App上提供了海量的图书资源、直播、讲座等,“扫码听书”、“码”上阅等活动多元化的阅读体验,让农民群众体验云端阅读的便利与丰富。
五、农家书屋新形态的空间价值启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家书屋发展新形态表明其空间价值日益凸显,农家书屋的发展路径从在空间中的生产转而投向激发空间自身生产力,在重视空间中的资源服务等基础上拓展到看到场所本身的价值。新形态下的农家书屋不再单纯提供图书,也可以是艺术空间、社交空间、教育空间等。实现空间价值,要以建设新型农村阅读空间为契机,促进农家书屋的提档升级。综合实践中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因地制宜的开展农家书屋建设,要使空间建设更新与农村农民实际需求相匹配,避免资源配置的错位、浪费。对于经济基础发达、城乡融合程度较高的乡村,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对农家书屋内部空间、环境创设提档升级,建设有品质、体现秀美乡村风貌特色的农村新型阅读空间,满足群众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对于欠发达的边远贫困乡村,要继续深化场所延伸,多形式开展阅读活动,将书屋开到村民身边,解决农村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二)多元化主体参与
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村民自治”的协同运作模式。多渠道吸收和整合资源,一是可以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化的社会机构开展农家书屋建设、改造、管理与服务;二是组织志愿者队伍,广泛吸引返乡青年、新乡贤、本乡在外企业家等社会群体参与农家书屋的空间营造,造福家乡,真正做到“农家书屋为农民”,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三)空间功能融合转型
促进农家书屋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推动复合型阅读空间的创新与整合。拓展“+书店”“+民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史陈列馆”等融合功能模式,让农家书屋参与到兴乡风、淳民风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参与到生态良好、产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各个领域中去。
推动农家书屋向数字农家书屋的转型,不仅仅在于硬件基础设施的提升,更在于通过空间交互设计实现线上线下阅读融合,虚拟现实空间的营造要切实服务于农民文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信息需要,增强数字阅读空间的智能性、交互性、专业性,让阅读空间更加人性化,提高农民数字信息素养。
六、结语
在新形势下,农家书屋不再是简单的图书供给,更在于通过对阅读环境、阅读场景的更新升级打造新型农村公共文化阅读空间,实现空间与人的互利共生,从而为建设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环境秀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添油加力。
参考文献:
[1]陈含章.农家书屋工程十五年:追溯、历程与建议[J].出版发行研究,2020,(11).
[2]唐丹丹,郑永君.农家书屋政策执行的“内卷化”困境——基于全国267个村庄4078户农民的分析[J].图书馆建设,2020,(1).
[3]颜彬.乡村振兴战略下农家书屋的媒介背景、现实困局与转型路径[J].图书馆,2021,(8).
[4]韩晗.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公共阅读空间的构建路径研究——以农村工业遗产改造更新为视角[J]. 出版广角,2021,(18).
[5]金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阅读空间设计在地性研究[J].中国出版,2022,(12).
[6]陈庚,周若依.农村公共阅读空间的弱化特征及优化策略——基于中部3省27个行政村的田野调查[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05-17.
[7]李军明,向轼.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J].广西民族研究,2018,(5).
[8]胡萍,许大文.礼堂书屋:乡村公共阅读服务高质量发展“嘉兴样本”[J].图书馆杂志,2022,(11).
[9]戚晓明,刘益馨.变迁与创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J].图书馆建设,2021,(4).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Space: A New Form of Rural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ng Wenya
Abstract: Rural Library Project is a top-down cultural welfare project that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promoting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enhancing the cultural knowledge level of farmers. However, the neglect of the spac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construction has brought some problems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librar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o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managers of rural libraries have noticed the value of space, shifting from providing services in libraries to utilizing rural library space to provide services to farmers. The selection of location, the creation of reading scenes, and the creation of reading space functions for rural libraries have received attention.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cas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librari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space i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libraries and the insights they bring.
Key words: Space; Rural libraries; Rural revitalization
責任编辑:邵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