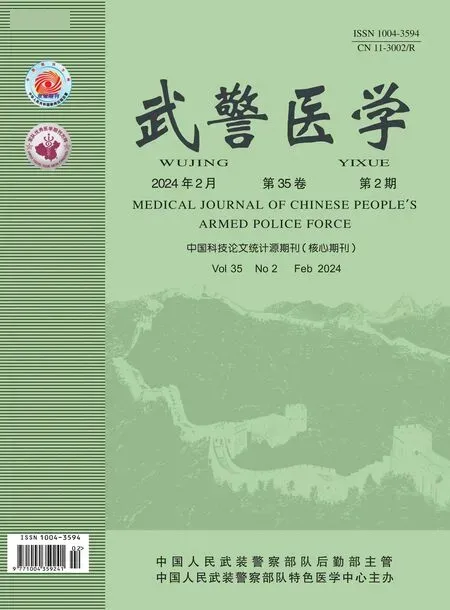表观遗传调控对幽门螺杆菌阳性胃癌致病作用的研究进展
高 春,江晶晶,陈玉春,于晓辉,郑晓凤,张久聪
表观遗传学是一种由染色质的结构变化介导的体细胞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模式或在不改变 DNA 序列的情况下发生的细胞表型。表观遗传修饰决定基因表达水平和时间,是响应内源性和外源性刺激的重要因素,涉及DNA修复、DNA复制和细胞分裂等[1]。表观遗传学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有效理论基础,如通过恢复特定甲基化基因的功能以防止癌症的发展[2]。近年来,致病菌抗生素耐药成为了临床难题,对与细菌抗微生物耐药性的遗传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学上。细菌基因组的表观遗传修饰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3]。本文就表观遗传学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阳性胃癌的影响及相互作用作一简要综述。
1 Hp致癌机制
研究表明,包括Hp在内的多数细菌为了更好地存活会对宿主进行表观遗传操作[4]。文献[5,6]报道,在致病性大肠杆菌感染的小鼠分离的尿路上皮干细胞系中,发现了染色质可及性的差异、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提示该菌充当重新编程尿路上皮表观遗传基因组的诱导剂,进而导致尿路上皮内在重塑对后继感染的先天反应。结核分枝杆菌细胞的生长需要伸长和分离之间的协调,分裂因子SepIVA甲基化位点的改变会影响宿主免疫应答[7]。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利用多种途径同样避免了调节宿主T细胞激活的清除[8]。Wnt、Hedgehog和Notch等信号通路常见于胚胎的发生和癌症的发展中。在胎儿的形成过程中,胚胎发生细胞必须通过改变结构以到达它们的正确位置,这些细胞会经历重要的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EMT表型包括迁移能力、侵袭性增强、抗凋亡性和E-chaterin的丢失[9]。一部分髓母细胞瘤患者携带SUFU基因突变,但该基因功能的缺失会通过上调Hedgehog和Wnt通路,进而导致细胞增殖失调[10]。了解癌症如何利用这些信号通路产生抗治疗耐药,这可以进一步探索以研发新的治疗方法。
Hp感染率已超过世界上50%的人口,感染可持续存在。85%感染者只患有轻微的胃炎,胃癌的发生率1%[11],文献[12]报道,Hp的致病机制可能取决于细菌遗传表达的毒力因子,这可能有利于或阻碍Hp逃避宿主免疫反应、建立定植及诱发疾病。而基因多样性本身就是细菌逃避免疫识别的关键环节。Hp可以依赖多种策略逃避宿主免疫,并产生慢性炎症和长期定植。Hp产生的脲酶可以提供NH3和CO2,这是中和胃的高酸性环境和允许细菌生存所必不可少的。NH3破坏了组织结构,CO2保护Hp免受吞噬细胞侵害,诱导血管生成和新血管形成,进而促进胃癌的发生[13]。
Cag致病性岛(cag-pathogenicity island,cagPAI)包含32个编码细菌IV型分泌系统(type IV secretion system,T4SS)和CagA蛋白的基因[14]。T4SS的作用是将CagA转移到胃上皮细胞并激活致癌信号通路。Bai等[15]发现,表达cagPAI的Hp菌株与胃癌发生密切相关。体外研究表明,CagA可诱导AGS细胞发生胃癌,这一结果已在Hp感染的慢性胃炎组织中得到证实[16]。空泡细胞毒素(vacuolating cytotoxin,VacA)是Hp的另一种高致病性的毒力基因,不同基因型具有不同程度的空泡活性。基因型s1/m1具有较高的空泡活性;s1/m2具有中等空泡活性,s2/m2无空泡活性[17]。携带s1或m1表达VacA的Hp菌株感染的患者发生胃癌的风险增加。Li等[18]提出,VacA抗体与胃癌发生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可能作为预测胃癌风险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综上所述,该菌以高突变率(每年每个10-6个位点)和混合感染时发生反复重组为主要特征[19]。这些特性赋予Hp高度的遗传多样性,以至于几乎每个感染者都携带一个独特的菌株。
2 Hp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
除了高突变率和重组外,Hp还进化出了相位变异,这为快速和可逆的基因表达开关机制提供了可能。相位变异一般是指编码表面表达毒力基因的基因启动子的串联发生突变[20]。这些基因的随机切换产生了表型多样化的亚群,有利于细菌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21]。而相位变化与编码表面结构的基因有关,包括Hp为主的细菌等具有与III型限制性修饰(R-M)系统相关的DNA甲基转移酶基因(modH基因),这些基因保护细菌宿主免受外来DNA的入侵,而不影响重组和因此产生的等位基因替代[22,23]。Hp含有许多II型和III型R-M系统的发现表明,这些甲基转移酶可能具有除防止外来DNA入侵以外的更多功能,这些功能之一被证明是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调节modH基因的表达而发挥作用。Hp modH基因有17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其中ModH3和ModH5常在临床分离的细菌中检测到[24]。在ModH5调控的基因中,有两个在人类胃中定植所必需的编码鞭毛(FlaA和Flik),还有一个逃避TLR5编码外膜蛋白HopG的基因也受ModH5的控制。此外,由HopG蛋白介导的细菌黏附是Hp定殖胃上皮所必需的[25,26]。该蛋白也被认为是预防Hp感染的潜在疫苗[27,28]。每个Hp菌株都携带一套不同的R-M系统,甲基组差异很大[29],在97%菌株中,只有少数靶标被甲基化[30]。
表观遗传学有助于胃癌进展,排除了与胃癌相关的表观遗传学标记物的检测后发现,尽管基因突变改变了DNA序列,但甲基化的存在可使DNA序列保持不变。这种差异为识别与胃癌相关的表观遗传标记提供了线索,对早期诊断和研发抗胃癌新疗法意义重大。Forkhead box(Fox)基因是调控代谢、细胞分化、细胞增殖和凋亡的转录调控因子。Fox基因FOXO3的启动子是Hp感染小鼠和Hp感染患者的人类胃黏膜样本中唯一显示甲基化增加的区域[31]。McLaughlin-Drubin等[32]发现,FOXD3一旦被激活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Hp感染小鼠胃癌细胞增殖,进而减缓肿瘤生长。其他Hp感染小鼠模型、人类胃癌活检和细胞研究数据也同样表明,FOXD3是一个被Hp甲基化的肿瘤抑制基因,并建立了FOXD3启动子被Hp甲基化作为早期表观遗传标记[33]。
文献[34]报道,一些Hp毒力因子可促进胃癌的发展,如CagPAI将CagA和细菌DNA转移到宿主细胞内。CagA是一种癌蛋白,可激活与癌变相关的多种因子并与之相互作用[35]。CagA的活性通过Hp诱导的炎症和与VacA的相互作用而增强[36]。此外,在合并EB病毒感染的胃上皮细胞中,CagA+Hp菌株受益于CagA和胃微生物群的致癌活性[37]。CagA是Hp启动癌变至关重要因素之一,但胃癌病理改变发生后,Hp就不再是必要因素,这就是发生癌变的逃逸模型,即一种感染因子在感染后不久就会诱发癌变,并且在它的存在不再是必要的时候就会直接诱发癌变。表达VacA和CagA的Hp菌株具有高毒力,可引起特别严重的胃部疾病,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因素是否与表观遗传学有关。
3 根除Hp影响表观遗传学和胃癌
VacA和CagA改变了胃上皮细胞的多条通路。慢性炎症和线粒体损伤,以及Hp感染相关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诱导胃黏膜的异常表观遗传改变,均是胃癌发生的主要原因[38-40]。事实上,在胃癌和Hp感染患者的癌前病变中发现的基因CDKN2A、CDH1和RUNX3使肿瘤抑癌基因失活。动物实验表明,抑制异常DNA甲基化通常可以防止胃癌的进展。遗传因素也有助于胃癌的发生。与胃癌相关的突变已在基因TP53、CDH1、ARIDIA和RHOA中被发现[41,42]。然而,突变占所有胃癌病例的15%。事实上,抑癌基因hMLH1和CDH1的失活通常是由于DNA甲基化异常而不是突变引起的。虽然早期胃癌切除术后根除Hp可防止胃癌的发展[43],但根除Hp并不能阻止异时性胃癌的发展[44]。根除Hp仅能在没有萎缩、肠化生(intestinal metaplasia,IM)和发育不良等癌前病变的患者中预防癌症的发展[45]。一旦IM存在,胃癌的风险会增加6倍[46]。考虑到癌症起源于具有分裂潜能的细胞,细菌重编程很可能发生在干细胞中。利用线粒体DNA(mtDNA)突变作为克隆扩增的标记,证实突变最初发生在单个干细胞中,该干细胞通过二元裂变扩散,直到发育出一批突变的上皮细胞,从而导致肿瘤的发展[47],同时也证明了mtDNA突变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48]。mtDNA突变经常发生在Hp阳性的胃癌患者中,关于Hp感染的慢性胃炎患者及Hp感染小鼠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49,50]。Hp通过诱导线粒体基因组突变,破坏氧化磷酸化代谢,增加ROS生成和mtDNA损伤。综上所述,Hp的致癌特性由多个因素引起,如其毒力因子的遗传毒性作用以及遗传和表观遗传因子。Hp还通过下调转录因子和DNA修复基因表达间接调节基因表达进而调控癌症的发生发展[51]。
Hp致癌特性机制不同,如细菌毒力因子的毒性作用、线粒体基因组突变、氧化磷酸化代谢改变,以及增加ROS的产生等[52],其中胃黏膜的异常表观遗传改变仍是最重要的致癌因素,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53]。Hp的抗生素耐药性正在逐年上升,如果能从表观遗传学方面研发相关药物,可以减少耐药发生,提高Hp根除率,是根除Hp以及治疗Hp阳性胃癌疾病患者的一种有前景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