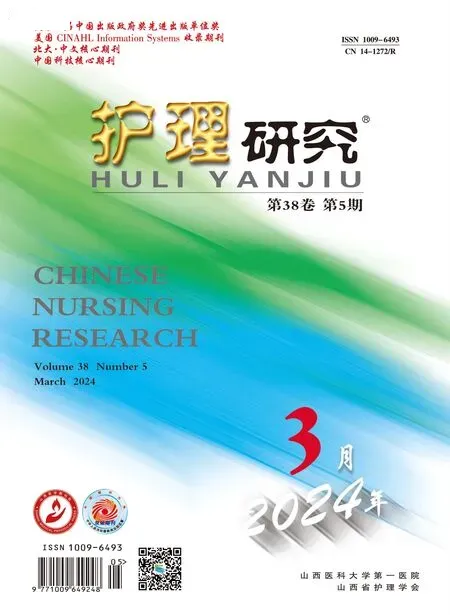基于安德森模型的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李 强,徐毓露,贺 鑫,谢纯琦,包 彬,曹梅娟
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浙江 31112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和癌症病人的死亡率逐年提升[1],专注于症状控制和舒适护理的安宁疗护对于在临终过程中保持病人的尊严和自主、满足病人多方位需求、改善病人生存质量、减轻病人医疗负担等方面至关重要。大力发展与推进安宁疗护工作不仅关乎医学的价值取向,也是建设“健康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自1988 年引入安宁疗护理念以来,在宏观层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努力推进安宁疗护,并在全国各地区积极启动安宁疗护试点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虽然我国政策支持与安宁疗护体系建设在不断完善,但安宁疗护服务利用率与接受意愿仍远低于发达国家[3]。个人的认知和意愿是影响安宁疗护发展的重要因素[4],系统了解影响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各类因素将有助于提高公众将优逝善终作为一种选择的认识。本文以安德森模型为指导,综述影响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相关因素,旨在为推动安宁疗护发展及提升老年人安宁疗护服务利用意愿提供参考。
1 安德森模型
美国学者罗纳德·安德森于1968 年创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5],简称为安德森模型,是分析医疗卫生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一类理论框架,也可用于界定和衡量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安德森认为,个人在决定是否进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时,受到前倾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3 个维度的影响,其中前倾因素包括人口学、社会结构和健康信念3 个变量,使能因素包括个人/家庭资源与社会资源,需求因素包括感知与评估健康状况。安德森模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历经5 次修正和完善,其解释力不断深化,能够更加全面和完善地分析卫生服务利用行为[6]。安德森模型已被应用于个体就医方式选择、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疾病筛查等方面的影响因素研究,且越来越多地被扩展应用到其他领域[7]。本研究尝试将临终阶段安宁疗护服务利用的选择视为个体基于自身需求的一种行为,将安德森模型作为分析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以期为安宁疗护服务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起到指导性作用。
2 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
2.1 前倾因素
2.1.1 年龄、性别
有研究表明,社会群体特征将不同程度对个体的安宁疗护意愿产生影响[4,8-12]。有关年龄、性别与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关系目前仍存在许多争议,不同学者间的社会调查结论不尽相同。孙佳乐等[8]研究显示,受传统的死亡观、伦理观和孝道观的影响,加之接触到的安宁疗护信息和资源相对较少,安宁疗护理念难以得到高龄老年人的普遍理解与接受,对安宁疗护的态度不够积极,易产生排斥心理。Tramontano 等[9]研究指出,年龄是影响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主要因素,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和与对未来期望的差异决定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但还有研究指出,年龄与安宁疗护接受意愿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分析为现有的调查研究受限于样本规模、人群结构与调查方式的影响较大,造成了不同学者调查结果的差异[4,9-11]。在性别方面,研究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不太可能接受安宁疗护服务[9,12];而国内的研究却发现,性别与安宁疗护接受意愿之间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4,8,11]。因此,关于性别、年龄与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2.1.2 种族、民族
不同学者关于民族方面的研究结果差别较大。孟春梅等[13]的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省汉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病人对安宁疗护的接受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病人。罗明琴等[14]的调查也发现,青海省少数民族的安宁疗护知识远低于汉族,整体的安宁疗护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国外一些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即非洲裔、亚裔和太平洋岛民)的安宁疗护接受意愿较低[9,12]。但国内有关于广州市[15]、天津市[16]和河南省[17]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区各民族民众间的安宁疗护接受意愿并无明显差异。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仅通过单一城市调研无法准确反映出整体的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但以上研究仍显示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在民族/种族间的差异会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低收入发展地区显著扩大,表明民族/种族这些看似不可改变因素也可通过更深层次的因素对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产生影响。
2.1.3 文化程度、健康素养
民众对安宁疗护的接受意愿除了受外部资源的可及性与可获得性的影响之外,缺乏生死教育及有限的认知也是影响民众意愿的重要因素[18]。Burge 等[19]通过研究教育状况对安宁疗护利用的影响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对安宁疗护的了解以及接受程度越高。Huang 等[20]研究证实,老年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的健康素养能力可较为准确地预测安宁疗护的意愿,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提高安宁疗护知识普及率,可有效提高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郑欣瑜等[11]的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广州市61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62.5% 的老年人从未听说过安宁疗护,余37.5%的老年人中比较了解或十分了解安宁疗护的比例也较低。此外,罗明琴等[14]发现,相对于接受安宁疗护理念的老年病人来说,处于矛盾态度的病人对安宁疗护的了解度不够,进一步研究发现,病人的安宁疗护知识主要来源于医护人员,医护人员缺乏安宁疗护相关知识和培训导致的相关宣传教育相对不足可能是影响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重要因素。
2.1.4 健康信念
我国多元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及传统伦理纲常对民众健康信念的铸造有着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着老年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及方式。研究发现,受到传统的死亡观、伦理观和孝道观的影响,高龄和农村的老年人对安宁疗护易产生排斥心理[8]。不同的文化、宗教精神内核对生死健康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精神属性会对老年人心理及健康信念产生重要影响,少部分老年人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审视死亡问题,决定了他们较低的安宁疗护接受度[21-22]。此外,相关研究指出,“死亡恐惧感”越高的老年人,选择逃避安宁疗护服务的概率就越大,而经历过生死教育的老年人将更倾向于选择安宁疗护[11,14]。我国的死亡教育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多数民众对死亡普遍存在恐惧心理,决定了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并接受安宁疗护的老年人较少。
2.2 使能因素
2.2.1 个人收入
国内外学者对老年人个人收入越多、消费水平越高,安宁疗护意愿就越强烈的结论做出了一致性评价。McCarthy 等[23]调查发现,与家庭收入较低的病人相比,家庭收入高的病人参与安宁疗护的意愿更高。同样地,Lackan 等[24]调查发现,与老年肿瘤病人群体的低收入水平相对应的是安宁疗护服务较低的接受意愿。此外,在另外两项来自中国的研究中,研究者分别对生活在低收入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老年人展开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地区老年人的安宁疗护接受意愿明显低于其他地区[8,25]。
2.2.2 家庭资源
在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中,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会受到家庭氛围、家庭类型与家庭支持的影响。张国增等[17]发现家庭关怀度高的老年人对安宁疗护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性。侯振华等[16]也发现,与家人关系越融洽的老年人其安宁疗护接受度越高。从这些研究可看出受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影响,受疾病困扰的老年人出于对家人的关爱更愿意尝试接受安宁疗护,以减轻家庭的照顾负担和经济负担。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受传统“重孝忌死”的孝道文化影响,安宁疗护的个人接受意愿和接受家人进行安宁疗护的意愿分别为70.2%和66.2%[4],即当安宁疗护的对象从自己变成他们的家人时,民众的接受意愿会相对降低,表明家庭支持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
2.2.3 社会资源
研究显示,与居住在城市的居民相比,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接纳安宁疗护服务的意愿较低[8-9,25]。农村地区居民不太愿意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原因可能与服务机构距离较远、获得服务的机会较少及信息资源匮乏有关[26-27]。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多数终末期老年病人希望在家中度过一生的最后阶段,开展居家安宁疗护十分必要[28]。针对北京[8]、深圳[4]等地的大样本调查显示,老年人对依托社区的居家安宁疗护模式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居家安宁疗护模式是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保护因素。
2.2.4 医疗保障
当考虑老年人对安宁疗护的接受意愿时,也必须考虑到安宁疗护的可及性。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超过12.4%的民众会认为费用高昂而放弃考虑安宁疗护,但实际上安宁疗护的感知费用和实际发生费用间通常有着相当程度的差距,感知费用对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负向影响可能大于实际费用对安宁疗护的负向影响[11]。推动安宁疗护与社会医疗保险相结合已被各个国家和地区视为促进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29-31],医疗保险兜底补差支付可大大降低民众安宁疗护服务支付负担,是提高老年人安疗护服务利用意愿的有效途径。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老年人的安宁疗护接受意愿不同,拥有城镇职工医保的老年人比城乡居民医保和自费老年人更易接受安宁疗护,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与隐藏于不同类型医疗保险后的社会人群结构和报销比例等客观因素相关[17]。但应当注意的是更高的医疗报销比例对老年人来说可能并不意味着更高的生存质量,李曼[25]通过对安宁疗护服务利用行为和医疗照料成本对终末期病人死亡痛苦影响的研究发现,拥有医疗保险且在临终前医疗花费越高的老年人在死亡前越痛苦。
2.3 需求因素
2.3.1 健康状况
与其他的卫生服务利用相同,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识与评价也会影响老年人对安宁疗护的接受意愿,大部分病人接受安宁疗护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轻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研究指出,疾病病程及合并慢性病数与老年病人对安宁疗护接受度呈正相关[13,16]。Lin等[32]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1.2%的参与者表示如果被诊断出患有非治愈性终末期疾病,他们更愿意选择专注于症状控制和舒适护理的安宁疗护。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加之共病状态下多症状的不断反复,使得老年人更易出现身体衰弱、功能退化及生活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这种持续的痛苦体验可能会促使他们选择了解并最终接受安宁疗护。
2.3.2 健康风险感知
健康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在面对威胁自身健康危险因素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提高个体的健康风险感知水平将促使其健康行为的改变[33]。病人在临终阶段通常会出于对未知事件及死亡的恐惧而非常迫切地想知道死亡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研究指出,疾病终末期病人对自身病情的准确了解将有助于其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临终护理计划,感知到自身疾病无法治愈的病人更有可能选择安宁疗护[34-35]。
3 医护行为提高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思考
3.1 前倾因素
目前我国民众对安宁疗护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社会认知度较低,这迫切需要医护人员提升安宁疗护主要受惠对象对安宁疗护内涵的理解。但安宁疗护的开展需在适时、适地、适人的原则下进行,在针对性别、年龄、民族等不可改变的行为影响因素时,尤其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及农村偏远地区要充分尊重个人价值观,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首先,可以考虑从提高老年病人的健康信念及健康素养的角度出发,逐步提升老年病人安宁疗护的接受意愿。其次,医护人员要加强自身的安宁疗护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医护人员对安宁疗护的理解决定了其处理死亡事件的能力,专业能力的储备半径决定着服务范围,懂得越多能够给予越多,才能更好地帮助病人。
3.2 使能因素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36]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推动安宁疗护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优质的安宁疗护资源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的大型医疗及康养机构,优质的安宁疗护资源难以下沉到基层卫生机构。因此,发挥安宁疗护技术指导中心医护专家对社区/乡镇安宁疗护机构的指导与支持作用对完成不同安宁疗护机构间同质化、标准化的服务至关重要,这也是提升偏远与资源匮乏地区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关键。且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安宁疗护事业的投入与支持力度,医护人员可主动参与远程医疗体系的开发拓展,通过积极探索“互联网+安宁疗护”等服务新业态,并定期开展相关知识培训以明确线上安宁疗护团队的人员构成和工作职责,提高线上安宁疗护团队的专业性及安宁疗护服务的便捷性,满足老年人个性化安宁疗护的服务需求。
3.3 需求因素
在面临医学伦理和法律风险等问题时,多数医护人员在与临终病人进行沟通时会选择刻意隐瞒病情,很少对病人的病情询问给予正面回应。盲目给予病人治疗信心导致病人丧失自身确切的健康评估信息是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阻碍因素,但优先征求家属意见后将疾病信息直接告知病人,往往也会引起短时间内病人心理上的强烈反应和变化,病人主观能动性的受损同样会造成较低的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现有的研究肯定了疾病告知在缓解病人负性情绪、增强医患配合度、提高家属满意度等方面的作用[37-39],恰当的病情告知方式成为满足病人健康评估需求并提升安宁疗护意愿的关键。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病情告知领域提出了多种模型[39],其中来自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尖峰模型(SPIKES Model)[37]和来自日本心理肿瘤医学会的分享模型(SHARE Model)[38]在国内应用较为广泛,可为医护人员病情告知提供清晰、实用的框架,可作为提升医护人员病情告知技巧及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的一般指南使用。
4 小结
为对治愈性治疗无反应的病人提供积极且全面的安宁疗护服务以提高其生存质量至关重要。当前国内的安宁疗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检索到有对安宁疗护服务接受意愿的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本文尝试将临终阶段安宁疗护服务利用的选择视为个体基于自身需求的一种行为,运用成熟且完善的安德森理论模型作为分析框架,较为科学、系统地总结了老年人安宁疗护服务利用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为探讨微观层面的医护行为对提升老年人安宁疗护接受意愿提供了依据。但针对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同一影响因素的不同研究结论,以及更深层次的老年人安宁疗护利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仍需通过大样本研究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