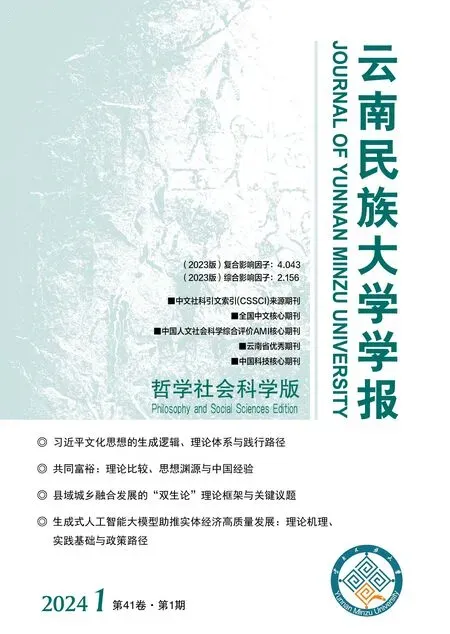云南移民与儒学发展
周大鸣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乔健先生指出:“世界上多民族的国家很多,但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民族聚集在一起,共同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最后终能共存共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却绝无仅有”(1)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对于中国的多民族共存共荣局面,他注意到中华文化本身的多元属性,同时也注意到各个民族之间基于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错综复杂关系。费孝通先生基于对中国历史与当下的整体性了解,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来高度概括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他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关注到中国社会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融合的民族特点,汉族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少数民族起到了充实作用,其中,民族走廊作为民族互动的通道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费孝通先生从“走廊”研究的视角,对“藏彝走廊”作了初步界定和设想,“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3)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藏彝走廊”很好地回答了区域内各民族互动情况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为了回应乔健先生中国何以“最后终能共存共荣以大团结为结局”的问题,本文试图借用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与区域板块的理论架构,从云南人的来源与多民族的形成入手,关注云南自古以来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的移民与云南儒学发展的关系,来探讨云南各民族如何融入中华民族的议题。
一、云南人的来源与多民族的形成
“云南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据林超民教授的考证,云南在历史上的较长时间,是用“西南夷”来指代的,而到了明代后期,“云南人”得以形成,进而取代了“西南夷”。这一转化背后,是“云南人”的地域视角代替了“西南夷”的边地视角,亦是“云南人”对中原的认同和华夏的认同。(4)林超民:《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载《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云南人”何以形成?我们先从区域的视角来看云南,云南分别地处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苗疆走廊、南疆区域范围内,同时,云南也是中国几大水系的发源地或流经地。云南是典型的“中间地带”(5)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16页。在此书中,“中间地带”指西南这一多民族区域内国家、地方、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有典型的文化混融性特点。而道路是云南混融性特征的基础架构,云南,得以在道路的互联互通中实现“中间地带”的位置。
(一)作为“中间地带”的云南
从藏彝走廊看云南。费孝通先生所关注的藏彝走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即“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6)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藏彝走廊所涉及的行政区域包括云南、西藏、四川,具体包括云南的迪庆、怒江和丽江,西藏的昌都,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和攀枝花。(7)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藏彝走廊区域内生活有藏族、彝族、怒族、傈僳族、纳西族等众多民族,并且每个民族内部的支系也纷繁复杂,民族文化十分丰富。藏彝走廊因独特的自然区位,民族文化也非常立体,造就了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藏彝走廊文化体系。透过藏彝走廊,我们得以理解多民族何以共生共存的逻辑。
从南岭走廊看云南。历史上,南岭走廊是沟通中原与华南的通道,该通道由成东西走向的五大主要山脉——“五岭”构成,在“五岭”之间自西向东分布开来的道路即我们所说的南岭走廊。(8)周大鸣,张超:《如何理解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2期。南岭走廊南北宽约330多公里,东西长约1000多公里。从具体的行政区域来讲,南岭走廊自西向东跨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及福建。广义的南岭走廊还是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分界线。(9)王元林:《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南岭走廊内,生活着汉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十几个民族。
从水系看云南。云南是珠江源头之一。珠江水系的源头有二,一是贵州的牂牁道部分,二是云南东部的宣威一带。一衣带水,把云南与沿海连接起来。除外,云南也是元江水系的源头。此外,云南还是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的流经区域,这些水系将云南整合进更为广阔的区域。
从苗疆走廊看云南。苗疆走廊起点为湖南常德,经贵州,至昆明,全程近三千米,途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云贵高原,是云贵高原上重要的交通线路。苗疆走廊线路在昆明与南方丝绸之路交汇,进而连接着更为遥远的南亚、东南亚地区,从这一层面来讲,苗疆走廊也是一条国际通道。
从南疆(越、老、缅、柬、泰)看云南。古代中原王朝曾在南疆(中南半岛)设置过交趾郡、永昌郡、安南都护府及其属下各郡、羁縻州、云南布政使司、三宣六慰、交趾布政使司、老挝布政使司、真腊布政使司、旧港宣慰司、安南都统使司等。云南著名的民谚“穷走夷方,急走厂”,即道出了云南与中南半岛的关系。
(二)云南人的来源与云南古代的交通
人是区域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在历史时期,云南有数次不同形式的移民。移民正是通过道路从中原、汉族区域及其非云南区域来到云南。“路”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是为人的连通而存在的,道路实则承载了人流、物流、信息流。云南有重要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上的人、物、信息的流动方式,是云南人形成的要素之一。
南方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到达缅甸、印度,乃至中亚与西亚。(10)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该道路“战国时已通,汉以来而盛”(1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4页。,方国瑜先生早至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该道路的重要性:“考两国(中印)两国间之交通,约有三途:一自葱岭,一自南海,又其一则自滇、蜀。……自滇以至中国,其道至便,故常通焉。因印、缅自滇与中国交通,影响于云南文化者至巨”(12)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载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茶马古道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线路之一,(13)中国对外交流线路主要为5条:南海道、西域道(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青藏高原“麝香丝绸”之路和滇、藏、川“茶马古道”。参见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5页。其两条主要的线路——滇藏线和川藏线,(14)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都连接着国内外交通。滇藏线以云南普洱为起点,经过云南的大理、丽江、中甸,而后进入西藏的察隅、拉萨、日喀则等地,进而直达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地区。川藏线以四川雅安为起点,经过四川的康定,进入西藏的昌都,最后到达尼泊尔、印度等地区。(15)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茶马古道除了滇藏线和川藏线,还有青藏线(甘青线),除外还有诸多有毛细血管之称的支线,共同形成跨越云、藏、川、青等诸省,连接南亚、东南亚,乃至西亚和中亚的庞大交通体系。
以上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是云南重要的两条道路,道路以连通性、开放性、互动性、聚合性的特性,整合了道路空间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道路整合了整个云南地域,亦使云南得以整合进超越云南的区域地域。移民得以沿着道路来到云南,带动云南儒学的整体发展。
二、元代云南移民与儒学发展
儒学,是边疆民族地区传播主流文化的重要阵地。全国意义的儒学发展在“百家争鸣”过程中,获得独树一帜的位置,体现出儒学的优越性。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对儒学的推崇,更是将儒学确立为思想文化的正统,亦形成一种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因素。就云南而言,因云南的边疆属性,云南儒学的发展滞后于全国整体性的儒学发展。据现有史料记载,云南最早的文庙始建于元代。(16)云南始建最早的文庙有三。云南府文庙建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大理府、临安府文庙均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云南省志》中指出:“云南书院始于明代,盛于清代,终于清代”(17)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六十《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木芹、木霁弘总结了元明清三代云南儒学的特点:元代生长,明代扎根,清代向纵深方向发展。尤其在清代,内地儒学已经走向没落,但云南儒学仍是方兴未艾。(18)木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周智生等学者也指出,元代以前,云南虽有儒家文化的传播,但影响有限,元以前,云南也并未纳入科举制度的范畴。但自元代,儒学在云南地方上层社会中得到了传播。明代,儒学不仅在云南的汉族地区,也在土司和少数民族地区相继传播。清代,云南儒学的普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周智生,周琼,李晓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6页。由此来看,云南儒学的整体性发展始自元代。
于云南的儒学发展而言,背后有一条重要的推动脉络,即持续不断来到云南的移民群体。云南儒学的整体性发展始自元代,云南的规模性移民也始自元代。云南移民的进程与云南儒学的发展呈现出共同发展、互为促进的关系。不管是元代入住云南的蒙古人,还是明代有计划有组织的官方移民军屯、民屯,抑或清代自愿自发入住云南的外地移民,他们的居住地多为交通沿线“坝子”地区,即云南府州县一级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正好这些地方也是国家统一设置儒学的地方。因儒学在府州县的统一设置,府州县自然成为该区域内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心。如在清代的永昌府,当地文化就呈现出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样态,“罗罗僰人罗武数种亦知伦理婚姻丧葬,与汉礼去不远,其子弟之俊秀者,皆知从儒,有古风焉”(20)刘毓珂:光绪《永昌府志》卷八《风俗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48页。。在此空间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纳,形成云南特有的多民族共同相处,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
元代进入云南地区的移民,以军事移民为主。在元世祖平定云南期间,带来了批量作战的北方士兵;云南平定后,又调入中亚一带及北方等地区的士兵。士兵成分较为复杂,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其中蒙古、色目、汉人成为元代迁居云南的三大移民主体。(21)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元代云南的外来移民具体数目没有详细记录。但在一些零星的记载中,可一窥元代移民的样态,(22)转引自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原见《元史》卷九十九《兵志二》、卷十三《世祖本纪十》。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原有外来戍守3000人的基础上,又调进2000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调集蒙古军及汉军4000人戍守云南。据《元史滇官之列传》的记载:“元代滇之统治阶级,以蒙古色目为要,然人数则不及汉族之多,盖一百人中,蒙古三十一员,色目三十二员,汉人及其他三十七员”(23)夏光南:《元史滇官之列传》,载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元代移民在云南几经繁衍,经历几代后,渐成土著。在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就有对移民入住促成人群多样性的描述:“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24)陈文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元世祖以“霸道”的武功形式征服云南,在云南设置行省之后,接下来需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如何治理云南的问题。元世祖采用了以“王道”的文教方式对云南进行思想文化的改造工程。元世祖主张用儒家的礼仪规范、风俗观念来管理云南,“建中和之政,凡以绳祖武,厚生民,无所不用其极”;“既有典常,被之服章”(25)程文海撰:《元世祖平云南碑》,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成为“以夏变夷”统治思想的一部分。元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被委以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积极贯彻“仁厚”之政,开始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26)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六),李春龙,王珏点校;李春龙审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页。。元代,在中庆路建庙学3所、鹤庆路1所、澄江路1所、建昌路1所、临安路3所、大理路1所,一共10所。(27)周大鸣,彭桥杨:《西南的儒化与教育发展——以文庙为线索》,载《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云南开科举始于元延祐元年(1314),(28)周智生,周琼,李晓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7页。在全国取仕300名的情况下,云南配额5名,居全国倒数第二,(29)海淞主编:《云南考试史 上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但于云南而言已经是质的飞跃。建水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其现存规模、建筑水平和保存完好程度都仅次于曲阜文庙和北京文庙。
立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碑刻《大理路兴举学校记》,呈现了大理当时的儒学发展情况,碑文中有记载:“盖质美而通学者也,其惟设立学校。……于是华夏之风□粲然可观矣。……夫子之道尊而明,而斯民果不难化也。他日人才辈出,彬彬然诚有齐鲁之风,则任斯事者宜无愧于文翁耳”(30)《大理路兴举学校记》,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0页。。碑文呈现元统一云南后大举推行儒学的情况,是云南早期儒学发展的写照。《大理路庙学残碑》也反映出元代大理儒学的发展情况:“学校,人才之所自出,学之源在教,苟设教……学以来,宜明勉励,未有盛于今日,……职教于学宫,而朝列大夫,大理……隆美其成功,千世英言以纪之……”(31)《大理路庙学残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1页。。该碑文呈现元代大理路儒学的发展情况,该时期,大理当地已经正视儒学教育的重要位置,并已经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儒学人才。并且,元代时期的大理,儒学已经从既有的“释儒”文化中脱离出来,得以成为与大理佛教并行的独立体系。
另外,在大理地区还有出自元代的《大理孔庙圣旨碑》,对大理此时期的儒学发展情况进行过详细的表达:“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本路总管府提举儒学肃政廉访司宣明教化,勉励学校,凡庙学公产,诸人毋得沮坏,据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圣旨施行”(32)《大理孔庙圣旨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5页。。此碑原在大理文庙内,该碑文考证立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理石碑文刊刻元世祖诏令,是元代儒学作为国家意志在地方得以施行的有力写照。元世祖平云南后,在云南大力施行儒学,开启了云南儒学的发展时期。这份诏令有律法的功效,明文规定了用于儒学开支的钱财的专用渠道,提供通畅的人才培养机制。
元世祖平云南,建立云南行省,调集大量移民戍守云南,在云南大力推行儒学,云南的儒学在元代呈现整体性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元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不稳固,对边远土司地区更难深入控制,设学效果有限。(33)古永继:《明清时期云南傣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及特点》,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元代的云南儒学在移民的推力下,虽然呈现整体性发展,但效果不甚明显,这也就为明清时期云南儒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明代云南移民与儒学发展
明代来到云南的移民群体,从规模和影响上都超过了元代。明代移民,使得云南汉族人口开始超过云南本地少数民族人口而成为主体民族。(34)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有研究统计,明代的云南人口,最多时期可达350万,(35)路遇,腾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这一人口规模中,移民就占了四分之一即100万左右。(36)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云南移民多为有计划有目的的军事移民,且在移民的规模、移民的数量、移民现象持续的时间上都远超前代。移民群体中主要有5种类别的移民:军士留戍、行政安置与自发流移、仕宦任职、谪迁流放、商人流寓。其中军事戍守的移民占了极大部分,整个明代入滇的军事移民共80余万人。(37)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明代,中央王朝有组织地将大批内地民众移往云南,尤其以明代洪武年间的政策性移民最盛。明洪武年间入滇的移民共30万。(38)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在历史上的云南,乃至今天的云南,常能听到“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的祖先溯源。如在云南白盐井的“四大家族”之一张氏家族,据现存祖茔(曰斗公墓)碑文记载:“始祖讳仁与义,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籍,爵封太和候世袭千户长,传至貤赠文林郎,寄迹羊城,讳栋已至数世矣”(39)来自田野资料。张国信,张公民:《泽厚堂家谱》,由张国信提供。。张氏家族原籍为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始祖公讳仁与义,于明代洪武年间随沐国公平滇。大姚县一带流传着“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为争米汤池,充军到云南”的移民溯源传说。据赵旭峰的研究,在云南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至少有100个宗姓的人认为自己是从南京应天府柳树湾而来。(40)赵旭峰:《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此次移民,使云南的民族成分和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开始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儒学得以扎根,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云南人通过祖先溯源的历史记忆,抑或族源建构的例子,呈现云南人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认同的积极性。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还有认为自己祖先来自汉族的情况,亦有少数民族用汉姓的情况。江应樑先生的研究中就有记载南甸土司“祖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人,汉姓龚,随师南征,剳驻南甸,赐姓刀”(41)江应樑:《近代傣族土司及其政治制度》,载江应樑:《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页。。关于少数民族姓汉姓,其中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赐姓。这一现象在《新纂云南通志》有记载:“又有受赐姓者,如丽江木氏、六宣慰司……赐姓刁、曩、罕”(42)龙云修,周钟岳,等撰:《新纂云南通志》(七),牛鸿斌等点校,李春龙审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615 页。。土司作为云南地方政权的代表,中央王朝赐姓给土司同时土司接受赐姓的现象,表明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的深度交往,及地方土司对主流文化的渐趋认同与效仿。(43)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载《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
明代,云南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朱元璋深知教化于民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迁徙到云南的移民后代的儒学教育议题。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王朝统治者对来滇的政策性移民以政策优待的形式继续跟进其儒学教育,正好促进移民群体的儒学发展及其对当地人的持续影响。明朝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儒学,开设圣谕坛,宣讲圣谕,广设学府,兴科举。至明末天启年间,云南共计有文庙63所、书院65所、社学163所;明代全国文进士25118名,云南260名,占1.07%。(44)古永继:《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明代移民批量进入云南,既有“汉少夷多”的人口格局彻底扭转,变成“汉多夷少”,并一直延续至今。明代云南的儒学发展,也与人口格局一道,取得了标志性的发展。这一期间,在云南的府州县一级,儒学得以全面覆盖。以楚雄府为例,楚雄府处于儒学发展的次核心区域,但在明代有了显著的发展。楚雄府于明永乐元年(1403)设立楚雄县儒学。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楚雄府设儒学教授一人,训导三人。楚雄县、广通县、定远县、大姚县各设儒学教谕一人”(4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540页。。这亦是明代时期,云南儒学继续下沉至更为地方的“县”一级的写照。作为地方的“县”,更多了国家儒学认定的行政官员。
四、清代云南移民与儒学发展
清代是云南历史上外来移民最多的朝代。(46)周智生,周琼,李晓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页。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云南人口从400万增至1000万,(47)[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页。这一时期,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外,较大部分来自人口的机械增长。与明代移民作为政策性产物不同,清代主要是经济互助性的产物。(48)李晓斌:《清代云南汉族移民迁徙模式的转变及其对云南开发进程与文化交流的影响》,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与明代、元代的军事类型的强制性移民相比,清代的云南移民更多是自发性移民,因此,在清代的移民中,多了许多“淘生活”的群体。关于清代时期有数据可查的移民来看,清顺治三年(1646),明之永历帝在云南的逃亡生活,开始有10万的随从者,到达缅甸仅剩下6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在途经云南的时候选择了定居。(49)周智生,周琼,李晓斌:《元明清云南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页。清代嘉庆到道光年间,进入云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群体至少130万人。(50)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来到云南的移民形成群聚效应,会馆是移民重要的交流空间,在清代云南共有移民会馆151个,包括江西会馆、四川会馆、湖广会馆、秦晋会馆、贵州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南会馆。(51)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云南地区会馆的地域构成,可以反映清代移民复杂的地域来源,不同地区移民来到云南,进一步促进“云南人”的多元性。
清代,中国内地的儒学已经走向式微,但与之不同的是,云南的儒学在“改土归流”背景下走向了兴盛。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云南儒学已经下沉到更为广阔的民众中间,成为“云南人”共享的文化给养。云南府州县一级普遍都建有文庙、书院、义学等完备的儒学体系,全省共有文庙91所,较明代新增18所;书院达到了247所,较明代新增182所;(52)廖国强:《清代云南儒学的兴盛与儒家文化圈的拓展》,载《思想战线》2019第2期。全国共产生文进士27038名,云南占2.52%。(53)古永继:《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清代的云南儒学,在科举人数、文庙、书院、义学层面均有质与量的提高,成为云南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云南儒学的发展,是以“改土归流”这一国家的整体性工程来进行推进的。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前后经历了长达540年左右的时间。(54)廖钰,李良品,祝国超:《改土归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云南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始自清雍正时期,在雍正帝的支持下,鄂尔泰在云南开展了大规模“改土归流”。以“改土归流”为节点,国家对云南的治理践行的是新的华夷观,通过“以汉化夷”的方式,传播儒家文化,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化水平。“改土归流”,使云南全方位归入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流。(55)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有研究就指出,“以汉化夷”的主阵地是“改土归流”地区,(56)廖国强:《“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归流地区两种文化治理方略及其关系》,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这些地方包括广南府、开化府、东川府、丽江府、昭通府、普洱府、昭通府、镇沅厅、缅宁厅,这些区域正是云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且在“改土归流”之前,儒学教化程度较低,甚至没有儒学进入的情况。因此,以“改土归流”为契机的儒学教育,对云南民族地区的儒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改土归流”地区施行的“以汉化夷”措施,其中在于提倡科举考试,将民族地区的教育统摄进儒学教育序列。具体来看,一是明文规定土司的子弟必须接受学校教育,他们只有走科举考试的序列,才可以世袭。二是在广大民众中普遍设立义学,以推动儒学教育最大范围的覆盖。义学的设置尤其向“改土归流”地区倾斜,清代时期在“改土归流”地区设置的义学共有202所,占全省827所义学的24.2%。(57)廖国强:《“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归流地区两种文化治理方略及其关系》,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改土归流”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义学的投入比重是最大的。以义学为重点,同时兼有文庙、书院的儒学教育体系在“改土归流”时期得以形成。
义学是清朝在西南地区施行的面向大众的教育形式,尤其在云南的义学发展,偏向于民族地区、偏远地区及府州县以下的地方社会,旨在实现面向大众的教育上升途径。义学开创了中国民众教育的早期形式,(58)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82页。且义学首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进而拓展到全国,(59)马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87页。从这一层面而言,云南义学具有向边疆民族地区民众普及儒学初等教育的初衷。(60)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陈宏谋是云南致力于义学发展的关键人物,在其义学的推行下,云南先后建义学近700所,每年的入学人数超2万人。(61)[美]罗威廉:《中华帝国在西南的教育:陈宏谋在云南(1733—1738)》,载陆韧译,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随着自发性移民的入住及云南的“改土归流”,云南儒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义学为标志,儒学得以下沉,持续深入到云南的诸多角落,为边疆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62)邹建达:《清前期云南儒学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备》,载《明清论丛》2018年第2期。在清代,国家统治者尤其兼顾了云南与内地的科举资源的差异性,通过发展义学,有效改变了儒学发展地域的不均衡现象。从制度层面对云南儒学发展给予保障,有效促进云南的儒学发展。在全国儒学走向衰落的清代,云南则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枝繁叶茂。
结 语
云南移民,是云南多元民族得以形成的力量,充实了既有少数民族,推动了云南儒学的推动。移民是理解历史人群交往、文化互动的重要因素。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的序言中就有指出:“移民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共同开始,移民的作用和影响无所不在”(6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就云南而言也是如此,云南民族关系的研究中,关注云南的外来移民与云南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云南民族关系的呈现重点。(64)周家瑜:《近十年云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综述》,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12期。笔者已在《西南的儒化与教育发展》中指出:“移民也是儒学在西南传播的一种路径,人的迁徙不只是人的流动,移民者所携带的文化也会进入移民地,这些移民作为传播儒学的先锋,在王朝国家推行儒学教化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其中,作为实践者与传播者,促进着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65)周大鸣,彭桥杨:《西南的儒化与教育发展——以文庙为线索》,载《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许倬云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统一的原因,是四套制度体系,及儒家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整合的力量仔细分析起来,由思想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这4个体系网络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力量。中国自秦汉统一后,普世性的儒道意识形态,以文官系统与皇权相辅的帝国体制,以小农精耕与市场交换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以编户齐民为基础,有阶级却可相对流动的动态社会,家族与社区相叠的社会组织等,即思想、政治、经济、社会4项体系重叠相合,互为影响,构成一个紧密而稳定的多体系的文化复合体。在现代之前,在没有外来体系干预之时,这4个体系中即使有部分的衰落和败坏,因为4个体系的互补作用,整个复合体能够自行愈合,一时不致崩溃。假如全体崩溃了,由于中国区域内自然条件不会变,复合体系中的经济体系会首先复原,而逐步导致其他3个体系的恢复。
儒学教化以一种持续的、温和的姿态,对云南区域的思想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有“中原”与“西南夷”二元对立的话语叙述,尤其一些文献,会用豺狼、盗贼、狼虎来指代边地的少数民族,即以中原为“我者”及与西南夷为“他者”的叙述。而云南儒学的发展正好消弭了这二者的对立与分立。作为边疆的云南,云南移民与儒学的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经验。作为边疆范畴的云南,至今的边境稳定、民族团结议题亦是云南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回到历史现场,云南积累了诸多边疆民族团结的历史经验,文化治边即重要途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措施孕育了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潜在基础”(66)郭纹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理论根基与现实路径》,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儒学教化思想可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沿着云南移民与儒学发展这一脉络,我们能够深化云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及边疆治理经验的认识。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陶红、张恩迅、肖明远的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