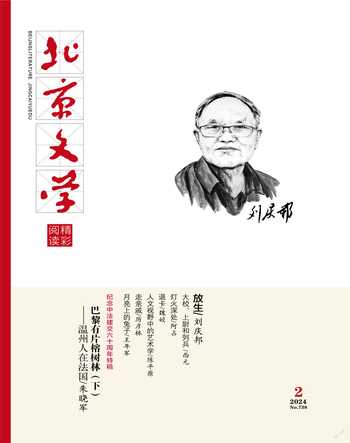月亮上的兔子(组诗)
王年军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丢失的东西
把泼出去的水收集起来,装进竹篮里
是任何人也无法做到的事
普通人很少意识到竹篮打水的失败
既然在语言中,一只篮子,必定是空的
不像铜盆、木盆,或荷叶折成的杯子
可以稳稳当当地装住水
想想第一个用竹篮的人,一定很惊奇
是不是总有一些事物,是另一些事物的缝隙?
时间被分成篦子
从黑色的头发上梳过
月亮上的兔子
居住在自己的天上国家
分布在不同的省份
爱德华多·卡茨的荧光兔
也在上面繁衍生长
和人工创造的草皮一起,绿色的月亮
把脚抬到地球之夜的红房顶
嫦娥年纪大了,她在环形山梦工厂拍完纪录片
坐在月球的电影院,和她的姐妹一起
向观众分享自己在集中营中被囚禁的经歷
月球上的兔子,联合卡罗尔镜子中的兔子
其他卫星和行星上的兔子
藏在桂花树的冷香中——
花瓣冷藏了几个世纪后往下落
被霜冻过的桂花,落在新鲜的月壤上
嫦娥老了,梦中,一只小狗扯着她的咖啡色大衣
但她没有注意,和她遥远的丈夫
隔着月球极地列车
在VR眼镜中接吻
月球看起来很小,就像她握在手中的一块石头
她把它磨了又磨,终于变成一颗圆圆的珠宝
通过自己在月宫中竖起的铜镜
天文学家李白发现自己投到月球的影子
他喝下一杯巴旦木做的酒,写下《玉阶怨》
当我正谈到这一点时,她说“那不是我!”
她的牙齿脱落了,扔在月球舞厅的中央
当她走过月球的红绿灯时,我跟她聊了几句
最初不敢辨认,就像一个印第安人
出现在阿尔卡特兹岛的照片上
她回忆起年轻的时候,世界大战刚刚爆发
她曾经在食不果腹中度过前三年,没有乳汁
只能讲自己家乡的方言,这种语言是不能使
人长大的
直到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嫦娥才发现自己喜
欢拍照
留下了无数的照片,被誉为东方诗国的梦露
作家们写了很多关于她的文字
她变得不再认识自己
月球上的兔子呈几何级数繁衍
占领了每一座环形山。
她死后
她的牙齿与土壤中的元素化合
成了今天的嫦娥石
松树
寒冷的冬天
像一团火,褐色的燃素
在水上茅屋的后方
漂浮的木棹岛屿,牵引着同心圆外围的弦波
船在更前线的浅滩
微张着
消除绝对贫困后的乌篷
一个渔夫
提着鳜鱼探出头,准备晚餐
那些像门一样的松树,对着风关闭着
树汁所分泌的琥珀
把一只蚊蚋滴入时间
在敌占区耗尽
潜泳的最后一缕氧气
窗户里的对弈者
坐在松木桌前
趁炉火更旺,水晶帘随时就要拉下
瀑布挂于欸乃声变白处
一只受惊的麋鹿,游进田野深处的忘川
枯萎的芭蕉,放弃隐喻的动机
如“除四害”期间的乌鸦
垂下无处飘落的羽翼
战败士兵的盾
抵抗着天黑之后的
风
题山水画
古怪的艺术家
把山中的彩霞绘制成一个天堂
没有用画笔,而只是用手完成了作品
纤细的鹈鹕羽毛,纯净的地平线
呈现出自然的样貌
没有表面的
装饰性风格
可以想象,在迷人的春天场景中
一个骑着毛驴的男人
正走上乡村的小桥
他的仆人跟在后面,赤脚、戴着草斗篷
文徵明也曾看到,并把它画到
扇面上
在漫长的冬夜,一个农民的梦想是狭隘的
一次又一次地掉进沟里
月亮照着也无用
星星亮着也无用
但这一切就像猜谜
自然只暴露其一部分样貌
就像画家刻意掩盖的
通过云与水之间的大面积空白
和树林遮盖下的路
让观察者无法辨清其中的行旅
侧后方并无北极星
毫无疑问,人
只是这伟大情感的一部分
作为音乐
他所感知到的共振
只有放到山里才能理解
穿过稻草上的积雪和弯曲的白杨树
钟声荡开紫色的雾霭
马铃薯被田鼠啃光了,哎!
一阵风像琴弦一样拉动
在芭蕉叶后面拨弄着什么
庭院
当雨水穿过小花园时
我的画增加了一些东西
离海如此之近,就像鲸鱼的种子
每一块土地都能把它孵出
不像秦岭驯化的山雨
需要几个世代的梦
才能开始旅行
在泥土里种上花、几头野蒜
蜿蜒的西葫芦藤蔓挂在棚架上
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
杂草渐渐被蔽除
外面是建筑工人,戴着安全帽
爬在被尼龙纱网遮住的钢架上
铅锤敲击,新年的早上也没有停
葵花开花的时候,也没有停
在山顶看海
Ⅰ
一眼就来到了海边
老轿车在路口别过身
在新村的萧萧马鸣中
留下了时代错误。
曾经有多少人,想要敲击这隔世石
又被以太一样涌动的海水所困
被画满塞壬的山海经屏风所困
实际上,头顶是海
左边,右边和身前,也是海
隔着十几里山路
看到中心城区的几栋高楼
像农耕时代的磨刀石
排闼于蒙蒙细雨之中
在这样的情境下
诗人是否应该克制抒情?
抒情是不好的
在某些时候,就像叙事是不好的
都无法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
除非有个恰当的时刻,你感到
语言宛如被潮汐磨圆的石头
沿着水位线不断下沉
降到比丹田更低的深处
这时你可以說:“啊,云真美!”
一条蛇躺在沙漠的肚子上
同样不需要解释
只需给语言破戒,说句“真美”
胜过任何动词或意象。
云中的金黄,是否就是这抒情诗的颜色?
Ⅱ
不下雨的话,我肯定会走回去
沿路细察,每一棵树
如何内置了微型的海
——并非我对海有什么执念
以至于它在装下现实的事物之后
还得装下我的意志
只是如此近处的海
改变了人所见过的一切。就像这槭树
如何因从西边来的水汽、低矮的平流云
和夜空石子一样多的星星
而具有不同的叶缘?
作为一个并非深谙于植被的人
只知道它的形成,就像这独一无二的地貌
已经无法被复读
就这样来到海边
并非在锯齿状的海岸线上
而是在前前后后的海与海之间
小小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株草的海
从珍珠梅、野牡丹、木本曼陀罗
到菖蒲、韭菜花、蔷薇、千屈菜
大大小小的芦荟、仙人掌、苔藓的海
记忆的地层,要被这些植被改变吗?
可能最终就成了巴洛克
当然,还有乌鸦
偶尔有松鼠、刺猬
空气就像被鲸鱼喷过水,湿漉漉的
把山的一半
掩映在白雾中
在山顶看海
实际上
就像在海中看海
……我的身体
变成一座有着沉重石头的岛屿
于幻想中拜访庞德墓
你的骨灰不会动,即使在高地上,
无论风怎样吹,墓碑也不会摇晃。
梦中我来过多次,拜访朋友
没有想到它就在隔壁,堆满白垩沙子
无论风如何肆虐,你的骨灰都不会飞扬
堆积于野生荆棘和沉默的树木。
你的墓穴无论如何也不会摇晃
在雨水浸泡的潮湿的海港和小巷
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走过月桂树,唱着歌
但你的墓前没有鲜花也没有风
“哦,不要说诗的坏话
因为这是一桩神圣的事。”
无数的微小生物,就像苏美尔字母
以细菌的速度在你的棺椁外生长
亚洲博物馆的明朝仕女图
月亮是圆的,如一口倒扣在天上的寓言之井
两位贵族女士在花园的石桌旁下棋
她们的饰品、发型、长袍和披肩
都是用精致的笔触细致描绘的
源自古典的风格——被东方化的神灵所泄露
周围的竹子、芭蕉树和岩石
暗示了私人花园的优雅环境和季节
当我们想要走进去,却被一块无形的玻璃所
拦住
松鼠们爬在葡萄藤上
藤蔓上的葡萄呈大簇生长
众所周知,它巨大的繁殖能力
与葡萄的形象一起,代表了无数子孙后代的
愿望
这幅图,陈列在旧金山市政厅旁的亚洲博物馆
外面,有西蒙·玻利瓦尔的青铜像——骑着战马
纵身越过电缆车和施工中的推土机
雕像的底座写着“1783-1830”
提示着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从虎门上方升起
喂着蓝色鸽子的人,拍照的游客,被充实的光
线照着的绿草地
这些神秘的事物在任何地方都一样
把我们行将过期的生命聚拢到一处
穿过大理石建造的长廊,在一个展厅中
这些碎片让我恍若置身神话
灯光暗下去之前,仕女身上的光泽
一直停留在黄昏。可以设想,无法被黑暗扑灭
仆人在弈棋结束前正往炉子中添火。
茂密叶子中的松鼠,多毛而好动,眼睛闪着狡
黠的光
在黑色的藤蔓上留下窸窣的声响
正没日没夜地朝画外的主人发出提醒
——能看到地上被它蹭掉的旧树皮
危险地闪烁于缝隙间落下的阳光。
地中海气候催熟的紫葡萄,曾经让印第安人
烂醉如泥
被夏多布里昂写进小说,我也曾在年轻的时
候读过
如同亲尝。那纸上总是被空白填充的地方
如今具有了意义,仿佛夏多布里昂的葡萄
也是16世纪明朝花园中的同一种。
醉醺醺的松鼠,在主人仍在弈棋的花园蹿跳
我在加州公园里见到的松鼠
也有可能被以类似的风格画在宣纸上
它们匍匐着穿过水泥路,以为谁也没有看见
硕大的棕色尾巴像扫帚一样扑打着
为亚美利加、外太空、十万光年外空间的存在
我们在尺幅之间留下了太多不能说明的事物。
还有伯克利植物园中的芭蕉与湘妃竹
被工匠们散乱地并置在龙舌兰和美洲蕨旁边
这样,它们跨过陆地和想象
铺陈在一个达尔文式的多物种之匣
死亡装扮成寺庙中的和尚
死亡装扮成寺庙中的和尚
尽管他也许什么也不信
对于一个沾湿鞋子的少女
死亡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陆地上是鸟群的巢
在裸露的树枝上等待树叶
死亡装扮成寺庙中出走的和尚
在越来越窄小的驿路边等待旅客
在天塌下来的地方
有一个和尚从山上走来
托着一朵云,近看是一个少女
她的鞋子上滴着水
死亡这个大男子把她在岸上放下
尽管在黄昏前不会再有人经过
树叶在裸露的树枝上尚未完全展开
死亡的重量像羽毛一样轻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