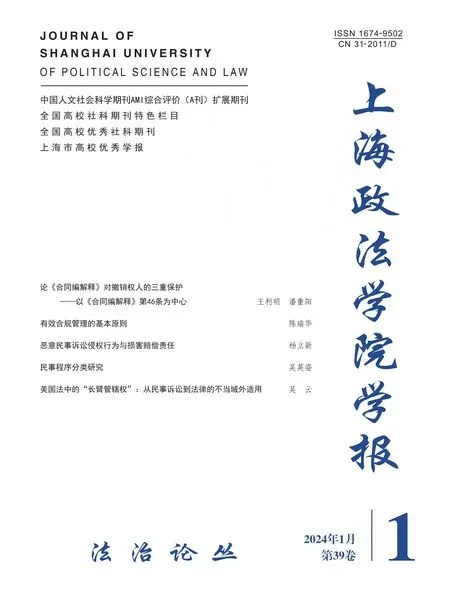论通用人工智能治理中管制与反垄断的协同
许丽
一、问题的提出
通用人工智能具有一般人类智慧,是可以执行人类能够执行的任何智力任务的机器智能。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①本文所称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指利用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提供通用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和个人。可通过向商家用户提供“通用大模型”,赋能各行各业。其强大功能改变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前景的认知,但也引发了学界对通用人工智能引致数据安全、算法歧视、网络犯罪、知识产权、技术垄断等风险的隐忧。在此背景下,探讨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治理理论与监管模式具有现实紧迫性。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当下在通用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公用事业的背景下,不仅需要探讨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反垄断执法克服市场失灵,还需加强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行业管制对结构性失灵进行矫正与治理。仅仅依靠事后的反垄断执法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必须通过事前的常态化行业管制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有效弥补。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反垄断执法只是事后“非常手段”,更需要完善的是常态化事前、事中行业管制机制,两者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反垄断执法作为事后手段,并不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自主决策与行为进行干涉,而只是在出现违法情形后才对其追究责任,功能在于制裁和制止违法行为。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的常态化行业管制在手段和措施上相对温和,但属于一种持续的管制。事前、事中行业管制是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基础大模型训练阶段、投入商业应用之前便对其进行及时干预或设定准入条件,预防数据泄露与不当使用、算法歧视等风险发生,弥补反垄断执法的滞后性。同时,它也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干预,可有效防止垄断及资本无序扩张。为加强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垄断行业管制,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7 部门于2023 年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这意味着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我国从专用人工智能时代对具体平台应用的监管向技术服务提供者监管的转变。然而,学界关于管制的研究集中于如何放松管制、引入竞争,将反垄断法适用于管制行业,而对于反垄断法与管制法的互补与融合很少被论及。面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如何平衡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成为当下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 条第3 款规定的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不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宣示性条款,除从反垄断执法层面的制度进行完善,明确其适用规则,并出台具体的反垄断适用指南有效指导实践,还需要实现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管制的衔接。为有效应对我国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的垄断问题,仅依靠反垄断执法本身显然不足,需统筹协调好不正当竞争、用户权益保护、行业秩序监管等多种管制工具并发挥作用,构筑权力配置格局,实现反垄断机构和行业管制机构之间相互协调互助,同时建立协商机制,实现共定政策、信息共享以及合作执法。
二、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管制的合理性考量
我国《反垄断法》第8 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其经营行为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这强调了在石油、电力、铁路、通信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并非以管制代替竞争,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反而应理解为管制与反垄断共同协同促进竞争,确保竞争政策更大程度地适用于管制行业。通常认为,对于存在资源稀缺性、规模经济效益而由一个或少数企业经营的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重要公用事业服务行业,因受到政府更多产业管制而称之为管制行业。①参见孟雁北:《论我国反垄断法在管制行业实施的特征》,《天津法学》2019 年第3 期。从管制行业的构成要件看,通用人工智能行业与传统管制行业具有类同性。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具有公共事业属性、自然垄断属性,存在结构性失灵并具有垄断高风险性,从而适用政府管制存在必要性。
(一)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具有公用事业属性
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不仅自己利用所研发大模型直接面向海量终端用户提供具体场景应用服务,还向各个垂直细分领域的下游企业用户提供通用大模型服务。当面向企业用户时,通用人工智能预训练大模型具有基础设施地位,与之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众多,预训练大模型是通用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设施层,处于上游地位。①Alex Engler,“Early Thoughts on Regulating Generative AI Like ChatGPT”,Brookings,Feb.21,2023,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earlythoughts-on-regulating-generative-ai-like-chatgpt/,accessed by Sep.13,2023.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向下游企业提供预训练大模型即“基础模型”,下游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开发出适用于不同场景的专业模型。预训练大模型可以深度集成于各项应用程序,在体育比分、股票价格、知识问答、网络购物、休闲玩乐、旅行出游等场景中提供高效且便捷的服务。②Stephen Wolfram,“ ChatGPT Gets Its ‘Wolfram Superpowers’!”,Stephen Wolfram Writings,March 23,2023,https://writings.stephenwolfram.com/2023/03/chatgpt-gets-its-wolfram-superpowers/,accessed by Sep.13,2023.由此,预训练大模型不仅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基建”和强化已有人工智能应用的“加速器”,还可充当催化新业态的“孵化器”。③参见张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现代法学》2023 年第3 期。预训练大模型与传统适用行业管制的公用事业具有类同性,通用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不仅本身具有通用性,且基于对下游产业的控制力而具有公共性。实际上,当市场上绝大多数下游产业依托预训练大模型提供商品或服务时,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事实上承担了部分公共职能,比如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相关方的权益等。因此,通用人工智能与公用事业④现代意义上的公用事业多属于国家基础建设行业,紧密联系并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基础性和公共性、一定的私人性、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特征。具有类同性。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甚至可以通过大模型算法设定下游产业运作规则,以制定规则为名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基于通用大模型时代政府的事后规制收效甚微,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逐渐承担了部分行政机关公共管理的职能。⑤Hannah Bloch-Wehba,“Global Platform Governance: Private Power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te”,72 SMU L.Rev.27 (2019).当私有资产在利用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公益效果,并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时,该私有资产就被赋予了公益的性质,并需要受到公众的监管。
在传统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两级下的稳定结构中,逐步增加了具有垄断技术能力的科技企业这一新的权力集合,这种数字权力既不同于国家公权力机关,也不同于私人的权利自治⑥Divya Siddarth,“Reimagining Democracy’s Defense”,34 J.Democr.173 (2023).,可表达为“私权力”。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围绕使用其通用大模型的下游企业构建一套私有的治理规范,即便为私权主体,它既能制定、执行规则,也能处理纠纷、处罚违规者,同时能有效弥补公共监管部门的监管乏力与监管漏洞,对公共监管部门难以全面、深入地监管造成的监管乏力与监管漏洞施以有力补充。此时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扮演了共同使用同一大模型这一“商业生态系统”公共场域内组织治理者的角色,作为“类政府”组织,具有公共物品属性⑦Joseph Farrell &Michael L.Katz,“Innovation,Rent Extraction,and Integration in Systems Markets”,48 J.Ind.Econ.413 (2000).,须为维护好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公共市场内各类市场主体的良好交易秩序而实施监管。例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 条规定,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个人信息处理主体,应对平台内严重违法违规的经营商家停止为其提供服务,并对其相关义务、法律责任和罚责作出明确规定。当数字平台企业为很大一部分公众提供服务的方式受到公众关注,并关系到公众的福利和利益时,该企业的服务便具有公共事业或者公共承运人的地位。基于这种地位,数字平台企业通过用户合约条款与技术控制,拥有控制接入的权利、数据使用的特权和控制数据流动的能力。与平台通过提供通用介质、应用程序搭载于平台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相同的是,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基于为下游企业提供通用大模型这一特权,在“国家-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下游企业”之间形成“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三元构架。①参见马平川:《平台反垄断的监管变革及其应对》,《法学评论》2022 年第4 期。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所扮演的角色是辅助执法机构保护公共利益,以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取代部分公共规制,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具有自然垄断属性
自然垄断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即具有成本劣加性、生产与投资显著的沉没性、产品或服务垄断经营性等特征。其中,成本劣加性是定义自然垄断的关键特征,随着产品或服务数量的增加,其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将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一家或几家经营者就能提供和满足既定的市场需求。②参见曾晶:《论管制行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政治与法律》2015 年第6 期。当前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甚至呈现寡头垄断状态,其前期沉没成本非常高,且随着通用人工智能企业用户的逐渐增加,边际成本甚至降低至零。尽管存储和处理数据需要的信息技术成本极高,但该系统开始运行之后,增量数据能以较低成本分析和改进算法③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Paris: OECD,November 2016,https://www.oecd.org/competition/big-data-bringing-competition-policy-to-the-digital-era.htm,accessed by Sep.10,2023.,从而降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边际成本。因此,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反而多个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不及单一供给者提供相同产量更便宜,市场上仅需一个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成本是最低的。根据传统自然垄断理论,治理自然垄断产业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实现国有化或者由私人企业运营自然垄断设施,同时政府对其进行管制。④参见姜春海:《自然垄断理论述评》,《经济评论》2004 年第2 期。由于通用人工智能业务的高度技术性,实行国有化不及由私营科技巨头经营更有效率。当前,国内科技巨头百度研发推出“文心一言”大模型,阿里推出“通义千问”大模型,讯飞推出“星火认知”大模型。基于昂贵的开发成本,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全球范围内都仅能由少数科技巨头企业提供,且数据、算法催生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产品的全球性与全时段提供等因素共同推动相关市场发展成为一个由单一或极少数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垄断的市场。
因此,通用大模型服务不仅作为一项新公用事业存在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也因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并成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⑤参见徐伟:《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其责任——以ChatGPT 为例》,《法律科学》2023 年第4 期。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呈现寡头垄断的结构特征,在世界范围内仅存在少量具有竞争关系的通用性基础大模型以及若干在特定行业高价值专业化的基础模型。超千亿参数的大模型研发,囊括了底层庞大算力、网络、大数据、机器学习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系统性工程,需要有超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支撑。⑥参见张凌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与分层治理》,《现代法学》2023 年第4 期。正是因为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基于海量数据的大模型训练、算法算力技术门槛等高研发成本的存在,存在高且持续的数据壁垒、资金壁垒、技术壁垒和监管壁垒,潜在竞争者难以与现时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进行竞争,从而存在结构性市场失灵,需引入事前行业管制机制。为构建事实上可竞争的市场,应降低现有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先发优势或沉没成本的影响⑦Jordi Gual &Sandra Jodar-Rosell,“European Telecoms Regulation: Past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in Xavier Vives ed.,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EU: Fifty Years on from the Treaty of Ro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38.,通过事前行业管制的方式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设定行为和结构性管制措施以预防竞争损害。
三、通用人工智能服务管制要素的转变
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是在海量数据与强大算力支撑下让通用人工智能得以记住训练期间获得的大量事实并生成新的内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通用大模型的生产素材、训练过程具有最强的控制力。他们不仅是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预训练数据来源的筛选主体,也是通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的主体。在通用人工智能治理中,“数据”“算法”仍然是最关键要素,应充分考量数据、算法、技术等各项要素。在通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阶段,应重点防范数据安全风险,加强通用人工智能研发者对数据收集、加工、处理等合法性审查。在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研发与运行阶段,应重点防范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算法安全风险,健全算法备案审查制度。一方面,数据作为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越多越能实现通用大模型服务对用户的精准画像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算法的训练以大规模数据为基础,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数据优势进一步转化成算法优势,促进人工智能服务更加智能化,且进一步帮助通用大模型获取更多数据。正是数据与算法循环驱动,增强了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竞争优势。
(一)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数据开放义务
通用人工智能的运行离不开通过海量的数据提炼信息、预测趋势、训练模型,需加强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数据治理责任,以防范数据泄露、违规利用风险。作为通用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筛选和控制的主体,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应当对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真实性负责,确保数据收集与使用的合法性。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行业管制重点在于,实现对其训练大模型数据的合理分享机制,以消除数据市场进入壁垒。在数据产权不明晰的当下,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往往将收集到的个人数据作为企业私产,甚至通过设置数据不兼容等方式阻止数据互联互通,以致其他竞争性企业难以撼动其数据垄断地位。数据产权不清被认为是数据垄断的根源,不仅在于企业对大量数据本身的控制地位,形成收集和存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①Bruno C.Smichowski,“Data as A Comm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A General Policy Proposal”,CEPN Working Papers 2016-10,https://hal.science/hal-01386644,accessed by Sep.12,2023.,加剧了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数据量上的垄断,还在于数据产权不清导致债权路径及反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局限性所引发的数据垄断。在实践中,各大数据交易中心(机构)均采取债权路径,通过契约意思自治实现大数据确权。然而,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大数据交易加剧了当前数据垄断的法律风险。由于未制定数据产权制度,且市场竞争极具开放性、激烈性,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穷尽各种行为方式并进行具体化和预见性规定。为此,司法实践中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 条一般条款来保护数据资源,但该方式过度依赖法官自由裁量权,在稳定性、可预测性方面存在缺陷。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其数据是否会受到排他性保护很难进行准确预测,这为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将数据置于秘密状态下或应用技术措施实施数据垄断提供了空间,使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受到严重阻碍,也因此导致了数据垄断的发生。
然而,只有提高数据的开放性和共享性,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才能不断发展,“数据孤岛”“数据分割”才能被真正打破,数据要素才能真正驱动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创新。通用大模型时代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具有市场参与者与市场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及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拥有海量数据的特殊运营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长期稳固的市场支配地位,数据是其战略资产,所以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有较强的动力实施数据封锁,使得数据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难以实现,而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决定了数据的公共价值属性,从而需要政府监管明确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数据开放义务;另一方面,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业务都以数据应用创新为主,若对数据共享过度限制容易造成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竞争与创新动力不足,不仅导致数据资源的浪费,也让中国在全球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发展浪潮中丧失竞争优势。
此外,在强调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主动开放与共享数据的同时,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不得阻碍用户可携权的行使,以确保数据可迁移性。个人数据可携权可追溯至1983 年德国进行人口普查时,曾有公民针对其拥有的个人信息自决权提起宪法诉愿。德国宪法法院支持了该诉求,即认定个人拥有决定自己信息归属的权利。2018 年5 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数据主体享有数据可携权,用户据此有权从数据控制者手中获取其曾经提供的数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具体包括数据主体获取个人信息副本权、请求数据控制者直接将与数据主体有关的个人信息传输给另一数据控制者的权利。设置数据可携权有利于破除数据封锁效应,促进数据流动、共享与使用,降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数字市场的垄断力,促进市场竞争。与此同时,数据可携义务不仅要求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其他竞争性企业之间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无须用户自行迁移,还要求数据控制者须以“结构化、通用、机器可读”格式实现数据移转①Ruth Janal,“Data Portability-A Tale of Two Concepts.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8 J.Intellect.Prop.Inf.59 (2017).,确保其他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企业获取数据不存在技术壁垒。数据可携带权作为一种促进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大大降低了终端消费者个人数据的跨平台转换成本。在数据确权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当下,促进消费者的多归属及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转,打破了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基于大数据的市场支配力量,维护了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公平竞争秩序。
(二)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算法备案审查
在由分析式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算法模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变了数据的产生方式、组织形式及流转方式。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中,算法的本质是将任务需要的系列化步骤完成,对步骤作精确描述,让步骤可在计算机上运行。②参见 [美]托马斯·H.科尔曼:《算法基础——打开算法之门》,王宏志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版,第1 页。计算机有能力对大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算法有自主学习、自主决策的能力,这使得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所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具备了从“上帝视角”处置相关事宜的能力,从而能够利用数据与算法,通过预训练、优化训练大规模的数据集,学习抽象出数据的本质规律和概率分布,并利用通用大模型生成新的数据,形成最终产品。③参见蒲清平、向往:《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 GPT 的变革影响、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 期。由于算法“模型设计+数学规则”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导致非算法专业人士尤其是普通公众无法掌握算法的运行和决策原理。①参见钟晓雯:《算法推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力异化及法律规制》,《中国海商法研究》2022 年第4 期。而通用人工智能依托的深度学习模型在前馈神经网络中引入自注意力机制,是经典的黑箱算法。②哈尔滨工业大学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所:《Chat GPT 调研报告》,2023 年版,第24 页。在算法设计、训练模式选择、模型生成与优化、提供服务过程中均可能出现算法透明性与可解释性风险、算法歧视与偏见风险,因此强化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算法事前备案义务尤为重要。
对通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的事前监管主要通过建立事前算法备案制度,预防事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隐瞒与错误披露导致的算法问责风险。算法备案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算法存档备查行为,目的是获取具有潜在风险的算法相关信息,为今后反垄断监管中算法问责提供依据。其内容主要包括算法设计的目的、算法自评估报告、算法可能产生的风险、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处理可能发生风险的预案措施等。反垄断执法部门需要评估备案的算法,基于相关标准确定算法的具体风险等级,按照风险等级实施标准不同的监管。③参见张凌寒:《网络平台监管的算法问责制构建》,《东方法学》2021 年第3 期。美国《算法问责法案》以用户数量为标准,明确平台的用户数量超过一百万,就应接受算法审查。④See H.R.2231-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19.《算法正义和在线平台透明度法案》提出在线平台对算法使用和处理记录的保留义务,要求在线平台对四类算法记录保留5 年备查。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对算法进行事前的备案登记,填报服务提供者所使用的算法原理、基本类型、目的意图、算法自评估报告等,增强算法透明度,打开“算法黑箱”。
反垄断监管机构需要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备案算法进行合理性及正当性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开发设计算法技术、数据输入、算法部署和自动决策、所作决策的输出等环节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这有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施事后惩罚时,对平台企业可能提出的技术中立、算法黑箱等抗辩理由施以有效的反驳。实际上,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导的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就强化治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提供了算法备案、安全评估、风险监测、监督检查四种治理举措。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明确记录模型、算法、数据、决策的过程、决策的结果,并以有效方法检验模型、测试算法。确有必要时,还可引入第三方审计,让事后问责能够真正发挥效用。然而,鉴于对算法合理性审查需要极高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为监管技术市场中的竞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了包括执法人员、员工律师、技术研究员的专门工作组,从而在在线广告、社交网络、移动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市场以及平台业务等复杂产品和生态系统化的服务方面均具备较强专业知识。英国竞争市场管理局专门设立“数字市场部”负责对市场上处于战略地位的科技巨头企业实施监管,该“数字市场部”招聘的员工包括数学博士、心理学博士、物理学博士等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水平的人员。然而,我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执法人员编制不到50 人,一些省市的反垄断执法人员甚至为个位数,执法人员严重不足。我国应扩充人员编制,吸纳各领域的专家,增强执法能力,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市场垄断行为。
四、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垄断行为的认定
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执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应探索制定人工智能领域垄断行为认定的通用反垄断政策。然而对于此种加速立法进程、构建配套制度的专门立法,将会使得每一项技术的出现都由全新的政策法律予以解决,从而导致重复立法、超前立法的立法资源浪费。在过去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治理过程中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彼时的专门条款和单行立法是为填补立法空白。而今个人数据挖掘、深度合成、个性化推荐等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较为成熟,无论是《反垄断法》,还是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针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治理仍然适用。与之不同的在于,在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垄断行为认定时,需对原有的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规则调整适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深入贯彻非强制性柔性执法方式,探索创建高效运行的数字反垄断监管系统,实现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的敏捷治理。
(一)通用人工智能反垄断中重塑行为违法规则
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对通用大模型服务垄断行为的认定坚持合理原则具有必要性。现代被广泛接受的合理原则分析框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由原告举证反竞争效果;第二,由被告提供促进竞争的正当理由;第三,由原告举证提供一种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式;第四,当前三步仍然不能处理案件时,最后由原告证明反竞争效果大于促进竞争的效果。①参见[美]赫伯特·霍温坎普、兰磊:《论反垄断法上的合理原则(上)》,《竞争政策研究》2018 年第6 期。合理原则作为垄断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主流规则,在很多案件中被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界定为特定行为促进竞争作为适用合理原则的直接证据。②Edward D.Cavanagh,“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 Theory: Finding a Balance”,45 Loy.U.Chi.L.J.123(2013).如在美国“李金创意皮革公司案”③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s.,Inc. v. PSKS,Inc.,551 U.S.877(2007).中,法院并未就个案进行评估,而是在查阅相关经济学文献后发现,有理论认为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存在促进竞争效果的可能性,为此决定采用合理原则。④Abraham L.Wickelgren,“Determining the Optimal Antitrust Standard: How to Think About Per Se Versus Rule of Reason”,85 South.Calif.L.Rev.52 (2012).有些法官甚至不阅读相关理论文献,直接根据经验法则进行决策。而具有采用合理原则判决经验的法官毕竟是少数,从而难以避免法官在选择何种原则上完全依赖于其价值判断。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垄断行为,仍坚持合理原则是反垄断法的基础原则,根植于合理原则是由竞争、公平、秩序、正义、消费者利益、竞争效率、经济效益等诸多价值综合的统一体,合理原则的适用有利于法院和反垄断执法中综合兼顾各方面的价值均衡。但是,对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反竞争行为的合理性分析,应删繁就简并形成迅速有效的合理原则适用方法。合理原则的快速适用,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快速浏览的合理原则”。该模式预设某些行为带来较大竞争损害,尽管违法但未达到本身违法程度,此时应给予经营者一定抗辩权,对抗辩理由进行合理性分析,如果抗辩不成立,再认定违法。①Herbert Hovenkamp,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St.Paul: West Academic,2005.另一种是“较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测试”。它是在适用合理原则中被告提出抗辩时,原告指出一个对于竞争限制更小的行为,但能实现同样的商业目的,此时即可认定被告行为违法。②参见孟雁北、赵泽宇:《反垄断法下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规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这种快速有效的合理原则适用,能够提高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反垄断执法效率,节约执法成本。
其次,引入本身违法原则具有合理性。本身违法原则最直接的适用是通过“直接证据法”,只要证明某一行为存在,即构成垄断。最早运用“直接证据法”的是美国的“印第安纳牙医案”③FTC v. Ind. Fed’n of Dentists,476 U.S.447(1986).,该案中法院认为,尽管相关市场界定以及市场力量分析为常用的判定行为会不会对自由竞争产生危害的手段,但是当不法行为造成销量大幅下降时,即无须再分析市场力量。在美国“Todd v.Exoon 案”④Todd v. Exoon Corp.,275F.3d 191,206(2d Cir.2001).中,美国法院跳过了相关市场界定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环节,根据竞争损害直接认定竞争垄断行为违法。当能够获取反竞争效果的直接证据时,执法部门也更倚重直接证据而非相关市场界定。⑤Dennis W.Carlton,“Revising the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6 J.Compet.Law Econ.619 (2010).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3Q 案”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4 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认可了即便不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若有直接证据证实经营者基于所处的市场支配地位作出的垄断举措有碍、排除了竞争,给市场竞争造成了损害,也可依此评估损害后果。这为“直接证据法”在我国反垄断法实践中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欧盟《数字市场法》明确列举了数字平台企业的限制、排除竞争行为,并以本身违法原则直接认定“守门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0 次修订新增的第19a 条规定,通过混合结构的优势和与竞争相关的关键职位的占领而产生的对不同领域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平台,由于拥有多种竞争优势从而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因而不应将市场支配地位作为对其进行干预的门槛。对于具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若按合理原则,个案化判定其究竟有无跨市场的竞争性影响、究竟处不处于优势地位,既降低了执法效率,又可能造成自由裁量权不受限制,有碍司法公正。在直接证据法模式下,数学建模、理论论证、后果分析等各种烦琐步骤都得以省却,取证程序明显缩减,执法成本大幅降低,执法效率大幅提升,司法的时效性、公正性将得到更好地保证。反垄断执法机构得以尽早发现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并提前给予处置,这将助力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的拨乱反正,为通用大模型提供者划定明确的行为边界,让反垄断立法的应有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通用人工智能反垄断中贯彻柔性执法理念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突破了人们的认知,很多阶段性问题在还没被清楚认识时,就在技术的更新迭代中消失了。从理论到实践都难以系统化地解决、回答相关问题。⑦参见孔祥俊:《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2 期。在很长一段时期,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都需适可而止,因为特定时期创新和发展才是真正的第一要务。⑧参见[德]阿希姆·瓦姆巴赫、汉斯·克里斯蒂安·穆勒:《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钟佳睿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6 页。行为违法性认定对企业损害竞争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事后制裁性,如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将阿里、美团所采取的“二选一”行为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的限定交易,并基于此对两平台企业实施高额的罚款。但若仅以单一的威慑性举措对其施以行政处罚,可能造成危害竞争的行为逃脱了规制。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罚阿里、美团的同时,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用行政指导敦促企业在内部构建长效的公平竞争机制,鼓励企业全面规范自身竞争行为,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企业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切实维护相关市场良好竞争生态。①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国市监行指反垄〔2021〕1 号)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指导书》(国市监行指〔2021〕2 号)。有效的反垄断监管不应仅依赖行政处罚,而需要将教育、制裁、引导等多种举措糅合在一起,激励、约束市场主体积极主动、自觉守法。
与硬法相比,反垄断中的柔性执法包含事前的合规经营教育、行政指导、约谈等,软法程序更灵活、适应性更强,可以服务于多种治理目标,已成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最常见形式。②Carlos Gutierrez &Gary Marchant,“How Soft Law Is Used in AI Governance”,Brookings Institution,May 27,2021,https://policycommons.net/artifacts/4144194/how-soft-law-is-used-in-ai-governance/4952788/,accessed by Sep.17 2023.为配合柔性执法方式的有效实施,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出台了《垄断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以下简称“《承诺指南》”),鼓励经营者在尽可能早的阶段作出承诺,《承诺指南》从适用范围、适用流程、执法机制三个方面对承诺制度作出了完善规定。③2021 年4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连点名34 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展座谈,找他们开会、座谈、并形成了34 份《依法合规经营承诺》。若经营者积极配合调查,积极落实整改措施,消除和挽回其行为造成的影响,达到《反垄断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执法目标,则可以对企业“中止”或“终止”调查,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企业的这种承诺可以被视为与反垄断执法部门的行政和解协议。对建立合规计划的经营主体可适用反垄断和解协议,将合规条款加设到和解协议里,督促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以合规计划作为补救举措,在合规计划的建立过程中充分调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让其积极主动地配合监管机构开展相关整改工作,填补体系漏洞,预防再次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在平等参与的基础上,利用承诺、反垄断和解协议,有效建立合规机制,从而取代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施以单一的经济惩罚。
(三)通用人工智能反垄断中引入敏捷治理方式
在通用大模型服务市场环境下,反垄断监管能力须跟上时代的步伐,监管部门应更加注重依托大数据、算法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提高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全程反垄断监管的自动化执法水平。运用区块链技术达到采取“以链治链”的监督和管制理念,反垄断执法机构将反垄断目的转化为合约机制,内嵌于通用大模型算法之中,从根源处规范算法歧视、算法共谋等垄断行为,使得“Code is Law”的“法链”(Reg Chain)监管理念切实可行。④参见杨东、侯晨亮:《论平台“封禁”的反垄断规制——以社交平台为研究对象》,《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4 期。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竞争执法及反垄断监管,推行法律与技术共同治理模式。⑤参见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5 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了解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算法规则和指令,掌握处理销售量、价格和成本等市场数据的方法,通过参与式反垄断执法,监测和评估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异常定价、实施垄断行为的技术能力。⑥See Jean Tirole,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p.378-379.可通过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竞争行为进行预测,从而实现对其精准监管的目标。
智能监管系统为市场监管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各国执法机构也开始创新执法工具,如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通过在其新设数字市场部的反垄断监管中引入“监管沙盒”工具,广泛学习借鉴了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成功经验,将进行备案的算法在可观察、可控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试运行,测试新的算法行为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①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Algorithms: How They Can Reduce Competition and Harm Consumers”,London: CMA,Jan.19,2021,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lgorithms-how-they-can-reduce-competition-and-harm-consumers/algorithms-how-they-can-reducecompetition-and-harm-consumers,accessed by Sep.17,2023.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出“推动敏捷治理”,表明我国人工智能监管由单一的“规范—技术”监管向“规范—技术”与“技术—技术”监管模式并行的转变,推进采取以技术治理技术、以算法监管算法的监管手段。实际上,在我国地方金融监管领域广泛运用的“冒烟指数”②冒烟指数由综合合法性、非法集资特征词、收益率偏高、负面反馈指数、传播力这五个维度构建,通过机器学习对每个维度进行自我赋权。冒烟指数越高,说明越接近非法集资的特征,监管部门就可以及早监测预警,做到“打早打小”。,将新技术用于辅助市场监管机构预判式监管,分析和固定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企业违法性垄断行为的证据,对可能导致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进行风险警示。浙江省创造性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建立了“浙江公平在线”系统,针对有重点风险的企业开展全天候监测,如发现问题及时预警③参见王世琪:《全国首个经济平台数字化监管系统——“浙江公平在线”昨上线》,《浙江日报》2021 年2 月27 日。,推动市场监管效率和监管实效的提升。广东发布并施行《广东省进一步推动竞争政策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落地的实施方案》,强调做好线下竞争执法工作,同时还运用互联网智能监测手段开展线上执法工作。青岛则依托山东省网监平台了解全市平台市场主体底数,建立全市平台主体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网络交易平台监测室,实现主动监管,让监管更具主动性与及时性。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强化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对区块链、大数据、算法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利用,以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为基础,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在在线识别、在线证据保全、源头追溯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从而有助于不断提升识别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经济风险和违法违规线索的能力,让“以网管网”真正获得体现。此外,还可以鼓励市场主体研发反制技术,如“消费者算法”可以帮助消费者识别价格、识别合谋,一定程度上降低垄断行为的发生概率,帮助消费者识别垄断行为的发生,固定有效证据,降低举证难度。
五、通用人工智能治理中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管制相衔接
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利用数据、算法工具和技术条件实施垄断行为,反垄断执法主要通过事后制止违法行为,矫正市场失灵。但并不能有效处理市场上是否存在“一家独大”的通用大模型产品提供者、现存市场是否存在有效的市场竞争、潜在竞争者是否存在市场进入障碍等结构性失灵问题。因此,反垄断执法不足以单独完成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垄断行为治理的重任,必须有行业管制作为补充。④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Ex Ante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Paris: OECD,December 2021,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ex-ante-regulation-and-competition-in-digital-markets.htm,accessed by Sep.17,2023.前者是通过执法行为事后对行为的结果进行纠正,侧重事后对市场秩序的矫正;后者侧重维护事前和事中的市场秩序。两者分别解决通用人工智能时代通用大模型服务的市场失灵与结构性失灵。仅通过反垄断执法,不足以矫正结构性失灵,须加强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企业的行业管制。
(一)反垄断执法仅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
当前反垄断执法以芝加哥学派效率分析为正统理论,以保护有效率的竞争过程为唯一目标。然而,在面临通用大模型时代《反垄断法》实现对隐私数据保护、消费者保护、下游平台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保护等任务时,《反垄断法》的单一经济效率目标无法满足通用大模型时代竞争诉求。在下游通用大模型使用平台与消费者用户、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下游通用大模型使用平台、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其他竞争性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三重利益关系中,这些利益关系同时关涉到数据安全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相关部门与行业的交叉监管和信息共享共治。以消费者个人数据被广泛滥用为例,由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体现为网络化、开放性和交互性等特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数据滥用和数据隐私涉及多个主体权责的相互交织问题,以“保护有效竞争”为单一目标的反垄断执法难以依据多部法律进行系统监管,针对不同利益关系的问题缺乏监管目标和重点,无法实现数据收集、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
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关涉的三重利益关系暴露了反垄断执法单一目标的弊端:在下游通用大模型使用平台与消费者用户的关系中,通用大模型使用平台对消费者拥有不对等的数据优势和信息资源,而反垄断执法部门却无法在消费者个人隐私保护和重点查处平台过度收集、不当使用用户个人数据等方面发挥足够的作用,从而无法真正触及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训练大模型过程中数据不当收集与使用情况。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通用大模型使用平台的关系中,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一方面基于自身提供竞争性服务,另一方面向下游平台提供通用大模型的“双重角色”,导致其与下游平台经营者的地位不平等。反垄断执法机构仅关注竞争效率,并不重点审查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是否对下游平台经营者实施排他性交易、自我优待行为。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与其他竞争性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基于自身的数据优势实施封禁行为,从而限制数据的转移与共享利用,排除限制竞争对手的竞争。反垄断执法虽关注限制竞争效果,但难以合理兼顾所有参与者的利益、纠正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凭借垄断地位捕获价值过多等问题。反垄断监管机构在平衡各方利益时应特别关注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捕获的利益,保护消费者用户和下游通用大模型使用平台的利益免受损害,如只关注个别参与者的利益,可能得出当前市场结构现状没有问题的结论。①Michael G.Jacobides &Ioannis Lianos,“Regulating Platforms and Ecosystems: An Introduction”,30 Ind.Corp.Chang.1131 (2021).由此,仅仅依靠反垄断执法这一种工具,难以实现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有效约束。
(二)行业管制对结构性失灵的矫正
长期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对科技巨头企业的反垄断监管采取较宽容的政策,强调市场主导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然而,在经历了长达40 多年的宽松监管之后,资本出现过度扩张,使得数字巨头垄断现象越发严重,导致美国经济活力下降。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GAFA)四大科技巨头市场估值超过五万亿美元。它们垄断市场、打压竞争对手、妨碍市场竞争,在此背景下推动了主张强化政府监管力量的新布兰代斯学派的兴起。新布兰代斯学派对市场力量持批评态度,主张不应当仅仅关注消费者福利,还应关注经济过程和市场结构。②Lina Khan,“The New Brandeis Movement: America’s Antimonopoly Debate”,9 J.Eur.Compet.Law Pract.131,131-132 (2018).在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定位及规制上,国外监管当局认为,其为下游平台企业提供通用大模型,占据战略市场地位,掌控着瓶颈权力,具有显著市场权力或重要中介权力。①英国竞争与市场监管局所提出的“战略市场地位”判定说,主张基于企业规模、企业控制市场的能力、接入系统用户在交易中的地位等多方因素,对企业是否处于战略市场地位做出判断;美国斯蒂格勒研究中心提出“瓶颈权力”判定论,主张基于企业控制市场的能力、对其他竞争者施以阻碍的能力来判定企业是否在市场上掌控着“瓶颈权力”;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提出“显著市场权力”说,主张基于企业对竞争活力的影响、对市场准入所具备的阻碍能力来判定企业在市场上是否掌握着“显著权力”;欧洲电信监管机构提出 “重要中介权力”论,此理论认为应当结合市场控制力、财力、渗透数字服务能力等因素判定企业在市场上是否掌握着至关重要的“中介权力”。新进入者难以跨越由规模经济所筑起的壁垒,或迅速被淘汰,或成为新的垄断主体。在没有能够打破这种市场结构的新技术出现的情况下,通用大模型服务提供者基于上述要素所形成的市场力量难以被超越,通用大模型服务提供者持续性的垄断力量造成了数字市场的结构性失灵。②Stigle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tate,“Stigler Committee on Digital Platforms”,Chicago: Stigler Center,May 15,2019,https://www.chicagobooth.edu/research/stigler/events/antitrust-competition-conference/digital-platforms-committee,accessed by Sep.19,2023.
当前,竞争管理机构的监管措施旨在事后消除或制裁具有强大市场力量的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的垄断行为。然而,通用人工智能的巨大经济活力和通用大模型的迅速发展倒逼监管机构进行更快、更有效地干预。“谷歌案”历时7 年广遭诟病的原因在于,事后反垄断执法无法及时有效纠正具有高度技术性和隐蔽性的违法垄断行为,调查审理历时较长,在此过程中市场竞争状况可能早已经发生变化,出现严重的竞争损害后果,事后处罚为时已晚,也毫无意义。③Geoffrey Parker et al.,“Digital Platforms and Antitrust”,in Eric Brousseau 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I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Market Regulation (online edn,Oxford Academic,Mar.14 2019),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0900571.013.34,accessed by Sep.18,2024.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反垄断应以预防思维矫正市场结构性失灵。对通用大模型服务提供者及早干预,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效应、数据优势的作用,数字经济市场表现出快速的市场集中趋势;另一方面基于作为市场中心战略地位的通用大模型提供者,极易基于其他下游市场参与者对其形成的依赖而扭曲市场正当竞争状况。④参见陈兵:《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信发展的法治基础》,《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3 年第4 期。若不对大型通用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者加以限制,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挤压下游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的生存及发展空间。与反垄断执法采取个案执法方式相比,行业管制并不将违法行为作为介入的先决条件,而是将消除垄断影响作为目标,通过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设置超越正常市场条件的规制义务,促使其改变市场行为,从而进入反垄断执法适用不能的领域。⑤参见侯利阳:《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比较法研究》2023 年第1 期。由此,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如果不能通过事后的救济来纠正垄断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就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的监管手段,通过制定合理的、谨慎的规则,来强化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事前、事中监管。⑥Philip Marsden &Rupprecht Podszun,Restoring Balance to Digital Competition-Sensible Rules,Effective Enforcement,Berlin: Konrad-Adenauer-Stiftung,2020.
(三)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管制的衔接与互动
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垄断存在数据隐私保护、数据资产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市场竞争及维护公共利益等多重目标,与传统分析式人工智能静态性与单维性的应用场景和具体情境不同,通用人工智能应用具有动态性,是对人工智能价值产业链的整体性重构。因此竞争执法机构也应采取多部门合作的方式监管市场竞争行为,形成以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管制良性互动的协同治理机制。
1.理论设想:新布兰代斯理论的兴起与多元共治
新布兰代斯理论认为,《反垄断法》只是众多治理工具之一,除了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美联储、农业农村部、国防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市场监管的权力。①Lina Khan,“The New Brandeis Movement: America’s Antimonopoly Debate”,9 J.Eur.Compet.Law Pract.131,131-132 (2018).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反垄断涉及多元交叉领域,涉及多重利益关系,更需要不同监管部门的多元共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 条规定,网信、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公安、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反垄断案件具有涉及多元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协同监管不仅表现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也表现为行业管制部门与管制对象之间的协同合作。②参见[英]罗伯特·鲍德温等编:《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606 页。在合作管制中,行业自律在约束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垄断行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监管的有力补充,相比之下采取自律规范立法及执法需要的成本较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的反垄断自律规则应由熟悉本行业业务的行业协会来制定,其制定的行业自律规则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强,能对维持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发挥积极作用。如行业协会可以制定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规范,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要求算法投入应用前的安全测试,以及投入应用后的实时算法监测,从而进行算法程序矫正。实际上,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外部监管与行业自律相辅相成,外部监管效率如何,受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体系内在自律程度的影响。通用人工智能服务体系自律程度越高,其内部控制有效性就越强,垄断行为越少,外部监管越高效。反之,外部监管则越低效。总之,合作管制的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而非强化管制行为本身,最大限度地拓展协商、对话的时空维度,塑造与共治格局相匹配的管制形态。因此,发挥通用人工智能服务行业协会参与和自律监管,是维护通用大模型服务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手段。行业自律具有自身优势③参见张忠军:《金融立法的趋势与前瞻》,《法学》2006 年第10 期。,从而形成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反垄断监管由政府主导走向“行业管制—反垄断执法—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自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2.实践检验:以算法设计中的差别待遇为例
管制行业法与反垄断法均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现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两者在通用人工智能治理上相互协调适用具有必要性。例如:英国竞争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数据保护机构共同强调寻求合作,克服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④参见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CMA-ICO Joint Statement on Competition and Data Protection Law”,London: CMA-ICO,May 19,2021。;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竞争管理局和电信监管机构针对大数据问题联合倡导11 个建议,提出要建立永久协作机制。⑤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Consumer Data Rights and Competition -Note by Italy”,Paris: OECD,May 25,2020.在我国“滴滴出行案”中,国安部、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审查,这充分体现协同监管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有助于减少国家数据安全风险,切实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促使公共利益获得有效保护,为实现反垄断监管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具体而言,行业管制于事前、事中实施常态化监管,直至反垄断执法、司法机构作出决定或判决,管制才停止。两者的衔接互动可以在案件发生前、案件调查中以及案件办结后的全过程。案件发生前与案件办理过程中,管制部门与执法机构可以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交流监管心得、执法经验。⑥参见王磊:《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3 期。实际上,联席会议的成效性在平台治理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检验,近5 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每年联合十四部门联合开展“网剑行动”交流网络市场监管的经验,其中“加强平台治理落实主体责任”是网剑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案件办结后,执法决定、司法判决作为网信办、工信部等管制部门强化自身管制工作的重要参考。假定某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过程中使用了歧视性数据导致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存在针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合理差别待遇,可先由管制部门采取约谈的方式,要求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差别定价行为作合理说明,积极履行算法解释义务,并承诺后续服务不存在不合理差别待遇。若管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差别定价行为给市场造成了实质性竞争损害且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管制部门应联合反垄断执法部门开展联席会议。而后由反垄断执法部门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差别待遇行为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界定相关市场,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该相关市场上进行以“数据、技术、用户黏性、潜在竞争威胁”为考量因素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判定该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的“差别待遇”行为,最后对该差别待遇行为对相关市场的竞争损害进行分析。必要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根据分析结果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实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事后惩治,管制部门也通过执法决定与裁判经验,进一步完善以后的常态化管制工作。至此,从案件发生到案件办结,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管制部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构成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实施差别待遇行为治理的“事前-事中-事后”闭环。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反垄断执法关注违法行为发生后的事后矫治,并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封闭系统,需要通过事前、事中的管制进行补充。①[美]赫伯特·霍温坎普:《联邦反托拉斯政策:竞争法律及其实践》,许光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782 页。相反,事前、事中的管制无法有效处理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需要两者衔接互动,形成 “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监管”的全流程闭环治理模式(见图1),强化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垄断行为的监管。

图1 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管制的衔接与互动
六、结语
单一的事后反垄断执法方式不仅调查耗时长、成本高,也因其滞后性导致执法弹性较为缺乏,无法适应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各种新型垄断行为,尤其是对特定行为严厉的事后禁止,会导致已有商业模式的巨大调整,使得创新发展的不确定性越发明显,这对通用人工智能实现创新发展极为不利。鉴于事后反垄断执法方式无法及时有效地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竞争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动态平衡,行业管制机构有必要在事前对通用大模型提供者进行适度干预,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市场及其细分领域频繁开展调研与竞争评估,对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数据处理及其算法技术的更新应用进行动态监测,在事前、事中对其垄断行为进行从严精准监管,便于掌握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涉嫌垄断的违法事实和更好地进行后续监管活动。采取这种动态调整的、具有阶段性的监管目标和原则,平衡保护市场竞争秩序、消费者福利与通用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创新发展动力和社会发展活力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