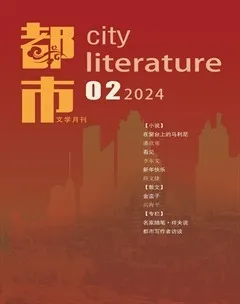新年快乐
傍晚六点多点,龚杰睁眼缓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关了闹钟。要说起床气,天黑以后的气要比早起的气大得多。这么一想,龚杰不禁乐了。
手机还在响个不停,微信群多出了几百条新消息,这是一个近五百人的跑步群。眉城虽说只有六十万人口,但随处可见跑者的背影。翻完这些有趣的人的有趣消息,才发现大豪给他打了两个语音电话。他又是一乐,回了个带问号的表情。大豪不久前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嚷嚷着要跟他跑步。瘦得像电线杆的人也会得这种病,龚杰真是想不明白。
大豪很快就开始了跑步,却对龚杰的提醒充耳不闻,结果,用力过猛又不注意方法,没几天就弄伤了膝盖。回老家休养了半个月后,大豪再也不跑步了,而是转头又跟别人去学骑行。这个比自己年轻几岁的男孩真让龚杰哭笑不得。一直没收到大豪回复,龚杰也并不在意。谁知道那家伙又在想哪一出呢。
离上班时间还早,他去常去的那家快餐店,吃了一碗馄饨和一个厚厚的牛肉餅后,就溜达上了彩虹桥。这里是拥挤城市的一处开阔天地。桥上看风景的行人很多,成百上千张嘴同时说个不停。所有人好像都是一个活法,又活得各不一样。龚杰第一次站在桥上的愉悦心情现在丝毫未变。周末或调休的时候,他总要来这儿跑一趟。
他有好几天没跑步了。望着不断从他身后路过的跑者,想跑的情绪依然不大。正因为不想跑才去跑,这才是跑者的思维模式。这是一次跑步途中偶遇的一位跑友说过的话。或许出于这个原因,龚杰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跑者,因为他只有想跑的时候才会去跑步。
风很大,他一个劲儿打冷战。今年冬天冷得太快又太早。望着东边的天际线,还能看见群山的轮廓,老家肯定下雪了吧。老家就在秦岭香山脚下,每年早早就落雪。小的时候他最喜欢冬天,到处捂着厚厚的雪,家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大人有大人们的乐事,小孩也有他们自己的乐事。他和伙伴扯着蛇皮袋子当坐垫,把坡路当作滑雪场,尽情地挥霍着童年。开始痛恨那个地方是他上中学以后的事情了。等到上了大学,他便决定毕业以后离那个地方越远越好。如今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在南方那些年,他连雪的影子都没见过。最初的时候,他还能从家人、同学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些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后来他和他们全都断了联系,那时他二十五岁,自认为刚从压抑他的地方挣脱出来,觉得这个决定很酷。
回忆给他脸上带来了异样的笑容。直到冷风吹得舌头发硬,他才闭上嘴。龚杰总是把肥厚的双唇一咧,让眼睛在一堆皱纹中间闪闪发光。小时候舅舅常说他凭张笑脸就能干成很多事。他叹一口气,心想,要是能倒成白班就好多了,连续夜班实在难有好心情。
操作间里依旧是不停歇的机器轰鸣。闻到尿素的气味,龚杰立马来了精神。他以前从未在工厂做过工,要不是眉城没办法让他拿起吉他,他还以为工厂生活就是人们抱怨的那样。刚来的时候,他确实很不适应,因为需要一直弯腰坐着,腰背疼得厉害,习惯之前,想坐的时间长一点都难。但没过多久他就喜欢上了这种工作节奏。身后的包装袋堆积如山,手中的药铲一刻不停,他学会了用最少的次数铲出规定的分量,规格越严越有干头。因为是计件工,干得多挣得多。干活的时候几乎人人缄默不语。他挥舞着药铲,想象着自己正在随意拨弄琴弦,脑袋里响起无数的新旋律。整个操作间似乎也回响着琴声。他干一会儿活儿,抬头扫一圈,看着别人脸上保持的别扭神情,好像只有自己干活的时候是快乐的。于是,他对这座城市的感觉也不再是印象中的幽闭和生锈了。
龚杰长大的地方离眉城只有一百公里。小时候他常和姐姐进城。等他再长大一点,就不愿意和她去了,总觉得这座小城和他们那片丘陵地带差不多。后来,父母开出天价彩礼也没能留住一心远嫁的姐姐,和山里多数的年轻女孩一样,多年来姐姐和他们也只是靠着“节日快乐”这样的短信在维持着亲情。他二十一岁那年才第三次成功考上大学,每当他和新同学交换社交账号的时候,泡在一个个酒吧里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可是那些儿时伙伴大多已结婚,并且不少人还生了孩子。
“可怕死了。”有一次,他和当时的女友聊到了这件事情,女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后这样说。他咧着大嘴笑了,那时的自己真是快乐。大学第一个学期,他就谈恋爱了,让那些中学生气息还未脱尽的舍友们羡慕不已,得空就来找他取经。他吆这个喝那个,俨然一副老大哥的派头。大学四年,每月生活费不出两个星期就会被他挥霍一空,算一算那几年舍友们接济他的钱也绝不会少。他们当然没说过要他还,只是这些事情偶尔冒上来的时候,他总会感觉自己还有账没还清。
封完二百个包装袋,龚杰就躲进厕所抽烟去了。有时会无意听到工友们讨论一天能挣多少钱,他算了一下,要是逼自己一把,这个数字他也能完成。不过,那样势必会把这份工作变成苦差事。所以每完成二百的量,他就会起来走走。让他开心的并不是把这份工钱装进了兜里,而是可以去抽烟了。一个夜班抽四根烟就过去了。只要有期待,生活就能忍受。——这简直成了他的人生哲学。
刚毕业那会儿,他还常用这句话安慰同事。那时候他在铁路局的工务段当线路工,每天面对的除了铁道就是群山。多数同事的年龄都可以给他当父亲了。一同分配来的那个同事,从没见过这样的工作环境,天天嚷嚷着要辞职。龚杰听到那些话就忍不住想笑。
当地人把那种略微隆起的土包也叫作山。他心想,这也算是山?老家就成了他宽人心的谈资。结果他这个劝人的人不声不响跑了,被劝的人至今仍在铁道上。真是奇怪。
吸完烟还刷了几个短视频,龚杰才重新回到工位。APP推荐给他的都是些游客拍到的秦岭腹地的雪景。这个冬天穿梭在秦岭的那趟6063次绿皮火车突然火了。第一次看到类似的视频时他还在深圳。时间洗去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异,有一瞬间他感到老家那片大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种感觉随着冬天的逼近愈发强烈。
在深圳那几年,为了还债,龚杰白天教学生吉他,晚上在快餐店兼职,老感觉一天24个小时不够用。只有深夜回到出租屋,才会想想自己的事情。
谢天谢地债务总算还清了。不用再为钱发愁,人就重新变得乐呵起来。家长们对他的印象几乎都不坏,孩子们喜欢和他待在一块儿。一个学生还给他起了个“娃娃头”的外号,他无端地喜欢这个外号。要做的事情见天变好,感觉真是好极了。然而自从看到老家那片大山后,过去的那种不安又回来了。
他和家人们并不是一下子就失去联系的。那阵子他老是开口借钱,钱总是不能按期还。他又不敢告诉他们实情,好在撒谎的本事练出来了。只是一次,表弟打来电话讨债,没有一点余地,他没办法只得说了实话。表弟在电话里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一条朋友圈就把他所有的事情全抖了出来。曾让家族引以为傲的大学生龚杰,如今是人见人躲的网贷者。
在快餐店炸鸡块的时候,龚杰认识了个流浪汉,大约六十岁。龚杰发现那老家伙对别的同事什么话都说,还常逗得别人哈哈大笑,可在他面前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弄得给他管饭成了龚杰每天必需的义务。不过也花不了几个钱。他上班的时候就拿当天没卖完的简餐给他,不上班的话就在路边摊随便打包一份顺路带过去。天气好的时候,两人就坐在店门口,望着深夜的街市,各自的吃食放在中间交换着吃。老人吃得很少,每次一大半的东西都要剩下来。
有一次龚杰忍不住问了句:“这些东西你带回去是吃了还是扔了?”老人睁大了眼睛,说:“当然是吃了。”龚杰就说:“看你这吃相,你一次就不能给肚子里多装点?”老人立马就反驳道:“不行。吃得越多饿得越快。”龚杰笑了。老人又接着说:“要是我把这碗饭全吃了,那最多只能顶半天不饿。如果只吃一半,就算没弄到下顿饭也不怕。饿得心慌了,一想我还有可以吃的东西,就没那么饿了。同一碗饭换个吃法,起码能顶一天不饿。而且剩饭更顶饿。一疙瘩湿米饭一口就解决了,连个米味都吃不出来。你把它晾干,干得一个不沾一个,一粒米就得嚼好半天。一粒干米顶三粒湿米,等于一碗饭变成了三碗。还能饿肚子吗?”
龚杰一下子红了脸。十五岁以后,他感觉吃撑比饿肚子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几乎没吃干净过一碗饭。以前也最烦女友问他“吃啥呀”。女友对吃的东西很挑剔,稍有不满,满桌的东西便一筷子不动。两人为吃饭不知闹过多少次别扭。老人的话耳光一样扇在他脸上。他当下就决定,在这个城市一天,就不会让老人再饿肚子。可不知从哪天起,他就再没见过那个老人。同事们都说,这种人都是四海为家,况且人生无常,突然哪天就见不到了也正常。但龚杰觉得自己还在这个城市,就得做点什么才好。于是休息日里他就四处溜达,走进一个个背街的垃圾运转站。晚上闭店,也总是最后一个走。望着窗外,可以看见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里,人们进进出出。但那个老人始终没有再出现。
或许是还记着那个老人,龚杰对见到的流浪汉都发自内心有种亲近感。为此大豪没少说他。这些年他不是不好意思联系家人,只是他们——所谓的家人们——似乎并没拿他当家人看。有时候他独自一人,一连好几小时都在思考真正的家人是什么样。
早上八点,走出操作间,疲惫一下子涌了上来。龚杰脱下工服摇摇晃晃去了卫生间,撒完新一天的第一泡尿,才发现外面下雪了。天空俨然一张脏棉被,沉重的棉絮肆意下坠。下的时间不长,地上还没坐住雪。他不打算睡觉了,准备带上吉他去桥上弹。昨晚脑袋里那段旋律,太适合在这样的画面里演奏了。
刚回眉城的時候他还想继续教学生弹吉他。而且在几个大学、中学附近租了房子。奈何一个月过去了,他连一个学生也没招到。后来他还在网吧里住过一段时间,和大豪就是在网吧认识的。大豪是附近学校的大三学生,一连几个晚上都来通宵打游戏。大豪个子高得吓人,也瘦得吓人,打起游戏来又满口的脏话,想不注意他都难。
有天晚上龚杰刚睡着就被捅醒了。“你花钱来这儿就是为了睡觉呀?”
龚杰没好气地说:“啥事?”
大豪嘴一咧说:“2K会吧?来上号!”见他没反应,大豪愣了一下又问:“《英雄联盟》呢?吃鸡总耍的吧?”
龚杰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始终没作声。“天哪,你这种人为什么要来网吧?把你烟给我来一根!”就这样,龚杰跟着大豪打了多半个月的游戏,才找到这份化工厂的工作。
第一次见到现在住的屋子,他就决定搬过来。干脆得让中介都蒙了。这个小区的房子最难出手,因为身后不远就是铁道,陇海大动脉,火车会把整个夜晚撕得稀碎。中介带着他转了几个小区,条件递减,最后似乎被他折磨得不耐烦了,直接说出来一个便宜得让他咋舌的房租数字,带他来了这里。
以前在铁路上工作时,他从没觉得自己喜欢过那份工作。如今离开铁道,却发现自己对铁道有种纯粹的爱。刚搬进屋子那个晚上,他早早躺下。没多久,火车扯着汽笛呼啸而过,大地随之抖了起来。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就像躺在一块漂在海面的木板上,摇摇晃晃仿佛可以到达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他居然舍不得就这么睡过去,直到听了四五趟火车声后,他才沉沉睡去。
他记得在铁路上刚工作那会儿,整晚被火车吵得睡不着,后来铁轨震动起来才能唤起他的睡意。等到从那里离开后,他反而再也没睡过一个好觉。
那天在出租屋里,中介脸上异样的表情一闪而过,不过还是被龚杰捕捉到了。他见识的白眼和脸色太多了,又能如何呢?想那么多干吗,自己开心就够了。这么一想,龚杰再没什么难为情,背着吉他出门了。
白天没有灯光,又下着大雪,桥上没什么闲人。正合他意。他望着河景,扫着琴弦。空气沉重,琴声传得不远,但还是吸引了几个行人。陌生的人们冻得原地跺脚,情绪却很高。他开始只是弹,后来唱了起来。上学的时候同学都叫他“歌神”,近几年虽没人叫了,但这个外号可不是白有的。一连唱了四首,最早停下来的人没有走的意思,还又聚过来一些。龚杰对这样的场景不陌生。大学四年,大小的舞台他上了无数次,每次都能收获不少掌声。现在看到有人给自己鼓掌反倒有点惧怕,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被这些掌声拍坏的。有人问是不是可以点歌,还拿着手机找他的收钱二维码。他笑着摇头说,唱首自己写的歌怎么样?昨晚脑袋里那段旋律仍在耳边回响,可他只想出了副歌部分的歌词,于是现场填词唱了起来,实在挤不出歌词就哼哼,一首还没唱下来,听的人就散得差不多了。他已经不是二十出头的愣头青,见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哪怕一丁点儿。路人的反应让他轻松了不少。面对渭河和群山,他把自己的歌逐个弹唱了一遍,过足了瘾才回屋。
一进门,龚杰就钻进被窝了。雪捂了足够的厚度,下得小了,屋子里很暖和,没一会儿身子就热了。很累但也着实开心。还能睡几个小时,他调好闹钟,闭眼就睡了。
晚上六点半,闹钟响了。脑袋晕乎乎的,洗漱的时候,看见镜子里自己熊猫一样的黑眼圈,忍不住笑了。这是这个月最后一个夜班,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一年又结束了。后面就是春节,算一算,这是自己在外独自度过的第五个新年了。以前为还债,每天过得紧张兮兮,从没有过孤单。最近他动不动就感到孤单。五年啊,这么久了吗……
感慨到一半,大豪的电话来了,问他晚上去哪儿跨年。
“晚上要上班啊。”他说。
“今晚还上个鸟班?”大豪劈头盖脸来了这么一句。
也是哦。龚杰不禁又笑了。
这几年他可以说没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挣钱的机会。不过,他决定元旦加班也是因为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事可干。大豪这么一说,他突然发现,单纯地为某个节日休息一天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的。
一个电话就解决了请假的事。龚杰重新换了身衣服。大豪意思是他们先去喝顿酒,快零点的时候去彩虹桥拍几个适合跨年发朋友圈用的照片和视频,之后就去网吧。计划得很完美,跨年夜就应该这样过。龚杰哼着曲子认认真真刮了脸,还抹了发蜡弄了个造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想小伙子还是蛮不错的嘛。
大豪一个劲发消息催他快点。因为事先没有预订,吃饭的地方可能不太好找。但也没想到这么难。他觉得又冷又饿,一开始的热情慢慢冷却了下来。大豪嫌龚杰磨蹭,龚杰埋怨大豪为何不早一点订个位子。你一句我一句,两人有点马上就要不欢而散的感觉。幸好有家火锅店在他们前面只排了三桌。大豪嘴一咧决定就这儿了。
上了桌,大豪酒杯按得低低的,一声“哥”就让刚才的不愉快烟消云散了。几杯酒下肚,两人就开始滔滔不绝。话题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回家上。大豪说下个星期就准备回家啦,学校放寒假了。龚杰就说羡慕,别说寒假了,像今晚这样的情况,他自从毕业后就很少有了。大豪一本正经地点着头,大着舌头说就是就是,他一点也不想步入社会,还说他的理想是当个作家,坐在家里。龚杰想笑又不好意思,想了想说:“干啥都行,只要是正经事。”大豪一听就不高兴了,非要他说说什么事才叫作正经事。龚杰叹口气,说:“别像我一样就行。”于是就把自己那档子糟事全给大豪说了,于是那孩子就沉默了。
龚杰不在意地举了举酒杯,表示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和自己现在无所谓的态度。大豪显然没把他的话听进去,只是追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家人,尤其是亲戚朋友已经知道了他的事情,为何还不承认。龚杰搪塞一通,不过大致说的也是实情。年少轻狂,因为借钱,被很多亲戚朋友伤了自尊心,就决定自己收拾自己弄的烂摊子。可大豪老是想听一些细节,比如当他知道龚杰五年没回家了,就问:“别人都回家过年了,你在空荡荡的城市不觉得孤单吗?”
而且龚杰已经讲到下一件事了,大豪才想起似的打断道:“原来你那会儿住网吧是没地方去,流落街头了啊。”龚杰便恼了,说:“你能不能抓住重点,我想说你现在的处境其实挺危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尤其是大学时光,贼他妈快。你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毕业以后的事了,而不是整天泡在网吧里,哪怕谈个恋爱呢。”大豪清醒了不少,说话利索多了,“我就喜歡打游戏,一天时间这么紧张,哪还有精力谈恋爱?”龚杰又气又觉得好笑,说:“那打游戏能当饭吃?”大豪一脸惊讶道:“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靠打游戏吃饭吗?”龚杰还未反应过来,大豪又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大概说了。龚杰赶紧表示自己的激动,连说:“那好啊。”大豪“啪”一声把杯子砸在桌面上,吼了一声:“好个屁。一想到毕业就要回我们那里,简直让我窒息。”
像,太像了。眼前这个少年,不就是五年前的自己吗。龚杰心想。这家伙具备想什么就敢做什么的精神,而且明显表现出对他过去几年经历的佩服。当然了,龚杰也很佩服自己。可如果回到五年前,知道一个选择做出后,要过几年那样的生活,他还敢像当年那样去干吗?现在想来,幸福的日子其实没过多久,那几年经历的事情只是隐去,稍一晃神,便如鲠在喉。和它一比,在铁道上的生活简直是天堂。他现在无事的时候,就喜欢趴在窗前望铁道,冷峻的铁轨,让他平静,心绪淡泊。想些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就只是发呆。
这时,大豪似乎意识到刚才的失态,沮丧地说:“我父母是非常强势的,别看我在你面前这样,在他们面前我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不知怎的,他们越是规划我的未来,越想把我按在笼子里,我就越想挣脱。”龚杰直盯着大豪,说:“我咋越听越来气呢?”大豪眼珠子一下子就突出来了,说:“你生哪门子气?”龚杰只是苦笑,完了严肃地说:“我不想依赖任何人。这种话都是从那些有人可以依靠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大豪不耐烦地打断道:“怎么不是,你以为只有你有理想?”龚杰摇了摇头,说:“你那不是理想,我这也算不上理想。”大豪热乎乎带着酒气的口气飘了过来,语气却是冰冷的:“你确实太失败了。不明白你怕啥呢,才三十岁就把自己关在那个化工厂里铲那些鸟药粉。”
龚杰有些不高兴了,说:“你的意思是我就没机会再拿起吉他了?你的意思是这么大的城市,我连一个学生都招不上?”大豪连忙又说:“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总是只想着教别人吉他,不能认为这样就是好的。那么多酒吧、广场,你去混混嘛,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去试试嘛。”大豪看龚杰没什么兴趣,就说了一堆想法和具体实施的细节,扬言这些事情自己都能帮上忙。龚杰笑了一声,说:“这就打算跟我干啊,还说自己是有理想的。”大豪想说什么,但筷子在空中划了几道,最终没作声。龚杰就安慰道:“这些都是填饱肚子以后的事。总之,要是我有个能为我规划未来的父母,我就不折腾了。不过,我不劝你,你爱咋折腾咋折腾。成了更好,成不了,你父母不是把什么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吗,回家呗。”大豪就问:“你怎么不回家?”轮到龚杰失语了,他还没有正式想过这个问题呢。
当初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辞了工作,和几个大学同学合伙开了家吉他店。结果不到半年就关门大吉,并且落了一屁股债。他打电话给姐姐,虽不怎么联系,也不常见面,但姐姐还是给他打了路费,希望他来她这边,再想别的办法。姐夫在他们当地县城有一家饭店,是那种只能摆四五张桌子的小店。知道他来帮忙,姐夫自然高兴。
一开始,姐夫还不太好意思使唤他。但情况很快就不同了。姐姐撒谎说他还未正式工作,出来锻炼锻炼,要丈夫按月给他工钱。店里的事情龚杰干得一塌糊涂还累得要死。姐夫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很多次就差说让他滚蛋的话了。有一次,姐姐去参加家长会,而那个该死的中午,店里连一个客人也没有。整个中午,姐夫的眼神针一样扎得他不安。他坐着的时候扎他,站着也扎,不坐不站走着还扎。龚杰担心这么下去,有一天会忍不住揍姐夫一顿,于是给姐姐发了信息,离开了。
龚杰比一般男孩敏感,自尊心又很强。小时候被父亲当着旁人训一句就会难过一整天。而父母呢,总是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或许并非自己父母的过错,那片大山里的父母好像都是这样。他长大后,和父母之间的交流很少能超过十句。正因为此,事情刚开始变化的时候,他根本没想过要让父母替他收拾烂摊子。
吃饱喝足,两人互相挖苦着,摇摇晃晃溜达着。跨年之夜,桥上挤满了年轻人。龚杰心想,哪一年不糟糕,不然怎么那么多人提起“去年”都感觉比“今年”好呢?但人们迎接新年的仪式感从未缺席。希望和期待在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是肉眼可見的。老家的人们肯定不会为这么个晚上兴师动众。就连春节也早已变成了累人的事儿。那片大山的麻木是深入骨髓的。他突然理解了姐姐和那些立志走出大山的女孩儿们,也谅解了那些留在那里的伙伴们。他从来只考虑自己那些年是怎么过的,未曾想过家人们这些年是咋过来的。要是他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妈妈那句就当没有儿子了,表弟的热嘲冷讽,亲戚朋友的冷漠……这样的场景每想起来,他内心还是会咯噔一下。总有一天,时间会解开这些疙瘩吧?虽这么想,可他还是没有冒险的勇气。
大豪本在拍一群大妈跳鬼步舞,拍着拍着就跟着跳去了。别说,跳得还真像那么回事。这家伙真是个活宝,好像永远长不大。反正不像个成年人。高兴的时候笑得满脸肉在动,不高兴了发几句牢骚就完事。龚杰由衷地佩服,这种人无论在哪里都能交到朋友。有朋友就好。
龚杰掏出手机拍下了他的第一个短视频。再有两个多小时就是新年了,他突然想大喊一声“新年快乐”。正想着,就有一双手环抱住他的腰,接着他就被拦腰抱进了广场舞的行列。他才发现当个活宝居然如此快乐。
他们两人踢踏着步子,像是要把那些挡在面前的障碍物一个接一个踢开似的,都铆足了劲。两人趁着酒劲尽情撒欢,直到精疲力竭,卧倒在地。“我想回家了。”龚杰说。大豪“哦”了一声,说:“早该回去了。”
龚杰摸出手机,输了一串号码。空号。又输了一遍,还是空号。手抖得太厉害。应该不会记错的。然而还是空号。别再为家里没人寻找你伤心了,他暗想。
大豪拍了他一把。他盯着键盘又输了一遍,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嘟——”了一声,那声音像静电一样打在他手上,他立马挂断了。打开微信添加好友,把号码粘过去,点击搜索。舅舅用自己的照片作头像,老得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但还是舅舅。龚杰搓着手机,望着大豪笑了。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薛文捷,男,1996年生。有小说见《延河》《都市》《中国铁路文艺》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