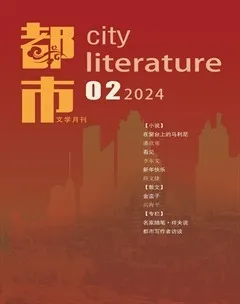在窗台上的马利尼
马利尼是那天下午坐在窗台上看到那一大片树的。看到那一大片的树时,马利尼吃了一惊。那里不久前还是一片由废砖、瓦砾等组成的光秃秃的高台,他记得。
马利尼没事儿的时候,便会坐在窗台上,盯着远处看。马利尼坐的窗台,在一座楼房六楼东面北边的一个房间。那座楼一共有六层。房子是马利尼的父母住过的,不过现在住在里面的是马利尼。马利尼坐在那里的时候,让人看了心惊肉跳。他吊在外边的两条腿,总是不停地晃啊晃的。但是马利尼自己似乎一点不害怕,两条胳膊抱在胸前,像个大虾弓着上半身,还微微地向外倾斜着,似乎准备离开窗台似的。
马利尼坐在窗台上朝外面看的时候,通常会让自己的视线像国王巡游,先穿过眼前像梯田一样灰扑扑而矮趴趴的楼房,再看向远处那些高一点的楼房,然后是远处的,更远处的,一直到看不见了,再将视线从另一边绕回来,由远及近的,最后看向中间的土台。马利尼一般不会先看那个土台,虽然那土台,就在他视线的正前方,他一抬眼就能看见。也有例外,马利尼有时也会让自己先看向那个土台,然后视线像涟漪似的,一点点荡向外面。不过那样做的时候很少,极偶尔的。
马利尼那天傍晚在看到那个土台变成了一片绿幽幽的树木时,有些惊讶。那样大的一片树,应该不是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是几个人。要有一大群人,花费一大段时间,可是马利尼居然没有发现,好像那些树一直在那里,他没有注意而已。后来,马利尼在盯着那片树看的时候,心里的一个疑惑也跟着冒出来:那个土台周围全是密密麻麻拥挤不堪的楼房,看上去连一根针都插不进,那些人是怎么进去的?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马利尼一直都在盯着那片树看,直到夜幕一点点笼罩了那片树。
此后,马利尼再坐在窗台上,便很少让自己去看那些灰扑扑的房子了。他的眼睛会盯着那些树目不转睛地看。马利尼在看着那些树时,那些树好像也在看他。早晨,阳光照在那些树木上面,那些树便像在朝他眨眼睛。
马利尼喜欢上了那些树。不过马利尼并不总是能看到那些树。事实上马利尼很少在家里,也很少有机会坐在窗台上。
马利尼供职于一家广告公司,他在那儿做文案。在那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的人很多,有几十个,马利尼是其中的一个。或许马利尼在那家广告公司并不起眼,他不怎么爱开口,做的文案也效果平平。那些文案交上去后,多数像石沉大海一样,很少有响声。如果不是马利尼那两条像竹竿一样的长腿,也许不会有人想起他。马利尼的两条腿又细又长,比一般人的要长上一大截。那两条腿让马利尼看上去像鹤一样,在人群中高高地直立着。马利尼走路,也像鹤,挺着胸,踢腿抬臀的,好像要故意引起人注意似的。马利尼有运动天赋,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动员过他,希望他改练体育。可是马利尼的家人不同意,他们希望他继续学文化课。最后马利尼考了一所普通的专科学校,类似技校那种的。他家里人有些后悔,有时会想马利尼如果改练体育会怎样。不过马利尼自己倒无所谓,他对任何事情都抱着那样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马利尼的朋友不多。唯一算得上他朋友的,是广告公司跟他座位紧挨的老黎。老黎胖胖的,跟马利尼不一样,老黎爱说话。两个人相同的是,文案都做得不好,很少有显山露水的时候。不过老黎似乎不太受那事的影响,他的文案被毙了,也会像没事人一样,请马利尼喝酒。喝酒的时候,老黎便会对马利尼说起他老婆的事。马利尼怀疑老黎的老婆在外面跟人有一腿,虽然老黎没有明说。
马利尼自己也有一个情人。也许他不应该叫她“情人”,她是马利尼的女朋友,可是马利尼喜欢在心里那样叫。马利尼的“情人”(按照马利尼的叫法)在超市做收银员,有时候会过来。她过来的时候,马利尼会跟她一起吃饭,两个人有时也会一起睡觉,倘若她留下来的话。马利尼不确定她是否会跟他结婚。马利尼感觉她在外面有人,不過是否这样,他并不能断定。或许只是自己心里感觉。
马利尼平常在广告公司坐班,只有周末时在家。马利尼上班的时候,很少有机会坐在窗台上,他回家的时候通常已经很晚。回到家,吃点饭,洗漱一下,便上床睡觉了。马利尼有时会在家里做饭,不过那多半是周末,他的“情人”过来的时候。平常,马利尼下班后,会在离家不远的老街角买上一个寿司,里面夹几片生菜还有一点酥酥的硬硬的肉沫那种的。马利尼边走边吃。等走到家,寿司便也吃完了。偶尔的,马利尼会带回家,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泡脚,一边吃寿司。吃完寿司,他便关上电视,去刷牙睡觉了。马利尼一般不熬夜,他到家时,便困得要死了,没有精力再熬夜。
马利尼不喝酒,不抽烟,也没有特别的期待。他的“情人”有家里的钥匙。她想过来时,便过来。不想过来,马利尼也不会特意打电话叫她。
马利尼唯一的癖好——如果那算是癖好的话——就是坐在窗台上,一边将两条竹竿似的腿垂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晃着,一边看着外面。其实马利尼不用坐在窗台上,也能看见外面。可是马利尼喜欢那样做。马利尼的两条腿已经够长了,他坐在那里,有时会在心里想象着,他的腿顺着下面的墙壁在长。如果他的腿能长得足够长,马利尼想,或许便能碰到地面了。那样,他就有六层楼高了,再走在街上,所有的人便会仰着头看他了。
不过马利尼知道那是痴心妄想。他在那里想一会儿后,便会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收回来。
马利尼心里想着那片树。有时做着文案,马利尼会突然想起那片树,然后,他便会将头从正在做的文案中抬起来,朝外面看。马利尼坐的位置的窗户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广告牌的正面,是一个嘴唇涂得红红的女人穿着一件性感的内衣的巨幅照片。不过马利尼看不见那个女人。正对着马利尼的,是那个广告牌的内侧。广告牌的内侧,落上了白色的鸟屎,还缠着一些白色或者黑色的垃圾袋什么的。那幅巨型广告牌将马利尼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的,马利尼什么也看不见。马利尼在盯着那块落满鸟屎和垃圾袋的巨型广告牌的内侧看时,会想象着正面女人涂得红红的嘴唇,然后再想到嘴唇下面。不过马利尼不会让自己想得太远。他曾经买过一盆多肉,放在自己的案几上。只是那盆多肉不久便死了。不知道是因为见不到阳光,还是因为马利尼。马利尼在那里写着文案或想着事情时,会抬头看看它。一看到它,马利尼便会从座位上站起来,拿了案几上的杯子,去洗手间接了水,给它浇。
马利尼之前晚上从来不往窗外看的,外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在马利尼发现了那片树后,晚上回家,他都会走到窗台那儿,朝外面张望一会儿。那片树所在的地方没有灯,看上去比别的地方还要黑一些、暗一些,好像一个看不见的黑洞。马利尼站在那里,盯着那个黑洞看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随着那个黑洞一点点往下落,往下落,落到深不可测的地方了,便将视线由那个黑洞一样的地方,转向一幢幢被灯带勾勒出漂亮轮廓的楼房,和楼房上一个个亮着灯的房间。
马利尼每天晚上都会想着那些树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感觉那些树就在他的身边,他拥抱着它们。马利尼不经常做梦。他希望自己能够做梦,可那样的情形很少光顾马利尼。有一次,马利尼终于做梦了,他梦见了那些树。他站在树下面,阳光透过树的缝隙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马利尼眯着眼,仰着头,看着那些被像花朵的触须一样的阳光包围的树木。不过马利尼很快醒了,醒了后,他不知道那究竟是梦,还是自己想的。
那个周末,马利尼坐在窗台上,没有像往常一样让自己的视线再做巡游,他先看了一会儿远处楼房上面的天空,然后是跟天空相接的戴着帽子的楼房,再之后是下面矮一点的楼房,最后是被灰色的楼房所簇拥的树。
那片被楼房簇拥在中间的树,宛如一颗巨大的心脏。左右两边深色的部分,是左心房和右心房。跟左右心房相接的下面凹陷的地方,是左右心室。将那片树木勾勒出椭圆形轮廓的灰扑扑的房子,是心脏外面的肌肉组织。一排排深色的树木,则好似血管。
马利尼端详着那颗巨大的心脏时,似乎能听见它在那里“砰砰”地跳。夜里,马利尼也会听见异样的响声。有时是“咚咚咚”的,有时则是“砰砰砰”的,像啄木鸟啄食树木虫儿的声音,又像一个人敲门的声音。马利尼有时会从床上爬起来,循着响声,走到窗前,朝那片黑魆魆的树木看过去。
那颗“砰砰砰”或者“咚咚咚”跳动的巨大的心脏,仿佛一把尖锐的小锤,撞击着马利尼的心。让马利尼的心里,生出撕撕拉拉的疼。仿佛身体下面的脐带,一扯一扯的。
马利尼现在不仅晚上回家会朝黑乎乎的外面看看。他在早上离家准备去广告公司上班时,也会先朝那边看一会儿。新鲜的一起一伏的心脏,像在召唤马利尼。
那天夜里,马利尼躺在床上听着从远处传来的如同海浪撞击礁石的“砰砰砰”声,想象着被一层层绿色包裹的巨大的心脏,在那里一起一伏地跳动。马利尼萌生了去上面看看的想法。
马利尼瞅着那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通过那些密密麻麻、看上去连针也扎不进去的楼群,他怕自己在里面迷失。马利尼是个路盲,他之前便总会在一些巷子中迷失。在那些楼群和那片树之间,也不太可能有路,那个地方那么逼仄,倘若再有一条路,会让那个地方更加拥挤。
马利尼瞅着那个地方看了几次,他找出一架高倍望远镜。那架高倍望远镜是他父亲留下的。马利尼的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天文爱好者,小时候,父亲经常将那架高倍望远镜搬到楼顶,夜里,他带着马利尼一起在那里观察天狼星。天狼星是北半球夜晚最亮的恒星,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和路上的旅人都依靠天狼星来指引方向。
马利尼将那架高倍望远镜放到窗台上,对着那个地方,仔细观察。那里的楼房一幢接一幢,彼此之间就像连体儿一样,看不出一丝缝隙。在小区里面,有一些弯弯绕绕的路。不过在那些小区之间,似乎没有路相通。
马利尼不死心,他再将望远镜的镜头对向那片树和附近的建筑。在那片树的周围,他发现了一圈的铁皮护栏,将那片树包裹得像铁桶一样。马利尼不相信没有路通到外面,否则那些绿化工人没有办法进去将那些树栽下。马利尼在那圈铁皮护栏之间,像蚯蚓翻耕泥土似的仔细搜寻。他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在两片不起眼的铁皮护栏之间,终于看见了那把锁。
即使他侥幸通过那片密密麻麻的楼群,找到了那条通往树林的路,还是没有办法进去。除非他像鸟儿一样有一双翅膀。
那架望远镜一直放在窗台上。马利尼每天早晨起来,便会走过去,对着镜头朝那片看一会儿。早晨的树林,带着露水,像块绿色的翡翠。在那些树的下面,有蓝色的牵牛花,在风里摇曳着。他还能看见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的鸟儿。马利尼的镜头时常追逐着那些小鸟。一只额头的羽毛呈深蓝色的小鸟,脖颈上像点了红色的胭脂,脸和背上的羽毛则是翠绿色。马利尼经常看见它出现在一棵白蜡树的枝丫上。
那片树林在早上和下午的风景不同。马利尼很快发现,早上树林刚刚从一夜的睡眠中醒来,带着露水和朦胧的雾气,像一位羞涩的少女。下午,树梢上的水分蒸发了,加上黄昏的光线笼罩着树林,在周围那些灰扑扑的楼房的映衬下,树林就像一位成熟而风度翩翩的男子。
而夜里,马利尼便会听见从树林中传来的像擂鼓一样“咚咚咚”的心跳声。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马利尼都是在那架望远镜和树林之间度过的。
马利尼的“情人”很久没有来了。那天晚上,她过来了,看见马利尼盯着那架望远镜看。她走过去,在镜头里看见了那片单调而乏味的绿色,转身去厨房了。之前做饭的事都归马利尼。她做好了饭,去喊马利尼吃饭,马利尼还在那里弯着腰,瞅着镜头。她吃了饭走了,两个人连爱也没有做。
马利尼一直想着那片树林。有天夜里,他被从树林里传出的“咚咚咚”的响声惊醒了,没有再睡着,又萌生了那个念头。
那念头折磨着马利尼。
马利尼在上班时总是走神。别人都下班走了,他还待在那里,手头的活没有完成,他不能离开。
马利尼待在广告公司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单位,却最后一个回家。上床的时间越来越晚,而上床后,总在那里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了,有时候又会被梦里的声音惊醒。马利尼醒了后,便会走过去,将头凑到窗户的玻璃上,看着黑魆魆的外面。
马利尼因为夜里睡得太少,白天坐在那里,便会犯困,困得要死。有时候坐在那里,马利尼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马利尼害怕让别人发现自己上班时睡觉,可是他太困了,无法抵挡住沉沉的睡意。马利尼开发出了一项新的技能:睁着眼睛睡。那项技能让马利尼很得意,因为谁也想不到一个人会那样做,那让马利尼侥幸逃过了一些窥视和苛责。不过有一次,马利尼又在那里睁着眼睡,别人没有发现,他自己从座位上摔下来,在额头上磕了一塊疤。这回的事引起了注意,马利尼睁着眼睡觉的事很快暴露了。后来,马利尼准备在那里故伎重施时,便会被拳头砸在桌子上“砰”的巨大声惊醒。有一次,马利尼的额头上还吃了几个栗凿。
马利尼在不知道晨夕的晦暗不明中昏昏度日。他经常分不清上午、下午,甚至不知道是否醒着。他有时会在半夜突然醒来,夹起包,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等走到外面,发现天还黑着,再彷徨着走回来。而白天他又昏昏沉沉的,总感觉自己睡不醒,被缠绵的睡意和困倦缠绕着。或许因为总是睡不醒,马利尼的脸变得苍白、沉郁,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上几岁。
生物钟紊乱,致使马利尼的工作效率低下,他不得不把白天在广告公司做不完的活,带回家做。因为熬夜,马利尼早晨总是很晚才能醒。而醒来时,已经快到了上班时间,马利尼连在路上停留买个早餐的时间也没有,只好饿着肚子去上班。
马利尼感觉自己就像一座岩浆快要喷发的火山,他明白自己要撑不住了。
上次见面后,马利尼的“情人”没有再来找他。不过马利尼又庆幸她没有来,否则他那副整天睡不醒的样子,再见了她,不知道该以何种面目相示。老黎则因为老婆要离婚,每天无精打采的,如同丧家犬。看到老黎那副如丧考妣的样子,马利尼在心里对他暗表同情时,又觉得自己没有结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否则也许更惨。
没有人倾诉心事,马利尼觉得出去休息一段时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觉得只有南方的酷热,才能配得上自己心里的焦躁。
马利尼想象着躺在南方的海滩上,火辣辣的阳光一股脑地泼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像“哧啦哧啦”的热油锅,冒出白色的烟雾。然后他又想象着悬崖蹦极,倒立的身体随着身上的绳索看着犬牙交错的悬崖峭壁和深不可测的山谷。
那天下午,马利尼坐在那里,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便从广告公司离开了。
马利尼回家后,上了床。他想让自己睡一觉。马利尼觉得自己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睡好的原因,等睡一觉,醒来,就好了。马利尼想。
可是马利尼在那里辗转反侧,没有睡着,便爬起来,又走到窗前。那一大团椭圆形的像翡翠又似玛瑙一样的绿色,在那里像被吹起的涟漪,轻轻起伏。马利尼的心又跟着摇曳起来。
也许那想法并非不能实现,马利尼目测了一下从他的窗户到那地方的距离,它们之间大约有两三千米,或许更远一点,也或许更近一点。人的视觉会有误差。
如果他能在助跑后,冲上窗台,然后从窗台开始起跳。马利尼一边在心里臆测着那段距离,一边想着那种可能。他在学校里总是跳得很远,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跳到沙坑的那头。有一次,马利尼不知怎么的,像飞似的,让自己轻轻松松地越过了整只沙坑。老师和同学看了大吃一惊。他们纷纷走上来,围着马利尼,拍打着马利尼的身体。那是马利尼整个学生时代难得的高光时刻,那一幕过了很久,马利尼依然记得。那会儿,他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嘴上的毛还没有长出来,个子也没有现在一半高。现在马利尼光那一双竹竿似的腿,便已经比那会儿的个头都要高了。如果那时他能轻松地越过一只沙坑,那么现在也应该能跳过从窗口到那地方的距离。
马利尼需要确定的是让自己万无一失。如果他不能让自己安全地越过那段距离,那么他所做的尝试便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须保证自己不在中途跌落或者出现闪失。
要保证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而且万无一失,意味着他要有足够的冲刺速度,让自己先冲上窗台,再在窗台上,借助第一次起跳的速度,完成第二次起跳。
马利尼遇到了难题,要保证有足够的冲刺速度,必须要有足够的距离,让自己冲起来。这就像飞机起飞前需要一段长距离的滑行,让飞机达到某个速度,然后借助这个速度让飞机获得足够的升力。可是马利尼的房间,只有60平方米。从中间的走廊到北面房间的窗户,连5米都不到,那距离不能让他获得足够的冲刺速度。马利尼即使凭借自身的力量勉强冲上窗台,他在到达窗台,准备第二次起跳时,会在那里有一个短暂的停顿,那也会让他消失一部分速度。如果他的速度这时冲不起来,势必会影响他的第二次起跳。
马利尼感觉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它不能保证自己安全地到达那里。不过马利尼随即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或许他可以借助滑索。
在他的房子和途经那地方的房子之间,拉一道滑索,只要他在经过那地方时跳下来。马利尼高兴地想着,他甚至为自己的这个想法自鸣得意了。这想法看上去比前一个想法还要可行。只要滑索足够长,他甚至可以不用考虑去那些拥挤不堪并有可能让他迷路的楼群间,去找一个拴滑索的地方。他可以到一个远一点的空旷的地方,只要确定中间经过那地方就行了。
马利尼在感觉到那个计划可行后,开始着手就计划的细节、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推敲。那计划看上去并不难,他发现,只要有一道滑索,再确保滑索经过的地方、两头的房子,三点一线就行了。
搞一个滑索很容易,在随便一个滑索批发市场就能买到。滑索的一头拴在他的屋子外面,另一头拴的地方,则需要他去做实际勘察。找到一幢房子应该不会很费劲,可是他不能保证房子的主人会答应。
然后他在如何就選中的房子说服主人答应他架设滑索,费了一番思量。那不是他的强项,他不善于跟人打交道。不过他决定放弃这个问题,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他可以对房子的主人说一顿好话或者求情,再不行,他还可以给房子的主人一点钱。倘若还不行,他便考虑找一幢不是私人的房子,譬如电力或者烟草公司的大楼。
他还需要一架梯子,那梯子必须保证他能到达六层楼高的房子外面。要将梯子带到那里,他还应该有一辆带斗的货车。那车斗也要足够长,长得能将梯子装下。他还需要一个帮他架梯子的人,他不能保证自己能将那架梯子架好。或许他还需要一个扶梯子的,以保证他在那里拴滑索时,梯子不会歪倒,而他也不会从梯子上摔下来。
那些或许都不难搞定,他曾经在路上看见过车盘长长的拖挂车。而帮他拉梯子、架梯子、扶梯子的,可以是一个人。
不过他在想到如何将索道的一端在自己房子的外面固定好,将另一端带到选中的房子时,感觉有些棘手,他不能拖着绳索在道上走,那对行人和车辆都是一个威胁,警察不会不过问的。也许他可以绕开那些道路,可是后面的问题跟着来了,他能否在空中拉一道滑索?
要知道那个做法是否可行,打一个电话就能知道。马利尼不善于跟人交流,但是在电话里,对方看不见他,所以马利尼不怕。
电话打过去,回答是NO。要建一条索道,要先立项,再等待文物主管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建设部门、市场监督部门、特种设备中心等几十个部门的审批,马利尼害怕别人在电话里听出他的声音,捏着鼻子说,何必那么麻烦,他不过是想拉一条绳索。电话那头听到马利尼这些无知的话,忍不住笑了。那还是在居民区拉索道,如果索道经过的地方在军事管辖区,则还要向军事和空管部门申请。
马利尼的热情被那通电话浇灭了。
马利尼对那个计划失去了兴趣,不过马利尼没有太在意,人总有些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马利尼决定放下后,仿佛解脱了,一下子变得轻松了,睡意也跟着来了。马利尼很久没能痛痛快快地睡一个好觉了。马利尼感觉困扰自己的,也许都是长时间没能睡一个好觉。
马利尼这次躺到床上,很快睡过去了。他睡得很沉,打着很响亮的呼噜。呼噜声透过楼板,传到了外面。邻居不堪其扰,纷纷跑过来,大声地敲着门。震天动地的敲门声,没能将马利尼叫醒。后来,他的“情人”来了,被马利尼的呼噜声吓了一跳,她叫了一顿,没将马利尼叫醒,便捏住了马利尼的鼻子。马利尼喘不上气来,睁开惺忪的睡眼看了看,像梦呓似的嘟囔一声,又再睡去了。
马利尼醒来时,是几天后的早晨了。他起来,对着镜子照了照,感觉自己像个山顶洞人。脸颊消瘦,眼窝深陷,眉骨和颧骨高突。马利尼随便洗涮了一下,刮了像杂草一样的胡须,然后走到老街口那儿,买了一个寿司,一边吃着,一边夹着包去广告公司上班。
路上,马利尼还有些心惊胆战,他担心自己几天没有去上班,公司会不会将他除名。等马利尼到了单位,看到他的座位还空着,茶杯也还在桌子上。坐下后,也没有人过来问他为什么这几天没有来,或者去干什么了之类的。马利尼若无其事地松了一口气,也许压根儿就没有人发现他离开。
马利尼不再在周末或没事的时候坐在窗台上了,也不再往外面看了。
没事的时候,马利尼就跟老黎一起去钓鱼。老黎离了,约马利尼去钓鱼。他们钓鱼的地方有一片芦苇,那地方有很多草鱼。老黎一个上午能钓上来十几条。马利尼却经常一条钓不到。不过马利尼看上去不在乎,那天,他在钓鱼时感觉手里的钓竿沉甸甸的,以为是一条大鱼,等拖上来,发现是一条装满了淤泥的鞋子。那只鞋子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到马利尼的钓竿上的。他和老黎一起盯着那只脏乎乎的鞋子看了一会儿,然后老黎便开始放肆地大笑。老黎笑的时候,牙花子都露出来了。马利尼直勾勾地看着老黎,他不知道老黎为什么笑,也不知道这事究竟有什么好笑的,可是马利尼不想让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便也跟着老黎笑。可是他的笑,像猿啼似的,尖利、刺耳,如同女人的脸上长出胡须一样,连水里的鱼也被吓跑了。老黎让他闭嘴。
不钓鱼的时候,他们便会骑单车,往城郊的“小山”进发。那座小山,是一个大土堆,老黎管它叫“小山”。他们到了那个土堆后,老黎便会四肢摊开,躺在那里,仰面瞅着天。马利尼则会一边嘴里嚼着草,一边在草丛里翻找蚱蜢。
马利尼的“情人”还会时不时地过来。她过来时,两个人就一起吃饭。吃完了饭,便会躺在床上。马利尼的手,像在草丛里翻找蚱蜢一样,在她的肋骨、胸骨、平坦的小腹和上面高耸的胸部之间,慢慢寻找着她的乳头。摸到了,便放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握一会儿。一天晚上,马利尼在广告公司加班,回家晚了,路过一家商场。马利尼在那家商场旁边的一处阴影里,看见他的“情人”踮着脚尖,在跟一个男人热烈地拥吻。马利尼悄悄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她再过来时,马利尼什么也没说。
那天早晨,马利尼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那声音,像从草原来的风掠过城市,又像一把急骤的琴弦划过夜空——马利尼被那个嘈杂的声音惊醒了,却没有起来,他躺在床上,视线从窗外的阳光,慢慢看向窗棂,再落到放在角落里的钓竿上,那个念头再一次破土而出。
如果他借助一根竹竿,或许可以到上面去。
马利尼在学校练过撑竿跳。他的撑竿跳又高又飘,像鹞子翻身。而且那些要领,他也熟记在心:持杆助跑、插杆、起跳、腾空、落到地上。他喜欢在插杆的一瞬间,让身体凌空飞翔的感觉。
只要竹竿足够长,或许他连助跑都不用。
马利尼去弄来了一条竹竿,先在附近的一个操场上练了几天。比起十几年前,马利尼除了身体长高了,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他依然身轻如燕。马利尼需要做的是,如何让自己跳得更远一点,然后稳稳地落到那里。
马利尼练了一段时间后,又去搞来了几十条竹竿。他将那些竹竿一根一根的,用铁丝严丝合缝地扭在一起,以防它们在自己起跳时扎了他的手,他再将铁丝捆扎过的地方,用布一层层包裹了。几十条竹竿捆扎在一起,比他住的楼都要高了,几乎捅到云彩里面去了。马利尼将它放在窗户外面。怕风将它吹倒,他用绳子绑在了窗棂上。
一切准备就绪了,马利尼却没有急着跳。他每天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窗前,将头伸到窗户外面,仰着脸,看看外面的那根竹竿。竹竿上,挑着一片片洁白的云彩,好像那根竹竿开了花。
马利尼仍旧像以前那样上班、下班。下班后在老街口买个寿司,然后一边吃,一边往回走。回家后,看着电视,泡一会儿脚,然后刷牙,上床睡觉。
那根竹竿不知道是不是放在那里久了,似乎在慢慢返青。
那个周末,马利尼起了床,先去老街角买了一个寿司,吃了,又去理发店理了发。回家后,马利尼先给老黎打了电话,告訴老黎,自己不能陪他去钓鱼了。老黎在那头“喂喂”地追着问,马利尼究竟什么意思。马利尼挂断了电话,又给他的“情人”打。电话通了,没有人接。
马利尼不想再等了。他将绑在窗户上的竹竿解开,上了窗台。马利尼站在窗台上,朝那片树看了看,然后闭上了眼,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持竿、起跳、腾空,一切没错。马利尼已经越过了车水马龙的街道,也越过了那些高高的密不透风的楼房,那片树就在不远的地方了。
马利尼将手里的竹竿插在地上,已经腾空而起了,却发现自己跟那片树之间,比看上去要远。在他和要去的地方之间,有一个坑。那坑似乎是建筑工人在挖一处地基时留下的,坑外面的土,还没有埋上。马利尼眼看着要落到那个坑里了,他想象着坑边的土埋到自己身上。这时那条被马利尼扔掉的竹竿在天上翻了一个筋斗后,突然飞过来,插在了他面前。马利尼趁机抓住它,骑在了上面。
马利尼跟那根竹竿贴合得如此紧密,就像长在了上面。有风吹过的时候,马利尼便会随风起伏,就像在朝人招手似的。如果你恰好跟马利尼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打开窗户,便能看见骑在竹竿上的他。
责任编辑 梁学敏
作者简介:
潘欣寒,女,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小说在《延河》《海燕》《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短篇小说》等刊物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