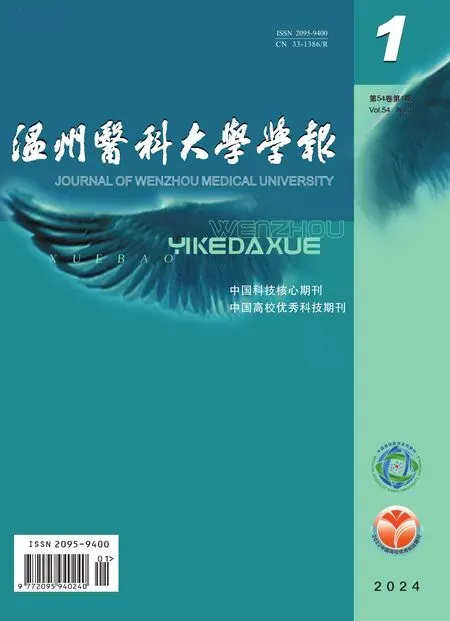迟发型遗传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1例
方玮玥,姚荣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血液科,浙江 温州 325027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TTP)是由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蛋白酶(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inase with thrombospondin motifs 13, ADAMTS13)活性缺乏导致微血管血栓形成,从而引起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发热、心脑肾等脏器功能障碍的一类血栓性微血管病变。根据不同的ADAMTS13缺乏机制,将TTP分为遗传性TTP(cTTP)及获得性TTP(iTTP)两种[1]。大部分cTTP患者从儿童期开始起病,少部分直到成年才发病,中老年发病的cTTP更为少见[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收治了1例老年发病的cTTP患者,现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73岁,因“神志改变伴皮肤黄染1个月”于2022年5月21日入院。患者1个月前开始出现神志改变,表现为反应迟钝、嗜睡,伴皮肤眼白发黄,未予处理,后皮肤黄染程度加重,尿色加深,遂至我院就诊。急诊血常规:白细胞计数5.41×109/L, 嗜中性粒细胞比率0.687,血红蛋白91 g/L(↓),血小板计数23×109/L(↓);血生化:总胆红素108.7 μmol/L(↑),间接胆红素101.4 μmol/L(↑),肌酐110.5 μmol/L(↑);以“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高胆红素脑病可能”收住我科。既往史:1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2019年起多次脑梗死病史(遗留口齿不清),父母非近亲婚配。发现血小板减少8年,曾有输血小板史,2018年至我院完善骨髓常规提示骨髓巨核细胞产板功能欠佳,考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2021年4月因“黄疸伴血小板减少”入院,再次复查骨髓穿刺提示产板巨核细胞少见,考虑Evans综合征。
入院查体:体温37.6 ℃,脉搏100次/min,呼吸19次/min,血压150/85 mmHg(1 mmHg=0.133 kPa), 嗜睡,反应迟钝,口齿含糊,对答部分切题,双侧瞳孔大小正常,对光反射稍迟钝,皮肤巩膜黄染,右眼睑可见瘀斑,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心肺听诊无殊,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四肢可见活动,病理征未引出。入科后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4.31×109/L,血红蛋白76 g/L(↓),血小板15× 109/L(↓),网织红细胞计数123×109/L (↑);外周血涂片提示易见红细胞碎片;CRP 9.17 mg/L;血生化:直接胆红素7.6 μmol/L(↑),间接胆红素94.2 μmol/L(↑),血肌酐121.6 μmol/L (↑),乳酸脱氢酶666 U/L(↑);Coombs试验阴性;凝血常规均正常;抗磷脂抗体及狼疮抗凝物均正 常;自身免疫系列抗核抗体弱阳性,其他未见异常;CEA 7.59 ng/m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17.8 ng/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3.87 ng/mL(↑),其余肿瘤标志物在正常范围;头颅MR提示左侧顶叶侧脑室旁、小脑蚓部及左侧小脑新发腔梗灶。
患者入院后予地塞米松针10 mg qd静滴免疫抑制治疗。2022年5月27日回报ADAMTS13活性<1%(frets-vwf73法,参考值70%~120%),检测到抑制物滴度0.89 BU(参考值0~0.6 BU),考虑为iTTP,立即转至重症监护室行血浆置换。于5 月28 日行1 870 mL的血浆置换,5月29日输注新鲜冰冻血浆140 mL后,继续予地塞米松针10 mg qd静滴。5月30日复查血常规血小板恢复至117×109/L。遂转回我科,复查血小板185×109/L,乳酸脱氢酶353 U/L,复查ADAMTS13活性为17.3%,抑制物滴度<0.6 BU,考虑病情好转于6月6日出院。出院后予地塞米松片10.5 mg qm口服。
出院后患者定期随访。2022年6月23日门诊复查血小板为23×109/L(↓),于6月24日再次住院。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9.31×109/L,血红蛋白95 g/L(↓),血小板29×109/L(↓);血生化:直接胆红素7.6 μmol/L(↑),间接胆红素27.6 μmol/L (↑),乳酸脱氢酶559 U/L(↑)。送检TTP基因,并于6月25日予利妥昔单抗700 mg免疫抑制治疗。 6月29日复查血小板为17×109/L(↓),再次转重症医学科行血浆置换(6月30日1 970 mL,7月2日1 490 mL,7月5日2 050 mL)。7月7日复查血常规血小板为173×109/L,乳酸脱氢酶269 U/L,遂转我科。7月8日再次予700 mg利妥昔单抗针治疗。7月10日患者出现肺部感染,予暂停利妥昔单抗针治疗,后因感染反复先后予多种抗生素抗感染,期间血小板降至56×109/L(↓)。7月21日患者基因检测回报为chr9:136321272 c.3650T>C纯合错义变异,诊断为cTTP,于7月22日开始多次输注新鲜冰冻血浆(7月22日450 mL,7月31日360 mL,8月2日260 mL,8月13日570 mL),血小板恢复至85×109/L,8月16日出院。出院后患者根据血小板变化情况定期输注新鲜冰冻血浆,输注后血小板均有恢复。末次至本院输注时间为2023年2月,末次血小板为120×109/L。 2023年3月5日患者因重症肺炎死亡。
2 讨论
TTP是一种少见的、严重的微血管血栓性疾病,大部分患者发病急骤,少部分患者隐匿起病。该疾病典型的临床表现包括:血小板减少相关性出血、溶血性贫血、神经精神症状、肾脏损害及发热,被称为“五联征”[3]。临床上以五联征为表现发病的患者相对少见,且部分患者的临床症状非同时出现,因此容易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Evans综合征等疾病混淆[4]。
根据发病机制TTP被分为cTTP和iTTP。绝大部分患者为iTTP,可继发于肿瘤、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cTTP发生率在TTP中占5%[1],发病高峰包括新生儿期和妊娠期,极少数患者中老年发病[4]。 2011年日本报道了43例cTTP,其中15岁以下发病的患者男女比例大致一致,15~45 岁期间发病的15 例患者均为女性,9 例与妊娠相关,45 岁以上发病的患者为3 例男性[5]。C3178T错义突变能够导致ADAMTS13第1 060位的色氨酸被精氨酸取代(p.R1060W),CAMILLERI等[6]研究显示,在一组成人发病的cTTP中C3178T突变占比大于11%,且未在儿童发病的cTTP中发现,因此认为该突变可能是成人迟发型cTTP的发病因素。在此类患者中,ADAMTS13活性的缺失不足以引起TTP的急性发作,仍需妊娠、抗ADAMTS13抗体或其他未知因素驱动诱导TTP发生。此外,有研究[7]提出,机体可能仅需少量的ADAMTSl3便足以裂解超大血管性血友病因子(ULVWF),当机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刺激,引起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释放出大量的UL-VWF时,机体内的ADAMTSl3就无法完全裂解UL-VWF,导致微血栓形成,这或许是某些cTTP患者直到成年才发病的原因。
本例患者首次检测ADAMTS13活性<1%,且抑制物(特异性以及非特异性抗体)滴度0.89 BU,血浆置换及输新鲜冰冻血浆后患者ADAMTS13活性恢复至大于10%,抑制物滴度<0.6 BU,当时曾诊断为iTTP,由于患者TTP反复发作,后完善基因检测,证实患者存在c.3650T>C纯合突变,且该患者后续予以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后血小板即可恢复,综合考虑后最终诊断为迟发型cTTP,抑制物滴度升高需考虑存在假阳性可能。2023年有研究对5例cTTP进行临床分析,其中2例也曾检出AMDAMTS13自身抗体阳性,后经复测验证为阴性[8]。此外,在体外试验中,血清血红蛋白对ADAMTS13活性有抑制作用,TTP急性发作时严重溶血可能导致ADAMTS13抑制物检测假阳性结果[9]。因此仅靠抑制物检测诊断iTTP仍需谨 慎,还需结合患者基因以及临床反应等综合判断,对于cTTP患者即使在缓解期ADAMTS13仍持续偏低,而iTTP患者ADAMTS13水平在缓解期能够得以恢复。
本例患者二代测序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c.3650T>C纯合突变,该突变是指ADAMTS13基因编码区第3 650号核苷酸由胸腺嘧啶变异为胞嘧啶,导致第1 217号氨基酸由异亮氨酸变为苏氨酸。2019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报道了1 例出生 2 d发病的cTTP患儿,经基因检查明确为ADAMTS13基因c.3650T>C(p.I1217T)纯合突变,cTTP诊断明确,后经血浆置换及换血后病情好转[10]。PARK等[11]报道1例在一条等位基因上c.330+1G>A的剪接突变和另一条等位基因上的c.3650T>C错义突变的杂合子突变导致cTTP并发烟雾病。MISE等[12]报道1例长期随访的cTTP患者,基因检测提示为杂合子突变,包括从父亲处获得的c.T3650C错义突变及从母亲处获得的c.G2723A错义突变。
cTTP主要的治疗手段是血浆输注。此外,关于重组ADAMTS13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BAX930是一种人重组AMADTS13蛋白,多中心一期研究对BAX930在15例cTTP患者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BAX930在体内具有药效学活性,且药代动力学特征与血浆输注相当[13]。BAX930的三期前瞻随机开放性研究(NCT03393975)预计在2023年11月初步完成,该研究共纳入了57例cTTP患者,旨在观察BAX930的预防及治疗作用。
目前对于cTTP的机制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由于cTTP发生率不高,症状不典型,常规实验室检测特异性低,ADAMTS13活性、抑制物及基因的检测未广泛开展,导致部分患者诊疗延误。因此如何及时而准确地识别此类患者仍是临床工作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