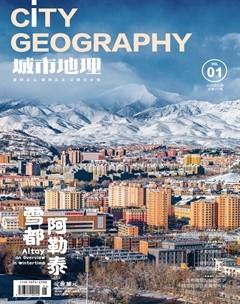古希腊城邦锡拉库萨寻找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北塔



公元前734年,古希腊人建起一座城邦——锡拉库萨(别称“叙拉古”),后成为西西里岛东部霸主。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阿基米德是它的“代言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也曾在这里取景。海浪拍岸,教堂的钟声传来远古的呼唤,这座古老城邦的一切,都像定格在了老电影的慢镜头中。
第42届世界诗人大会别出心裁,在地中海游轮“神曲”号上举行。中国诗歌代表团从罗马的奇维塔韦基亚码头登上游轮,在第二天抵达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按照计划集体登岛考察。由于西西里岛非常大,我们只有半天时间在锡拉库萨游览。看到行程上的地名时,我一头雾水,全然不知道锡拉库萨是哪个“犄角旮旯”,直到后来看到“Syracuse”这个词,才恍然大悟。它在有关古希腊罗马的一般中文文献里被译作“叙拉古”,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城邦、“力学之父”阿基米德的故乡、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第二故乡。“锡拉库萨”是新近的译法,或者是旅游业的译法。
现存最大的古希腊剧场与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重逢
锡拉库萨的码头很大,吃水很深,能怀抱重达13.9万吨的“海上移动城堡”。午饭后,我们下了巨船,直达停车场,大巴车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大巴车先把我们拉到了考古公园门口。大门右侧有一块牌子,上面是一张西西里岛的地图: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部,地中海中部,形状类似一个三角形,其东北端与亚平宁半岛相望,中间隔着3公里宽的墨西拿海峡。作为地中海海域内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在古希腊时期曾经容纳多个城邦,其中三个最大:西部的迦太基、东南部的叙拉古和东北部的墨西拿。迦太基和叙拉古曾一度是大希腊版图内实力最强的城邦,即西西里岛乃至地中海的霸主。两邦的实力此消彼长,因此相互之间势不两立;墨西拿则相对较弱,夹在两强之间,有时左右逢源,有时左右为难,如同三国时期夹在魏国和吴国之间的蜀国。
转弯经过一座瘦高的石头门,再往里走不到十分钟,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椭圆形露天大剧场遗址。整个剧场像一扇大鹏鸟的翅膀,贴附在一片缓坡上,观感特别开阔,舒缓如一支小夜曲。我曾在希腊、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地方见过古代剧场遗址,但像眼前这么大的还是罕见。
据说这个剧场能容纳约15000名观众,放到现在也可以称作恢宏大气,更别说是在公元前5世纪了。当时人们来这里观看的是比赛和戏剧。他们热爱体育和戏剧,或直接参与其中,或充当观众,这促进了古希腊体育业的繁荣和戏剧业的兴盛。
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叙拉古基本由三兄弟统治。老大叫革隆,是西西里岛上盖拉和叙拉古两个城邦的僭主;前478年,革隆病死,由老二希隆继位,史称“希隆一世”;公元前467年,希隆一世去世,老三塞拉西布勒斯上台。老大是强君,老二是弱主,老三则是暴君。老三上台后,叙拉古人掀起民主风暴,刮走了暴君,建立了民主政体,政事由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每年换届选举的将军委员会处理。无论是独裁统治还是民主治理,彼时的叙拉古领导者们都崇尚文学,不仅支持本邦的文士,还邀请许多外邦的文人和哲人来到叙拉古。比如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品达,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等人都曾在叙拉古受到优待。
“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一生中多次受邀前往叙拉古。公元前470年,他应希隆一世的邀请,前去参加埃特纳建城的纪念活动,不仅排演了他的悲剧代表作《波斯人》,还专门撰写了悲剧《埃特纳女子》,来颂扬希隆一世主持建立的埃特纳城。也许是因为感念王恩,也许是因为感动于叙拉古人对戏剧的热情,让他觉得在这里有大展宏图的舞台,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干脆移居叙拉古。不过,在那里生活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在南部的革拉城去世。我站在眼前这个超大剧场的边缘,在刺目的阳光下,想象着当年埃斯库罗斯在剧场里奔来跑去,指导演员们排练他的剧作,并接受观众如潮欢呼与致敬的场景。
据说,一直到公元4世纪,这座剧场仍在使用。如今我们看到的剧场观众席位都是翻新过的,有的铺上了木板,有的直接用水泥浇筑。只有一小块地方保留着原样,但都已经是伤痕累累的遗址。每年夏季,此地仍然会举办戏剧演出,埃斯库罗斯的剧作肯定是保留剧目。艺术的永恒价值在这里被生動表现。在这次出访前,我读了好几部希腊戏剧作品,觉得那些文字依然鲜活生动,打动我心,启迪我脑。
狄奥尼索斯之耳山洞里的暴君窃听事件
西西里九月的阳光相当酷烈,从露天剧场出来,身上汗津津的。导游显然有经验,旋即把我们领到检票口另一侧的小树林中。林中路很短,我们很快就到了一座小山前,那峭壁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挖空,形成一个偌大的洞子,其高有二十多米,进深有六十多米。导游说,眼前这个景点名为“狄奥尼索斯之耳”,又称“暴君之耳”。
此处的狄奥尼索斯,指的是锡拉库萨历史上的一名独裁统治者。此人军人出身,善于玩弄权术,先是爬到将军职位,然后通过一些蛊惑人心的做法,赢得了甚有人望的哲学家菲利斯图斯的支持,由此收获了叙拉古民众的所谓爱戴,让自己成了后来的僭主。由于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得罪的人太多,为确保自己的独裁地位万无一失,他到处窃听反对派人士的议论,连已经关进监狱的人也不放过。
有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这里原本是一个采石场,大量石头被挖出来后,形成了一个大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这个洞能放大声音,起到监听效果。于是,不知道哪个奸贼给暴君提供的建议,这里就成了关押犯人,尤其是重刑犯、政治犯和战争俘虏的特殊监狱。问题是,被监听的也都是聪明人。假如狱卒或警察整天趴在洞口撑着耳朵听,自己在洞内的言论很可能被拿来治罪,因此,囚犯们有所议论的时候,肯定会躲到洞子的深处去,找一个更加隐蔽的说话点。传闻后来,狡黠的狄奥尼索斯一世派人从山顶打了个直孔,直通洞顶,让人悄悄趴在山顶的孔口偷听。
据说,“狄奥尼索斯之耳”这个名称,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天才画家卡拉瓦乔流落叙拉古时取的。他的根据是洞穴本身的形状像一只猫耳朵,所谓“猫耳洞”者。卡拉瓦乔之所以对耳朵这么敏感,可能是因为之前在罗马打架斗殴、失手杀人,一路逃避通缉,让他觉得周围草木皆“耳朵”,于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洞命名为“耳”。而加上狄奥尼索斯这个所有格,可能是因为他从当地人那里听说了暴君窃听的故事。
我们庞大的一群人陆陆续续走入洞中,就好像往一口大锅里投入了几小块肉,一直走到底,还是空空洞洞。刚进去时特别黑,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稍稍适应之后,能看到微亮的光,应是从洞口射进来的光线在石壁上反射的效果。好在洞口没有被封住。假如当年暴君一时兴起,下令把洞口彻底封闭,那么里面就会失去阳光和空气,囚犯们必定呜呼哀哉!
我们在洞里只待了短短三两分钟,心情就变得紧张、沮丧、沉重,待撤到洞外,大家伙如释重负。阳光是轻松心情的催化剂。有人开起了玩笑:“把团长关进洞里去。”我淡然回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力学之父的故乡寻访“百手巨人”阿基米德
来到锡拉库萨,我们当然要寻访阿基米德这位当地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叙拉古古国留下来的古城被称作“奥提伽(Ortigia)”,应该是当年繁盛时期王国的一部分,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这里是一个小岛,与西西里本岛之间隔着一湾窄窄的海峡,由两座并行的桥连接着。两座桥一新一旧,但是由于形状和环境相似,如果不仔细看,并不能分辨得清。
两座桥梁之间是一片广场,广场中央是建于1878年的阿基米德雕像。我站在他旁边,跟他合影,脖子只能够着他的手腕。在古希腊人心目中,那些能力远超普通人的人,都是半人半神或者就是神,所以他们的雕像都要比真人高大许多,给普通人一种必须顶礼膜拜的感觉。阿基米德被称为“数学之神”,当然是早就被神化的人物之一。
阿基米德雕像上身半裸,下身穿着袍子,赤裸着双脚,头发微微卷曲,身材略显消瘦。他目光炯炯,表情庄严,面朝大海,望向远方,右手半举起来拿着镜子,左手垂在胯部拿着圆规。圆规象征他的数学家身份,镜子象征什么呢?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使用光聚焦原理的伟大案例流传很广:叙拉古城曾遭到罗马舰队的攻击。城里的青壮年都上前线去了,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年逾古稀的阿基米德为了自己的祖国挺身而出,让城内的妇女和孩子们每人拿出自己家中的镜子,一齐来到海岸边,让千百面镜子的反光聚集在敌军船帆的一点上,船帆燃烧起来,火势趁着风力越烧越旺。罗马人不知底细,以为阿基米德又发明了新武器,旋即落荒而逃。这支罗马军队的统帅马塞拉斯将军苦笑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之间的战争!”“阿基米德真乃神话中的百手巨人!”
西西里的神话世界与月亮女神不期而遇
眼看暮色即将四合,我们赶紧向阿基米德告别,急急奔入奥提伽小城。导游先带我们来到城中心的阿波罗神庙,能看到的除了地基遗址,只有残垣断壁。神庙的说明牌上写道:这是希腊西部最古老的多利斯式建筑风格的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距今已经有2600年!上有铭文:“尼戴达斯之子克里昂米尼所建,献给阿波罗……”
此庙是奥提伽乃至整个西西里历史的一个缩影。它曾几度变形,从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变作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再变作诺曼底风格的教堂,又在1562年被用作西班牙兵营,1664年则与恩宠圣母教堂叠加。整个建筑的复原工作始于1858年,竣工于1942年。
在附近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处喷泉群雕,其中心是高大的月亮神兼狩猎神阿尔忒弥斯,她的身材高挑而丰硕,面庞圆润而标致,既温柔多情,又威风凛凛。她背着弓箭,随时准备射击,不仅射击野兽,偶尔也射击猎人——尽管她是野兽的女主人,也是猎手的保护神。
她的左边有一个赤裸的少女,右边有一个赤裸的少男。那少女在女神脚下,右手臂向上举起,目光也随之上扬,体态纯洁而大方;那男孩则显得比较调皮,紧贴着面向女神,左手向上伸出扶着女神的胯部,目光微微向下,仿佛在注视少女的脸。周边四个方向各有一个英俊少年骑着动物,有鱼有马,这些少年无一例外都长着长长的尾巴。群雕厚重而生动,逼真有质感。我绕着圈仔细赏析,对这件巨大的街头艺术品叹为观止。
大教堂的不老传说卷进街头歌手的音律旋涡
離开狩猎女神群雕,我们沿着小巷转个弯,继续往里走,就到了奥提伽的中心,其标志是气宇轩昂、敦实魁梧的锡拉库萨大教堂,现在是天主教锡拉库萨大主教教区的总部。这座教堂见证了多个朝代、多种文化,也历经多种建筑风格。它最早是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娜神庙,当时的多利斯式立柱现在还保留在教堂墙壁中;到公元7世纪,左西莫主教把它改建为教堂;其中殿的屋顶和拱点的马赛克则是诺曼底时期建造的。
教堂马上就要关门了,我们决定就在教堂的前广场和四周随便转转。暮色降临,广场上人烟稀少,广场的另一边有一小群人围在一起,欣赏一对歌手的弹唱。男歌手穿着简朴随意,理个了嬉皮士发型,头发像一道波澜往上卷起,其中一小半还染成了白色。他不苟言笑,目光低垂,盯着自己的吉他。女歌手裙子稍显花哨,但也得体,面露微笑,表情丰富,她演奏着小提琴,手臂像波浪一样微微起伏,富有韵律感,嗓音既甜美又嘹亮,一首曲子唱得声情并茂。这首英文歌旋律丝滑,我听出来里面有模仿波浪的节奏。为了证实,我等她停下来的间歇,走上前去询问,果然,她说那是一首爱尔兰民歌,题目是《摇晃的海》。
我们绕着教堂走了一圈,再次走到来时的小巷子时,里面已是一番热闹景象:大小饭馆包括小吃摊全都开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商店也都张灯结彩地迎客,有的甚至把商品摆放到了门外街边。
这时,无比皎洁的月亮已经冉冉升到教堂尖顶上。当我们走出幽深的小巷,行至双子桥上时,天已经彻底黑了。桥上华灯初上,璀璨却不张扬。海边的建筑物只有三五层高,大部分外立面都是白色(希腊人尚白)。它们在港湾的一侧,我们的“移动城堡”在另一侧,两边放射出来的灯光明亮但不耀眼,仿佛相互之间在暗暗较劲,它们射到碧绿的海水里,形成光柱,随着微波轻轻荡漾。
我久久盯着这水中的光,似乎有海妖随时从中飞跃上来。有好一阵子,我既不愿意回到船上去,也不愿意回到城里去。我就想在那桥上,在那梦幻般的夜色里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