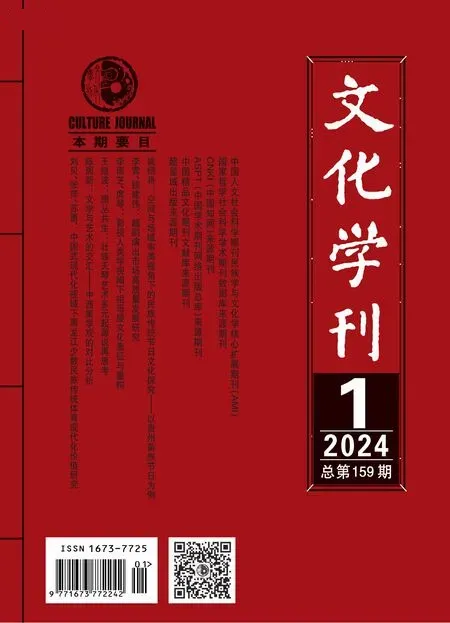谱一曲共鸣,奏精神高歌
——论麦家创作中的鲁迅影响
王桂荣 张 旭
2019年召开的麦家作品研讨会中,吴义勤认为“他的小说确实非常有力量,有阳刚之气”[1]68,高度赞扬麦家小说的精神价值。“鲁迅小说全译本进入英国主流市场,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容忽视;莫言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阐释20世纪中国社会丰厚的历史内涵而荣膺诺奖;麦家的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古典美的翻译风格走红欧美[2]。”麦家的作品在国外读者群体庞大,因此,研究者比较研究麦家与鲁迅和莫言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分析麦家对鲁迅跨越数年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呼应,浅析两位作家创作产生的文学与社会影响。
一、内容选择上继承发展
麦家塑造出独属于麦家式文学韵味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鲁迅笔下人物形象的影子。
《伤逝》中的子君是奋起反抗的一代觉醒不彻底的知识分子的符号象征,涓生与她最终一伤一逝,体现了在封建社会中迈出自由解放步伐的知识女性一旦沉溺于情爱之中,不求进步,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暗算》中黄依依继承了子君的勇敢追爱,她有知识、有超乎常人的数学能力与解密天赋,是新一代知识解放的女性,但她却控制不了情欲,因此,惨死在医院的厕所里。无论是刚接受启蒙思想与知识熏陶的先批觉醒女性还是学识充沛思想解放彻底的科学女性,最终都耽于情欲。鲁迅和麦家在用女性形象塑造来带领读者寻找并成为真正独立优秀的女性。祥林嫂是鲁迅笔下最为经典的女性形象,像一头默默无声耕耘的黄牛,被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所统治的旧社会折磨得丧失求生意志。《风语》中的惠子是日本女性,不顾家庭阻拦与世界战争的严峻形势来到中国,即使与陈家鹄情比金坚,也挽回不了悲惨的结局。一个是封建社会吃人导致的悲剧,一个是旧统治阶级惨无人道的阴谋陷害。麦家继承了鲁迅对封建旧社会的横眉冷对,更延续了对遭受生命威胁的大众的同情。生活的不幸层层加压,但总有人在忍耐前行。《人生海海》中杨阿姨前半生磨难重重,但她选择直面磨难,默默守护着只有儿童心智的上校,脸上布满岁月和苦难的印记,仍乐观地生活着。这是麦家对鲁迅的女性系列和自己前期女性创作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更新,是人道主义光辉的一种彰显。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大声疾呼“吃人”是对社会现状认知的袒露,狂人是天才,只不过这个天才的言论与思想招致羞辱责骂,受到看客的嘲笑与管制,这是一个时代看透现实的天才的陨落。天才坠落的悲剧意味也是麦家写作的核心。《解密》中容金珍破译密码的惊人天赋,最终败给被偷走的笔记本,沦为一个疯子;《暗算》中拥有超强听力的阿炳败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子身上,还有隐姓埋名的鸽子等。在麦家笔下,天才确实拥有常人无法匹及的才能,同时也有着比常人更加脆弱的内心,“麦家试图通过小说向我们表明:人有可能征服强大的对手,但要战胜自我却极其困难。就像古老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王那样,他能以非凡的智慧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却对自己的命运束手无策”[3]。这就增强了小说中人物的物质感与实体性,是天才陨落的深度思考。
绝望中进行抗争是鲁迅在作品中主要传达的一种理念,绝境中极端里叙事也是麦家一贯的创作风格,并且相较于鲁迅来说具有更加明显的绝境氛围,前期作品中充斥着对于701隐秘位置与极致人身限制的表达,环境压抑封闭最典型的是《风声》中敌我对战的公馆,在这里智力与心灵的双重折磨,使绝境达到了顶峰,但“它恰恰暗合了中国文学的某种精神转型:无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中,在一些滚烫的、坚定的身体较量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种令人尊敬的痛苦、一种庄严高贵的人生;懂得辩识、体认这种人生的民族,才堪称是一个精神已经成人的民族[4]。”鲁迅与麦家笔下的这些人物无论处于何种绝境都执着地前进,因为他们每前进一步,就离中国美好光辉的未来进一步,他们隐姓埋名不应该也更不能被遗忘,作家向我们传达文学与历史带给我们的确信与肯定。
综上,虽然两位作家之间的创作相距几十年光阴,但麦家的作品中仍然可以品味鲁迅伟大启蒙精神的源远流长与继承发展。
二、形式创作上借鉴创新
麦家采用的亡灵自述与书信日记的写作形式,以及创作题材的选择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鲁迅对死亡主题的写作有独特思考。《死后》借助的是梦境,采用的是一种亡灵自述的写法,虚构自己死后经历的事情,荒诞怪异惊悚绝望充斥着行文,《故事新编》中的《起死》通过庄子与鬼魂之间的对话,这种死后虚构来对人性进行剖析挖掘与深度嘲讽。《暗算》中《韦夫的灵魂说》是更加直观的亡灵自述,灵魂亲口叙述自己的战前经历、战中故事以及死后尸体是如何被化妆运到中国来充当他人尸体。韦夫跟随自己的身体逐步经历,像是并未去世,行文遍布一种凄凉与心酸之感。“文学中的‘虚构死亡’,主要有两种意味,一是借死亡鬼魅世界,曲折讽喻现实,二是借由死亡探讨生命哲学,向死而生[5]。”两位作家融合了“虚构死亡”的两种意味,鲁迅是借助自己死后的描述来表述当时社会的冷漠无情,民众麻木不仁,但鲁迅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体现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哲学思想。麦家借用异国人的灵魂说,一方面是揭示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另一方面通过韦夫的段段内心独白,体会到他对家乡的渴望与思念,对死后尸体肆意使用带来的人性丧失的思考,更有人类精神世界的共性启发。
《狂人日记》以十几则狂人自我意识流动毫无逻辑的记录,真切地表述自己的悲愤与思考,几乎是做到了随心所欲的写作。《伤逝》是涓生的手记,这篇手记书信体小说弥漫着涓生哀伤的情调,读者自然而然地走进两人的爱情悲欢离合故事,走进涓生的内心。这种书信记载与独白的方式在麦家笔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解密》《暗算》中大篇幅运用访谈录和采访稿以及个人日记来呈现主人公的一生。《风声》中东风、西风与静风的博弈对峙以及《人生海海》中“我”不同时期的记载,是在运用独特的形式来写作。在两位作家的创作理念中,书信与日记的写作形式是对书中人物最逼真的描写,同时也是抒发个人情感、宣泄写作热情以及带给读者身临其境感受的绝佳创作形式。
鲁迅与麦家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可谓是匠心独运。《故事新编》选择重新编写神话与传说,所谓故事新编,可以说是旧有的神话传说故事的新型编写,更可以说是将社会生存人物、社会历史环境用神话传说的方式进行新编写,这种独特的题材选择与创作与其说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不如说是鲁迅主动尝试另辟蹊径的启蒙式创造与书写。麦家的小说带有明显的红色题材与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子。三部曲与《风语》的故事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讲述了英雄人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传奇事件,基本吻合红色经典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人生海海》是对革命英雄传奇的继承创新,改变了传统革命英雄的故事发生地,将人物放在一个普通平凡的乡村中进行讲述,穿插传奇故事,衔接故事情节,增添写作内容。传奇英雄的上校最后是一个悲剧惨淡的形象。“《人生海海》对英雄传奇的改写与重构既丰富了英雄传奇的内涵,创新了英雄传奇的写作模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6]。”
两位作家在形式上的遥相呼应是优秀作家对作品创作格式探索创新的体现,亡灵叙述讽刺现实,传递哲学思想,日记书信袒露心声,诱人深入,独特题材的开创增强文学阅读趣味性的同时激励民众奋发向上,这是作家对时代的写作,也是对使命的把握。
三、创作意义上融会贯通
文学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在于其具有独特的启蒙意义与审美价值。鲁迅发现了从医救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效甚微,所以弃医从文,以笔为剑,划破社会黑暗的障壁,书写社会黑暗面。麦家《解密》创作10余年,退稿17次,支撑他的仅有赤诚的文学之心,其文学创作中反映了时代需要英雄的创作倾向,“小说并非仅仅是一个好玩的游戏或“智戏”的展示,它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悲歌。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麦家书写了我们期待和想象的革命时期的孤胆英雄[1]71。”鲁迅和麦家以文学启蒙性与审美性为重的创作宗旨,对时代使命的正确把握,是作家最基本的文学素养和责任担当,需要所有作家铭记在心。
鲁迅与麦家都有一段心酸孤独的生活经历,鲁迅见证了自己的家庭由盛及衰,目睹了中国备受屈辱的现实,他投入写作为的是启蒙民众、唤醒民众,也是为了疗救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麦家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孤独是笼罩在他青少年时期的阴影,在作品塑造的天才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家身上的特质,伤疤隐藏起来只能永远成为伤疤,两位作家从事写作治愈自己,而后由此出发,结合社会现实疗救世人。看客是鲁迅创作中一个庞大的人物体系,他们对社会麻木、对周边人冷漠,反复咀嚼着他人的痛苦,浑浑噩噩,他们遗忘了何为生之意义、何为生之本质。麦家也在作品中提到了遗忘,《风声》中“老鬼”式的人生何尝不是被国人遗忘的?这样的遗忘,映照出的其实是当下文学中的精神残缺。时代需要温情,我们不能遗忘,时代需要英雄,我们不能遗忘,时代需要信仰,我们更不能遗忘。“文学要写普通人的生活,写好普通百姓人物,但假如我们的文学不去写天才和英雄的故事,不对天才报以同情和尊敬,不对人才表达敬意,那么中国和中国文学都会没有希望[1]69。”麦家继承了鲁迅的文学思考与文学使命,塑造出独属于中国的天才英雄。社会生存环境总是闭塞压抑的,这代表的不仅仅是人类在特殊时代的生存困境,更展露了人类的精神困境,时代飞速发展,如何与时代共处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大难题,作家启示我们,人类面临精神困境时,绝望地抗争与英雄主义的高扬能够赋予困境中的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
前文提到,鲁迅、莫言作品的海外研究多集中于学术研究,外国学者针对其研究主要侧重于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政治性因素占据主要地位。麦家打破了这一传统的文学接受动机,首先其故事十分传奇,吸引读者深入其中进行解密;其次,作者设置的故事背景不受政治、地域、时期、民族的限制,受众群体广大;最后,麦家深刻把握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在欧美国家地区,悬疑探秘类型作品广受欢迎,麦家的小说中普遍包含大量的侦探解密成分。
鲁迅和麦家发挥文学作品的启蒙作用和审美价值,因其艺术性与内涵性也吸引了无数海外读者。麦家的创作将政治性与技术性密切结合,展现中国形象与中华特色,不仅满足国内民众的猎奇心理、主人翁意识,更重铸了英雄主义精神,高扬爱国主义。同时启示当代作家,必须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也要能够符合海外受众心理,形成海外读者接受群体。梁海教授在麦家作品研讨会中所说“麦家的小说能够引起西方世界这么大的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确实在讲述一个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传统的一个命运观”[1]79。麦家将中华传统文学创作特色与中国哲学思想结合,并与吸纳的博尔赫斯和毛姆的创作特色融会贯通。文学作品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如今正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展现中国形象的好时机,作家在创作中要致力于打破西方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印象,增强文化自信。
四、结语
麦家作为当代崛起的作家,作品中明显带有文学巨匠鲁迅创作的影子。探讨麦家创作中鲁迅的影响,意在分析杰出作家的创作共通点,更意在引导众多作家承担起文学创作的重任,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树立中华形象,对于中国文学书写如何向国人“走进来”与向世界“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定然存在其文学价值。麦家的创作水平与鲁迅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但他对于文学作品初心的掌握以及其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都将辅助他取得更加显著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