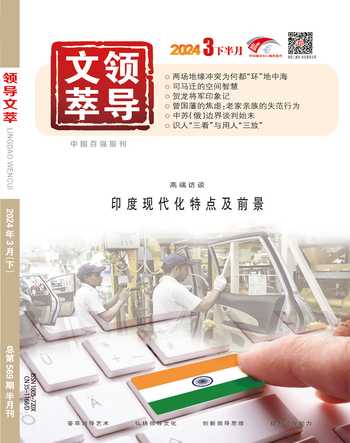梁启超的最后岁月
孙文晔
梁启超只活到56岁,人们在怀念时不免感叹,“正写到最佳状态、写到兴头上的梁启超的突然弃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损失”。
清华园
1925年秋,梁启超52岁。
9月8日,他从天津“饮冰室”的意式小楼,搬到北京清华园,在这里开启了入清华为师、专注学术的新阶段。
这位在晚清和民国都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拒绝了多所大学的校长之邀,去清华当老师呢?报人陶菊隐就说:他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他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
1918年“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张君劢、丁文江等一行七人,对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考察。他观察到,“一战”后的西方,正经历着一场“精神饥荒”——对物质的追求,使人丧失了精神价值、人格尊严,使人无限地苦闷、彷徨和失望。
对西方文明祛魅后,他深信,可以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而人格修养作为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能治愈“精神饥荒”。
1925年2月,吴宓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简称国学院)筹备主任。他赶赴天津,谒见自己的启蒙者梁启超,一番洽谈之后,梁表示“极乐意前来”。毕竟,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刘东认为,“梁启超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清华三年实为其一生用力最专、治学最勤、写作最富的时间”。
梁启超的文章以感情奔放著称,他的课堂又是什么样呢?梁实秋给我们再现了一位有趣又独特的梁启超:“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
从1925年到1928年,国学院在开办4年间共招生70多人。这70多人中,以师从梁启超的最多,他教的学生日后都成为国学大家。不失威严又相当融洽的师生关系,是中國书院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是清华国学院成为传奇的秘诀之一。学生蒋百里说,梁启超最适合当老师,这样“才把他的活泼泼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
错割肾
在清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梁启超决定利用寒假去治病。从1924年冬开始,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时轻时重。起初,他瞒着家人,直到病情加重,他担心自己得了癌症,才决定去医院查一查。这一查,就引出了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事故。
他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没查出所以然,又转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华开办的医学院,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诊疗水平在亚洲也算一流。
协和医生借助X光,发现他的右肾有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尿血症的病因。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尿血的病症依旧。
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5月29日,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对误诊的失望溢于言表。随后,陈西滢、徐志摩等也接连撰文兴师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
面对舆论,梁启超不仅拒绝起诉,还带病撰文,平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就医过程,并在结尾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为避免后人误解协和医院,他还特地把这篇声明的英文稿放在病案里。然而,这件事传到现代,还真从“错割肾”变成了“割错肾”。
一个细节是,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外科专家正在协和,可以主刀,大家都觉得梁启超很幸运,他却执意要换成了中国医生,因为“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
梁启超以自身性命为“西医”作担保,并不代表他对误诊不知情、没情绪。
他的好友,协和医院筹办者、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在调阅病例后指出:“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梁启超在家信中写道:“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借伍连德的口说出这几句苛责后,梁启超再无牢骚。
有趣味
在这些事之外,他还要写专著、论文、应酬文章与演讲稿。据统计,仅1927年一年时间,他就发表了《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书法指导》《儒家哲学》等,总字数在30万以上。
别看他的文章以“速成”著称,内容却不掺水。陈达回忆,自己初到清华教书时,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向梁启超约稿,不过几天,稿子就送来了。虽然事务繁杂,但他总做得津津有味,他曾说,“梁启超”这件东西,就是由“趣味”元素组成的。在他眼中,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恨一天没有四十八小时。无奈的是,再有趣的灵魂也是肉体凡胎,这三年中,他屡次尿血、着凉、发烧、右膀发痛、心脏不适……
他最割舍不下的,是对政治的趣味,“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
1927年的中国,北伐中断,国共从合作走向破裂。5月前后,“国家主义”派、实业界及国民党右派的一些人,天天缠着他,希望他能出面组建“一种大同盟”,与南方的政党相角逐。梁启超内心蠢蠢欲动,又觉得这是摊浑水,天人交战,苦不堪言。在纠缠、烦恼、失眠中,梁启超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立场,不组织或加入党派,还是以他的一贯做法,著书立说来“救中国”。
不朽者
自1928年起,梁启超身体每况愈下,发病不断,这与至亲师友的接连去世,有极大关系。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梁启超在北京闻知噩耗,失声痛哭。梁启超凑钱为康有为风风光光地办了后事,却仍逃不过“叛师长”的骂名。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沉湖自尽。作为同事和有相似背景的知识分子,“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年底,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助手范源濂英年早逝,又让他“伤之至”。此后,梁启超又添了尿闭的毛病。
1928年6月,因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他连赶了三天,发生尿路阻塞50余小时。无奈之下,梁启超极不情愿地辞去清华国学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
下决心不以俗事萦心后,他提笔写《辛稼轩先生年谱》。拼命奋战下,到9月已编至辛弃疾52岁。9月27日,他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10月12日,梁启超将年谱写到了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梁启超考证出,辛弃疾的悼词已失传,仅存四句为:“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写完“生”字,他不得已搁笔,这个“生”字,竟成他此生1400万字著述中的最后一个字。
梁启超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临终时,竟无一语遗嘱。他对家人的最后要求,是向医院捐献遗体,用于研究。
为父亲设计墓碑、墓园,成了梁思成与林徽因毕业后的第一件作品。墓碑上未写任何生平,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毕竟“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