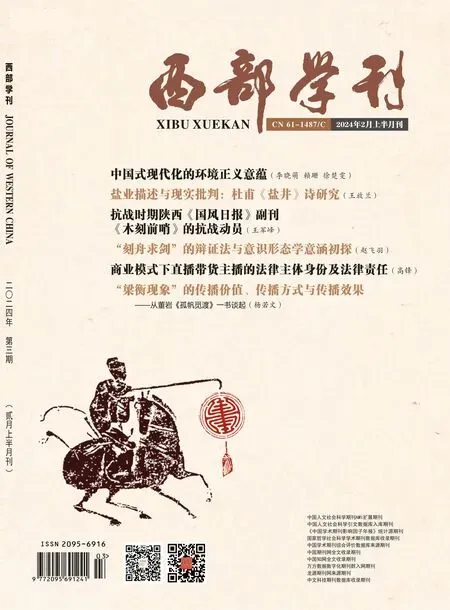论皮埃尔·贝尔的中国观
——以《历史和批判词典》为例
严晓磊
(浙江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皮埃尔·贝尔(1647年11月18日—1706年12月18日,以下简称贝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作家、启蒙运动先驱,他编纂的《历史和批判词典》影响遍及欧洲。我国学者较早肯定贝尔在中欧思想交流史上的地位,如朱谦之[1]提出,贝尔是最早注意天主教教士礼仪之争的启蒙思想家。张国刚和吴莉苇[2]认为,贝尔通过指出天主教会内部分裂以打击其权威性。程艾兰[3]认为中国为贝尔批判宗教蒙昧主义提供了素材。Janik[4]指出,《历史和批判词典》重建了近代早期中欧思想间的联系,值得继续挖掘。
围绕该词典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待明晰:它体现怎样的中国观?依赖哪些资料来源?在贝尔的中国观中处于什么位置?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通过哪些途径和文化知识界形成互动?本文将基于词典学视角在文献法的辅助下对1697年版《历史和批判词典》进行分析,试着解答这些疑问。
一、《历史和批判词典》简介
贝尔撰写《历史和批判词典》的初衷,是更正早前出版的一些词典,尤其是路易·莫雷里(Louis Moréri,1643—1680年)的《大历史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中的错误。然而,贝尔在词典编纂过程中调整了计划,他解释道:
“为了更好地捕捉公众的趣味,我是这样改变计划的:我把手稿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纯粹的历史,是对史实的简要叙述;另一部分是大段的评论,是论证和讨论的结合。在第二部分,我加入了对于错误的查证,甚至还会有大段的哲学思考。简而言之,它们的多样性足以让身处各地的读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5]
在这样的安排下,贝尔的《历史和批判词典》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结构上都和绝大多数语言词典或百科词典大相径庭。其词条由正文和注释两部分构成,正文进行叙述,注释用来论证。论证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同一词条中作者本人撰写的叙述部分;二是更早出版的词典,尤其是莫雷里的词典相应词条中的错误。
《历史和批判词典》于1697年由阿姆斯特丹的Reiner Leer出版,对开规格,共包括4册、2卷。1702年,这部词典被再版,并增加到了3卷。在1706年作者去世后,《历史和批判词典》一直有新的再版出现。1820年,第11版的词典已被增补至16卷。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部词典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一直在欧洲受到市场的欢迎。根据Labrousse的说法[6],它至少在1715年、1734年和1738年成为盗版(1)1715年版出版于瑞士日内瓦,号称词典的第三版,而正版的第三版于1720年由荷兰鹿特丹的P.Marchand出版。1734年版和1738年版分别出版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瑞士巴塞尔,均被标为词典的第五版,而正版的第五版于1740年由P.Brunel, et al在阿姆斯特丹出版。1741年,1738年版盗版词典又重印一次。对象,这反映了这部词典为出版商带来的可观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词典的成功。
二、《历史和批判词典》的中国观
《历史和批判词典》有关中国的论述零散分布于十几个词条中,涉及不同话题,被较为频繁、集中论及的有中国人的信仰、基督教和中国、斯宾诺莎和中国。
(一)中国人的信仰
贝尔高度关注中国人的信仰。在Ruggeri词条的注释D中,他转述德拉卢贝尔在《暹罗游记》[7]中的描述:“相信世上普遍存在好坏各异的灵魂。……认为他们拥有神一般至高无上的力量”。他首先试着剖析其原因:“他们不知道上帝存在,……,如果他们是无神论者就不会承认精神存在和灵魂不灭。”接着试着重建中国人变成无神论的过程,引用德拉卢贝尔的评价:“士大夫是该国最重要的人。……,对宗教毫无情感,不信上帝也不信灵魂不灭。他们供奉孔子于庙堂,崇拜其外在”。他还补充道:“他们尊重孔子只是政治要求。……他们将最高智慧与之相剥离,用人的智慧取而代之。”最后,他引用《暹罗游记》进行了总结:“士大夫们渐渐……彻底变成了无神论者”。
除了士大夫,贝尔还简单提及普通中国人信仰无神论的原因。在Piccius词条的注释B中,他说:“……中国统治者必然让中国人成为不信教者,……”。可见,贝尔认为普通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和中国统治者的政策不无关系。
在Maldonat词条的注释L中,贝尔试图通过阿尔诺的话描述中国人的无神论[8]:“派去中国的最好的传教士……都认为士大夫是无神论者。他们崇拜偶像是因为他们虚伪。……,士大夫缺乏灵魂;高高在上的皇帝……只是物质上的天子”。
孔子在词典的数个词条中被提到,也是唯一真实存在过的中国人。其附录中专门设置Confucius条目,引用龙华民的评价:“孔子和其他士大夫一样,对真神上帝视若无睹”。在Maldonat词条的注释L中,贝尔借龙华民之口进一步确认孔子及士大夫对待神态度一致,将中国人的无神论归因于儒家思想创始人。在贝尔看来,将孔子证明为无神论者,士大夫们及百姓自然就成了无神论者,而中国顺理成章成为无神论国家。
(二)基督教和中国
《历史和批判词典》两处提到欧洲在华的传教活动。Marests(Jean des)词条的F评论中,贝尔引用了尼克尔[9]转述德圣-索兰的话:“将耶稣·基督的规则和统治扩展到世界,直到波斯、蒙古帝国、鞑靼利亚以及中国”。
该主题的一些描述还反映了贝尔对礼仪之争的关注。在Bellarmin词条的注释E和Loyola词条的注释Q中,他引用勒泰利耶的话[10]:“耶稣会士是最早服从也是唯一服从的,……。这有用吗?这并未阻止其敌人……声称教皇对他们极度不满,因为他们竟不承认自己派往中国的主教”。在Maldonat词条的注释L中,我们也看到贝尔借其他学者之口指出在华传教士间的矛盾。
(三)斯宾诺莎和中国
在Spinoza词条的注释R中,贝尔用很大的篇幅对斯宾诺莎和中国的关系进行论述。贝尔对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持正面看法,但也未回避其思想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中国的无神论:“在所有无神论中斯宾诺莎的最不具欺骗性。……如果他更努力弄清中国人的无神论就可以更具战斗力”。他说:“一位神父曾认为不应宽恕任何哲学家。因为正是那些否认上帝和天意存在的哲学家,或出于自身动机,或为了攻击敌人,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举例。……如果其言为真,或是因为一些哲学家认为宇宙中存在众多各异独立存在并依靠内在本质法则运行的灵魂。……这正是中国人信奉无神论的主要思想,……”
接下来,贝尔再次引用了德拉卢贝尔的《暹罗游记》:“……中国人的教义一直在将灵魂赋予给星辰、山岳、江河、植被等四方一切。……同时,中国人又承认万物有灵,那是种内在的力量,生来独立于天。天就像强大的帝王统治着自然:其他灵魂均臣服于它……”。
三、贝尔中国观的发展
《历史和批判词典》的中国观是贝尔中国观的一部分,其不同时期的著作,如《关于彗星的各种见解》《文学共和国新闻》《哲学评论》[11],以及《〈各种见解〉的续集》都提到中国,其中国观经历了明显变化和发展。
在《关于彗星的各种见解》中,贝尔批评中国占星术并警示欧洲人不要迷信。从《〈各种见解〉的续集》到《历史和批判词典》,他明显转向无神论并试图证明无神论社会存在的可能性。贝尔中国观的发展尤其体现在《文学共和国新闻》和《哲学评论》中。此时他高度关注中国并广泛阅读有关书籍,包括旅行者的游记及传教士的记叙;既有赴华欧洲人的直接描述,又有到过中国邻国的欧洲人的间接传闻;不仅限于奇闻逸事,还包括风土人情、思想观念,甚至连中药知识他都有所涉猎。在《历史和批判词典》之后出版的《〈各种见解〉的续集》中,贝尔虽未脱离无神论中国的主题,但已摆脱儒学、士大夫及普通中国人的例子,转而试图从佛教思想中寻找新的论据。
总体上,贝尔的中国观相对局限于宗教和思想,随时间推移聚焦于中国人的无神论信仰。可见对其而言,中国作为论据支撑了他关于在欧洲建立无神论理想社会的论点。
四、贝尔中国观的来源
贝尔《历史和批判词典》的中国观来源包括自发评论和他人文献,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篇幅最多的是德拉卢贝尔的著作——《德拉卢贝尔先生论暹罗王国》。
贝尔编纂这部词典之前,已存在数部由欧洲传教士或旅行家撰写的著作,如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金尼阁、利玛窦和卫匡国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的《中国史》,珂雪的《中国图解》等。贝尔并未对这些著作进行任何引用。与贝尔编纂词典同年代的著作也有数部,作者中不乏安文思、南怀仁、柏应理等赴华传教士,贝尔词典对这些词典也未进行任何引用。
贝尔在引用来源上的偏好与其意识形态立场有关。1685年法国的新教宽容政策告终,新教徒贝尔离开法国流亡荷兰,期间对天主教多有攻击,并批判法国的宗教政策,亦抨击属于天主教系统的耶稣会及其会士。在此背景下,贝尔不引用由耶稣会士占绝对主体的赴华传教士的著作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贝尔也未完全以意识形态决定引用来源。早期耶稣会士,尤其在礼仪之争升级前,均力图构建中国传统思想与天主教信仰的内在联系,试图证明中国人自古信仰上帝,贝尔很难在其中找到有用论据。在其掌握了龙华民在礼仪之争中描述的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观点后,便将其采纳作为论据。
五、贝尔中国观的影响
《历史和批判词典》问世后,它最先受到的是各方批评,如法国胡格诺派新教神学家雅克洛就在其《对贝尔先生神学理论的研究》中对贝尔的中国观进行批驳,反对将中国人的无神论和基督教完全割裂。
也有不少学者对贝尔表示支持,法国伦理学家德圣艾夫勒蒙[12]就坚定支持贝尔的中国观,为贝尔赢得了一定影响。此外,对贝尔的其他观点进行过批判的贝尔纳在无神论中国的问题上与贝尔保持一致。
贝尔的中国观将中国视为欧洲的镜鉴,这为关注中国的思想家树立了范式,影响至少延续到二十世纪。布吕尔认为贝尔的著作是十八世纪无信仰者无穷的宝藏[13]。马克思[14]对贝尔赞誉有加,认为他是十七世纪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也是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哲学家。
六、结语
基于词典学视角以文本分析法和文献法对贝尔《历史和批判词典》的中国观进行了研究。文献分析显示贝尔在着手编纂词典前已对中国抱有兴趣,其对中国的认识最晚于1685年的《关于彗星的各种见解》中就有迹可循。随后十几年中,他一直对中国保持广泛关注并试图阅读更多相关著作。贝尔在其词典中的多处论述和引用涉及中国,包括无神论、基督教及斯宾诺莎三大主题。他试图证明中国人信仰无神论及中国是无神论国家,其引用来源使他得以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有力论证。贝尔的中国观在启蒙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及学者之间产生了回响,为后来的欧洲人看待中国树立了范式。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