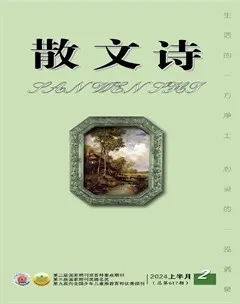在图书馆 (外二章)
◎朱锁成
图书馆是一条小径, 是一面镜子。
在图书馆, 才能找到童年的我。
走过弄堂, 弹革路, 月季, 白果树; 走进课堂, 粉笔, 黑黝黝的土壤……
又在默默朗读, 书是最好的老师, 历史在这里回荡, 科学在这里讲述, 翻卷的每一页或许都是剑影, 打开的每一章都是海洋,都是波澜, 都深邃、 深蓝和壮阔……
所有人都凝神, 不斜视, 不喧哗。 翻阅的每一缕风, 也许都很陌生, 又都那样熟悉。 陌生的是老花镜, 是学生证, 是原住民,是出租屋。
熟悉的是眼神, 一个下午都在默读、 摘抄, 或正襟危坐, 或端坐轮椅, 或有形, 或无形, 行走长街, 衣冠的内心就没有一点残疾?
认不认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吸取和充实, 补充水分和纠正纰漏。
一个春天都在沐浴春风, 一个夏天都在翱翔蓝天, 一个秋天都在收割稻浪, 一个冬天都在收集阳光。
这里没有酒吧的血红和迷醉, 没有咖啡杯越望越深的夜色,没有高分贝的舞步; 少了化妆品和物欲。
这里静得挪一下座椅也能听到长啸, 吸一口气也能听到高山流水。
真该让世界静一静, 人心静一静。
在城市, 还有多少人正踏上那一格格上升的台阶, 走近那柠檬的灯盏、 茉莉的花香? 还有多少河流需要泅渡, 多少心灵需要补血补铁?
窗外, 一把扫帚清扫尘埃;
窗内, 我同名家握手, 向小草致敬。
在图书馆, 我才找到过去的我——
一个朗读者, 找到富有和自信, 找到下午时光, 华灯点燃的通衢和夕阳……
保姆介绍所
门面不大, 甚至别人的锅棚都能贴上几块瓷砖。
一张桌子一部电话, 一扇活络玻璃门, 就开始轱辘生意。
操不同乡音的行旅包来得最多。
也许刚挪下车门, 就风尘仆仆地坐在了长沙发上。
来的次数越多, 就和电话机聊得越熟, 自己的名字和行踪,就会被当作名片, 夹在抽屉出售。
因为, 越是春节, 行情会随入夜的火车票紧俏。
笑眯眯的是行旅包。
笑眯眯的也是上了锁的抽屉。
也有操本地口音的。
她们的手也许接过纱头, 她们走过车弄。
有一天, 她们发觉自己的手也能交响锅碗瓢盆时, 就把黄昏停泊在都市拐角。
只是匆匆和电话机耳语几声, 然后, 就静候佳音, 最希望电话那端响起的是一个外语单词……
这, 是一道繁华背后的缝隙。
每天在给别人寻找生存空隙的同时, 我们也寻觅到了自己的寻觅……
黑夜,其实很灿烂
老远就是东方明珠, 外滩, 轮渡, 万国建筑, 咖啡张望的衡山路。
灯光的镶嵌, 绿树的掩映, 霓虹是黑夜的主调, 直至搅动黑夜的火锅, 公交和出租车。
每一条街道都是城市的流火, 都有城市的血、 呼吸和体温。
台灯和湖心亭, 一张纸和一壶茶, 都能找到合适的座位。
比起还没停歇的九曲桥, 无疑我是一张纸, 我在黑夜坐着,看——
长啸的游龙, 出炉的钢花, 玉佛寺的佛灯, 穿过马路的黑衣,等车的双肩包, 掌心闪烁的月色。
电波拉长夜色, 深水港的塔吊, 铺设隧道的橙衣, 犁开大海的水手, 急救的管道和手术器械, 送达最后订单的马甲, 午夜返乡的星辰。
路边摊倚着墙根, 在等下班的女工, 影院的票根。
我在黑夜坐着, 因为过于微小, 我看到他们, 他们看不到我,坐看潮涨璀璨, 上弦月没过头顶。
以及呼啸划过的顶灯, 另一种眼睛或璀璨。
路会安静, 树会安静, 梦会安静, 直至黎明向我们走来。
风、 阴影或车流, 黑夜的腹地, 其实很灿烂, 我们都是灿烂的一部分, 一张树叶或一堵矮墙, 一盏转角的路灯和小区门灯。
无声, 或者轰鸣, 投入绿, 投入亮, 呼吸和体温, 我们互不相识, 但又相知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