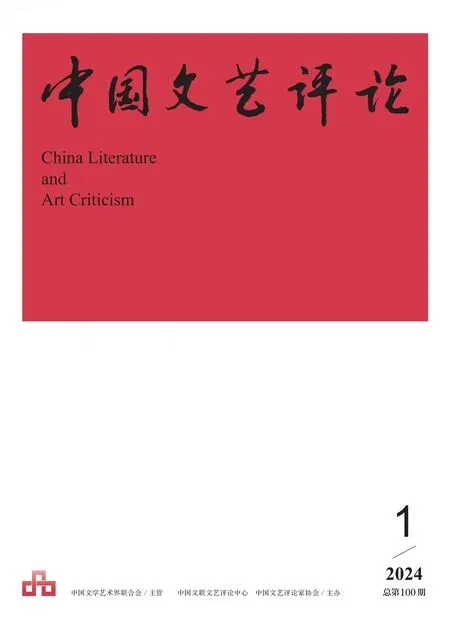非遗传统技艺传承人“四圈共生”模式论
■ 陈天一
一、理论缘起
“共生”,一个来自生物学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医生、著名真菌学奠基人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他认为,共生就是不同生物可以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随后,科学界就“共生”概念展开了持久的讨论。植物学家斯科特(G.D.Scott)在其著作《植物共生学》中指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而达到平衡状态。[1]参见G. D. Scott, Plant Symbiosis,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69, p.58.原生动物学家维斯(Dale.S.Weis)则把共生定义为几对合作者之间的稳定、持久、亲密的组合关系。[2]参见Richard G. Burns, J. Howard Slater, Experimental Microbial Ecology, Oxford London: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 1982, p.320.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提出“盖亚假说”,认为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力。随后,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等人又在“盖亚假说”的基础上借助德贝里的“共生”概念提出了“共生理论”,这一学说曾盛极一时。[1]参 见Lynn Margulis, Origin of Eukaryotic Cell,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在“共生”概念提出百年之后,洪黎民教授将共生概念引入中国。[2]参见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4期,第50—54页。随着人们对于共生概念认识的不断加深、成熟,最终形成了广义的学科理论。即认为生命并不像新达尔文主义所假定的那样,是消极被动地去“适应”物理化学环境,相反,生命主动地形成和改造它们的环境;生命有机体与新的生物群体融合的共生,是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创新来源。[3]参见夏征农等主编:《大辞海•哲学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708页。
生物共生理论诞生后逐渐被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广泛关注,并引发诸多思考,尤其是在共生哲学、工业共生、商业共生、经济共生、社会共生等方面生发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理论成果。共生哲学的实质“就是藉以阐明大道或存有是如何在宇宙及其现实世界中彼此共同相处与和谐共进的”[4]吴飞驰:《“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第29页。,包含生命理念、过程理念、异质共存理论、中和理念、关系理念及生活理念等多方面[5]参见李燕:《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理论学习》2005年第5期,第73—74页。。丹麦卡伦堡公司出版的《工业共生》中认为,工业共生指不同企业间的合作,并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并获利能力,同时,通过这种共识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对环境的保护。经过多年的理论实践,工业共生理念逐渐在独立企业、企业间以及更为广阔的区域生态工业网络三个层面中得到运用。而在商业与经济领域则衍生出金融共生、商业集群共生、智能网联商业生态圈共生等诸多研究视角,这不仅丰富、深化了工商经管领域的理论维度,同时也为文化艺术研究带来有益启示。
早在194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在其著作《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单列章节谈及“共生与契洽”[6]参见费孝通:《世代间的隔膜》,《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210页。,而社会共生理论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则始于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提出“社会共生论”并出版《走向共生》《社会共生论》等专著。虽然“共生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界,在中国甚至还被应用于“和谐社会”的相关研究中[7]参见刘荣增:《共生理论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运用》,《中国市场》2006年第Z3期,第126—127页;杨玲丽:《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6期,第149—157页。, 但这种关于某物及其与之紧密联系的他者共同存在的一个作用场域,某物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他者之中所包含的诸多因子对某物的发展产生相应影响、彼此互促进退的概念,其理论触角尚未延伸到中华传统艺术的研究之中,而对传统技艺传承人的诸般研究则更是鲜有问津。
按照生物共生论,生物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社会共生论认为,人同其他生物一样,不可与他人、环境隔绝,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没有共生,也就没有人的存在。”[1]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序”,第9页。人自一出生便与自然、社会共生,拥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离开自然与社会便无法生存。人们为了生存,需要主动与社会建立共生关系。同理,传统技艺要想延续、传承,离不开技艺的文化主体——传承人(生物共生理论称之为生命体)。传承人不仅是传统技艺的传承者,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承人在承载、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浸润在与之密切相联的共生关系之中。传承人作为个体无法脱离社会共生系统,必然处在各圈层之中,即传承人与自然地理之间、与个体家庭之间、与社区社群之间,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传播等因子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无法彼此脱离的共生关系。
当前,传承人的困境就在于如何将传统技艺产品的生产、传播、使用、鉴赏等社会活动融入更多人的日用而不觉的日常生活,如何让其成为人们无法剥离的生活方式,如何让非遗作品提升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意涵。在传统艺术的传承中,技艺传承是核心,因为“技艺是保障一门艺术存在和延续的关键,也是维护其特征和样貌的核心依据”[2]王廷信:《技艺视角下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7期,第4页。。既然“盖亚假说”认为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力,那么我们也不难发现,传承人在各圈层里因各种因子相摩相荡,不断互相建构,其生存境遇不断得到改善与发展。如果传承人在其中不能与各种因子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传播等发生“作用力”,就无法让技艺言说生活,无法让艺术作品为时代做注。而不与正在发展着的社会共生建立如鱼得水般的互构,就没有传承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传统技艺的代际传承,永久赓续更将无法实现。
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共生理论的视角出发,以传承人的生存境遇为例,探索各圈层划分是否科学,并以诸如艺术实践以及传统技艺传承过程中主体与时代、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等为观照对象,思考机械复制时代、后机械复制时代带给传承人的挑战与机遇,为中华传统技艺传承问题提供可备一说的理论思考。
二、传承人的“四圈共生”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缘起,笔者将传承人的生境划为“四个圈层”,其主要逻辑起点是运用共生理论来分析传承人在各个圈层里不同的依存度、平衡性、持久力。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四个圈层”是按照生存半径的空间地理意义来构建的。当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按照时间意义(如农耕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也可进行顺畅的逻辑推演。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构建这四个圈层的逻辑起点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只不过某一个圈层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时空特性显得特别稳固或者特别脆弱罢了。下文将分而述之。
(一) 第一圈层:家庭(家族)共生圈层
在1879年德贝里最早提出共生理论之前,法国思想家丹纳在1865年曾说过,“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页。。丹纳虽不是共生理论的发明者,但他却道出了那时艺术家的艺术之路的发轫之地——家族。如果用丹纳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文化(技艺)传承者,也是较为契合事实的。
中国自古有幼蒙庭训、弟子入室的家教、师教传统。孔子弟子三千随其周游十五国着实有一种人身依附意味;《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作者司马迁其实是子承父业;《水经注》文辞隽永、流传百世,其作者郦道元曾跟随父亲游历秦岭淮河、广纳风土民情。可以说,幼蒙庭训、子承父业是中国长期以来最为可靠的文化传承方式之一。
当今,我国已经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语境中,传承人家庭学艺的“前现代”传承方式还在延续。例如,景德镇许多瓷器传承人是因“带子传艺”而入。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挽救景德镇瓷器工艺,允许老艺人将子女带进工厂传承技艺;将中国苏绣带进威尼斯双年展的姚惠芬生长在刺绣世家,十岁便开始学习刺绣;朱仙镇木版年画《天成老店》的家族传承谱系可上溯至明末清初,第五代传承人尹国全六岁便同父亲尹福祥学习木版年画。除了家族传承,传承人对于任何一项非遗的学习更离不开师承,需经“转益多师为吾师”方可有所造诣。侗绣传承人陆永江为了学习不同的绣法,在村寨里寻找老绣娘拜师,甚至辞去工作到老绣娘家去干农活,随其学习绣法;光福核雕传承人陆小琴先后拜师学习木雕,经过12年的积累转学核雕技艺,将师承的木雕技艺与核雕技艺相结合,使其核雕作品独具特色……
“一招鲜,吃遍天。”中国人对于自己家庭(家族)的独门绝技总是密不示人,就连李渔的《闲情偶寄》中也说:“含珠不吐,谁知是宝。”他把与人分享戏曲创作经验作为了一种貌似“高风亮节”的恩赐。只有“子承父业”或“入室学艺”才能变成传承人。这可以看作是传承人进行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学徒与掌握技艺的家庭(家族)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用共生理论的定义来说,这是一种“稳定、持久、亲密的组合关系”。在此阶段的传承人学习掌握特定技艺,倘若“传者”与“授者”彼此分离,“授者”则无法依靠特定技艺获得安身立命之能力,这就印证了上述斯科特所说的共生理论中“依存度”的合理性。
(二) 第二圈层:族群共生圈层
相较于第一圈层,族群共生圈层要稍微大一些,正如丹纳所说的“(艺术家)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页。。丹纳这里所说的“趣味一致的社会”在交通并不便利、生活半径逼仄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是一种族群。
一般说来,无论表演艺术还是造型艺术,生活在上述第一圈层中的学徒们由于有了师父们的传授,终会成为掌握一定技艺的熟练工而等待社会的检验与淘洗。当然,人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后便会不断朝着更高的层次寻求发展,笔者将其称为因“作用力”而导致的发展共生过程。例如,被誉为“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梅巧玲是四代梨园世家的创始人,他的儿子梅竹芬、孙子梅兰芳、曾孙梅葆玖等都是京剧大师。他们生活的圈层当属第一圈层即家庭(家族)圈层。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如果他们拒绝多元共生、美美与共而缺失发展共生的过程,仅仅限制于“梅家”这第一圈层,最终势必枯萎凋谢。他们必须进入第二圈层即“族群圈层”方能业务精进、持续发展。顾名思义,第二圈层的存在形态主要是“族群圈层”中的“群”的形态。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梅派艺术之所以能够进入鼎盛时期,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当时的“四大名旦”出现了一种族群意义上的作用力,他们互相发展共生。梅兰芳《红线盗盒》、尚小云《红绡》、程砚秋《红拂传》、荀慧生《红娘》等“四红”以及梅兰芳《一口剑》、尚小云《峨眉剑》、程砚秋《青霜剑》、荀慧生《鸳鸯剑》等“四剑”传诵一时。这种争奇斗艳的局面实际上提升了族群中每个个体的竞争力,因此这种“共生关系”其实是一种生物共生意义上的竞争(作用力)关系。
竞争是为了共生,这种共生并不仅仅是“丛林法则”有你无我的共生,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力。社会学的发展共生有如生物学意义上的互相提供彼此生存所需的营养共生,他们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撑的命运共同体。例如程砚秋少年时就曾拜梅兰芳为师,梅兰芳又向陈德霖学习昆曲,尤其是向俞振飞学习昆曲“橄榄腔”,更是丰富了梅派的声腔艺术。
(三) 第三圈层:机械复制共生圈层
大工业生产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捷以及不可逆转的变化。目之所及,如机器制面代替了手工擀面,机器纺织代替了手工织布,机器剪纸、机器版画、机器编织俯拾即是。毫无疑问,机器生产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大工业生产中,人们高呼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连马克思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章也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43页。
但是,300年的工业大生产似乎没有给“乡土中国”带来机器的轰鸣,几千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产方式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民间手工艺还在以“交换”的形式存在着。曾经落后的中国真正进入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境况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手工版画、对联、剪纸、服饰等逐渐销声匿迹。机器印刷的对联“抢夺”了手工书写的“笔墨费”,塑料窗花迫使农村老太太放下了剪刀,东南沿海机器生产的服饰使中国农村的孩子脱下了虎头鞋虎头帽……总之,人工制品正被机器制品无情地“驱逐”。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瓦尔特•本雅明就在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道明了机械技术革新将会为现代社会中的艺术带来变革。他认为机械复制艺术以追求展示价值替代了传统艺术致力的膜拜价值,机械复制艺术使传统有韵味的艺术“灵韵消散”而走向崩溃。[2]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9页。诚如本雅明所说,现代人“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该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3][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4页。。机械复制品在满足了大众占有、消遣愿望的同时,手工艺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被极大地压缩了,他们的工作效率远不及机械生产,在机械制品极大供应的情况下,问津纯手工艺作品(即“真正的对象”)的人愈发寥寥。
而瓦尔特•本雅明仿佛在半个多世纪前无意中预言了机械复制时代非遗传承人将会面临的生存境遇。第三圈层“机械复制圈层”里的传承人,他们在这场浪潮中基本上是以或“坚守”、或“改良”、或“退群”三类进行分化。所谓“坚守”者,他们一方面获得了一些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坚守非遗在其心中的神圣性。“改良”者,则投身到机械复制中,如舞台上的演员投入到影视演出中,一些农村的手工艺者,介入甚至开发“机械复制”,依靠机器生产,获得利润,维持生存。所谓“退群”者,即一些传承人面对艺术品失落了的内在意义,面对自己温饱问题,面对新的“艺术”在声光电色中的炫惑,被迫另谋生路。
(四) 第四圈层:互联网共生圈层(人工智能共生圈层)
“互联网共生圈层”是指从机械复制技术的时代迈入了以互联网为核心、以人工智能为要件的“后机械复制时代”的传承人的生存境遇。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统计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4]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年9月26日,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2/0926/MAIN1664183425619U2MS433V3V.pdf。
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脑就是当下非遗作品的复制机械(生产工具)。例如每逢节日,一些老百姓会通过互联网下载并打印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贴在窗户上来增加节日气氛。不仅如此,后机械复制时代的电脑“兼具汇聚各方信息、链接各种机器的终端属性,以及各种重新组合、加工的生产属性。这便是电脑区别于机械复制时代机器以及以往所有时代复制技术最根本的特性”[1]刘毅:《灵韵消散之后——艺术生产与审美经验的跨媒介重建》,《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26页。。
机械复制时代的非遗复制毕竟在受众审美约定中难以改变“母板”的形状、色彩等,而后机械复制时代的电脑却具有“创作”意识。这种“创作”意识特别是在当今AI技术的加持下其实是一种借助工具的文化再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罗杰•马利纳(Roger Malina)所说,“电脑不只是进行机械复制的有效工具;更是适合于艺术家进行后机械的、生殖性的复制最理想的工具”,“后机械复制的目的是设定初始规则,而后尽可能生产出彼此不同的副本”。[2]Roger F. Malina, “Digital Image–Digital Cinema: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Post-Mechanical Reproduction,” Leonardo. Supplemental Issue,Vol.3(1990), Digital Image, Digital Cinema:SIGGRPH’90Art Show Catalog, p.37.这里所说的“彼此不同的副本”就是一种“再造”。
在机械复制时代里,人们依靠印刷、摄影等技术手段将艺术复制品通过不同的媒介、方式或形态传递给受众。而在后机械复制时代,即在智能手机、电脑等终端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当下,基于互联网的交互性,受众的接受不再是被动的,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主动参与艺术的生产、接受。如此便对非遗传承主体的技艺传承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技术对传统艺术的传承效果与传播方式展现出了强大的控制力,甚至改变了艺术生产方式以及大众审美接受习惯。
“互联网共生圈层”中的传承人也在应验着社会共生理论,即“个人与社会在共生中,永续不断地互相构建”[3]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例如,互联网共生圈层中的传承人是无法改变互联网的时代性的,他们必须要懂得与科学技术共生。在被誉为人工智能里程碑的ChatGPT诞生以后,通过人们对其进行“奖励”训练,目前已经能够完成信息抽取、机器翻译、智能写作;并通过自然语言的处理可以生成各种文本,如新闻文章、脚本、音频剧本。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经过足够的非遗信息的摄入与训练,有可能会产生新的“格萨尔王”,有可能产生新的戏曲样式,有可能产生新的传奇、俗讲与变文,有可能产生新的“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
三、“四圈共生”中的“斥”与“补”、“危”与“机”
如前所述,“四圈模型”(即家庭或家族共生圈层、族群共生圈层、机械复制共生圈层、互联网共生圈层)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传承人共生模型。从空间上来说是不断递进、由小到大的,从时间上来说是与时俱进、由远及近、由往及今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类似“倒金字塔型”的模型中,是可以按照共生理论来验证每个圈层之间的关系不是断裂的,圈层内部各生命体提供给彼此生存所需的“营养”,可谓“斥”“补”相应、“危”“机”并存。
首先,关于圈层因素“斥”“补”相应。一方面,就“相斥性”而言,如前所述,生活在每一个圈层里的传承人都会受到该圈层的主导因素制约。如在第一圈层里,制约传承人生存和发展的就是技艺“稀缺性”因素或者说是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因素,无论是幼蒙庭训的“父传子”,还是入室弟子的拜师学艺,弟子们都被这种“稀缺性”绑住了手脚变成了人身依附,离开了这种家族式的传承,他们的身份就无法获得业界认同,甚至生活都无法继续,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即是。当然,一些传承人确实在“守正”,而另一些没有创新意识的弟子们却又会将此筑成人生“安乐窝”而无法走出舒适区。但另一方面,就“互补性”而言,另一圈层的诱惑始终存在,弟子们只要挣脱了上述相斥性或者约束性,便会完成一次蜕变或突破。如第一圈层的技艺的稀缺性,会被第二圈层(族群)的“互补性”所吸引。这样,具有创新意识的传承人在成长过程中尽其所能超越原有圈层,因此这一过程是对舒适圈的一种拒斥,也是一次获取更多技艺养分的自我更新的过程。1912年年仅18岁的梅兰芳获得了一次与“伶界大王”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当时谭鑫培已经65岁,面对如此德高望重的前辈,梅兰芳心生敬意,并暗自努力不可出半点差池。这次合作不仅是梅兰芳对原生圈层的一次突破,也是向族群圈层的一次融入,而且是为自己的演艺事业补益更多成长空间的过程,实则完成了一次从拒斥到互补的跃升。由此可见,传承人生存圈层间的“斥”与“补”是相辅相成、营养共生的关系。
再举一个从第二共生圈层(族群共生圈层)向更高圈层迈进的例子,我们可用共生理论来考察时下大热的数字藏品。国家级非遗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传承人魏立中身体力行将木板水印技艺带入大中小学课堂,在国家级、省级博物馆开展各类讲座,还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英国王储基金会传统艺术学院开设木板水印课程。2022年魏立中第一次尝试数字藏品拍卖,作品《一团和气》每件200元,共计5000件,上线后瞬间售空。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传统技艺的热衷,同时也为传承人打开了数字化市场推广的新路径。从“四圈共生”这一模式论来看,经过在木板水印领域的数年深耕,魏立中已经得到了同行、社会,甚至是国际上的认可。如果他仅仅停留在工作室、博物馆和各大院校,那么他还是处在具有一定族群意义的第二圈层(族群共生圈层)。但2022年他对数字藏品线上售卖的一次尝试,不仅是机械复制圈层的升级,也是向着互联网共生圈层的融合。如果按照共生理论的互补性来说,他获得了两大“互补性”,一是进一步发掘了传统文化的艺术生产力(即上文所述的文化因素),二是运用了第四圈层即互联网共生圈层的传播力。当然,2023年数字藏品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从如何促进非遗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充分利用上述“四圈共生”的“两大互补性”是具有一定实践与理论意义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机械复制圈层“丧失非遗灵韵光环”的现状时,只是哀叹制约非遗发展的“相斥性”,而不充分利用互联网共生圈层的“互补性”,我们的非遗事业发展则难以为继。
其次,关于圈层因素“危”“机”并存。由于不同因素主导了不同的圈层,处于不同层级的传承人会受到不同因素的诱惑,一旦突破就有可能为生存创造新的“机会”,但是这种突破也有可能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就是“斥”“补”相应造成的“危”“机”并存。机械复制时代、后机械复制时代给传承人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其挑战是,机械复制剥夺了诸如手工作品等非遗作品存世的唯一性,机械复制生产者以低廉的商品价格抢占了传承人的市场,一些迫于生计的传承人开始迷恋市场带来的利润,甚至脱离创作一线转而投身于市场拓展,传统技艺因此陷于停滞甚至逐渐僵化。其机遇是,新媒体的传播使得部分有见识的受众认识到非遗作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灵性,以及手工制作非遗作品存世的唯一性,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中,反而披沙拣金,使得传承人的技艺有可能得以生存并实现代际传播。这样,技术成为传承的手段,成为活化传统技艺的钥匙,发挥着新兴媒介的传播优势,在看似冲击非遗生存空间的技术面前化“危”为“机”。在今天,非遗作品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传承人的地位也得到极大的提高,非遗事业呈现一派繁荣,其品类之盛便可明证突破圈层获得“生机”的可能性。
此外,理应道明的是,传承人“四圈共生”模式均是按照传承人与圈层的依存度、平衡性、持久力划分的,各圈层中的传承人无不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共生关系之中,即“社会通过共生关系网络,影响个人”[1]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传承人作为非遗传承主体不应错过任何可以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营养”因子里获得滋养的机会。只不过不同的圈层、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空间、不同的影响因子会对传承人产生不同的作用。例如,关于政治因素,在四个圈层尤其是在族群共生圈层中的政府政策支持是传承人获得荣誉感的重要保障(如政府择优命名“传承人”);关于经济因素,在四个圈层尤其是在家庭(家族)共生圈层中的传承人必须能生存或者生活,其创作才有所附丽;关于文化因素,在四个圈层尤其是在机械复制圈层中传承人的文化修养决定了非遗产品的根本意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我们只有在不同的圈层施以不同的引领方法,方能使之获得的引领力最大化。只有充分消除互斥性、发挥互补性,各圈层中的传承人才能生存下来并得到良好的发展。
四、“化危为机”——传承人在AI时代之作为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思考在互联网共生圈层(人工智能共生圈层)中的科技因素对于非遗发展的制约与促进。在这一圈层中,电脑终端通过互联网的“喂料”与“奖励”,不仅可以复制非遗作品,而且还能“创作”非遗作品。我们不禁要问,“灵韵”逝去后的机械复制品或者通过AI “创作”而成的非遗作品是否能够完全替代传统的非遗作品?AI、互联技术又为非遗传承带来了什么?传承人该如何为技艺的传承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些都是关乎当下一些传统技艺传承人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大事。
随着科技的进步,技术虽然可以做到短时间内大量复刻,满足人们对于传统艺术的消费需求,起到普及介绍传统艺术的作用,但纯手工制作的唯一性、稀缺性、人文艺术性(灵动性)则是科技无法逾越的。传承人能否把握住手工艺术的优长并将其发扬,是其能否抵御机械复制带来冲击的关键所在。机械复制的雕刻、版画、蜡染、瓷器、刺绣看似对纯手工技艺有所冲击,却映照出手工制作的弥足珍贵,二者并不排斥,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非遗传承主体可以从机器做不到的地方寻找突破,面向专业受众群,在精细程度、式样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方面深耕,让“光韵”在选择者的手中熠熠生辉。
一方面,技术的裹挟让传承人更加坚定了纯手工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生存于后机械复制时代的人们理应高度重视科技的进步给非遗创作者带来的生存危机。
1. 正视智能技术代替人类基础性劳动成为现实。相较于机械复制,AI的一些“创作”功能确实超过了机械复制。人类只要奉献“思维”,AI就能迅捷完成人类“思维”里想要的结果。例如,就戏曲而言,“梅派”艺术与“程派”艺术风格迥异,但是我们能否用“梅派”的技法来展示“程派”的经典艺术呢?能否用《贵妃醉酒》的声腔来展示《锁麟囊》的故事呢?在现阶段,即使某一门派的演员能够展示另一门派的作品,如张火丁版的《霸王别姬》,但这些演员是有限的,所展示的作品也是有限的。而通过AI技术,这确实是随时可以实现的。
2. 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化危为机”。生物共生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环境的变化诸如山火肆虐、天敌增多等,往往会提升生物的竞争力和生存力。因此,网络时代的数字技术给非遗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却也提升了非遗主体的思考力。例如,近年来流行的沉浸互动式艺术以技术为支撑,颠覆了传统展陈方式,通过构建特殊的光影空间,增强观展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这种互动式艺术在创作者、作品、受众三者之间构建起交错的对话空间,让观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发现作品的价值、意义。2021年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知造局以《刺桐泉州》为题策划了一场环幕投影作品展,通过多台投影拼接形成环幕画面,用四个篇章以大众化、年轻化的影像勾勒出古城的演进,为观众展现了22个遗产的地理分布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与宗教繁盛之间的关联。观众在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里置身于影像的包围之中,如同穿越一般身临10世纪至14世纪以来的泉州,泉州宽容、仁爱的文化品格与历史人文风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数字光影交互展《重返万园之园》,是将清华大学二十多年的科研项目“样式房图与圆明园研究”的科研成果,通过数字影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从历史废墟中还原出圆明园遗址的历史原貌。漫步在“御园莺歌”的光影空间,观众可以用手触碰墙上的动态光点,看荷花绽开、仙鹤展翅;还能身临研究过程,如一个瓦片纹饰、颜色的还原。通过数字交互技术观众可以全方位立体地感受艺术与科技的交融,体会文化遗产的魅力,享受酣畅淋漓的感官体验。
3. 努力将AI等数字技术变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人类艺术传媒史告诉我们,在审美的峰顶上,一定是科技与艺术的握手。例如,古代服饰由于其本身的物理性质,明以前还存世的成衣实物几乎没有,但山东博物馆和孔子博物馆联合利用3D制衣技术对古代服饰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实现了古代纺织品的数字化保护。这些都是传统技艺与数字技术跨界融合的范例,可见数字技术非但没有为非遗带来冲击,反而为其打开了一扇窗。以数字艺术的形式保护非遗传统技艺,使其能进一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互联网共生圈层中的传承人在未来应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5页。其中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表现在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中华民族都能够坚定信心、勇于挑战、无所畏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华夏儿女勤劳与智慧的结晶;传承人作为非遗传承的第一责任人,有责任让非遗的璀璨光辉更加绚烂夺目。这不仅是传承人的责任,更是亿万儿女的心愿。近年来,数字技术的确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非遗传承人顺势而动,学习、运用各类新技术、新科技。在各地非遗展销会上,科技赋能非遗的新玩法层出不穷。数字技术不但满足了人们欣赏的需要,而且通过数字区块链技术也让数字藏品获得了唯一的数字凭证,满足了人们对于艺术品的收藏需求。整个非遗产品的数字化过程涵盖了发行、购买、收藏以及使用。数字藏品不仅形式新颖,价格上也更为民众接受,业已成为非遗走进千家万户的科技新形式,如舞台上活泼生动的皮影、精雕细琢的纹案样式、形态各异的京剧脸谱等,通过数字化赋能让观众可以随身携带、展示,仅在手机之中便能领略传统技艺承载的文化精髓。如前所述,传承人如何将手中的传统技艺融入日常生活是其传承的题中之义,与新技术链接是他们进入更高圈层获得更大展示空间的必经之路,也是助益传承人破圈、创新的方法指南。
总之,在社会共生理论的观照下,非遗传承人或以空间维度、或以时间维度总是处在上述四个圈层中,他们在其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共生圈层中,非遗创作、非遗展陈、非遗体验相较于传统已大相径庭。尤其是关于非遗的审美体验更是建立在多维度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走向跨媒介艺术体验。传承人切不可与时代变革逆向而行,必须找到与新科技联姻之更大可能,主动探求非遗与科技相结合的路径。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可以深入社会生活、丰富乡村建设,还可以赋予数字艺术以中国气质、民族特色,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传承人理应打开思路,努力填补信息科技与传统技艺之间的沟渠,在二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与社会多方面共生的同时主动接触新技术,让技术为非遗的传承做嫁衣,革新展陈方式,提升受众对于非遗的个性化体验,让非遗传统技艺在科技的助力下绽放出“技之灵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