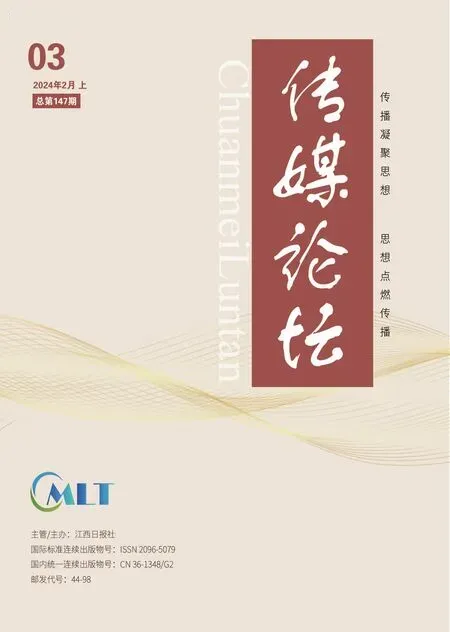时空迷乱:数字电影中的复古未来主义视觉设计
诸 佳
复古未来主义(Retro-futurism)为合成词,是指当代艺术中对早期的未来主义设计风格的模仿。该设计风格将复古风格和具有科技色彩的未来主义风格相结合,通常反映了早期艺术家对未来的构想,如同现实的平行时空一般。复古未来主义在建筑、设计、时装、音乐、影片和电子游戏中均有涉及,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具有复杂的多个面向。在数字电影时代,由于虚拟影像技术的进步,复古未来主义的表现空间进一步得以拓展,其中在视觉设计上有两个较为凸显的趋向,即复古废土设计和赛博朋克设计。其设计理念则都是未来与过去元素的混搭,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能凸显时空迷乱特质的独特的视觉美学形态。
一、复古设计的未来化与废墟化
复古废土设计并没有统一规范的学术定义,可以说是融合废墟美学、废土美学、复古美学等元素,又体现未来主义的设计形式。在数字电影中多呈现为巨大遗迹、无垠荒漠、文明痕迹、未来装置等视觉符号,既蕴含末世内核,又承载复古描绘;既体现宇宙未知的浩渺和无限,又涉及人类文明在此间的绵延与局限。
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系为了还原现实或构建幻想世界,其目的是不断趋近创作者所要表达的视觉意象。复古废土设计是对失落记忆的追寻,要营造一种失落的湮灭感和荒芜感,留下历史的沧桑感与印迹感,又要体现在未来环境中的各种可能性,将历史、传统、虚拟、畅想相融合。这种被创设的“湮灭”,形成废墟美学的数字化投射,即数字废墟在电影中的视觉呈现,具体有以下两种表达方式:
(一)复古元素的未来化
传承自《银翼杀手》(1982) 美学风格的《银翼杀手2049》(2017),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这种视觉意象进行了延续与扩展,如在漫天黄沙中若隐若现的高耸遗迹、极简主义的岩石建筑、荒凉废弃的城市废墟,而在这些复古视觉背景的构建中,又以飞行载具、人工智能等科技元素体现一定程度的未来性,这种通过视觉营造的时间观上的反差带来了强烈的疏离感和异质感。[1]而这种风格在《沙丘》(2021)中有了进一步的展现,其室内场景以大量的巨型浮雕为主,近似中世纪古堡的采光环境,光影风格阴暗浓重,勾勒出古朴厚重的历史纵深;室外场景也以简朴的粗野风格为主,用色与装饰极为克制。[2]而蒸馏服、无重力灯、蜻蜓飞行器、星际舰艇这些影片中出现的未来科技装置,同样秉持着这一设计理念,外观粗犷极简,视觉上的技术要素被降至最低,可以称得上典型的未来复古主义设计作品。这些内涵多元的内容,被统一的视觉风格嫁接在一起,通过神秘主义、古典主义的情节铺陈,共同呈现出一种末世中的挣扎和希望并存的视觉意象,与影片置身未来、回眸过去的叙事主旨完全契合,既能从历史中找到隐约的镜像,又能不断拓展畅想的边界,建构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特定时空。
(二)现实元素的废墟化
《后天》(2004)中经历大冰暴侵袭后的世界已完全被茫茫白雪吞噬,包括各国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均已成为被冰封的遗迹,只能依稀辨认出些许原有的特征,像自由女神像只余半个头部与高擎着火炬的右手在冰面之上。这些注重残破感的设计,通过对熟悉的现实元素的改造与留白,特别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除了以视觉奇观引发观众的感官震撼,更能进一步增强观众的沉浸感与恐惧感。《2012》(2009)沿袭了这一设计思路,并进一步加强了视觉上的破坏感,通过隆起的地表、陷落的空洞、错位的建筑,全景呈现了被海啸与地震摧毁的大都市废墟,更加具象地去表现灾难的暴虐与人类的绝望,也为后续的情节发展定下悲壮的基调。[3]《遗落战境》(2013) 在视觉设计上则倾向于更细腻地表现现实世界元素的破败形态,像月球已被炸裂、沿着破坏的轨迹留下了巨大的空洞与碎石,宛如天空中一条巨大的伤痕;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已与山崖同化,其间有瀑布奔流而下;垮塌斜倾的布鲁克林大桥,一半已被沙土吞噬;在岩层的裂缝深处,是已被绿植覆盖的第五大道。这些无声的视觉场景,通过将现实景物进行奇观化、差异化、废墟化的设计,用视觉语言表述了受众所熟悉的人类世界经历的巨大变迁,表达着一种悲悯、磅礴的末日想象与废土美学。
二、超然设计的未知与诗意
数字电影中有一类视觉景观尤为引人注目,即那些庞大、无垠、未知的物体,被设计为永恒超然的浩瀚存在,反衬的是个体的渺小与消解,但又带有复古与历史的余韵与品格,延伸了人类个体的诗性与意趣,在对未知神秘的敬畏与无尽时空的怅惘中,传达着个体命运的脆弱与梦想。被设计成静默如谜的超然之物,其视觉上所具有的永恒与无尽的审美,也分别对应形成了两种指向。
(一)永恒的未知——神圣性
超然的物体设计,其目的是打造一种超越现有认知的物体,一般会设计得巨大且无法理解。如《迷雾》(2007),在隐晦弥散的大雾中显现影影绰绰的巨大生物轮廓,展现出惊人的破坏力,但始终无法辨别真容。这类巨物在影片中不展现全貌,而是利用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将其塑造为烘托惊悚氛围的重要视觉形象。而《降临》(2016)中的外星飞行体,巨大的碟形外壳封闭整一,外形与材质简朴至极,与一般电影中模仿地球飞机与舰船所设计的外星飞船天差地别,并没有对外的出入口与交流通道,只是静默如山地悬停在地表上空,令人难以探查。这类远超人类现有文明水平的超然物体在设计中兼具复古的外形与超自然的特质,形成了跨越恒久时间之后的神圣形象,会让人不由心生敬畏并自感渺小与无力。《沙丘》(2021)延续了这一视觉美学,其中如都市般超级巨大的星际飞船,设计风格凝重洗练,没有任何的纹理修饰,却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厚重感与写实感。而《沙丘》(2021)中的外星沙虫以沙虫为原型,身长数百米,头部为一个巨大的空洞,内含无数的尖刺形成环状,内里似乎隐藏了大千万物,既像凝视着主角的宇宙之眼,又像吸收一切光线的宇宙黑洞。这一形象和《迷雾》(2007)中的未知怪兽相比,构成了另一重庄严和崇高的视觉形象,代表了自然宇宙的化身,是远超人类理解的范畴的终极秘密。神圣的超然形象,是刻意经过反差与对比,从极简设计中展现极致力量,人类的自尊被消解在庞大的未知之中。在这一剧烈的视觉反差中,人的命运身在其间是漂浮无依的。
(二)无尽的诗意——艺术性
这一设计从另一层面去考量,借由时间和空间的互换,从美学的维度体现为无尽绵长的诗意。《星际穿越》(2014)中的五维空间将时间以物质形式来呈现,用“线段+超立方体”的复杂架构,构建时间线上的每一时刻都能同时呈现的视觉奇景,完全打破了以往数字电影中空间设计的模式。同样是打破线性时间的束缚,《降临》(2016)中的外星文字,以圆环形上的不同触端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不仅秉持了与外星飞船一贯的复古风格,而其与人类文字最大的不同,在于并非采用线性的思维路径,而是传达时间线上非线性的内容。这种违反人类时间观的文字,展现了万千宇宙中的另一种可能的表达方式。[4]还有一类体现时间之永恒性的是数字电影中的各类巨型雕塑。《指环王:护戒使者》(2001)中在诸王之门前耸立的两座巨型雕塑,是中土世界中人类王国的缔造者的形象,代表了不受时光侵扰的威严与不容侵犯,为电影世界观中历史环境的构建提供了更为丰沛的艺术支撑。同样,《普罗米修斯》(2012)中的巨大头像,既代表了已消逝的过往,也是人类被放置在时间维度下之短暂与渺小,是永恒宇宙与瞬时生命的矛盾。其他如《星际穿越》(2014)中对黑洞的刻画,在巨大星体重力的影响下,时间被无法阻止地加速流逝;[5]《太阳浩劫》(2007) 中近似被神化的太阳,是单向朝圣之旅的最终目的地。电影中以数字虚拟技术构建的这些巨大物体,实质上却是思索人之存在意义的实验场。在永恒超然的背景下,除了凸显人的局限外,同样投射出时间的诗意,以及人作为个体之熠熠星光。人类在被放置在巨大存在的面前时,既有对世俗烦扰的超脱与释然,又闪现人之自我救赎与主动抉择的个体光芒。
三、赛博朋克的“矛盾”设计
赛博朋克(Cyberpunk)作为一种亚文化趋向,是复古未来主义的重要表现类型。Cyber意味着虚拟,而Punk则意味着叛逆,这个合成词天然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它往往描述不可一世的权威,却又用元素丰富的画面大量展现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群,从而表现人性中的麻木顺从和反抗一切权威这两种相互矛盾本能。而在视觉设计上,常表现为陌生与熟悉的对冲,技术与人性的撕扯。
(一)陌生与熟悉的对冲
在赛博朋克的电影世界里,总是有下着大雨阴暗狭窄的贫民窟,也有着摩天大楼高耸入云的后现代未来都市,是陌生与熟悉的混合和对冲。虚幻与现实的纠缠,是探讨数字视觉无法回避的永恒课题。数字电影中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已经模糊,现实世界的崩溃与消失,往往意味着真实与虚幻进行了潜在的互换。[6]《黑客帝国》(1999)中的所谓“现实”,是绿色的代码世界,是经过扭曲的虚拟镜像,原有的现实幻化为绿色的数字序列而崩溃,这种反差产生的张力形成了独特的视觉冲击。[7]随着技术的迭代,赛博朋克凭借全息投影、3D投影、霓虹灯、VR等视觉元素呈现出了越来越类型化的美学风格,视觉上的科技感和未来感不断增强,这一切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充满陌生感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也有熟悉的英雄悲歌式故事,垃圾成堆的阴暗角落,贫富差距的现实困境,且往往主打阴郁美学。如《银翼杀手2049》(2016)彰显了这类典型的赛博朋克风格,缤纷炫目的色彩混搭,暗黑意象的主旨表达,繁华的街道看起来毫无生机,潮湿拥挤的生活环境凸显数字虚拟世界的压抑,深蓝、暗红色系的使用暗示人与人的陌生与疏离。[8]数字影像的变化与幻灭,凸显的是人心的悸动、挣扎与释然。
(二)技术与人性的撕扯
高科技、低生活是赛博朋克电影视觉设计的核心,也体现了废土电影的特性,和前述废墟化的复古未来设计一脉相承。赛博朋克世界中的残破的文明与缺失的希望,带有独特的废土美学特征,这既是对过往消逝文明的见证,又留下无穷解读的空间余韵。这类未来感与湮灭感共存的混合表达,可视为数字化视觉诗性的独有面向,同时也是众多赛博朋克电影中技术与人性撕扯的具象表现。在《移魂都市》(1998)压抑阴暗、永无白昼的未来世界中,技术对人的改造令人的本质日益模糊,技术与人性的矛盾被放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中进行展现。巨变的科技对当代人类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力,以及旧科技与架空新科技相遇所带来的震撼感,是此类影片的核心表达。[9]《阿丽塔》(2019) 主人公重生的废铁城是建设在机械废料中的都市,肮脏逼仄而又混乱残酷,但真实可感,而空中都市则是不可触摸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是另一维度的理性无情的掌控者和操盘者。两个城市视觉上的强烈对比,也彰显了人性在技术的挤压之下慢慢丧失和异化。[10]这些超现实的视觉奇观都是在科技与美学的共同支撑下建设出了逼真的城市景观,书写了充满想象、具有视听震撼特质的赛博视觉美学。
四、结语
从上述复古未来主义在数字电影的视觉设计可见,复古未来主义混合了未来和过去两条相互纠缠的视觉脉络。一方面,以未来主义为肌理,以现有技术趋势为基础,以视觉艺术家对未来的构想为血肉,勾勒出未来的视觉景观,同时令受众强烈地感受到难以脱离过去的羁绊和传承,呈现出一种动态的随技术和历史不断跳跃的视觉形态;另一方面,以复古主义为锚点,在艺术审美复古化的同时将未来的幻想元素进行一种错位的配置和拼贴,营造混沌的时间万花筒般的迷宫,以及一种在熟悉的境况中却难以自我定位的失衡感和不稳定感。
回到数字电影中的复古未来主义,以人的视角为基准,这些数字视觉意象始终聚焦在湮灭与存在的命题上,因为人存在的先天物理限制,决定了其期望在虚构作品中打破、重塑并探索时间与空间的种种可能。数字废墟碎片的痕迹,赛博朋克美学的氤氲,静默如谜的神秘未知以及被消融的边界,人在历史与未来的无尽夹缝中寻找自己与世界的真相,并用记忆与想象去度量时间与空间。这种哲学、艺术与技术上的探索本身就值得记录与传达。毕竟,人性即生命与共情。时空的湮灭与复现,可作为诠释、观察与见证数字时空视觉意象的诗性之眼。从这一视角,复古未来主义视觉意象设计与历史、记忆与幻梦形成互文,共振出永恒与转瞬的诗性美学。
现代电影以数字技术构建的复古未来主义视觉意象,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桎梏,在非线性的视觉叙事脉络中,以碎片化的数字废墟重塑已经湮灭的过往,以未知浩渺的静默消融现实的存在,以无限多重镜像虚拟时空交错的迷幻霓虹。从此意义上观察,复古未来主义设计混合了毁灭与重生、宏大与人性,是失落中的创造,是超然中的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