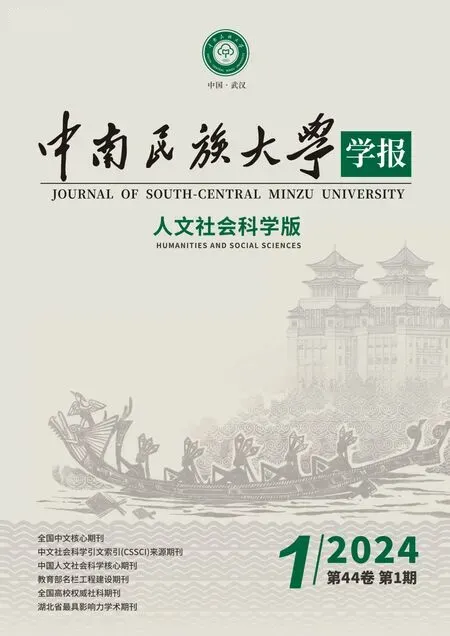闲居的诗思:士不遇焦虑消解与自我形象书写
邹福清 程 鑫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士不遇现象由来已久。《诗经·大雅·柔桑》较早表达士不遇主题。其中,芮伯哀叹“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流露出其“朝不可仕,不如在野。然即退处亦难安居”[1]的心理。《诗·邶风·柏舟》“言仁而不遇”(《毛诗小序》)[2]154,汉代郑玄解释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2]154孟子曾感叹“不遇”于鲁侯[3]53;荀子曾慨叹“嗟我何人,独不遇时当乱世”(《成相篇》)[4];还有屈原、宋玉等,都是不遇的文人。《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国古代士人实际以立功为上,功成身退才是理想境界。然而,立功就要入仕,入仕一旦被阻,再高调宣称退隐的好处,其实是牢骚话、愤激语。士不遇既指一种现实处境,也指一种心理感受。隐逸于山林的文人固然产生不遇心理,朝廷官员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时也会产生不遇心理,如“朝隐”的张衡、“吏隐”的谢朓、“中隐”的白居易。
古代士人如何消解士不遇的焦虑?从三国时期的嵇康,到中唐的白居易,再至北宋的邵雍,是古代士人探索对不遇焦虑的调适与消解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嵇康“乐道闲居”,一生基本处于闲居状态;白居易闲居洛阳达18年,提出“中隐”说;邵雍绝意科场后闲居于洛阳,标举“安乐”境界。他们的政治身份不一,退隐动机也不相同,价值观念存在分歧,但难掩其共同的文化追求:走出士不遇焦虑的困境,实现现世性的精神超越。在此精神超越之旅中,建构闲居期间日常生活的价值成为重要维度,嵇康、白居易、邵雍都在这个维度的思考与实践中作出了突破性贡献。他们在书写士不遇焦虑的调适与消解、人生境界及自我形象时,将屈原的凤凰和凡鸟对立与错位书写模式进行转换,也呈现出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6]47的贡献。
一、强调闲居的价值:嵇康的“逍遥”境界与自我形象
嵇康“仰慕严、郑,乐道闲居”(《幽愤诗》)[7]43,一生基本处于闲居状态。他“性复疏懒”“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与山巨源绝交书》)[7]196,约20岁移居河内山阳至40岁去世,主要居住于此。因娶沛穆王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迁为郎中,再升为闲官中散大夫。曾一度居住洛阳,与向秀一起锻铁,到太学抄录石经。也曾拒绝做官而避居河东3年,一度至汲郡天门山从游隐士孙登约3年。嵇康沿袭老庄的思想,对政治持悲观态度:“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太师箴》)[7]534他还目睹了司马氏与曹氏争权过程中齐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被弑等惨烈的政治事件。这些影响了他对现实及自身处境的体认:现实社会就像一张让人无处可逃的巨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其一)[7]5,而“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杂诗》其六)[7]137。再结合《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表达的“必不堪者七”[7]197可以看出,“网罗”既包含曹氏与司马氏两个集团之间残酷倾轧给士人带来的压抑的政治环境,也包含“施报更相市”“权智相倾夺”(《答二郭诗》其三)[7]109的人际关系。因此,嵇康的闲居既出于本性,也是为了逃避政治的险恶。
嵇康继承庄子的“逍遥”人生境界。嵇康曾拟《卜居》作《卜疑》,对人生进行了思考。在占卜之前,作者已表明自己“思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执竿”的人生志趣。然后,列举28种人生选择。最后,借占者之口道出:“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人间之委曲。”[7]236-237这是庄子的逍遥人生境界。嵇康常将理想人生境界的空间放在“区外”,即想象的仙境,从其游仙类诗作可见一斑:
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戏灵岳,弹琴咏泰真。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一纵发开阳,俯视当路人。(《杂诗》其七)[7]137-138
在其宴饮、赠答等题材诗文中,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更加直观,主要描绘日常生活情境并剖白内心。分别以其宴饮、赠答诗为例: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酒会诗》其二)[7]126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其十五)[7]24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将其理想人生境界表述得最具体、清晰:
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7]199
不论是现实还是仙境,嵇康笔下的理想人生境界主要以弹琴、啸歌、垂钓、打猎、泛舟等为主要内容。这实际上是将日常生活作为政治生活的对立面,使其具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也就是将人生安顿在日常生活中。因此,罗宗强认为,嵇康是“第一位把庄子的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为人间境界的人”[8]。
亲情、友情等私人情感对于嵇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嵇康区别情与欲。“欲”指本能,与生俱来,需要加以抑引,即“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答难养生论》)[7]296。“情”是善的,经过了“智”的调节而与大道无违,“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释私论》)[7]402。其次,从积极方面主张“任自然”,从消极方面主张“无措”(《释私论》)[7]402。“任自然”或作“任心”。嵇康所谓“心”相当于“情”,“情”是自然,是人的本性,因此才可以“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释私论》)[7]403。“无措”是“心无措乎是非”“心不存于矜尚”(《释私论》)[7]402,即要求行为主体不计虑是非、善恶、得失而迎合名教,意在防止出于功利目的而滥用名教。总之,只要做到“任自然”和“无措”,可以“言不计乎得失而遇善,行不准乎是非而遇吉”(《释私论》)[7]403。但亲情、友情在嵇康心目中何以成为价值所在?嵇康系狱所写《幽愤诗》道:“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7]43一旦将人生价值取向转至对人性本真的呵护,日常生活中的亲情、友情可以从“任自然”的高度被视为人性本真的表露,是心灵自由、精神超越的表现。嵇康在现实生活中,为朋友吕安仗义直言而不惜招致灾祸,以及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将“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作为自己的人生境界,均源于此思想认识。嵇康只是“托于老庄忘情”,实际是“情至之人”[9]218。在嵇康所处时代甚至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日常生活作为政治实践的对立面出现,亲情、友情等私人情感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常见于文学作品,既有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10]130-131的陶醉,也有鲍照“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11]的愤激。但是,除稽康外,尚未有其他作者从呵护人性的高度建构私人情感的价值。
嵇康否定了当时通行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王康琚《反招隐诗》)[12]952的山林之隐和吏隐,在思索与实践闲居生活的意义、调适士不遇焦虑的进程中向前迈出了一步。嵇康秉持“养素全真”的人生价值观,退居的空间不是林薮、仙界、田园,而是日常生活,通过建构日常生活的精神价值来超越对抗政治生活的功利目的,化解不能入仕或不愿意入仕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钟嵘称嵇康诗“托谕清远”[13],刘勰称“嵇志清峻”[6]67,造就“清远”“清峻”的正是其人生选择所造就的超凡脱俗的人格。但是,闲居的嵇康难以真正达致内心的安宁,起码无法慰藉内心的孤独,就像其《述志诗》其二所说:
何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幽微。[7]62
闲居虽是观察与思考现实后作出的冷静选择,但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难怪明末清初,陈祚明说嵇康“托于老庄忘情”是“愤激之怀,非其本也”[9]218。不仅如此,嵇康还将其价值追求凌驾于礼法之士汲汲于功名利禄追求之上并加以嘲弄,使自己成为当政者的对立面。难怪隐士孙登对嵇康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14]而后,陶渊明将隐逸的空间转向田园,努力在田园生活中实现超越,基本沿袭了嵇康建构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的途径。萧统评价陶渊明使用的“任真”(《陶渊明传》)[10]611一语,实际就是嵇康的“任心”,他既指出了陶渊明与嵇康之间审美价值追求的渊源,也揭示了陶渊明以田园生活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10]430的批判。
挣脱网罗、远翔“区外”的“鸾凤”是嵇康自我形象的隐喻,如“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游仙诗》)[7]561和“鸾凤避罻罗,远讬昆仑墟”(《答二郭诗》其三)[7]109。嵇康诗歌也表现凤凰和凡鸟的对立与错位,如“斥鷃擅蒿林,仰笑神凤飞”(《述志诗》其一)[7]62,但更多描写的是凤凰远翔异域的情景,如“眇眇翔鸾,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凌蹑玄虚,浮沉无形。将游区外,啸侣长鸣”(《杂诗》其三)[7]136。可以看出,先秦两汉士人有着以凤凰隐喻、对现实与处境体认的文学传统[15]。《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其一“双鸾匿景曜”[7]5几乎是一首关于凤凰的咏物诗,现置《嵇康集》之首,可视为嵇康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以及对人生道路选择的思考的隐喻。如果说汉代文人笔下高飞不下的凤凰传达的是对君德的吁求,那么嵇康诗中远翔异域的凤凰则传达的是对当政者甚至整个社会的批评。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称嵇康“风姿特秀”,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称嵇康“龙章凤姿”[16],此评价应该是从嵇康诗中的鸾凤形象得到启发。“鸾凤”渐渐成为后人对嵇康形象的想象。南朝颜延之可谓嵇康的知音,其“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五君咏·嵇中散》)[12]1235之语,道出了嵇康的孤傲品性与艰难处境。南朝江淹的《杂体诗·嵇中散康言志》曰:“灵凤振羽仪,戢景西海滨。”[12]1572明末,夏完淳在《嵇叔夜言志》中云:“灵凤矫羽翼,飘然云际飞。”[17]均把嵇康塑形为高飞不下、远栖他方的凤凰。
二、悬置闲居的价值:白居易的“闲适”境界及自我形象
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白居易在谪居江州期间思考进退出处时,萌生过“吏隐”的想法,如其在《江州司马厅记》中云:“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18]933他也产生过归隐山林的想法,庐山草堂山居生活便是尝试。长庆二年至四年、宝历元年至二年分别出刺杭州、苏州期间,白居易才真正践行“吏隐”。例如,他任杭州刺史时,作《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因严亭》云:“箕颍人穷独,蓬壶路阻难。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18]448任苏州刺史时作《郡西亭偶咏》云:“莫遣是非分作界,须教吏隐合为心。”[18]534都表明其“吏隐”的心志。从大和三年分司东洛,至会昌六年去世的近18年,白居易基本居于洛阳,称此时的生活为“闲居”。大和三年,白居易提出“中隐”说,并在《中隐》《咏所乐》等诗中阐发其内涵。他为居洛期间的诗作写序时,曾慨叹“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序洛诗》)[18]1474,可以窥见其以“中隐”说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
中国古代士人居庙堂之高,梦想退隐时的洒脱;处江湖之远,则渴求建功立业的荣耀。心灵往往徘徊于仕与隐之间而承受焦虑之苦。东汉张衡称“聊朝隐乎柱史”[19],魏晋时通行“大隐隐朝市”,都是郭象所谓“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20],其实质是“涵容作为终极追求的入世仕宦事业与作为心性超脱的出世自然生活,平衡政治体制与个体人格的矛盾”[21]112。魏晋南北朝,士人倡导的“吏隐”是针对太守等地方官员对“大隐”作出的调整,试图利用公务之暇的日常生活缓解公务的压力或贬谪的焦虑。但是,“吏隐”依然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无法解决“身心相离”[21]112问题,更不能超越现实。白居易也曾践行“吏隐”,其郡斋诗显示了这一点。他后来又提出“中隐”,通过悬置隐与仕、穷与通的差异和对立,对价值有无高下不以为意,不作思考。“中隐”“将身和心重新合一”[21]112,理论是洪州禅的“平常心是道”[22],是不问是非、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既不执著于染又不执著于净,即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23]157“热即取凉,寒即向火”[23]210。“平常心是道”瓦解了持戒、诵经、坐禅等宗教生活的神圣性,并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变成修行的方便法门,实际抬高了日常生活的价值。“‘空’的思想把一切都放在了否定的位置上,同时又把一切放在了肯定的位置上。”[24]白居易深受洪州禅的影响,“浸染洪州禅学”。谪居江州时,跟马祖道一法嗣智常、持律兼行禅的神凑等过往密切。闲居洛阳时,又跟马祖道一弟子如满过往甚密[21]108-110。其谪居江州时,作《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云:“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闲居洛阳时,又作《吾土》云:“身心安处是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18]642即是对“平常心”的诠释。
白居易的“中隐”以“闲适”为人生境界。白居易称其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与元九书》)[18]964“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序洛诗》)[18]1475的作品。学界将“闲适”解释为“从公务中解放出来的完全自由的时空”和“身心都毫无拘束感与不自在感的境界”[25]5,或解释为“无事”,即“无可无不可的态度”[26],都是强调闲居时身心的自由与安适。诗人居洛时作《三适赠道友》自矜足适、身适和心适[18]672,《北窗三友》称琴、酒、诗为三友[18]665-666,都体现了这一点。游赏、宴饮、睡眠、垂钓、读书等日常生活跟洪州禅的衣食住行一样具有修行意义,成为白居易“闲适”境界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安眠’与‘饮酒’,作为使白居易的‘闲’境得以成立的核心活动,被反复地叙述。”[25]7白居易的“中隐”将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价值高下搁置起来,为退居文人指明了消解不遇焦虑、追求人生超越境界的新方向。
白居易服膺庄子,也信奉洪州禅。在贬谪江州前夕,他作《赠杓直》称:“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18]125贬谪江州途中,又作《读庄子》云:“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忍得无何是本乡。”[18]318学界讨论过庄、禅在白居易思想中孰重孰轻的话题,或认为白居易“外虽信佛,内实奉道是”[27],或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庄禅合一的倾向”[28],或认为白居易“在二者之间作出轻重判断时,则始终置禅于老庄之上”[21]125。笔者以为,与其讨论白居易思想中庄、禅孰重孰轻,还不如讨论诗人对庄、禅思想的取舍问题。大和年间退居洛阳时,白居易曾作《读庄子》云:“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胜蛇虫。”[18]716他接受了庄子“逍遥”和洪州禅“平常心”的超越境界,但没有完全接受二者的本体论,也无法将进与退、巧与拙、贤与愚、是与非等同起来。既然此差别无法抹杀,那到底如何才能实现“逍遥”或“平常心”呢?大和三年,白居易任职长安时作《对酒五首》,其一云:“巧拙贤愚相是非,何如一醉尽忘机?君知天地中宽窄,雕鹗鸾皇各自飞。”[18]598又作《喜与杨六侍郎同宿》曰:“浊水清尘难会合,高鹏低鷃各逍遥。”[18]742巧与拙、贤与愚、进与退的确有差别,但只要不去追问这些差别,而是将其悬置起来,就可以超越压力与痛苦。可见,白居易不论信仰庄子还是洪州禅,都是试图突破仕与隐、朝与野、穷与通二元对立带来的心理压力。
白居易初谪江州,常引屈原为同道,十分同情屈原,“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偶然》其一)[18]345,但他否定屈原不愿调和仕与隐、出与处的决绝态度:“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咏怀》)[18]341不过,白居易受到了屈原的凤凰和凡鸟的对立与错位书写模式的启发,在悬置闲居与入仕价值高下的判断时,将其置换成凤与鱼的飞沉异势,并以“潜鱼”书写自我形象。谪居江州期间,好友钱徽被罢翰林学士,而另一好友崔群入相。于是,白居易思考如何面对进退出处:“泥泉乐者鱼,云路游者鸾;勿言云泥异,同在逍遥间。”[18]138诗中以云路中的鸾和泥泉里的鱼分别喻入仕与退处,潜文本既有屈原的凤凰与凡鸟的对立,也有唐人常说的“云泥之别”。不过,诗人将“逍遥”作为终极追求,化解了鸾与鱼的对立。此后,白居易多次以凤、鱼为喻表达对仕与隐、出与处的体验与思考。大和初年,他于长安作《玩松竹》,其一云:“栖凤安于梧,潜鱼乐于藻。”[18]225以凤与鱼表达了其升沉异势却各安其分的观念。晚年闲居洛阳时,又作《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相府》云:“双凤栖梧鱼在藻,飞沉随分各逍遥。”[18]778以“凤栖梧”喻杨嗣复、李珏入相,以“鱼在藻”喻诗人和刘禹锡闲居,称自己虽居闲职,却能逍遥自适。
白居易曾苛责嵇康没有及时真正“出世”:
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彼戮辱时,奋飞无翅羽。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读史》其二)[18]38
“中隐”生活需要四个要素:政治、经济、风景和交游[29]33,嵇康所处政治环境显然比白居易的恶劣得多。嵇康正是缺乏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才没能真正“出世”。白居易其实了解嵇康及其所处的时代,并从嵇康的命运中吸取了教训。白居易与嵇康都看到了闲居期间日常生活对于消解士不遇焦虑的重要性,但他们对入仕的价值判断却迥异:白居易无法否定入仕对于“中隐”的重要性,而嵇康彻底否定入仕。
三、重建闲居的价值:邵雍的“安乐”境界及自我形象
邵雍曾“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30]12726。因此,朱熹说“康节本是要出来有为的人”[31]。北宋皇祐元年,邵雍绝意仕进,迁居洛阳。其间还以疾病为由,谢绝举荐。起初,寄居天津桥畔道德坊的天宫寺;随后,友人为其置宅于履道坊;嘉祐七年,友人在道德坊为其置建新居。此时,邵雍对处境的体认是:“有人若问闲居处,道德坊中第一家。”(《闲居述事》)[32]61将其居所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并一度择居于此。邵雍是如何调适退隐的焦虑心理,其“安乐”与白居易的“闲适”又有何异同?
邵雍标举“安乐”的人生境界。邵雍迁居洛阳,在友人的资助下逐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与白居易闲居洛阳时的境况相同。但是,不同于白居易搁置闲居生活的价值判断,邵雍努力重建和实践闲居生活的价值。他曾剖白隐居的心态:“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首尾吟》其七十三)[32]418邵雍的“乐”包括“名教之乐”和“观物之乐”[32]2。“名教之乐”是通过道德实践来提升人格获得的快感;“观物之乐”是探求宇宙化道并融入自然,从而获得生命共感[33]。邵雍从追问天地之道的学问中获得快乐,也在提升道德修养中得到满足。他在《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中剖白了关于人生选择的思考: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知于人而发挥才能,“道之未行兮,其命也在天”,强调“安分”与“委命”[32]8。他还在《答人书》中重新解释“人爵”与“天爵”的区别:“卿相一岁俸,寒儒一生费。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尝匮?不有霜与雪,安知松与桂?虽无官自高,岂无道自贵?”[32]55《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3]271天爵表现为品德的差别,人爵表现为官职的差别。白居易称“身闲当贵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18]612,将孟子天爵的道德内涵置换成心灵的境界。邵雍则回归孟子天爵,将道的追求作为天爵的内涵,认为卿相与寒儒虽人爵不同,但在道的追求上可达到同等的天爵。这实际上重估了出世的卿相与隐居的寒儒的地位差别和人生价值。
每年春秋季,邵雍出游洛阳城,“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窝’”[30]12727。“行窝”应该从名教与观物两个层面来理解,邵雍实际是将游赏、宴饮等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哲学与道德实践,努力践行与社会、自然的和谐。需要指出是,“安乐”境界与物质条件并无关联。邵雍不刻意回避物质生活的富足,只是以过度为戒。他爱饮酒,爱赏花,但主张“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批”(《安乐窝中吟》其十一)[32]197。他不仅在生活优裕时秉持安乐态度,而且在生活贫贱时也秉持安乐态度。初至洛阳时,他生活很贫困,“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30]12727;即使在迁至新居时,还是过着“岁时耕稼,仅给衣食”[30]12727的生活。四库馆臣云“邵子抱道自高,盖亦颜子陋巷之志”[34]1322,邵雍的“安乐”是颜回安贫乐道的延续和在新环境下的变异。他将立德置于立功之上,通过彰显闲居期间的体悟天道与实践道德的价值,来重估仕与隐、立功与立德的高下,也就消解了仕与隐之间选择的焦虑。
邵雍关于本体论和人格论的表达,也受到屈原的凤凰与凡鸟对立错位书写模式的影响。他认为,构成宇宙的阴阳二气具有善与恶的伦理特性并以凤凰与蛇蝎来标示,“唯天有二气,一阴而一阳。阴毒产蛇蝎,阳和生鸾凰”(《唯天有二气》)[32]116;继而沿袭屈原将凤凰与凡鸟对立的思路,以凤凰与凡鸟的对立来表现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如“如鸾如凤,意思安详。所生之人,匪忠则良。如鼠如雀,意思惊躩。所生之人,不凶则恶”(《观物吟》)[32]340;还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善与恶的对立来解释历史,将历史的演变归因于执政者对善恶的选择:“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观物篇》之五六)[35]不过,邵雍在建构和书写其自我形象时没有借鉴屈原,而是另辟蹊径。
首先,邵雍通过“观物”所得来建构和书写自我形象。他将洛阳宫城五凤楼作为重要观照对象,体认世事变幻。五凤楼是宫城正南门,因城楼和两边的垛楼、阙楼恰似五只凤凰而得名,又称凤凰楼。“安乐窝”位于洛水南岸,通过天津桥与北边皇城正南门相连,邵雍常驻足天津桥观照五凤楼。如“五凤楼前月色,天津桥上风凉”(《小车六言吟》)[32]285“凤凰楼下天津畔,仰面迎风倒载归”(《安乐窝中吟》其五)[32]169等。邵雍伫立天津桥,向北方眺望,流露出阅尽兴亡的沧桑感,“危亭独坐人,浪把兴亡阅”(《天津晚步》)[32]242,继而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真是“诗是天津伫立时”(《首尾吟》其十)[32]410。咏怀组诗《天津感事》或借景抒情,或咏史怀古,主题是对兴亡盛衰之叹及人生选择的反思。其诗云:
凤楼深处锁云烟,一锁云烟又百年。痛惜汾阴西祀后,翠华辜负上阳天。(其三)[32]58
凤凰楼观冷横秋,桥下长波入海流。千百年来旧朝市,几番人向此经由。(其九)[32]59
作者置身凤凰楼上,在超越物理时空的范围内观察到变迁景象。由立足天津桥眺望凤凰楼触发的兴亡之感可由《雨后天津独步》概括:“洛阳宫殿锁晴烟,唐汉以来书可传。多少升沉都不见,空余四面旧山川。”[32]193
其次,邵雍通过物我关系的体认来建构和书写自我形象。他先将五凤楼、天津桥等洛阳城市地标构建为颇具政治意味的文化空间,然后强调其与该文化空间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反差来建构和书写自我形象。邵雍反复书写凤凰楼、天津桥,显然是强调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意味。《天津幽居》就是表达诗人对洛阳城及天津桥的权力文化意味的体认:
予家洛城裹,况复在天津。日近先知晓,天低易得春。时光优化国,景物厚幽人。自可辞轩冕,闲中老此身。[32]56
“日”“天”常用来指帝王、皇权,“日近先知晓,天低易得春”是说诗人置身于政治文化空间的中心。《六十五岁新正自贻(熙宁八年)》“虽然在京国,却如处山涧”[32]285将以天津桥为中心元素构成的政治文化空间“京国”视为“山涧”,显然是以诗人与政治中心的物理距离的迫近来反衬其与政治中心的心理距离的疏离。
当友人在道德坊为其新居购置园林时,邵雍赋诗答谢,流露出对生活方式的欣喜:“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32]248他在《伊川击壤集》中反复表达此义旨,如“凤凰楼下逍遥客,郏鄏城中自在人”(《安乐窝中酒一樽》)[32]169“郏鄏城中,凤凰楼下”(《自适吟》)[32]271等。既然作为道德和哲学实践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一样具有价值,闲居又怎会让人焦虑?邵雍的“安乐窝”与司马光的“独乐园”,虽然在标明退居时努力超越焦虑、达致乐观心理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显示出他们精神状态存在的差异。绝意仕进的邵雍从卫州共城迁居洛阳,生活水准与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安乐”传达的是其内心对于物质与精神的满足。而司马光从枢密副使退居洛阳著书,“独乐”却暗含着怀才不遇的愤激,“身病尚未攻,何论疗民瘼”[36]6066才是其真实内心写照。
邵雍从未提及白居易,但是其生活空间到处有白居易的痕迹,诗作与白居易一样频繁使用“闲适”“安乐”等话语。四库馆臣认为,“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34]1322。邵雍的朋友司马光也持此看法:“只恐前身是,东都白乐天。”(《戏呈尧夫》)[36]6213尽管邵雍诗的语言、技法乃至立意等与白诗有相似之处,二人也都注重日常生活的书写,但他们的旨趣却存在差别,特别是邵雍的“闲”与白居易的“闲”并不相同:白居易的“闲”是悬置仕隐价值高下判断而达到的心中“无事”状态,其理论背景是洪州禅的“平常心是道”;邵雍的“闲”则是洞彻外物及物我关系的自由与欢欣,其理论背景是先秦儒家的“安贫乐道”。
士不遇焦虑必须在现世而不是在来世或天堂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精神超越的智慧。屈原、宋玉及汉代文人没有找到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方式,魏晋以后的文人通过重估、建构闲居期间日常生活的价值对抗政治实践的价值来调适不遇的焦虑,走上一条现世性的超越之旅。这种超越包括以下三个逻辑层面:其一,肯定闲居的价值、否定出仕的价值;其二,不作价值高下的思考与评判;其三,肯定闲居与入仕同样具有价值。名士嵇康强调闲居的价值、否定入仕的价值,诗人白居易悬置闲居与入仕价值高下的评判,理学家邵雍重建闲居的道德实践意义,使其与入仕具有同等价值。他们利用道家、佛教或儒家的思想资源,成为中国古代士人寻求精神超越旅程的重要领路人。中国文人闲居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不再因不遇而栖栖遑遑。日常生活具有修行的意味,也是诗意所在,成为山林、田园之外又一个灵魂安顿之所。中国古代文人逐渐能够通过心理调适,超越士不遇焦虑的痛苦,保持平静与快乐,甚至“对痛苦的超越成为了一种道德原则”[29]170。同时,在“诗可以怨”的传统之外,文学创作也注重表达日常生活带来的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