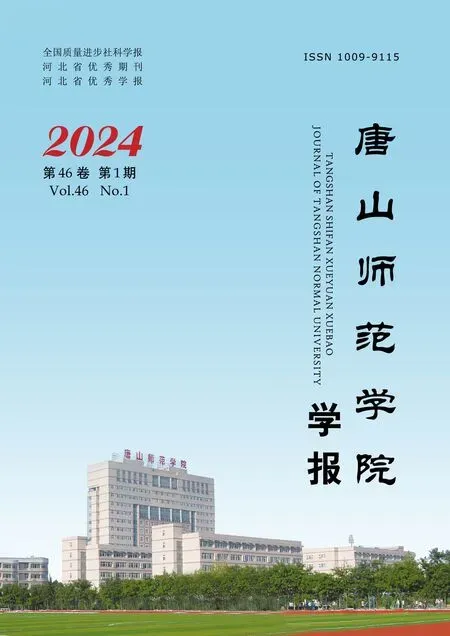《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严雨家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尚书》是“政书”之祖,在儒家思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段玉裁对《尚书》研究极感兴趣,其称“经惟《尚书》最尊”[1],并著有《古文尚书撰异》(下称《撰异》)。段氏《尚书》学成果除了《撰异》以外,其《说文解字注》(下称《说文注》)遍引群籍,囊括了《尚书》在内的经史子集等诸多文献。据余行达《〈说文解字〉引用书籍及通人简表》统计,《说文》引《尚书》共164见[2],故段氏在注释《说文》时,十分注重对《说文》所引《尚书》的研究。学界对《说文注》暨《说文》引书研究比较充分,如“征引赋类文献考”[3]“对《诗经小学》训《诗》的继承与发展”[4]“对《方言》的征引及探究”[5]“引《孟子》训诂研究”[6]“引《周礼》考”[7]等,涉及文献、训诂、语言、文化等方方面面,而对《说文注》中的《尚书》研究较少,研究《说文》段注中的《尚书》训诂,意义有以下两点:第一,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的过程中征引了大量《尚书》训诂材料,通过全面考察《说文》段注中的《尚书》训诂材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群经训诂在解释和阐发《说文》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二,段玉裁身处乾嘉时代,严谨的考据成为学术研究的利器,古音研究臻于完善,因声求义作为训诂学的重要方法,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运用,这两点都是前人所不具备的条件。因此,段玉裁在《尚书》训诂上有超越前人之处,研究其《说文》段注中的《尚书》训诂,将有助于准确定位段玉裁在《尚书》研究史上的地位。
一、《说文》段注引《尚书》训诂证字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辞书,在训诂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清初以来,随着经学复兴,作为经学研究工具的小学也愈发得到学者的重视,于是《说文》研究风靡一时,段氏《说文注》是其中成就最高的。《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字古义,段氏为了证明字词的本义、假借义、引申义,征引了大量古书训诂,《尚书》训诂为其中重要材料。
(一)《说文》段注引《尚书》训诂,证字的本义
“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8]788《说文》通过分析小篆的构形体系来揭示字的本义,其不仅反映出文字初期的造字意图,同时还能探索古代典籍中使用的实义。《尚书》是许书释本义的重要古籍之一。
段玉裁用《尚书》训诂证明字的本义,如:
“琨”之本义为美丽的石头,《说文·玉部》:“琨,石之美者。”段玉裁用《尚书·禹贡》来证明“琨”之本义,他在“琨”下注:“王肃及某氏注《禹贡》皆曰:‘瑶、琨皆美石’……从王、昆声,《夏书》曰:‘杨州贡瑶琨。’”[8]28
“呱”之本义为小儿啼哭声,《说文·口部》:“呱,小儿啼声。”段玉裁用《尚书·皋陶谟》来证明“呱”之本义,他在“呱”下注:“《皋陶谟》:‘启呱呱而泣。’从口,瓜声。”[8]95
许书成书于东汉,经历漫长的岁月后,至清已出现了大量的讹误,故段氏除了用《尚书》训诂来证明许慎《说文》字词之本义以外,还利用《尚书》训诂来校订《说文》释本义的讹误,如:
1.《说文·言部》:“误,谬也。从言,吴声。”段氏注云:“按,‘谬’当作‘缪’,古‘缪误’字从糸,如绸缪相戾也,《大传》‘五者一物纰缪’,是‘谬’训狂者妄言,与‘误’义隔。”[8]174
按:段玉裁认为“谬”当作“缪”,古“缪误”字从糸不从言,如《尚书大传》例句,而言旁“谬”则训为狂者之妄言,与“误”字义相隔,此为“谬”当为“缪”之理由。
2.《说文·羊部》:“羑,进善也。”段氏注云:“‘进’,当作‘道’,道善,导以善也。《顾命》:‘诞受羑若。’马云:‘羑,道也。’‘文王拘羑里’《尚书大传》《史记》作‘牖里’。”[8]262
按:段玉裁认为“进”当作“道”,以《顾命》“诞受羑若”马注“羑,道也”为证。今文《尚书·康王之诰》“惟周文武,诞受羑若”,《传》云:“文武大受天道而顺之。”《疏》云:“羑声近猷,故训之为道。”[9]747《尔雅·释宫》:“猷,道也。”注云:“道路之异名。”[10]145。
(二)《说文》段注引《尚书》训诂,证字的引申义
《说文》段注在阐明许书本义的基础上,认识到词义引申的现象,往往引《尚书》训诂证明引申义。如:
“眚”之本义为眼睛生病导致昏花、模糊、看不清楚,《说文·目部》:“眚,目病生翳也。”由模糊、昏花引申为过误,段玉裁引《舜典》证明“眚”之引申义,他在“眚”下注:“眚,引申为过误,如‘眚灾肆赦’‘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也。”[8]239
“猒”之本义为饱足,《说文·甘部》:“猒,饱也,足也。”由饱足引申为厌倦、厌憎,段玉裁引《洛诰》证明“猒”之引申义,他在“猒”下注:“《洛诰》‘晚年猒于乃德’,此古字当存者也。按,饱足则人意倦也,故引申为厌倦、厌憎。《释诂》曰‘豫、射,厌也’是也。”[8]358“猒”与“厭(厌)”为古今字,“厭(厌)”专行而“猒”废矣。
“格”之本义为树木生长的样子,《说文·木部》:“格,木长貌。”由“长必有所至”引申为到达、来到,段玉裁引《尚书》中多篇证明“格”之引申义,他在“格”下注:“木长貌者,‘格’之本义,引申之,长必有所至……凡《尚书》‘格尔众庶’‘格汝众’是也。”[8]442段氏指出《尚书》中的“格”字均为引申义,一为到达,一为来到。
(三)《说文》段注引《尚书》训诂,证字的假借义
所谓假借义,即借用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文字而表示的意义。段氏引《尚书》训诂证假借义,如:
“譣”之本义为问,《说文·言部》:“譣,问也。从言,僉声。”段玉裁用《尚书·立政》证明“譣”因假借为“憸”而有诐的意思,他在“譣”下注:“《周书》曰:‘勿以譣人。’《立政》文。按此称《周书》说假借也。《立政》:‘勿以譣人,其惟吉士。’此‘譣’正‘憸’之假借。”[8]165《尚书·立政》中的“譣”字为“憸”之假借,言部“譣”训问,而心部“憸”训诐,即奸邪、佞人的意思。
“诪”之本义为詶、诅,《说文·言部》:“诪,詶也。”段玉裁用《尚书·无逸》证明其假借义,他在“诪”下注:“《周书》曰:‘无或诪张为幻。’……皆本无正字,以双声为形容词。此称‘诪张’,训诳,不训詶,是亦假借之理也。”[8]173即经传中本无其正字,或假为“侜张”,或假为“侏张”,或假为“辀张”,均为双声假借为形容词。
“翊”之本义为飞翔的样子,《说文·羽部》:“翊,飞貌。”段玉裁用《尚书》中多篇证明其多假借为“昱”字,他在“翊”下注:“经史多借为‘昱’字,以同立声也……自同其字,又同其音,以七部立声之字读一部异声之与职切。”[8]249即经史中多假“翊”为“昱”,而“翌”“昱”同为立声而假借,故《尚书》中的多个“翌”字实为“翊”的假借字。
段氏引《尚书》训诂注解许慎《说文解字》,证字义是其主要内容与目的,以上征引《尚书》训诂文献来说明字词之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力求通过对“本字”的寻求与“字义”的还原来实现对经典原义的还原,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理性精神。
二、《说文》段注训诂《尚书》的特色
段玉裁在文字、音韵研究方面成就巨大且极具特色。其一,他特别重视语言发展的特性,常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训释字词,即动态性。其二,段氏在前人训诂的基础上,精准总结出了形音义互求的方法,并在《说文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动态性
所谓动态性,即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分析语言。语言是一个发展运动的体系,所以在具体的训诂实践之中,尤其要注意词义的纵向发展变化和横向的异同,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段玉裁注意到了语言文字的社会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色,善于将不同时期的语言材料进行历时的、动态的分析,如:
1.越:《尚书》有“越”无“粤”,《大诰》《文侯之命》“越”字,《魏三体石经》作“粤”,《说文》引“粤三日丁亥”。今《召诰》作“越三日丁巳”[8]112。
按:此处段氏辨析“越”“粤”两字。首先指出《尚书》中有“越”而无“粤”,《大诰》和《文侯之命》中的“越”字在魏三体石经中被写成“粤”字,《说文》引《周书》“粤三日丁亥”,今《召诰》又作“越三日丁巳”。“越”的本义为“度也”,“粤”的本义为“亏也”,有审度慎重之义,“粤”“于”双声,“粤”可训为“于”,《诗》《书》多假“越”为“粤”,段氏引材料证“越”“粤”在流传中的通用关系。
2.逆:迎也。逆、迎双声,二字通用。如《禹贡》“逆河”……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自关而东曰“逆”[8]126。
按:“逆”的本义为“迎”,“迎”的本义为“逢”,“逆”“迎”二字双声通用,《禹贡》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均为“黄河入海处的一段河流”。段氏举《方言》释许慎“关东曰逆,关西曰迎”[11]之义,辨析“逆”“迎”二字的差别。除此之外,段氏还阐明了“逆”“屰”为行废字的关系。
3.敩:《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按,《兑命》上“学”字谓教,言教人乃益己之学半,教人谓之学者……详古之制字作“敩”,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攵”作“学”,主于自觉。《学记》之文,“学”“敩”分列,已与《兑命》统名为“学”者殊矣[8]226。
按:段玉裁辨析“敩”“学”两字,指出《学记》中引《尚书》“学学半”实为“敩学半”,意为教人是学习的一半。“敩”从教,训教导、使觉悟,自秦以来去掉“攵”旁作“学”字,故“学”是“敩”的篆省。古代“敩”“学”统谓之学也,到《礼记·学记》时将“学”“教”分名,与《尚书》统名差别甚远。
(二)音、形、义互求
段玉裁有言:“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12]187根据汉语语言的特点,他概括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12]187的方法,这一理论成为了段氏训诂的核心。
1.《说文·日部》:“昱,日明也。从日,立声。”
段注:“昱”字,古多假借“翌”字为之。《释言》曰“昱,明也”是也……俗人以“翌”与“翼”形相似,谓“翌”即“翼”,同入职韵,唐卫包改《尚书》六“翌”皆为“翼”,而“昱日”之义废矣[8]538。
按:“昱”之本义为日明,“昱”与“翌”同为立声,本来两字都为缉韵,音转都转入屋韵,刘昌宗读《周礼》“翌日乙丑”之“翌”音育[13],因声求义,“翌”“昱”同音假借。卫包根据“翌”“翼”两字形相似,将“翌”改为“翼”,误。
2.《说文·玉部》:“璪,玉饰,如水藻之文。从王,喿声。《虞书》曰‘璪火粉米’。”
段注:玉饰,如水藻之文。谓雕饰玉之文。“璪”“藻”叠韵。按,《虞书》“璪”字,衣之文也,当从衣,而从玉者,假借也。衣文、玉文皆如水藻,声义皆同,故相假借,非衣上为玉文也[8]23。
按:段氏据形旁辨衣上之文与玉上之文,认为《尚书》此处之“璪”应为衣上之纹理,而非刻在玉上的花纹,应当从衣,而此处从玉则为假借,无论从衣还是从玉,皆表示像水藻一样的花纹,其音、义俱同,均为“藻”之假借,表示刻在玉上或画在衣服上的水藻花纹。此处为音、形、义互求的典型。
《说文》段注训诂《尚书》,注重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的演变,征引不同时期的《尚书》材料进行分析比较,采用适合汉语特点的形音义互求研究方法,以本义为核心,以语音为枢纽,以引申、假借为演变轨迹,溯寻语义发展之源流。可见段氏以经传为依据,辨语言实际之应用,在小学与经学领域独树一帜。
(三)以字考经、以经考字
清代经学家、藏书家陈奂《说文解字注跋》有言:“焕闻诸先生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8]789段玉裁在《尔雅匡名序》中有言:“许书专言本字本义,而其义之引申转徙,似异而同,似远而近者,抑同音而即可相代者,无不可以书中求之。”[12]374-375“以字考经”在段氏解《尚书》中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说文》本字本义来阐释《尚书》假借、引申等用字情况以及阐释《尚书》训诂等来实现的。上文详述,此处不再赘述。相反,“以经考字”在段氏解《尚书》中的实践是通过借《尚书》训诂文献来阐明《说文》本义,甚至对《说文》篆文脱、讹进行纠正等途径实现的。如:《禹贡》“厥土黑坟,厥草惟繇”条:
按:段氏运用《尚书》训诂文献怀疑《说文》遭后人省略或转写误脱,并尝试补充。《说文·艸部》曰:“,艸盛貌,从艸声,《夏书》曰‘厥艸惟’。”大徐本虽作“厥艸惟”,可是陆德明、王伯厚皆不引《说文》“厥艸惟”为异字,故今按徐锴本作“惟”《说文》有“”无“繇”,“”即今“繇”字,“”训为随从,《说文》“下引《夏书》“厥艸惟”以证“”字从艸,会意字。据许慎《说文》引经体例:如引《易》“百谷艸木丽于地”以证“”字从艸丽,会意;引《易》“丰其屋”以证“寷”字从宀丰;会意。引《易》“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以证“相”字从目木,会意。“同此例,故段氏怀疑《说文》“,艸盛貌,从艸声”遭后人省略或转写误脱,其补充为“,艸盛貌,从艸,亦声”。
段氏利用“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辩证关系,使得文字学的成就又促进了经学、古文献学的发展。
三、《说文》段注在《尚书》训诂上的成就
《说文》段注训诂《尚书》时尤注重寻求字义、词义,对《尚书》中名物词的训释是其成就之一。另外,段玉裁尤注重“训诂须以校勘为前提”,故《说文》段注在训释《尚书》字词时,往往对其讹误先进行一番校订,以恢复其本来面貌,此为成就之二。
(一)《说文》段注对《尚书》名物词的训释
《尚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名物词,由于时代久远,已不清楚这些名物词具体所指为何。历代典籍中有不少对《尚书》中名物词的训释,段玉裁在此基础上对字形字义的细微差别进行精准辨析,训释了不少《尚书》中的名物词。
1.《尚书·禹贡》:“惟箘簬枯。”
《说文注·竹部》:箘,箘簬,竹也,《禹贡》郑注曰:“箘簬,聆风也。”按,箘、簬二字,一竹名。《吴都赋》之“射筒”也……古者累呼曰“箘簬”,《战国策》“箘簬之劲不在不能过”是也。单呼曰“箘”,《吕氏春秋》“越骆之箘”是也。《书正义》及戴凯之说“箘簬”为二竹,缪矣[8]336。
按:段玉裁赞同郑玄的说法,即“箘簬”为“聆风”也,为一竹名,也就是《吴都赋》中所说的“射筒”,一种细长节稀的竹子,两者同体异词。接着引《战国策》与《吕氏春秋》,证古时“箘簬”既可呼“箘簬”,也可呼“箘”,驳孔颖达与戴凯“箘簬为二竹”的说法。
2.《尚书·皋陶谟》:“山行乘欙。”
《说文注·木部》:欙,山行所乘者。《河渠书》作“桥”,丘遥反。徐广曰:“一作輂,几玉反。輂,直辕车也。”《汉书》作“梮”……按,輂、梮、桥三字同,以梮为正。桥者,音近转语也,欙与梮一物异名,梮自其承载而言,欙自其輓引而言。纍,大索也。欙从纍,此声义之皆相倚者也[8]469。
按:段玉裁先依据《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韦昭注、应劭注及《尚书正义》、伪孔《传》证明“輂”“梮”“桥”三字同,其中以“梮”为正字。“欙”与“梮”一物异名,“梮”是从装载器具角度来说的,“欙”是从牵引器具角度来说的。“欙”从“纍”,声、义兼通,应该将韦昭与应劭两人的说法相结合,这样的训释才是全面的。
3.《尚书·禹贡》:“三百里纳鞂(稭)服。”


(二)《说文》段注校订《尚书》讹误
《尚书》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出现了大量的讹误,《说文》段注在注《说文解字》的同时也对《尚书》进行了一番校订,对恢复《尚书》的本来面目做出了贡献。今举二例以见其大概。
1.“极”讹作“殛”
《说文·攴部》:殛,殊也,《虞书》曰:“殛鲧于羽山。”
段注:殊,谓死也……然则马注《尚书》、赵注《孟子》、韦注《国语》皆云“殛,诛也”,何也?曰:此皆用《释言》“极,诛也”之文,谓正文“殛”当作“极”也[8]289。
按:“殛”的本义为殊杀,殊即死的意思,与诛责之“诛”意义迥别,不可混淆,段氏认为《尚书》此处不为殊杀之“殛”,理由是:《洪范》“鲧则殛死”《释文》云:“殛,本又作极。”《多方》“我乃其大罚殛之”《释文》云:“殛,本又作极。”[9]674《左传》“昔尧殛鲧于羽山”《释文》云:“殛,又本作极。”[14]1244《释言》又云:“极,诛也。”[15]然而马融注《尚书》、赵歧注《孟子》、韦昭注《国语》皆云“殛,诛也”,因为他们都用了《释言》“极,诛也”[10]92,而当时注家有本经作“殛”而后引作“极”的通例,故他们认为此处本经应作“殛”,误。
2.“共”讹作“恭”
《说文·共部》:共,同也。从廿、廾。
段注:廿,二十并也。二十人皆竦手,是为同也。渠用切,九部。《周礼》《尚书》供给、供奉字,皆借共字为之。卫包尽改《尚书》之“共”为“恭”,非也……《汉石经》之存者《无逸》一篇中“徽柔懿共”“惟正之共”皆作“共”,“严恭寅畏”作“恭”,此可以知古之字例矣[8]188。
《说文·共部》:“龚,给也。”
段注:《糸部》曰:“给,相足也。”此与人部“供”音义同。今“供”行而“龚”废矣。《尚书甘誓》《牧誓》“龚行天之罚”,谓奉行也。汉、魏、晋、唐引此,无不作“龚”,与供给义相近。卫包作“恭”,非也[8]188。
按:“共”字本义为共同,《周礼》《尚书》中的“供给”“供奉”义均假借“共”字为之,“龚”的本义为给,与“供”字音义俱同,后“供”行而“龚”废,“供”又假借为“共”。唐天宝间卫包将《尚书》中的“共”字全部改为“恭”字,故此误系后人妄改。
段氏往往溯本求源,利用训诂、考证等方法对《尚书》中的重要名词概念进行训释、校订,力求恢复经义原旨,通过“复古”来“求真”“求是”,却又不囿于“复古”,敢于揭示和纠正前人著述中不合理的训释,秉持实事求是的训诂原则,促进了传统小学的全面发展。
四、结语
在具体的《尚书》训诂实践中,段氏不仅关注语言发展的特性,遍引群藉,而且擅长用形、音、义互求的新方法来寻求《尚书》经文中字词之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均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态度。除此之外,段玉裁与乾嘉学者一样注重考证,主张“训诂以校勘为前提”“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等科学理论,在训释字词时先对《尚书》进行了一番校订。以上种种使得小学与经学联系愈发紧密,两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可见,传统训诂材料所包含的学术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是汉语学术史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藏。虽然《说文注》中的《尚书》训诂材料是零散的,但仍然值得后人去关注和整理并从中吸取相关的营养。因此,在研究段玉裁《尚书》学时,除了研究其《尚书》学专著《古文尚书撰异》以外,同时也不可忽略《说文》段注中的《尚书》训诂,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分析段玉裁的《尚书》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