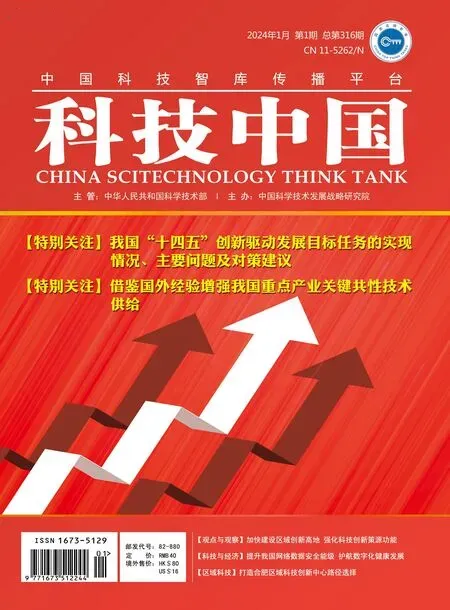加快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的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进程
■文/张志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
发达国家基本完成深海采矿的总体技术储备,并进行了多次试开采,全球深海金属矿产进入商业化开发的前夜。深海采矿领域的先进国家大多是美国构建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成员,恐将对我国深度参与深海采矿领域国际合作、矿产供应链安全构成威胁。
一、全球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现状
一是历经长时间勘探,深海金属矿产资源的分布已基本探明。深海金属矿产主要以大洋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的形态存在,储量极为丰富。尤其是锰、钴、锂、稀土等被列入世界主要国家关键性矿产目录的金属,相比陆生矿,深海矿藏储量更为丰富。大多数深海金属矿产资源(尤其是大洋多金属结核)分布在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专属经济区。
二是深海金属矿产大规模商业化开发进入倒计时。发达国家基本完成深海采矿的总体技术储备,并进行了多次试开采。从需求侧看,随着电池、电动机和涡轮机等脱碳技术的发展,对镍、钴、锂、铜和稀土等矿物的需求快速增长,加之陆生矿开发成本逐渐提高,导致对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的需求增加。从供给侧看,深海金属矿产开发装备性能改善,降低了深海采矿的经济成本;环境监测、评估、修复技术水平提升,降低了深海采矿的社会成本。从环境侧看,国际深海法律框架逐步健全完善,商业化开发具备了基础法律保障条件。
三是环境问题是目前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面临的最大拦路虎。深海采矿可能会对海洋生物、生态系统产生毁灭性且不可逆的影响。目前,人类对矿区环境基线特征和生态系统认知有限,深海采矿对海洋环境影响程度和强度无法准确监测评估,环境修复技术显著缺乏。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来临之前的这几年准备期,主要解决环境监测、评估、修复等难题。
四是深海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具有明确的国际管理机构与制度安排,但美国不愿接受相关约束。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是代表全人类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权威组织。截至目前,国际海底管理局共有168个成员(由167个成员国及欧盟组成),不包括美国。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约国家,在海洋领域,美国不受国际组织及其规章约束。
五是国际海域“蓝色圈地”运动已经开始,我国矿产供应链安全遭遇新威胁。美国在深海采矿领域乃至整个海洋事务领域,均保持极高的“自由度”。一旦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开发阶段,大多数国家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际海底管理局制定的规则框架内进行开发,而美国会凭借行动的高自由度,采取不合作行为,为自身谋取高额收益。深海储量丰富的铜、钴、镍等,均是我国稀缺的金属资源。深海采矿领域的先进国家,如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均是美国构建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成员(2022年6月,美国和加拿大等主要伙伴国家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保障对清洁能源和其他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的供应。从该组织的宗旨及其展开的活动看,对中国具有针对意图。目前MSP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委员会),恐将对我国深度参与深海采矿领域国际合作构成威胁。
二、我国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一)现状
开发深海金属矿产,需要服从制度安排、取得勘探开发资格,需要技术装备达到相当水平,需要做好深海环境保护工作。此外,参与深海治理、加强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快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的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进程。下面从勘探开发资格、技术装备、环境保护、深海治理四个方面,介绍我国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现状。
一是勘探开发资格方面,我国成为第一批深海金属矿产勘探开发的先驱投资者。我国先后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多份勘探合同,取得5块具有优先开发权的海底资源“矿区”,矿区面积达23.5万平方千米。我国目前是世界上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矿区数量最多、矿种最全的国家。
二是技术装备方面,我国已经基本具备深海金属矿产勘探开发的总体技术储备,但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尚需时日。从20世纪90年代至2021年,我国先后完成技术方案研发、陆上验证、海上单体海试、系统联合海试等。总体来看,我国已经完成深海采矿的全流程试验。但试验多为样机试验,海底采矿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监测预警,应急处理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验证。
三是环境保护方面,我国高度重视深海采矿领域的环境监测、评估和修复等问题。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多金属结核采矿试验工程”项目支持下,我国初步构建了深海矿产开采羽状流理论模型,并在2021年深海采矿联动试验中开展环境监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我国实施的“基线及其自然变化”计划,已列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组织的四大国际合作项目之一。
四是深海治理方面,我国通过国内立法、参与国际立法等方式不断提升治理水平。201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规范了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目前正积极参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以下简称《开发规章》)制订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BBNJ协定》)谈判等重大深海国际立法进程,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相关制度规章,已取得多块国际海底“区域”矿产的勘探开发资格,深海金属矿产开发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技术装备、环境保护与深海治理等方面。
一是技术装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深海科技研发力量较为分散,协同创新能力不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深海采矿关键技术实现时间上落后。在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方面,我国恐将落后于发达国家。
深海采矿关键装备可靠性不足。我国深海采矿泵管关键设备可靠性较差;提升泵的耐腐蚀、耐磨损、耐冲击等技术难题仍未解决;我国深海采矿系统尚未实现多元信息融合与协同作业,国产组合导航定位装备和算法的深水定位精度不够;国产大功率深水电缆和光纤技术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不足。
二是环境保护方面,对深海采矿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我国尚无法对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程度和强度进行准确监测与评估。我国尚未专门针对环境影响开展全面、系统的原位扰动测试与技术评估,对采矿活动周围环境的物理化学过程、生物多样性影响等尚无明确认识,针对深海采矿的环境评价方法尚未建立。我国的深海矿产开采羽状流理论模型只是初步构建,缺乏现场观测数据与可靠预测模型,尚无法进行可靠的定量评价。我国深海采矿的环境修复技术显著缺乏,深海生态修复仍处于探索阶段,实践经验不足。
三是深海治理方面,我国参与国际海域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国际海洋规则正在重塑,《开发规章》正加速制订,《BBNJ协定》谈判已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但我国熟悉国际规则和深海事务的复合型人才不足,推动国际海域治理体系变革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较弱。
三、相关建议
(一)优化深海金属矿产开发顶层设计,加强深海科学基础研究
加强顶层设计,围绕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制定占有、组织管理与国际合作方面的实施细则。增加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研究的资金投入,积极利用国际、区域、双边海洋法律制度研究成果,制定我国深海金属矿产开发战略,建立开发决策支持系统。
加强深海地球科学、深海生物科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强化开采目标区海洋科学研究,收集和分析矿产资源与环境资源数据,建立海域特征数据库。加大海底科考力度,开展水文、地质、生物、化学和地球物理等多学科综合调查,为矿产开发和环境影响评估做好知识储备。
(二)构建新型创新组织体系,加大关键深海技术研发力度
构建以深海国家实验室为龙头的新型创新组织体系,加快整合国家海洋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全国海洋院校、海工装备企业等的研究力量,打造综合性深海科技研究中心。
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为牵引,以深海金属矿产开发技术和环境修复技术为核心,部署一批服务国家深海战略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构建深海资源开发技术体系。
(三)提升深海采矿系统安全可靠性,研发高效智能装备
制定严格的深海采矿系统安全标准,确保深海采矿系统在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持续可靠生产作业,包括数据精准及时传输、水下装备和控制系统稳定可靠、水下监测网持续有效等。
研制无人化、智能化、集群化深海装备。紧密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数字技术,实现海面—海底、开采—监测—转运、海上—陆地等跨域装备协同作业,包括全链条智能调度、全系统自主协同作业、全天候健康监测、危险状态自动预警、主动避险智能控制等。
(四)加快深海技术成果转化,培育深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
强化深海采矿技术研发单位与企业合作,加快解决深海技术成果产权模糊问题,让深海采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
制定融资、税收方面优惠政策,培育深海采矿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公共财政、专项资金、风险基金、股权融资多元融资体系,扩大投资主体范围,创新合作方式,完善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激励机制。
(五)增强我国深海治理话语权,在深海金属矿产商业化开发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深度参与《开发规章》《BBNJ协定》等的制定过程,增强我国深海治理话语权。瞄准深海金属矿产开发的环境评估与修复难题,凝聚国际科研力量,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支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尊重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全面参与国际海底管理局事务。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反对超级大国霸占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