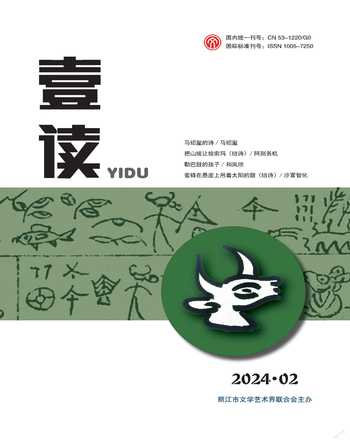四个亲人的死和一个亲人的札记
崔玉松
2008年5月到2009年11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失去了四个至亲的人,我的生活一度处在伤痛之中。八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已经勇敢走出来了,但是,四个亲人的死去,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父亲
2008年5月3日,父亲离开了我们。是的,我从来不曾想到,父亲真的就这么离开了。
有人说,至亲离世,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预感,或做梦,或莫名奇妙心神不定。可是,我没有,我们都没有。从父亲确诊为喉癌的那一天起,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我们知道父亲会离开,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因为父亲是喉癌初期,癌细胞没有扩散,到死都还没有扩散。
“120”赶到的时候,我和哥哥、嫂子跟着上了车,我用我的手握住父亲的手,他的手由于输液,有些冰凉,我想用手上的温暖去焐热他。一路上他一切正常,赶到医院后我忙着交钱,哥哥办住院手续,嫂子陪着医生进行急救。十分钟左右,脉搏越来越弱……
父亲走了。
嫂子说,父亲是笑着离去的。我一直纳闷,父亲死的时候,到底为什么会笑?是觉得这一年多的痛苦终于解脱了吗?还是父亲认为在儿女身边死去是一种幸福?
当时我愣住了,我有些恍惚,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觉得是医生弄错了,一个人的生命怎么可能如此脆弱?更何况是父亲。父亲怎么可能会死?
我摸了摸他的脸,分明还有热气,我看着围在他身边的那几个医生,忽然说不出话来。其中一个问我,老人是不是埋了输液管,要抽出来吗?凉了就拿不出来了。我回过神来说,麻烦你们了,赶紧帮他拿出来。另一个又问,你们有车吗,怎么拉回去。我说,没有,医院有车吗?他摇摇头说,我告诉你一个电话,专门拉尸体的,你可以请他拉。
是个微型车,后排位置拆除,他们帮我把父亲抬到车上,我赶紧让嫂子回去通知母亲,我和哥哥一起护送父亲回家。
路上,我给丈夫打电话,他单位有事,根本分不开身。我又给在老家的妹妹打电话,让她请人把棺木拉回来,准备好柏树枝,再买一点檀香木,给父亲净身沐浴。这时候才想起,去医院的时候走得急、口袋里根本没带钱,送父亲回家办丧事要花钱,又连忙给小叔子打个电话,让他赶紧送点钱过来。
路上,妹妹打来电话说,邻居们说了,父亲不是在家里落的气,不能进家门。而且门太窄了,棺木不好抬进去,怎么办?我有些生气,对着电话吼,那个家都是他一手挣来的,死了还不能让他进?哪有这个道理。门窄了进不去,把前面那堵墙拆了。
车经过高坡顶的时候,警察堵住车说,超速了,要罚款。我阴着脸说,我爸死了,得赶紧送回家。警察一摇手,走吧,到前面有人堵的话,说一声!
说真的,我非常感谢这些人,人死了该怎么做,要注意什么,我一概不知,我甚至想不起要把父亲身上埋的输液管抽去,我也找不到可以拉尸体的车,如果没有那些陌生人的指点,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警察,平时总是威严不容分辩,在死亡面前,也会有恻隐之心,也会给死亡让路,现在想想,这个世界并不像平时想象的那么冷漠无情。
我急急忙忙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没掉一滴眼泪,后来的日子,我常常会想,我是不是有些无情?是不是跟父亲的感情已经淡漠如此?
当我把父亲送进院子的时候,公公和小叔子在帮妹妹搭灵堂,公公的眼睛红红的,一看就哭过。小叔子递过一万块钱,我把开车师傅送走以后,依然没哭。
其实父亲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懂,他早就把他身后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提调、接客这些事其实他生病之后就陆陆续续讲过了,我只不过是按他的安排一一办理。
灵堂还是设在院子里,主要是家太小,放下棺木,就基本上转不开身,吊唁的客人来了也不能没有一个坐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些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的人逝去该如何处理?这次父亲的离去,让我不自觉地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家这套老房子,是一直这样空着的,虽然窄,但门前有一个院子,不管怎样,办起这些事总会方便一些。我们全家搬到城市以后,妈妈提出要把这房子卖掉,我坚决不同意,我说虽值不了几个钱,但总是父亲置下的家业,留着它,就当是家乡还有个家,有个念想的地方。
其实,我是害怕妈妈以后没有地方办丧事。
表姐帮我们找好了办事的先生,在老家,办这种丧事叫“白喜事”,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只要按照先生的要求準备、办理就行了。我们请的先生,几乎包揽了全县城的丧事,瞧日子、看坟地、出殡,做花圈大钱等纸货,鼓手、唢呐,只要是葬礼上要用到的,不管规模大小,他都可以帮你做到。
按照老家的习俗,父亲回到家的当晚,先生就到我们家瞧下葬的日子了。瞧日子的时候我想起父亲一直念叨五月六号要回家,请他看看六号这个日子,他翻书一看说,大凶大凶,与家里人相冲,只有五月九号才是下葬的吉日。而入殓的日子则是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傍晚。
当天他安排一帮人来帮父亲净身穿衣,那是几个手脚麻利的乡下女人,她们用柏香木煮水帮父亲擦洗身子,又点燃檀香木熏香,然后穿衣。穿衣的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僵硬,她们给他翻身的时候动作过大,我担心弄疼父亲,让她们轻一点,一个女人一边忙碌一边回头看了我一眼,很奇怪的样子。想来,在她眼里,死人是不会疼的,可是那是我的父亲呀,无论是生是死,她们手脚只要一重,我都会心疼。穿上衣服的父亲,被停在用四根凳子垫着的一块木板上,我怕父亲冷,又找了被子给他盖上。
那一夜,父亲就这么躺在那块木板上,上面是我们笨手笨脚地用篷布搭的简易灵堂。从这夜开始,哀乐一直没停,长明灯昼夜亮着,我们跪在灵前,不停给灯加油,不住点香烧纸钱。
妈妈赶回来了,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商量着父亲的葬礼,我忽然有一种虚脱的感觉,我不知道,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明明早上起来,父亲还吃了我给他煮的鸡蛋,明明他还精精神神走着路去输液,明明他还比划着对我说,让你妈回去休息,明明他还想着六号回来,看看他的生祭碑,怎么一转眼他就躺在这里了呢?我甚至还有一丝侥幸,半夜里父亲会被冻醒,就会悄悄起身进家门。我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父亲可能只是窒息,或许那些帮忙的人一翻弄,父亲就会醒过来。妈妈、我和哥哥、妹妹就这么坐了一夜,第二天天刚发白,我出去上香烧钱纸,父亲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
父亲真的走了……
我给父亲磕了三个头,独自跪了一会,我告诉父亲,有我,我会好好孝顺妈妈,会把这个家好好撑下去,我会代替他做蒜头中间那根杆,把这个家紧紧拢在一起。
我和哥哥到山上砍松樹柏树枝,我们要好好地给父亲扎个漂亮的灵堂。灵堂搭好后,又到纸火店买香纸,买麻线买孝衣,按习俗准备好一切葬礼上要用的东西。
先生姗姗而来,按照程序将父亲入殓,装进了那个黑黑的棺材里,我的心安定下来。里里外外穿上了三套衣服,又盖上厚厚衾被的父亲,晚风再也吹不到您了,我想父亲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好好休息了。
五号这天,天气忽然热了起来,正午的时候气温高达28°,灵堂里更是闷热无比,妈妈也变得烦躁起来,她说这样下去父亲会受不了,她担心尸体腐烂,等不到下葬的那天,必须去买冰块降温。我十六岁离开家乡,对当地的情况已经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冰块,到处打电话求助。最后,到冷冻厂买了许多冰块,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听到妈妈的哭声,原来帮忙招呼客人的叔叔,在家里和几个客人谈论父亲,说了一些父亲的不是,忽然灵堂里的纸花掉下一朵,正好落在长明灯上,灵堂瞬间起火,幸好发现得快,扑救及时,并未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妈妈觉得是因为叔叔说了父亲的不是,父亲生气造成的。看到妈妈跪在灵前哭诉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疼了起来,头一下子蒙了,冲进堂屋,对着叔叔说,叔叔,都说人死为大,你对我爸有什么意见,你出去说,你看看,我爸还在外面躺着呢,你知道他的脾气。这个叔叔也吓着了,连忙给我道歉。
那一刻,我忽然失去了理智,变得好斗起来,我真正地感到我必须强大起来,必须好好保护妈妈,保护好这个家。那一刻,我在想,倘若叔叔还有什么不妥的言语,我相信,我会放下脸把他轰出门的。其实有些事也只是巧合而已,但这个巧合,让我找到了必须强大的理由。
六号晚上,忽然下起了大雨,雨点发火了一样,“噼里啪啦”砸在灵堂的篷布上,雨水从四面八方涌进灵堂,我们垫在地上的稻草全都湿透了。那几天气候格外反常,高温、大雨,好在我们兄妹,没有一个人生病。
按照老家的风俗,我的父亲去世,小姑子必须给我和丈夫买身衣服,过关的时候,由小姑子给我换衣服。我没有小姑子,丈夫一家都是男孩。我们商量了一下,这个环节随意,有小姑子的就换,没小姑子的就不换了。第二天,小叔子他们来看我,他们说,你虽然没有小姑子,但你有小叔子,没事,该小姑子做的事,我们做就行了。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丈夫的姑爹也去世了,下葬的日子跟父亲是同一天。公公为了让他的几个儿子都来给我父亲送葬,在五月八号这天就带着儿子们到姑爹家先祭拜完毕。结婚好多年了,我一直改不了口,从未叫过公公“爸爸”,父亲走后,看到公公一次次流下的眼泪,那份感动油然而起,我失去了父亲,可我还有公公,自然而然的,一声“爸爸”脱口而出。人与人的相处不用刻意,只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温暖了你,这个人就会成为我的亲人。我忽然庆幸,虽然爸爸走了,可我并没有与爸爸这个词分离,我依然可以叫声爸爸,依然可以有一份深深的惦记。
下葬的头晚是最重要的日子,所有的亲朋好友会在这天晚上前来吊唁,丈夫和大姐也终于在这一天赶到了。我们按照先生的指点,掩钉、绕棺,最后看看父亲的遗容,我看着父亲安静地躺在棺材里,我抬起头,把即将掉出的眼泪咽了下去。这个好强的男人,争了一辈子,斗了一辈子,四十多岁还跑到北京读书,开始自学法律,六十多岁发动族人查资料、搞调查,重修家谱,临死的前几天还惦记着重修“崔官阁”,想这么多,管这么多,到头来,却安安静静躺在这里。有时我会奇怪地想,生的争斗和死的安静,是不是就是同一个词?
堂祭的程序非常复杂,由先生一项一项操持,庞杂的仪式结束后,亲戚们开始唱祭文,由于了解父亲生平,祭文写得非常贴切伤感,跪在灵前的我再也忍不住,几天来的疲惫和伤痛一涌而出,从“尊一声爹爹呀,听儿言禀”直哭到“如想见我爹爹面,除非南柯梦里寻”。我不知道是祭文写得过于伤感,还是因为父亲的一生就随着短短的祭文灰飞烟灭,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无常让我深深伤心着。
父亲生前一直在安慰我,他说他的一生虽然很短,但比起他的童年伙伴他的同学,他的一生已经很有意义。可是对于儿女来说,我们要的不是生命有没有意义,而是要我的父亲好好的活着。父亲是一个家的支柱,是一家之主,有父亲的家是牢固有威严的,没有了父亲,瘦弱多病的妈妈怎么办?内向怯弱的哥哥怎么办?顽劣无成的弟弟又怎么办?那一刻,我哭父亲,哭妈妈,哭我自己,我忽然有一种撑不住的感觉,哥哥为了照顾父亲,一年多没有出去找过工作,弟弟顽劣任性,整天不着家,连父亲的死讯都没法通知他,姐姐远嫁他乡,根本赶不回来,还有爷爷,爷爷也在病中,父亲的死还瞒着他。我不知道父亲丢下的这个家将来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九号的葬礼非常顺利,墓地是父亲生前准备好的,是我们家族的祖坟,下葬的时候,棺上的公鸡打鸣,雨住天晴,亲友们都说是个好日子。
回到家里打扫,帮忙的亲戚朋友走后,屋里死一般寂静,全家坐在堂屋里守着妈妈,我才发现,妈妈好像忽然老了很多,她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就这样静静坐到深夜。
刚送走父亲的那段日子,我的头一直昏沉沉的,像是病了,却查不出病因,吃药也不见效,整天迷迷糊糊的,没人的时候眼泪就会自然而然流出来,很多时候落到嘴角我才发现原来我流泪了。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侄子没考上高中,妈妈病了,我才硬撑着租了一套房子,把妈妈哥哥侄子妹妹一同接来。给哥哥妹夫找了个临时工作,给侄子找了学校补习。父亲走了,可我们还活着,生活还得继续,我们还得坚强地活下去。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梦到了父亲,我急急忙忙告诉他家里的近况,他没有回答,只是忧郁地说了一句:这个家拖累你了。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从梦中惊醒的时候,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忽然意识到只要心怀思念,只要用心感受,逝去的亲人就一定会知道的。多年来,父亲是忙碌的,除了工作,他常常奔波在各地,帮别人找证人、找证据、查阅法律条文,就连他查出喉癌以后,还坚持把手中的五个案子一一了结,圆满结束。父亲是威严的,他从来不屑在我们面前流露一点点温情,表现出一丝丝的慈爱。在昆明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帮他洗脚,他都很不好意思,把脚缩回去,暗示说他自己洗。在梦里,他却亲了亲我,那份从未有过的温情让我瞬间百转千回,我忽然觉得,我所有的辛苦父亲都知道都懂得,所有的付出也都值得,我相信父亲能看到我,他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忍耐与努力。
时间过得真快,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离世的悲痛以后,慢慢地,对痛苦有了一种抵抗力,我们依然顽强地活着,跟许许多多家庭一样,过着凡俗平安的日子。
五年后,女儿考上了重点大学,侄子也已经大二,我把女儿的通知书复印了一份,给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我把这封信和女儿的录取通知一并烧成灰,我想父亲能收到纸钱,就能收到我给他的信,我希望他不要再惦记这个家,没有他,我们依然会好好地活着,勇敢地活下去。
今年清明,我们去给父亲上坟。按照风俗,我们拉了一车草垡子给父亲垒坟、拍土,摆好水果、酒菜等祭品,点燃香、纸,当我们跪下去磕头的时候,两岁的侄子奶声奶气地说了声:爷爷,我来看你了。我一抬头,阳光扯开厚厚的云层,像水一样倾泻下来,我忽然感到了温暖。
是的,地上的草开始发芽,草丛里星星点点地开着几朵紫色、黄色的小野花,到处散发着生机和希望。生命中的那片沼泽,我感觉我已经走出来了。
爷爷
父亲走后一个月,妈妈、我和哥哥一起回乡下老家看爷爷,爷爷已经八十八了,又在病中,父亲死亡的消息还瞒着他。
爷爷在院里的躺椅上晒太阳,我们刚进院子,爷爷就问哥哥,你爸爸的事办得还顺利吧?我们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爷爷说,那几天家里都没人了,冷冷清清的,连你二爷爷家都不在家,我就猜到了。我们岔开话题,没有再说父亲的死,爷爷也不再说,只是不停问我们几姊妹的情况,问丈夫、妹夫,甚至我们的孩子,精神状态很好。
看过爷爷,我们就回城了,没想到这一面居然又是永别。清醒明白的爷爷在我们走后一个星期,忽然气虚无力,就像年久的油灯,油尽灯枯了。爷爷的死,离爸爸去世只有四十四天。
接到妈妈的电话,我还在上班,爸爸生病、去世,已经用光了我所有的公休和丧假,我没法再请假去给爷爷办丧事,只能靠妈妈、哥哥和妹妹他们了,我只是在堂祭那天赶回去。
下葬的日子瞧在六天以后,哀乐、唢呐在空旷的村落哀鸣着,焚香烧纸的味道弥漫在村子的上空。还没从父亲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的我们,还来不及擦擦脸上的眼泪,爷爷的死亡再一次将我们推进了哀伤的黑洞,妈妈硬撑着,含着眼泪安排着爷爷的葬礼。
其实,爷爷不是我爸的亲爹,是三叔,爷爷这一生带大了五个孩子,却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我亲爷爷死的时候,爸爸才有八个月,姑妈也只有三四岁,爷爷看着爸爸可怜,就娶了奶奶,帮衬奶奶把爸爸他们拉扯大。爸爸成家没两年,奶奶病故了。爷爷又从邻村娶了后来的奶奶,新奶奶带过来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才有五六岁,爷爷又将三个孩子视同己出,辛辛苦苦养育成人。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从来没有糊涂过,从来不会说一句难听伤人的话,性子温温和和,说话有理有据,死的前两天还把身后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连一周前我给他的几百块钱他都作了安排,到死都没有说一句胡话。
爷爷死后的第二天夜里,在外做工程的小叔来了,他带着后娶的婶子,开着路虎趾高气扬冲回老家,翘着二郎腿坐在火塘边的凳子上,说要尽快办,不由分说地把爷爷的葬礼提前到第三天,也就是6月18号,亲戚也说尽量少请。妈妈说,这该走的礼还得走,不能失了礼数。他说,我哥不在了,这个丧事自然该我来操办,你那点工资,又要管儿子孙子,这事你就别管了。妈妈据理力争,说你哥不在还有你侄子在,这事自然该我们管,我们虽然工资低,但该办的事我们是不会含糊的。小叔不再说话,自顾自操办着爷爷的葬礼,根本不让我妈和我哥插手。
妈妈打电话跟我诉苦,妈妈说,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他是严家,又不是我们崔家没人了,他这样做是欺负人。我劝妈妈别争了,反正小叔也是爷爷带大的,虽然没跟我们家姓,但他来操办也是应该的,总算他还有点良心。他无非就是想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一下他有钱,他会办事,成全他就行了,你们乐得清闲。我妈虽然嘴上答应,却终归放不下,心里不舒服,但为了把葬礼圆满办下去,还是忍下来。
进客那天,我妈的后家按照小叔说的一个都没来,但小叔后娶这个婶子的后家却是全来了。在农村,这种婚丧嫁娶的大事,后家没人来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说明后家没人,后背不硬,在村里会被人小看,我妈对这事耿耿于怀。我劝妈妈,没来就没来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我们又不在村里过日子,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所以,整个葬礼,我的母亲,是郁闷多于忧伤。
所有事情处理结束以后,一大家子坐在老家的堂屋里,妈妈又说,老人这事是小叔出钱来办的,你大哥虽然死了,但还有儿子,我们那份我们是一定要出的,你看办了多少钱?我们出。小叔说,你那几文工资,出什么出,不用你们出。妈妈说,实在你不愿意,我们出一半。小叔还是不同意,妈妈只好拿出几千块钱给离了婚的前小婶冬梅,说,伺候老人的事原本是我和小陈的事,人家冬梅是在帮我们敬孝。小叔也拿了一些给她。小婶说他给我是他欠我的,嫂嫂你的我不能要,一大家子人等着你那点工资呢。妈妈说,这是应该给你的,真的,我在得远,你哥哥病了一年多,我也顾不上老人,要好好谢谢你,你太不容易了。推让一番,小婶终于收下钱。
事后听说这些,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妈一直待人温和热情,为什么会对小叔这样?虽然小叔说话霸道难听,但也可以像平时一样,听听就过了。后來我妈一直不愿出门,常常封闭自己,我才明白失去丈夫的她心里一直放不下,她总怕别人欺负我们,随时摆出一副保护我们、维护父亲声誉的架势。爸爸走后,她完全忘了自己也是接近七十的老人,只想着要好好支撑这个家。我妈那副样子,常常会让我想起带着小鸡的老母鸡,只要我们稍稍走近鸡群,它就竖起满身的毛吓唬我们,如果我们不停住脚步,它便会张开翅膀冲过来,狠狠啄我们一口。
爷爷的葬礼,让我妈深深切切感受到失去丈夫的冷遇。她一直闷闷不乐,我们从小在城里长大,对这些什么脸面尊严这类事看得不是很重,我总觉得,都是爷爷养大的孩子,虽然姓氏不一样,但总是在这个家长大,都想为爷爷尽孝出钱出力,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分什么大的小的。
还好,我妈不是个过于拘泥固执的人,在我们的开导下,也慢慢想通了。
爷爷走后,他辛辛苦苦建立的家算是散了。离了婚的小婶守了三个月的孝,把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仔仔细细地扫了一遍,像是要把那些恩怨纠葛全部从她的生命中清扫出去,之后,嫁到邻村去了。一直陪她在家的大儿子把门锁了,外出打工。那个家忽然没有了一点声息,就连院子里那棵每年开得灿烂娇艳的大丽菊也慢慢枯萎死去。
老家的大门一直用一把大铁锁锁着,这个家里所有的亲情、恩怨,也被牢牢地锁在那间屋子里了。老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关于故乡的词,只是偶尔的时候,才会牵挂和念想。
姨妈
父亲病故的时候,姨妈每天缠着表哥、表姐开车送她过来,每次来总要坐在灵堂使劲哭。她会农村那种哭丧调,有时候她哭唱着我爸,哭这么一个能干的人终究逃不过病魔的手掌。有时候她哭她可怜的妹妹,哭不争气的侄男侄女。有时候她不理我妈,她总是怪我们让爸爸放疗夺去了爸爸的生命。
她颤巍巍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身体多好,多能干的一个人。有时候她会对我说,这个家靠你了,你可不能不管,你妈老了,真的老了。
父亲的葬礼结束以后,又是爷爷的葬礼,忙来忙去,我们根本没顾上姨妈,也根本没有发现姨妈的身体有了异常,只是觉得姨妈似乎更啰嗦、更健忘了。
爸爸、爷爷走的那年,我们家的春节过得有些冷清,从年初二开始,姨妈家那边的表姐表哥们开始请我们吃饭,过了大年三十,我们就几乎没在家里吃过饭,常常是早上过去,就要到晚上才回来。见姨妈的机会多了,就发觉她常常喊饿,刚放下碗就说表嫂没给她做饭,成天抱怨表哥表嫂不给她煮甜白酒鸡蛋。有一天刚吃过饭坐着聊家常,她居然流着眼泪对我妈说,我都好多天没吃肉了。我妈愣了一下,说,姐姐,快说不得,大过年的,满屋都是肉,要是让儿媳妇听见,就多心了。我在旁边坐着,心里想,这种婆婆太难相处。姨妈的六个儿女,虽然过得平凡简单,但都很孝顺,尤其是表嫂,当过医生,伺候婆婆那是我们亲眼所见,正因为这样,姨妈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发觉她哪里不对,心里反倒是对她有意见的。
中秋节回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了身,我喊她的时候她不知道我是谁,把我叫成我妈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之前的健忘、胡说都是小脑萎缩的征兆,这个时候的姨妈,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什么都记不得了,但还记得我妈,她唯一的妹妹。偶尔清醒的时候,会叫我妈的名字,也会叫她早年夭折的弟弟妹妹。出门的时候,我跟妈妈抱怨表姐表哥没把姨妈送进医院,妈妈说,要送的,你知道你表姐表嫂都是医生,请人来家检查,说不能送了,所有的器官都衰竭,全身的机能也已经减退,没有办法了。
姨妈死的时候,正好是国庆节,我妈接到电话,没有流泪,把我们几姊妹召集起来,要求我们全都去帮忙、送葬。其实,忙是帮不上的,姨妈的丧事不用我们操心,她的六个儿女安排得妥妥当当。在老家,办丧事已经成了一个产业,瞧日子、收殓入棺、扎灵堂、做纸火、做孝服、请先生、点主、祭文、做饭,甚至还有跳神唱戏的,只要有要求,没有办不到的,孝子孝女只管出钱,跪着迎客就行。作为侄男侄女,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点柱香、烧点纸钱了。
作为我妈唯一的亲姐姐,我妈的伤心可想而知,可以说,没有姨妈,就没有我妈的今天。姨妈从小就是一个任性有主见的女人,外婆给她裹脚的时候,她白天裹晚上放,硬是没把脚裹成形,只是鞋的码子小得多。她违抗父母退掉大她许多的娃娃亲,自己跑出去读书,成为那个叫吊井的小村子里第一个出来工作的女子。工作以后,她又把我妈也带了出来,用她微薄的工资抚我妈读书。至于为什么当医生?她说,外公死的时候,她还小,只记得外公拉肚子,没几天就没了,过了两个月,大弟弟的脚在山里划破,一个月不到就死了,到了年底,才三岁的小妹妹也病死了。跨过年来,小弟也病死了,加上小叔,那两年,她们家就死了五个人。姨妈只有外婆和我妈两个亲人了,她说,从那时起,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医,一定要走出大山。
我妈常常说,没有我姐姐就没有我。我妈师范毕业以后,也带大表姐和大表哥去她教书的学校读过书。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肠炎经常发作,我妈直接把我送到姨妈家,好了以后再接回家,记得我的痧子、水痘都是在姨妈家出的。我妈和姨妈的感情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我爸死的时候,我妈坚强地挺着,她怕我们处理不好,不敢有一丝松懈,反而顾不上忧伤。爷爷离去,她也还能接受,毕竟人老了,八十八岁,在老家已算高龄,有思想准备。姨妈的离去,仿佛把我妈的心抽走了。送走姨妈,我们回到家,担心我妈在这接二连三的变故中倒下,我在离我家不远的小区租了套房子,哥哥、妹妹也搬上来,在曲靖找事做,结束了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零碎生活。
白天我妈一个人待着,给上初三的侄子做饭,下班的时候,我们全都聚在那儿,重享天伦之乐。每天吃过晚饭,一起散步的时候,我妈总是不停地跟我说爸爸,说姨妈。说起姨妈的时候,她总会说,怪了,你姨妈当一辈子医生,救了多少人,怎么会死得那么受罪?看到孕妇,她又说,你姨妈在旧营的时候,队里有一个产妇横生,要不是你姨妈,那家孩子大人就死定了,后来那个产妇硬是认了你姨妈做干妈,只可惜她命不好,还死在你姨妈前面。我妈有时候也会说起我,她说你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不是肠胃不好,就是感冒,所以常常把你往你姨妈家送。有时候她会说,你姨妈太可怜了,从小都是靠自己,你姨爹从来没出去找事做,就这么一直闲着。你姨妈这辈子还是挣了不少钱,两个儿子一人一栋商住房。说得最多的,还是姨妈死之前糊涂瘦弱,湯米未进的样子,老是抱怨一个做了一辈子医生的人不该这么受罪。
后来我妈慢慢安静下来,不再唠唠叨叨地一会说爸爸,一会说姨妈,除了从小区到菜场,又从菜场到小区,她从来不去别的地方,就连和她一起在农村教过书的王老师打电话来,让她过去坐坐,她都找借口推掉了。
我有些担心,周末的时候常常带她到处走走,实在找不到走的地方,我就开着车带她去看别墅,这个小区、那个新区的,这些小区里的风景比公园都舒适,开始,我妈不去,她说天天看别墅,又没有钱买。我笑笑,说,咱买不起还看不起吗?这么好的风景,不看浪费了。看得多了,我妈开始品头论足,回家后,会跟哥哥说哪个小区的房子漂亮,哪个小区的绿化更好,哪个小区的鹅卵石随便丢在花架下都没人会拿一颗。
哥哥、妹妹买的房子终于交房了,我们常常约着我妈从这个建材市场到那个建材城,看材料、比价格,找装修工,进入紧张的装修中,我妈开始忙碌起来,除了选材料,有时候还帮忙看看施工现场,多数时候是在家里给儿女们做饭,亲人的离去在她的忙碌中慢慢淡去,我们长长地舒了口气,坚强的妈妈没有倒下,又重新站了起来。
晚饭后我和她在小区里散步,走在假山旁的妈妈忽然叫起来,快看,小区里也有这种花,香棵花,我们小的时候,你外公他们就用这个做香的,看着那一片肆意灿烂的黄花和瘦小佝偻的妈妈,我的眼泪忽然涌了出来。
嫂子
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哥哥在二十多公里以外的一个县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妹妹有了孩子,我妈虽然没有彻底走出忧伤,但也开始面对现实,尽力撑着这个家。我妈甚至笑着对我说,没事,不用担心我。
周末,丈夫带我到近处的山上走走,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他说你嫂子今天没去上班,怕是病了,让我陪他去看看。我二话没说,开着车就走,刚转过弯,哥哥又打来电话,说你快点,你嫂子死了。
接到哥哥,他告诉我头天嫂子休息,他去看她,昨天吃过午饭才从嫂子那里回来,今早嫂子车间的人打电话来说,嫂子没去上班,电话也没人接,没办法只好打哥哥的电话。哥哥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只好打了保卫科的电话,请他们砸碎窗户钻进去。
嫂子已经死了,身子都硬了。
嫂子的三姐一直在车上哭,我心里特别烦躁,又不好说,我始终不信这是真的,心里有一种侥幸,嫂子只是休克了,或者等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抢救过来了。
到嫂子厂里的时候,很多人围在家属楼前面的空地上,当地公安局的人也来了,我们下车后就陪着我们往嫂子家跑,嫂子的门大开着,还有几个警察在保护现场、拍照,我们往卧室沖去,嫂子趴在床上,一只手按着胃,一只手伸出去想要拿电话的样子,电话离她的手只有五公分左右,她就这样僵死了,我的眼泪忽然止不住流了出来,我终于相信她死了,真的死了。
我本来要求警察验尸的,哥哥不让,他说,一个小工人,还会有人谋杀吗,人都死了,还要被划开,肠花肚子到处翻,我不忍心。嫂子的父亲也不同意,他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再受罪,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毕竟他们更亲,也更了解我嫂子。只是,嫂子到底死于心梗还是脑溢血,我们都不清楚,不弄明白,我的心里始终噎得慌。
我们将嫂子就用她的床单随便裹了一下,请人抬到院里,厂里工会已经联系好火化场,安排好车送嫂子去。路上,嫂子的电话响了,是侄子打的,响了几声,哥哥忍不住把手机挂了,关机。
回到城里,给嫂子换完衣服,我接侄子下晚自习的时候,对他说,你妈妈死了。侄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根本不信,他问,什么时候?应该是凌晨三四点左右,今早才发现的,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侄子说,你骗人,吃晚饭的时候我还打她的电话,她没接,挂断了,我再打就关机了,她怎么会死?怎么可能死?她明明还挂我电话呢。我再也忍不住抱着他的肩哭了起来,我说,那是你爸爸挂的。侄子不再说话,眼泪从他的眼里不停地往下淌,他咬着牙,不出一点声音。
嫂子只有四十二岁,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埋在哪里?怎么埋?三天以后就要火化,骨灰盒是要存放吗?如果要买坟地,哥哥已经多年没有上班,没有一点收入,怎么买?我们和妈妈商量以后,决定还是送回老家安葬,老家祖坟埋着我爸和祖人们,每年上坟的时候也方便一些。由于老家的族人我们认识不多,怕哥哥谈不妥,只好由丈夫陪我妈回老家商量坟地一事,我和哥哥请人瞧日子、买骨灰盒,商量火化和其他事宜。
一切如期进行,厂工会为她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妈非得参加,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妹妹扶着妈妈,我拉着侄子。到送进火炉的时辰了,嫂子的姐姐们哭着拉住炉车不让进,我在一旁一个一个用手拉,不让她们的眼泪掉在嫂子身上,不让错过进炉的时辰。终于把她们拉开,火炉像一个魔鬼,张开红红的大嘴,把嫂子一口吞了进去,侄子忽然瘫在地上,怎么拖都拖不起来。送到医院,量了血压,听了心跳,号过脉,医生说没什么,只是急火攻心。
一瞬间,嫂子已经化成一捧灰,装在那个我为她精心挑选的小盒子里。
回家葬嫂子的那天,天特别冷,才十一月份,就下起了冰凌,相比其他几位老人来说,她的葬礼简单冷清,因为举办过追悼会,加之年轻,我们没有通知其他亲戚。
嫂子就葬在爸爸的坟后面,她喜欢漂亮,妹妹特意为她买了一束花,侄子摸出几颗巧克力,轻轻放在他妈妈的坟前。
我妈小小的出租房里挂着我爸和嫂子的遗照,刚刚缓过来的妈妈几乎要崩溃了,每天早晚烧纸点香,从不间断。我们刚走到楼口就是满脸满嘴焚烧香纸的味道,弄得我们根本不敢提几位亲人,更不敢提侄子。
一直严格要求的妈妈对侄子忽然溺爱起来,每天早早起来叫侄子起床,偷偷给他塞零用钱。对妹妹的孩子却不闻不问,有时候妹妹腾不出手,让她抱一下,她说,我抱不动,老了。她把所有的心思全都花在哥哥和侄子身上,对其他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动不动生气发火,饭不好好吃,还天天喊胃疼,说带她去看她又不去,给她买药她说一点用都没有,只有哥哥买的药有用。
两个月过去了,我让我妈把我爸和嫂子的遗照拿下来,妈妈不干,说得等嫂子满百天。我说算了,妈妈,你不要一天拿死人折磨活人了,你自己也一样,一看见照片就难受,我想他们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的。
妈妈终于同意把遗照取下来,但是又提出要回老家请先生念经超度,她说,钱不要你们的,我出,只是你们要有人陪我回去。超度一个人三天三夜,你爸爸你爷爷你嫂子三个人要九天九夜,我年纪大了跪不动。看她义无反顾的样子,我们只好同意了,但我们全都在上班,只好让孩子不到一岁的妹妹陪她回去。后来妹妹说,她要照顾孩子,跪不了那么多天。表姐刚好退休,又去陪她跪了几天,终于把她的钱花光,把超度的事做完。回来后,我妈唠唠叨叨地跟我们说,爷爷怎么说,爸爸怎么说,嫂子又怎么说,我们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听她唠叨了快一个月,她终于又站起来了。
跟妹妹聊天的时候,我们都感叹我妈的意志力,从头到尾,她都没有倒下过,甚至没有躺下让我们丢下工作伺候过,或者,从小到老,妈妈经历了太多,对于痛苦,对于伤痛,早就做到淡然处之了。之后,我妈居然病也少了,除了风湿、视力之外,其他毛病没有了,后来她自己跟我开玩笑说,这人一穷,连病都不敢生了。
从嫂子死到下葬,侄子只流过一次眼泪,他一直没哭,哪怕瘫下去,动不了,输液的时候他也没有一滴眼泪。这孩子小学跟着外婆读书,初中跟着奶奶读,从小就不爱说话,有什么心事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说。刚考上高中又没有了妈妈,想想都让人心疼,我怕他自己憋坏了,就把他和我妈接到我家,总想着每天有女儿陪着,会热闹一些,可能会好一点。
可是,我低估了嫂子的死对侄子的打击。进入高二,他的学习一落千丈。我每天把他接回家,等我们睡觉以后,他又偷偷跑到游戏室打游戏,好多晚上,午夜之后,我和丈夫开着车找遍全城的游戏室。
哥哥对他无能为力,只会气急败坏地说,我不管,我管不了,我就当没生这个儿子。
上大学以后,这孩子忽然懂事起来,大二的时候,居然还去批发被套床单来卖给新入学的同学,又到快餐店打过工,至于他是否挣到钱,我没过问,我更高兴的,是他已经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了。
每年回家上坟的时候,侄子总是在嫂子坟前摆上几颗巧克力,有一次他看我看着他,就笑笑,对我说,我妈爱吃。
如今,侄子已经大学毕业,找了一份工作,经常在野外作业,非常辛苦,同去的有几个受不了那份苦偷偷走了,他依然坚持下来,并且从不在我们面前说。有时候我问他,辛苦吗?他总是笑笑说,还行。
责任编辑:尹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