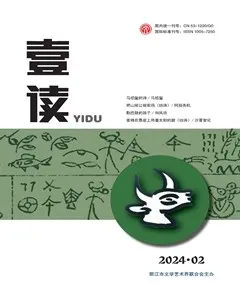小徐的香格里拉上学记
徐梦颖
那些将要去的地方,都是素未谋面的故乡。
——王小波
今年九月,揣着好奇与期待,我迈入新生活的开始。
应学校三天两检的防控要求,我提前抵达香格里拉。四个字的地名本身就带有一种迷幻感,延迟开学的日子又恰好在中秋节后,加上家里大人单位上的硬性要求,十九岁的小徐不得不一个人踏上漫漫求学路。
离家前,总被妈妈嫌弃。走之前的晚上收拾行囊,问妈妈:“我要走咯,开不开心。”可爱的妈妈回答我:“不开心,你走了,我就一个人在家。”是吧,姐姐,弟弟,爸爸都待在学校。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总是要难过的。
其实是蛮期待的,好不容易熬过高考,要去往一个旅游圣地学习导游专业,想来应当是好玩的。没办法,我一个人拖着行李,买车票,坐六个小时的大巴,订酒店。那个时候还很兴奋,就连没有晕车也觉得自己好棒。到酒店的时候,房间里摆着双人床,我一个人躺比较宽敞。洗去一身疲惫,等外卖的时候,阿姐打来电话,她说,“你真的一个人就去了吗?有同学约在一起没?”“懒得约,再说,谁会没有人送啊?”她一眼看穿我,其实还是有点委屈的,但我的骄傲不允许我讲。挨到睡觉时间,明明很安静,房子里也是暖洋洋的,未免太宽了一些,桌子,椅子,柜子,镜子全都衬得我好小一个。那天晚上,我的好朋友亚东陪我打了一晚上游戏,虽然输了一晚上但是也不再那么难过。
生物钟醒,我醒。吃过东西,退完房间。打车去古城,新订的客栈老板娘已经在门口等我,我掏出糖给她家的小孩子,他笨笨地照着他妈妈的意思喊我姐姐。我问:“州医院近不近?”老板娘说:“很近,我不是中国人。”见怪不怪,她问我:“不去玩吗?要租藏服吗?”不在我的计划之内的选择摆在我面前。
想去,没有人陪着。简单,新同学喊一个。算好时间,在泰国老板娘的介绍下,租好藏服,回来。对面的客人不好意思地敲开我的房间问我怕不怕被宰,这一身也是客栈老板娘推荐的,要交三百押金吗?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反问他。我下楼去租电动车,外省人就去租藏服去了。电动车老板夸我会挑,其实我只是喜欢绿色,又付过五百押金,稍微试着骑上一会。头顶的天,头顶的云,越发好看了。我给阿姐说,阿姐那个笨蛋居然问我,就会骑啦?我本来就会骑电动车好不好呀。
见到新同学的时候,要是赶过去的话也错过松赞林寺的售票时间了。随意跟着导航走,一直往前,往前就好了。沿着公路往前,我都能感受到穿薄衬衫的同学在发抖,真的有景区吗?跟个小村子似的,遥远的地方总是要抵达的。买完票,跟着牵马人往里去才晓得景是在里面的。马儿乖乖的,遇到车子经过也会停下来,车子里放学归来的小孩乌拉乌拉地讲着藏语,脸蛋都红扑扑的,小手也是一挥一摇,真是一群可爱鬼。景区里的湖水映着蓝天和白云,捏着自然的笔,画出来一幅绝美景色。天好看,云好看,牛好看,羊好看,草原也好看。文字的苍白是显示不出自然的鬼斧神工来的。
我要去寄明信片,逛到古城里面去,跟着导航走,总是遇到死路,怎么也寻不见一家店。快要天黑,越来越冷,坐在吃饭的地方,往外面看去,游客不算多,有着古城该有的样子,晚上的城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韵味在。不好吃的牛肉锅也没扫兴,至少酸奶是好喝的,青稞饼是好吃的。吃完饭,得去看一下转经筒吧。跟着那个导航走,又寻不见,我说那个亮亮的地方好看就去那吧。没想到,爬完不算多的楼梯以后,看到的就是转经筒,一圈一圈的人转动着它。那一刻,我像模仿人类的猿猴,虔诚地祈福。树影婆娑,被灯光晕染,转经筒也好看。
晚上,还完东西,拿回押金。我照着老板给的提示,去找寄明信片的地方。小白塔,走过去,太晚了点,驿站歇业。没关系的,第二天很早我就坐在里面,挑了几张明信片。我不会忘记你,我会寄明信片。
读书就得上学去,办好手续,铺好床,认识新的人,就已经在消耗能量了。当我一个人提着超级沉的行李箱,爬楼梯,候车赶车,看地图认方向,就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面对了。獨行的时候总会遇到有趣的人,军训前,拜托学校的漂亮姐姐帮忙拿快递,后来收获到美女老师给的带着祥云富有当地民族特色的手工制品。
军训了不算长的时间,慢慢适应着生活,你会发现,你从来不会想到云会堆得那样厚,常有人把云朵比作棉花糖,但这里的不像,它堆叠得那么厚,像羽绒服里的鸭绒,填充得满满的。刚来的时候,每天的天都好得不像话,学校对面的山似乎一天天地背着我们在变幻,稍不留意,再看见已经是另一个颜色了,云藏在里面让你只想拥有一片云,日头照在上面,金灿灿的,是该朝圣的吧。
日子溜走,零下几度的天,对落雪的期待又多了一分,想听一座雪山。那些山一座连着一座,看不到尽头的。读书月余,逛够了城里,特色建筑也总是会看烦的。要待个几年的地方,还有那么多山川好景等着无畏的人去探险,怪不得要徒步去旅行,人,要有些坚守,有些浪漫,要拯救自己。于是“敬畏自然万物的思想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往这里来,往里面去,去寻找天堂。
2022年高考,已经遥远得像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一样。人生就是这么刺激,短短几天竟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我,往哪去,命中注定。在迪庆,在香格里拉,在民专,我在。
九月,身穿薄外套时老是感慨怎么他们穿的这么厚,那等到了真正的冬天,他们又得穿多厚啊。那时候觉着好玩,觉着有趣,在一众朋友们想家的时候,我可以脱口而出:“我不想。”九月过得太快了,成天在校听听讲座,上着那早八晚九的课,吃着那些陈旧不变的饭菜。也许到了新的地方见什么都会觉着稀奇吧,就连二十二号那天看到了双圈彩虹,也记了这么久。
十月,在期待着放假的日子里,迪庆没给放。时刻蹲守的我,“抢”到了出游的机会,怎么出去的并不重要了,较为开心的是,在别人上学的日子里,可以悠闲自在地游走在校园之外,空气也开始变得不一样。陪生病的同学在医院打上点滴,我开始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游走,城就那么大一点,一个人,又能逛到哪儿去呢。我去看了巨大的毛主席挥手像,记住了池慈卡街,用脚步再一次丈量了独克宗古城,外面的阳光洒在身上的时候,看见的每一朵云都是那么好看。什么时候能自由呢?我甚至一个人坐上公交车,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只记得这些路,这些石头,我见过。在通往达娃路的时候,车上有一群人,她们穿着我没见过的民族服饰,哼着我没听过的曲子,在别人的捧场下,她们哼了很久,耳朵里都是别人在讲好听。她们要去哪,她们要去做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又回到那个了无生趣的地方。刚过五天,又在听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大讲座,溜出校门以后,我们仨在医院做完核酸做完检查,其中一个人被迫留在那里打点滴。现在好了,两个人了,去哪?我们晃啊晃,没有找到导航里的那家店,古城,就这么好逛吗?来都来了,转经筒再去转上一圈吧。转完以后,我们继续走,盲目地进了一家店,它叫什么名字,我想,我和她都不会记得,东西难喝得要命。八号的时候,迎来首次出门放风的日子,没有什么比出去吃饭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吃饭毕竟是每个人都无法割舍的。在大理的阿姐还在穿短袖。我已经被这里的风催着往前走,走了很久。九号的时候,难得吃上会使人幸福的小蛋糕,分享,让这份幸福不止成为我一个人的。在学校里的日子,大体上是麻木的,麻木着,麻木着,就会想家,想我的小破家,想我的爸爸妈妈,想我想的每一个人。
十一月离回家好像又近了那么一点,但还是不能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小王子》里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六号与我而言就是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在迪庆特别开心的一天。中午和来迪庆遇到的第一个帮助我,我喜欢的人一起吃饭。晚上,我的大学班主任肖老师拎着蛋糕来为班级庆生。我们还像一些小孩,慌慌张张地去采买东西,拜托在城里的同学捎上一束鲜花。我翻找出一张好看的卡片和一些纸条,每个人都在上面写字。我们一起吹灭蜡烛的时候,心中的光亮悄悄点燃。遇到这样的老师,真的会让人开心好久好久。我们的许多青春,她在替我们见证着。我那天真正发自内心的觉得来迪庆读书好似不赖。我想,如果没来迪庆念书,大抵是会遗憾的。我们无法预知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这个瞬间变成回忆。月末,期待着,盼望着,急着快些期末考,好快些回家。
十二月七号,是我回家的日子。通知来得突然,七手八脚地收拾行李。坐上学校为我们准备好回家的车子时,激动是难以避免的。车子一路往前开,离家越来越近,好多画面在脑海里交织,过去那几天的苦,我不怕吃苦,只怕不开心。九月离家前的清欢,到校后的不安,慢慢认识到的新朋友,渐渐适应的新开始……就这样暂告一段落了吗?还没见到这里的雪呢。
到家后,总觉着少了些什么,总觉着好像还在做梦,我说不准有没有开心,有没有……看了某位老师的朋友圈,她甚至把“突如其来”错打成“突然其来”,看见文字的时候,分明让人产生强烈的感情。文字不会说话,我又清楚的听到它在说,说我们的时间也会这样短,说也许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会离别。甚至,有的人还没说上句话。不过,我始终相信,始终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是光明的。
三个月的短暂光阴一起构成了我们潦草的大一上学期。记忆里,对香格里拉的记忆仍旧停留在一天转了几次的转经筒上。才惊觉,原来还哪里都没去。
责任编辑:尹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