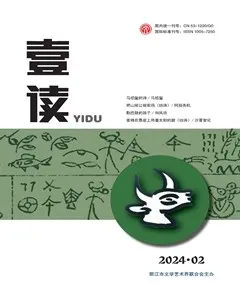小说中诗性世界的建构
陈映铷
诗学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诗艺学,是指与诗歌创作相关的理论研究。诗学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这一体式,戏剧创作、小说等文学文本中也在其讨论范畴。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和生命的关怀,文学形式不仅是主体生命的扩张和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于生命本体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发轫于生命意识,对生命本体进行观照,创作了众多富有生命气息和生命活力的作品,“生命诗学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本质特征。”彝族青年作家苏钰琁的中篇小说《老白脸》(载《安徽文学》2023年第9期)讲述滇西地区山林中的滇金丝猴守护人蜂猴和年迈的滇金丝猴“老白脸”的故事,作家聚焦原始的生命欲望,关注白雪千里、悬崖之上的生命群体,从其艰苦环境中的生存渴望和生存方式出发,通过凝视和书写人与动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了滇西大地蓬勃的生命力,构建了一个生命千姿百态的诗性的世界。
本文在生命诗学的视角下,从叙事语言和结构、自然生态以及精神生态三个方面探讨苏钰琁《老白脸》中诗性世界的构筑。
一、生命意识的诗化书写
《老白脸》中苏钰琁用诗化的意象、诗化的语言和诗化的抒情方式书写雪山上炽热燃烧的生命,“生命诗学的出现,须要生命意识成为创作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生命意识指人类对生命存在状态、生命本体问题及永恒价值的体察、珍视与省思,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生命苦难的消释和超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作者的生命意识在清新动人、婉约绮丽的描写中磅礴,是对土生土长的滇西山林中所有动物爱得深沉的蜂猴,是白雪皑皑山林里精灵一样活蹦乱跳的滇金丝猴们,是可爱憨厚偷吃蜂蜜的母熊和熊崽,是飞过千山却被毒死伶仃挂在枝头的戴胜。
苏钰琁写生命意识,不写激烈的对抗,不写灾难的痛苦,她写生命的可爱,写生命的脆弱,写生命和生命之间的惺惺相惜,正如其笔下皎洁月光下的潺潺溪水一样,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都化为无言的、诗化的语言和抒情,静静地流淌在小说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唯美的生命画卷,对生命意识的诗化书写是作者构筑其诗性世界的第一向度。小说和诗歌之区别在于抒情,苏钰琁的小说运用了诗化的语言和抒情方式,使其小说充满了浪漫的气质。
艾略特在《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中提到戏剧创作中“客观对应物” 这一理论,该理论的内涵是指通过具体的物象来表达特定或者抽象的思想和感情,小说中主人公和其他角色的感情流露和变化不是通过角色的内心独白,而是巧妙隐晦地暗含在景色的描写当中,如写到蜂猴给儿子娶了媳妇回家之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他温馨又满足,作者放弃大面积刻画人物心理活动过程,而是转向风景的描述——“远处的山一层比一层黑,月辉洒在山肩,蓝黑的大幕披在顶上,白里雪山既伟岸,又柔美,像通水村的母亲。”蜂猴早年丧母,最疼爱他的爷爷也因为采摘蜂蜜维持生计而跌下悬崖,家庭温暖是他在大山深处生活的梦寐,也是他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蜂猴追寻的家庭温暖是亲情伦理的纽带,也是生命最简单最原始的渴求。享受天伦之乐的蜂猴在那一刻感到月光不再清冷,雪山不再寒冽,通水村不再孤苦,而是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当蜂猴清晨起床发现老白脸中弹死去,作者将蜂猴巨大的悲怆埋藏静谧的景物之中——“脚下的土地传来冰冷,也传来迷惘,所有杂念都在此刻死去了。”“一阵风过,柿子树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用土地的冰冷和迷惘象征蜂猴感情源泉的枯竭,小说的结尾用“最后一片叶子”的落下暗喻死的定局,也象征生命中的无力感。柯勒律治在《论诗或艺术》中提出“艺术之本质即心与物之契合”,认为“艺术中天才的奥秘”在于“自然变为思想,思想变为自然。”作者善于运用这一“天才的奥秘”,将《老白脸》中人物的情感变化与自然景物串联,交织而生的正是“心与物之契合”的艺术的诗。
作者将人物感情的起伏藏于星月之际,藏于山水之间,藏于天地之中,藏于一树一叶之间隙,用诗化的意象为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意味和绵长的哀伤。写赵娣儿害怕杀猴秘密暴露的恐惧——“风轻轻扬起,森林空洞的涛声一浪又一浪袭来”,“蜂猴身后森森的杉树影越长越高,扇动着溪水发出风声,听起来像是白里雪山在长叹”;写蜂猴的最终抉择——“柿子树上显现出清晨的颜色,将要落尽的黄绿叶片上,蒙着一层微微的蓝。那种蓝非常清冷,是眼睛看到的瞬间就能感受到温度的蓝,带着霜,带着和白昼交换命运的决心。”雪山、流水、月亮、风和柿子树,这些无生命的意象恰恰熔铸了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它们隐含着与人类情感和生命共存的美感,构成了意蕴悠长的独特的诗性空间。作者的生命意识还体现在生命本体个性的理想化之中。笔下的老金丝猴老白脸具有“人性”,代替蜂窝煤他妈坐在高堂接受赵娣儿的跪拜;蜂猴下山寻找偷猎人的时候,老白脸担忧地望着他;和蜂猴同吃同睡,甚至能读懂蜂猴的眼色,连儿子蜂窝煤也禁不住诧异“老白脸成精啦?”。而主角“滇金丝猴守护者”蜂猴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神性”的色彩,他的灵魂自由热烈,世世代代在条件艰苦的山上生存,年轻时以狩猎为生,为了保护滇金丝猴和自然环境甘愿放下心有留恋的猎枪,不为名利也不为钱财,每天都跟猴子打成一片,与其说是滇金丝猴守护者,不如说是白里雪山的守护神。
动物人性化,人物神性化,人性与神性的并行是作者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美好构想。
除了用诗化的意象和语言书写生命意识,小说通过叙述以老白脸为代表的动物生命,直视生命的本质。他们生于山林,长于山林,在藤蔓之中穿梭,在陡崖峭壁之间飞跃,在广博高深的雪山之中自有一番恣意的天地,但人类的贪婪和私欲会使它们死于非命。作者纵然直击人性之恶的痛点,记录生命的脆弱,但她仍然相信跨物种之间的真挚情感,在深山之中呼唤生命的平等、尊重和关爱。
二、生命共同体的空间营构
“生命共同体”的具体内涵是指,具有生命特征的物体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之中的各部分共生共存并相互制約。现代工具的理性统御使得人的欲望像打了催化剂一样过度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日益严峻。生命共同体包括了“生命”和“共同体”两部分,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是概念的核心,而“共同体”中的“共同”则是落脚点和基本底色。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共识”,它是共同体自己的意志,是共同体成员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因此,共同体中的人类应该享有同一共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命运紧密相连。”苏钰琁在小说中通过刻画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凝眸生命共同体中“共生共享”的生命意识,实现了其诗性世界构建的第二向度。
“生命意识复归与生命空间建构是生命诗学发生的逻辑起点。” 苏钰琁在《老白脸》小说的创作中直面自然生态的发展问题,植根于滇西山林特定的地理条件,设置横跨三个年代的时间线索,运用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事方式,营构一个具有厚重时代印记的、但又丰富鲜活的生命共同体空间。作者通过人物之间的回忆和对话,跨越时间的长河进行架构,滇西山林数十年的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强烈体现着时代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苏钰琁建立的生命共同体空间不是停留在特定时间的地理空间,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的限制,是历史的、动态的、延续的,具有时空艺术特征的存在。在人物的回忆和对话中,滇西山林的村民不再以狩猎为生,而是转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作者着眼国家政策支持下的乡村建设,将片段式的关于白里雪山乡村变化的叙述串联起来,从蜂猴爷爷“生存艰苦,靠山吃山”的年代跳跃至“80年代国家委托蜂猴等村民寻找滇金丝猴”,再跨越到“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打破了传统单一的乡村改革故事的线性叙述,在回忆和现实的重叠之中,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构建了一个活态的滇西山林。
苏钰琁在人与人关系的书写中,采用了符号化和对照的形式,颇有沈从文式创作的味道。作者将蜂猴所在的乡村世界和赵娣儿所在的城市世界进行符号化,在“乡村和城市”两者的冲突和相互对照中透露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蜂猴所在的乡村山林类似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蜂猴为代表的乡下人有着至纯至善的情感和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即使是对蜂猴颇为妒忌,违法制造土枪,幻想重新狩猎的熊卫民,最后亦和蜂猴冰释前嫌,放下心中的执念和芥蒂,对山林保持尊重和敬畏;蜂猴、熊卫民一家的家庭氛围都十分融洽。相反,同样是出于私心,赵娣儿处心积虑,罔顾法律,开枪杀猴;赵娣儿城里的爸妈对赵娣儿极为冷漠,家庭气氛达到了冰点。作者透过蜂猴与赵娣儿、熊卫民与赵娣儿两组人物的对照,指出了乡村世界对人心灵的净化,这里的人性尽管显得些许粗俗和野蛮,却保留了人性最初的纯真善美和原始的健康活力,呈现一种粗犷的、雄健的、勃发的生命形态,作者赞美并向往此种理想健康的人性。不难看出,赵娣儿身上体现着城市世界对人的异化,阴暗、算计、病态,带给人的压抑和变形,把赵娣儿的美丽揉碎变成墙上坑坑洼洼丑陋的弹痕。在人与人的比较中,城与乡的世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苏钰琁在两个符号的对照和互见中,呈现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和人性形态,表达了对乡村世界中和谐共生的人性与人际关系的赞美,对城市世界中物化、异化的人性缺陷深感遗憾,在横向空间上为其诗性世界描绘了一幅关于人性思考的侧写。
生命共同体中的“共同”表现为统一性和整体性。人类凭借科技和工业化的力量对自然毫无节制地进行索取,导致人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恶化,修复环境,挽救自然,回到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之关系,是营构生命共同体的必要之举。这与道家所提倡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整体生态自然观相契合,亦与儒家“天人合一”“仁民爱物”之说暗暗相通,可见,无论儒或者道,中国古代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伦理智慧,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自古以来便有之的生命观念。在表达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感情关系时,作者表达了“生命与天地同构”朴素的整体自然观。蜂猴和老白脸的情感和生命紧紧捆绑在一起,老白脸的去世让蜂猴心如死灰;蜂窝煤悲观地认为不准打猎使得山林的动物吃不饱,蜂猴劝解他“傻小子,这山不够还有那山,山自有把水端平的办法,你操啥心。”余鲜花劝丈夫熊卫民放弃不切实际的打猎梦,“猎人只能是过去式,也必须是过去式。”苏钰琁笔下的滇西山林体现着人物情感的朴素,思想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苏钰琁对滇西山林的凝眸,无声地渗入她对生命本质的赞美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百里雪山下的一隅,是她对“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形式的无限向往。
三、“诗意栖居”的理想遥寄
现代科技力量冲击下的社会,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逐渐紧张恶化,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中彼此猜忌和怀疑,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早已瓦解坍塌,“精神生态”是“生态学”中继“自然生态”后提出的另一重要概念。关注人的精神生态,对于抚慰人的心灵,重塑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觀,重建人类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有重要意义。
苏钰琁以敏感的触觉捕捉到人类精神生态的错位,在小说《老白脸》中,她用人性的对照和老白脸的悲剧表现了人类心灵的扭曲以及精神世界的失衡。在乡村山林中审视城市文明,苏钰琁意识到现代文明不仅会使人类丧失自然家园,而且会使精神家园变得荒芜一片。在书写生命意识与自然之美之外,苏钰琁还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观照,她笔下的白里雪山的一切人物,代表性地刻画了当代人的群像——像熊卫民一样“违猎之心”隐隐作祟的人,像赵娣儿一样的为自己的私欲而走火入魔的人,像毒鼠强一样对自然毫无敬意的人,揭示了欲望包裹之下的摇摇欲坠的精神生态危机。作者毫不避讳地描写“丑陋”和“遗憾”,她写赵娣儿姣美外表之下的被异化的心灵,写被枪声破坏的幽静的山林,写年迈的老白脸安静地在蜂猴怀里死去。将安静打破,将美丽撕碎,将美好毁灭,作者有意识地将悲剧呈现给读者,其在深深浅浅的弹痕背后,在支离破碎的人际之间,深切地召唤着人们关注人类心灵世界,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别让枪声打破诗意的宁静。
在“诗意栖居”的理想遥寄中,苏钰琁完成了其诗性世界最后的构筑。不像内蒙古的雪山牦牛大草原,也不像湘西乡村的小桥流水人家,苏钰琁的小说,写滇西山林的自然生命,写傈僳族生存的挣扎,写滇金丝猴和人之间的爱,《老白脸》中流动的生命诗学的观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风景无比写意,视野无比开拓的诗性世界。
责任编辑:李惠文 和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