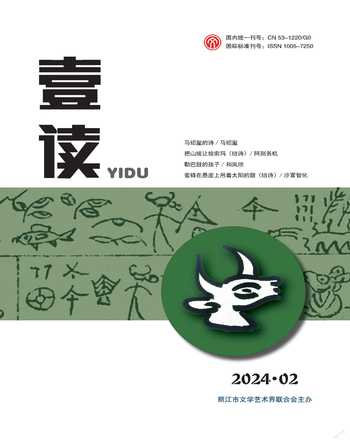马绍玺的诗

马绍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兴滇人才“文化名家”。有诗歌发表在《诗刊》《民族文学》《西部》《草原》《西藏文学》《边疆文学》等刊物上。出版诗集《秋天要我面对它》《襁褓与行囊》。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山毛榉
叶是山毛榉的唇
沿雨水的視线静静张开
让天空看清挤在树身两侧的语言
谁更亲近脚下那簇深埋的
火焰
一朵花模仿一种笑容
或是山毛榉一年的泪水
谁也说不清
也许是一些美丽的泥土
它们开在山毛榉的眼里
忧伤之夜
为一种姿势祈祷
把向往吹向远方
埋进每一扇向阳的窗
鸟一定是山毛榉的又一种果实了
作为鸣叫的伤口,它们
无力躲过
脚下的泥土和河流
这些阳光手里捏紧的血的声音
怀念
那时,天上的云是说着话的
湛蓝蓝的
星星们结队走过它们的门
那时,鸟们栖居宽广的大地
秋天染红了它们的嗓音
只是,起飞后
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时,我走在孤寂沉思的林间
像那率领春天一齐开花的黑少年
纳帕海
牧人的帐篷边我遇见你
蓝眼睛的纳帕海
你有
一夜的星宿和半扇
小小的窗
以及驮来飞鸟的
十二月的马匹
——全在这里了
幸福的我们和热爱草场的人民
还有黑夜中
光芒闪烁的青稞
秋天要我面对它
如果阳光命令,我就刻写阳光
在万物散布的大地上
用南国的温暖和农夫耕作的细心
如果秋天命令,我就刻写秋天
用天空的宽广和精明
催促果实成熟,在季节里加进最纯的甜浆
如果村庄命令,在芦花枯败的河岸上
我祈求泥土将我酿作
稻谷玉米和马铃薯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像直插而入的刀
深入事物内部
中断了我跟朋友的交谈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便收买了整个空间
像一个预先存在的妓女
在我窗外肆意地奔跑
并用带寒的手
划破我们的深处
很简单地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便是整个世界
它湮没了我们以及昆虫的叫声
我们谁也说不出更多的感慨
除了满脑子的风声和雨声
那是我们的一些日子,
一些秋天的日子
那些夜晚
我们把火种藏在深处
用植物普遍生长的饥渴相互交谈
双手靠墙
像游戏的孩子
我们的语言触摸黑夜的真实
并且深深理解
我们各自来到对方的暗区
然后点燃火,深藏的火
栅栏之内照亮一切的火
那样明亮的时刻
我们无限地朴实,像田间劳作的农民
我们围火而唱
火啊火啊,请宽恕我们,燃烧我们
因为这全是你的赐给
因为早晨播种的我们下午便已收割
然后又在子夜之时祭祀我们的神
鸟类的神,河流的神,原野上葡萄架下的神
顿时,我们是宽广的粮仓
置于时间和真实的内部
我们接纳,承受
并且带着广泛的宽容
就是那些夜晚,当黎明擦洗天空
在早早的大路上
我们浑身接近了生存
以及天空中更好的阳光
要是我也是一只鸟多好
夏天,你手中的世界
何其广袤
你绿化了我的心
把青草和阳光赐给我
我看见鸟们在欢乐地鸣叫
(尽管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它们每天拖着
长长的
幽怨的爱情
跟太阳一起
在我们的头顶以及树林间
飞行
夏天呀,要是我也是一只鸟多好
你看,你手中的世界
何其广袤
它让我想走出房子
像草们那样青青地绿
像鸟们一样高高地飞
你蓝色忧郁的内心……
玫瑰
你的内心是泥土和美丽
路
你的内心是孤独和远方
星星
你的内心是蓝色的忧郁
窗前那棵树
我六岁那年,父亲还没有
种下窗前那棵树
可如今
它已遮盖了我家的屋顶
——我是早起洗脸时
毛巾划过眼前的瞬间
忽然注意到它的长大的
我听见一群人从山坡上下来
我听见一群人从山坡上下来
黑得平坦无垠的夜是她们的路
那些黑色的面孔和谈话
告诉我
一群姿态正趁夜潜来
并申明,那是些
多情的女孩
身体和笑声一并挤满了黑夜
这就是我听见的一群人
一群女孩
她们正从山坡上下来
像一列
晚点了的火车
她们依然走着,像记忆中
那列晚点了的火车
欢快地,把笑声
阵阵地送到高处暗淡的天空
让所有的夜和黑
发出星星那样的光来
照着自己走路
我在墙内的小屋里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
拉亮我的灯
或者
动身出去迎接
音乐会在最早醒来的……
音乐会在最早醒来的
鸟群间举行着
剧场
就在有七棵树的小院里
七棵树
是不同颜色的七个演员
在鸟儿间飞来飞去
我躺在黎明与黑夜交汇的时刻
像挽歌里无法从昨天醒来的
乐章
独奏之后
音乐会在我梦中
走向欢悦的合唱
歌声里洒满新生的阳光
法署村
我来到之前
它就在這里生活着
陡峭的山坡,把它
像一排青稞架一样
竖立在荒凉大山的肩上
几乎是空寨了
年轻人都坐着途经村脚的汽车
去了武定,去了楚雄,去了昆明
去了深圳、北京,或者上海
就连剩下的羊群
也爱在高速路旁吃草
有汽车驰过时
它们会停下嘴里的活
听牧羊人那句
“还是高速路上才有风景”
老人们在院墙里
吃饭,睡觉,晒太阳
还常年喝酒
孤独的他们
非常乐意跟我的录音笔
倾诉他们勤劳挣扎的一生——
“五年前修高速公路时
那个住着我们神灵的山洞被挖了”
——当第三个老人再次说出相同的话时
我的录音笔闪了一下
没电了
五月二日,我们夜宿法署村
一切都静得有些害怕
读马金莲小说《长河》
伊哈死了,大雪给他盖上一床被子。
小小的素福叶死了,大雪给她盖上一床被子。
母亲死了,大雪给她盖上一床宽宽的被子。
老老的穆萨爷爷死了,大雪给他盖上一床厚
厚的被子。
死亡是时间黑色的伴侣,如河水,
透过白雪缓缓流淌;
像一个女人的怀抱
用无尽的苍茫
把村庄裹进她宽阔温暖的
胸膛
妻子的出走
每天去菜市场
你都要和许多人讲话
涨了又涨的菜价
无法判断阴晴的天气
各种说不清的疼痛
所有说了又说的重复
……
可是,那天,跟你说话的也许是上帝
时间也许只有三秒
甚至更短
你选择了空手而归
回家时还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表情
你轻轻地说
你累了,你要慢下来
你想把自己像豌豆一样
储藏在远古的记忆里
你还想……
儿子不解地望着你
只差把声音哭出来
之后,你独自去了远方
去听了洱海的宁静
看了玉龙雪山的飘渺
你把叹息放在灌木的肩膀上
还把几根早白的头发埋在鹰的故乡
三天后
你还把高跟鞋也借给了瘦瘦的金沙江
“那不是爱情的表达”
你说——
“一条大江更不容易
双脚到处,不知撞碎了多少岩石
老岩变成了砂砾
堆满河床的苦难和疼痛了
还得不回头地走……”
幸亏有你
我天生胆小
亲爱的,幸亏有你
在尘世替我
向陌生人问路
如果我先死了
我一定会在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等着你
请你替我问
通往天堂的路
如果有来生
哪怕隔得再远
人海再茫茫
我也一定想办法
找到你
请你继续为我
问另一生的路
母亲的艺术
母亲的艺术,就是
用最勤劳的双手
把阳光植入田野的深处
让乡村飘满泥土的芬芳
用从少女到老妪的时光
把故乡雕塑成
稻谷、蔬菜、向日葵和子孙们
瓜熟蒂落的天堂
母亲的艺术,就是
用一生的信仰
与阳光为伴
在最朴素的事物和人情中修行
把破碎抚摸成平整
把时间雕刻成家屋
把暗夜守成光明
把平凡养育成美德
伤口
我的身心从小就布满了伤口
有针尖扎的
有石头砸的
有刀从背后戳的
有黑暗和贫穷灼伤的
当然,也有自己摔伤的
……
有的伤至今还开着口
看得见里面千疮百孔的灵魂
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就是这些带血的伤
养育和创造了我
它们是另一种乳汁
带着疼痛味的乳汁
读曾昭抡的《缅边日记》
出自化学家抗战期间
由昆明到滇区边境的考察
文字铸就的日记
像一座故乡的博物馆
里面珍藏着
绵延千里的滇缅公路
以及滇缅公路出生时的激情和样子
一个天上完全无云的晴天
“道治”牌汽车惬意地
穿过昆明湖旁的一片坝田
向西行十六点六八公里
是尤加利树和白杨的碧鸡关
又西行一百二十五公里
是熬制食盐的一平浪
再西行二百五十二公里
车已过楚雄,公路盘旋上山
当众峰都来到脚底时,化学家相遇了
“前不見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人
滇缅公路的高潮在杨梅岭的“杉松哨”
那里,一个走出了时间的乡下女孩
戴着山茶缀成的花冠
玫瑰色的脸也被点燃
在“功果桥”,澜沧江自群山中流下
涛声里沉浮着老虎翡翠色的吼声
而它野性的四蹄早已流浪到
七百五十九公里外横跨怒江的惠通桥了
江水的西边,是住着
和尚、土司、土人和洋人的
芒市、遮放、护浪、畹町
……
在所有的书中,只有这一本
能引领我回到故乡
它让我看见了
我可能的脚印
一串串地
在文字中排列着
秋已深了……
秋已深了
妈妈——
心
应该安放在
哪里?
母亲,我对不起你……
那个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人
如果你遇见我母亲
请不要告诉她
这几年的我
每天在哪条路往返
每天在哪一间房子里荒废和凋落
每天怎样一寸一寸地感受生命的卑微
求你了,请不要告诉我的母亲
因为
我对不起十月怀胎的痛苦
对不起乳汁的温暖和纯洁
对不起故乡的阳光和泉水
我和我们
秋天,午后小睡醒来
发现,自己
并不完全躺在床上
有一部分
还在前几天住过的小酒店里
有一部分
在刚刚坐过的
北方原野那列行驶的高铁上
有一部分
被某些人
朝他们的方向
使劲地拽着
还有一些部分
上了山岗
随云飘荡
离我最近的那些部分
也已经在时间中碎裂
像窗台上下午金黄的阳光
我想起床去追他们
让他们带上我
一起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哭泣微笑
无论
青丝
白发
可是,他们实在太多了
各在各的方向
各在各的远方
他们把我留下
在一个孤独的
他乡
爱和恨
好几次
母亲对我说:
“唉,你们弟兄几个,
刚刚还在我怀里,找奶吃,
即时就个个成了半老人了。”
说这话时,苍老的母亲
眉宇间充满了无奈和懊恼
母亲也许在想
要是
我们都是她手里的蔬菜瓜果就好了
她要用积累了一生的农家智慧
让我们在来年春天
重新——
发出新芽
开出
新花
黄菊
大地上的野花
我课堂上的小女孩
泥土的滋养,说话
带着露水的味道
还有,夜色的体温
书房里插满了
拇指大的风筝
……
最大的遗憾是
父母常在落日时分的海边
彼此把对方的影子
打倒。甚至是
活埋
她告诉我,她故乡泥土的深处
埋着大片大片红色的铜
大地的心脏
火焰往暗处燃烧
而她把一双
穿牛仔裤的腿
深深踏进稻花的胸膛
仿佛大地长出的根
责任编辑:黄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