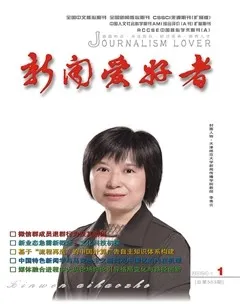非遗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传播逻辑与文化传承
徐竟涵 王赫玺
【摘要】非遗微纪录片,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文化事象、传承主体在微纪录片的形式下进行叙事建构的文化影像志。借助于影像人类学对特定社群文化的研究与表述能力,表达出具有丰富文化描述和理论阐释价值的影像文本。从叙事策略、传播逻辑、文化传承三个不同侧面出发,以影像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微时代下非遗微纪录片生产、传播、延续的路径。
【关键词】影像人类学;非遗文化;微纪录片;叙事策略;文化传播
移动视频作为一种迎合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不仅符合了人们不断变化的观看习惯,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新的观看方式,其以迅速崛起的姿态成为主流的传播方式。根据CNNIC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络视频和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0.44亿和10.26亿,用户使用率分别达到96.8%和95.2%。[1]這些社会趋势和行为明确地证实了“微”时代和微文化的到来。
微纪录片作为微文化样态下的产物,相较传统纪录片更加契合当代社会多元化、碎片化、快节奏的特性。关于微纪录片的概念厘定,有学者认为: “微纪录片应是指依托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媒介,适应网络化传播的时间较短、篇幅有限,但是能够以小见大,进行多种艺术尝试的纪录片作品。”然而,在阐述媒介形态嬗变的同时,不可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在这一媒介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非遗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不仅代表着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承载着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其同样在日益成熟的纪录片制作中逐渐成为一类稳固的要素。同时,非遗借由传播建立起一种具备明确观念以及受众认同的文化空间,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建构创造了可能性。[2]
在“纪录片+”的题材融合创新模式下,基于微纪录片的形式表征,以“非遗”项目作为表现主体和审美对象的非遗微纪录片,生产出以人类学理论为依托的非遗影像志文本与趣味性、互动性、话题性强的纪录影像作品。这些作品书写了具有人民性和时代性的记录影像,不断地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媒介作用,充分体现了“时代影像志”的使命。
一、非遗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在非遗微纪录片的叙事建构上,基于非遗文化自身的历史价值,采用故事化、情节化等叙事手法,符合新媒体互动、单义、时效等媒介特征,进而实现约翰·格里尔逊所谓“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与将表现对象“置于与之共时的现代文明语境中审视,对过去时态的文化形态加以现在时关注,使其具有历史的厚度和现代意义”[3]。
(一)“社群文化”的主题聚焦
近年来,微纪录片成为一种有力的文化观照工具,特别是在非遗题材方面。其叙事主题以非遗文化本身为物质载体,通过展现与文化时空性关联的处于社群中的个体,如陕西百集非遗微纪录片《匠人故事》,以短小精悍的6分钟篇幅,选取了某一特定非遗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从个人史出发讲述微时代下“一生择一事”富有匠人精神的传承者;或从社群本身完成叙事构建,如长城非遗系列《远行的毛毛匠》,关注阳原县的毛皮文化,通过对非遗文化历时性的表述,展现了百年前以阳原毛毛匠为代表的张家口皮毛商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群的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与非遗相关联的群体正逐渐转变为有着共同文化诉求的人们。
(二)创作主体的“主”“客”转换
在影像创作中,区分“主位”和“客位”涵盖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应于影像人类学中的“本位视角”和“他位视角”。基于人类学诞生土壤的关系,传统人类学式的影像大多按照他位视角,即外部观察者的角度,这可能导致固有的文化偏见和种族中心主义,使他们呈现出刻板化和符号化的方式来展现他族文化。
随着参与观察,文化相对主义等方法和概念的提出,以及爱德华·萨义德的“人类观”,均意在强调观察者自身文化背景对观察和理解其他文化的影响。在“本位视角”下,人类学式的纪录片主要记录了一个社群中普通群众视角中的文化,即观察当地人的“眼睛”里的文化。在当下非遗微纪录片的创作中,创作者采用平等的姿态记录非遗文化本身,让拍摄的主体阐释自己的文化。在选择景别和摄像机运动方式时,通常使用广阔的视野和平稳的摄制方式,以保证对文化和“关联域”的信息完整性。
在非遗微纪录片创作者的专业化、精细化制作团队之外,在抖音、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以非遗微纪录片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了大量由本地居民所拍摄的“社区影像”。尽管这些影像制作通常简单朴实,画面可能粗糙,但它们传播着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文化风貌。由于拍摄者与当地联系密切,更能够理解其文化内涵,避免了信息的失真。而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当地居民具备了自主表达的影像能力,他们所创作的社区影像表达了对本社群的“主位”文化叙述,并弥补了“他位视角”下人类学知识的不足。
(三)非遗文化的影像深描与语境强化
人类学意义的“深描”是指民族志工作者对田野事象进行深入社会表象之下多层级、结构性的细致描述。[4]这一研究方法是由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盖尔兹在他的著作《文化的解释》中首次提出,并指出深描的四个关键要点即深入理解,多层次描述,文化背景、语境和理解。[5]
而对非遗类文化的深描,创作主体将影像媒介作为呈现方式,深入到原住地社区和文化土壤中,对物质性非遗文化元素进行精密记录和细节呈现,如文化实体、传承主体、传统技艺和地区风貌,并以“语境强化"的方式,丰富和准确地描述了这些文化事象中蕴含的多维信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留住手艺》和北京电视台的《匠心北京》以影音方式记录了各种传统制作工艺的工序,如手工榨糖、酿酒、竹编等。这些影像作品不仅展示了手工艺的细节,还呈现了非遗文化传承所面临的挑战、传承者的家庭生活以及原住地的地区风貌等多方面内容,构建了语义丰富的影像志文本。这些社会行为和文化事象的呈现丰富了深描的语境关联。
考虑到非遗微纪录片的“微文化”特点,其叙事篇幅相对于传统纪录片更为精练,这更加考验了创作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对叙事节奏的把握,体现了微观、精细、真实等内涵。
二、非遗微纪录片的传播逻辑
(一)用户导向的生产逻辑
非遗微纪录片在“PC+移动+OTT”的多元生态下,尽管经过媒介语境对信息碎片化的处理,依然保留着客观真实、诗意表达等传统纪录片的核心要素和其自身独立而完整的语义。而在这一基础上,微纪录片基于平台属性、受众群体的收视习惯,生产出适应年青语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新技术手段的不断涌现使传播形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受众利用这些新的传播技术手段成为更加积极、具有参与精神的用户。”[6]借由互联网高度的互动性与信息丰富度,受众在互联网这一开放性平台,面对下沉市场的媒介技术所带来不断降低的创作门槛和播出渠道多元所带来的自主选择权的增加,促使其作为市场主体的本质。在“抖音和ta的朋友们”的官方账号下以“非遗正年轻”为主题,非遗创作者以抖音为词条,收录并持续更新非遗创作者的纪实故事,播放量超6000万。由此可见,受众不再局限于观看者,更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重塑微纪录片的内容生产逻辑,并通过网络的互动连接功能,实时高效地通过弹幕,评论参与非遗微纪录片的后续生产步骤。与此同时,生产者也可以通过观看人数、完播率、实时在线人数等多维数据指标判断视频所存在的问题。
(二)多元联动的播出渠道
非遗微纪录片的播出在自身的衍生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外,结合与因制作单位和内容需求的原因在腾讯、爱奇艺、芒果TV、哔哩哔哩等长视频平台和中央媒体与地方电视台的官方渠道的合力下,形成了跨屏传播、网台互动和台网互动的多元联动播出方式。以《故宫100》为例,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力打造的系列非遗纪录片,首播平台在央视纪录频道直播,随后上线至央视网等门户网站,被视频平台进行二次转播后,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获得了超百万的点击次数和播放量,在哔哩哔哩达到506万播放量和5.2万点赞量。
(三)精准复调的投放逻辑
基于Web3.0时代的SICAS的营销新模式下,文化类产品的非遗微纪录片能否建立起与用户高效的互动感知并让用户产生一定的兴趣,取决于内容的吸引力和基于算法属性视频平台的精准、重复的营推。从媒体平台层面而言,这些视频平台依据平台底层算法逻辑和后台用户数据,通过多维数据源对用户画像进行精细化、粒度化描绘,进而实现视频、用户、平台的智能匹配。
在关注其自身巨大流量的同时,“泛媒介化”的媒体如公共空间的大屏、广告牌等线下流量也成为平台整合与开发的对象。而长视频平台的入局催生了以非遗为主题的系列影像展,“云游非遗·影像展”通过八家网络平台同步启动,在线展映2300余部非遗传承纪录影像。各大视频平台的创作者对非遗微纪录片的影像内容以超文本方式,通过技术使用获取文本解码甚至再编码的自由权限,进行内容的再生产。所生产的视频文本以切片传播的形式,完成对流量的进一步整合。
三、非遗微纪录片的文化传承
(一)拯救人类学:影像载体的人文价值
从爱德华·柯蒂斯、阿尔伯特·卡恩和罗伯特·弗拉哈迪等学者在拯救人类学影像实践方面的贡献开始,以胶片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像获得了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成为可供后代研究的宝贵视觉资源。在此背景下,非遗微纪录片崭露头角,成为非遗影像的典型代表,保存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全民影像时代的兴起引发全社会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为这一遗产留下了时代印记。然而,影像记录并不等同于过程的结束,需进一步建立人类文化影像档案与资料馆。而对文化保护的紧迫需求早在上世纪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探险队》一书中就有所提及:“在民族学田野研究方法逐渐完善的同时,这些文化元素都悄然消失了。”[7]为应对因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非遗文化造成的更大挑战,我国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產的数字保存工作,各地非遗博物馆建立了保护机制,并在文化馆区内提供了与非遗项目相关的体验活动。
(二)民族志对话:文化空间的塑造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将“文化空间”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体现形式。对于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的诠释,存在三种不同的内涵:一是作为与特定的时空性民俗活动紧密相连的地点;二是作为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环境;三是作为遗产传承的具体空间。
在进行影像民族志的实践时,创作者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式,最大程度地避免对非遗文化空间的意义生成的过程产生干扰。同时,通过媒介化手段,创作者以对话和分享的方式,扩展了非遗文化的存在空间。微纪录片的拍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生成和空间塑造的过程。摄影机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工具,具有霍华德·贝克的媒介决定论所提到的具有引导和塑造意义的能力。互联网媒体平台的易操作性和影像的直观性为非遗影像志的作者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与被记录的对象一同观看影片,讨论文化细节,甚至修改记录的影像内容。广泛的受众参与更有助于促进这种良性对话,塑造了在分享人类学视角下共鸣、共情和共振的文化空间。
四、结语
微纪录片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生力量,通过近些年来的迅猛发展已经有力地弥补了传统纪录片在新媒体领域和微时代叙事能力的不足。同时其为迎合年青语态,以更为年轻化、时代化的方式将古老的非遗文化展现给青年群体,完成文化保护和传承活态文化的任务。
随着信息时代所带来的信息芜杂,景观社会下以影像为媒介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正如德波所言,充斥于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广告和媒体文化,制造出一种“伪需要和欲望”,因而人们普遍具有一种摒弃浮躁、厌恶虚假、探寻真实、渴望真诚的心理需求。以客观记录为创作前提的非遗文化影像志,呈现历史真实、文化真实的视听画面,迎合了当下的受众需求。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需要非遗微纪录片,在影像民族志创作方法基础上达成创造性表现方式和尊重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平衡。“而在这种平衡的寻找中,纪录片在艺术性与真实性之间找到了一种既创新又真实的表现方式。它利用现实,指涉现实,同时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现实”[8]。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3-10-09)[2023-08-01].[EB/OL]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3/0908/MAIN1694151810549M3LV0UWOAV.pdf.
[2]李鹏飞.文化空间再造:新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承[J].文化艺术研究,2018,11(04):1-6.
[3]张千山,沈鲁.人类学纪录片在保护赣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研究[J].电影评介,2010(20):14-15.
[4]朱靖江.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的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22,35(04):121-128.
[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5.
[6]田智辉.新媒体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57.
[7]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8]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7.
作者简介:徐竟涵,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4);王赫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024)。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