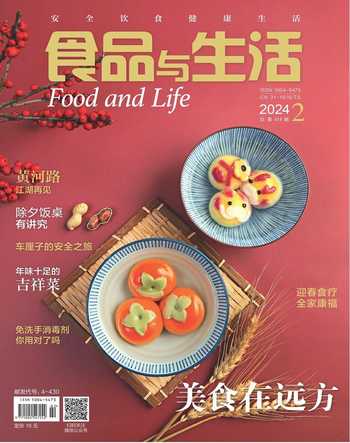黄河路江湖再见
何菲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市情感作家,专为本刊撰写熟男熟女的奇情美食。
随着王家卫首次执导的电视剧《繁花》的热播,没落、沉寂多年的黄河路突然火出圈了。剧中至真园的原型“苔圣园”酒家的包房一房难求,不少人带着富有 20 世纪 90 年代时代特色的装备细软在黄河路拍照“打卡”,我想这些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武康大楼的“打卡”人群中分流出来的。
上海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城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上海,值得玩味、细品。上海人说“我来买单吧”和“我买单”也绝对是两种意思。“土著”上海人也无法精确复刻出一个 90 年代的上海。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生活在离黄河路步行不过七八分钟的街区,那个街区由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构成,有着黄浦区弄堂特有的气味,那是镇江陈醋、阴沟、油煎带鱼、风鳗、葱姜、磨出包浆的竹躺椅的味道,间或能听见蒋调的《夜探》,那是上海的布鲁斯。弄堂口的过街楼使得整条弄堂有着独特的光影效果和人间琐碎。过街楼下总有早点摊,坐下来就能吃到热烫的粢饭和泡着剪碎的紫菜、虾皮和葱花的小馄饨。
那个街区到黄河路最近的路程需要穿过弄堂,弄堂七拐八绕,有着柳暗花明的幽微。主妇们顶着卷发筒、穿着家居服在天井的水斗边刷牙,阿婆们坐在门口的小矮凳上边晒太阳边择鸡毛菜,男人们坐在客堂间读晚报,小孩吃着棒冰、雪糕蹿进蹿出。复杂的弄堂网络通向哪儿,恐怕除了住户外谁也搞不清楚,就像没几个人能拿捏上海人心一样。但他们也见惯世面,正在吃泡饭、酱黄瓜、泥螺的老先生会边吃边指导小青年 :衬衫配圆领毛衣时,领子不需要翻出来的。
这些弄堂使上海完成了从生煎馒头到慕斯蛋糕的无缝接轨。小时候外婆给我准备的早餐常常是生煎馒头配牛奶咖啡,而牛奶咖啡是小钢盅锅里烧出来的。
上海的百年歷史,有一半封存在弄堂里。这些黄金地段的弄堂,与繁华一步之遥,开门是风景,关门是人生,指向曾经真正的上海生活。每个细节都不忌讳细看,哪怕有不少痼疾和狼狈。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没有流光溢彩,没有浮夸,没有王家卫镜头下的美拉德色,其实是灰扑扑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式新式小饭馆在弄堂和小马路上崭露头角,90 年代中期的黄河路上塞满了至少六七十家餐厅、酒家。黄河路的老板娘们巧舌如簧,个个精干,当然也是磨刀霍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这里生意清淡不少,于是拉客比较多,很多店家门口都有刘海高耸入云、喷了大量发胶的上海阿姨热情招呼进去吃饭,颇似《繁花》中的卢美琳。这时只能扬长而过,绝不能搭讪,一旦搭讪,往往会招架不住阿姨的热情,进去就挨宰了。即使不进去吃饭,上海阿姨心情好时会顺口赞美“妹妹皮肤老白哦”,她们观察力惊人,只一眼就能找出特征伺机赞美。大家心里开心,没准以后还会成为客人呢。
20 世纪 90 年代黄河路临街挂满了像香港那样的店招,霓虹闪耀、富丽堂皇、灯红酒绿,这里官商汇聚、鱼龙混杂,短短 700 多米,“金八仙”“苔圣园”“来天华”“粤味馆”“雅园”“悦来”“半岛”“阿毛炖品”“乾隆美食”等各显神通,弥漫着“新钱”和虾蟹的生猛味道。
对,是“新钱”不是“老钱”,“老钱”通常去“和平饭店”和“国际饭店”。1989 年我 12 岁时,小舅舅的结婚喜宴就设在国际饭店,那天需要我打扮得淑女点,妈妈便给我穿了一件玫瑰红羊毛衫,胸前有闪闪亮片堆砌、勾勒出花样,长发披散,戴了个蓝色头箍,还第一次涂了胭脂、口红。婚房里有当时的奢侈品——钢琴,这足够洋气高级、引人注目,即便舅舅、舅妈谁也不会弹。我还被安排在钢琴前拍了几张照片。那天最高兴的除了一对新人,应该就属我的外婆,那是她操办的一件大事,是她的高光时刻!
这种镶满闪闪亮片的衣服在当年十分时髦,不过在我大学开始有了服装自主选择权后,就再也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过。
从黄河路穿过国际饭店就到达了南京路。有了黄河路的灯红酒绿,南京路反而不那么繁华了。舅舅的一位弄堂发小曾是黄河路上的“打桩模子”(沪语指站在街头像桩子一样的掮客、炒卖外汇证券及贩卖外国香烟的人),赚了钱不拿回家给老婆,而是藏在舅舅凤阳路的办公室里。舅舅婚礼那天,我在钢琴前的照片很可能就是他拍摄的。而我一位亲戚当年的女友,后来选择了黄河路某饭店大厨,尽管其颜值、气质、学识皆不如亲戚,但月薪却是亲戚的 10 倍!
在《繁花》 剧中,有大量镜头呈现了商贾云集的黄河路对于当时上海商业的重要性。在移动通讯并不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很多经贸往来信息交换都是在饭局中进行。剧中冷艳神秘的“至真园”老板娘李李(辛芷蕾饰)引领了上海粤菜的流行。
王家卫很会拍辛芷蕾,使她美得极具攻气。下三白的攻击性,厚唇大嘴的欲望感,造型上的金钱感、年龄感和神秘感,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商战里的狠女人就立起来了,后劲很大。
90 年代,港台文化风靡沪上,并开始流行粤菜,帝王蟹、东星斑、大王蛇、澳龙、象拔蚌……这类山珍海味撑起了黄河路的档次和流量,使其夜夜良宵,纸醉金迷。
我当年第一次吃到咸蛋黄焗的虾蟹也在黄河路。在粤港地区,咸蛋黄是百搭,可以连接万物,咸蛋黄焗菜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既时尚又有点档次。那时还开始流行吃上汤做法的蔬菜,内有皮蛋、火腿、干贝等,让少年的我开了眼界。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皮蛋鱼片汤也在黄河路,据说在香港有个说法,吃了能治牙疼……黄河路各饭店、酒肆的创新能力很强,很是不拘一格,据说毛蟹炒年糕、啤酒烩草虾等菜都起源于黄河路。
2001 年是我本命年,据说临近本命年前要吃点猛兽,本命年才会更安然,于是,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的朋友在2000 年底请我去黄河路吃了椒盐大王蛇。那时黄河路周边住户已陆续动迁出去,黄河路已不复当时繁华,越来越少的人会把聚餐、饭局放在黄河路。我去进贤路的概率倒是远高于去黄河路。
大王蛇后来我也吃过多次,却都不在黄河路,直至如今彻底不见踪影。2003 年“非典”让黄河路遭受了重创。近二十几年来,杭帮菜、川湘菜、干锅菜、广式汤馆、澳门豆捞、小龙虾、台州菜、顺德菜、融合菜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多数活动在西区,日韩料理、台式火锅等曾经也占了聚餐的很大份额。黄河路是许久不去了。不知哪天黄河路上悬挂在建筑物以外的霓虹灯都拆了,曾经天天在电视台做广告的“来天华酒楼”变成了“天华宾馆”,黄河路上曾经金碧辉煌的饭店、酒肆,成了小吃店或小旅店,业态凌乱。
记忆中的黄河路消失了。
回忆起来,黄河路当年再繁华,也是有富而无贵,颇具江湖气。当年去黄河路消费的大多是个体户、江浙乡镇企业家和股票大户。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及周边最早富裕起来的那批人。
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改革开放前十几年,遍地是机会,财富如潮水般涌入,让无数人梦想成真。而此时游戏规则尚未及时建立,这成就了一批草莽英雄,第一批下海的个体户成了中国第一批万元户。
20 世纪 90 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大量外资、央企和民企纷纷进驻上海,这些力量的合力助攻,使得上海商业飞速崛起。对普通人而言,影响最大最深的就是金融改革。那时溢出资源很多,勇于把蛋糕做大的人大多实现了草根逆袭、阶层跃迁,这些经历了浪奔浪流的弄潮儿,如今多数人淡如菊,坐看云起。
90 年代初期,股票刚开始发行,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新事物,那些被强迫买股票的人,待股票上市,一夜之间暴富。1999 年5月19日,中国沪深股市迎来了“5·19 大牛市”,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上证综指从 1 100点以下,攀升到 1 700 点以上,涨幅超过 50%,那波行情造就了一批上海富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批人可能就是黄河路辉煌年代的客人,他们的黄金年代与黄河路的辉煌年代基本同频。
进入新千年,中国经济和商业环境发生着本质变化。乱世枭雄的草莽时代逐渐落幕。上海人的严谨、规矩和契约精神开始生逢其时,成为成熟商业社会最根本的基础。在这期间有过一些发财的风口,比如 2006 年、2007 年的股市也造就了一批富人。以及 2000 年 - 2018 年那些炒房者,尤其早期以租养贷的人。互联网和物流也曾是风口,一些踏准节奏的人,还是赚到了钱。他们也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这些人的消费场域,显然不是黄河路。
在我的記忆,黄河路从来也没有旖旎含蓄过,非常直截了当。就像在《繁花》剧中,大人物有大人物的一掷千金,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拜高踩低,却都不乏血性和情义。黄河路有江湖气,不会只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上躺在上海旧梦里自我陶醉、冷眼看人。他们眼中的上海是“大上海”概念,是开放宏阔的,是连接苏浙、粤港和海外的,是连接资本、产业和民间的。
记忆或许有偏差,我记忆中的黄河路,有霓虹招展,却无珠光宝气。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繁忙热力,也有用尽力气最终一场徒劳的繁花散尽、悲情谢幕。如今的黄河路回归到她该有的本真,不慌不忙、不焦不躁地存在着,倒有点天荒地老的况味。有时,失去比得到让人更踏实。
进入 21 世纪后,黄河路、乍浦路、云南路这类老式美食街逐渐落寞萧瑟了。曾经繁华的商圈、百货公司、酒吧街、休闲街等渐渐沉寂,很多业态如同一梦,速热也速朽。上海仿佛也迈入了中年,与我们的中年同频。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繁花。渐渐地,我也理解了黄河路,我想黄河路的道理,不在于看清了多少事,而在于看轻了多少事。
不管王家卫把黄河路拍成了波谲云诡的、臆想中的江湖,还是把黄河路作为一个江湖的意象,都不会改变黄河路给人的真实回忆。在上海,没有无缘无故地出现和消失,上海的水就是那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