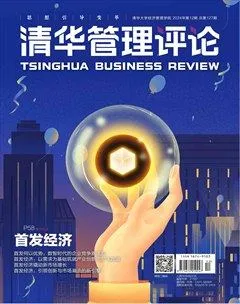领导调色板

一个秋日的午后,一名学生送给我一幅肖像油画,那是根据我曾经参加学生活动时用手机拍的一张照片所画,这让我很惊讶。没想到,我的学生竟然还有这样的水平?“老师,我不会画画,现在有一种技术叫数字油画,它可以针对上传的照片进行色彩分析,然后将不同色彩标记好数字,再给你对应的色彩盒,人们只需要按照画布上已经标记出的数字涂上相应标号的颜料即可。”那张肖像画的确是学生的“心血”,它与真正的艺术作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绝对可以用“说得过去”来形容,毕竟它让一个完全不会画画的人,将自己心仪的照片用油画的方式变得“高级”起来,至少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了。
我对画家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一只手托着调色板,一只手拿着画笔,画笔在调色板上不断调试,混合出心仪的色彩。一幅美好的作品就是在那个调色板的调度下、尝试下诞生了。说起来,颜料都是一样的,考验的无非是画家对色彩的感知并在此基础上配搭出合适的颜料。虽然调色板在一般人看来略显凌乱,但经此产生的色彩融合却又很神奇地表现出美妙的艺术作品。现在,数字分析技术替代了画家手里的调色板,大自然的色彩可以被精准地用数字标识出来。
这样的艺术“捷径”让我联想到在商学院一门名为“领导艺术”的课程。虽然在课堂讲了很多领导理论、原则、方法,但学生们对于在领导实践中做出艺术来依旧是一头雾水。看看数字油画的逻辑,在现在技术的支持下,它将最难以拿捏的、最关键的构图和色彩用数字分析的方法明确下来,这样就能够呈现一幅和谐的图画,给人一种“理性的”艺术的感觉。同样是提升艺术水平,我们能否从数字油画中找到一些线索应用到领导实践中?
有效领导的底层逻辑
一般认为,领导者是有效领导的关键,于是有了聚焦“提升领导力”的各种项目。事实上,在围绕领导的绝大多数研究中,关键词也都是领导者。后来出现的领导胜任力模型,更是成为组织选拔和培养领导者的依据。纵观那些形形色色的胜任力模型,大都是在一个给定的组织背景下,界定出领导者应该具备的能力。其潜在逻辑就是,当一个领导者具备了更多的能力时,就更有可能带来有效领导。胜任力就好像一个士兵外挂的装备,拥有更多装备就意味着拥有更强的战斗力。但现实是,一个拥有了更多装备的士兵并不意味着能够适应变化莫测的战场。
研究者意识到被领导者的重要性,随着新生代员工日益成为职场主体,被领导者的追随力状态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关追随力的研究认为,现实中出现的领导无效问题,并不仅仅是领导者胜任力缺失,被领导者不愿意追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不是磁铁出了问题,而是对方已经不是铁了。提升追随力要求将领导的重心转向被领导者,甚至认为被领导者决定了领导效能,在这样的情形下,领导者需要更大尺度地迁就被领导者。然而,领导者的“委曲求全”也没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很明显,对被领导者的激励并不是有效领导的全部。
既然上述两个因素都无法带来有效领导,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决定有效领导的关键呢?为了弄清楚有效领导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回到领导实践中。领导现象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丰富多彩。在形形色色的领导实践中,一些品德高尚、能力突出的领导者最后似乎也会一败涂地,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一无是处的领导者有时也能获得匪夷所思的成就。这种貌似反常的例子还不在少数。为什么会这样呢?跳出对于领导的刻板印象,回到领导的最基本定义:领导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为实现目标而发生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领导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两个主体共同构成的系统,只有他们之间良好的互动,才能赋予整个系统动力,并最终实现目标。由此不难得出判定:作为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最好的领导者或最好的被领导者都不能支撑起有效的领导,唯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匹配才是有效领导的根本保障。
单纯地强调系统的某一部分并不必然带来有效的领导,忽略了两者的匹配才是领导力问题的根本症结。这就好像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构成了硬币的两面,只有他们是匹配的,这个硬币才是合格的。中国历史上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君臣际遇”就是对匹配的最好证明,例如齐桓公与管仲、秦孝公与商鞅、刘备与诸葛亮等,他们在一起紧密合作并肩作战,表现出最佳的领导效能,带领组织取得了非凡的业绩。
匹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次领导力的研究中,一家3D打印公司的领导者很真诚地和我们交流他的困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这些孩子们到底应该怎样激励呢?”这位领导者是典型的技术专家出身,对于产品设计有着权威的认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领导者,同时也是非常情绪化的,尽管他对于员工是慷慨的,看待员工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平时也非常关心员工,但总感觉员工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回应。然而,当调研在员工端展开时,我们得到了不同的声音,“领导给我们奖励,给我们股权,我们当然也很感谢,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将工作与生活分开,我们更希望能够专业化地对待项目,我们希望他能在项目成功时给我们一个微笑或肯定而不是‘继续努力啊,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等等”。今天,类似这位领导者的情形并不少见。尽管领导者们还在不断提升自己的领导力,但总有一种不对路子的感觉。这就好像一个画家将错误的颜料涂进了错误的地方,错配的画作怎么可能是美的呢?

让我们回到数字油画的逻辑中:手握已经编号的颜料,看看标注出的、需要被填充的色彩号,然后小心谨慎地描摹进去即可完成匹配。那么,对于领导者来说,为了能够匹配,他必须要类似地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他需要深入了解领导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他需要知道手里都有什么颜料以及都是什么色号;第二,他需要了解被领导者对于领导方式的需要,也就是说,在画板的某个区域,需要什么色号的颜料;第三,领导者必须要根据情境要求调整出合适的色号。
琳琅满目的颜色:领导方式
这些年,围绕领导者进行的大量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领导者的认知,尤其是,研究者乐此不疲地总结出各种各样的领导方式。这一方面解释了领导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知道每个领导者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尽管每种领导方式都试图更全面地描述领导现象,但显然,它只是整体领导现象的一个局部。就好像万紫千红的世界不只是由一种色号所呈现的。但不管怎样,已有的较为成熟的领导方式还是相当于为我们准备好了相应色号的颜料。

大自然有多少种色彩?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准确的答案。实践中有多少种领导方式?也同样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理论界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研究中被广泛接受的当属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当然,还有更为悠久的领导方式,例如魅力型领导,这种领导方式与围绕领导者的种种“异象”密切相关,常常用来解释君权天授。至于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谦卑型领导、辱虐型领导、包容型领导、共情型领导、战略型领导等大致都是在领导学研究繁荣阶段,经由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侧重点和优先顺序而提出。另外,根据不同的领导情境,研究者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领导类型,例如,家长式领导的提出,基本上是根据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实践,所调研的样本也大致是东南亚国家企业内的领导现象;创业型领导的提出则是基于创业实践。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结论和模型让人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色彩。幸运的是,领导学研究还在不断地创造新名词,领导方式的清单还远没有罗列完毕。
尽管通过这样一些分类,领导者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分析和理解自己的领导方式,但事实上,每个领导者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类型,而是各种类型的综合。换句话说,每个领导者既是变革型领导,也是交易型领导,也是伦理型领导等等,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就好像仅仅是红色,就有很多种。不同领导者,调色板上的颜料的种类、成色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领导方式就相当于领导者手中拿着的一托盘的各种颜料。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领导方式是存在明显区别的,例如变革型领导与谦卑型领导;但有些领导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例如包容型领导与共情型领导等。本文的目的不是区别这些领导方式,对于实践者来说,只需要知道每个领导者是多少色号就可以。就目前已经研究出的色号而言,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领导者在不同场景下、面对不同人员随时切换。说起来,一个油画家一般也只是使用十多种基本色,在这些基本色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调适出新色彩。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就像有些画家有自己的“习惯之色”,例如伦勃朗喜欢棕色,领导者对领导方式也是有偏好的。久而久之,领导者对某种领导方式的偏好就形成了所谓的领导风格。尽管这是事实,但领导艺术毕竟与纯粹的绘画艺术不同,领导者也不可能像艺术家那样任性,个体偏好终究要服从于目标最终达成的具体要求。
需要填充的色彩:被领导者的期望
一般而言,在领导系统中,被领导者适应领导者。但是,更为高明的领导者,尤其是当领导者的影响力还不具备的时候,他需要通过适应被领导者来积累自己的影响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领导者会像春秋五霸的楚庄王那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掩饰自己的状态,了解被领导者的需要,然后再去表现自己的领导力。
手握颜料,看着空白的画纸,如果随意地着色,那结果就是涂鸦。数字油画之所以会在构图中精准地标出色号,就是将客观需要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领导者当然也希望有这样的辅助,更好地了解被领导者需要被填充的色彩。但领导实践还没有达到这样精准的状态。不过,了解对方需要是实现匹配的重要前提。
毫无疑问,在需要认知方面,最为基础的理论就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这里我们不妨尝试将五个层次的需要对应相应的领导方式的需要。当人们处在生理层面的需要时,交易型领导最直接务实也最能立竿见影地解决被领导者面对的具体问题;当人们处在安全层面的需要时,他们希望身心都能得到来自领导者的照顾,这时的共情型领导能够凸显出风雨同舟的感受;当人们处在归属层面的需要时,家长式领导无疑更有利于营造出“家”的氛围;当人们处在尊重层面的需要时,服务型领导、包容型领导、谦卑型领导等能更好地调节和增进双方关系;而当人们处在自我实现层面的需要时,变革型领导能够引领大家向梦想迈进。这么看来,处于不断变化需求层次的每个个体以及处在不同需求层面的个体们,对于领导方式的需要也是有差别的。
了解被领导者状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和调整的过程。如果某种领导方式没有得到被领导者的认可,这时,领导者就需要带着一种“过则勿惮改”的精神重新认识对方。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经理培训班上,一位在白俄罗斯负责工程项目的经理说,尽管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时刻提醒自己要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但是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感到很茫然,由于各种担心,工作上畏首畏尾放不开,领导效能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于这种情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认真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吧,不要担心可能的错误,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充分了解的。即使最有经验的画家,他们对于色彩的理解也是通过反复的揣摩和大量的习作来不断提升的。
“性相近,习相远”,今天,新生代员工对于领导方式的期待显然和之前的人们有所差异。对于领导者来说,一定要摆脱对于被领导者的惯性认知,尤其是有些领导者受其前任的影响,常常以自身的标准要求被领导者,忽略了被领导者的独特性,在心理投射下,还经常将“我认为的被领导者的需要”误以为是“被领导者的需要”。另外,被领导者的期望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对于领导者来说,他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目标,因此,领导者可以将目标当成是一个滤镜,用它来评判被领导者的各种需要。简而言之,有利于目标实现的需要才是应该予以考虑的需要。
调出合适的色彩
在弄清自己的状况以及被领导者的需求后,领导者就要准备调配出最适合当下情境的色彩来,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画家手里总是拿着一个调色板,不断地尝试哪种色彩更适合。这种动态的调整其实已经在很多经典理论中有所体现。例如,著名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该模型从两个维度——能力和态度——对被领导者进行界定,领导者面对被领导者的不同状态时,必须主动地作出调整,从而在与被领导者的互动中表现出指令型、教练型、支持型和授权型等不同的领导方式。
约翰·科特的领导力模型是另一个经典,它从获得权力、运用权力和移交权力的角度展现了领导者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表现。虽然模型没有明确说明一个领导者在其领导生涯过程中领导方式的转变,但是不难发现,在获得权力阶段,领导者会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谦卑型”和“服务型”领导方式,在运用权力阶段,“交易型”“伦理型”更为常见一些,而在移交权力阶段,领导者采用“包容型”更容易被继任者接纳。
考虑到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匹配关系上,更具有影响力或主动性的还是领导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站在领导者的角度来看看如何更好地实现有效匹配。还是以前面所描述的那家3D打印公司为例。从领导学的角度分析,那位企业领导者是比较典型的家长式领导,但员工们所期望的领导者的领导方式是伦理型领导。家长式领导通常与权威、仁慈和德行等特质相关联,研发人员则需要摒弃传统的家长式领导风格,转向支持性、平等的开放式领导行为,很显然,领导者所表现出的领导方式与员工所期望的领导方式之间是不匹配的。在之后的调研反馈中,我们将员工们对于领导方式的需要转述给公司领导者后,同时也指明了从家长式领导向伦理型领导转变的关键行为。虽然这会在行为上与之前有所不同(当然,也不至于截然不同,就好像很多色彩都有相似和过渡一样),只需要在行为侧重上做一些调整就好。在后续的跟踪中,双方的关系果然缓和了不少,相处得也更为自然,组织绩效也得到了改善。对于领导效能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人际之间的误解。也就是说,领导者所努力表现的,并不是被领导者所需要的。对于这种情况,只要能够澄清误解,一幅作品还是有机会被挽救的。

是不是存在不可调和的关系?当然会有。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调整的成本。对于领导者来说,为了实现目标进行必要的调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领导者在调整的过程中,也要看付出的成本有多大。例如,领导者为了更好地配合被领导者,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超过一定的极限,匹配就无法实现。但一般来说,关系都是可以藉由深入认识而重新调整的。就像一句广告语说的,“男人有很多面”,至于表现出哪一面,也就是说,领导者要采取怎样的行为与下属进行互动完全是可以调整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反求诸己”就是要求人们从自己的角度,多自我批评和改正。不得不说,在认识了匹配的重要性后,领导者要常常反省调色是否合适。虽然人们也会说要坚持自己的独特性,不要失去了自我等等,然而,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从来都是目标导向的,只要能够有利于实现目标,他们一定会积极改变和调整,从而更好地强化匹配。
在领导实践中,的确存在极少数领导者,他们拥有超乎寻常的领导魅力,他们的每一次领导活动就像完成了一件艺术品。然而,更多的领导者需要通过后天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如何让领导成为一门艺术,数字油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只要领导者能够拿起手中的调色板,“机械”般地调适出被领导者所需要的色号,或许就能够提升领导的艺术性,即使不能成就真正伟大的艺术品,但至少“像”艺术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