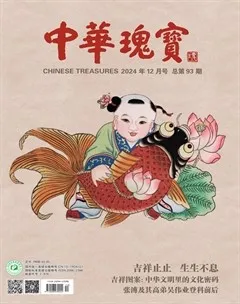张溥及其高弟吴伟业登科前后




张溥有『江南士林领袖』『东南坛坫主盟』之誉,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在吴伟业的成才之路上,张溥的热情赏识与悉心教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溥(1602—1641年),字天如,号西铭,明南直隶苏州太仓(今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人,复社主盟、著名学者、文学家,有“江南士林领袖”“东南坛坫主盟”之誉,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其高弟吴伟业(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诗歌成就尤为突出,开创娄东诗派,其诗有“梅村体”之称,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在明清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吴伟业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明代生活三十五年。其青少年时期,尤其是登科前后,与乃师张溥交游密切,受到张溥的诸多影响。
张溥早年行迹
张溥年长吴伟业七岁,收吴伟业为弟子约在天启五年(1625年)。在此之前,二人虽然同处太仓西城,人生轨迹却各不相同。张溥因为是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在大家庭内受官至工部尚书的大伯张辅之家奴多次凌辱。少年张溥忍无可忍,愤而在墙壁上血书“不报仇奴,非人子也”。欺辱他的家奴知道后,轻蔑大笑:“塌蒲屦儿,何能为!”(陆世仪《复社纪略》)意思是,一个贱人生的庶子能有什么作为呢!受此刺激,张溥夜以继日发奋苦读,凡所读书皆认真抄写一遍,再高声朗读一遍,然后烧掉,再抄、再读,如此重复七遍。其书斋名为“七录斋”,正是其勤学苦学的见证。张溥后来以学问渊博和富有气节著称,与这一段遭受欺辱、发奋苦读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张溥十六岁时,父亲病逝。少年丧父,本是人生的至痛,又因身处复杂的大家庭,其间的家庭纠葛更是令人伤感寒心。于是,张溥奉母金氏搬出大家庭,居住在太仓城西郊一处陋室,潜心向学。这一时期,张溥结识了住在太仓南郊的张采,成为生死之交。后来,二人影响日巨,并称“娄东二张”。
“二张”均少年丧父,以勤学著称,志在大儒。张溥邀请张采到“七录斋”共读五年。在这期间,“二张”一方面准备时文,以应对科举;另一方面着意研读经史,广觅同道。天启三年(1623年)冬,“二张”前往金沙(今江苏省南通市中部)拜访著名时文选家周钟。三人相谈甚欢,最终达成以经史厚殖学问的共识。次年冬,“二张”又去常熟拜访杨彝、顾梦麟。因学术旨趣相近,他们联合杨彝、顾梦麟、周钟、杨廷枢、朱隗、王启荣、周铨、吴昌时、钱栴创立应社,每人分治一经,众人合治五经。张溥此时名声渐起,影响日大。
吴伟业投师张溥
吴伟业祖上原居昆山,为昆山名族。然而至其祖父吴议时,家道中落,迁居太仓,入赘于太仓琅琊王氏。其父吴琨,字禹玉,号约斋,能文章,但多次科考不中,便以教学课徒为生。吴伟业少富才华,随父在外坐馆读书,不断提升学养。
约天启五年(1625年),吴伟业投师张溥。当时,张溥创立应社,与江西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等组织的豫章大社和山东宋玫兄弟组织的莱阳社鼎足而立,颇具影响。年轻学子也乐以文章投师其下,请其指导。其时,嘉定有一富家子弟,窃取吴伟业多篇文章冒充己作献于张溥。张溥读后颇为欣赏,后来得知为吴伟业所作,于是主动邀请其在门下学习(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恰逢此时,与吴琨同在王家坐馆的李明睿因宴会琐事与东家发生口角,于是负气离开。吴琨前来相送,并慷慨解囊,资助路费。李明睿颇为感激,临别时对吴琨说:“令郎是奇才,贵乡后劲张溥正以古学振兴东南,前景无量,何不让令郎拜入其门下以得早售?”吴琨对张溥也颇有好感,于是让吴伟业拜入其门下(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张溥对吴伟业颇为激赏,认为其是“大贤之器,非徒显文之流”(张溥《吴骏公稿序》),对其文章予以高度评价:“文章正印,其在子矣!”(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可以说,在吴伟业的成才之路上,其父作为启蒙老师、李明睿的慧眼识人、张溥的热情赏识与悉心教导均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溥鄙薄一心只知时文的浅俗时风,主张加强经史的学习,以通经致用,通过改变学风来净化社会风气,以期将来务为有用。吴伟业在投师张溥之前也是厌弃俗儒之所为。师徒二人,治学宗旨一致,教学相长,俱有所获。张溥以身示范,吴伟业心摹手追。张溥的勤学与治学精神,对吴伟业尤其富有激励作用。
师徒双双高中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张溥和张采前往南京参加乡试。张采中试,张溥落榜。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八月二十四日,遗诏以信王朱由检即皇位,以第二年为崇祯元年。崇祯以登极恩典,令每学选拔一人入京学习。张溥被选为恩贡,得以进入国子监学习。
崇祯元年(1628年),吴伟业也考中生员。四月,张溥入京师国子监学习,这时张采已考中进士。张溥廷对时得高等,更为崇祯新政所激励,颇以振兴学术为己任,大声倡议:“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吴伟业《复社纪事》)于是“二张”召集参试士人举行成均大会,并结燕台社,一时名彻都下。
张溥回乡送别张采赴任临川后,又集合吴越间优秀的年轻人,在吴江县令熊开元、吴江大户吴䎖的支持下又建立复社,明确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相标榜,在其学术精神上实也寓“复东林”(唐文治《张天如先生遗像记》)之意。其高弟吴伟业成为复社骨干成员,以至后来有好事者一度将张溥比拟为孔夫子,将吴伟业比为“十哲”之一。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诏定逆案,消除魏党残余,朝政一新,正气与革新的气息弥漫于朝野之中。胸怀大志的年轻士子更加热衷于研读经典和讨论时文,准备大显身手。在此热烈氛围下,张溥因势利导,通过其卓越的组织统筹,将十五个地区的十七家社团统合到复社,此乃文坛旷古未有之事。这既为众多年轻士子切磋交流提供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平台,也通过文章的选集、评点、标榜而扩大了其影响和声誉,为其接下来考中科举奠定了学养和人气的双重基础。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乡试,张溥和吴伟业师徒二人双双高中。乡试后,张溥又组织前来参加乡试的复社举子近两千人召开了金陵大会,汇聚其文为《国门广业》。张溥和吴伟业俨然成为这次大会的焦点人物,也成为众人眼中明年会试高中的热门人选。
次年二月,张溥和吴伟业至京师参加会试。在会试前半个月,张溥与吴伟业、陈子龙、杨廷枢等九人又成立日社,切磋制艺,每人作文十至二十余篇,并拟刻《九子社义》,以记一时鸣和之乐(张溥《杨伯祥稿序》)。
此年会试主考由首辅周延儒、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担任。按照惯例,以往由次辅担任主考。但首辅周延儒这次亲自下场,既为国家选拔人才,又为自己招揽门生,扩大其势力与影响。这当然引起了次辅温体仁的不满和攻讦(陆世仪《复社纪略》)。张溥、吴伟业及复社后来与温体仁的矛盾,也与此有关。
在会试中,张溥和吴伟业所选本经都为《易经》。张溥出于《易》一房杨世芳门下,吴伟业出于《易》三房李明睿门下。吴伟业高中会元,张溥为会魁,名列第八名。据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载,吴伟业能高中会元,除了自身高才外,自然也有人情因素。原来,其座师首辅周延儒为诸生时,路过娄东,与吴伟业之父吴琨相善,房师李明睿则与吴伟业之父吴琨有共同坐馆、诗酒唱和、慷慨相助的雅谊。周延儒意在收罗名宿,于是授意各位房师在交卷前,悄悄打开中式封号以确认姓名。李明睿因此确定吴伟业为本房头卷,周延儒也很高兴其为故人之子,拟定其为会元。温体仁授意党羽薛国观将此事泄露于朝廷,御史袁鲸准备上疏参论。情急之下,周延儒将会元卷进呈御览。崇祯皇帝阅后,在卷首书写“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一时舆论才得以平息。
其后殿试,吴伟业高中榜眼,张溥为三甲第一名,一时传为佳话,天下争传二人文章,推敲模仿(张采《治娄文事序》)。殿试后,吴伟业授翰林院编修,张溥选翰林院庶吉士。此时又发生了一个插曲。按照惯例,新进士的刻稿一般请房师作序,吴伟业的会元刻稿竟以“天如先生鉴定”的名义出版,这实际也是张溥影响力的一个侧证。李明睿知道后大为光火。于是同馆兼张溥妻弟王启荣连襟的徐汧带领吴伟业前来请罪,并将此事推诿给书肆。尽管此事以此了结,但李明睿心中对张溥大为不满。另外,琼林宴排座次一事,也可看出张溥的影响。琼林宴上,新进士的座位一般按考试名次排序,吴伟业虽为会元、榜眼,但不敢坐在老师张溥之上,于是皇帝下旨“张溥坐会元之上”,这可谓科举史上的“盛事亦奇事”(陆世仪《复社纪略》附录)。此时,周延儒作为座师,对门生张溥大为欣赏,恩礼倍至,既推荐张溥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又令其撰写《进士题名记》。
中进士后
吴伟业中进士前一心学文,不曾作诗。此期中进士后,因为交游酬赠,于是先向张溥学习作诗,并受其激发,开始讲求诗歌创作。清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四《杂缀类》记载:“王中翰昊述吴梅村语:“余初第时不知诗,而多求赠者,因转乞吾师西铭。西铭一日漫题云:‘半夜挑灯梦伏羲。’异而问之,西铭曰:‘尔不知诗,何用索解。’因退而讲声韵之学。”
九月,吴伟业得皇帝赐假回乡完婚,张溥作诗《送吴骏公归娶》,为其赠行:“孝弟相成静亦娱,遭逢偶尔未悬殊。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富贵无忘家室始,圣贤可学友朋须。行时襆被犹衣锦,偏避金银似我愚。”字里行间,既有调侃,也有羡慕,读来颇有趣味。
此时的张溥春风得意,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难免有孤傲和不尽老练之处。于是,本就心怀不满的次辅温体仁借机敲打:“庶吉士成材就留下,不成材就离开。”张溥对此毫不畏惧,反而针锋相对,搜集温体仁结党营私诸事,写成奏疏,授意吴伟业参劾。吴伟业考虑到立朝未久,不敢直接参劾温体仁,于是将奏疏稍加调整,转而参劾温体仁的得力干将蔡奕琛。温体仁勃然大怒,准备严厉处罚,幸得首辅周延儒从中调解。从此,温体仁与蔡奕琛对张溥更是侧目而视,房师李明睿又因会试刻稿事而不时督察责备于他。在这种充满敌意与挑剔的政治氛围下,张溥颇不自安,次年便以请假葬亲之名回太仓,从此不再复出。
陆岩军,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