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壁与野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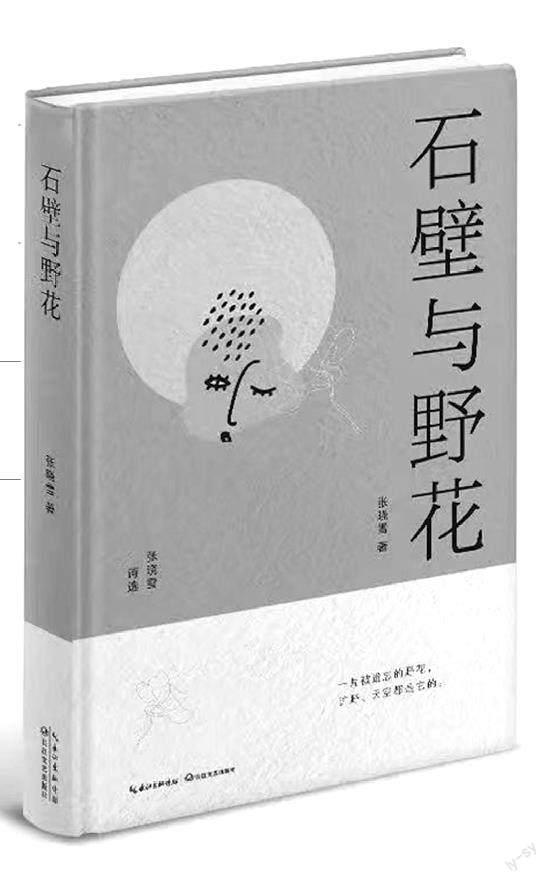
它与生俱来的底色
当然不是黑暗诞下的。
是旷野里的锈迹,
一点儿沉默,变黑的谜团。
一点儿神性,埋藏于群鸟丝鹭
和芦苇的摇曳中。
它把防备展开又抱成一团。
那一刻,务必高冷贵重
披着乌亮的反光。
务必看清凸凹不平、
吉凶成败的河滩,
敢于立在银色的波浪里
做白日梦。
它当然不是白天鹅的一面镜子,
默默对视却一片模糊,
曾绊倒过几只躲避的天鹅。
因渴望蜕变而使高瘦的身体
颜色加重。在它看來
所有的光芒都是微闭的样子。
群居中,认命般地领受了自己
——一个旁观者,
一枚流浪的黑影。
它素来不做冒险之事。
静谧、微息。
爬青藤,院落冷寂,
赤脚于奇崛、裂松。
爬奇石,白云归去,
八百里楚河汉界被摸到时,
高处皆矮,输赢全无。
它素来不做冒险之事,
比如垒石、伐木、筑长城。
兀自进出泥土,与野葡萄、
石榴、藤梨相安无事,
不似头顶上那颗流星
匆匆来去中如一根断线
或一段言语,消失了。
当它拱出沙粒,海啸后
沙海激扬不过是杳然的顿挫,
那逐渐散去的,像露水
只漫过了它小小的惊讶。
当它爬出砖头瓦砾,
在大地震中侧身倾斜的那一刻,
目睹的虚弱和卑怯,
竟然是山河和石头,而非自己。
钟响,百里寂静。
旧尘震落,又覆上了新尘。
钟响时,银杏幽喟,黄叶相继离去,
后人开始描述前人的季节,
无言者向背啜泣,保持着震颤的写意
与吟诵。
钟声里有草木,有衣袂。
耕种之手收好了锄具犁耙,
抖袖持肩,待余音散去后,
不耽搁收割、翻土、捆燕麦。
钟声轻,钟声栖上树枝,
遁入白云或巨石,如歌者认归了缄默。
钟声昭示沉思,西风是必经之路,
一阵清幽声像一个人自酿的痛苦,
只用来拒绝。
而安详和普度离人心最近,
被背叛一次,复活一次,
与钟声保持着一缕一缕的沉入。
与钟声,在某个黎明的时刻,
为渺小者表达过贫弱心和不眠夜。
野花倾斜,过微风。
飞鸟配一朵闲云,
抵挡着枯草上的卑微与病。
一群镇定自若的绵羊,
被山坡那头的表情不断地
试探着。
头羊沉默,食草,锋刃一样
陷入。想必它有对彼岸的追问,
但又保持着克制。
宁可徘徊,以迟疑的步伐
抵抗内心的指向,也绝不回头
与身后任何一只有同样想法的家伙
撞在一起。
一路上,
星星离我最近,
德令哈,离我最远。
此处,
太阳专注于
炫耀群峰,
描述它们的脊背,
俨然鲸鱼一般的
静止。
一万里的蓝色,
小得不起眼。
当宁静被云
轮番撕破,
野花挺向天际,
像例外的生长
带着背叛
……
四千五百年,
活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对流逝一无所知,
还是执意将流年击败?
雷声一响,
心脏开出了怎样的花?
当月光和大风袭击山涧溪流,
它用力摇晃,哗哗哗的笨重,
是在跌宕古老的往事,
又像以无尽的耐心刷新一种
巅峰艺术。
它老了,朽木枯枝布满荒凉。
春天不断地传播它的来世之春,
而嵩山则承担了它全部的孤独。
墙下有人,看着一棵小树疯长,
披散成偌大的场面。
粉色如患时,路人张望
只是匆匆一瞥。只因花朵沉实、
芳香柔软,与温饱和抱负无关。
纷繁无序时,风放慢了速度,
因迷恋一小簇一小簇的鲜妍,
而蜷曲了自己。
蝴蝶与蜜蜂乱如幻觉。
而花朵喧动,不解世情,
以浓烈的芳菲篡改你,奔赴你,
葬你……
田地迁徙,
安命为广场。
蟋蟀委身于此。
草芥矮小,几分隐忍
窝着更强烈的乡愁。
雕塑、路灯与喷泉是广场的主人,
以无尽的耐心学习站立。
高处,一只鸽子数次回旋,
不知身在何处?还是
欲重新确定一个小位置?
人群攘攘,灵魂从练习行走的
躯体分出。高耸的眼眸
是看淡还是看重了人生?
此时,看客倚着树干,无语。
奔跑的少年,抿着嘴。
大风一吹,那些花白开始舞蹈和喧哗。
我喜欢浪费甜蜜的祝词,
从一朵苹果花一直到它累累的果实。
我赞美它——
与薄凉、逆光、雾霭构成的差别,
没有裂痕的结实,一步步甜下去。
我喜欢挂在绳上的衣物,
离开人体,沥干多余的水分
像获得了一切的准许。
我赞美它的自由,在阳光下
细细的碎花成倍地荡漾着香气
和自身的空旷。
我赞美半开的门,此刻朝阳,
所剩的宽度不多。一段摩擦关在里面,
穿制服的人瞥见室内,
但不足以使一床、一桌、一错句
被轻易推开。
我喜欢小宅境,闭上眼睛,
赞美转身抵达的迎接和平凡的事:
每一个都接受另一个的分歧,
然后和解。每一个都身无长物,
只剩下了“我们”。
风跟着,铃声像一条很响的溪流
淌过来,窗户是必经之路。
我喜欢它不能忍住的摇动。
理解这归来般的声音,
有点儿自问自答,又像有针对性。
它替代时钟和鸟鸣,重新布置了
我洗漱、早餐、刷碗的生动感。
类似笑声划破冥想,令小世界的偏僻
大面积地天真起来。
我喜欢房间里的小事物,
恬然简单的无用之物容易使人快乐,
容易动摇那些类似铁石心肠之类的病症。
你有一处僻静等我浅尝,
你有几片萌芽,携春色晃动,
投下的新绿有多重意思。
我喜欢你道出的一切,
能缓解沉默中的不安,
令细小的气馁、困顿
顺从妙不可言的微苦。
归寂于舌尖上的念白,句句都轻。
一杯雀舌,
我喜欢你风平浪静,视无常若等闲。
就像你懂得了无常后,
并不告诉谁,
并成为那无常的一部分。
它微微张开的嘴唇
招来风的拥抱,
被吻过的地方,
泪水取代了沉默。
仍是无争之静词,
白玉一样,
隐去了情节和内容。
它铺张新鲜的日子,
无际的虚怀随风丰满,
像鸽子栖上树枝,
簌簌的翅膀扇动,
处理掉了生活的乌云
和胸中的黯然。
有时,桂花是女人的心思,
分泌脂粉气,
为了擦去生活灰心的部分。
是最早的爱情。含糊的表达
实为对欢喜保持一丁点儿克制。
是你长期被忽视,停下时,
它冲破喑哑,迎了上来。
素花意义稀薄,淡妆适合靠近。
暗香如真情,经受了数不清的浪费,
经受了数不清的手指伸出,又收回。
似俗人难以承受的轻,像仇人
不忍获取的报偿。多么幽僻啊,
多少碍难被这绵薄之力解构,
而这之前,你的心是乱的。
对于抽身俗世的人,
嵩山的海拔即为其要义,
耸立于无惊涛的内心。
是成败之后的结论,
一路阒寂召唤野花、风光,
被溪流处理过的石头。
召唤低处的苦思,
将多余的盲目减去。
它认同站着的人
和他心中没有说出的话,
像好文章的开头,
關乎内涵。
它参透世情的样子,
愈显沧桑,愈不被理解。
仅与千年古柏树的沉郁
产生共鸣。仅适合对少数人,
说出。
它叙述缓慢流逝的事物,
但从不玩味自己的命运。
一如方丈的余生,
隐忍了太多的疑虑后,
不阐释幽冥与深刻了,
只感知命运的无语。
奔跑,用尽全力,
九十八路车还是错过了。
而视线所及皆是车流,
滔滔绵延而平静。
路边,一阵风吹来,
衣角翻动着焦灼。
站牌之上,
一片闲云低回,静止,
说着安慰的话:
尚有一朵,刚好是留给你的。
几分坚定,秋风将如意湖
吹成了镜子。
澄明之物不接纳附和的掌声。
几分旷凉,爱意在心头决堤,
猝不及防的言辞,须另起一行。
一树楚楚展开的苍然,
独具消散、加固、孱弱
和坚韧的能力。
在前进路小学的门前
抖掉积尘,落下了种子。
1
他的心,无限放大了
一枚果核上的万古界、无忧境。
漫漫毫厘中,田埂蛰伏,
渠畔和路旁留出了许多空隙,
待一节柳枝插地发芽,
待小南风挂在树上,轻轻摇晃。
2
针尖似的蜜蜂,旁若无人亦无己。
来自“上天的磨炼”表达清楚了,
一个翅膀无法自抑,另一个
与他应和,一样发出了
嗡嗡的轻颤。
3
刻刀游弋,不急于寻找河岸、
固定人心。船桨、炉子静安于船中,
已经受戒。痴迷者沉淀纤毫,
以念珠、手卷的逼真,摁住了
人间的咳动。
4
他爱核舟上朝南的窗户、
卷帘的女子,
胜过八百里浩渺、一万米的
追念与秋风。
爱核雕里的菜畦、麦地和打谷场,
粗布衣衫的胸襟处,
敞着粮食和蔬菜的气息。
5
他受难般地倔强。专注于
刻出一枚果核的辽阔——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刻到苍老动情,人世形同虚设。
它纷乱,像粉尘
虚化了喧哗与悲情。
它独自,日夜流淌的
一行白、一行轻,
如不食人间烟火的遁世者。
无限的耐心,
如同还在苦等那个安定天下、
烟尘一缕的行者。
一意孤行地解释着
一个身世的源头。
1
它过人的能量
以“虚怀”和“恳切”示人。
了无生趣时,
为我播放音乐,沏一杯茶。
铺开白纸,用颜体楷书抄写了
一首古诗。
2
流水线上,它分送玫瑰、蜡烛
和蛋糕,如同抚慰一个个陌生的
亲人:“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我的主人!”
对方虚弱了一下。仿佛撞到
一个结痂的小伤口,
她双手冥合,真切地获得了
一个愿望。
3
疏于自述,却是对弈的高手。
耕种瘠田,挫败了劳动模范。
它礼赞春日,对于脱离轨道的歧路,
则侧身回转,挥臂变冷:
我怀疑你,反对你,我
离开你。
4
大雨来临,一个踽踽独行的人
克制着寥落感,等候机器人
擎伞接送。
明明与它走在一起,
你却倍感孤独。
只因它不牵你的手,只因
它交不出一颗欢喜心。
蛙鸣阵阵,草色入帘。
诸事安顿好了,林、鸟、月、树,
每一处都是执子之手。
每一处都能交出翠绿银白,
瓦解你内心的狼藉。
菖蒲和芦苇平分了涓流香溪,
小有起伏的虫鸣,一首为情所困的
萎靡音,与秋风一起灌满了衣袖。
一棵银杏是我们共同路过的,
以慈爱之心回应我的惜别之意,
清雅战胜了苦涩。
长圻码头上,太湖清风纷扬,
一半止于橘红和篱笆,
一半碰撞西巷村的白果树。
脆裂的响声推动暮色和香气,
并将石板路上的我,退成
瑟瑟的柔弱。
它从不陈述衰老和错失,
内心的波澜——
没有生死差别的声息
像一种复活,初来乍到。
这些毫无经验的杏叶、
蜘蛛和蜜蜂,如修炼之人,
与世界失去联系太久了,
如何参透狂风和雨天的危险性?
这些毫无经验的杏叶、
蜘蛛和蜜蜂,将时间越拉越长
越磨越亮,像心头默续的承诺书。
我触不到它闪闪发光的空间,
如彼岸的孤独,难以评估。
我赞叹这翕动的沉默,
无一破损。甚至忍不住想挤进去,
这样,那一万多年的时光
就是我的了。
——写于攀枝花营盘山顶
云朵碰着云朵。
云朵踩上滑行跑道,
嬉戏于一种游弋的速度。
一时,它的尘世反复挪动,
既交付天空又飘坠绝顶。
云朵蹭着过客的脚踝,无果。
把言辞压至心底。
当是嗔怪一个复返的恋人,
瞬間又下定了决心:爱不爱由你。
它叹息,营盘山顶适合告别,
不适合相互厮守。
此言无声,却将阳光微微晃动,
忐忑贴着修辞,结队悬浮,
类似柔软的伤感,依附永恒的山谷。
而此时,蓝色如美德驻步,
允许爱允许恨的样子,
缓解着自身的庄重。
不远处,云朵一动不动,
任蝴蝶在它身上扑翅、颠簸,
直到找出适合闪现的起点
和适合隐没的终点。
它长久地缱绻,一堆怡乐充裕地
抵御、消化一座山的空旷,
无数次地扣押游客的眼眸,
以便阻止他们搬走金沙江
潺潺的流水。
走进电梯,只有我和他。
瞬间的相望,算是彼此来去的
应答声。
我们分立两侧,
止住了内心的颠簸。
凝望清晰的虚无之处,
开始寻找另一个搁浅的自己。
大段空白,沉默不语。如眼眸里
行将渐远的风景,无可恋。
并身站立着,两缕形状平静的心绪
可交织每一寸的体悟。
虽然转身已是不再重逢的两个灵魂,
走时也不会丢下一个眼神。
但那一碰即碎的静谧,
发生过隐秘的揣探与克制。
解下围巾。经风一吹
内心的籽粒与草木一起
开始移步。长出绿芽,
长出没想好的那种瘦弱。
我喜欢这样的春天,
没有仇恨,亦不需要勇敢。
飞燕出发,望过去
斜侧的影子风一样跟着。
一种野生的快乐松开了,
很容易就滑到了季节之中。
它们毫不介意过往的危险性
是否被仁义礼智修葺过。
春天,一片空着的山坡
被重新装满:
金盏花、藤蔓、小鹿和豌豆,
一个个轮回,和我一样,
被承认过了,
并习惯将无数个春天里
已承受过的境遇浪费、模糊、
经不起回想。
对带着阴影路过的人,
小区里的广玉兰以最大的善意
开白花,开紫花,朝着他寒暄。
打开的真貌反对虚无,
收拢的,穷尽秘密。
有风吹过时,花瓣簌簌落了一地:
深陷其中的一串脚印,
终是遇上了自己的愿望,
走着走着就平静了。
一直走到芬芳的尽头,
即将用完的一天就完整了。
现在,一个暗淡的模样毫不自知地
生逢皎洁,恣意地轻盈起来,
像被原谅过的。
那块石壁的跟前
长出了一朵野花。
像是在一个极偏僻的地方
安放了童心。
它们全都承认自身的孤独。
只不过,一个似先知,自省,
是我们一直想抵达的去处。
另一个两手空空,等凋落,
懵懂无知地爱这个世界。
它们像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
再无未竟之事。
又确定是彼此的轮回,
都保持着被解救的样子。
(选自《石壁与野花》,张晓雪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本欄责任编辑 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