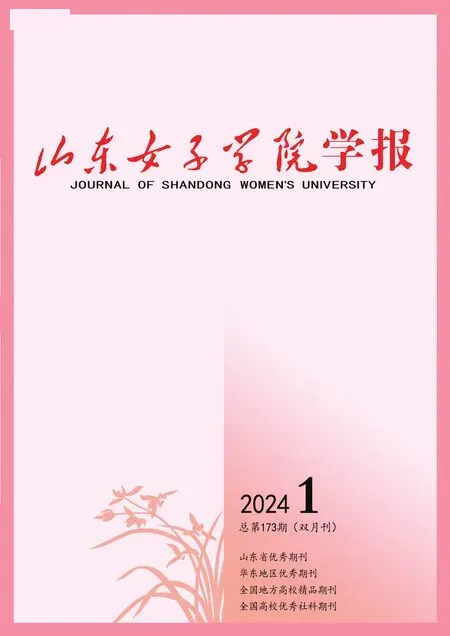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武则天:成因、功绩及局限
李 勇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父权制控制的封建社会,女性是从属性的存在,她们的人格受贬低、发展遭到抑制。然而,当自由之光渗透进父权制的裂缝时,亦曾开出旷世奇葩——武则天。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国有关武则天的研究非常丰富,但遗憾的是,既有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不足。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有人指出,“尽管曾有史学家、剧作家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翻过案或塑造过‘矫枉过正’的武则天形象,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评论界,审视和评价武则天的依然是男性视角和双重价值标准而缺乏女性意识”(1)陈怡:《“从女性视角重评武则天”讨论会》,《妇女研究论丛》,1995年第4期。。如今,有关武则天的性别意识(2)参见辛珑豆:《论武则天的女性意识》,《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和武则天对同期女性的影响(3)参见毕秋生:《武则天与武则天时代的女性命运》,《菏泽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的研究虽然已经出现,但细致、系统、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仍然罕见。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出发,阐释促成武则天成为国家掌权者的关键性别因素、“共情伦理”指引下武则天给同时期女性带来的福祉,以及在父权制和性别阶级分化的交互作用下武则天作出的必要妥协。
一、武则天何以成为国家掌权者
关于武则天何以成为国家掌权者,或是认为武则天的出现只是孤立现象,并没有明显的前因后果;或是用宗教和迷信为武则天掌权附上神秘的色彩。实际上,对孤立性的强调和基于神秘主义的阐释都不尽合理。武则天的出现既不是无迹可寻,亦非只能够求教于宗教和迷信,而是多种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为武则天的出现提供了土壤;父母特殊的培养是孕育武则天的摇篮。袁天纲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说,是父母改变对武则天的性别角色定位和武则天披荆斩棘登上皇位的助推剂。
(一)夹缝中的自由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社会。”(4)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意识才会如此强烈,进而有条件孕育出武则天这样“离经叛道”的女性。在武则天生长的唐初社会,“儒教的衰微、‘胡风’盛行等种种原因,使得唐朝形成了它特有的‘闺门不肃’、礼教不兴的状况”(5)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就儒学而言这或许是劫难,对唐朝女性来说却是莫大的幸运。这时,附加在女子身上的禁锢大为松弛,男性中心的道德观被弱化,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封建礼法的相对松弛,从多方面改变了唐朝女性的生活。一是她们在婚姻家庭上获得了更多自由。她们敢于追求爱情,贞操观念相对淡薄。闺中女儿私结情好、已婚女性另寻伴侣之事多见,离婚、改嫁更是常态。二是社交活动增多。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与异性交往,同席共饮、戏谑谈笑,或书信往来、诗词相赠。她们喜好“胡服骑射”“衣男子衣而靴”“露鬓驰骋”(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4,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19页。,经常参加打球、射猎等体育活动。三是贵妇干政蔚然成风。在处于鼎盛时期的百余年里,唐朝近半数时间是由贵族女性控制的。后妃干政在中国古代常见,但多出现在皇帝年幼或多病时,唐朝则非如此。唐时即便精明强干的君主在位,后妃辅政也常见,公主中亦出现了一批积极参政的女子。唐代宫廷女性求权之心炽盛,她们对权力的争取似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史发展经验的启示是——时势造英雄,伟大人物多是时代和环境共同造就的,女皇武则天的出现亦如此。在封建父权制牢固束缚的时代,女性处于集体沉默状态。但这种沉默多是被迫的,当束缚她们的礼教有些许松动时,女性则迅速挣脱,甚至以一种求偿的心态,奋力寻求曾失去的东西。在挣脱牢笼、寻求自由的女性中一般会出现少数突出者。她们在表现上与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她们却是时代和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对她们的阐释需要融入大背景。就此,武则天的出现非偶然事件。“夫权的削弱、妇女在家国中地位的提高、男性士大夫宽容的性别观念、‘牝鸡司晨’政治禁忌的打破和女性贵族在政治中作用的增强,都为女皇的出现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7)张菁:《唐士大夫的女性观与武则天现象的产生——以墓志为中心》,《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由此形成的开放社会风气为唐朝女性提供了难得的自由空间,亦在召唤武则天出场。
(二)父亲男性化的培养
无论是基于父权制对女儿的管控,还是出于人性本能对女儿的爱,父亲在女儿的生命历程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搞清楚武则天何以具有超前的性别意识,破关斩将登上男性把持的皇帝宝座,不能忽视其父亲武士彟的影响。武士彟原系山西木材富商,一生好学进取,政治上发迹于李渊起兵。武士彟突破商人的狭隘逐利本性,为李渊提供支持(有人认为是捐出家产(8)参见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虽结果未卜仍誓死投效之。据记载,“士彟为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后三让,方遂所陈”(9)(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6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4页。。武士彟虽为商人,但未受商人固有之自私、唯利是图、精明狡猾、投机钻营等“劣根性”的钳制,其具有的“廉俭”“忠节”(10)(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627,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12页。等良好品性为他更好地培养武则天奠定了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改变武士彟对待武则天态度的袁天纲相面事件。贞观元年(627年),武士彟担任利州都督,袁天纲赴京途经利州。袁天纲到武士彟家中,见其妻杨氏说,“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在给二子、一女相面后,乳母抱出着男服的武则天,袁天纲道,“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试令看行”。后大惊,“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转侧视之,又惊“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93-5094页。。这里流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武后时衣男子之服”。如果说此时少女喜着男装是自主选择之果,作为3岁小儿的武则天着男服就是父母性别意识的直观反映。蕴含其中的信息有二:一是武士彟有超前的性别意识,混同的性别观念使他认为男女皆一样,女儿可着男装,儿子亦可着女装;二是武士彟的“求偿心理”(12)已有二子的武士彟求子心切或可解释为:一是二子资质平平,且生母地位低下,难担其厚望;二是杨氏身份高贵,且系皇帝指婚,头胎生女,故望生子。参见[日]原百代:《武则天传》上,谭继山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让他把本为女儿的武则天视作男孩对待,故着男服。无论出于哪种理由,都显示出武士彟具有在封建父权制相对松弛的环境中培养出女性国家统治者的积极性别意识。
史书虽未曾记载武士彟此时的心理活动,但基于常理不难发现他的心理活动及前后发生的转变,即从最初的惊讶,进而怀疑,再至内心认同,以及由此带来行为的转变。“关于武则天的童年生活,正史上记载不多,可以确知的是武士彟无论到哪里上任,都会把她带在身边,跑遍了小半个中国。”(13)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11页。孩童时武则天涉足之处,后来都留下喜闻乐见的传说。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甚至夸大的故事性叙事固然不足为信,但可从侧面反映出幼年武则天深受武士彟宠爱。这种宠爱不仅是传统的父亲对女儿的爱,更类似于父亲对儿子或继承人的培养,这使幼年武则天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基本的面向男性掌握的政治社会公领域的处世之道。或许基于当下的观点审视,武父对武则天偏男性化之爱或培养的做法不足为取,但考虑到依旧是封建父权制社会的背景,武父对武则天男性化的培养方式就应被看作是有价值的超前之举。
(三)母亲积极性别意识的影响
在那些走出家庭、获得显著成就之女性的身后通常存在着一位伟大的母亲,女皇武则天也不例外。有关武则天母亲——杨氏的史料记载不多,按照袁天纲相面得出的说法,“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1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1,第5093页。,杨氏本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子。“杨氏出自弘农。弘农杨氏打从东汉年间出了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后,成为名门。”(15)韩昇:《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新探》,《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这说明杨氏拥有高贵的血统。“杨氏既为高门贵女,颇具北朝女子精明强干、大胆泼辣之风,不好针线女红,轻视纺纱织布,喜诗书,善属文。”(16)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10页。在学识、才情和性格方面,杨氏亦不同于一般女子。经历南北朝从分裂走向统一,见证隋朝从建立到灭亡,唐朝从起兵到建立,以及在此过程中经历的坎坷命运后,无论内在品性还是对外在世界的看法,杨氏都得到了磨练。
据“咸亨元年(670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17)(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21页。推测,杨氏结婚时至少已42岁。将之解释为“父来不及为她寻得佳婿就撒手人寰,接着天下鼎沸,隋朝灭亡,岁月蹉跎,好不容易熬到唐朝建立,天下初安,杨氏才得以由唐高祖主婚,嫁给武士彟”(18)韩昇:《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新探》,《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不尽合理。即便一般人家,父母死后,闺中女儿的婚姻亦会由其他尊长主导,更何况出身贵族的杨氏。而且,相较之平民女性,战乱对贵族女性的影响相对较小。更毋论,“出身于周、隋大贵族的唐高祖李渊,对隋朝的皇族、宗庙和旧制度加以保护,使豪门贵族地主仍拥有相当大的势力”(19)谢建明,黄华强:《武则天——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3期。。杨氏结婚是唐后至少3年以上,此时再认为政治和社会因素导致杨氏晚婚亦显牵强。另外,杨氏嫁给武士彟系高祖指婚。若非如此,已逾不惑之年的杨氏何时完婚,有无终身不婚的可能,是仅用现实因素无法解释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杨氏拥有一定程度的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精神,这样一位不甘封建礼教束缚的母亲必然会在各方面对女儿产生影响。
另外,笃信佛教为杨氏相信袁天纲相面的说法、改变对武则天的性别观念和培养方式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唐朝佛教兴盛,相术流行。佛教与相术背后之玄学的关系为何,以使二者同时存在?因为重玄思想属于道家,故佛玄关系演变为了佛道关系。在唐朝,佛道关系复杂。道教通过“援佛入道”(20)张耀南,钱爽:《“离四句绝百非”与成玄英“重玄学”》,《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3期。以完善理论建设。玄、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为杨氏相信“女主天下”之说提供了现实条件。自此以后,始终持守佛教信仰的杨氏会相信女儿终将成为掌权者的预言,至少她对女儿必定与众不同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这种确信还会反映在行为方式上,无论是培养目标定位、教学内容安排还是性别角色认定,杨氏对幼年武则天的教导必将有别于其他女性。在武则天争宠夺嫡的关键时期,杨氏通过积极行动给女儿提供支持,亦表明她对女儿将成为皇帝的确信。
(四) “女主天下”的内心确信
袁天纲相面时,武则天虽为3岁小儿,但随着慢慢长大,无论是从父亲(21)按照原百代的说法,“父亲反复告诉她那个预言,直到年幼的武则天能够背诵清楚为止,她并且答应父亲,自己要努力促成这件事”。参见[日]原百代:《武则天传》上,第69页。还是他人言语中,幼年武则天都知悉“女主天下”之说,是可以确定的。加之,父母对自己特殊的培养方式,强化了武则天对“女主天下”的认同。根据后来在称帝时/后试图通过宗教玄学证成政权合法性的做法(如,利用弥勒佛化身为人普度众生的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给自己取大周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22)参见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32页。)不难看出,或是受母亲笃信之佛教的影响,武则天是相信宗教玄学之说的,亦为她认可袁天纲相面之说奠定了心理基础。随着内心认同而来的是对自身定位的改变,即武则天相信自己的命运有别于其他女性/皇帝妃嫔,她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女主天下”的预言。
武则天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入宫时,母亲流泪告别,她坦然答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2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4页。。武则天表现出的异常冷静态度可解释为,在相面之说的指引下,她对进宫有必然的预期,或早已作好入宫准备。进宫十余年里,她的品级未获升迁。太宗驾崩后,其更被迫出家感业寺。若将这些遭遇置于任一其他妃嫔身上,命运的沉浮将把她们伤得体无完肤,又有谁会再抗争。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武则天或怀疑过“女主天下”之说的真实性,但经过艰难的内心争斗后,她还是相信“天命在我”(24)[日]原百代:《武则天传》上,第262页。“天地之间一定有神秘力量的存在,帮助自己取得非凡成就”(25)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334页。。另外,“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令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说:‘当有女武王者’”(2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9,第2524页。,此与袁天纲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说不谋而合。“此种不谋而合的神秘,给武则天强烈的冲击。”(27)[日]原百代:《武则天传》中,谭继山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第456-457页。于是,她又想起袁天纲相面事件,进而强化了其对“女主天下”之说的确信。
基于幼年和入宫初年的不幸经历,将武则天“想象成为单纯由戾气凝结而成的怪胎”(28)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5页。的观点,不足以阐释她隐忍数十年,经过艰难险阻,最后登上至尊皇位的事实。武父去世之后短短两年内,兄长的刁难形塑了伴随武则天终身之暴力性格的说法,按照性格形成的一般规律是很难成立的。对武则天而言,初入宫伊始“心里便有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念头,亦深知前途布满荆棘,困难重重”(29)[日]原百代:《武则天传》中,第456页。。在险恶异常的环境中,儿时袁天纲相面得出的“女主天下”之说成为武则天的重要心灵依托,及其在艰难岁月里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和克服重重困难的核心动力。它像明灯一样,将武则天从信与不信、挣扎、纠结、痛苦的深渊中拉出来,指引她走向权力的制高点。
二、武则天给同时代女性带来的福祉
共情伦理的核心主张是,“我了解你的处境,因而我支持你”之设身处地的同理心。故不同于有研究者主张的武则天“基本遵循男权权力行使规则,以‘女扮男装’进入封建权力系统乃至权力之巅,按照男权统治和文化规则治理国家几十年……似乎没有丝毫女性气息”(30)徐琛整理:《女学者论武则天》,《妇女研究论丛》,1995年第4期。。本文认为,基于共情伦理和现实情况的审视,武则天不是没有女性气息,而是在被儒家礼教限制手脚和思想的情况下策略性地纳入了女性气息。事实上,提高女性的地位是武则天的长期目标,但凡有性别意识能够嵌入的地方,武则天便采取行动以与同时代女性共荣耀。
(一)否定并反抗儒家礼教
在结构性贬低和压迫女性方面,儒家礼教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在母权制社会,世系按母亲计算,母亲拥有崇高的地位。“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31)[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若说从根源看,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源于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制度化方式固定这一变更的则是儒家礼教。儒家礼教打着“有序”的旗号,通过一系列礼法将女性合法、永远地囚困在第二性的位置。在以父权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男性凭借儒家礼教成为了“当然”的掌权者,然后通过儒家礼教强化男权统治、证成男权统治的合法性,其间存在压迫女性的恶性循环。就此,武则天反对儒家礼教是必然的,她成为国家掌权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武则天反儒是一以贯之的。一是通过自身行为反抗儒家礼教。武则天敢于亲自执政,本就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蔑视和造反,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批判。二是在科举方面,武则天蔑视儒学经典,提倡诗赋文章。逐渐地,“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32)(唐)杜佑:《通典》卷15,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1页。。当这种文化风俗渗透至被儒家礼教形塑之男性身上时,他们对妻子、女儿乃至所有女性的态度亦会发生改变。对女性而言,新文化风俗的传播将提升她们的自我认知。三是在保皇派以儒家礼教为据阻止立武则天为后时,她怒说道:“何不扑杀此獠”(3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90页。,亦表明她对保皇派儒家信徒及其背后之儒家礼教动刀的决心和勇气。在此,不能仅用残暴和专断来批驳之,因其涉及另一场无声但激烈的斗争——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束缚和压迫女性之儒家礼教的斗争。故清除保皇派儒家信徒不仅是武则天个人的胜利,还具有重要的反性别歧视和压迫的意义。
鉴于在儒家礼教形塑起来的文化和政治中,女性不能执掌国家政权,是武则天面临的最大阻碍。从此意义上讲,武则天反儒,在策略上确实是为自己执政扫清障碍。就结果而言,这对束缚在儒家礼教下的同时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恪守儒家礼教的封建社会,多年不得太宗赏识、尼姑出身的武则天敢于反抗“男尊女卑”的传统,打破“三纲五常”的礼教,登上至尊皇帝之位,是女性冲破儒家礼教、寻求自身发展的重大事件。试想之,当国家掌权者是女性时,又有谁敢明目张胆地说男尊女卑。武则天掌握国家政权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除了逆来顺受,女性还可以且有能力在所谓本属于男人的世界里取得和男人同样的成就。概言之,武则天掌握国家政权具有的示范意义,加之她采取的反儒举措产生的积极社会效果,在当时的唐代社会形成了反儒的风气。在封建父权社会的大背景下,这是对女性最友好的环境。
(二)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在宗法礼制下,“丧服是表示身份等级和服丧人和死者之间政治、血缘关系亲疏的原则”(34)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212页。,由此确定亲属集团的范围边界,及其内部的从属关系。在封建礼教下,父亲是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仪礼·丧服》规定,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三年),丈夫为妻子服齐衰(一年),母在为父服和父在为母服差异明显。如左散骑常侍元行冲所言,“天地之性,惟人最灵者,盖以智周万物,惟睿作圣,明贵贱,辨尊卑,远嫌疑,分情理也。……。天父、天夫,故斩衰三年,情理俱尽者,因心立极也。……而妻丧杖期,情礼俱杀者,盖以远嫌疑,尊乾道也”(3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8,第1023页。。服丧时间的差异体现了在以男性为中心、惯行家长制的封建社会,女性祖先受到严重不公正对待。在认识到提高女性地位必须先提高母亲地位后,武则天又一次采取了“越轨”行为。
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上表高宗说道,“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报母之慈有阙”(3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8,第1023页。。就此,武则天提出了“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九条为“父在为母服齐丧三年”(3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第3477页。,被认为是在其执政生涯中最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提案之一。该建言被高宗采纳,并下旨落实。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主政时,将之列入《垂拱格》,成为正式的法律。“至(开元)二十年,萧崇与学士改修五礼,又议请以上元元年(674年)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为定。及颁礼,乃一切依行焉”(38)(宋)王溥:《唐会要》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78页。,“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成为后世标准丧期。
武则天上表时提到“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不足多也”(39)(宋)王溥:《唐会要》上册,第675页。,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典型表现。从“礼缘人情而立制”和“因时事而为范”可看出,此时武则天已对礼法古制产生了质疑。在质疑礼法古制的基础上,武则天始拥有“变古”之意。她明知会遭到竭力阻挠,依旧以“伤人子之志”为由请求变更服丧制度,表明武则天清楚地认识到服丧制度喻示的女性从属地位,并知晓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所在。理由方面,武则天提出的“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4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8,第1023页。等,呈现出的是传统女性以子女生养和照料为核心的家务活动,以及由此面临的不利处境,依此为据主张父母丧服同制,乃是变相地承认了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概言之,武则天将亡母适用的“齐衰”改为“斩衰”,打破了家无二尊的局面,在服制上提高了母亲家庭法律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妻子乃至所有女性的社会地位。
(三)改革婚姻家庭制度
武则天深谙在儒家礼教下,婚姻及由此形成的“家庭始终是妇女们难以冲破的牢笼”(41)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25页。。但在封建制度下,即便是作为国家掌权者的武则天,亦无法彻底为所有女性打破婚姻家庭礼教的束缚。然而,武则天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以更具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式为提高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采取了不少重要举措。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武则天时期,女性在家庭生活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说,此阶段女性的婚姻家庭法律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是空前绝后的。考虑到皇帝后宫虽特殊,但本质上仍是家庭的一种,故本部分的探讨既指通常意义上的封建家庭,又包括广义的家庭——皇帝后宫。
武则天在通常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方面采取的举措主要如下。一是聘礼充嫁妆。显庆四年(659年)朝廷下令:“天下嫁女受财……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42)《唐会要》显示,聘礼充赀妆是李义府的提案。需要注意的是,在遭长孙无忌贬斥之际,李义府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成为第一个支持立武则天为后的大臣,后为武则天宠臣,直至客死他乡,武则天对这位追随者都念念不忘。鉴于武则天和李义府之间的特殊关系,该提案很可能是李义府希武后旨上表的,奏折的通过是二人上下配合的结果。而且,此时武则天在朝廷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如果说聘财充嫁妆这一极具性别色彩的举措没有武则天的参与甚或是决定,很难成立。意为,此前由女方父亲/家庭所有的聘礼均抵充嫁妆,归出嫁女所有。此举具有重要价值,对在室女而言,这在提高其家庭地位的同时,有助于减少父母卖女求财的行为;从出嫁女角度看,将嫁妆规定为私人财产、夫家不得侵占,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的财产权,亦有助于提高其在夫家的地位。二是改大婚时女子的跪拜礼为站立式参拜礼。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风起洛阳》中有个看似格格不入的画面:大婚时,新郎行跪拜礼,新娘站立行礼。唐之前,大婚时男女均行跪拜礼。《宋史》显示,“太祖尝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否,普问礼官,不能对。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是妇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43)倪其心:《宋史》第九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5778页。,武则天当政废女性跪拜礼。男跪女不跪的结婚行礼方式具有提高女性地位的象征意义。
武则天在皇帝后宫采取的典型举措是改革妃嫔制。龙朔二年(662年),武则天主导进行妃嫔制改革:“置赞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仪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嫔。承闺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卫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宝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侍栉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又置侍巾三十人。正九品”(44)(宋)王溥:《唐会要》上册,第32-33页。。此举弱化了妃嫔的传统角色,突出了女性职能的价值。“至少在名义上,她们是掌领宫中职事的人。”(45)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下,妃嫔本属妻妾,生死荣辱均系于天子。此举反映出,妃嫔像朝中大臣那样拥有政治或实务上的职能。为每个位阶设置定数,削减妃嫔数量,变相体现了武则天反对多妻制的态度。故研究者提出的武则天和高宗“形同一夫一妻”(46)[日]原百代:《武则天传》中,第442页。虽有夸大之嫌,但妃嫔数量减少确属事实。考虑到深宫的寂寞、束缚和危险,对因此无须进宫的女性而言,何尝不是福音。皇帝如此,官员百姓亦效法之,纳妾的情况将会减少,卖女、强抢民女的情况亦有望减少,对普通女性来说又何尝不是福音。
(四)调整政治、娱乐、祭祀活动
特开女试。武则天“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广,其深闺秀闺能文之女,故不能如苏葱超今迈古之妙,但多才多艺如史幽探、哀萃芳子类,自复不少。设俱湮没无闻,岂不可惜?”(47)(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故拟令天下才女俱赴廷试,以文较高下。次年武则天下诏:“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蘋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48)(清)李汝珍:《镜花缘》,第196页。。类似于科举中第者入朝为官,武则天设“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之职。若有意到内廷供奉,可在试用一年后量才取用。女性不仅能参加女试,通过者还有官职和俸禄,父母亦可享受相应的待遇。神龙元年(705年),女官已达三千(49)参见刘晓云:《唐代女官的特点》,《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S2期。,这从侧面反映出武则天时特开女试的真实性。女官从事的固然是与传统女性职能相关的工作,却也通过协助处理政务最大可能地接近了权力的中心。
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俳优,古称倡优、优伶,后多指从歌舞艺人中分化出来的以调笑逗乐、滑稽表演为艺术特色的职业艺人。”(50)成军:《隋唐俳优“戏弄”表演研究》,《戏剧文学》,2017年第12期。据《韩非子·难三》记载,“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俳优的地位极其低下,他们只是主人的附庸甚或奴隶。隋唐时,俳优在法律上属于贱民,加之职业的特殊性,他们通常被限制在特定场所内,世代群内婚配。“乐人、歌者,舞者,穿着华丽,袍袖冠冕,舞衣翩跃,而俳优则上身袒裸,只是下身着裤,从未见有衣冠整齐者。”(51)于天池:《两汉俳优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如果说这在男性身上彰显的是地位低下,附加上性政治的作用以后,物化和低等级性在女俳优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女俳优不仅会成为供男人性娱乐和戏弄的对象,甚至还会成为主人的性工具,这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极度贬损。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以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武则天力图禁止女性为俳优之戏。故在显庆六年(661年),时任皇后的武则天“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5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第82页。,该建议获得高宗的准许。

三、武则天性别意识和行动的局限
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数十年里,武则天虽提出不少对女性友好的举措,但从整体看,她对封建社会中女性面临之消极处境的改变并不多。“这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基本格局决定的。”(54)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86页。武则天是儒家礼教的挑战者,但她确实也置身于由此形塑的大环境中。“挑战与妥协,斗争与放弃,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对正统伦理观念准则的力不从心,同样存在在她身上。”(55)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261页。武则天的性别阶级身份——贵族阶级女性,亦注定她无法真正地跨越阶级限制,在更广泛层面给普通女性带来福祉。
(一)封建父权制根深蒂固
早在奴隶制时期,以男性士大夫的生活为参照,儒生对两性附加了双重道德标准,进而形成了男女之间强弱、主从、刚柔、尊卑的鲜明对比。“商周更替完成由父系制定型到父权制确立的过程,确立了父系本位、男性中心的父权制体系,基本格局是男主外女主内,婚姻的目的是为男性本位的父权家族利益,政治权力和家族财产传承都在男子之间进行。”(56)张菁:《唐士大夫的女性观与武则天现象的产生——以墓志为中心》,《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至两汉,男性士大夫强化了女性对家庭的依附,赞扬女性谦和之气,要求女性柔顺贞孝,卑弱寡欲,为丈夫、子女和家庭甘愿作出牺牲。“自汉代儒学立于‘独尊’地位后,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逐渐成为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57)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142页。,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等伦理纲常成为定礼,封建父权制正式确立。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女性内化了儒家伦理纲常,并依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公认之理想女性形象亦是符合这套定礼的女性。
封建父权制社会的基调如此,哪怕身处开明的唐朝,女性依然处于由此构建起来的密网中。武则天固然有幸成为“漏网之鱼”,但远无与封建父权制“鱼死网破”的条件和力量,而且事实上武则天的突破也是在父权主义框架下进行的。若试图改变女性备受歧视、压迫、剥削的封建父权制整体环境,仅凭作为统治者的武则天或少数贵族女性群体的意识觉醒还远远不够,而是需要女性整体的意识觉醒。意识觉醒是向内的,它要求女性认识到附加于己身的父权统治是错误的,女性有权拥有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自由,进而形成改变不自由现状的自觉。基于对唐代社会的审视不难发现,通常所说的唐朝女性社会地位高,指向的不过是穿低胸装、男扮女装、女性走出家庭等现象层面的东西,它们不能够成为证成唐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充要条件。在唐代女性依旧从心理上认同封建伦理纲常并依此安排自身生活的情况下,试图彻底改变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现状并不现实。
(二)性别阶级分化的作用
依据恩格斯的说法,“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58)[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7页。,女性在总体层面可以被视为受压迫阶级。依此,在将封建父权制作为敌人的情况下,武则天确实与唐代女性乃至封建社会所有女性同处同一阵营。但正如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的研究所显示的,除共同面临的父权统治外,女性并非同质性的群体,阶级分化带来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59)SEE ZILLAH EISENSTEIN,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Critical Sociology,Vol.25,No.2-3,1999,pp.196-217.。纳入阶级因素的考量不难发现,武则天与同时代女性的阶级地位悬殊,这决定了仅借助父权制分析难以全面解释武则天性别意识及其行动的局限。在揭示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时,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不容忽视。
按照标准不同,武则天与同期女性之间的阶级差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方面,如果说武则天能为同期女性带来福祉,更多指向的是地主阶级(庶族地主)而非平民女性,这是她生长于地主家庭的事实决定的。基于对武则天掌权时期采取的措施的审视不难发现,打压士族地主、扶持庶族地主是她始终坚持的立场。武则天的性别意识和行动与她代表的庶族地主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是一致的,这注定了她无法跨越阶级限制,设身处地地为社会中下层女性考虑。另一方面,作为贵族女性的代表,武则天的性别意识和行动亦有限定性。从初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她便脱离了普通女性的生活,她所经历以及看到和听到的亦只是贵族阶层女性在深宫中的遭遇。无论是泰山封禅还是变革妃嫔制度,武则天性别意识觉醒及采取之行动的受益者更多是同属贵族阶级的女性群体,而非普通的社会中下层女性。
根据传统政治哲学家的说法,人类“自利”和“互利”的本性决定了“行动者”和“受益者”一般是等同起来的。这种等同在争取权利或寻求解放的女性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而言,女权运动是由特定女性发起并主导的,旨在解决的是她们所关切的问题,这可以适用于对武则天性别意识和行动的分析。立场决定思想,作为地主阶级女性和贵族阶级女性的代表,武则天很难真正了解中下层女性的需求,更毋论超越阶级限定性,对她们给予更多的爱与关怀了。故有学者谴责道,“武则天作为女性登基称帝,完成了堪称伟大奇迹的逆袭,是改变万千女性命运的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但武则天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她仅是给自己和极少数贵族女性的生活带来重大变化,未从根本上推动女性命运的改变”(60)毕秋生:《武则天与武则天时代的女性命运》,《菏泽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即便没有那么绝对,这种谴责亦有一定的道理。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及由此带来之立场的差异,注定了武则天难以从根本上推动同时代女性命运的改变。
(三)局限的具体表现
女性参政依旧受到严格的限制。自儒家礼教被确立为指引女性的行为规范以来,女性的活动领域便被划定在家庭内部。在武则天执掌国家政权的唐朝,固然有少数女性成为宫官,皇室女性亦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但男性主导政治的状况并未有实质性改变。武则天执政时虽面向全国才女开女试,但诏书显示,女试中第者,“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61)(清)李汝珍:《镜花缘》,第196页。。也即,即便通过女试并拿到名次,女性可以获得的最多不过是成为“内廷”官员的机会,与朝廷官员不可同日而语。唐朝的“内廷”是参照“外廷”(朝廷)设置的,设有宫官(多为女性)制度。女性宫官负责掌管内宫事务,工作内容与普通女性在家中负责的事务有相通性。就此,“女试”与科举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女性成为宫官亦不等同于“参政”。即便经过武则天的特许,权倾一时且有“巾帼宰相”之名的上官婉儿终究也不能上朝议政。
还政于李唐。皇位同姓相袭是封建王朝的常规做法,武周则是例外。武周皇位继承更具突破性的两种可能都被武则天推翻了。一是立太平公主为皇太女。武则天称帝后,在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6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651页。、嫡亲皇子资质平平、社会相对开放的情况下,出现了立皇太女的最佳时机。二是参照封建父权制传统,在侄子中寻找皇位继承人。然而,武则天既未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而传位于公主,亦没有将皇位传给武姓后代,而是还给高宗嫡亲皇子。另外,武则天发布了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遗诏——袝庙、归陵、去帝号。武则天决定将神主归李唐宗庙,自称“则天大圣皇后”。如果说年轻时武则天试图颠覆以父权制为底色的国家政权,在确定皇位继承时确实动过册立皇太女和传位于武姓后代的念头,但最终仍决定将皇权还给李唐。在心理和行为上,武则天最终都向曾经挑战过的世界和森然可畏的秩序屈服了。如果说武则天在与男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试图推翻宗法制度的斗争却是失败的。
武则天的举措更多反映的是特权阶级女性的利益。无论是初衷还是结果上,武则天采取的具有性别意识的举措多有阶级限定性。变革妃嫔制度体现的是贵族女性的需求,相对提高的只是少数女性的地位。更多普通女性依旧被束缚在家庭内部,无休止地从事家务劳动。消耗女性青春乃至生命的家务劳动被认定为没有经济价值,她们不得不依靠丈夫的供给而生活。女试方面,武则天颁布的诏令提到,“他如体貌残废,及出生微贱者,俱不准入考”(63)(清)李汝珍:《镜花缘》,第197页。。出生是女性参加女科的前提,出生微贱的女性被剥夺了唯一可能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武则天称帝的行动传达了“女性不能参政的规则可以被打破”的重要信息,故相较于他朝,此时女性参政的情况确实更为常见,以太平公主为代表的宫廷贵族女性曾掀起一波参政浪潮,其他女性的参政之路依旧被阻断。除一般意义上的特权阶级女性外,这里提到的特权阶级女性还包括武则天的同族女性。从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参与国家政治伊始,其母、姊、侄女均获得封赏。武则天称帝后,武姓四代女性亲属和姨母亦得到了相应的封赏。
四、结语
或是出于器重酷吏的任人偏好,或是出于心狠手辣的处世之道,或是出于有悖常礼的生活作风,或是出于对儒家礼教动刀的果断,甚或只是出于女性的性别身份,武则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以“悍妇昏君”的形象出现在研究者的书写中的。然而,透过女性主义的棱镜,撕开父权制文化传统编织的性别歧视面纱可见,武则天不是昏君、僭主、崇尚酷刑的法家代表,而是拥有辉煌而伟大一生的传奇女子。身处极度压制女性的封建父权制社会,武则天不屈服于传统有关女性命运的设定,而是大胆地挑战父权制的安排,最终将男性统治者拉下神坛,成为中国唯一的正统女皇,掌握政权数十年。武则天用登上至尊皇位的事实打破了女性是劣等主体和从属者的谎言,证明了她们同样有能力做此前被认为只能由男人做的事情。作为封建礼法制度的“反叛者”和同男性争取国家最高政权的“先驱者”,在争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道路上,武则天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前有高宗以无法控制为由,“阴欲废之”(6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第81页。,后有朝臣兵变试图讨伐之,一路走来的艰难险阻都注定了她“只能在刀尖上跳舞,难有一刻安稳”(65)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第34页。。庆幸的是,历史没有辜负她数十年的隐忍和持守一生的期许,武则天终于在夹缝中以英雄主义的姿态找到了属于自己和同时代女性的一片天空。遗憾的是,在封建父权制丝毫未被动摇的情况下,这片天空终究是有限的。无论是武则天还是同时代其他女性,她们面临的束缚均非短时间所能打破。故即便在性别意识和行动上有局限,对武则天亦不能够太过苛责,更毋论对她“祸国殃民”“垂帘听政”“牝鸡司晨”的定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感叹其身处父权制环境仍能尽最大可能为女性发声的同时,考虑到女性解放是长期且艰难的事业,女皇武则天的未竟之业亦需后时代,乃至今时和未来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