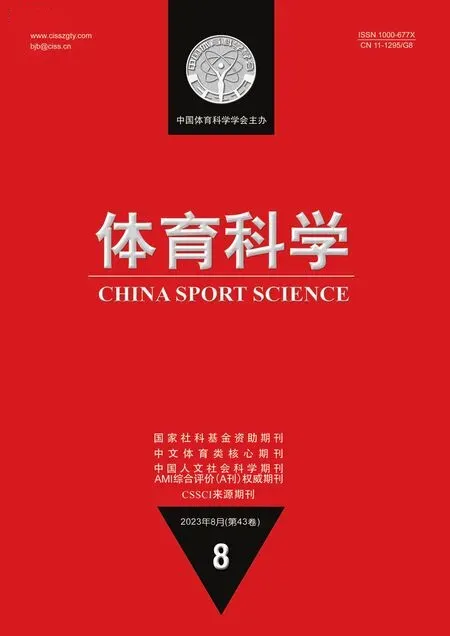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演进、经验与路径
郭 振,王 松,李含宜,刘 波
(清华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084)
近年来,我国体育学界持续关注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研究,旨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一些研究从体育学科发展史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体育学科的发展现状与困境、内涵与任务、成就与动力等,指出在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学科融合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学术界跟进研究(卢元镇,2018;齐大路 等,2023;王家宏 等,2021)。历史社会学是一种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赵鼎新,2019a)。随着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推进,历史社会学被学界视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丹尼斯·史密斯,2000)和分支学科(理查德·拉赫曼,2017),逐渐在国内成为显学。
体育学研究也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在理论与证据、叙事与分析之间不断交融。在体育学研究中引入历史社会学理念与方法时,需要立足于学科特质,在学科谱系中发现二者的密切关系。对于体育社会学而言,与其说它是时代的历史性产物,不如说其试图用穿透历史的普遍理论来解释体育现象。对于体育史学而言,随着体育叙事史、体育文化史、体育全球史的回归和兴起,从叙事型历史社会学以及阐释型历史社会学来解读事实成为新趋势。可见,历史社会学为体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路径,把体育学研究从学科分化中解放出来,走向交叉融合。对此,本研究立足于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发展历程,凝练体育学科分化与融合进程中的历史社会学经验,提出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策略与前景,助推我国体育哲学社会学科体系的建设。
1 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发展
自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社会学在欧洲诞生后,学科不断分化造成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对立”(彼得·伯克,2010)。历史社会学虽扎根于古典社会学,却因社会学起源于欧洲而有着浓重的地域烙印,历经二战后的理论“阵痛”,历史社会学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主流学术界的视野,并不断调整发展。从地缘上看,现代体育(sport)诞生于欧洲,在学科创建上,体育社会学亦始源于欧洲,可见历史社会学与现代体育自诞生后就在地域上产生了联系。而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引入、扩展与成熟,反映了体育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突破。
1.1 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根源、重生之路与现代之思
在现代欧洲社会学产生之时,历史社会学被第一代社会学家所运用,即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根源之所在。奥古斯特·孔德(2009)依据人类认知演变规律,将知识发展划分为3 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基于这一欧洲社会学传统,马克斯·韦伯采用比较社会学的路径,将“阐释”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卡尔·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与逻辑,成为批判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资本论》无论在经济史还是经济理论领域,都具有巨大贡献(吴帆 等,2009)。马克思和韦伯立足于历史构建其理论,奠定了历史社会学范式(姚中秋,2020)。
二战后,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更为关注总体史观,特别注重挖掘历史现象与时代变迁的多层次因素。布罗代尔在历史社会学方面有着诸多建树,特别是其提出的“结构史”概念,即以结构-情势-事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是对马克思历史社会学分析的一种继承与发扬,已然成为日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孟庆延,2022)。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进入“凤凰涅槃”时期,从理论和方法上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反思。巴灵顿·摩尔、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等举起历史社会学大旗,开启了历史社会学的“重生”之路。历史社会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抽象化整理,强调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并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来关注重要活动的历史性。此外,一些研究对战后欧洲所产生的东西方冷战、移民流动等现实性问题的思考,推动学界从20 世纪初到20 世纪30 年代对欧洲历史社会学重要性的再发现。延至20 世纪70 年代末,作为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的所处地位仍极为“暧昧”,但至少历史社会学有了存在的必要性,正如杰拉德·德兰迪等(2009)指出,“其最突出的理由异常明显(令人尴尬的是,它却经常被忽视),那就是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历史社会学的第二波浪潮出现。随着多元史观的崛起,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转向宏观,关注结构叙事,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努力寻找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点。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历史社会学被明确看作社会学的一个独立分支。20 世纪90 年代,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浪潮发端,其突出特点是研究维度的文化转向和对于行动者能动性的强调。此时期的研究站在重塑现代性的立场上,透过对微观情境中行动者主观行为和动机的分析,试图实现从社会结构到主体行动的转变(严飞,2019)。研究转向历史,专注于革命、社会冲突与变迁、工业化、阶级形成、国家形成、民主化、资本主义起源与变迁、官僚制等议题,开创了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新潮流。换言之,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场知识运动,起初是作为批判主流社会的武器,共同抵制帕森斯主导的系统论与功能论社会学(郭台辉 等,2022),它让社会学再次注重历史因素与历史结果,促进了历史学的理论转向,协同了结构叙事与时间叙事。
1.2 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引入、扩展与成熟
19 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现代体育运动开始了全球化传播。在顾拜旦的斡旋与努力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各大体育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全球传播与发展。体育运动出现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中。欧洲一些学者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进而确立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向。德国学者海因茨·里塞于1921 年写就了《体育社会学》,是第一部体育社会学专著(Taylor,1983)。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2007)的《游戏的人》,从文化史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2013)的《文明的进程》,把体育现象作为文明推动人类行为发生特殊变化的一大佐证。20 世纪3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历史学者关注了体育史研究,如霍利曼的《美国体育:1785—1835》、杜勒斯的《学习玩耍的美国人:1607—1940》等。他们紧随时代的史学语境,以美国职业史学奠基者特纳的“边疆学说”为指引,将美国体育的成长置于“美国例外论”的宏大语境中,在帕克森之后,继续将“透过体育看社会”的“大体育史”传统发扬光大(王邵励,2019)。时至今日,这些经典著作所蕴含的历史社会学观点仍然为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如文化研究的切入、动态的视角、对人类发展长期过程的关注等。审视现代体育的发展表征和危机,通过这些普遍认识来把握现代体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如全球史视域下的体育运动价值取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对生态环境的应对、西方竞技体育对东方传统体育生存的冲击等,都需要采用历史社会学的观点予以回应。因此,体育学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应把历史社会学纳入其中。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体育社会学在对古典时期社会学继承及对结构功能主义反思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体育学研究中,对历史社会学的自觉认识是建立在20 世纪30 年代古典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诸如埃利亚斯对体育社会学的贡献,布迪厄的阶级、场域、社会资本等概念在体育学研究中的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体育研究的影响等,大都是建立在动态的历史分析情境之下,体现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埃利亚斯及其追随者对猎狐、足球等运动项目的研究。埃利亚斯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关注了竞技体育对“文明的进程”的作用,并提出“体育化”(sportization)这一概念。埃利亚斯的学生埃里克·邓宁对“文明的进程”应用于竞技体育研究之中,并与埃利亚斯合作编著了《追寻兴奋:文明的进程中的体育与休闲》,为历史社会学运用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模板。邓宁对竞技体育进行“特殊化”处理,其研究成果成为“文明的进程”在体育社会学论述中的基础,这种竞技文明化论述并非止步于体育学本身,还极大影响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邓宁进一步总结了以抑制暴力为主旨的“文明的进程”和现代竞技体育的产生,对“足球流氓”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通过追溯“文明的进程”对现代竞技体育未能包含的“理性暴力”的问题进行了论述(Dunning,1986)。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研究让体育社会学在社会学体系中拥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之后,邓宁和克里斯·罗杰克合著的《文明的进程下的竞技体育和休闲》中,呈现了对文化研究的批判与反批判(Dunning et al.,1992),从而把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体育议题引入文化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历史社会学注重学科交流,如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体育学界也存在着体育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历史社会学、体育社会历史学等多研究范式,并由此衍生出较多共同点,即尊重历史的传统,共同强调社会现实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Maguire,2011)。对板球、武术、足球等运动项目开展历史社会学研究后,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逐渐走向成熟。板球运动对英国民族身份的定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 世纪中叶,英国不同社会阶级在板球运动中进行互动,对该项运动在美洲的传播具有显著但未被承认的影响,这种非计划性的社会进程只能通过英国和英裔美国人、上层和下层英国移民、英国移民和“白印混血美国人”之间的特定相互关系进行理解(Malcolm,2006)。另外,在体育运动项目的研究中,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占据主流,涉及日本武术(García,2018)、爱尔兰盖尔足球(Connolly et al.,2010)所经历的体育化与文明化探索,即运动规则更为严格、运动员的自控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
2 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策略
法国历史学家Chartier(1988)指出,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裂痕来源于观念和方法论的差异,体现了学科之间为争取学术优势而产生的斗争。很明显,两者的裂痕是对历史学和社会学及其子学科相互对话的蔑视和诋毁。体育学研究中也存在体育史学和体育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裂痕”。体育史和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融合在于结构/机制叙事与时间叙事的融合,体育史研究的理论取向与体育社会学的价值转向需要通过历史社会学重新概念化。在体育社会学中,尤其是在批判传统的过程中,采用历史视角开展相关研究几乎是“理所当然”(Maguire,2011)。因此,在体育学研究中运用历史社会学时,需要注意厘清价值理念、认清理论与证据的关系,以及把握可行策略。
2.1 厘清价值理念
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无自觉意识的研究者往往察觉不到自我认识受到了束缚,只会感到研究问题像卷入漩涡一样飘摇不定。这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尤为明显。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研究者往往不自觉地把研究限定在“业余体育”方面,因为他们认为职业体育不是体育,而是商业(Brundage,1956),选择职业体育进行研究会引发一定的学术争论。20 世纪70 年代,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在体育研究中大行其道,其主要表现为大量使用数理分析方法,过分关注结构性因素,忽视历史因素。近些年,我国体育界对电子竞技是否为竞技体育的讨论,莫衷一是。若20 世纪60 年代兴起的“生活方式体育”(lifestyle sport)是对主流文化的挑战(Wheaton,2010),那么电子竞技便是数字时代对传统体育形态发起的挑战。体育学的研究受到思想、理论以及方法潮流的左右。研究者的价值理念约束了其对体育问题的认识,研究者的学术立场越是被束缚,其对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便越会迷惑。一旦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所导致的价值判断就会出现割裂,从而影响到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选择。具体到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应在明确历史社会学的价值理念这一认识论基础上,选择有效的研究经验。
2.2 认清理论与证据的关系
迄今为止,运用于体育社会学之中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在以明确的理论认识为前提的基础上获得太多成果。体育史学相关研究鲜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而体育社会学研究则往往忽略时间叙事。作为全球史研究先驱者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多次呼吁采用一种过程思维来为历史研究提供信息。荷兰社会学家约翰·古德斯布洛姆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离对两者都是有害的,它使历史学家不必要地对结构的概念过敏,而社会学家则害怕处理单一事件(Goudsblom,1977)。由此可见,理论与证据、叙述与分析之间的融合在研究中至关重要。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试图建立几种不同形式的历史社会学模型,努力挖掘体育学术界经典的历史社会学问题,融合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史学两者都关注的研究议题。例如,历史变迁如何影响了体育运动发展?体育运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自我的体育运动经历?这些研究既可以从理论经验来解释,也需要从历史证据中总结规律,找寻理论。
2.3 把握可行策略
历史社会学的任务不仅要回答历史基本问题,还要解释事实。因果关系是历史社会学的本质追求,但不能把因果关系全部归结为某个人物的行为故事,或戏剧性的故事中那些特殊的、琐碎的情节。在一些体育学研究中,由于没有从事实解释出发分析因果关系,其研究结论也就不能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前期探索成果。但这种人物的行为故事以及戏剧性的情景或主题却提供了与体育相关的记录或文献,其本身就是体育的历史现象,而这一历史现象可以成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但需要切实可行的策略来描述、总结、分析甚至比较这些研究主题。西达·斯考切波(2007)在论述历史社会学方法论时,提及了3 个策略:一是将一般模型应用于历史,二是运用概念解释历史,三是分析历史中的因果规律。在体育学研究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可以聚焦到第3 个策略。该策略首先排除了模型的优先性,试图寻找最适合分析实际历史现象的假说,重点关注形成一种适当的、明确定义的对历史后果和模式进行解释的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既不是包罗万象的单一模型逻辑,也不是对每个单独时期和地点的复杂特点有意义的解释。相反,研究者认为偶然性中的规律,至少是有限范围内的规律,可以在历史中被发现(西达·斯考切波,2007)。对于在体育学研究中运用历史社会学而言,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套在过去的档案资料、史料故事之上,还需进一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出非故事性的过程,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关联以及不同时空脉络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严飞,2017)。
3 体育学研究中历史社会学的路径选择
体育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以及体育史学的理论转向使得历史社会学有了用武之地。在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史学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对体育的历史因素与历史结果的分析,还是注重结构叙事与时间叙事,都表明了历史社会学在融合相关学科,逐步形成体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3.1 理论导向:体育文化研究
体育文化研究是体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为了展现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想象力,选取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进行分析。葛兰西是继埃利亚斯、福柯和布迪厄之后,在西方体育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人物之一(Bairner,2009)。在体育社会学相关研究中,葛兰西的思想被文化研究倡导者广泛引用(Bairner,2007)。20 世纪70 年代,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指出,葛兰西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能开始认真对待包括休闲(leisure)和娱乐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流行文化(Williams,1977)。威廉斯的观点引发了体育研究者对葛兰西的关注。理查德·格鲁诺深受威廉斯的影响,使用文化霸权的概念来解释体育如何成为一个竞争领域,并阐明现代体育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发展其独特的制度和文化表达方式方面的根本差异。简单地说,格鲁诺展示了文化生活的规范如何成为阶级关系的核心。通过考察加拿大体育从殖民时代到20 世纪80 年代的发展过程,并将其与更广泛的阶级结构、国家、政治生活、军国主义和宗教联系起来,梳理出商业和“理性官僚主义”背后的动力,以及在加拿大体育界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Gruneau,1988)。另一位将葛兰西思想应用于体育社会学研究之中的开创者是约翰·哈格里夫斯,哈格里夫斯的著作《体育、权力和文化》,是常被引用的社会学著作之一(Rowe,2004)。哈格里夫斯认为,大众文化涉及“人民”(the people),尽管它不是任何特定群体的产物或占有物,但大众文化确实与工人阶级文化和从属群体文化有着令人困惑的重叠(Hargreaves,1986)。他还指出,葛兰西文化霸权的概念解释了体育等文化体验既具有剥削性又具有存在价值(Hargreaves et al.,2000)。哈格里夫斯关注英国大众体育文化的社会和历史分析,将文化霸权作为核心概念工具,认为体育是19 世纪阶级和文化斗争的组成部分,其中心论点是体育与阶级霸权密切相关(Hargreaves,1986)。格鲁诺和哈格里夫斯使用历史特定和文化特定的例子,展示了人类能动性与社会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
文化研究虽然描绘了体育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权力作用机制与动力,并在叙事方面具有不同于重视结构叙事研究方法的理论特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无法以静态的视角来进行。正因如此,体育文化研究在体现历史社会学想象力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判,即其缺乏规范的理论基准。因此,体育文化研究要尊重历史,在分析权力关系的同时,要强调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现实的丰富性。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为例,从“传统的发明”和“被发明的传统”两个概念出发,一些体育文化看似源远流长,实则是晚近的发明,甚至可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社会阶级变迁中被刻意选择、调整和使用的。霍布斯鲍姆指出,德国民族主义从旧有的自由形式向新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形式的转变,在德国国旗由黑-红-金色变为黑-白-红色的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明确(尤其是1890 年代),而非在组织当局或发言人的官方声明中。英格兰足总杯决赛的历史揭示了通常在数据和资料中未提及的城市工人文化发展历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等,2020)。因此,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融入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体育史研究尤其是聚焦近现代体育史的研究,应注重使用国家主义、社会变迁、阶级等结构叙事下的社会学分析工具。
3.2 方法导向:体育型构研究
埃利亚斯是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座上宾”,其型构社会学理论极大影响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尤其是“莱斯特学派”(Leicester school)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埃利亚斯依据型构社会学理论研究竞技体育中的暴力问题,认为型构(形态)的概念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比社会学现成的任何概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被我们称作“社会”的东西,它既不是从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个人特征中抽象出来的,也不是一种脱离个人的“体系”和“整体”,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互为依存关系的网络(诺贝特·埃利亚斯,2013)。型构社会学超越了欧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它不是美国社会学所要求的中范围理论,而是形成了一种从历史社会学到一般社会学的理论。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利用“体育经验者-社会学考察”(对象-方法)分析图式进行的研究占据主流,而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其他研究领域则主要以“社会学考察-域内经验者”(方法-对象)的分析图式为主导。对此,埃利亚斯提出需要思考政治、经济、宗教等其他研究领域所采用的逆向式方法,能够给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带来何种启示。事实上,这一思考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埃利亚斯体育型构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即“社会学考察-体育研究”(方法-对象)的分析图式不由个体的经历或价值观构成,而由他的型构社会学理论构成。具体而言,埃利亚斯的体育型构研究不以体育的当然性为前提,重在考察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状态下产生的体育文化,而这一体育文化会随着不同个体所编织成的型构(相互依存关系产生的文化和状况)发生变化,以此展现出该体育文化所表达的各自不同的意义,如此就能有效把握住体育的文化特性(王松,2023)。
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理论对竞技体育现象的研究,是体育社会学探索方法论的开端,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1)体育社会学研究需包含体育的社会性结构和社会学功能,而不能把体育看作固有的社会实际状态,必须厘清它和其他社会学现象之间的关系。2)与第一个论点相结合,将体育的历史看作远古乃至古代以来的自律性、内在性的发展,或者把近代体育看作古代体育的复兴。以体育暴力为例,人们普遍认为竞技体育的形成与暴力应该毫无关系。这样常识性“感觉”的确立,在于现代人会觉得从事体育的人对暴力都非常厌恶。埃利亚斯认为有暴力问题的人本来就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疏远(厌恶感的历史原因),这是一种长时间后形成的感觉,其过程也是有迹可循的。埃利亚斯采用型构社会学研究竞技体育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竞技体育将暴力视为禁忌的同时,也将其作为身体文明化的象征。另一方面,竞技体育则被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合法性暴力”,即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平常不允许发生的身体暴力行为,这赋予了它可逆的文化特征。埃利亚斯认为,拳击比赛时人对攻击欲的节制体现了文明的发展结果(诺贝特·埃利亚斯,2013)。综上,竞技体育中的暴力问题应放置于历史社会学的背景下来审视。
4 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在中国学界兴起并备受关注,主要涉及学科边界、学科概念、研究方法、发展脉络以及实践案例等方面的学理性探究,已然呈现出研究内容与日俱增和研究范围日益延展的学术繁荣景象(严飞 等,2021)。历史是中国社会学传统的母题,而这些将历史作为母题的本土社会学研究,则构成中国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孟庆延,2023)。进入新世纪,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区域史等分支学科兴起,“历史的想象力”愈发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素质,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得以发展。特别是最近十余年,由北京大学牵头,围绕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工作坊相继开展,并于2017 年筹建了中国社会学会历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可见,我国的历史社会学已展现出清晰的学科定位和范式革新(严飞,2019)。历史社会学起初并不像历史研究那般对史料如此苛刻,只是利用“历史取向的研究路径”。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历史社会学愈发注重“历史”在场(应星,2018),即更加注重历史叙事。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推动我国社会学界与史学界回归本源,倡导融合,渐次形成了本土化的研究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历史社会学的关注不断增强,推动了体育学界对历史社会学的引入与应用。
4.1 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现状
早在20 世纪90 年代,易剑东(1996)提出要将社会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引入我国近代体育史研究之中。事实上,当时我国体育史研究也确实需要新的理论介入,其中就包括沃勒斯坦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以此突破20世纪80 年代以来长期主导我国体育史学界的“五个社会形态说”(郎净 等,2005)。但是,这并没有引起我国体育学界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广泛关注,仅有少数学者将研究视野转向历史社会学。
从理论挖掘的角度来看,王智慧(2021a)在研究口述史与体育记忆的建构机制中提出,口述史作为体育记忆研究的方法,不仅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社会学的结构意义叙事,还融合了历史学的过程时间叙事。从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角度来看,历史社会学范式/视角被用于探讨国术馆的摔跤活动对民国时期中国摔跤发展产生的历史影响与意义(王晓东 等,2017)、探究两宋都市民间体育结社的生成、建构与特征(丁洁 等,2020)、阐释《体育之研究》及其时代意义(刘爱,2023),以及追寻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差序共竞”的格局生成(曹胡丹 等,2023)。此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常涉及历史社会学的展望,如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对相关史料及现世文化遗存等展开田野考察及探究(陈连朋 等,2022);从社会变迁与村落衰微的变化中,探寻导致民间传统武术日渐衰落的重要因素(胡昌领等,2022);提出历史社会学与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结合的研究思路(张博,2023)。
近些年来,我国学界掀起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热潮,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相继出版《历史社会学的技艺》《源流:历史社会学的思想谱系》《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双学科视角下的理论探索》等著作及系列历史社会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等期刊长期关注“历史社会学”主题(郭台辉 等,2020)。相比之下,体育学界在历史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空疏化”,导致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发展较为滞后,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与足够的汇整史料的耐心。究其根本在于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尚不具备完整的知识一致性,至今在理论建构方面没有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分析工具或研究范式,在方法运用方面缺乏体育社会学所提倡的中观视角,而且一些带有社会学本质属性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其研究者在运用体育史料时往往不如体育史研究者娴熟,且对一手、二手体育史料的理解与把控也没有体育史研究者透彻与精准,导致历史社会学至今难以被体育史研究接受。此外,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史相关研究过于注重叙事,进而忽视了史学理论建构。体育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史对于现代新史学理念、主张、方法的疏离。正如孙淑慧等(2021)所指出的,灵动且极富个人体验的“体育”,事实上是宜于运用现代新史学范式进行研究和书写的。但我国体育社会学相关研究缺乏历时性的思维,而对近代竞技体育起源、传播、价值取向等议题却迫切需要借助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
4.2 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特征
历史社会学在应用于我国体育学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如下两方面的特征:其一,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碎片化”与“连续性”;其二,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融合性”。这些特征既回应了反思现实、时间序列以及强烈的批判性,也反映了当前历史社会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运用还不够成熟。
“碎片化”是指我国体育学界尚未出现系统性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以体育社会学为例,现有的几部著作(含译著),如《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视点、方法》《身体、社会与体育:西方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体育》《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体育与社会学》《论文明、权力与知识》等,虽然或多或少涉及埃利亚斯的思想在体育学研究中的阐述,但是缺乏以历史社会学为论题的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历史社会学为方法的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以及对诸如埃利亚斯等历史社会学家的体育思想研究。此外,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看,运用历史社会学的体育学研究成果偏少,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研究。
“连续性”是指近十多年来,我国体育学研究持续关注历史社会学,初步形成了相关研究内容。在关于体育概念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方面,有对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历史社会学维度的考察(陈怡莹 等,2020),历史社会学视野下游戏的形态演变分析(郭振,2010);关于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在体育研究中的引入与应用研究方面,有运用型构社会学分析体育暴力(侯迎锋 等,2010)、解读竞技体育情感(郭振 等,2012)、阐述埃利亚斯体育化概念(郭振 等,2016;王松 等,2022)、梳理埃利亚斯体育竞技核心理路(李洋 等,2018)、分析街舞运动的文明的进程(王珊珊 等,2018)等研究。由此可见,历史社会学为体育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学想象力,对体育学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融合性”是指历史社会学促进了体育史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融合。社会学与历史学从分离走向融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研究的融合,历史社会学则是促进这一融合的必然。虽然体育史相关研究率先提出引入历史社会学,但是,实际上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更为注重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体育史和体育社会学的藩篱,把时间叙事和结构叙事融合起来,两者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学科交叉,而是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突破。例如,有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武术现代性的内涵、起源及其演进(廖上兰 等,2022);在体育口述史与社会记忆之间建立联系,实现体育口述史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及方法转向(王智慧,2021b);提出计量史学也将成为体育史学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促使了体育史的社会学化(王俊奇,2014)。
5 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发展前景
无论是斯考切波把二战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归纳为3 种策略,还是保罗·皮尔逊(2014)提出的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3 种方式(因果分析、模式解释、提炼方法),都是西方视角下的历史社会学策略。贺雪峰(2006)在论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构建时指出,“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基本上所有的现象都是多因多果,而且这些多因多果未经过充分的定性研究。在这种前提下,许多研究却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由此,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策略应注重方法、立足中国议题,实现理论本土化。
在研究方法上,关注叙事融合。模式解释、过程阐释与因果分析已成为20 世纪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3 种主要策略(郭台辉,2019)。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而言,应注重“历史取向”,从关注体育社会问题的结构维度到时间历史与过程维度,开展体育社会史层面的研究,从而“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现代性”(严飞,2017)。对此,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应注重方法论研究。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融合社会学的阐释/解释与历史学的叙事(赵鼎新,2019b),从而为体育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即郭台辉(2019)指出的“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层次可以超越叙事、阐释、解释之间的策略对立,转而使之成为一个实—名—实的逻辑递进和抽象化过程”。例如,对体育口述史的研究可以以口述的历史叙事策略为基础,通过非历史性的阐释上升到解释,从而在相关研究中有效结合结构性/解释性叙事与时间性叙事。
在研究内容上,立足中国体育议题。中国新兴的历史社会学相关研究需立足于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转向中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与中宏观层次的理论分析,在承认主题与方法、历史与理论之间“适度紧张”的基础上再使之有机结合起来(郭台辉 等,2020)。在此基础上,历史社会学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注重中国话语下的体育学研究。中国社会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身的社会底蕴,由此衍生出诸多独特的体育议题,如民族传统体育代表的体育文化、体育组织的变迁机制、近代竞技体育的起源与发展、中国足球的历史性与现代性、体教融合背景下的青少年体育等,这些议题呼应了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文化研究、制度演变、民族与国家等主题。比如,曹胡丹等(2023)从“差序”入手,指出中华竞渡文化谱系呈现出一种“差序共竞”的格局。该研究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明土壤,为后续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启示。再以中国足球相关研究为例,体育学界聚焦于足球技战术的微观研究以及足球发展规划的宏观研究,缺乏对中国足球历时性的思考。应把中国足球置于中长时段,从时间叙事出发,研究足球文化这一中观议题;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足球的历史文化,回应当下中国足球发展的症结。
在研究思路上,立足理论本土化。中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出现两种明显的研究取向,一种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另一种则强调重返社会学的古典时期,同时借鉴中国自身学问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学术传统,进而将历史社会学作为重新激活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资源(孟庆延,2020)。后一种取向勾勒出了我国体育学中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实践形态,即扎根体育的本土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历史社会学研究,亦是在推进中国本土体育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甚至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中国体育学理论根植在中国特色体育实践的沃土上,在强调和回答中国体育实践重大问题的关切中发展,由此形成的通过体育学探索中国体育问题的基本理论视角,具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和理论特色(杨桦 等,2022)。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为体育学研究运用历史社会学思维和方法带来了机遇,虽然我国体育学界已经对引入与应用历史社会学进行了不断的尝试,但仍需进一步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上进行探索,围绕独特的体育议题展开深入研究。
6 结语
赖特·米尔斯(2005)指出,没有哪门社会科学能被假定是超越了历史的。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贯穿于社会学发展历程,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体育社会学中所体现的历史社会学特征亦是如此。虽然西方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史学相关研究在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获得了一定成功,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对体育学研究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从根本上探索历史社会学“为谁”和“为何”两个元问题,否则便难以从认识论上彻底建构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史学的学科体系。从我国历史社会学研究来看,还没有把“体育”作为其研究内容,实际上限制了在体育学研究中运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可能。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也需要在学科研究上寻求理论突破。本研究没有触及体育史中的体育社会史以及体育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鉴于此,能否找到一条从体育社会史出发的研究途径,在体育史研究中设定具体主题,并展示其成果,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考察、评价这些主题和成果,探寻新的研究方向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