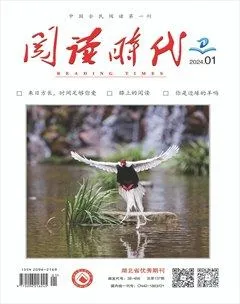江州寻陶潜
钱红莉

字面意思看“九江”,无非九条江河汇合处。实则不然,这里的“九”当虚词解,是众水汇合之意。此地更有古名——江州,氤氲着无限诗性的一座小城,一条大江傍城而过。
陶潜在此做过江州祭酒。别人在陶潜的田园诗里读出了闲适恬淡,我读出的却是困苦忧惧——年岁愈长,愈甚。在柴桑的陶渊明纪念馆,最后一爿小屋内,玻璃长柜里陈列一幅陶潜山居图卷,解说员大姐热情招呼众人来看,指这里,复指那里,末了,进入忘我之境,大段背诵《归去来兮辞》,抑扬顿挫,令独自面墙而立审视陶潜一生行旅图的我,忽然泪水上涌。彼时此刻,似与他心意相通,体会着他精神上的困苦、愤激。这首辞赋,是陶潜的精神自况,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读它,如同温习着他高洁的人格。故欧阳修才要说,《归去来兮辞》是东晋唯一文章。诗赋文章向来是一个人的灵魂自传,映照出的是作者的心性、骨骼。
我最佩服的是陶潜的坦然自若,你看《归去来兮辞》小序写得何等坦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时间之河顺流而下,一路自晋、隋、唐,到宋,有了一个苏轼,他被一贬再贬,何等困苦受辱,怎么就不曾崩潰过?他谪居黄州时,便早早找到了精神支柱陶潜啊。苏轼生命中的这一段,虽说早前于史料中厘清过脉络,但,直至真正伫立江畔眺望对岸黄冈,方才恍然有悟:黄州、江州两地何等之近。黄州当地政府也曾辟一片荒地给苏轼,可惜地力欠肥沃,根本种不出粮食。东游西逛排遣苦闷的苏轼,日日饮酒迟归。时不时乘扁舟一叶,过江到访庐山东林寺、西林寺,此地正是陶潜故乡,一下抓住了灵魂知音。日后,他自黄州、惠州、儋州,一路书写“和陶诗”不辍。或许,苏轼不折不屈、随遇而安的性格,正是为陶潜精神所滋养。《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宇宙观,不正呼应着《归去来兮辞》中天地自然的和谐吗?
继续往柴桑乡下深入。午餐在村里吃,农家门前便是南山,视野开阔,储养着满谷满坡野草闲花。我把南山看了又看,天是空的,山也是空的,生死一场,可不就是“终归当空无”?陶潜入公职13年。41岁时,受叔父引荐,独自一人往彭泽,履任县令一职。履职80余日后,乡官前来视察,旁人令其束带迎候,深觉灵魂受辱的他,忽然恼了,索性辞官回乡。这个乡,便是柴桑——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生辉之地。一个文人,岂能种好地?难免窘迫,内外交困。但,你看他的田园诗中丝毫不见怨尤,孜孜白描天地自然之美。偶尔的一次低落情绪,见《乞食》诗。长期营养不良的他,一日饿得心慌,敲了陌生人家的门。人家一看是大诗人,欣然开门纳客,恭敬招待。末了,他又添愧疚,怅惘一声,“我不能像韩信那样报答一饭之恩了”,何等自责啊。一个人为了不违逆自己的心性,执意溺陷于世俗窘境之中,得要付出多少孤勇?
中国诗歌史中,三篇辞赋不能绕过去:屈原的《楚辞》里,有愤慨激烈;陶潜的《归去来兮辞》,转为冲淡平和;苏轼的《赤壁赋》,彻底明心通透。这三人的诗文内核中有一种共通的东西,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温暖心肠,以及不曾折屈的气节。
回程时,天已透黑,西南方向隐约有群山剪影,暮霭虚白,庞大绵长,沿着山脚游走……此情此景,正应了陶潜那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洪荒宇宙中的时间轴,说长也短,说短也长,江州这广袤的一片土地,都是陶潜的故乡啊,他所热爱的天地自然之景,我也领略过了。日升月落,星挪辰移,而人类的一颗诗心大抵是相通的。
(源自《新华日报》,王传生荐稿,有删节)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