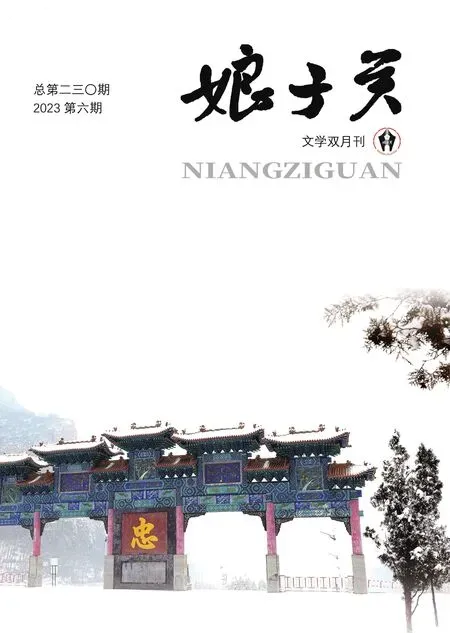李建永散文小辑
◇李建永
阿Q的读法
我注意到,近期有几个“顶流作家”做视频号,他们放下身段,接着地气,用几分钟的时间,说些家长里短的话,道点花絮逗乐的事,有时也会“深刻”一下,不时还会“剧透”几句,“我的朋友胡适之,那个时候……哈哈哈”,反而比正经八百高谈阔论更有意思。
那天晚饭后,我躺在沙发上划拉手机,忽然听到某“顶流作家”说,“阿寇”如何如何。我赶紧正襟危坐,端正态度,坐起来盯着视频聆听,“顶流”昂着头,正讲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呢。“顶流”一口一个“阿寇”,把我整得——也可以说是震得——一愣一愣的,颇不自信了。我从书架上取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将收入《呐喊》的《阿Q 正传》郑重打开,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多年做编辑养成的职业习惯,竟然还找出一个错字——“赵太爷”写成了“赵大爷”(第500页倒数第7行),呵呵!
鲁迅先生《阿Q 正传》“第一章 序”,开篇写道:
我要给阿Q 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这段文字共有6 个“传”字,很多读者被它们“转”得不轻。亲戚和朋友有多人问过我,到底读“撰”呢,还是读“船”呢?我说,就我理解,第一句“我要给阿Q 做正传”的“传”自然读“撰”;“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的“传”也读“撰”,只有书写塑造不朽的人(为之立传),才可能成就不朽之文;“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第一个“传”即“人以文传”读“撰”——重要历史人物是靠传记来记载塑造的,第二个“传”即“文以人传”读“船”——文章又是凭借其所塑造的重要历史人物而流传下来的,第三个“传”即“究竟谁靠谁传”仍然读“船”,指“文”与“人”的传承及流传;最后一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的“传”读“撰”,即鲁迅先生为阿Q 立传。如果不把这几个“传”字的读音搞搞清楚,还真有可能把人“转”晕!
鲁迅先生接着写道,“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通学问次第“输出”。“第二,立传的通例”,首先是阿Q 姓什么的问题,某次阿Q饮酒后似乎说他姓赵,但第二天被赵太爷抽了一个嘴巴子,大骂“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阿Q 的姓便不确凿了。第三,轮到阿Q 名字究竟叫什么的问题,幽默大师鲁迅先生这样写道:
我又不知道阿Q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 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
阿Q 这个名字,属于典型的旧中国农村光棍汉的“有名无字”,大家见面都叫他阿Quei——我姑且给他写作“阿柜”吧,但到底是哪个“柜”字呢——“桂”呢?还是“贵”呢?人们却说不准确,鲁迅先生也说不准确。当然,先生笔下的阿Q,是一个典型人物,是一种艺术创作,是“故意”让它说不准确的。《阿Q 正传》发表(连载)于1921 年12 月4 日到1922 年2 月12 日的北京《晨报副刊》,而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36 年后的1958 年2月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并正式颁布实施的,所以“阿柜”的“柜”字,其时还不能准确地拼写为guì,只能用“洋字码”拼写为读音近似的Quei。当然,这也是鲁迅先生为幽默起见而创作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农村,绝不会有一个叫“阿Q”的人——我说的这个Q,就是26个英文字母的Q,也就是那位“顶流作家”口中的“寇”。所以阿Q 应读作“阿柜”,《阿Q 正传》也要读作《“阿柜”正传》。在《阿Q 正传》里,还有一个人物叫小Don,简写为小D,也不能读作“小笛”,而要读作“小同”。这是很确切的。因为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得明白:“他叫‘小同’,和阿Q一样。”
我的夫人对我说,如此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一位小说家,难道没有读过《阿Q 正传》原文吗,文中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叫阿Quei吗,鲁迅先生还一直“纠结”于写作“桂”还是“贵”呢,并未有一字提到“阿寇”,读作“阿寇”,他是怎么发明创造的?
我说,这也难免。我童年到整个少年时期,所能大张旗鼓看到的书,多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全集》(单行本)。我问过村子里当民办教师的五叔,《阿Q 正传》里的阿Q 怎么念?五叔说,念“阿克油”。所以,我一直“克油”到高中二年级,才让我的语文老师马汉贵先生“治愈”。马老师是我在课堂上听到用普通话朗读《“阿柜”正传》的第一位语文老师。一个人私下里念个错字不打紧,但作家在作品中写白字,在视频里念错字,并非小事情。
也许有人会说,这纯粹是“吹毛求疵”。其实并不。这不像孔乙己的“拽”,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或者读书人以“偷”和“窃”相蒙混过关的问题。这是一个是与非、黑与白及其语言行为误导社会大众的原则性问题。这些年,我写过好几篇类似的文章。譬如,指谬某著名作家把“致仕”(退休)解读为“搞个官当当”,这完全是满拧嘛。更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人专门在报纸上撰文,说某大家把“致仕”解为“搞官”,也是“约定俗成”的。至于谁和谁“约定”的,又是怎样“俗成”的,并未解释清楚。“俗”是够恶俗的,但这样的解释却不“成”。谬误这东西,人的名头越高,影响越大,“流毒”越深。我写《阿Q的读法》,就是担心那些动辄吸引数以百万千万粉丝计的影响甚巨的“顶流作家”,将“阿寇”之类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带歪视频前的观众、听众和读者。《诗经·王风·黍离》说得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认 屐
读《南史》列传,发现在名字末尾缀“之”字的人物颇多。诸如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南朝宋、齐时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祖冲之,以及徐羡之、毛修之、傅弘之、赵伦之、王裕之、垣护之、褚裕之、綦母珍之等“之”名者,足有六十余人。
其中,南朝隐逸高士刘凝之,不喜做官,不慕荣华,平日里朴质俭苦,乐于救助“有饥色者”。一次走在路上,“有人认其所著屐,笑曰:‘仆著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此人后田中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南史·列传·刘凝之传》)某人丢了屐,咋瞅咋看凝之脚上屐,就是他所丢失的屐。凝之不以为忤,说自己的屐已穿旧,笑呵呵从家中找出一双新屐给他。后来此人从田里找到自己的屐,将凝之屐送还,凝之摆手说,不必了。
战国时期的《庄子》中即有“木曰屐者”,并说木屐制作者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介子推抱树烧死,晋文公伐以制木屐也”。至于晋文公到底是不是我国历史上木屐的第一发明者,已不可考。东汉许慎《说文》云:“屐,屩也。”东汉刘熙《释名》亦云:“屩,草屦也。”屐(jī)、屩(juē)、屦(jù),都是鞋子,既有木屐,亦有草屦。鞋子这东西,未必有多贵重,但它是人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人的“生存底线”。俗话说,脚下没鞋,穷了半截。又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见,一旦无鞋可穿,人的冒险性与革命性,就会噌噌地往上“冒顶”。譬如,鲁迅先生笔下土谷祠里穷得叮当响的阿Q,就骂骂咧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阿Q 正传》)
南朝的另一位高士沈麟士,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志,早期以编织竹簾为生,“织簾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簾先生’”。麟士与凝之一样,都有被怀疑“窃屐”之经历。“尝行路,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南史·列传·沈麟士传》)啥叫“即跣而反”?就是把邻人错认的自己脚上的屐,毫不犹豫地脱下给他,自己却光脚走回家。
东坡先生对两则“认屐”故事做过评判,称“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苏轼文集·刘沈认屐》)。至于为什么呢?坡翁未做进一步阐释。想必是对待还屐的不同态度而言的吧。被怀疑“窃屐”,刘、沈二君均未做过解释,便将屐付与;但当还屐之时,凝之“不肯复取”,麟士“笑而受之”。可能坡翁想到的是给对方“下台阶”的问题,乃至刘、沈二君被怀疑“窃屐”是否计较的问题。不过,也可以将凝之“不肯复取”,视为“不忍复取”。可不是吗,某人误认凝之所著屐,凝之即对他说:“仆著已败,令家中觅新者备君。”连家中新屐都肯给他,还会把旧屐拿回去吗,更不会计较其他。
然而,这“两桩公案”给我的启示却很深刻。多年来写杂文,被周围不少人误以为“针对”他,“挖苦”他,“内涵”他。其实,倒也未必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人,可能既有张三的眉眼,也有李四的声口,还有王五赵六的心肺肚肠,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让读者强烈地“意识到”“他者”和“自我”的存在,这正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和艺术移人的价值所在。文章乃公器。杂文,剜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病灶”和“毒瘤”,但讽喻、批判、针砭的却是一种独特而又具有共性的人情世象。“认屐”就是寻找丢失的“自我”。如果有谁感觉在下所写的“屐”,就是他足下所失之“屐”,对号入座,上门认领,“一翁衰病,努力攀筇屐”,这对于一个杂文创作者来说,是最高礼敬!如有“雷同”,无上荣幸!
格 局
老三和夫人几十年置办家具的历程中,最后悔的事有两件:
一件是十年前在通州家乐福购物中心,过道旁边有一家小而精致的家具门面店。夫人看中一个红木躺椅,高大而气派,华丽而厚重,微鼓而硬实且富有弹性的绒线靠背垫,图案绣制精美,有如迪拜挂毯。老三躺上去颤动晃悠几下,下来跟夫人悄悄说,真舒服,若躺着看书,更舒服。夫人说,买下吧。老三说,六千块,有点贵,晾晾再说。过两周又问,还是六千块,一文不减。老三说,再晾晾。过三周再来,撤店了。哎哟!把老三夫人后悔的。
另一件是在丽泽桥某家具中心,十七八年以前,夫人和老三同时看上一辆金丝檀木小酒车,车身三尺长,一尺半宽,二尺来高,分上下两层,雕工精细,木质精粹,灯光下,每一缕金丝都闪烁着它的气质和价值。夫人问,怎么样?老三说,好是好,但家里没存几瓶好酒,还要买一辆“豪车”拉来拉去,何况一个小酒车大几万块,太贵了吧。夫人笑着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我想用它盛书,把新购的书放进去,推在床边,晚上躺下,尽可信手翻阅,自在品赏;写文章的时候,将相关资料和书籍搁上去,推到书桌旁,随手取用,豪华而美气,方便而实用,何乐不为?老三何尝不动心,只是觉得有点偏贵。老三向来自信是“砍价高手”,便说,晾晾。那时尚无微信扫码支付一说。老三和夫人心里惦记着,隔天怀揣重金再去探望,小酒车了无踪影。老三扼腕长叹,只好打趣说,天命不在我。
信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十大几年过去了,这两个搁在心尖儿上的物件,再未从老三和夫人的眼皮子底下经见过。
还有几件挂记心头的物事。譬如,老三二十五年前在中国美术馆西侧沙滩街边店铺,看上一串翡翠珠子挂链,最大的翠绿圆珠有莲子那么大,自下而上,渐次而小,挂在脖子上可以垂到肚脐,质地水色均上乘,只要四千块,夫人却不舍得买。从此后,时乎时,不再来。再比如,二十年前,老三偕夫人逛通州某玉雕店,看上一枚洒金皮翡翠大扳指,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老物件,老三戴在左手拇指上,熨帖而华贵,左看右看,摩挲把玩,天设地造,得此新欢,店家开价三万八,并说这是缘分。夫人规劝老三,一个文人记者,戴着一个玉疙瘩上班,出来进去像个王爷,让别人怎么看你呢。从此后,青鸟殷勤为探看,时不再来。且不说这两件玉玩,多年后已然增值十几倍甚而几十倍,仅仅是对于心仪的“这一个”艺术品失之交臂,便令人久久怅然。
唐代无名氏《金缕衣》诗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不过,在老三看来,人生太匆匆,莫待花枝空,既要惜取少年时,也要珍惜金缕衣。老三母亲常说:“要吃趁牙口,要穿趁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剁手”时要“剁手”。此之后,老三和夫人商定了一个规矩,若是两人同时看上的好物件,首先要实行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
人常说山西土老财是“穿得烂,走得慢,腰里别的真圪蛋”——“真圪蛋”也有说“金圪蛋”的,总之是有钱而不露声色又抠门儿。老三深得此中三昧。但老三腰里却又没几个实实在在的“真圪蛋”,这就需要实行“家庭计划经济”。老三跟夫人说,好光景要细盘算,好钢使在刀刃上。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爱就有不爱。老三第一不喜欢买豪车嘚瑟,第二不喜欢满世界游玩撒钱,第三不喜欢购买各种理财产品。前些年特别流行“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之类的“金句”——诱惑人们购买各种外来“基金”,老三却说,“你不理财,财不坑你”,它们割不了老三的“韭菜”。
有不爱必有所钟爱。老三第一爱买书,有价值的好书(特别是古籍经典方面的)一次买两套,一套自己看,一套封存起来,留给女儿和未来的外孙们看,他说,“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老三第二爱买房,一旦腰里有几个“真圪蛋”,周六日便到处逛游看楼盘,他喜欢在北京买房,最喜欢在“紫气东来”的通州买房。老三擅长砍价,2000年通州果园一平米一千五百块,2006 年通州梨园一平米三千二百块,你说值不值?老三第三还爱买一点点古玩和家具,名之曰“雅趣”,这一点与夫人志趣颇相投。前些日子,夫人跟老三说,你习惯盘腿坐着写文章,想给你买个红木小炕桌。
好说。老三立马打车,偕夫人直奔附近六七公里的运乔建材城。三年疫情未逛此城,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运乔建材城即将改换门楣——更名为居然之家,听说很快要重新装修。进门一看,黑灯瞎火,已是半壁“空城”,仅有几家规模较大的红木家具店硬挺着,“含泪清仓大甩卖”!老三窃喜,和夫人先问红木小炕桌,再看红木大衣柜,然后将目光落在两套组合书柜上,一组乌金木的,三件套,另一组黑檀木的,是两件套的。老三跟夫人咬耳朵说,这两套书柜,如果砍到一万块,就拿下。夫人说,不可能,标价都在三万上下,怎么可能砍到一万块?老三说,试试呗。牛刀小试,手起刀落,折冲折中,片时成交。老三单位有几个年轻女记者,曾目睹老三砍价风采,鼓动他写一部《砍价宝典》,以案说砍,笑傲江湖。老三夫人也说,真奇怪,售货员小姐姐跟咱家老三谈价码,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就反过来帮着老三说话了,能砍不下来吗?
砍下了,犹豫了。夫人私下对老三说,原本只说买一个小炕桌,现在倒好,又要拉回两套组合书柜,便宜归便宜,可是往哪里搁呢?老三转头对店家说,我回家丈量一下卧室尺寸,两天内送货。当晚正好与老同学骏医生夫妇两家一起吃饭,三杯落肚,说起书柜事,骏医生夫妇对黑檀木书柜颇感兴趣,看过图片,打算盘下。散席回家,夫人拉着老三从客厅到书房到厨房到各卧室转了一圈儿,说,除了书柜就是书架,你看看哪里还有空间吧!老三打着“官腔”说,改革嘛,就是要挪动一些坛坛罐罐桌桌椅椅,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格局,给新生事物腾出充裕的生存空间。
老三回到卧室,泡了一杯“熟普”,对夫人说,尼采讲过,“格调越高,成功机会越小”,但我认为,格局越大,生存空间越宽广;讲求格调需要格局,需要人生智慧,古贤讲“仁义礼智信”——“智”是最难阐说的,可它与人生联系又是最紧密的,生活就在于雅俗之间,取舍之际。老三呷一口茶,接着说,譬如买这套乌金木书柜,也就等于平日里和朋友们喝两三顿酒的饭钱,均属于快乐消费。夫人说,你就爱穷大方。老三说,我妈说过,“过光景不得不仔细,宴宾客不得不大气”,这是传统的待客之道;不然的话,大方地请人,小气地招待,没人会原谅你的。老三扳着指头数说,咱这个卧室的电视墙(老三家所有地方都没有电视机)宽度是460 个(厘米),现在摆着的电视柜(系装修公司赠送品,上面堆满书籍)长200 个,宽50 个,高56个,电视柜到床头之间的过道宽度为68 个。如果置换成新买的三件套乌金木书柜,长300 个,高220 个,宽38 个,书架到床头之间的过道宽度为80 个,比之前拓宽12 个;关键是把原来堆放在电视柜上的书籍整齐上架,整面墙看上去,既美观又雅致大气。夫人问,那电视柜搬到哪里?老三说,原来客厅大写字台与南边窗户之间那张放宣纸的台桌有100 个宽,置换成50 个宽的电视柜,还可以腾出一条50 个宽的小过道儿;这样,不仅卧室拓宽过道,客厅又开辟出一条新路,全新地规划出了咱家的“一带一路”。
夫人呵呵笑着说,那张放宣纸的台桌挪到哪里去?老三说,隐藏在大写字台下面,仍可以放宣纸,桌子底下套桌子,就像俄罗斯套娃。夫人说,说了半天,只顾谈书柜,却忘了买炕桌。老三说,已经和黑檀那家店说好,送书柜的时候,顺便给咱带三个小物件——一张黑檀小炕桌,两把黑檀小方凳,各一千块,据店家说,砍成了白菜价。
送家具一般在傍晚时分,厂家赌你看不分明。不过,老三检视得很周到很仔细。三件套乌金木书柜搬进卧室,电视柜挪到客厅南窗底,黑檀木小炕桌摆在双人床中间,一双方凳放在床边。一切安置就绪,再将所有书籍码上书柜,清理完毕,力竭精疲,简单洗漱一下,倒头便睡。次日清晨,夫人醒来,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斜洒在整面墙的乌金木书柜上,显得雅致,大方,富丽,气派。她忍不住赞叹,真好哎!老三迷迷瞪瞪发问,啥好啊?夫人笑着说,改革好,心情好,书架买得好,整体布局好——噢,是格局好!
母亲碎碎念
1
母亲个头矮小,只有一米五高。但母亲“能量”巨大,底气足,胆气豪,嗓门高。由于父亲是抱养的,据说“命硬”,三岁时养母仰药(洋烟土)而死,十一岁养父因病离世,父亲十岁就去离家三十多里的安祥寺村当小长工,包吃包住之外,每年还能挣回七个银圆。母亲虚岁十八岁那年,从十里外的南口前村嫁到高庄村,跟着十七虚岁的父亲打拼一生。父亲打小善良,或者说是懦弱,受人欺负之际,孤苦无依,万般无奈,默然洒泪。俗话说:“没娘的孩儿,天照顾。”母亲在家顶起了天!母亲晚年多次对我回忆说:“那会儿,哭得比尿得多。”
2
母亲发誓要多生几个儿子,起好名字才生——给儿子们取名“和、平、永、远”,寄托着美好的希望和强大的力量。母亲总共生了八个儿女,姐姐最大,大哥,二哥,我,弟弟,最末一个小弟送人了。据母亲说,其他儿女生下来奶水都充足,但生我之后奶水寡淡,我整日里哭唧唧的,紧挨着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就没有“抬掇”起来,让我吃了本该属于生“龙凤胎”弟妹的“口粮”。“吃接奶”的这段特殊经历,使我身体从小就很健壮;然而,这也成了我多少年来心底里感到最深的罪过。还有,生我之后,姐姐跟着受累。本来母亲是让儿女们累苦了,不打算“抬掇”起我,可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哭着闹着想要把我留下,正巧用破布裹着的我,一哭一蹬小腿儿,露出了黄红色的小膝盖。父亲说,你看就像个鸡蛋。姐姐趁机大哭。母亲妥协了,流着泪说,留下了他,你就得看他。尚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姐姐,从此辍学带我。后来有城里人,知道“没有‘抬掇’起来”,是溺毙的委婉说法,便叱咤我的母亲“造孽呀”。那是他不了解什么叫穷人的日子,什么叫度日如年。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好人老说病人虚。”我理解我的母亲。我深深感恩父母,还有姐姐,千辛万苦把我拉扯成人。
3
俗话说:“大家分穷,小家吃穷。”又说:“穷人肚大。”“养家糊口”四个字,重如千钧!那时父亲一个人劳动,拉扯着五个孩子,把嘴“糊”住就很难。作为孤儿,父亲自幼缺疼少爱,便把全部疼爱给予儿女。母亲常回忆一桩往事:某年父亲和我二哥一起去县城,父亲给家里每个人买一个“干锣儿”(类似烧饼),但自己舍不得吃,从四十五里开外的县城步行回来,走到离村二里的小柴棚村时晕倒了。二哥赶忙到人家讨了一碗水喂父亲,父亲醒过来歇一会儿,继续走回村,没舍得咬一口“干锣儿”。母亲何尝不是!母亲的活计更重。白天压碾,把两三天内要吃的米呀面呀,都会碾出来。我五六岁未上小学之前,经常被母亲逮来压碾,在碾道里推着碾杆转上大半天,头晕得天旋地转,有时候看见碾子就头疼。每天晚上,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全家人一年四季要穿的单的裌的棉的衣裤和裌腰腰、棉腰腰(类似坎肩),以及单鞋、棉鞋和鞋底,都是母亲一针一线连明昼夜缝制出来的。俗话说:“娃们外边走,带着娘的手。”说的就是这份甘苦;当然还要讲究穿得齐楚,好看,排场。民以食为天。每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加一点干粮,就着“烂腌菜”吃。午饭和晚饭,主食大多是玉米窝头、高粱饼子或黍子糕,平日里的“副食”,就是一大家人一锅烩菜,白菜、土豆、胡萝卜、倭瓜和西葫芦等,有时加一点粉条和豆腐,那就很稀罕很丰盛了。七个碗,在炕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母亲掌勺,往每个碗里盛菜,我们虎视眈眈地望着,其中六个碗是平均分配的,只有一个碗,刮一点锅底剩菜剩汤,那是母亲的一份。
4
都说严父慈母,我家是严母慈父。母亲脾气暴躁,经常没好气,我又是吃过“接奶”的娃,有无限的精力淘气,挨打是不可或缺的。母亲上树特溜儿,到六七十岁时腰后别一把斧头,嗖嗖嗖爬上高树,还能上树顶砍梢子。大哥二哥都会上树,我从小一上树便腿抽筋,不服气,故经常蹬着梯子上房顶去“放眼世界”。那时农村都是连檐房,一排房可以串五六七八家,上了自家的房顶,可以蹑手蹑脚溜达到高家常家贾家的房顶上。某日夕阳西下,景色迷人,家家户户的窑独(烟囱)炊烟袅袅,各家都在做晚饭。我心情大好,突然来了“灵感”,把每个窑独上边西北面挡风的砖头,扳倒盖在窑独上,除自家以外,高家常家贾家一溜烟儿挨着盖,然后,坐在自家窑独旁,居高临下,观赏“实验”结果。结果是,各家窑独不冒烟,各家家里冒黑烟,呛得人都往院子里跑……最令人气愤的是,老家乡俗对人最恶毒的诅咒是“炕上不卧娃娃盖了窑独”,故“盖窑独”意味着家破人亡绝了后!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只想做一个新奇的“实验”,并无恶毒用意。但结果被母亲现场拿住,好一顿棍棒招呼!当晚我愤怒得“绝食抗议”,母亲说,不吃是他不饿!夜深人静,父亲抚摸着我红一片紫一片的身体,哄我起来吃饭,母亲从锅里拿出热着的饭菜说,吃,你这个灰猴!还有一次“大事故”也不能不提:父亲的生母去世,我们全家到三十里外的快乐村奔丧,大爷的三儿外号叫“三地主”,我四岁,他三岁,几个小兄弟玩“斗地主”游戏,玩着玩着进入了角色,我用绳子把“三地主”的脖子套住,吊在院子里的梯子上“批斗”,幸亏大人们及时发现,差一点酿成大祸,所以当天就把我送回姥姥家。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每次“肇事”,母亲都会骂我,“三天不打,上房搬砖蹓瓦;一天一顿,欢喜不尽!”我现在回想,母亲用笤帚、鞭子、树梢、擀面杖、搅火棍、火铲子等顺手抄起的家伙儿都招呼过我,却没有打坏小胳膊小腿儿和小脑瓜等小零件。用今天的话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熊孩子”,不打真不行。俗话说:“宠儿不孝,宠狗上灶。”世上少有打坏的儿,人间多是宠坏的仔。我对母亲没有一丝半毫怨意,只有无尽的歉意。
5
上学之后,我记性好。我们村子小,学生少,学校是复式班,一、三、五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二、四年级在另一个教室上课,所以上完二年级,等于听完小学所有的课,一到五年级的算数都会算,一到五年级的课文都会背,我因此而屡次“跳级”。初中到马营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中学去上学,并顺利升入高中,但因两件事被迫离开学校:一是跟同学裴某某打架,打破了人家的头;二是给班主任老师起绰号。二罪归一,我被开除,这也是“罪有应得”。但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回家痛哭流涕不已。母亲叹口气,拿出家里的半口袋黍子,央告当民办教师的五叔去送礼通融,私自改名“李隽永”到另一所高中读书,被领导识破读不成,最后进入离我们村只有四五里路的雁北地区果木技术学校(二年制中专,毕业后不包分配)。到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的技校同学文春离开学校,插班进入县城高中,两年后考取大学本科。这一“事件”,太震动我了!其时,我已毕业回村劳动一年,从此就“翻心”了,长夜思索——怎么才能去读书!于是,偷了家里几颗鸡蛋,卖了五毛钱,交了考试报名费,报考县城一中高中班,很快被录取。虽然“既成事实”,但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对我说,咱村你四哥,还有高某和常某某,都是高中毕业,还不是回村?我说,现在不一样,我的同学文春已经考上大学了。父亲说,咱家穷,跟人家不一样,你两个哥哥还没成家,你跟大受吧。我说,大大,我要念书,您就当少生了一个儿。父亲怒道,由不得你!我陷入了大悲愤。母亲沉默几日,最后一言九鼎,硬朗朗说,嗨,想念就念吧,就当坐在“白花上”输了!故乡把赌徒叫作“白花”,把赌场叫作“白花上”。坐在“白花上”意味着赌命运。母亲说完这句话,把两个手腕上的银镯子摸下来,平静地交给我,说,妈就这点家当,换个钱儿,交个学费,以后就没了,全凭你自个了。七个银圆打制的一双银镯子——母亲一生的钟爱,被我拿走了。我到县城银行去兑换,亲眼看着工作人员用钳子嘎巴嘎巴铰断,然后从窗口递出二十五块钱的纸币。这笔钱,够交第一笔学杂费和前两个月的生活费,从此,此生,再没有从家里拿过一分钱。父亲一生穷苦,穷怕了,苦怕了,输了胆子,我心疼父亲,也理解父亲。对于母亲,一生亏欠太多,不知该如何报答。
6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阳泉工作。那时,从阳泉到山阴再回到村子里,交通很不方便。那时,父母五六十岁,对于农村人来说,正值“盛年”。所以,那时回家少,一年也就中秋和大年回两次。不过,家里所需要的,只要母亲说到,我尽量办到。自从读高中离开家,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概不知。母亲对我最放心,也最自豪,觉得三儿有本事,啥都能办到。我每次回家过年,母亲都问,咋还不结婚,多大年纪了!我笑而不答。母亲哪里知道,像我这种农村娃在城市里叫作“农圪榄”,“圪榄”是棍子的俗称,“农圪榄”直译过来,就是农村来的小光棍儿。现在城里人,又给我们起了个新名字,叫“凤凰男”。那时,母亲有啥需要,托五叔给我写信;有急事,打电话。母亲到小学校五叔办公室,打电话说,三三,咱家房子漏雨,刮风下雨,你大拿塑料布苫房顶,风吹下来就灰下啦!我知道母亲已经有了主意,问,妈,咋扎?母亲说,要不瓦(四声)瓦(三声)哇。我问,多少钱?母亲说,三间房,三千块,包工包料挺省事。我给当时在县政府工作的老同学志斌打电话,拜托他给母亲送去四千块。再过一段时间,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三三,咱家院子里得打个井,吃水方便,浇园也方便。我问,多少钱?母亲说,四千块。我给志斌打电话,请他送去五千块。母亲说出来的要办到,母亲没说的也要办好。那些年,我心里总惦记着,攒一大笔钱,在村里盖六间红松檩椽架构、红砖砌墙的大瓦房院落,让父母心情敞亮地安享晚年。
7
1996 年我挈妇将雏到北京文化打工,做起“北漂”。2000 年,筹了5 万块钱,交了个首付,在通州果园买下一套130 多平米的房子。2001 年我被北京某报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眨眼之间,困扰一家三口的户口和工作均顺利进京,真是开心!2002 年花两万多块钱,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2003 年元旦之后,我回村把父母接过来,住一住我的新房子。到北京火车站出站,找到一个路边的大商店,叮嘱父母在商店门口不要走动,母亲和父亲同声说嗯嗯,我去找开着豪车来接站的好友晓宁。当我和晓宁来到商店门口,哪有父母的影子!我的头发一下子全都站起来了!……终于寻见了!我长出一口气,反而不着急了,静静地跟在父母身后观察:好奇心重的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走走停停,正在忘我地仔细观赏周边的花草树木、景致图案和高楼大厦。有鉴于此,在京的日子里,上班时间,给父母留好吃的喝的,把防盗门反锁着;下班后,陪父母在附近走走,看看,吃点好吃的;只有到星期天,才能陪二老去看看名胜景点。母亲没啥要求,父亲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并希望到故宫逛一逛。那天,我叫女儿早早起来,一起陪爷爷奶奶去看升旗,在天安门广场转悠一会儿,母亲说,不想转了,回家吧。打道回府。过几天去故宫,父亲兴致特别高,对啥都想了解一番,像个孩子似的,充满好奇;可是走到故宫正中间时,母亲满头满脸都是汗,坐在石阶上歇了一会儿,说,妈腿疼得不行,咱回家哇。我说,妈,已经走到正中间了,往前走,往回返,距离是一样的,大大想看,咱们把故宫逛完吧。母亲摆摆手,坚定地说,不想看了!原路返回。事后我很懊悔,本来应该租个轮椅,推着母亲好好逛一逛,只是当时觉得母亲还挺硬朗,未想到这个茬。母亲晕车,打出租车,坐便宜一点的“夏利”,母亲头晕,坐稍贵一点的“富康”,母亲说不晕。我笑着说,咱妈这是“富贵晕”。母亲呵呵笑了。我当时已被北京某报莫名其妙“停职”,正在一家老年杂志试工,不敢让父母知道实情。坐在出租车上,我第一次意识到,生于1931 年、1932 年的母亲和父亲,已经年逾古稀,真的老了!
8
盖房子的事,提上了日程。我回老家跟父母亲和姐夫姐姐商量此事,询问做木匠的姐夫,修盖一处新院子,满打满算得多少钱?此时,姐姐有个“新提法”。她说,在村里盖六间瓦房,跟县城买一套楼房,花销也差不多。我愣了一下,问母亲,妈到城里去住,能舍下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母亲说,有啥舍不下的。我问父亲,大大舍得离开村子里的老朋友们?父亲说,也没啥舍不得,我和你妈意见一样。记得前几年,接父母到北京“暖新房”,母亲临走时笑着说,可不稀罕住这楼房,就像“蹲监狱”哩。也许母亲怕我心里难过,又补充道,住楼房也有两个好处,一是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了,二是坐着上茅茨(厕所),腿不犯困。因此我从未计划过在县城买楼房。此时,我忽然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一直惦记着住在县城的儿孙们,想到城里去住,应该是父母早有的打算。我返京后,跟老戴商议,咱们在县城买套房子如何?老戴说,给她爷爷奶奶住哩?我说,是的。老戴说,买吧。我私下借点钱,筹划买房子、买家具、装修房子事宜。过了一周,老戴突然问,买房的钱从哪里筹借?我说,已经“立项”,钱的事儿,领导莫操心。我给老同学志斌打电话,让他帮忙,在县城问询买一套房子,最好是新楼,最好在一楼。志斌很快落实,回复,说好三处楼房,你回来看一看。我只看了一处,面积104 平米,楼层是二楼,地理位置,布局结构,都很满意。我对志斌说,深谢老弟,“叹观止矣”,别处不看了。当年春节前夕,选个黄道吉日,将父母从老家搬进县城新家。看着操劳一生的父母,脸上洋溢着满足而自豪的笑意,哦,我觉得这是此生做得最值的一件事!住进新房,父母哪里都不愿意去。母亲对我说,你大离不开茅茨,妈爱干净,洗涮也便利。关键是父母住在城里,我回家方便。父亲去世后,姐姐和二哥交替来家陪伴老母亲,我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最多一个半月回一趟家。每月对出一个周五,上午搭乘“拼车”,傍晚即可到家,给母亲带点日常用品和好吃的,陪母亲住两晚一白天,给母亲剪剪指甲,和母亲拉拉家常,扶母亲到附近的桑干河湿地公园走走,周日早晨搭乘“拼车”返京。周而复始。知道我要回来的那一周,母亲周四下午就会坐在楼前的石头上等着。门房工作人员问,大娘,等儿子哩?母亲说,是哩。门房问,哪天回来?母亲说,明儿个。三年新冠疫情回不了家,旷日持久,望眼欲穿,只能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三儿,你把妈给忘啦?
9
每年春节,和母亲一起过。跟母亲一起准备年货;跟母亲一起包饺子;我贴对联,母亲帮我端糨子。母亲家是地暖,我喜欢盘腿坐在床边的地板上写文章——每年除夕写一篇《新年试笔》,母亲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聊一些陈年往事,说她的奶奶从前说什么,她的姥姥从前做什么,说我的二奶奶那些年如何如何,我的三妈近些年怎样怎样……母亲知道我的腿怕风吹,为我缝制了几个五六尺见方的棉的裌的小被子和小褥子。母亲没念过一天书,肚子里却装着好多好多的俗谚。童年时,我跟母亲压碾,愁得不行,母亲就说,“不怕慢,只怕站。小腿儿勤快能搬倒山。”我玩耍累了,饿得不行,半前晌半后晌跑回家要“搬的吃”,母亲从蒸笼里取出一块窝头,或者一块软软的黍子糕,抹点黑酱,笑着说,“我养你个小,你养我个老。我养你牙大,你养我牙跌。”母亲七十多岁以后,真的从嘴里时不时捏出一块大米粒大小的东西,对我说,你看,妈的牙又跌了一块儿。我青年时期工作忙,回家少,母亲安慰我,“吃人一碗,受人束管。官差不自由。”有时隔得时间太长没回家,回家时带一堆好吃的“赎罪”,母亲又会委婉地批评我,“娘想儿,流水长;儿想娘,筷子长。想见你个人哩,谁争你那一口吃的哩!”当我有了女儿出出进进扛在肩头上,母亲翻着白眼儿“笑话”我说,“唉,看好的!含在嘴里怕化哩,捧在手里怕炸哩。”然后老人家再补上一句,“不看当初娘养我,但看今朝自养儿。”俗谚颇不俗,经典又精辟。母亲经常用来表白形容自己的那一句谚语是:“好多说也不好白说。”“好”读四声,爱好的好。母亲向来话多,此谓“好多说”;母亲又非常厌恶“没影儿货”的信口开河白抓生道,老人家喜欢不留情面的真话直说,故曰“不好白说”。我自幼听母亲讲过的谚语,何止千条万条!我问母亲,您的这些话都是听谁说的?母亲说,我奶奶。从1992年到《山西晚报》工作时,我开始凭记忆整理“母亲的话”。谚语——“母亲的话”,我是听母亲讲的,母亲又是听她的奶奶讲的,母亲的奶奶也许又是听她的母亲、奶奶或者姥姥讲的……2010 年8 月我出版了40万字的《母亲词典》。其时,有几位朋友建议书名改为《母亲的话》。我说,《母亲的话》范围局限了点,本书展现的不仅是我的“母亲的话”,而且是“天下母亲的话”,并以谚语词条作为文章标题的形式来书写呈现,同时又以“时令·风俗”“人情·物理”“饮食·健康”这种“天·地·人”结构来谋篇布局,她反映的是“中华母亲的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个“母题”,所以我坚持书名叫《母亲词典》。我为她提炼概括了两句话:“谚语是一部口口相传的文明史,谚语是一个民族的回想与记忆。”当年9 月17 日在京举办《母亲词典》茶叙会,老作家从维熙讲道,在传统的中华国学研究中,历来缺少谚语研究这一块,而《母亲词典》让传统的国学与流传于民间民谣民谚进行对接,在弘扬中华国学中填补“国学之圆”。评论家雷达表示,《母亲词典》是一个首创,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他说,我想问一下建永——到底是什么样的灵感,使你动念创作一部这样体式的书?作家李辉更是在《书城》杂志撰写专文《雁来燕去,二十春秋》勉励道:“四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十几年的记忆追寻和旁征博引,晋人李建永——相貌彪悍,看似颇有契丹人的塞外风采,实则心细如发,且忍耐力惊人——终于完成了《母亲词典》。……如今,这本写了十几年的厚重作品,为其写作生涯竖起了一块里程碑。”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母亲词典》是第一部系统性地用谚语词条作为研究对象和书写文本的专著,具有文化学与文学史的标本意义。我引用几位先生的话,不是为了证明这部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我最想表达的是,我的“最没文化”的母亲,成天说着“最有文化”的话,《母亲词典》是母亲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哺育我的乳汁,教诲我的结晶。这也正是雷达先生所追问的“灵感”之泉源吧!评论家李朝全为本书写过一篇《用一本书向母亲致敬》的评论——是的,“母亲的话”是母亲留给我最宝贵最丰厚的馈赠,我几十年心心念念,就是想写一本书对母亲感恩,用一本书向母亲致敬!
10
今年春节(公历1 月22 日),画家罗雪村老师给我的拜年微信说:“建永,你一定回老家过年了,祝你过节愉快!祝全家特别是你的妈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回复极简单:“谢谢罗老师!”罗老师一直关注我的微信——我和母亲互动的图像,他多次对我说过,建永,你和母亲躺在床上那张照片,令我感动。故大年初一,不忍心让罗老师为我悲伤。今年5 月12 日——“母亲节”前两天,为岳母庆祝九十八岁大寿。老人家气色尚好,就是记不住事了,前几秒说过的话,后几秒就忘得无影无踪。岳母一次次问我,你妈身体还好?我一次次地说,我妈走了。岳母也一次次吃惊地问,啥时走的,我咋不知道?
我接到大哥电话,说妈不行了。老戴当场跌坐地上,放声痛哭。我说,不要哭,妈现在只是不能说话。又过了几分钟,我打过电话去,大哥说,不咋啦,妈好啦,能说话啦。我对母亲说,妈,等我,我这就回去。母亲声音很平静,也很遥远,轻轻地说,你倒回来呀?我说,是的妈,一定要等我。二十分钟后,大哥来电话说,妈走了。公元2022 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永远地走了!父亲9 年前突然失语住院,我们兄弟和子侄们在医院侍奉两周,端屎端尿,喂汤喂水。某日早晨,不能说话的父亲,用右手抚摸我的脸,又拿起我的手抚摸他的脸,这一天,父亲走了。当时医生说,快回家吧,“阴阳瓣子”下来了!我亲眼看见父亲脸上,从额头向眼睛向鼻子向嘴巴向下颏有一条白色的平行带迅速向下移,这可能就是“阴阳瓣子”吧,我抓住父亲的手,哭着说,大大,可不敢走!父亲还是走了,享年八十三岁,寿终正寝,儿孙满堂。母亲走时,身边只有大哥大嫂和几个本家的哥哥弟弟。母亲上午还到院子里上厕所,中午躺下说胃不舒服,下午就平静地走了,享年九十二岁。我赶回家,母亲已睡在棺材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不知道有无来生,但我相信缘分,我与母亲不知修行了几千万年修下的这场母子缘分,说散就散了。五叔两岁时我妈嫁到高庄村,住在一个院子里。五叔回忆说,你妈心地善良,性格刚强,心灵手巧,拿起一张红纸,一把剪子,就能枝繁叶茂花枝招展地剪出一个美丽生动的图案来,用现在的话说,你妈是个“女强人”。我妈从前常对我说,“拿起筷子想起娘”,现在常常出现这种情景,吃饭时咬着筷子发愣怔,回想着母亲的过往从前。母亲去世前一两个月,曾打电话对我说,妈走呀。我说,去哪呀?母亲说,死呀。我说,妈,不敢瞎说。母亲说,妈活着有啥意义哩,就是糟害你两个钱!我说,妈呀,难道钱比妈亲,回家叫妈妈答应,这就是妈活着的最大意义,没了妈,我叫谁呀?母亲说,噢,好了。我的老岳母尽管现在忘性大,但说话思路一如既往地清晰。岳母对我说,家里没个老的,就没意思了。岳母回忆起她年轻时母亲走了以后,说,回娘家,就想见个娘,娘没了,满肚子话不知跟谁说,走进院子里,心就凉了。我深信我的岳母——一位世纪老人的话,具有普世性和真理性:娘没了,心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