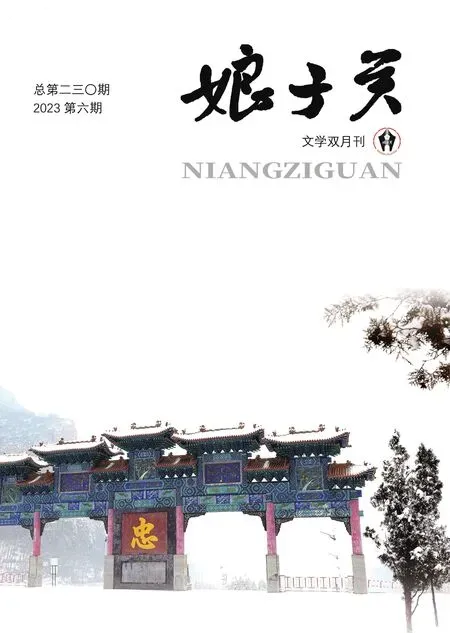卷与躺平(外二篇)
◇李雨书
说起卷,就会联想到《诗经·周南·卷耳》;读到“采采卷耳”,也会想到生活工作中的内卷。其实二者风马牛。
内卷本来是指发展到瓶颈期,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而充满问题的社会形态。因而,我从不认为,评论某人是卷王,是对其努力的褒奖。
然而很不幸,我总被称为卷王。
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到夜里零点结束,基本全年无休。在参加工作的三年里(博士后),我没过过春节,没休过国庆。有时是坐在电脑前对着蛋白结构看一整天,有时是脚步带风地穿梭在发酵间、称量间、仪器检测间做湿实验。可能这才是很多人眼里内卷的定义:牺牲自己的个人休息时间,没有止境地推进工作。
内卷绝非仅仅如此。
内卷除了过度努力,也包含了个体间的比较。在非工作时间加班,会显得自己格外用功努力,更快推进KPI,构建自己工作能力超群的泡沫,这已经算是能够产生良性结果的内卷了。更糟糕的情况是,倾尽全力却并不能获得满意的成果,使得努力工作变成“屎上雕花”的无用之举,且在大家都卷的环境中,为了不掉队而被迫牺牲休息时间磨洋工,就会渐渐从自尊受挫,转变为憎恨这个“别人在卷所以我不得不卷”的社会。其实内卷,也无非是想要获得比身边人更好更优越的生活罢了。跳出横向比较的牢笼,一部分人就可以在不被裁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刮老板们的脂膏——躺平!
身为劳动者的我们,难道只能在内卷或者躺平之中二选一吗?作为一个被称作“卷王”的人,我不这样认为。太过在乎平均值这个概念的人,往往会觉得在一个团队里特别努力的那位格外烦人,他们的过分努力会逼迫群体里的其他人也付出更多。然而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卷”的人设,也不关心整个群体的状况,而是单纯喜欢自己正在完成的工作本身?
我不眠不休的工作,仅仅是因为我很想知道自己研究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它并不只是我谋生的手段,更是我满足好奇心的媒介。一想到还有诸多细致问题暂时无法解答,就没法坦然放下工作,早早放松休息。人都有惰性,可在求知欲旺盛的时候,那种心痒难挨的感觉根本无法忍耐,定要找出背后真理,声色犬马之餍足怎能与之匹敌,那是一种灵魂超脱感官的纯粹愉悦。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做自己热爱的工作。
卷不卷并不是问题的本质,也不是这个社会在逼迫个体像一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而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世俗角度容易攀爬的路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路径,随后发现选择这条路径的人格外多,最后拥挤在这条单一的路上走得越来越慢,终而躺在了察觉到累的那块里程碑旁。倘有着过多世俗的计算,就要承担相应的社会压力,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既然为名与利典当了灵魂,那就得接受快乐被剥夺。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在我看来,“卷耳”与躺平,均非好的人生,亦不会有快乐的收获。世间真正能让自己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的,是自我的认可,而不是大众的指戳与评判。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忘我,臻于化境。
榜 样
在过去几个月里,学界顶刊《自然》杂志连续三次报道了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世界各地的博士后不得不面对的职业窘境。《自然》称,博士后被认为是学术界的无产者——工作不稳定,收入很差,获得终身教职的道路充满未知……然而,博士后阶段又是大多立志投身科学研究者所必经的职业道路。《自然》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受访的博士后人群中,竟有51%曾因为抑郁、焦虑或其他与工作有关的问题而考虑离开学术界。刚开始博士后工作的我,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思考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条布满荆棘的学术之路上负重前行。
我在牛津每每做完DNA 提纯后,需要对这些DNA 样品进行测序。送样的网页界面显示,该测序服务被称为“桑格测序”(Sanger sequencing)。某天,我终于没能克制住好奇心,上维基百科查询这位Sanger(桑格)到底何许人也?他的讣告中写道,他自认是“一个在实验室里一通乱搞的家伙”(just a chap who messed about in a lab),且“搞学术不太行”(academically not brilliant)——尽管他曾因建立了在生命科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蛋白质和DNA测序方法,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Sanger 家境富裕,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就读的自然科学系,大一时需要学习所有自然科学基础课(part IA),其中物理和数学,Sanger 学起来很吃力;大二(part IB)分科后,他将物理学换成生理学继续学习,三年才完成通常为两年的part I 学习,学业表现平平无奇。直到随后的part II学年,他选定研究生物化学后,才获得了一等学位(学年前30%)。在剑桥读博士期间,他也没有显现出类拔萃的学术能力。毕业时,他申请了剑桥的博士后职位,并在自荐信中申明可以不领薪水,因此获得留校机会,在生物化学系自费做研究。
研究期间,他使用从化学系同事那里搞来的2,4-二硝基氟苯(后被命名为“桑格试剂”),测定胰岛素两条链的N-端氨基酸,将其水解为肽链片段后,通过电解、色谱层析,并使用茚三酮显色获得胰岛素的二维指纹图谱,完成其蛋白测序,并于1958 年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后,剑桥终于把他位于地下室的实验室挪到了顶层,并将他升职为蛋白质化学部门主任。随后,Sanger 立刻着手RNA 测序的研究,然而同行Robert Holley率先完成了转运丙氨酸的tRNA 测序,比Sanger 完成的5S 核糖体RNA 测序要早一年发表。Sanger随即又开始了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DNA 测序研究,建立了“桑格测序法”,为“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奠定测序基础,并因此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即便功勋卓著,他也一直真心实意地觉得自己非常普通,并拒绝了女王封爵的邀请,因为他不想被别人使用“Sir”(爵士)来称呼,好似他多么与众不同。最终,他只接受了女王颁发的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Sanger 一生极为谦逊,获奖后依旧奋战实验一线。在从事科研工作的39 年间,他写完了35 本实验记录本。
2018 年,我的导师做博士后时期的女同事,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导师耿直地评论道,我们无机化学楼里的Goodenough发明了锂电池,他都没获过诺奖!第二年,97 岁高龄的Goodenough(该姓氏的英文单词原意为“足够好”)因发明锂电池而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这位“足够好”先生,迫于牛津大学65岁退休的硬性规定,只好在退休那年离开牛津,移驾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继续从事电池方面的科学研究并持续至今,以98 岁高龄依旧工作在科研一线!我博士期间工作的无机化学楼门旁,一直挂有讲解Goodenough 于此发现锂电池的蓝牌。这种介绍重要历史事件的蓝牌(blue plaque),在牛津的各个院系屡见不鲜。我出门遛弯儿常常走走停停,端详路边的蓝牌,看这些地址究竟曾发生过什么惊人的大事。
博一期末,我马上要进入Abbot’s Kitchen(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实验室)进行博士开题报告口头答辩,导师问我:“你觉得博士毕业答辩是什么?”我怯生生地回答:“是教授们考察学生获得专业知识程度的考试。”导师说:“不不不,博士答辩不是专家在考核你,而是你在向其他研究者展示你四年所做的研究成果,是炫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研究的课题。你,才是你要讲解的问题的专家。”
博二那年,我旁听博三师兄师姐的结题答辩,做答辩研讨会的闭幕演讲者曾因研究分子机器获诺贝尔化学奖。他坐在能容纳200 人的阶梯教室最前面,认真听取每一位博士生的结题汇报,并在每个汇报结束后提出切中肯綮的问题,请学生们回答。他完全没有任何刻板印象里学术权威自带的傲慢,反而对每个听到的化学问题都充满好奇。随后不久,我去利物浦开学术会议,我自己研究领域内获得诺奖的女教授,在做完令人热血沸腾的学术演讲后,正与几位学界大佬在演讲台边交流。我默默等在一旁,希望与她聊上几句。她注意到我在等她,径直走来询问我是否有问题与她商讨。我做完自我介绍后,邀请她在随后的海报展期间来看我的海报。之后,我站在海报旁边等待,她如约而至,并给出一系列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
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群杰出却不骄矜、勤奋又真诚的科学家,在学术之路上为我掌灯,令我不愿脱离他们的队伍。
尽管我导师经常吐槽,牛津化学系最大的失败,就是培养出一系列聪明优秀的化学学者,毕业后就扎堆搞金融、做咨询,只有零星几个学者愿意潜心学术。但是,就是这一小撮儿留在学术界的学者,已为后辈营造出充满活力的科研气氛,足以让我这样普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深受感染,见贤思齐,被感召而坚守理想。这也正是留学的意义所在吧。人对舒适物质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生物本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留学海外的这些经历,为我呈现另一种人生态度:有这么一群人,摈弃享乐与世俗等级观念,不断为推进人类科学前进而奋斗。我穿行在牛津的街道上,仿佛在科学史的长廊里行进,一块一块的蓝牌被甩在身后,我们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去赢得更多的蓝牌——挂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跨 越
一位来自四川的牛津旧识,曾提及一则她与日本朋友同游印度的旧闻。
在当地游玩的几天,他们在“地陪”的帮助下包一辆出租车随行。出租车司机在载他们去泰姬陵的路上,提起自己仍在上学的儿子,称儿子的梦想是做一名书记官,他为此感到十分骄傲。这位四川姑娘在转述的同时,表达了她与朋友对此事的惊诧,强调自己无法理解把做文员、秘书当成理想,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难道印度的种姓制度,连人的思想都禁锢了吗?
我把这件听来的事,讲给做印度哲学研究而熟悉印度文化的好友。
她向我科普,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某一个层面上,是因社会分工产生的。比如Kayastha 种姓就是由几个地区的书记官构成。这些职业种姓嵌在秩序严密的社会等级中,不同种姓能够参与的社会工作有明显的阶级分化。而这位出租车司机父亲所在的种姓阶层,并不能做高于自己阶层的书记官工作。然而,同样种姓身份的儿子却有跨越阶级的梦想,父亲作为一名惯常的普通人,又怎能不为自己敢于挑战“常规”的儿子感到骄傲?对这位父亲而言,成为书记官已经是难以实现的“远大理想”。能够在“身在此山中”的客观条件下,主观地挑战现有的社会制度,行为本身就是充满勇气。
我独坐时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扪心自问,我是万万不愿连做梦的自由都被束缚。有人也许认为,只有如今还在光明正大地保留、实施种姓制度的印度社会,才缺少跨越阶级的梦想。但事实并非如此。
观看英国电影《赛末点》(Match Point)时,我第一次听说社会攀爬者(social climber)这个群体概念。顾名思义,就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改变自己阶层的人。这在我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阶层,过上更体面的生活。然而在英国,社会攀爬者连中性词都算不上,是恶意满满的鄙夷之词,指那些夤缘攀附妄想提升阶层的人。在牛津生活学习的几年里,在潜移默化之中,我渐渐触到英国社会平静水面下的暗流。
在英国,中小学分为公学(public school)与公立学校(state school)。公学,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私立寄宿学校(比如举世闻名的伊顿公学),占全英学生的7%左右。而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每年招收英国本土的本科生中,公学毕业的学生足足占42%,且数据显示公学毕业生在大学期间的成绩,明显优于公立学校毕业生。不仅如此,英国绝大多数薪资可观的公司,对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学历等级要求至少为“2:1 学位”,但是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获“2:2 学位”(比“2:1 学位”低一等),依旧可以和其他学校持“2:1 学位”毕业生“公平”竞争。也就是说,在英国想要活得体面,先要获得一份优质大学学历,而这又需要出色的基础教育。因而如有可能,家长还是会尽力把孩子送进公学,以期将孩子获得“完美人生”的概率提升大半。
然而,公学的教育,十分昂贵。
据我带的part II 学生(牛津大学化学系四年本硕连读学制学生,前三学年为本科阶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英国的各个阶层固化严重,政治家的儿子依旧是政治家,银行家的子弟依旧是银行家,农民的后代也大多还是农民。虽然顶着平等自由的旗号,确是布满裙带关系与隐形世袭制度的社会。出身平凡雄心勃勃想要出人头地者,一边忍受着上流社会精英祖传的傲慢与偏见,一边千方百计和其他社会攀爬者争夺已经被上层攫取得所剩无几的优质资源。
但是,有梦想有错吗?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应当被现实社会所捆绑吗?
我在高中读《易经》时十分困惑,遂问爸爸:为什么《泰卦》的卦象是地上天下,而《否卦》却是天上地下?如果文王真的依照对自然的观察而推演出六十四卦,那么难道天上地下不才是真正的自然之道,才是“泰”啊!何以“倒”哉?爸爸解释说,就卦象而言,《否卦》的天在天上,地在地下,天地之间无交流;而《泰卦》本来就是一个“交通”卦,地在天上,天在地下,天地交通,则“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其映射的社会形态而言,君在上,民在下,无沟通,与君俯下,人才能够合理交流晋升,哪种情形更能够和谐而良性地运转呢?
顿时醍醐灌顶。
我们的传统文化,看上去有很多规则约束,虽区分为士、农、工、商,但却没有堵住人才晋升的途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就是开拓人才选拔之路,网罗民间俊士英才。如今我国广泛实行“以分取人”的高考制度,使人才上升的道路更加通达而宽广。只要学习资料容易获得,学生足够聪明努力,基本都是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这是一种颇为公平而合理的制度。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书期间,身边的同学大都来自全国各省市县的普通家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两千多年前就发出的呐喊!绝不像英国文学巨擘狄更斯那样,由于出身贫贱以致欲作社会活动家不得,只能在自家客厅搭个演讲台,“模拟”组织社会活动。
近十多年来,印度也意识到种姓制度给人才选拔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首先从教育制度入手,提升三所印度顶级学府(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和全印医学院)的低种姓学生录取率达50%,甚至激起高种姓学生抗议政府反相歧视。阶层的跨越和人的解放,推动了印度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心。教育供人以养料,以相对公平而不问出身的标准选拔任用人才,才是励精图治之根本。基于此,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教育资本化、产业化,以及通过“知识付费”,有意识地用资本将社会成员分割成三六九等的阶级分化行为。
出生于平凡之家,我为能自由地做梦,有权怀有“跨越阶级的梦想”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