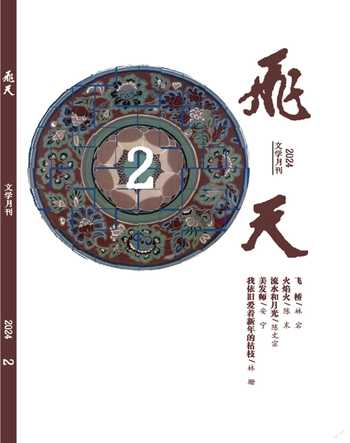凝望
李宝堂
一
六月的敦煌风和日丽,花繁树茂,是这个绿洲小城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常书鸿先生逝世28周年之际,我和朋友一大早就来到常书鸿先生的墓地,祭奠这位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大师。
常书鸿先生的陵墓坐落在敦煌莫高窟对面邻近宕泉河东岸的一片坡地上。深灰色花岗岩墓碑上镌刻着“常书鸿同志之墓”七个金色大字,墓前一方黑色大理石上刻着赵朴初先生的题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周围生长着大漠戈壁特有的沙生植物红柳。陵墓就地而建,庄重简朴,坐东朝西,与鸣沙山和莫高窟隔河相望。
我和朋友在常书鸿先生墓前鞠躬祭拜,敬献鲜花,缅怀先生曲折而又光辉的一生。
在温暖和煦的晨光里,我转身望向不远处的九层楼,恍然间明白了,这完全是遵从了常书鸿先生的意愿,生前他在这里度过了艰苦卓绝的39个春秋,死后他要在这里凝望和守护奉献了一生的莫高窟……
二
常书鸿生于1904年4月6日,浙江杭州人,满族,名取“往来有鸿儒”之意。1918年考入浙江大学的前身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学习,1927年6月赴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国立专科美术学校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师从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教授。作品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获金质和银质奖章,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并在巴黎成功举办个人油画展。被评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跻身法国知名美术家行列,也是首位进入该协会的中国美术家。发起成立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等中国留法著名艺术家参加的“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徐悲鸿曾亲临寓所拜访。常书鸿在重庆举办个人油画展时,徐悲鸿亲笔作序,称之为“艺坛之雄”。
1936年秋天,旅法长达九年零十个月的常书鸿,听从命运和祖国的召唤,毅然放弃了在巴黎的功名和舒适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来到大漠深处的敦煌,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三
常书鸿命运的改变完全始于一次偶然的凝望。
那是1935年隆冬的一天,常书鸿从巴黎卢浮宫出来,来到塞纳河畔一个出售美术图片的旧书摊前。翻阅之间,眼前一亮,发现了一部六卷本盒装的《敦煌石窟》。这部大型图录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7年从中国甘肃敦煌千佛洞拍摄的108个洞窟和外景的399幅照片。常书鸿逐页阅看,无比震惊,爱不释手。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东方,在他的积贫积弱且正在遭受战火的祖国,竟有一座如此辉煌的艺术宝库。
正是这次常书鸿对印刷在纸上的敦煌艺术的深情凝望,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敦煌莫高窟的命运。
经书摊主人介绍,第二天常书鸿又赶往位于巴黎16区的法国吉美博物馆。在这里,他看到了陈列着的伯希和盗自敦煌莫高窟的大量唐代绢画。其中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年代竟比欧洲文艺复兴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早了700年,比油画的创始者文艺复兴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早了800年,比法国学院派祖师波生早了1000年。
这是常书鸿第一次亲眼看到古老的敦煌艺术的原作。他发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早期历史和作品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敦煌艺术更显出先进的水平。而自己却一直倾倒于西方文化,认为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世界文艺发展的高峰,不惜远渡重洋来巴黎学习西洋画。这不仅是舍近求远,也是对祖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无知,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惭愧和追悔。特别是身在异国他乡,看到自己祖国被盗的国宝竟然堂而皇之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常书鸿悲愤交集,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暗暗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回祖国去!到敦煌去!去守护这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宝库——莫高窟!
十个月后,常书鸿毅然告别了巴黎,乘坐国际列车回到北京。他先在北平艺专任教,同时开始谋划西行敦煌之举。
1941年因战乱北平艺专迁址重庆,次年5月常书鸿在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受启发,更加坚定了西赴阳关的决心。
1943年2月20日清晨,經过近七年的几番周折,在于右任、梁思成、徐悲鸿的鼓励和帮助下,常书鸿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之职,靠教育部发给的和他本人在重庆开办个人画展筹得的微薄经费,由重庆经兰州踏上了艰难的敦煌之行。
四
当时兰州到敦煌一千两百多公里,途经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三地和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城——嘉峪关。常书鸿一行六人乘着一辆破旧的苏制敞篷卡车,顶着高原早春的寒风,沿着古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西行。
唐代诗人王翰著名的边塞诗《凉州词》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汉代名将班超塞外征战三十年后曾上书汉武帝“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河西地区早有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常书鸿一行越往西走越感苍凉荒蛮,人迹罕至。悲怆中他细细品味行前梁思成“破釜沉舟”和徐悲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真情勉励,切身体悟到此行的不同寻常和意义非凡,更加坚定地向西、向西、再向西……
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终于于3月24日到达了心心念念的敦煌。由于车到安西茫茫戈壁荒漠无路行车,只好雇了十头骆驼,走了四天四夜,才走完了这段最后的旅程,来到梦寐以求的莫高窟。
五
这一天,他们忘记了旅途的艰辛和劳累,顾不上洗去一路风尘,迫不及待地进入窟区巡看。
这是常书鸿第一次实地凝望浩若烟海的敦煌壁画和彩塑。他再一次被眼前真真切切的辉煌艺术所震撼。他完全没有想到莫高窟石窟群的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丰富,艺术如此精湛,处境如此险难。
莫高窟分南北二区,由南至北崖壁共1680米,高三五十米不等,上下分布着700多个洞窟,其中多数都有壁画和彩塑,绵延1500多年。那五代时期的装饰纹样,隋代的联珠飞马图案,犹如东晋时期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恰似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李思训般的青绿山水,还有数不尽的体现着民族传统和风格的艺术珍品,美伦美奂。
常书鸿还看到了伯希和《敦煌石窟》中看不到的各时代壁画的绚丽色彩。特别是北魏和西魏的30几个石窟中,完好保留着的几千平方米壁画、装饰图案和一些质朴淳厚的彩塑,完全是汉代艺术传统,从4世纪到14世纪,历经千年而不衰。
常书鸿还特别查看了道士王圆箓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流沙时偶尔发现的“藏经洞”。此时已是四壁空空,一派凄惨。常书鸿百感交集,惋惜之间他想,莫高窟这座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窟,在此前几百年间竟然一直处于无人管护、自由来往、任由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的状态。藏经洞发现后,曾有英、法、日、俄、美等国近十批次探险家前来轮番劫掠,而此时距数万件国宝被盗也已经过去三四十年,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珍视和保护。崖体坍塌,栈道毁坏,洞窟内满是流沙,甚至很多洞窟被流沙掩埋,残垣断壁间散落着壁画残片,甚至窟前还放牧着牛羊,一些洞窟竟有淘金沙的人栖身夜宿,砌灶台,盘火炕,烧水做饭,烟熏火燎,一片破败,这真是民族的悲哀!常书鸿心痛不已,默默地在心中立下誓言:今天,我常书鸿来到莫高窟,从此开始,我将在有生之年,为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艺术而努力,决不让这举世之宝再遭受灾难了!
就是从这一天起,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守护莫高窟的漫长的苦行僧和殉道者般的敦煌岁月。莫高窟也因此翻开了千年历史上新的一页。
六
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住在几间破旧的土屋寺庙里,开始筹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1月1日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正式将莫高窟收归国有。
当时,他们在莫高窟喝的是咸水,没有蔬菜,日复一日靠一碗醋、一把盐伴着一碗面度日。偶尔凭张大千临走时留下的路线图,到戈壁深处采摘一点野蘑菇,已经算是佳肴。他们忍受着地处荒漠戈壁,远离县城五十余里,交通完全靠驴马或步行,信息封闭隔绝,犹如孤岛一般的艰苦环境;忍受着经费严重不足,物资极端匮乏,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工作条件都不具备的窘迫和拮据;忍受着三天两头刮狂风、起沙暴和夏热冬寒的恶劣气候;还有无边的孤独寂寞等常人无法忍受的炼狱般的艰难生活。他们用拿画笔的手和民工一起,筑起一千多米的土围墙,清理了约十万立方米的流沙,架通和修理了洞窟间险象环生的栈道,支护了一些破败不堪的洞窟和建筑,保护和新植了树木。他们搭着“蜈蚣梯”攀爬洞窟,逐窟调查,给洞窟重新编号,以宗教般的虔诚,一尺一寸地研究492个有壁画和雕塑的洞窟中,总量达44830平方米的壁画和2415尊雕塑,考证历史,推断年代,研究内容,分析艺术风格和特点。他们用自制的颜料和低廉的画纸,举着油灯在昏暗的洞窟中看一眼,画一笔,艰难地临摹;他们一丝裂缝一丝裂缝,一个孔洞一个孔洞,一片泥皮一片泥皮地修复佛像龛窟和壁画;一个卷子一个卷子,一张纸片一张纸片,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残经破卷、断文损帛和遗书题记,开展研究工作,并在艰难困苦中,期待着中华民族的光明时刻和莫高窟的福音……
七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前三天的9月28日敦煌解放。温暖的春風终于吹进了古老的玉门关,莫高窟迎来了最为光辉灿烂的历史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国家先后拨款,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洞窟和建筑进行了高质量的整体抢险加固和修缮,使莫高窟彻底摆脱了濒临垮塌的险境,既保持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焕然一新,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褒奖文物研究所在建国初期卓越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还向研究所颁发了由郭沫若副总理亲笔书写的奖状和奖金。其间常书鸿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评为“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当选甘肃省党代表大会代表、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鲜花和荣誉接踵而至。
新中国的成立和条件的极大改善,使常书鸿和全所同志倍受鼓舞,精神振奋。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临摹壁画,整理遗存,举办展览,出版画册,研究学术,著书立说,引进和培养人才,加强管理,精心保护,攻克难关,创造先进保护方法,治理壁画病害,尽可能延长壁画和雕塑寿命。常书鸿还出访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全国和国际范围传播敦煌艺术,推动莫高窟对社会开放利用,建设高水平专业化保护研究队伍等等。
就这样,经过几代“莫高人”薪火相传和呕心沥血的努力,曾屡遭劫难,成“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莫高窟,发展为当今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美术“博物馆”。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7年12月,莫高窟以中国首批、排名第二的突出地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又运用数字化技术,建成数字展示中心,自主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使莫高窟跨越抢救性保护和传统保护时期,进入到预防性保护、科学保护和“数字敦煌”的新时期,使莫高窟珍贵的价值和历史信息得到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如今数字化技术不仅实现了全球在线共享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让莫高窟艺术活了起来,也更好地兼顾了文物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关系。敦煌学研究也硕果累累,在世界范围绽放出夺目光彩,终结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尴尬局面。莫高窟最初的六人研究所也已发展为现在全国最大的“一院六地”,集研究、设计、施工一体化、全链条的专业文物保护和研究团队。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任名誉院长)樊锦诗,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锋”、“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最美奋斗者”等众多荣誉称号,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1月中央宣传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莫高窟考察,观看石窟、壁画和彩塑,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研究弘扬敦煌文化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莫高窟进入了千年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八
常书鸿出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青春年少即到法国巴黎留学,可以说从小过惯了富裕安逸的生活。但自从他到了敦煌莫高窟,就在戈壁荒漠深深扎下了根,即使在近乎绝望的困境中也不言弃,几度力挽莫高窟于灾难甚至绝境之中。由于最初生活条件极端严酷,随他而来的人几年内都以各种原因一一离去。就连从杭州到巴黎,从巴黎到敦煌,一路相伴20年,甘愿为他做人体模特以成就他的艺术,并生下一双可爱的儿女的妻子,也终因忍受不了大漠之苦,到敦煌两年之际忍痛不辞而别。常书鸿知晓后心如刀绞,连夜独自策马追出两百多公里,最后累得人仰马翻,昏倒在茫茫戈壁。幸遇玉门油田的发现者和创建者、正在戈壁滩上寻找石油的地质学家孙建初一行相救,才免于一死。
几十年中,常书鸿在敦煌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自然的、工作的、家庭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等等,但他从未动摇,即使是在残酷的政治刧难中也坚守初心,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敦煌的保护和艺术事业。
1981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来敦煌考察,常书鸿陪同参观。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82年3月,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兼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后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举家迁往北京,以优厚待遇安度晚年。
到了北京,常书鸿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可谓“夜夜敦煌入梦来”。他常给女儿常沙娜说:“我要回敦煌去,还要住那土房子。”他在家里挂了好几个铃铛,把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当作莫高窟九层楼窟檐上的铁马声,以慰藉对敦煌深入骨髓和灵魂的痴爱与苦恋……
曾有共同工作多年的学者劝常书鸿,“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别回敦煌去了,能放松休息最好。”常书鸿却坚定地回答“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如果真的有来生,我将还是常书鸿,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还要守护莫高窟。”
常书鸿晚年患病后嘱咐家人,“我将来死了也要回敦煌!”1994年6月23日,90岁高寿的常书鸿怀着对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深切留恋在北京病逝,8月9日部分骨灰护送回敦煌安葬,1995年在常书鸿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敦煌研究院在宕泉河畔为常书鸿修陵立碑,实现了先生的遗愿。
九
我曾有幸拜访过常书鸿先生,得到先生的亲切教诲。我所就读的甘肃师范大学艺术系(现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前身为吕斯百亲手创建的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成立于1959年由常书鸿兼任院长的兰州艺术学院,1962年并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常书鸿是我的母校引以为傲的前辈和大师,师生们都对常书鸿先生怀有特别的敬仰之情。
1972年经导师介绍,我随甘肃人民出版社美術编辑在兰州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常书鸿先生。当时常先生已年过六旬,但精神很好,满面慈容,和蔼可亲,睿智儒雅,谈兴很浓,足见大师风范,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早在1945年,常书鸿和女儿常沙娜就在兰州双城门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展出常书鸿在敦煌所作速写和油画写生作品以及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慕本共六七十件,在甘肃早期的美术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59年常书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亲自主持学院建设工作,并设立“常书鸿画室”,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学习油画。1962年常书鸿当选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常书鸿还先后在甘肃创作了很多作品,特别是为兰州中川机场创作的巨幅油画《激流颂——刘家峡》和大型油画《献给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同志们》,在全国特别是甘肃美术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此可见,常书鸿先生不仅是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一代宗师,还是新中国甘肃美术事业的奠基者、开创者和领导者。作为晚辈、后学和继任者,我认为常书鸿先生是甘肃美术家永远的骄傲和旗帜。
2013年,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提出打造“敦煌画派”,我了解到早在1980年,常书鸿先生在会见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时,就曾论述过他对“敦煌画派”的构想。他说:“我期待不久的将来,新型中国画会诞生,那或许是敦煌画派的复活。到那时,我四十余年来一直期待敦煌画派产生的梦想,便成为现实,我就心满意足了。”多年来,常书鸿先生播下的艺术种子正在勃发成长,常书鸿先生的先见之明引导我们继续朝圣敦煌,传承和弘扬敦煌艺术,追寻新时代的敦煌之梦……
十
沉思中太阳已经高高挂在三危山巅,天空出现了美丽的彩霞,莫高窟九层楼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更加壮丽。这时,我环顾四周,看到九层楼前、宕泉河畔、三危山下和莫高窟前的树丛中,矗立着很多佛塔。我想这是那些为莫高窟献出了生命的先人们,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莫高窟。千百年来,这些佛塔早已和莫高窟融为一体,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象征着久远的历史、虔诚的信仰和崇高的精神。
由此我想,人们称常书鸿为“敦煌的守护神”,这是非常贴切的。对莫高窟而言,常书鸿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千年莫高窟得遇常书鸿这样一位“舍命相护”的守护人,是敦煌艺术之大幸,是中国艺术之大幸,是中华文明之大幸。如果没有常书鸿,如果不是常书鸿“一生只为守敦煌”,也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
如今常书鸿先生长眠在这片他称之为“永远的故乡”的神圣土地上,他可以在这里安详地凝望和护佑他为此献岀了一生的莫高窟,倾听九层楼檐角高悬的铁马在大漠的风中悠远地呜响,让不朽的灵魂在这举世闻名的艺术天堂自由飞翔……
责任编辑 维 宏
——常书鸿与敦煌的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