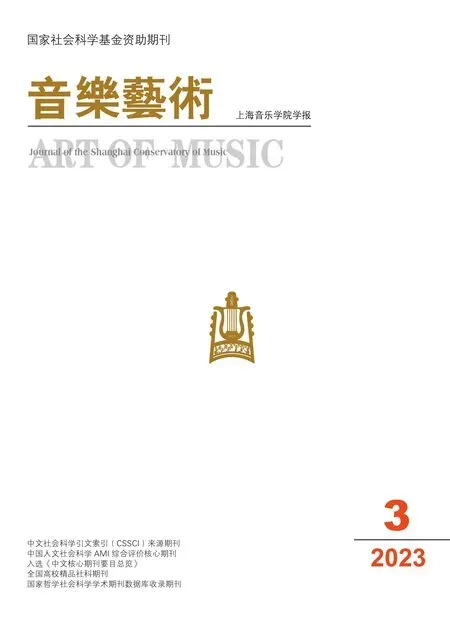早期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发展与历史意义
汪静一
内容提要: 以黎锦晖《麻雀与小孩》为起点的早期儿童歌舞剧,是在“美育”“国语运动”的推动下、借鉴西方戏剧样式而创生的,反映出时代对“儿童”的发现和关怀。该剧表明儿童歌舞剧在“儿童歌舞剧—歌剧”的整体语境中得到发展,既有儿童歌舞剧探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歌剧探索的支撑和影响,又有歌剧创演经验对儿童歌舞剧的“反哺”,展现出儿童歌舞剧与歌剧的互动和转化。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雏形,开启了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国语白话模式,显露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构建了中国歌剧的戏剧结构空间,搭建了中国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在中国歌剧百年历史发展中具有先导地位和铺垫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种旨在表现儿童、启蒙儿童的音乐戏剧样式—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剧将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吸取借鉴早期“文明戏”(话剧)的创演经验,取材同时代的儿童生活,以通俗的音乐和简明的舞蹈为主要戏剧手段,用白话体和童话式的台词和歌词,讲述少年儿童喜欢的故事,承载浅显的寓意,最终形成一种以“话剧加唱”为基本戏剧表达方式且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形式。儿童歌舞剧由致力于普及音乐教育和推广国语的作曲家黎锦晖首创,1920年至1927年,其创作了《麻雀和小孩》(1921年正式首演)等12部经典剧目,并带动了早期(20世纪上半叶)儿童歌舞剧的发展,成为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开拓者。中国的儿童歌舞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舞台演剧样式,其创生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其发展在20世纪留下了不平凡的历史轨迹,尤其是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所呈现出的“唱歌→表情唱歌→儿童歌舞剧→歌剧”的演进,以及最终的“歌剧”(opera)雏形①,为人们带来了关于中国歌剧“发生学”的文化想象和史学演绎。20世纪上半叶,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的初始形态,不仅有助于当时的国语推广、美育推行及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的开展,而且对中国歌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一、 儿童歌舞剧创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的儿童歌舞剧较之同时期其他音乐体裁样式,无论是表现形式、思想内涵,还是受众类型和传播范围,都有其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样式,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创生的,其中既以近代中国新兴“儿童观”为思想基础,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以黎锦晖、“春蜂乐会”作曲家,以及叶圣陶、赵景深、朱震西等音乐教育家为主力军的儿童歌舞剧创作群体应时而生。这一创作群体以较强的积极性和默契度,热情地投入到当时并不被看好的儿童歌舞剧创作中,完成了一批数量可观、质量优良、影响力大的剧目。除开拓者黎锦晖的12部儿童歌舞剧外,还有“春蜂乐会”作曲家单独或联合创作的22部儿童歌舞剧,以及叶圣陶、何明斋、赵景深等音乐教育家创作的近50部儿童歌舞剧,笔者推断,或许还有一批儿童歌舞剧(或其脚本)有待学界的挖掘与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物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文学家和戏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展开儿童歌舞剧的创作,并将其用于儿童音乐教育和学校戏剧表演实践。
(一)“孩子”的发现
在“父为子纲”的传统中国,儿童一直未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也未能出现真正将艺术视角指向“孩子”的儿童戏剧。中国古代不乏载歌载舞的儿童表演,如《论语· 先进篇》记载:“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②描绘了两千多年前儿童春日郊游时的歌舞场景,且展露出儒家对儿童的“仁爱”。宋元以降的戏剧中也不乏适合儿童演出的戏剧类型(如傀儡戏、皮影戏、肩担戏等)、描写儿童的戏剧情节、可供儿童扮演的角色类型,以及适合儿童观看的剧目。但更应看到,这些与“孩子”相关的戏剧形式,其目的主要不在启发儿童心智,而在于使其形成以“父为子纲”为前提的伦理观,因此始终未能展露出表现儿童、启蒙儿童的旨意。③这也表明,在中国古代,儿童与妇女一样,并未得到“解放”。
但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孩子”逐渐得到重新发现。早在戊戌新文化运动中,谭嗣同的《仁学》就对“父为子纲”等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这为“孩子”的重新发现作出了思想铺垫。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率先发现了“孩子”,并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与当时关于个体“人”的认识及对“人”独立人格的尊重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现代教育学,尤其是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一批作家作出了积极响应,有力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庸俗的“子孙”观,将视角指向“孩子”,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本位论”。这种“儿童本位论”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响应,也引起广大民众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所应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性的重新审视与珍视,并力图将“子”从“父”的阴影下剥离出来,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对此,黎锦晖及其后“春蜂乐会”作曲家,以及叶圣陶、何明斋、赵景深等人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以“新儿童观”重新发现了“孩子”,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回应。由此可见,以儿童为本位的“新儿童观”正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儿童歌舞剧等儿童戏剧得以创生的思想基石,在其引导下,早期儿童歌舞剧真正成为视角指向“孩子”、表现“孩子”、服从“孩子”的戏剧样式。
(二)“美育”的引导
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育”的引导。早在1912年4月,蔡元培学习、借鉴康德、席勒等人的思想,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并提出“五育”的教育方针,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将“美感教育”(即“美育”)提到重要的位置。④1912年9月2日,由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签署公布的《教育宗旨》中说道:“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⑤这部教育法典进一步将“美育”规定为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所提及的“美感教育”思想在之后一系列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中均受到重视,并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进一步得以深化。伴随着学堂乐歌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当时的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但袁世凯于1915年2月推行的《特定教育纲要》又指出“教育部前颁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各教育,唯未标明实用主义”,使“美育”的理论和实践受到阻滞。然而,新的思想势不可当,1917年8月1日,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蔡元培在《新青年》上撰文,旗帜鲜明地提出著名论断“以美育代宗教”:“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阻者也。主张舍宗教而易之以纯粹之美育,即通过美感教育来陶冶人的品质。”⑥正是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引导下,儿童歌舞剧这一儿童戏剧样式得以创生,并以追求真善美、培育儿童健康身心、帮助儿童感受戏剧音乐之美等为宗旨,践行着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总之,儿童歌舞剧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生得益于“美育”思想的引导。
(三)“国语运动”的推动
“国语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国语运动”酝酿于19世纪末,与“白话文运动”相呼应,以“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为口号,以1917年“国语研究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标志而崛起,作为“五四”之后的一项语言变革运动,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此时掀起的“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关乎语言的变革行动,更重要的是,语言背后所映射的国民思维、社会文化和民众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革。⑦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进而使“国语运动”成为一场异常艰难且需发动社会各阶层、动员各种力量、辐射多方领域的变革运动。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期待儿童成为推行“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成为一种必然,一些新办学校将此前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学堂乐歌歌词改为白话文歌词;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儿童歌曲也以白话文歌词歌曲居多,使得用国语白话文作为台词和唱词的儿童歌舞剧应运而生,进而成为推行“国语运动”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黎锦晖就是 “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在其胞兄黎锦熙的影响下,提出“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并借助儿童歌曲和儿童歌舞剧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有力配合“推广国语”全民教育运动的开展⑧,儿童歌舞曲(如《空中音乐》《老虎上门》《可怜的秋香》等)和儿童歌舞剧,均是“推广国语”的实用教材。黎锦晖于1922年4月创办《小朋友》文艺周刊,此刊所载的大量白话文儿童文艺作品(包含12部儿童歌舞剧剧本和一批儿童歌曲曲谱)是推行“国语运动”的见证。“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为此后儿童歌舞剧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使白话文剧本在歌舞剧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被认同,进而推动了中国戏剧的发展。“国语运动”为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带来了绝佳的文化语境,其中的语言变革也使得儿童歌舞剧的创演者与受众达成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和统一,顺应了历史潮流;尤其是“春蜂乐会”作曲家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更表现出与“国语运动”的密切关系。
(四)“西方戏剧”的传入
“西方戏剧”的传入也是影响中国儿童歌舞剧创生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门洞开,许多沿海城市都设立了租界,并成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前沿;从1845年起,各国传教士和经商者都以各种名义前往上海,北方的哈尔滨也因中长铁路的修建,聚居了大批俄侨,这便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前提;大量外籍人士入境并侨居中国,使西方的戏剧(话剧)、歌剧、交响乐、芭蕾、油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传入中国,一些包括音乐家在内的西方艺术家也将其艺术活动延展至中国;在这一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中,俄侨占比最大,其在上海和哈尔滨创办俱乐部、开展艺术培训,频繁的文艺演出活动大大促进了侨民与中国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据《申报》报道,20世纪上半叶,东京、意大利等著名歌剧团和欧洲知名艺人曾携多部剧目赴沪进行商业性演出;同一时期,一些在国外求学的学者和艺术家也纷纷归国,并以极大的热情向国人介绍欧美的戏剧和音乐,出版了许多相关的著作或译作,其中张若谷的《歌剧ABC》(1928年)是最早向国人介绍西方歌剧的通俗读物。⑨这一时期西方文化艺术的传入为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创生提供了良好氛围,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之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于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于地理,受之于历史,胎之于思想,播之于风俗,此等特性。有良焉,有否焉。良者务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必采用他人之可以补助我者,吸为己有。”⑩当今世界是民族的世界,各民族之间只有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但长期以来,国人一直沉浸在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对涌入的西方戏剧,特别是“歌剧”这种“舶来品”,需经历一段漫长的消化过程,从接受到理解,然后开始仿效,这也正是早在17世纪歌剧就传入中国,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国人才尝试创演歌剧的原因。这个尝试者就是黎锦晖,正是这位致力于儿童音乐和儿童歌舞的作曲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发现了“儿童”,践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配合“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汲取早期“文明戏”(话剧)创演经验,尝试创作儿童歌舞剧,并开启了歌剧在中国得以创生和发展的篇章。
二、“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历史演进
在早期中国歌剧的理论语境中,“儿童歌舞剧”与“歌剧”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理论范畴,但这并不限于两者之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不因为黎锦晖曾用“歌剧”指陈其儿童歌舞剧。一方面,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的一部分,是中国歌剧的雏形,其创生与发展为中国歌剧的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支撑和影响;另一方面,歌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同时基于儿童歌舞剧的中国歌剧也“反哺”了儿童歌舞剧的发展,因此,在探讨20世纪上半叶儿童歌舞剧或中国歌剧的历史演进时,“儿童歌舞剧”和“歌剧”可合并为一个整体范畴,即“儿童歌舞剧—歌剧”。其整体性在于前者对后者的铺垫,后者对前者的辐射,两者同在一个互融互补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
(一)“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先期探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人们重新发现了“儿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倡导“国语运动”,同时西方戏剧也不断传入。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催生出黎锦晖及其后“春蜂乐会”作曲家的儿童歌舞剧。但无论是将艺术视角指向“儿童”,还是助力“美育”、配合“国语运动”、借鉴西方戏剧,创演儿童歌舞剧的目的均是配合学校教育,启发儿童心智,也是先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前期)儿童歌舞剧创生的内在动力。兴起于清末民初、率先在新式学堂推广的“学堂乐歌”,体现了富国强兵的救亡思想、培育新民的启蒙意识,以及“乐教”的思想。但在黎锦晖看来,基于“学堂乐歌”的“乐教”不足以完成这种启蒙,于是其对儿童歌舞剧报以极大热情,进而使中国歌剧的百年历程得以开肇。黎锦晖以开展“美育”和推广“国语”为突破口,借鉴西方戏剧(“歌剧”“戏剧”),以启发儿童心智为目的,创造出以“话剧加唱”为基本戏剧表达模式且载歌载舞的儿童歌舞剧。黎锦晖不满足于“学堂乐歌”,且熟悉京剧、昆曲、花鼓戏等地方戏曲,精通多种民族乐器,接触过西方音乐文化(如西方乐理、美声歌唱、钢琴音乐、风琴音乐),故能借鉴西方戏剧并在中西结合的“视界融合”中创造出初具“歌剧思维”的音乐戏剧样式,进而汇入“五四”以后重视“儿童教育”“平民教育”的社会思潮。黎锦晖以《麻雀与小孩》为开端,陆续推出《葡萄仙子》《最后的胜利》《春天的快乐》《七姐妹游花园》等12部今天被视为经典剧目的早期儿童歌舞剧,力图让孩子们在依托戏剧手段所营造出的“真”“善”“美”戏剧情节中受到启迪。
尽管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更多地借鉴了“五四”以前“文明戏”(即“话剧”⑪)中“新剧与中国现代(民间)小调的融合”的戏剧表达方式,即后来所说的“话剧加唱”⑫,但又在借鉴西方音乐戏剧的过程中显露出朴素的“歌剧思维”,即一位论者所说的“初显端倪的歌剧思维”⑬。素朴的“歌剧思维”是20世纪中国歌剧逐渐成为“音乐戏剧”的重要因素,更具“歌剧思维”且作为“音乐戏剧”的其他样式的中国歌剧,又成为儿童歌舞剧得以不断发展的参照,进而营造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歌剧或戏剧的整体文化氛围。
其后“春蜂乐会”作曲家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和沈秉廉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如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一样,在这种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生成,保持着启发儿童心智的价值取向。“春蜂乐会”作曲家均求学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师承一脉,在音乐创作和作曲技法理论上,均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较正规的学习和训练,因此在戏剧结构的把控和作曲技术的运用上具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使其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更接近西方的戏剧、歌剧。偶有采用选曲填词的手法,但在戏剧结构形式上更接近西方的校园小歌剧,且大多题材新颖,呈现出中西融合的原创曲调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儿童歌舞剧的剧本采用五线谱为主、简谱为辅的双版形式刊印发行,其中一些剧目的唱段附有钢琴伴奏,其音乐风格也以中西融合化风格为主,替代了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中植根民间音乐的风格,因此“春蜂乐会”作曲家的儿童歌舞剧更具有歌剧的“音乐戏剧”特征,我们可在1926年至1936年十年间的《名利网》《广寒宫》《天鹅》《面包》等22部儿童歌舞剧中找到佐证。以上海为核心,20世纪20年代涌现了由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叶圣陶编剧、何明斋作曲的童话歌剧《蜜蜂》(1923年)、儿童歌剧《风浪》(1923年)等剧目,这些剧目注重剧本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成为“儿童歌舞剧—歌剧”的一种类型。
(二)“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后期实践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儿童歌舞剧—歌剧”在新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展现出新的发展格局。一方面,中国歌剧创作依托20年代至30年代初儿童歌舞剧的探索经验正式起步;另一方面,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歌剧实践又“反哺”儿童歌舞剧创演,使得儿童歌舞剧获得新的发展,进一步体现了“儿童歌舞剧—歌剧”这一理论范畴。
于1930年推出的五幕歌剧《王昭君》曾被认为是中国歌剧的开篇之作。作为一部中国歌剧,《王昭君》表现出中国歌剧探索者对西方歌剧的改造,将“广东传统音乐”和“传统戏曲身段”与“美声”及四件西方乐器融为一体,用全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因此,《申报》认为这部歌剧“为未来的歌剧开一条新的道路”⑭。如果说《王昭君》的创作与前期儿童歌舞剧的关系尚不明显,那么1934年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扬子江暴风雨》则与前期儿童歌舞剧的探索有着内在联系。这不仅因为聂耳与黎锦晖之间的“师承”关系,而且在于这部“左翼”歌舞剧保持了从早期“文明戏”(话剧)到黎锦晖儿童歌舞剧、“春蜂乐会”儿童歌舞剧一以贯之的“话剧加唱”模式。尽管《扬子江暴风雨》的话剧色彩十分浓厚,其中的音乐也不过是几首作为插曲的歌曲,以致有学者作出“是歌剧还是话剧”的辨析,但其“话剧加唱”的歌剧模式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种戏剧表达方式与早期儿童歌舞剧不无关系,无论是继承戏曲的《王昭君》还是借鉴早期“文明戏”成果的《扬子江暴风雨》,其中的探索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早期儿童歌舞剧有关联。以早期儿童歌舞剧为文化积淀,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音乐家和戏剧家致力于探索中国歌剧,短短十年内就推出了《西施》《农村曲》《桃花源》《洪波曲》《大地之歌》《秋子》等真正具有歌剧或“音乐戏剧”特征的剧目。尤其是1942年在重庆首演的《秋子》,作为第一部较为成熟的“正歌剧风格歌剧”,运用了咏叹调、宣叙调,以及合唱、重唱、序曲、间奏等音乐形式,初步体现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音乐戏剧”品质。尽管一些剧目与早期儿童歌舞剧无直接关系,但后者对前者的铺垫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歌剧的实践正式起步,儿童歌舞剧得到新的发展。这一时期,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曲《可怜的秋香》在中央苏区被重新填词为《可怜的白军》,自此,儿童歌舞剧这一戏剧样式在苏区得以呈现。随后,《高举起少年先锋队的旗帜》⑮等儿童歌舞剧应运而生,其保持了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基本格局,其中的音乐也均为旧曲填词的歌曲。进入全民族抗战以后,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解放区,儿童歌舞剧均得到较大发展。从抗战时期的《小鸟与蜜蜂》⑯、《乞儿的梦》⑰(均1935年)、《梦神》⑱(1936年)、《姑娘不见了》⑲、《小山羊》⑳、《跳舞破了的鞋子》㉑(均1944年)、《秦奋宝放牛》㉒(1945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莫把小孩看不起》㉓(扬大戈编,1946年)、《老狐狸偷鸡》㉔、《生命的锁匙》㉕(均1947年)、《小弟弟和小公鸡》㉖(1948年)、《春姑娘》㉗、《仙女送报》㉘(均1949年),加上国统区儿童歌舞剧的创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整体逐渐凸显出“音乐戏剧”特点,其思想主题也由“启蒙”变成了“救亡”,并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民主运动相呼应。一方面,其发展得益于前期儿童歌舞剧的探索经验;另一方面,是创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歌剧创演经验的“反哺”,从《王昭君》到《秋子》,正歌剧风格歌剧的探索为儿童歌舞剧创演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儿童歌舞剧作为“革命叙事”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如1940年由高阳作词、方冬(李鹰航)作曲、夏静编舞的《小小锄奸队》㉙就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歌舞剧。该剧讲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某村儿童锄奸队捉拿汉奸和奸商的故事,1940年4月10日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开学典礼上首演,就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1942年,该剧剧本及插曲连载于国统区《新音乐月刊》(第5卷第2、3期),并在国统区得到传播;类似的剧目还有1941年抗敌剧社创演的四幕儿童歌舞剧《乐园的故事》(汪洋、红羽、崔品之、洛灏等编剧,徐曙作曲)㉚等。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叙事”的儿童歌舞剧以不同的形式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发展,尽管其数量不多,但演出效果较好,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尤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儿童演出团体,在抗战时期对儿童歌舞剧的创作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国统区的儿童歌舞剧一样,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儿童歌舞剧也得益于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和30年代中期以来歌剧的滋养,尤其是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对儿童歌舞剧的创演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儿童歌舞剧,在其后近30年(至1949年)的时间里得到较大发展,不仅走出了“创生(模仿)—探索(创新)—发展(中国化)”的历史轨迹,而且为新中国歌剧的发展提供了文化积淀,进而展现出“儿童歌舞剧—歌剧”这一整体理论范畴的历史与文化特征。
三、 早期儿童歌舞剧的历史意义
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雏形,在中国歌剧的百年历史发展中具有先导作用,并为中国歌剧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其在中国歌剧乃至整个舞台演剧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通过黎锦晖及其后“春蜂乐会”作曲家等一大批从事音乐教育、音乐创作、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儿童歌舞剧在叙事方式、戏剧结构、音乐设计及表演导演方面均有较大提升,逐渐显现出其“歌剧思维”和作为“音乐戏剧”的艺术特征,进而成为中国歌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正是早期儿童歌舞剧在“儿童歌舞剧—歌剧”这一整体语境中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早期儿童歌舞剧借鉴西方歌剧、西方戏剧(drama、话剧)和校园小歌剧,将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力图凸显中国特色、贴近儿童生活、追求趣味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创演模式,也为中国歌剧借鉴西方歌剧、继承中国传统、满足现实需要的价值取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学术界关于早期儿童歌舞剧历史意义的研究较多,但大多数是建构在“歌剧思维”和“音乐戏剧”的本质特征上,未能在“儿童歌舞剧—歌剧”这一整体语境中充分探讨儿童歌舞剧在中国歌剧百年历史发展中的先导地位和铺垫作用。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开启“儿童歌舞剧—歌剧”国语白话模式
儿童歌舞剧的创生发展是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中开始的。黎锦晖受其胞兄黎锦熙的影响,积极促进国语推广,依托儿童歌舞剧宣传国语,践行其“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理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对白和歌词采用白话表述,强调语言与音乐的结合,使歌唱更加贴近生活、接近口语。因此,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得以广泛传播,尤其得到了儿童的喜爱,配合“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也开启了“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国语白话模式。
黎锦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显露出鲜明的国语白话风格。“你不要慌,你不要忙,飞了上去,要提防。老鹰老鹞很可怕,坏心肠,那你要提防。也有那猫大王,还有那蛇大娘,他们都能够爬上墙,他们都能够爬进房。”㉛这是剧中老麻雀的唱词,其白话风格鲜明可见,同时也与戏曲韵白和唱词的文言或半文半白风格大异其趣。自此,国语白话儿童歌舞剧脱颖而出,不仅开创了中国白话儿童戏剧的先河,而且使国语白话风格的对白与唱词成为“儿童歌舞剧—歌剧”的重要识别特征。国语台词和唱词与早期“文明戏”中的对白(京白)和五四以后的“话剧”(或“新剧”“白话新剧”)共同推进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为包括歌剧在内的国语白话戏剧的创生发展作出重要铺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言文、白话文和文白相间几种文体风格在中国并存,但随着“国语运动”的不断深入,国语白话逐渐被更多的国人接受。因此,黎锦晖及“春蜂乐会”作曲家选择儿童歌舞剧,并使其作为推广“国语”和“白话文”的载体,国语白话儿童歌舞剧也广受欢迎,并得以传播。可以说,“国语运动”成就了儿童歌舞剧,儿童歌舞剧也成就了“国语运动”。受成功效应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歌剧探索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使用白话风格的对白和唱词;另外,早期儿童歌舞剧的对白和唱词本身也十分考究,不仅具有白话新诗的风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春蜂乐会”作曲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再加上享有盛誉的文学界泰斗(如赵景深等)的参与,儿童歌舞剧的对白和唱词更具文学性,其叙事性与文学性兼具。总体而言,儿童歌舞剧的对白与唱词不仅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身心特征和接受能力,而且十分注重本身的韵律感,为旋律写作带来便利,反之,其旋律往往也能凸显国语白话的韵律。在《恶蜜蜂》《蝴蝶鞋》等剧目中,剧作家在写作歌词时,多采用对称、押韵、排比、拟人等修辞方法,以五言和七言居多,形成对称式的歌词结构,力图体现出歌词本身的形式美感,这种具有形式美感的唱词不仅有助于旋律的写作,而且更适合“国语”和“白话文”的推广。
因采用国语白话模式,“儿童歌舞剧—歌剧”与文言或半文半白风格的京剧(Beijing Opera)乃至整个中国戏曲迥然不同,成为继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俄语、英语歌剧后的又一新语种(“母语”)歌剧—中文歌剧。
(二) 初现“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
如果说“歌剧思维”涉及歌剧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数”,那么“以音乐承载戏剧”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歌剧思维”,也是歌剧作为“音乐戏剧”的本质特征所在㉝。但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中,“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仅仅显露端倪。“歌剧思维”最早在黎锦晖和“春蜂乐会”的儿童歌舞剧中得以呈现,并诉诸对西方歌剧和中国戏曲的借鉴。关于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中的“歌剧思维”或“歌剧观”,居其宏、满新颖等歌剧理论家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㉞,以下笔者仅对唱段音乐的形态特征进行补充。
早期儿童歌舞剧已显露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创作意图,通过音乐的戏剧性配合对白和唱词进行戏剧表达,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运用音乐的宣叙性叙事。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中的演唱形式多以对唱为主,以表现人物之间的对话,但这种对唱是具有宣叙性的,进而具有较强的叙事性,体现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
第二,采用重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凸显音乐的戏剧表现功能。例如,在1927年创作的《小羊救母》中运用重唱,凸显了音乐的戏剧表现功能,为戏剧表达服务。黎锦晖和“春蜂乐会”儿童歌舞剧中合唱、重唱的运用,也旨在“以音乐承载戏剧”。由此可见,借鉴欧洲歌剧的演唱形式,将重唱、合唱引入儿童歌舞剧是黎锦晖儿童歌舞剧探索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作为“音乐戏剧”的最早征兆,其历史意义毋庸置疑。
第三,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唱段还借鉴了中国戏曲中板腔体唱段的结构原则,进而体现出通过板式变化推动情节发展和矛盾展开的意图。这在其首部儿童歌剧舞《麻雀与小孩》中得以显现,每一场音乐都存在速度上的变化和对比,尤其在后来的《小小画家》中更为明显。这使音乐具有一种速度或板式变化而形成戏剧性,进而体现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唱唱段中的宣叙性,还是重唱唱段的启用,唱段之间速度和板式的变化,其目的都在于强化音乐本身的戏剧表现功能,旨在实现“以音乐承载戏剧”的目标。这种对音乐戏剧表现功能的强化对于“儿童歌舞剧—歌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早期儿童歌舞剧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总之,黎锦晖及“春蜂乐会”作曲家的儿童歌舞剧已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音乐的戏剧性,即抒情性、叙事性和冲突性。黎锦晖和“春蜂乐会”的作曲家不断学习西方歌剧和中国戏曲,通过“音乐的冲突性”推动戏剧情节发展和矛盾展开,以凸显音乐的戏剧张力,进而刻画剧中人物在戏剧冲突中的心理变化与情感层次。如《小小画家》一剧,其音乐中充满具有讽刺意味和情绪表现的冲突,并初步体现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和作为“音乐戏剧”的本质特征。这种微不足道的“歌剧思维”,在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发展中留下一颗可贵的种子。
(三) 建构中国歌剧的戏剧结构空间
歌剧的戏剧结构空间,即一部歌剧的戏剧情节发展与戏剧矛盾展开所构建并最终呈现为戏剧冲突的叙事场域。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戏剧叙事,既有戏剧情节发展(故事“起因—发展—结局”),又有戏剧矛盾展开(矛盾“建构—发展—激化—解决”),在戏剧情节发展和戏剧矛盾展开中,构成完整的叙事场域,即戏剧结构空间。这意味着,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的雏形,一开始就给观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空间。
以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为例,其儿童歌舞剧共12部,其中第一阶段(1920—1925)的7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长恨歌》《三蝴蝶》《春天的快乐》《七姐妹游花园》)呈现出完整的戏剧结构空间。上述剧目既有戏剧情节发展,又有戏剧矛盾展开,且体现出戏剧情节发展与戏剧矛盾展开的同步性(或一致性)。正如歌剧理论家居其宏所说:“黎氏第一阶段的作品,其情节框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比性的戏剧矛盾上的:例如葡萄仙子在其成长过程中与帮助她成长的五位仙人的关系,与频频向她索取的喜鹊、甲虫、山羊、兔子、白头翁的关系,以及与她甘愿为之奉献果实的哥哥妹妹的关系,都是一种对比性关系。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戏剧矛盾,带有某种象征性和寓言剧的色彩,其戏剧性张力也比较微弱,还不足以构成戏剧冲突。其他如《三蝴蝶》中蝴蝶与花、与风云雨雷电的关系,《春天的快乐》中忧愁公主与花、虫、鸟及邻家姐弟的关系,《七姐妹游花园》中万花仙子、布花仙童与人间七姐妹的关系,也都是这类对比性关系。”㉟这种对比性关系呈现出以戏剧情节发展为戏剧结构外形的内在戏剧矛盾展开。这种外在的戏剧情节发展与内在的戏剧矛盾展开,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空间,一个叙事场域。在黎锦晖第二阶段(1925—1927)的5部剧目(《神仙妹妹》《最后的胜利》《小小画家》《小羊救母》《小利达之死》)中,其内在的矛盾展开更为明显,并将戏剧的发展诉诸戏剧矛盾展开—“建构—发展—激化—解决”。第二阶段剧目的戏剧结构空间是一个戏剧矛盾的发展空间,一个建构在戏剧情节发展之上的叙事场域。但较之第一阶段的7部剧目,其内在的戏剧矛盾冲突更为激烈。如居其宏所说的:“到了第二阶段,黎锦晖明显地引入了‘戏剧冲突’的概念,使对比性关系发展为对立性关系,从而大大强化了戏剧矛盾的力度,将情节真正建立在戏剧冲突的基点之上。”“这一积极变化是从《神仙妹妹》开始的:在本剧中,黎氏将剧中人物分为以三个小朋友、神仙妹妹和山羊、鸽子、蟹为正义善良一方,以狼、鹰、鳄鱼、老虎为邪恶一方的两个对立阵营,写邪恶者捕食弱小动物,被神仙妹妹和三个小朋友击退,后又与老虎进行决战,大家在神仙妹妹带领下智取老虎,获得最终胜利。在本剧的情节铺陈中,除了加强戏剧冲突的力度之外,另外一个积极变化就是强化了人物的戏剧行动,使情节展开和戏剧冲突不仅仅通过语言和表情,更通过人物自身的戏剧行动和舞台动作来实现,而这一点正是戏剧作品最重要的标志之一。”㊱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戏剧结构空间作为充满戏剧冲突的叙事场域,须具有一定的篇幅,因此产生了“多幕剧”的儿童歌舞剧。如陈啸空与沈醉了(沈秉廉)合作的《成功与自助》就是典型的三幕剧结构。而邱望湘的《天鹅》是六幕结构的作品,超越了儿童歌舞剧的一般规模,标志着儿童歌舞剧在戏剧结构及音乐结构上的稳步扩展,并显示出中国儿童歌舞剧向歌剧的过渡。
早期儿童歌舞剧中,由戏剧情节发展与戏剧矛盾展开共同构建的戏剧叙事场域,也为后来中国歌剧建构了一个充满戏剧矛盾的戏剧结构空间。
(四) 搭建中国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
早期儿童歌舞剧受西方戏剧影响,又吸收中国传统戏剧和传统音乐因素,进而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融歌、舞、剧等诸多元素为一体的新型戏剧样式,搭建起中国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从表演形式上看,早期儿童歌舞剧综合了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舞美、服装、化妆、道具等多种表现形式,体现出综合艺术的基本格局。比如,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中加入了较多舞蹈,甚至在《葡萄仙子》的脚本中详细标注了舞蹈的技术特点和要点;另外,其儿童歌舞剧还十分重视舞美及服装、化妆和道具,黎锦晖在其每个脚本中都明确了对布景和化妆的具体要求,甚至还有关于道具制作材料质地、制作方式及成本等问题的描述和规定,虽然在具体表演时,还是追求从简、从易、从新,但在事前的脚本写作中,他会事无巨细、十分清楚地规定和描述舞美、服饰、化妆、表演、舞法、道具、登场人物关系等;在其每个剧目的脚本中,均有关于“登场人物及服饰”“布景略记”“道具略记”等事项的说明,如《神仙妹妹》的脚本中有对“登场人物及服饰”的规定。因此,可以说早期儿童歌舞剧创作将舞台上各种元素及其呈现方式均考虑在剧目的脚本中,为中国歌剧搭建起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尽管早期儿童歌舞剧的结构和容量不大,没有歌剧的宏大场面和磅礴气势,但以音乐、舞蹈和戏剧为主体搭建起的基本构架是清晰的,为后来中国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形成奠定了基础。
结 语
20世纪上半叶,以黎锦晖及“春蜂乐会”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儿童歌舞剧,在“美育”和“国语运动”的推动下,借鉴西方戏剧样式而创生,反映出时代对“儿童”的发现和关怀。其发展在“儿童歌舞剧—歌剧”的整体语境中实现,其中既有儿童歌舞剧探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歌剧探索的支撑和影响,又有歌剧创演经验对儿童歌舞剧的“反哺”,展现出儿童歌舞剧与歌剧的互动和转化。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中国歌剧的雏形,开启了中国“儿童歌舞剧—歌剧”的国语白话模式,显露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构建了中国歌剧的戏剧结构空间,搭建了中国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基本构架,在中国歌剧百年历史发展中具有先导地位和铺垫作用。早期儿童歌舞剧作为特定历史与文化语境下的产物,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其创生和发展离不开西学东渐所带来的影响,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浸染。其对中国歌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体裁、样式、语言、形式和风格上,均为后来中国歌剧创演提供了较早的模板。这正是早期儿童歌舞剧的历史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