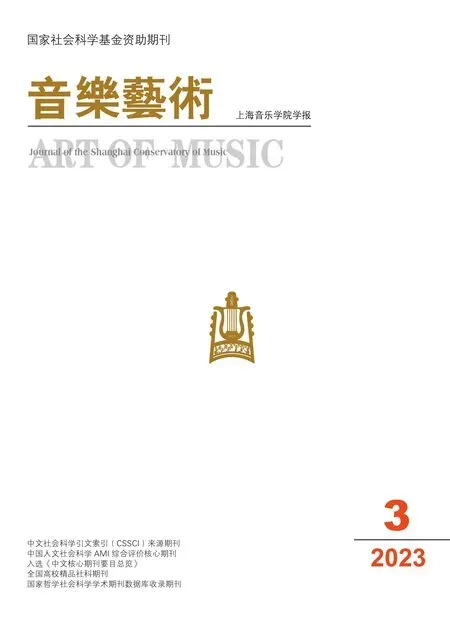中国钢琴曲的“中国风格”之辨析
谭缨英
内容提要: 中国钢琴曲的“中国风格”或“中国风格钢琴曲”早已成为中国钢琴音乐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但其所指一直不明。“中国风格”既以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征的音乐语言为表征,又以这种音乐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为精神内涵,因此“中国风格”的实现旨在用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征的音乐语言去“模拟”“象征”“类比”与中国相关的物质和精神。“中国风格”既应诉诸特定的感性音响,让听众获得听觉上的认同,又需要诉诸只能依赖于理性感知的观念及其形态。
对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的探索始于20世纪初。如赵元任在作品《偶成》(1917年)中运用天津传统曲调,探索钢琴作品的“中国风味”①。当时采用民间曲调创作的还有沈仰田的《钉缸》(1921年)、郝路义( L. Hammond)的《梅花三弄》(1921年)等。1934年11月,美籍俄裔钢琴家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1899—1977)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活动是唤醒中国作曲家探索“中国风格”钢琴曲的标志性事件,自此开启了西方钢琴与中国音乐的对话和交融。在此次活动中获奖作品有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摇篮曲》、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这些作品是探索“中国风格”钢琴作品的“开山之作”。其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最为成熟,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完全成熟的钢琴曲”②。1940年代,丁善德的钢琴曲集《春之旅》(1945年)、瞿维的《花鼓》(1946年)等作品继续更为深入地探索中国钢琴曲的“中国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桑桐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1952年)、陈培勋的《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1952年)、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第二新疆舞曲》(1955年)等作品从中国不同民族、地区的民间曲调中汲取养分,发展“中国风格”。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风格”钢琴曲更如雨后春笋,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随着“中国风格”钢琴音乐创作的不断发展,对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的理论思考也氤氲而生。何为“中国风格”,学者对“中国风格”的概念与内涵、“中国风格”钢琴音乐史、钢琴音乐创作、表演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探讨③。目前,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但其所指一直不明。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中国风格”的构成要素、实现手段、审美与文化认同等方面进行梳理,以发掘中国钢琴“中国风格”内涵特征。
一、“中国风格”的构成:音乐语言与精神内涵
“中国风格”钢琴曲作为一种音乐创作,其“中国风格”既诉诸音乐形式的“中国风格”,还包括音乐内容的“中国风格”。所谓音乐形式的“中国风格”意指基于作曲技法的体裁、语言和风格上的中西对话与融合,寓于中国钢琴曲的音乐语言。所谓音乐内容的“中国风格”意指中国钢琴曲主题内容的精神内涵,源于中国的现实生活。④
(一)“中国风格”音乐语言
近百年来,“中国风格”的音乐语言探索是中西音乐创作对话过程,作曲家将中国传统音乐、戏曲音乐的调式、结构、旋律、节奏等元素引入中国钢琴曲创作,赵晓生将中国钢琴音乐语言总结为“声韵、气韵、装饰、音色、节奏、奏法、踏板、结构”八个方面,认为这些音乐语言对世界音乐文化具有重要贡献。⑤这种探索体现在西方音乐语言“民族化”、中国传统音乐“西方化”两个方面。
1. 西方音乐语言“民族化”
20世纪初,西方音乐本土化产生了“新音乐”,在“全面西化”“中西融合”的语境下,作曲家全面开展对西方音乐语言诸如和声、曲式、复调对位的全面学习与“有限”改造。作曲家要处理好中国传统音乐线性思维与钢琴音乐多声思维间的关系,首先是中国钢琴的和声语言“民族化”。和声作为重要的音乐语言,其民族化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赵元任曾指出,中国原本几乎没有和声,“中国派”的和声探索需把和弦或复调做得像中国的乐调,同时又可以配合得上主调。⑥关于如何形成“中国风格”和声,贺绿汀确立了“中西融合”的基本原则,即解决中国和声问题,需要学习欧洲古典传统和声,特别是从19世纪民族乐派大师的作品中汲取成功经验,了解其如何从古典传统经验中创造自己的民族音乐。⑦
因此,对中国钢琴作品“民族化”的探索,首先是基于对西方古典传统功能和声的学习与延展,即遵循西方传统三度叠置和弦的连续平行进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改造”。如贺绿汀的《摇篮曲》与格里埃尔同名乐曲的和声基本相似; 《牧童短笛》的B段模仿学习莫扎特《变奏曲》的和声;钢琴协奏曲《黄河》模仿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肖邦《降A大调波罗乃兹》等乐曲和声。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中国传统的五声性功能和声,作曲家将中国五声调式体系与西方大小调功能和声相融合,呈现出三度叠置的三和弦基本样态。
其次,西方曲式结构“民族化”方面,赵元任的《偶成》虽采用了天津民间曲调,但本质上,其还是西方音乐中的“音乐瞬间”或“即兴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是一首运用传统五声调式音阶、旋法的二声部复调作品; 《摇篮曲》则具有浓郁中国风味的单三部曲式作品;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和陈田鹤的《序曲》直接采用西方音乐体裁,凸显出作曲家对民族风格的追求。
再者,复调对位“民族化”方面,以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创作最为成功,其融合了西方对位技法与中国传统五声调式旋法,形成一个二声部的对位织体,且每个声部完全是五声性的旋律。此后,中国作曲家在多声部钢琴曲创作上继续探索。瞿维在《花鼓》第三段,将两首民歌《凤阳花鼓》《茉莉花》的主题对置,形成二声部对位织体,且具有“装饰性支声复调”⑨的性质。丁善德在《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中运用中国特色支声复调和其他复调手法,使得作品的主题、不同主题、不同声部的形态不一,疏密对置。⑩
总之,早期中国作曲家运用中国传统的音阶、调式、旋法进行中国风格音乐创作,并以之与西方音乐创作技法相结合,即西方音乐语言“民族化”。其本质是模仿西方音乐创作的大小调功能和声、曲式结构、复调对位法等,探索出基于中国传统民族调式体系的五声性功能和声与复调对位手法。这种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的音乐语言是基于西方音乐语言之“形”,又融入了“中国风味”。
2. 中国传统音乐的“西方化”
随着中国钢琴“中国风格”创作的进一步探索,中国钢琴音乐语言除西方音乐语言“民族化”外,更多地向着中国传统音乐的“西方化”方向发展。首先,在和声语言方面突破功能性和声,在非传统功能和声、五声纵合化和声、线性逻辑和声等方法上进行探索。中国传统音乐存在“凭听觉直接感知的音响效果”的色彩性和声,无需遵循既定的和声原则。这与西方现代和声基于和声结构的和声色彩特点不谋而合。⑪在非功能和声方法中,不必遵守和弦三度叠置原则,使用四度叠置、二度叠置、以四/二度叠置为基础的各种附加音和弦、四五度叠置和弦各种偶成和弦等。如储望华的《翻身的日子》《兄妹开荒》中使用小二度音程;叶露生的《蓝花花的故事》低声部中大量运用纯四度、大二度的色彩学和弦。在五声纵合化和声方法上,以桑桐的《内蒙古主题小曲七首》最具有代表性,其中第三首《思想》右手部分直接使用民歌曲调的主题旋律,左手部分则采用五声音阶(含偏音)的流动形成和声支撑。另外,陈培勋的《平湖秋月》、黎英海的《夕阳箫鼓》等作品使用了这一方法。除此以外,复合功能的和声方法、自由十二音和声等方法的使用,使得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的和声语言具有更大的表现空间。
其次,在曲式结构上,中国传统音乐的西方化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西方化,而形成的独特的中国风格音乐语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赵晓生的《太极》,采用唐代“大曲”的结构特点,其“‘破、承、起、入、缓、庸、急、束’暗含‘八卦’,实际上来自唐大曲式的散—缓—庸—急—散的速度逻辑”⑫。除上述和声和曲式将中国传统音乐西方化外,调式、节奏、音色等音乐语言的运用,也从早期模仿阶段单纯地“引入”,到进行“西方化”的创作。如彭志敏的《风景系列》、陈怡的《多耶》等作品受中国传统“十番锣鼓”启发,探索出数控型的节奏组合模式。音色的“西方化”方面,运用古琴音响写作中国钢琴作品最多。黎英海的《夕阳箫鼓》,通过装饰音展现古琴游移、走动、虚实相间的音响特征。⑬这一技术在赵晓生的《太极》、周文中的《梅花三弄》《杨柳叶子青》,以及谭盾、赵晓生的钢琴协奏曲中,也得到大量运用,音响源于中国传统弦乐器板胡、二胡,弹拨乐器筝,吹管乐器箫、笛、唢呐、笙、芦笙等。
综上所述,中国钢琴“中国风格”音乐语言的丰富多样性是中西对话、本土与西方对话的结果。其音乐语言既有西方传统、现代的和声、曲式和复调,又有在中西对话中直接引入或间接发展的中国传统音乐语言,包含结构、调式、旋律、节奏、音色等,整体展现出西方音乐语言的“民族化”与中国传统音乐语言的“西方化”。
(二)“中国风格”的精神内涵
“中国风格”钢琴曲主题内容的精神内涵,源于中国的现实生活。其内容来源广泛,与中国历史、地域和民族相联系,作曲家在使用钢琴音响描绘时,自觉地将其总结、凝练、升华为某种文化精神。
1. “中国风格”钢琴曲主题内容
“中国风格”钢琴曲创作主要分为原创作品与改编作品。其中改编作品所占比例较高。这些原创或改编作品大多使用明确的标题作为曲名,也有兼用无标题音乐,或无标题音乐与标题音乐相结合的方式作为作品题名。⑭标题性”是“中国风格”钢琴曲的一大特征,这种标题性既体现在作品题名,也寓于作曲家的创作思路中,是“中国风格”钢琴曲内容的最直接体现。因此,“中国风格”钢琴内容以中国文学艺术、中国绘画、中国书法、风俗文化、民歌、民族舞蹈、民族器乐、戏曲等⑮为根基进行创作。
以文学艺术内容进行创作的作品,最为突出的当属黎英海改编的《阳关三叠》和王建中改编的《梅花三弄》。黎英海的《阳关三叠》根据唐代同名琴歌改编,原歌词由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发展变化而来,通过对“朝雨”“轻尘”等景物的描写,抒发对友人的惜别之情;王建中的《梅花三弄》构思于古曲《梅花三弄》。除此以外,林华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曲解集注》创作构思于晚唐诗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
以中国绘画内容进行创作的作品,最为突出的当属黄虎威的《巴蜀之画》。该作品以6首四川民歌为素材,描绘了巴蜀自然风光。朱践耳的《流水》虽以民歌作为主题,但其展现出画面式的写意效果。
以中国书法内容进行创作的作品,最为突出的当属汪立三《他山集》中的《商:书法与琴韵》。作品运用中国书法与中国古琴艺术的表现手法,音乐苍穹遒劲,旋律追求中国书法的线条感。⑯
以民俗文化内容进行的创作,有崔世光的《山东风俗组曲》。作曲家并未完整地引用某首民歌素材,而是高度提炼自小耳濡目染的民歌和戏曲音调,展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⑰
以民歌为内容进行创作的钢琴曲占据较大比例。这是由于民歌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且各地民歌能够展现中国人民精神气质。这类作品不胜枚举,如上文提及的《偶成》《牧童短笛》《钉缸》《锯缸》等原创作品,都在创作中采用中国民歌的曲调。改编作品有汪立三的《兰花花》、王建中的《浏阳河》《猜调》、桑桐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刘福安的《采茶扑蝶》等。这些作品运用民歌主题或主题元素,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以民族舞蹈音乐内容进行创作的有黎英海的《花灯》,展现出云南地区节日欢腾的场景。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储望华的《新疆随想曲》以新疆民间大型歌舞音乐“赛乃姆”作为创作源泉。
以民族器乐内容进行创作的有赵晓生的《冀北笛音》、王建中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王建中的《百鸟朝凤》、蒋祖馨《庙会》组曲中的《笙舞》、赵晓生的《苗岭笙舞》等。以戏曲音乐内容进行创作的有倪洪进的《练习曲四首之一》,构思于京剧曲牌;陈培勋的《卖杂货》,构思于广东粤剧曲调《卖杂货》《梳妆台》。作曲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历史文化积极探索,推出一系列中国音乐文化、民族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融为一体的优秀作品,以此为载体既使钢琴艺术在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获得人们的青睐与关注,也传播、传承了中国独有的精神特质和精神内涵。
2. “中国风格”钢琴曲精神内涵
关于中国钢琴曲的精神内涵,周为民将中国钢琴曲的精神与文化内涵总结为品格“中和深邃”、意境“静虚淡远”;⑱李成远认为,中国钢琴曲承载了“人生相交,天人合一”“和谐中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⑲代百生认为具体体现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中和含蓄”“气韵生动”⑳。以上观点是对“中国风格”钢琴曲精神内涵的总结,但钢琴作为“舶来品”,其精神内涵必然也是中西对话的结果。
“中国风格”钢琴曲的精神内涵诉诸钢琴作品的内容、主题和思想,源自中国的现实生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探索,“中国风格”钢琴曲高度展现出民族性、时代性的精神特征。作曲家总会不自觉地将“立足中国、表现中国、为了中国”的理念融入创作中。作曲家张朝谈及自身作品创作时,认为写“土风”作品注重原生态鲜活的生命力和乐观精神;写“古风”作品注重中国古代文化的空灵诗意;写“自然”作品注重自然的朴素、宁静、变化、平实、谦逊、广袤、超越。㉑“中国风格”钢琴曲精神内涵的民族性体现在其总是基于中国社会生活,无论在艺术表现对象(内容)上展现“中国性”,还是在音乐情感内涵上追求“中国性”。㉒其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寓于钢琴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既来源于中国古代以来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来源于近代“五四”以来民众启蒙、救亡图存的革命精神,还来源于中国当下现实社会的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作为西方乐器,其和声、曲式、旋法等音乐技法,也必然暗含了西方文化精神内涵。齐尔品等外国作曲家对“中国风格”钢琴曲创作的探索,特别是对多元文化融合观念和调性混合技术的探索,这种“中国精神”与西方作曲技法,特别是“现代作曲技法”的融合统一,对“中国风格”精神内涵表达方式具有启发价值。如桑桐运用具有神秘主义意涵,西方表现主义思想的无调性手法,创作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将调性和无调性两个观念上矛盾的创作手法融为一体㉓,在创新中仍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哲学“中庸调和”。因此,“中国风格”精神内涵也从一般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主题和思想逐渐发展为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维,寓于钢琴作品的音乐形式与音乐内容的统一体,众多学者将此喻为“气韵”,并旨在追求“气韵生动”的精神境界㉔。综上所述,“中国风格”钢琴曲精神内涵诉诸钢琴作品的内容、主题会让思想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方式,在与西方钢琴创作技法的对话融合中,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二、“中国风格”的实现:模拟、类比和象征
钢琴曲作为一种音乐艺术,以声音为表现手段完成音乐的“描绘、抒情、叙事”功能。作曲家运用旋律、节奏节拍、调性、和声、曲式等不同音乐语言要素,有机组合塑造音乐形象,使人产生视觉形象联想、情绪共鸣和抽象事物的想象。同时,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借助不同创作手法表现不同的内容和描写不同的对象。因此,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的实现,旨在用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征的音乐语言“模拟”“类比”“象征”与中国相关的物质和精神。
(一) 模拟
“模拟”这一创作手段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模仿论,认为艺术就是对自然的模仿。随着音乐模仿说的发展,定义发生改变,不仅是指的对自然界的模仿,还包括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及人的行为、性格、情感生活的模仿㉕。因此,中国钢琴曲的“中国风格”主要通过作曲家创作,模拟中国传统音乐形态。
首先是对中国传统器乐的模拟。作曲家对中国传统器乐中二胡、琵琶、古琴、筝、唢呐、扬琴作品进行改编与创作,如模拟二胡的有储望华的《二泉映月》、崔世光的《刘天华即兴曲三首》(《良宵》《光明行》《空山鸟语》)、朱世瑞的《夜深沉》;模拟琵琶的有江文也的《钢琴叙事曲“浔阳月夜”》《第三钢琴奏鸣曲“江南风光”》、黎英海的《夕阳箫鼓》、陆华柏的《浔阳古调》㉖、殷承宗、刘庄和储望华的《十面埋伏》等;模拟古琴的有王建中的《梅花三弄》《阳关三叠》;模拟筝的有江文也的《渔府弦歌》《典乐》;模仿唢呐的有王建中的《百鸟朝凤》;模拟扬琴的有陈培勋的《旱天雷》。另外,还有模仿民乐合奏的作品,如王建中的《彩云追月》、储望华的《翻身的日子》、魏廷格的《金蛇狂舞》等。对中国传统器乐模拟的最大难点在于对不同乐器音色的模拟,以及中国传统乐器“线性旋律”演奏的模拟。如储望华的《二泉映月》中,大量使用单倚音模仿二胡的滑音,使用钢琴颤音、上下波音模仿二胡上的颤音音响;黎英海在《夕阳箫鼓》变奏五“箫声红树里”中,设计左手声部为和弦琶音,模拟琵琶“扫弦”,右手使用颤音重复左手高声部,模仿琵琶“轮指”。《百鸟朝凤》原为吹奏乐器唢呐曲,钢琴为“打击弦鸣乐器”,两者的发声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以钢琴模拟唢呐音色无法做到“形似”,因此作曲家在“神似”方面加以考虑。㉗王建中在创作中为了模仿唢呐的艺术特色,以及作品中山林间各种鸟鸣的音响,使用了大量的“前倚音、颤音、波音、震音等装饰音润腔技法”,使用小二度倚音模仿布谷鸟、野鸡鸣叫;使用八分音符左手前倚音的装饰模拟唢呐的双吐技法效果;使用连续的颤音结合力度、速度的自由强弱、伸缩处理,模拟林间蝉鸣的画面。㉘由此可知,作曲家们多使用倚音、颤音等装饰音技法来模拟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技法。
其次是对中国传统戏腔和人声的模拟。作曲家在创作、改编“中国风格”钢琴曲时,多采用民歌、戏曲的旋律、唱段进行创作。因此,在中国钢琴“民族化”过程中,通过模拟性的音响组织技巧,生动地展现丰富多彩的民族声腔形态。如汪立三的《他山集》第二首《图案》,作曲家使用连续的十六分音符进行加花快速处理,并以和A为主、属和弦基音,模拟湖南花鼓戏民族声腔的独特韵味;㉙陈培勋的《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融广东粤剧小调,通过旋律加花、和声变形,结合西方变奏曲结构达到清新、明快的风格;丁善德则模拟《玉簪记》中的《琴挑》一折,创作出《降G大调序曲》;㉚张朝在《皮黄》【导板】中的前四小节,通过在F、上的重复、延长和前倚音,模拟戏腔中的反复“砸夯”。㉛
此外,作曲家通过动机上行的中断音调表现疑问,下行的短小动机表现叹息,断断续续的音调表现泣不成声,节奏尖锐有力的动机表现决心,节奏平稳柔和、连续出现的短小动机表现深情的倾诉等方式,实现人的语调模拟。另外,通过节奏、节拍的变化,时值的扩张、紧缩等手段来模拟人的行动,如行军、划船等。总之,作曲家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速度、节奏、情感情绪等以多种手段的模拟来实现“中国风格”。
(二) 类比
“中国风格”钢琴曲通常采用类比的创作手法,表现无音响特征可模仿的内容。如事物的形状、体积,距离的远近,光线、颜色等直观特征。作曲家依据“联觉”效应,即对某一事物质量、空间、时间、运动等性质,可以引起人们对相近事物的联想,㉜进而进行创作。首先,作曲家常采用柔和、流畅与高亢、奔放的不同音色,类比不同区域、民族之间的性格差异。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与老志诚的《牧童之乐》,两者均以“牧童”为中心塑造音乐形象,但贺绿汀运用婉转悠扬的音色音响处理、展现出南方牧童的形象,老志诚则以热烈活泼的音色音响处理象征北方牧童的音乐形象。㉝其次,作曲家也采用中国传统音乐散板节奏来类比流水、白云、晨曦、月光等景色。如王建中的《浏阳河》在引子、中部、尾部均使用散板,并结合九连音、六连音、十连音的节奏型,以不规则的节奏处理类比“水”的运动,描绘出浏阳河的宽广与惊涛骇浪。㉞再次,采用音乐的轻响变化的时间过程类别空间的移动。如汪立三的《商:书法与琴韵》(《他山集》第一首)中,对中国书法“草书”的视觉形象进行类比。作曲家通过类比“草书”书写时的运笔轻重缓急、字体线条粗细长短,通过视觉与听觉“通感”,运用旋律线条起伏与和弦“块状”旋律、和声停滞、节奏频繁转换变化、力度上的轻重对比来实现听觉上的“草书”描绘。另外,采用数列结构来类比建筑、景色等。罗忠镕在《花团锦簇》(《钢琴曲三首》之三)中采用“斐波那契数列”设计节拍节奏,来类比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景象。同样,彭志敏也运用“斐波那契数列”组织乐曲的结构,创造《风景系列》。
类比手法更多的是表现人情绪发生时的各种特殊生理、心理活动状态,音乐作为“感情的艺术”,可以动人地类比出各类细腻的内心活动。这类成功的例子在“中国风格”钢琴曲中不胜枚举。综上所述,类比手法常与模拟手法相结合,描绘无音响特征可模拟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都是物理层面形状、体积、颜色,或是具有运动形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精神层面的内容,如感情、爱憎等内容则需要使用更为深入的“象征”手法来进行描绘与联想。
(三) 象征
象征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旨在用事物某一具体的外部特征,象征性地表现其他事物㉟。这一手法可以描绘难以模拟、模仿的事物,或通过模拟或类比的音乐信息,进一步转意联想,达到象征的目的。作曲家往往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一事物特征的描绘,引发听众的联想,进而感受钢琴作品的“中国风格”。
这首先体现在中国钢琴作品标题的象征性。中国钢琴曲的标题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绘画、书法、历史等内容有十分重要的联系,作曲家拟定标题的方式主要是照搬和提炼。如《二泉映月》《夕阳箫鼓》《阳关三叠》《彩云追月》《浏阳河》等,照搬器乐、民歌、古诗词、歌剧、历史的标题;《 牧童短笛》《隔江相望》《随想组曲—灵隐之声》《巴蜀之画》《谷粒飞舞》等则是作曲家根据作品内容提炼而来。无论是照搬标题或是提炼标题,都继承了中国传统音乐标题“标意性”特点㊱,具有引发听众联想的功能。
其次,中国钢琴创作象征手法还体现在音乐形式要素和组织形态中,如旋律、调式调性、和声、节奏节拍、音色音响。作曲家作为音响组织者,其在创作过程中本身就有或多或少的“隐喻”,如钢琴协奏曲《黄河》中作曲家采用“一唱众和”的船歌号子、山西民歌《河边对口曲》、陕北民歌《东方红》的主题旋律,选取这些旋律象征作曲家希望通过作品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争取民族解放伟大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汪立三的《涛声》(《东山魁夷画意》第四乐章)描绘一幅我国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的壁画,描绘日本风格,融入中国元素,体现鉴真的崇高精神。作曲家通过模拟寺庙钟声加强鉴真伟岸的形象,融入中国佛曲《目连救母》音调,并采用日本“都节调式”音型织体,象征东瀛扶桑形象的、壮丽的波涛。罗忠镕在《托卡塔》(《钢琴曲三首》之一)全曲的整体对称原则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对称美学,使人联想到北京四合院、故宫等建筑群,体现出中国人对“对称美”的追求。赵晓生在《太极》中运用“虚”“实”结合,营造乐曲的意境和韵味,创造出独特“阴阳”思维的现代钢琴,体现出中国人追求“虚实相生”“阴阳调和”“刚柔相济”的“和合”思维。中国钢琴曲通过“标意性”标题引发听众的联想,有助于作品的审美与理解;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形式元素,如旋律、调性和声、节奏节拍、音乐音色等的象征性处理,呈现中国文学、绘画、书法、历史等场景与情感。
三、“中国风格”的认同:听觉认同与理性感知
自20世纪以来,中国钢琴借鉴西方钢琴艺术成就,融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和民族音乐的中西对话中,逐渐形成“中国风格”,但其在国内的重视程度与国际的传播影响力仍有不足。一部作品的完成需要通过创作、演出和欣赏三步,21世纪初,有学者表示中国钢琴的繁荣受困于“三不”,即“作曲家不太愿意写、钢琴家不太愿意演奏、听众不太愿意听”㊲。当下,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关注,对专业作曲家、演奏家的深入培养,以及相关赛事的持续推动,㊳“作曲家不太愿意写、钢琴家不太愿意演奏”的困境已经扭转,而“听众不愿意听”这一窘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听众的欣赏“困难”主要是对80年代以来,作曲家以个性理解和现代作曲技术的运用所创作的“中国风格”钢琴曲。缺乏听众欣赏的感情作品,其作为“中国风格”钢琴曲的价值判断会大打折扣。从创作层面来看,以具有中国传统、民族特征的音乐形式、内容、文化与哲学精神创作钢琴作品,可以被认定为“中国风格”钢琴曲,但基于听众的审美层面、文化层面乃至信仰层面的价值认同也是中国钢琴“中国风格”探索成功与否的考量标准。因此,中国钢琴“中国风格”价值判断最终应以中国人的价值认同为目标,遵从人的听觉认同与理性感知。
(一) 听觉认同
中国钢琴“中国风格”的百年历程经历了“从形到神”扬弃的过程。赵晓生从“形态”和“神韵”入手,归纳出中国钢琴创作的三重意境:“有形无神,形存神佚;有形有神,形神兼备;有神无形,得神忘形”。㊴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的音响从“显性”步入“隐性”,“从形到神”的“扬弃”中,“扬”的是中国传统气韵、文化、哲学思想等“传统的抽象化”之“神”,“弃”的是中国传统音乐曲调、和声、结构之“形”。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钢琴的创作中运用大量可感的民间曲调、调式音阶、题材内容、民族性的和声色彩等,是此时“中国风格”钢琴曲的标志性因素。80年代后,作曲家着手对这标志性因素进行消化吸收,并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前者在创作过程中,把具有民族性的旋律、和声和结构作为追求“中国风格”的重要手段,呈现出一种可被识别和接受的共同特征,如“五声音调的浪漫主义”“中国式的印象主义”等㊵。这一时期,中国绝大多数中国钢琴创作以“共性写作”为基础,具有西方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色彩,其作品短小精悍、旋律优美、织体精致、和声丰富、标题明确,具有可听性。特别是作曲家在和声民族化的探索,与西方19世纪末民族乐派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阶段,作曲家关注到浪漫主义音乐风格、德彪西式的印象主义音乐风格,特别是德彪西作品中的东方气质、色差性和声与中国的传统审美习惯相吻合,可自然地运用到中国钢琴的创作中。㊶因此,20世纪80年代前,大多数作曲家对中国钢琴“中国风格”的探索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中国风格”就是“民族风格”,钢琴作品越是具有地方色彩,越是能从民间音乐中汲取音调特色,越具有民族风格。这种“中国风格”钢琴曲的创作理念与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后依然有延续,出现如储望华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刘庄的《三六》、廖胜京的《钢琴前奏曲24首“中国节令风情”》、张朝的《滇南山谣》等具有可听性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潮音乐”的兴起,作曲家在“中国风格”的探索上展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放逐了可听性。此时,大批作曲家开始探索新技法,追求新的音乐结构,采用十二音技法或个人独创体系创作。现代技法的采用,使得中国钢琴作品在现代影响的基础上体现民族“神韵”。如汪立三的《东山魁夷画意组曲》《他山集—五首前奏曲与赋格》等作品,运用十二音技法表现中国传统山水意境;罗忠镕的《钢琴曲三首》运用“五声性十二音序列”作为音高控制及中国民间锣鼓的节奏组合作为节奏控制原则。赵晓生在《太极》中运用中国古代周易六十四卦的逻辑为基础,将中国传统阴阳哲学的逻辑关系与现代音集理论中的音高关系相结合,创制“太极作曲系统”,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创作方式。这些作品在“中国风格”的探索上都具有创新价值,其以西方“数理”思维展现中国文化与精神内涵也有许多成功之处。但一些作品对中国钢琴民族风格探索进入另一个极端,片面追求作品在“神”方面的艺术追求,即把作品的“神致、意蕴、气质等看成民族风格的全部”,忽略了作为“形”的音乐语言部分。㊷追求奇特的音响,极致的创作手法,丢失了基于旋律的情感表达,丧失了可听性。因此该类作品无法得到听众的喜爱,成为孤芳自赏的试验品。
从形式与内容上看,部分作曲家对“中国风格”形式的重视与追求忽视了内容上的“中国性”,阻碍了“中国风格”钢琴曲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听众对现代音乐作品的理解与认识也是影响当下“中国风格”钢琴曲欣赏与传播的重要因素,“中国风格”钢琴曲创作须注重时代的创新性,但同时作曲家也应注意音乐创作技术手段的创新与审美水平的关系,音乐创作形式与所展现内容的契合度等问题。如何做到作曲技术服务“中国风格”,音乐形式服务音乐内容,这在中国钢琴创作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成功案例,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瞿维的《花鼓》、丁善德的《快乐的节日》、黎英海的《夕阳箫鼓》、张朝的《皮黄》等。这些能够成为“经典”并被频繁搬上舞台的作品,均体现出不同时期中国钢琴的民族性、时代性,实现“形神兼备”,得到不同时期的听觉认同。
(二) 理性感知
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的探索体现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探索历程。20世纪20年代,中国专业音乐出现“全盘西化”的端倪,齐尔品试图唤醒中国音乐家对中国传统音乐和本民族音乐的重视,希望中国作曲家通过“征求有中国风味钢琴曲”,从审美角度提炼出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特征。自此,中国音乐家开启对“中国风格”的探索道路,历经“中国风味”“民族风格”“中国风格”三个阶段,音乐家对“中国风格”构建形成统一的认识,即“中国风格”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标签(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㊸。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作为一种音乐风格,从文化认同上包含中国的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民族风格、个人风格等方面,成为“中国风格”组成部分。
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内容、体裁、乐种和形式成为“中国风格”的文化内涵,如江文也的《为北魏古筝〈典乐〉而作的钢琴奏鸣曲》《杜甫赞歌》、陈培勋的《“音诗之二”流水》、储望华的《满江红》《解放区的天》《翻身的日子》《红星闪闪放光彩》、崔世光的《松花江上》《夫妻识字》、黎英海的夜曲《枫桥夜泊》、马思聪的《汉舞三首》、倪洪进的套曲《圆明园漫步》、瞿维的《洪湖赤卫队》幻想曲、权吉浩的《宴乐》、饶余燕的《“长安古乐”复调小品三首》、王建中的《梅花三弄》《大路歌》《军民大生产》、邹向平的《夔—四手联弹》等。中国不同地域、地区的音乐、文化,均为“中国风格”的文化内涵,如陈培勋的《广东小调“思春”》《旱天雷》《平湖秋月》、鲍元恺的《炎黄风情—24首中国民歌主题钢琴曲》、陈思的《东北风》、储望华的《江南情景组曲》《中国民歌八首》、崔炳元的钢琴组曲《西藏素描》《川西高原素描》、崔世光的组曲《东北大秧歌》、丁善德的第一、第二新疆舞曲、储望华的《新疆随想曲》、黄安伦的《塞北小曲30首》、钢琴音诗《鼓浪屿》、倪洪进的《云南民歌两首》、瞿维的《蒙古夜曲》、石夫的第一、第二、第三新疆组曲、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张朝的《皮黄》、赵晓生的《太极》、周龙的《五魁》等。中国56个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均可成为“中国风格”的文化内涵,如陈铭志的《乌苏里船歌》、但昭义的《苗家新歌》、黄虎威的《巴蜀之画组曲》《四川民歌十二首》、江定仙的《甘肃行组曲》、江文也的《台湾舞曲》、桑桐的《内蒙古主题小曲七首》《苗族民歌主题钢琴小曲22首》、邹向平的《即兴曲—桐乡鼓楼》、李世相的《蒙古族长调风格钢琴曲二首》、陆培的《山歌与铜鼓乐》等。中国作曲家的个人风格,以及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情感的作品,均是“中国风格”的文化内涵,如江文也的《木偶戏》、蒋祖馨的《庙会组曲》、饶余燕的钢琴组曲《延安生活素描》、孙以强的《谷粒飞舞》《春舞》、高为杰的《孩提时代》《童趣》、秦文琛的《春趣》(四手联弹)、桑桐的《苗族舞曲“酒歌”四首》等㊹。
因此,中国钢琴曲“中国风格”既要基于感性的审美认同,融入中国人的音乐生活,与中国人的实践、生活产生关联,又须诉诸理性的文化理解,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寄托㊺。这要求作曲家能够深刻领悟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本质和精髓,并在作品中合理展现。
结 语
中国钢琴曲的“中国风格”或“中国风格钢琴曲”作为中国钢琴音乐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但其所指一直不明。究其所以,“中国风格”既以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征的音乐语言为表征,又以音乐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为精神内涵,因此“中国风格”的实现旨在用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征的音乐语言,“模拟”“象征”“类比”与中国相关的物质和精神。“中国风格”既应诉诸特定的感性音响,让听众获得听觉上的认同,又需诉诸只能依赖于理性感知的观念及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