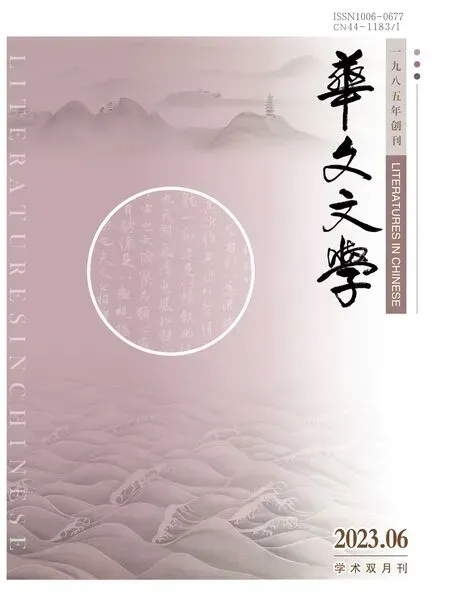美感的引渡
——李渝小说中的古典中国
吕欣桐
在海外华人作家李渝的文学书写中①,如果说“左翼”与“现代主义”构成了两类既殊异又有共通性的“思想资源”,那么前现代的“古典中国”则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汇集为作家创作视野里两种重要的“审美资源”。从1960 年代至21 世纪初期,李渝的创作风格经历了由中向西,再由西返中的变化过程,她的后期作品显露出一种现代与古典彼此圆融的风貌。
一、由现代到古典:“前现代潜能”的寻回
自从柄谷行人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诞生后,现代东亚文学场域内便同时存在着两种结构性元素——一是一个持续对西方影响开放和吸收的视野,二是作为自己实践现代主义美学精神的本土传统资源。后者看似是前者的对立面,但实际上更是西方外部话语进入后亟待被再次阐发的“前现代潜能”②。以李渝、白先勇、欧阳子等人为代表的台湾现代派作家,成长于1950-60 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青年时期受到风行一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风潮影响,当他们离开故土、旅居欧美之后,往往又因为各式各样的缘由,回到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汲取养分——或是借鉴了古典小说的母题,或是参照了章回体白话小说的结构笔法,作品的意象、主题、叙述风格、表现手法等常常显露出本土传统美学资源的鲜明印记。
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派艺术代表了一种倾向于“创造性的破坏”③的“激进的现代性”,那么在现代性语境中被重新打开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则可视为一种“古典的现代性”,二者均可视为某种对启蒙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拨。
从李渝的个人经历来看,她对于“古典中国”的兴趣其实是始于1966 年赴美留学之后,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出国留学导致的时空视点转换,反而在异域重燃了作家对属于自己身份群体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兴趣;另一方面,应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的保卫钓鱼岛运动触发了左翼理想与民族主义情感的接合,使得作为一种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古典中国”重新进入作家的视野。在1950-60 年代的台湾,曾经大力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但是“华夏传统文化”这一美学系统在由国家机器推动的话语体制内逐渐僵固为“乏味、权威、主流”,自然会引起青年人的逆反与抗拒。即便如此,青少年时期的教育仍旧留下了当时未曾察觉的印痕,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关于古典中国美学的基本文化训练,“其实后效深巨”④。1970 年前后,保钓运动在北美发酵,留学生群体对美日帝国主义行径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使得运动迅速染上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感色彩,并以此为契机,启动了重识中华文化、重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身份意识再生产历程。对于李渝而言,这一探寻过程,不仅涵盖了“五四”以来的精神文化遗产,还可以回溯至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如李渝所说,当他们离开台北到伯克利念书后,时空的改变带来了新的视角,于是“到底是看见了这影子,在某种程度上才明白了这影子的巨大”,如同“普鲁斯特说失去了才获得,或者像赵无极离开了中国才中国”⑤。当保钓运动退潮后,李渝深耕于中国美术史研究,师从著名的汉学家高居翰,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这一学术背景对李渝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具体而言,中国古典美学对李渝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绘画为代表的古代视觉艺术,二是古典小说。前者深刻地附着于李渝的学术背景,后者则沉淀于她的阅读创作经验之中。
二、画与文:视觉的航行
在李渝的小说作品中,绘画、建筑等实体艺术形式经常被当作记忆的容器或符号,承载了作者与人物的某种情结,既作为串联小说情节的关键线索,又彰显了文本独特的审美趣味。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李渝来说,绘画、雕塑、建筑是她的研究对象,也是其小说创作中频繁出现的“题眼”。譬如,《关河萧索》一文的题目取自清末民初画家任伯年的“关河一望萧索”系列画作。《江行初雪》描写了叙述者“我”到浔县玄江寺寻找公元六世纪的观世音菩萨塑像,却发现此地不久前发生的一桩骇人听闻的案件。玄江菩萨的神情纯净慈悲,有着“早期南北朝的肃穆”与“盛唐的丰腴”,“庄严里糅合着人情”⑥,寓意着悲悯众生、分担苦难,但现实的暴虐与之形成了强烈反差,艺术与历史二者既是对话又是对照。《无岸之河》《寻找新娘》等篇目中也以或真实、或虚构的绘画作品作为叙事推进的关键元素。
李渝称自己青少年时“本是在西洋绘画中游荡的”——生长在五六十年代的台北,却不知道怎样看中国画,“偶尔翻到一些有关的书籍,不过加深了成见,愈发把它看成是鸦片、麻将、裹小脚、玩戏子等的世界的一部分”⑦。直到有一天,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和赵幹的《江行初雪》,这两幅画“像电炬一样照来”,使她成为“回家的浪子”,而之后的异乡留学经验更使得她思考自己的身份特质,激发出对中国古典绘画的兴趣。李渝于1981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博士学位,出版有美术研究专著《任伯年——清末的市民画家》(1978)、《族群意识和卓越风格》(2001)、《行动中的艺术家》(2009),译有《现代画是什么》(1981)和《中国绘画史》(1984)两部作品,另有大量文艺评论文章散见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联合报·副刊》《雄狮美术》等期刊。李渝的前后转变令人想起了她喜爱的、同样经历了“由西返中”历程的当代华裔画家赵无极。赵无极在1948 年离开祖国赴法留学定居,原本专习西洋油画,却因为将油画技法与中国画的意境巧妙相融而在现代西方抽象画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重新在简净的水墨画里寻得心中的原乡,“离开了中国,却获得中国”。与之相似,“由西返中”的李渝在自己的文学书写中也融合了古典意象和现代技法,形成独特的美学风貌。
对绘画和艺术史的研究使得李渝小说的“空间性”格外突出。根据李渝的看法,绘画活动是寻找、遇见和调度操纵空间的艺术。空间既是画框框住的面积,也是画框框不住的看不见的内在,前者是外部视觉,后者是内在心性。绘画的过程就是与空间周旋、争执、协商的过程,于外在和内在之间建立共存的关系。画家与空间的关系是“存在主义性的”,经营视觉的广度深度,其实是在和生命的虚无搏斗着。这一对空间维度的思考也深刻地贯穿于李渝的文学书写之中。她的小说中最常见的意象就是“河流”,也是其美学体系中的关键象征物。“河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同时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自然景物,不仅占据着实体的空间位置,又以流动不息的河水象征着时间的绵延。通过对“河流”进行或实或虚的描绘,李渝有意识地进行了绘画中的“有岸之河”与小说中的“无岸之河”的相互转化。
以《江行初雪》为例,这篇写于1983 年的小说是李渝在接受过美术史训练后的第一篇重要作品,于当年获得了台湾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与她60 年代早期作品抒写少女心事的空灵纯澈相比,这篇作品更加渗透了时间的厚度与历史的分量,同时,也凸现出十余年来的美术史研究对作者的影响。
《江行初雪》的小说题目来源于南唐画家赵幹的《江行初雪图》。赵幹此画使用了“平远”的构局法,即在平旷的陆地或河水上展现无际的视野,在各个空间小单元之间建立起关联。这幅纵25.9 厘米,横376.5 厘米的绢本设色长卷,描绘了江南渔民初雪时节捕鱼的景象。在缓静的江水之上,芦苇、树林、舟艇、茅舍、渔人等元素由明净的线条落于画面,覆盖上白粉绘就的雪景,以和谐的比例经营出疏密错落的空间感,又以细腻的笔触呈现出动人的人性关怀,达到了“虽在朝市风埃间,一见便如江上,令人蹇裳欲涉而问舟浦淑间也”⑧的境界。
与同名画作相似,小说《江行初雪》的叙事同样营造出了一种递进有序的空间感和萧瑟孤寂的抒情氛围。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海外侨胞,在80 年代初回国寻访北魏时期的玄江菩萨塑像。在一个雾气迷蒙的清晨,叙述者抵达了江南浔县郊区的机场,随后,读者跟随“我”的视点来到下榻的立群饭店,“我”一边向接待人员强调想要去看玄江菩萨的意愿,一边仔细观察着周遭的人与环境。叙述者的观察始终是透过某一种“窗”的介质进行的——机舱的舷窗、旅馆庭园的雕花木窗、汽车的后窗、白色钩花的窗帘、轮船舱内的窗。“窗”构成了画框式的空间结构,提示着主人公身为外来者的观看视角,同时塑造了一种类似于纵深透视法的行文风格,可以与北宋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的“自山前而窥山后”的深远意境相互对应。小说描写的虚实、结构的疏密、文字句法的层次,都蕴含着古典绘画空间技法的“文字化”倾向。从艺术表达的层面来看,文本与绘画一样,对空间感的经营是一种“视的旅程”和“往里去的航行”⑨,讲求叙事节奏的疏落有致、描写铺陈的形状肌理。
除此之外,文本中的结构、颜色、形式不止是写作(或绘画)的要件,更是一种情感的场域和情感的指标。在《江行初雪》小说中,叙述者“我”虽然看到了向往已久的玄江菩萨,但塑像早已不复北魏时期的古朴温润,而是被后人涂上了面目全非的金箔,大受打击的“我”随后还从亲戚表姨那里了解到关于玄江菩萨的一桩悲惨往事——一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少女,因为浔县当地恶绅要使用“以脑补脑”的方法医治自己的头痛症,而被迫害致死。小说结尾处,叙述者“我”带着遗憾乘船离开了浔县,回头望去,只见眼前的景象竟与千年前的同名画作有几分神似:
“马达开动了,船身缓缓掉过头,掠过萧瑟的芦杆,向苍茫的前路开去。我站在船尾,一直等到表姨矮胖的身影隐失在飞雪里。船身江中一片肃静,哒哒的机器声单调地击在水面,雪无声无息地下着,我从舷窗回望,却已看不见浔县,只见一片温柔的白雪下,覆盖着三千年的辛苦和孤寂。”⑩
《江行初雪》一文的致敬对象是鲁迅,“无非也想放在另一个闰土或长妈身上”,说出“无声的中国”[11]。此时的叙述者俨然成为了《江行初雪》画中之人,飞雪掩映下的江水由空间意象转化为时间意象,引渡出“无声的中国”所承受的“三千年的辛苦和孤寂”。小说中的浔江与画中的河流遥相呼应,代表着横亘于历史空间中的、剔除了杂质的、永恒的时间。正如作者所述:“《江行初雪图》里的,《富春山居图》里的那条河仍旧流着;在世上所有的琐碎,所有的纷扰,所有的成败中,有比它更永恒的么?”[12]
作为“最伟大的渔人画”,赵幹《江行初雪图》展现了同情渔人艰辛现实生活的真挚情感——寒冷的冬季,一片萧瑟暗淡的河水上,芦花被风吹得弯折起来,两位渔人蜷缩于高跷支撑着的捕鱼台上,只得一片草席遮挡风雪。远处有一叶扁舟,两名船夫撑着篙载着衣着华美的乘客缓缓驶过。高居翰认为这种同情渔人艰辛的情感在明代之后的渔人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洋溢着世俗幽默感的渔乐图。可以说,小说《江行初雪》与同名画作在内容主旨上颇为相似,都体现出对承受生活艰辛的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乡土的关怀和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照眼光。李渝曾在评论文章中特别肯定了1950年代中国大陆艺术史学者的历史意识。1960 年代在伯克利读书的李渝,对当时西方“唯画面是问”的形式主义研究路径十分不满,希望能在艺术批评中表现出社会、历史、个人的挣扎。作为“本就向往艺术上的现实精神的人”[13],在保钓运动期间她更进一步认可文艺现实主义美学观,历史意识和贴近底层的精神亦成为她美学思想的底色。
《江行初雪》小说营造出了与画作相仿的疏离孤寂之感,那始终漂浮于文本间的“雾气”与结尾处被白雪覆盖的河流江岸,令人想起韩拙《山水纯全集》所提到的“景物至绝而微茫飘渺者”,显然已具备古典山水画的意韵精髓。
另一幅对于李渝有着重要意义的绘画作品是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瑞鹤图》为绢本设色画,纵51 厘米,横138.2 厘米,有徽宗瘦金体自题,作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 年)上元节次夕,记录了宋徽宗所目睹的群鹤绕殿祥瑞之景。画面以淡石青色渲染天空,十八只鹤翱翔于天空,另有两只立于殿脊的螭吻之上,群鹤翻飞,姿态百变,无有同者,祥云布满天际,瑞鹤与祥云萦绕飞舞,显出构图与技法之精妙。在《无岸之河》(1993)和《待鹤》(2010)这两篇小说中,《瑞鹤图》都作为小说的关键线索和象征物出现。画中的群鹤绕殿飞升之景暗喻了作者在艰难境遇中不断与“下坠”、“深渊”等意念搏斗的“上升的意志”,并烘托出文本叙事虚实交织的艺术效果。
“鹤”是李渝最喜爱的动物,也是她自中国古典艺术中提炼出的、最能映照自我的美学精魂。无论是《瑞鹤图》中仿佛追随某种奇妙韵律的鹤群,还是苏轼《后赤壁赋》中的“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抑或是黛玉月下联句时湖面飞起的鹤、宝玉怡红院前庭养着的鹤,这种在帛画、砖画和诗词歌赋中常常出现的“神秘之鸟”以其华美的姿态、高洁的意志铭刻了李渝的内心诉求。
1997 年,李渝的丈夫郭松棻突发中风病倒,李渝因压力过大患上了抑郁症,经过长时间休养才逐渐好转。2005 年,郭松棻在第二次中风后不幸过世,李渝难以走出失去挚爱的痛苦,再次遭遇精神危机。2010 年,她发表了自传色彩浓厚的“半虚构”小说《待鹤》,描绘了精神世界中的一场“奥德赛”之旅以及重访故地后的启悟。小说的叙述者“我”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因为饱受忧郁症困扰,试图通过心理咨询进行治疗,遍寻名医却屡屡受挫。为了寻找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场景,“我”不远万里来到不丹的一座寺院,希望看到传说中的鹤绕金顶。旅途中突发事故,不丹向导因山路湿滑不幸坠崖而亡,留下他新婚的妻子。三年后,“我”重访不丹,再次看到那位不丹女子,虽然她已经离开过去重新出发,但身为旁观者的“我”却仍旧“停留在原时间”,惊疑于生命的偶然与虚无,一直受困于创伤发生的幽暗时刻。
《待鹤》是一个虚实相交、虚实相生的文本,其中纯虚构的部分是两次不丹之旅与观鹤的情景,现实的部分则是“我”与“松棻”的回忆。李渝在采访中提到,她没有去过不丹,借用这一地理上遥远的国家,是为了“设立一个彼邦、另地、他乡”,使其成为“替换的场域”,在实况不尽理想时可以“转境过去”[14]。小说所讲述的内容中,位于“虚实之间”的是叙述者的大学执教经验、抑郁症经历、类似“某一种奥德赛”的心理咨询治疗过程,以及对于“下坠”与死亡的思考。下坠的生活与上升的艺术构成了一组镜像对照:“下坠”的包括失足掉落深渊的不丹青年向导、从图书馆天井坠落自杀的医学院学生、堕落于名利的精神治疗医师,和在心理层面处于不断下坠状态的主人公“我”。如作者所述,人每天都在“边塌陷边过日子”,上升只发生在艺术或传说的“虚妄与迷人”之处——“人间的错失和欠缺,由传说来弥补”,“是传说,不是现实,能对付现实”。
小说中多次渲染“下坠”/“深渊”意象所具有的梦魇特质。爱人逝世的打击成为了叙述者精神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她在小说中不断追叙一种被创伤经验定格的艰难状态:
“一片荒瘠的岩漠,一声无声的叫喊响彻黑暗的渊谷,一个身躯下沉,下沉,沉到沉重的梦里;影像卡在放演机的齿轮间,固执地拒绝前移,和那日一样清晰,使得,在记忆的底片上某些图影已经蚀印成定格,变成了白日和夜晚都挥不去的梦魇。”[15]
与下坠的黑暗沉痛相对,《待鹤》一文中与“上升”有关的元素包括了宋徽宗《瑞鹤图》中盘旋于宫殿上空的鹤群、黄昏时分不丹金顶寺庙的“鹤至”美景,以及结尾处一种传说式的桃源想象。作者以赵佶的《瑞鹤图》开启全篇叙事,艺术家描绘的“绮丽的黄昏,刹那的一个时空”是来自艺术的“不朽的祝福”,也是作者在孤独世界中的美的邂逅。以上种种,让叙述者“我”重新发现了值得坚守的美与可以抵达的希望——“有一块金色的屋顶不舍弃地守望着,指引着对危机的警觉和反应,送来光的承诺”。在光的指引下“我”仿佛回到了台北的夏日,在温州街的木屋旁看到了失去的爱人:
“梦者果然如约再访……他抬起头,转过身——多么熟悉的容颜——让册页中的人物一一走过罢,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亲近的和疏远的,诚实的和虚假的,衷心的和欺凌出卖的——有谁,会前来梦中相会且陪伴?是谁,会递来叫人安心的消息,跟你说,放心,我跟你是在一起的呢。
是有这样一个人的;只有这样一个人。啊,是谁,还有谁,是松棻呢。”[16]
《瑞鹤图》所描画的群鹤绕殿之景唤醒了一连串关于过去的讯息,而存储回忆的“记忆之场”拥有本雅明所说的神秘光晕,它是一种“由空间和时间组成的奇特的织物”,把在场与缺席、感性的当下与历史的过去交织在一起[17]。对记忆之地的重访(实际与想象均可)或许有一种心理治疗式的疗愈功效,因为主体的积极介入行为打破了创伤的重复机制,开启了一种新的叙事可能,而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美学层面的渡引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桥梁和中介的意义。
三、多重渡引:古典文学的影响
李渝不止一次地提及过,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是“很后知后觉的”。她的阅读与创作经历了自中向西、由西返中的过程,“返中”的经验里不仅包括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还涵盖了“古典的启蒙”。复杂的知识背景使得李渝的文风呈现出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结合。
李渝认为古典文学里的中文的准确性和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例如《左传》和唐小说,就其文字的叙述力度和速度来说,可以在很短的句子中凝聚时间和空间,“在有限中载负无限”[18]。李渝又以唐传奇小说《红线》为例,论证中文的准确性和速度——红线深夜从婢女换装为侠客,夜潜田承嗣寝帐,偷盗枕下金盒,短短百余字的描写明确、快捷、绮丽,一种推进速度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了极限,充满了叙述的劲力,仿佛“再进一步每行句子就要像钢丝一样啪地一声断了”,这样的写法“充分开发了中文的能量”[19]。中文的字声、字形也是一大优势,因为汉字有四声,有头韵、尾韵,所以音韵节奏感强,“要铿锵要柔软绵延都可以”,而且字形也可以构成视觉的绵密。
在《和平时光》《贤明时代》等篇目中,李渝采取了向古典小说致敬的描写手法。例如,《和平时光》一篇描写聂政刺韩王的场景,其笔法简洁凝练似《史记》,又颇具唐传奇小说的明快绮丽的风格:
“女子前进,提手,伸向的却是盘底某位置,韩王骤然惊觉,立刻转向榻边,索剑;霎时匕刃从盘底抽现,横来眼前,王才看出,女子发色跟那日刺者是一样的丰黑!……韩王起身——一道强光扫进……再接一记雷霆,简直就像扔打在窗口,窗扉碰碰撞击,强风夹急雨拉扯锁扣,哗然冲刮进来。这风驰电掣之中,蒙面女子从地上站起,用出弓之箭的速度奔向窗口,一个飞身跃出开窗,雷光乍闪,打亮一头黑发,不见了。”[20]
在上述片段中,能够看出李渝字斟句酌的细腻风格,这种追求极致、准确、优美的“文字炼金术”贯彻于她的写作之中。除了《左传》与唐传奇,李渝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是特殊的一部,特殊之处首先在于曹雪芹运用、拿捏文字的方法:
“中国古典小说叙述风格以白描为主流,注意情景、行动的再现,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唐传奇小说等,追求行文的简洁利落明确。《红楼》走向繁复缜密,同时运作声与色的多媒体,常常搓揉踌躇在一个点或面上,着意铺陈绵延扩充不已,仔细挑引感官和感觉,进入暧昧的情绪和幽微的心理,进入了现代小说的领域。”[21]
其次,在李渝看来,《红楼梦》另一个不同于一般古典小说之处在于它呈现的不是“剪纸、传奇式人物”,而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写实人物,不在意道德成见,不轻易施加道德评判,从而走入非黑非白的灰色暧昧地带,关注人性隐晦面和生命的荒诞虚无。从这层意义上讲,“十八世纪曹雪芹已经把中文小说领入了现代的场域”。可以说,李渝的《贤明时代》《和平时光》承袭的正是曹雪芹的“古典与现代交融”的道路——“揉捏词汇,翻转句子,使书面文字发出色彩和声音,现出纹路和质地,把读者带到感官和思维迴鸣,现实和非现实更迭交融的地步,拓宽了中文小说的道路”[22]。
在《贤明时代》《和平时光》两部作品中,李渝对原有的历史素材进行了重写、拼贴、剪裁,将现代主体自我投注于另一个时间维度的他者身上,并且融入现代主义隐喻象征技巧和诗化的语言风格,使其焕发出新的文学价值。提到历史新编小说,不能避过的是鲁迅的《故事新编》,李渝的创作也受到了鲁迅的深厚影响,但是,与《故事新编》所采取的语式杂糅、戏谑讽刺的笔法不同,李渝的文风更偏重于华美庄严,她笔下的人物大都怀揣着庄重严肃的情感和不可告人的秘密抱负,时常处于自我与他者相互角力的矛盾关系当中。小说采取的叙事语言婉转多变、意蕴丰富,在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的张力之中烘托出文本内部的紧张氛围。
除了叙述语言、文本素材之外,古典小说对作家的创作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启发。在分析《红楼梦》第三十六回“放雀”这一情节时,李渝引出了自己的一个重要创作理念——多重渡引观点。所谓“多重渡引”,指的是:
“小说家布置多重机关,设下几道渡口,拉长视的距离,读者的我们要由他带领进入人物,再由人物经过构图框格般的门或窗,看进如同进行在镜头内或舞台上的活动,这么长距离的,有意地‘观看’过去,普通的变得不普通,写实的变得不写实,遥远又奇异的气氛出现了……”[23]
由此展开的叙事方式为小说“拉长视的距离”,给情节、修辞、情感的辗转腾挪留出了足够的叙述空间,同时在引领读者“观看”的氛围中让作者的声音一直浮动于文本之中,与小说叙述者的声音构成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江行初雪》是如此,《无岸之河》《关河萧索》以及“温州街的故事”系列也是如此。
此外,李渝的书写承续了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注重“意象”的经营,在写作中常常是以“美”作为方法,从而与现代主义文学中常见的对丑恶、病态、崎岖之事物的聚焦拉开了距离。她的小说中有大量对服饰、美食、植物的详尽描摹,例如《贤明时代》中描写永泰公主的衣裙、绮丽斗艳的花朵,《金丝猿的故事》里详写将军府内的水晶玫瑰加沙酥饼,《温州街的故事》聚焦于台北街道上郁郁葱葱、四季繁盛的亚热带植物等等,几乎制造出一种比《红楼梦》更为繁复盛大的“物的美学”。《和平时光》中写韩王与聂政的琴音之美,则是借助了通感的手法,将听觉的美感转换为视觉的意象,在对“美”的描摹中,作家专注于对颜色、声音的刻画,显然是借鉴了绘画技法来调动视觉、听觉元素,在感官的互动生发之中将小说呈现为一种有如画作的视觉艺术。
总体而言,李渝是典型的文体家,她的前期创作着意于经营“句子的冒险”,通过故意扭曲字词句型来追求语言的私人性和奇异效果,但后期创作受到了《左传》或者唐传奇小说精准、简净风格的影响,语言逐渐流畅自然起来,与细部的雕琢相比,更加注重故事整体的铺陈与演绎,重视视觉效果,在长句式、排比和名词连缀的笔法中铺洒出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意境。有研究者提出,民族文学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活世界”,深深扎根于“男男女女的日常语言、经验、历史记忆、意识、情感、梦想、无意识和非理性之域”[24]。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行为看起来是一种日常的消闲,其实是读者变成以赛亚·伯林所称的“群体个人”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生成了一个个意义的漩涡,不断熏陶着读者的美学取向与道德心性,而旋涡的底部通向“中国性”这条民族暗河,每一次进入文本都可以使阅读者更贴近“想象的共同体”。由李渝的创作经验可知,当积攒了足够多的民族文学阅读经验后,她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民族的与世界的、古典的与现代的相互融合的特点。
四、结语
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中详细分析了现代性是如何导致个体产生意义的匮乏感的。现代性的来临使得古典时代的“可渗透自我”(porous self)逐渐转变为“缓冲自我”(buffered self),转变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匮乏”[25],现代性的三类隐忧——意义的脆弱感、庄严感消退、日常生活的虚无性——也随之浮出历史地表。泰勒进一步提出,应对现代性隐忧有两条道路,一是走出内在性,重新回到超越性,二是在内在性之中发掘新的价值,找到更高维度的存在意义。从李渝的经历来看,当保钓运动的实践行动告一段落之后,作家面临着意义匮乏感与现代性隐忧的困扰,因而重新转向文学书写,试图寻回生命主体存在的价值感。可以说,在她所汲取的美学资源中,“古典中国”对应的是第二条道路,通过物我感应的一元论宇宙观、因果相应的循环时间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现代个人找到了心灵与世界的“可渗透边界”,发掘内在性的新价值与新可能。
对于李渝来说,“文字炼金术”指的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方面的特点,更是一种对写作本体论式的探索。李渝关注主体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让书写本身变成抵抗现代性隐忧与意义匮乏感的最有力的途径。中国古典美学除了在形式、技巧、意蕴等方面给予作家艺术滋养之外,还将“天人合一”“中和之美”的认知框架,以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创作信念,深深植根于作家的内心,使其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面貌。
①李渝(1944-2014),生于重庆,长于台北,1960 年代初期开始发表小说,1966 年赴美留学,师从高居翰学习中国美术史并取得博士学位,80 年代后重新开始文学写作,多次获得重要奖项。
②[美]张诵圣:《试探几个研究“东亚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框架——以台湾为例》,《当代台湾文学场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80 页。
③“创造性的破坏”原本是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术语,形容资本主义创造并破坏经济结构的过程。戴维·哈维借用这一概念,说明现代主义思想家实施种种现代规划时的困境。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24-28 页。
④宋雅姿:《乡在文字中:专访李渝》,《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118》,梅家玲、钟秩维、杨富闵编选,台北:台湾文学馆2019 年版,第112 页。
⑤李渝:《乡的方向——李渝和编辑部对谈》,《INK 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 年7 月,第75、79 页。作家在访谈中提到,如果一直住在台湾,恐怕仍旧会浸淫于翻译文学中,阅读的航道不会传承回溯,“发展出这样的汇合”。李渝此处提到的赵无极(1921-2013)是一位华裔法国画家。
⑥⑩[11][23]李渝:《应答的乡岸》,台北:洪范书店1999 年版,第126 页,第133 页,第154 页,第8 页。
⑦⑧[美]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李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13 页,第61 页。
⑨李渝:《时光忧郁——赵无极1960-1970 年代作品》,《行动中的艺术家》,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2 页。
[12][13]李渝:《族群意识与卓越风格》,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版,第157 页,第152 页。
[14][18][19]李渝:《乡的方向》,《INK 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 年7 月,第86 页,第75 页,第79 页。
[15][16]李渝:《待鹤》,《九重葛与美少年》,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版,第20 页,第15-16 页。
[17][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353 页。
[20]李渝:《贤明时代》,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8 页。
[21][22]李渝:《拾花入梦记:李渝读红楼梦》,台北: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版,第28 页,第8 页。
[24]程巍:《隐匿的整体》,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 页。
[25]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Bonst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11-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