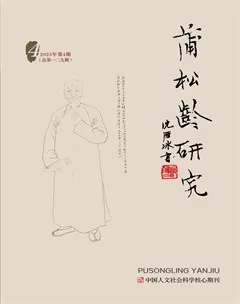《聊斋志异》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
池 田 范祥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描写翻译学派的思想发端于50 年代,它试图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范围内跳脱出来,将翻译语境化,“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的内部,而是将研究的视阈延展到翻译的外部,并以社会文化功能为纽带将两者联系起来”[1]61。该研究聚焦《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翻译外部研究数据,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探讨,提出拓宽典籍英译传播广度的建议,以推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
《聊斋志异》拥有众多外文译本,其中英译本广受欢迎。然而,以此小说英译本研究为主题的文献并不多。检索并整理文献发现,《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体为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主要分为单个译本研究、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史研究及研究综述,传播研究及影响研究并不多,且未见基于各类数据调查和科学框架为基础的传播研究。因此,有必要以《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为切入点,将19 本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各译本的再版重印、海外阅读与评论情况、谷歌学术引用量以及世界图书馆馆藏量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理清各译本的传播现状,让译本“走进来”,便于学者对广受好评的译本进行后续深入研究,对比学习其翻译出彩之处,丰富典籍翻译策略,为中国典籍“走出去”带来一定参考意义。
一、《聊斋志异》的英译概述
研究《聊斋志异》英译本的传播情况,首先应对其英译历程做整体把握。此小说集的英译形式多样,包括杂志和书籍中的零散译文、漫画译本、选译本和全译本。前两种英译形式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选取《聊斋志异》已出版的选译本和全译本为研究对象,对各个英译本的相关信息进行介绍,并进一步研究译本的前言部分,以明确主要译者的翻译目的。英译本的搜集为后续传播研究奠定数据框架基础,译者翻译目的的探究则为后续数据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聊斋志异》英译本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翻译至今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程。根据2022年蔡乾在《明清小说研究》上最新发表的论文可知,此典籍在西方的译介最早可追述到1835 年《弗雷泽杂志》的“中华之晷”专栏中刊载的《白于玉》短篇独译,经过译介策略和译者身份多重探讨,译者可能为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2]《聊斋志异》早期译介者多为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因此他们的译介“不可避免地会有误读和偏见”[3]167。此后,一些汉学家也开始此典籍的选译工作,最早的选译本出自翟理斯之手,共包含164 篇选文。20 世纪为《聊斋志异》英译高峰时期,白廼逸译本为第一个华人译本。改革开放后,更多国内翻译家也展开相关选译工作,唯一一本全译本由六卷组成,出自汉学家宋贤德之手。搜集发现,《聊斋志异》共有选译本18 本,全译本1 本(表1)。从时间上看,译本可分为19 世纪、20 世纪、21 世纪三个时段;从译者角度出发,可以分为汉学家、海外华人、国内译者。

表1 《聊斋志异》英译本一览表(按出版地和初版年份排列)

表1 《聊斋志异》英译本一览表(按出版地和初版年份排列)(续)
(二)主要译者的翻译目的
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它认为“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首要原则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4]27。因此,有必要考察主要译本的前言部分,理清不同译者的翻译目的。目前共收集到已出版《聊斋志异》选译本和全译本共19 本,其中汉学家翟理斯译本最早由T.De La Rue & Co.出版社出版于伦敦。翟理斯熟练掌握汉语句法,了解中国文化习俗,练就了严谨细致的翻译风格。译本中注释所占篇幅较大,旨在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与补充说明。其译本出版后“被转译成多种语言, 在西方代表蒲松龄超过一个世纪之久”[5]xxxii。译本前言中表明,着手翻译此书,这位汉学家希望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使之“将兴趣点放在除中国的国家大事之外的层面上”[6]xiv。此外,翟理斯还认为此书蕴含大量中国文学典故及隐喻,这些民间故事的译介为英语世界读者展开一幅幅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
闵福德译本于2006 年由企鹅经典出版社出版,包含104 篇选文,译本整体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用词简洁不失灵动,颇受国内外读者欢迎。副文本是译本的一大特色,译者花费大量笔墨与页数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背景等信息,然而,“闵福德并不认为自己的译文是中国某位评论者所说的‘消费主义’、迎合西方低层次的读者,他只是在忠实地传达蒲松龄的故事旨趣和艺术主题,而这些旨趣和主题正是西方读者了解古代中国的窗口”[7]90。
法国汉学家苏利耶·德莫朗意识到《三国志》等一些中国小说颇受中国各年龄段大众欢迎,在塑造中国国民的思想上其重要性远大于众多经典著作,因此这些小说的研究价值比肩孔孟经典[8]v-vi。《聊斋志异》等小说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的映射,这些故事有助于西方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学。
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与其夫人戴乃迭合译本于1981 年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该译文注重呈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译文保留原文简练风格,在晦涩难懂的社会制度与节日等方面加以阐释说明,加深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识。
所收集的英译本中,一些译本由著名出版社出版。其中企鹅经典出版社(Penguin Classics)由埃伦·雷恩爵士于1935 年在伦敦创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英语语种出版商,其影响力遍及国内外,为闵福德译本的传播打下夯实的受众基础。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1897 年创办于上海,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重视对外合作与中外交流,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其次,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成立于1952 年,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出版资源,是我国主要的对外出版机构,拥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旨在助力中国图书走向世界。
二、《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
研究一本书的海外传播,需要了解其各个译本在海外的接受范围。本文从再版重印、网络读者评论、杂志书评、谷歌学术引用及世界图书馆馆藏量五个方面,以统计学方法制作表格,可以量化分析《聊斋志异》各个译者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情况。本文表格数据于2023 年中旬搜集完成。
(一)再版重印统计分析
世界图书馆馆藏(WorldCat)成立于1967 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联网联合目录,拥有近15600 个图书馆数据库,便于服务数据统计与查找。在此网站上检索《聊斋志异》英译本再版重印情况,结合谷歌图书(Google Books)和亚马逊(Amazon)网站的相关数据,可以收集各译本的再版重印等信息。
结合上述网站信息,共检索出11 个译本的再版重印数据,包括电子版本及亚马逊按需印刷(POD)版本。基于数据统计得出《聊斋志异》各类英译本整体再版重印情况不够乐观。其中,翟理斯译本再版重印次数最高,为47 次。汉学家翟理斯的翻译水平一直颇受译界认可,尽管其初版译本年代最为久远,但是凭借对中文句法及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他的译文质量受到普遍认可,译本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且具有较高的英汉对比研究价值。综合读者需求及社会发展等因素,其修订版、精简版等各类版本相继问世,以适应各年龄段、各学识层次读者的需求。
其次,苏利耶·德莫朗译本再版重印14 次,夏琳达和岳罗杰合译本再版重印4 次,剩余译者译本不超过3 次。除此之外,闵福德译本、宋贤德译本、莫若强等译本、张庆年等译本、黄友义等译本、宋德利译本、王国振译本以及吕宝军等译本均未找到再版重印数据,推测其原因为译者国内外知名度不高、译文无较强特点或译本出版较晚。虽然馆藏中无闵福德译本再版重印数据,却收录其诸多独篇式《聊斋志异》选译篇章。
(二)网络读者评分及评论统计分析
好易读(Goodreads)隶属于美国亚马逊公司,截至2019 年7 月,此网站已有9000 万注册用户,网站用户可以搜索书本的评分及评论数据。在此网站检索各译本的读者评分量和读者评论量,可以从译本的读者接触度和接受度考察译本的传播情况。
好易读网站共检索到12 位译者的译本(表2)。就读者评分量而言,深入研究发现,闵福德译本、翟理斯译本、夏琳达和岳罗杰合译本、乔治·苏利耶译本、卢允中等译本以及张庆年等译本的读者评分量相同,1931 位读者对这6 本译本的星级评分数量在此网站上被整合呈现,推测其原因为网站识别译本的译名相近。其余6 本译本的读者评分量均未过百,由此得出这些译本在该网站上的传播能力不足,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不高。其他7 本未在表格中提到的译本在好易读上没有数据呈现,推测这些译本在读者接触度与接受度等维度上缺乏影响力。

表2 《聊斋志异》译本好易读读者评分量统计
从读者评论量来看,好易读网站共搜集到9 本译本的读者评论量信息(表3)。此网站也将上述闵福德译本等6 本译本的读者评论量整合呈现。深入研究发现,依次点击各条评论右侧的日期可以准确定位每条评论所评价的译本。研究中还发现其他书籍的评论也掺杂其中。因此,除去不相关评论,9 个译本共有196 条评论,其中闵福德译本评论量最高,为154 条,翟理斯译本次之,为20 条。其他7 本的评论量均未超过10 条。

表3 《聊斋志异》译本好易读读者评论量统计
对于读者评论量最高的闵福德译本,有读者在评论区直接叙述了自己喜欢的篇幅故事,可见《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志怪短篇内容生动精彩、深入人心。对于读者评论量位居第二的翟理斯译本,读者们认为其译本中加入大量注释,有利于对文章整体把握的同时了解一些中国文化习俗,这对于喜爱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整体上看,读者评论数较高的译本均为精通双语的汉学家所译,由此可见,英译本需要更高的中英契合度才能更好地为英语世界读者所接受与理解。作为跨文化、跨语言传递信息的行为,“翻译行为需要明确隐性市场的目标读者,进行清晰的市场定位,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接收和接受”[9]80。中国典籍英译的出版应与国外出版社多加合作。国内译者译本大多由国内出版社发行,未能在世界图书市场抢占先机,因此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受到阻碍。
(三)杂志书评
在JSTOR 中检索《聊斋志异》译本发现:JSTOR 网站仅收录了翟理斯译本书评3 篇和邝如丝译本的书评1 篇,其余搜集到的文章与译本内容没有直接相关性,故不计入统计。
学者Yu-Shan Han 认为邝如丝译本的贡献在于“她选择的故事中呈现了比翟理斯更完整的中国原著。她以最清晰的方式翻译了中国人对性的处理,性在生活中有它的地位,但既不是主导,也不是生活的目标”[10]392。相较而言,翟理斯译本对此话题有明确的闪避。美国人类学家和东方学家B.Laufer 表示翟理斯译本第一版中的注释索引中所包含的中国习俗、制度等信息是其在满族统治者掌权时所译,随着时代的发展,译文中的时态应作出改变。[11]86他将翟理斯初版译本与1908 年再版译本进行比较,认为再版译本存在封面插画不匹配,字母“b”大量使用倒“P”替代等问题。
(四)谷歌学术引用统计分析
2004 年问世的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是一个国际搜索引擎,拥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可以搜索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文献等。通过谷歌学术引用网站查找各个英译本的被引数量,从学术研究价值维度探讨译本的传播情况。
经检索,谷歌学术上共有11 位译者的译本被引用,翟理斯译本拥有最高谷歌学术引用量146 次,闵福德译本次之,为128 次,其余9 个译本引用量均未过百;王娟等其他8 位译者的译本未在此网站上检索到数据。由表4 可见,翟理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且译本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而大多数国内译者的译本在学术研究层面的价值有待发掘。作为《聊斋志异》的经典译本,翟理斯译本无疑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相关研究涉及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等层面。尽管受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翟理斯的译文存在对原文的删改,但其译文流畅易读,并添加大量注释,对中国文化及习俗进行介绍,因此“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西方对神秘东方中国的固有偏见,为后来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打下了基础”[12]106。

表4 《聊斋志异》译本谷歌学术引用量统计
闵福德译本的副文本内容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与《聊斋志异》的其他英文版相比,“闵福德英译本对《聊斋》故事背后深远‘孤愤’情结的深入解读和精准把握,是英语世界《聊斋》阐释与研究走向深入的标志”[13]106。国内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本位居谷歌引用量第四,可见其译本的学术价值和传播广度比其他国内译者更胜一筹。
(五)世界图书馆馆藏统计分析
在世界图书馆馆藏中搜索各英译本的总馆藏量,并突出主要英语国家和中国的馆藏数据。海外图书借阅者更易接触到馆藏量较高的译本,因此,馆藏数据也是研究译本海外传播的重要参考维度。在WorldCat 中搜索译者和译本书名,将“筛选依据”设定为“此版本”进行数据搜集。各译本的数据由其初版、再版重印本(包括电子版本)相加而得。
从总馆藏量而言,翟理斯译本拥有最高馆藏量750(表5),约占所有英译本馆藏数据的27.23%,推测该译本借阅量大、受认可度高。在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序言中,他声明自己的译文为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所译,不仅仅是学习中文的学生。“虽然20 世纪后一些翻译理论家对翟理斯的翻译策略颇有微辞,但翟理斯译本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译本。”[14]83-84闵福德译本次之,总馆藏量为326,占比约11.84%。值得欣慰的是,总馆藏量排名前5 的译本中,有两本分别为澳籍华裔邝如丝和中国译者杨宪益及其英国籍夫人戴乃迭所译。这两本华人译本的广泛传播离不开译者双语翻译素养的加持。

表5 《聊斋志异》译本世界图书馆馆藏国别统计(以总馆藏量排序)
按国家馆藏完整度和丰富度而言,美国位居榜首。除宋德利译本在美国没有馆藏数据以外,其他18 个译本均有数据,翟理斯译本馆藏量更是高达555本。然而,各译本在中国的馆藏数据却屈指可数,由此可见中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需增加各类型图书的藏书量,以提高读者的书籍接触度。
除上述6 个具体国家外,WorldCat 上还检索到丹麦、西班牙、马来西亚等亚欧国家的馆藏数据,纳米比亚、哥伦比亚等个别非洲和南美洲国家也有少量数据呈现。由此可见,《聊斋志异》的英译本将这部典籍带到六大洲。
结论
运用统计学方法与描述性方法,本研究借助互联网技术与各大学术网站搜索引擎发现:共搜集到《聊斋志异》英译本19 本,其中翟理斯译本的再版重印量、JSTOR 学者书评量、谷歌学术引用量以及总馆藏量最高,闵福德译本的好易读读者评论量最高。闵福德译本等6 本译本的好易读读者评分量综合呈现为1931。从国家馆藏量看,美国馆藏量最大,所藏译本最全。总体而言,翟理斯和闵福德两位汉学家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传播最广;国内译者中,除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本,其余译者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力度不够大。对于本国的文化输出,不能一味指望屈指可数的汉学家们,国内《聊斋志异》的译者应当加强自身的译者修养,国内著名出版社也应当考虑与国外出版社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值得欣慰的是,不论如何,这些英译本已让众多国外读者感受到中国志怪文言小说的魅力所在,逐渐激发其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典籍的兴趣,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及中国思维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