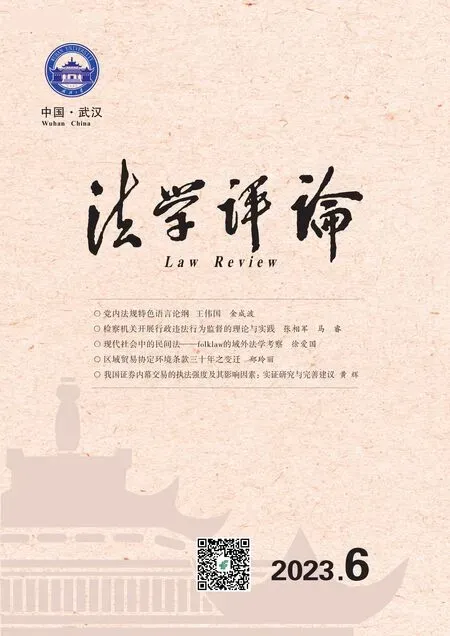区域贸易协定环境条款三十年之变迁*
郑玲丽
以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的环境保护潮流和以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标志的贸易自由化潮流间发生激烈的碰撞,贸易与环境问题则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1)参见秦天宝:《WTO与环境问题研究报告》,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07年第1期。GATT/WTO迄今尚未有效解决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一系列重要的多边环境条约(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Agreements, 以下简称MEAs)(2)多边环境条约概分为三种:第一,调整某一特定类型产品(如野生动物)贸易;第二,以保护国家不受有害物质对其国内环境的损害(如有害废料);第三,保护“全球共同财产”,如臭氧层或全球大气系统。所有这三种类型都要求跨境合作,特别是第三种类型,须归类为具有整体性。包括《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生物多样性公约》诞生,成为国际环境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比较法的视角看,国际环境法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化和碎片化的特征。(3)参见秦天宝:《后里约时代国际环境法的回顾与展望》,载《世界环境》2012年第6期。多边环境条约是环境保护最原始最直接的条约体系,但环境问题的发展速度远超MEAs解决环境问题的速度。规范性与有效性的矛盾是当代国际环境法实施中普遍面临的基本矛盾。(4)参见曹炜:《国际环境法造法机制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NAFTA)为逻辑起点,环境条款逐渐被纳入大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以下简称FTAs)或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以下简称RTAs)(5)区域贸易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以成员间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歧视性经济政策为目标而缔结的贸易条约或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间经贸安排。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协议彼此取消进出口关税和各种非关税措施,各自仍然保留与第三国贸易关系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自主权。参见左海聪:《国际经济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本文区域贸易协定,包含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优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s)、新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甚至新的经济安排(Economic Arrangements)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排除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s Agreements, BITs)或多边环境条约。之中,开启了RTAs环境保护的新纪元。在许多全球性的MEAs中,缔约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区域来帮助执行这些协定。(6)See Edith Brown Weiss, The Fiv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 Living History, in Engaging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rds. ch. 5, Edith Brown Weiss &Harold K. Jacobson eds., 1998.RTAs超越MEAs及WTO成为保护环境更有效的国际条约典范。环境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主流的贸易问题,(7)Steve Charnovitz,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0, September 2007, p.3.为了从国际贸易法层面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这三重全球危机,回顾梳理三十年来RTAs环境条款(8)本文RTAs环境条款是指任何直接和明确提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环境相关问题的条款,包括RTAs/FTAs可持续发展条款及RTAs/FTAs气候变化条款。之变迁实属必要。(9)研究RTAs环境条款国内代表性著作有:郑玲丽:《环境与贸易——CPTPP环境章节解读及我国法律对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李丽平:《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环境议题研究》,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国内代表性论文有:林灿铃、魏林耀:《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环境义务及其应对》,载《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曾文革、刘叶:《〈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CPTPP环境保护条款的比较及启示》,载《国际商务研究》2022年第1期;边永民:《〈美加墨协定〉构建的贸易与环境保护规则》,载《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梁咏、侯初晨:《后疫情时代国际经贸协定中环境规则的中国塑造》,载《海关与经贸研究》2020年第5期;陈咏梅、吴曼嘉《美国FTA中的环境条款范式论析》,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3年第1期;朱京安:《应对TPP高标准环境政策的新思路——适度环境标准》,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李振宁:《环境保护的“多-双边”协调模式:基于自贸协定环境条款的文本分析》,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4年第5期;赵玉意:《BIT和FTA框架下环境规则的经验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5期;李寿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载《时代法学》2005年第5期。
一、1992年以来RTAs环境条款的演变脉理
WTO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10)https://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WTO环境数据库(Environmental Database, EDB)(11)https://edb.wto.org/.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均为RTAs环境条款定性和定量分析提供了重要客观依据。据WTO官网统计,1992年至2022年共有354个RTAs生效,载有环境条款的RTAs多达202个,占比57%。(12)http://www.rtais.wto.org.基于“贸易与环境”综合性数据库,(13)加拿大Jean-Frédéric Morin教授领衔与德国发展研究所联合开发的“贸易与环境”综合性专业数据库(TRend and ENvironment Database, TREND),https://www.greengrowthknowledge.org/tools-and-platforms/trade-environment-database-trend.本文针对202个RTAs环境条款进行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和比较分析,拟从RTAs环境条款变迁的主要阶段及其总体特征总结其演变规律,并对未来RTAs环境条款进行预判。

表1 系作者根据WTO的RTAs数据库统计制成
(一)RTAs环境条款1.0(1992年-2002年萌芽阶段)
在联合国《里约宣言》影响之下,1992年有28个RTAs生效,载有环境条款的RTAs就有8个;2002年有98个RTAs生效,载有环境条款的RTAs有31个。从国别来看,美国在签订MEAs方面往往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14)根据美国国务院2023年统计,共9项美国政府已签署的多边环境公约迄今未得到参议院批准,包括《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跨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议定书》等,https://wwww.state.gov/treaties-pending-in-the-senate/。但却是目前在贸易协定中嵌入环境条款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卷入贸易-环境争端最多的国家。(15)参见周亚敏:《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治理——南北国家的地位调整与关系重塑》,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1期。因为美国国会定期为国际贸易协定提供快速通道批准程序,但MEAs无权享受此等优待。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主要是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型RTAs环境条款居多。(16)Jean-Frédéric Morin, Andreas Dür, and Lisa Lechner, Mapping the Trade and Environment Nexus: Insights from a New Data Set,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8, Issue 1, 2018, pp.122-139.而且南北型贸易协定中的若干环境条款实际上更多地与发展有关(development related),而不是与贸易本身有关(trade related)。(17)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Rosalie Gauthier Nadeau, Environmental Gems in Trade Agreements: Little-known Clauses for Progressive Trade Agreements, CIGI Papers No. 148, October 2017, p.4, https://www.chaire-epi.ulaval.ca/sites/chaire-epi.ulaval.ca/files/publications/paper_no.148.pdf.
GATT/WTO判例法助力RTAs环境条款萌发。1991年是RTAs环境条款演变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1991年以前,只有少数RTAs就环境条款进行谈判。(18)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是第一个包含环境条款的RTA,第100条和第235条分别规定了欧共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总体目标、原则、考量因素等,从而为欧共体的共同环境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尤其是为解决那些影响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行相关的环境问题。1991年美国在GATT金枪鱼-海豚案中败诉,导致美国国内环保主义者激烈的抗议,之后美国更频繁参与到贸易谈判进程中,其成果包括1992年NAFTA及其附属环境合作协定(NAAEC)、GATT关于环境措施的规定等。1992年至2005年期间含有环境相关条款的RTAs数量增长较快,但这些RTAs环境条款具体数量仍然有限,主要是与环境有关的例外情形和序言。然而,这一期间出现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环境条款的RTAs。1992年签署并于1994年生效的NAFTA,是将贸易自由化目标置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国际协定,该协定为协调贸易规则与环境标准而做的相关规定,被视为成功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典范之一。NAFTA规定了有效执行环境法律和标准的承诺,并且缔约方承诺不会为了吸引投资而降低这些环境法律和标准。NAAEC还包括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体制安排、审查和监测机制以及争端解决程序。NAFTA共创造了46项前所未有的环境条款,分布于农业、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和投资等章节,且NAFTA及其环境议题谈判过程对美国后续FTAs产生了重大影响。(19)Jean-Frédéric Morin, Joost Pauwelyn, and James Hollway, The Trade Regim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Environmental Norms in Trade Agre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20, No.2, 2017, pp.365-390.晚近美式FTAs采用一整章来讨论环境问题,包括执法和争端解决机制。
(二)RTAs环境条款2.0(2002年-2012年发展阶段)
2002年伊始,RTAs环境条款创新更加丰富普遍。2002年以来,每年签署的含环境条款的RTAs数量超过20世纪60年代的总和。从缔约主体来看,2005年开始,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RTAs环境条款数量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南南型RTAs环境条款的数目激增,但南南型RTAs环境条款的范围和承诺水平通常不如南北型RTAs环境条款那么详细可执行。虽然权力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RTAs环境条款创新的分布,但RTAs环境条款创新随着参与方的增加变得更加普遍。(20)同上。2011年载有环境条款的RTAs数量首次突破100个,达105个。南南型RTAs环境条款的持续攀升,意味着环境承诺不一定由监管力度大的发达国家强加,发展中国家在自己的南南型贸易协定中承担了环境保护的义务,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层面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和条约承诺。(21)Lisa Lechner and Gabriele Spilker, Taking it seriously: commitments to the environment in South-South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https://doi.org/10.1080/09644016.2021.1975399.但RTAs环境条款可能演变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或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如何在RTAs层面贯彻MEAs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国家自主贡献原则及预防原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内容来看,环境例外与环境合作仍然是最常见的RTAs环境条款类型,但不同区域、不同成员的RTAs在不同范围、深度和广度上渐次纳入更多创新性环境条款,特别RTAs层面的环境合作与环境治理已超出了WTO涵盖的环境议题。2010年之前RTAs一般只在序言中提及环境,而没有介绍缔约国各自的环境目标,“高标准”的环境基准尚未制定出来。除了RTAs本身,一些与RTAs平行谈判或在协定生效后谈判的附带文件也包括与环境有关的具体条款。如2006年日本-菲律宾FTA包括一份换文,确认该协定不妨碍根据《控制危险废物跨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在现有和未来的国家立法下通过或执行禁止出口有毒废物的措施。
(三)RTAs环境条款3.0(2012年-2022年深化阶段)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22)The Future We Want,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27 July 2012,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强调贸易协定领域高环境标准的规则制度建设,推动了新一代RTAs环境条款进一步强化和夯实,巨型FTAs、RTAs、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乃至经济框架成为环境保护包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兴规则载体。在已通知WTO的RTAs中,一半以上RTAs主体部分包括环境相关条款。2018年12月31日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以下简称CPTPP),堪称迄今为止覆盖区域最广、涉及环境领域最宽、环境规范标准最高、环境条款内容篇幅最长的巨型FTA。在某种程度上,CPTPP也可以被称作是NAAEC的升级版。CPTPP第20章代表了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主流,(23)参见韩立余:《TPP协定的规则体系:议题与结构分析》,载《求索》2016年第5期。也代表了RTAs环境条款的关键转折点。鉴于CPTPP内容的先进性及其成员的代表性,其环境章节成为贸易与环境关系的重要内容,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WTO多边贸易体制中环境协定的模板。(24)CPTPP除第20章环境专章外,其他许多章节均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详见郑玲丽:《环境与贸易——CPTPP环境章节解读及我国法律对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263页。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以下简称USMCA)作为NAFTA2.0版本,曾被美国贸易代表断言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所有FTAs中最详细的环境章节。USMCA在NAFTA基础上回应了当代环境问题,包含了比以往任何贸易协定都更为丰富的环境条款,(25)USMCA第24章“环境”包含了30项NAFTA并未涉及的环境议题,与CPTPP第20章高度相似,设置了关于多边环境条约、保护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免受船舶污染、空气质量、海洋垃圾、贸易和生物多样性、外来入侵物种、海洋渔业捕捞、可持续渔业管理、海洋物种保护、渔业补贴、森林、遗传资源、环境产品及服务和未列入NAFTA的转基因生物等的具体规定。制定者力求使其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新范式”。(26)Noemie Laurens, Zachary Dove, Jean Frederic Morin and Sikina Jinnah, NAFTA 2.0: The Greenest Trade Agreement Ever, World Trade Review, Vol.18, Issue 4, 2019, pp.659-678.但CPTPP及USMCA环境章节内容设置实际上并不完备,最大瑕疵在于缺乏明确的气候条款。2022年5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启动了“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以下简称IPEF),核心是促进各国经济的韧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公平和竞争力。有别于传统的FTAs,IPEF包括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并承诺在环境领域展开具体谈判。除了传统的环境和气候问题外,还打算利用国际农业基金在农业问题上履行承诺,确保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农业体系。(27)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september/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prosperity-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gotiating-goals-connected.美国意图通过FTAs环境条款的创新修正其对外贸易政策,产生规则溢出效应,进而影响WTO。
与美国力推价值观贸易不同,欧盟积极抢占在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等应对气候问题的先机。2012年7月1日生效的欧盟-韩国FTA包含了“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专门章节。2016年签署的《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EU-Canad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CETA)(28)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canada/eu-canada-agreement_en.设置了环境与贸易的“双保险”章节,堪称新一代FTAs环境规则的集大成者。(29)CETA被欧盟考虑作为欧式FTAs环境条款的“黄金标准”。但也有批评观点认为,CETA不是一项进步的协议。CETA无法正确执行“无牙”的环境章节,特别投资法庭优先考虑企业利益而忽视公众诉权,还威胁为公共利益采取的措施,如欧盟的燃料质量指令,CETA 的国内法规章节在颁发环境许可证时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例如是否批准燃煤电厂,也未能反映加拿大和欧盟对《巴黎协定》的承诺。其第22章“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节包括内容与目标、透明度、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合作与促进等,第24章“环境与贸易”章节涉及渔业养护、濒危物种、森林管理、环境产品贸易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其中一些环境承诺比MEAs更精细和可执行。截至目前,2021年欧盟-英国FTA(30)See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of the other part. Se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22021A0430(01)&from=EN.可谓“气候”出现频率最高、涉及领域最广泛的贸易协定。“气候”一词在该协定及其附件中出现过40余次,直接涉及20多个条款,FTAs气候变化规则的数量和质量均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但2022年1月1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31)fta.mofcom.gov.cn/rcep/recep_new.shtml.作为涵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FTA,却并未包含关于环境或可持续发展的专门章节,可谓新一代FTAs环境条款的重大缺失。(32)RCEP部分章节暗含环境例外条款,如第17章第10条提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7章第12条一般例外把GA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经必要修改后纳入。
二、RTAs环境条款三十年变迁的总体特征
综上所述,RTAs环境条款的结构、内容、国别、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在RTAs中纳入这些环境条款是个动态发展过程,多年来一直在演变和扩张,且环境条款在RTAs中的位置、措辞、范围、深度、法律和体制影响等方面均有差异性。然而,RTAs环境条款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契合模式消除了缔约方“环境义务”和传统的“贸易义务”之间的差异,增强了环境义务在RTAs层面的法律约束力。RTAs环境条款三十年来呈现如下特征:
(一)“冲突条款”加强成员在RTAs层面遵守MEAs是重大条约创新
如果某些MEAs项下环境义务与RTAs具体贸易义务不一致,RTAs规定应以MEAs的环境义务为准,此类条款可概括为“冲突条款”(conflict-of-laws provision)。为什么“冲突条款”加强成员在RTAs层面对MEAs的遵守是重大条约创新呢?因为贸易义务与MEAs之间的不一致是目前WTO谈判中尚未解决的问题。(33)参见祁欢:《WTO与多边环境协议(MEAs)关系中的条约法问题》,载《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基于国家意志协调理论,所有MEAs遵约机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其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主权国家是否同意并愿意妥善执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包括《巴黎协定》在内的大多数MEAs都缺乏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倾向于采用不遵约机制(Non-compliance Mechanism),也不包括对缔约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的义务。(34)Daniel Bodansky,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Paris Agreement, Review of Europea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5, Issue.2, 2016, pp.142-150.
RTAs大量与环境有关的条款集中于成员对所涵盖的MEAs做出具体义务承诺。其中一些条款重申了MEAs的重要性,另一些条款则重申了MEAs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他条款要求缔约方确保他们的环境法律和政策与MEAs的义务相一致。少数条款进一步要求缔约方通过并维持环境法,以履行特定MEAs项下义务。少数条款还进一步要求缔约方加入某些MEAs。RTAs也包括RTAs环境章节与其他MEAs之间关系的规定。此类条款的承诺也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环境条款,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当贸易自由化承诺与MEAs相关措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时,MEAs项下环境义务可以优先于贸易义务。(35)NAFTA第104条规定,在发生任何不一致的情况下,某些环境条约应优先考虑,“只要一缔约方可以在履行此种义务的同等有效和合理可用的手段中作出选择,则该缔约方应选择与本协定其他规定最相符的替代办法。”美国在2007年5月社会议题政策改革后放弃了这一条款,但重新启用了一个版本。此后美国缔结的FTAs载有下列条款:“如果一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与[所列环境]条约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则该方应寻求平衡其在两项协定下的义务,但这并不妨碍该缔约方采取特定措施,以遵守其在条约项下的义务,前提是该措施的主要目的不是对贸易施加变相的限制。”RTAs这一类别条款出现频率较高。
例如,USMCA第24.8条关于MEAs共有5项具体规定,明确列举了七项MEAs,呼吁各国政府“努力确保”MEAs的实施,并要求缔约方承诺如果MEAs与USMCA存在分歧,MEAs将优先适用。(36)七项MEAs分别为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73年《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1971年《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80年《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理公约》和1949年《美洲热带金枪鱼公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争端是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下产生,专家组会根据贸易协定的文本做出裁决,而不是根据其他协定(如MEAs),除非这些协定在贸易协定中明确注明。2002年加拿大-哥斯达黎加FTA(37)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 entered into force in 2002,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gc.ca/site/eng/9.541624/publication.html.环境条款第1.4条专门规定了当FTA与MEAs之间不一致时,MEAs优先适用。2005年澳大利亚-美国FTA(38)Australi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force on January 1, 2005,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australian-fta/final-text.第19.8条要求双方应继续设法加强它们都是缔约国的MEAs和国际贸易协定的相互支持,各方应就WTO内有关MEAs的谈判定期进行磋商。CETA第22章“贸易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缔约方尊重劳工和环境国际协定,第24章“贸易与环境”要求缔约方以加入的国际环境协定为基础,第24.12条“环境问题合作”要求就MEAs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交换意见,第24.15条规定,“关于第24.4条规定的与多边环境条约有关的事项,专家小组应征求根据这些协定设立的相关机构的意见和信息,包括这些机构通过的任何相关可用的解释性指导、调查结果或决定。”
(二)“不减损条款”及“有效执行条款”在RTAs层面地位持续攀升
第一,在RTAs环境条款1.0阶段,“环境”逐渐从GATT/WTO协定下贸易义务的“例外”条款,演变为RTAs项下高水平环境保护义务的承诺。其主要文本措辞为“各缔约方不得以影响贸易或投资的方式放弃或以其他方式减损其国内环境法”,从而将环境与整个协定的主题——贸易甚至投资关联起来。此类条款可称之为“平衡条款”(39)参见赵玉意:《BIT和FTA框架下环境规则的经验研究——基于文本的分析》,载《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9期。或“不减损条款”,属于消极防御型条款。
如NAAEC规定,NAFTA各缔约方“有权设立各自的环保水平、环境发展政策和优先事项”,但是必须“确保其法律法规提供了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应继续努力完善这些法律法规”。(40)NAAEC第3条。该条款既未界定何种程度是“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也未对环保水平规定统一的有约束力的最低标准。除此之外,“不减损条款”还采用“建立各自环保水平”、“高水平保护”、“努力”等字眼。如美国-新加坡FTA第18.1条、欧盟-韩国FTA第13.3条以及欧盟-中国香港FTA第8.3条均如此规定。时隔二十余年,这一“不减损条款”在CPTPP第20章环境专章“一般承诺”、UMMCA第24.3条“保护水平”中再现,甚至要求更高。(41)CPTPP第20.3(3)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努力保证其环境法律和政策规定并鼓励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努力继续提高其各自的环境保护水平。”CPTPP第20.3(6)条规定:“通过弱化或减少各自环境法律所提供的保护以鼓励贸易或投资是不适当的。因此,一缔约方不得以弱化或减少环境法所提供的保护的方式,豁免或减损或提议豁免或减损其环境法。”但它受到“为了……”这一短语的限制,意味着缔约国既需要表明环境保护的国家意愿,也需要表明专门针对其他缔约方增加贸易或投资的国家意愿。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这样的国家意愿问题通常很难证明。这一条文规定是否有效值得密切关注。
第二,在RTAs环境条款2.0、3.0阶段,RTAs文本深化了缔约国的环境规制义务,从区域性条约层面缔约国高水平环境保护的空泛承诺发展为确认缔约国具体的环境保护义务,并确保有适当的程序法来执行。此类条款可概括为“有效执行条款”,属于积极进攻型条款。
与“努力确保”相比,“有效执行”是一项要求更高、更明确的责任,但也给缔约国保留了调查、起诉、监管和合规事项审查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缔约国环境保护义务从实体法到程序法都有明确条约规定。实体法方面,规定了诸多部门条款、企业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如USMCA第第24.13条“企业社会责任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程序法方面,如美国-新加坡FTA第18.3条,美国-澳大利亚FTA第19.3条,美国-智利FTA第19.8条,USMCA第24.6条“程序事项”共有7项具体规定。
(三)“争端解决条款”使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法律约束力由软趋硬
RTAs适用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有政治解决模式(磋商、调停、调解)、混合解决模式(磋商、调停、调解;仲裁庭、专家组裁决)和司法解决模式(特设/常设仲裁庭、专家组)三大类型。(42)参见钟立国:《论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及其选择》,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3期。三十年来,这三种模式在RTAs环境争端解决中按顺序逐渐过渡,意味着从“权力为导向”向“规则为导向”的变迁。
首先,RTAs从强制力最弱的程序性方法来尝试解决“环境义务”争端,严格遵守“谈判”的政治/外交解决模式,发生争端完全依靠缔约方协商解决。(43)统计数据表明,三十年来约30%RTAs环境条款采用这种争端解决模式。如2009年加拿大-秘鲁FTA及其附带环境协定。甚至2013年韩国-土耳其FTA第5.12(3)条规定:“对于本章(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下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得求助于第六章(争端解决)”。
其次,最为常见、影响最深远的是混合解决模式,(44)统计数据表明,三十年来约65%RTAs环境条款采用这种争端解决模式。亦称“准司法解决模式”,这种“武装到牙齿”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环境义务”争端与传统“贸易义务”争端程序上的差异。1994年NAAEC创建了与贸易问题不同的独立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当任一缔约方针对“另一缔约方持续性地未有效执行其环境法律”而请求进行书面磋商时,可启用该争端解决机制。(45)NAAEC第22.1条。当仲裁庭认定“另一缔约方持续性地未有效执行其环境法律”,一缔约方可对其进行货币制裁和贸易处罚,这是FTA第一次通过贸易制裁来执行环境法。(46)Errol Meidinge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Megaregulation Contested: Global Economic Ordering After TPP, Benedict Kingsbury, et al.,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http://ssrn.com/abstract=3165490.美国是全球率先在贸易协定中对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实施贸易制裁的国家。2000年美国—约旦FTA是美国首次将环境条款直接纳入贸易协定正文、使环境问题可以适用与贸易问题相同的FTA中的一般性争端解决条款的首例。(47)参见陈咏梅、吴曼嘉:《美国FTA中的环境条款范式论析》,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3年第1期。后续有RTAs进一步规定,可就环境章节和/或附属环境协定项下产生的环境事项进行磋商,当环境磋商未能解决环境章节或环境附属协定下争端时,少数RTAs进一步建立了具体的争端解决程序。如美国-新加坡FTA第18.7条规定,磋商程序于磋商请求提交后30天内进行,成员磋商可以寻求第三人或机构的意见和协助;如磋商未能解决问题,成员可要求FTA联合委员会予以解决。如果RTAs项下义务与所涉及的MEAs规定的具体义务不一致,少数条款规定了只诉诸RTAs争端解决;其他条款则规定,RTAs争端解决章并不适用于环境争端。
最后,最硬核的司法解决模式通过特设或常设仲裁庭或专家组,由其对环境争端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从而将环境义务提升到贸易义务同等的法律地位。(48)统计数据表明,三十年来仅约5%RTAs环境条款采用这种争端解决模式。此外,司法模式下的少数常设法庭建立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制度,即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有资格提起诉讼。在新一代FTAs中,关于有效执行环境法的承诺,FTAs通过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或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这种最具法律约束力的机制予以保障。(49)José-Antonio Monteiro, Typology of Environment-Related Provis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2016, WTO Staff Working Papers, ERSD-2016-13.CPTPP首创四级兼双重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包括环境磋商、高级代表磋商、部长级磋商和专家组程序。(50)参见魏沁宁:《CPTPP环境治理范式及中国的实践进路》,载《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对争端解决判决,争端各方必须予以承认并执行之,这当然是对争端各方主权的一种制约;司法解决模式限制了RTAs成员的政策调整能力。(51)参见钟立国:《论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及其选择》,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3期。
三、RTAs环境条款三十年变迁之困境
在对RTAs环境条款三十年的变迁进行系统全面梳理之后,不难发现,RTAs正成为贸易领域推动环境保护的主要规则载体。追求环境、劳工等非贸易目标,使得RTAs从自由贸易、降低区域内关税、削减区域内非关税壁垒的传统领域,到倡导绿色、包容性、可持续贸易、公平贸易的实体到程序规则的体制性扩张,揭示了RTAs对当代重要社会问题的共同关切(mutual concern),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
(一)“冲突条款”并未有效澄清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关系
国际法缺乏固有的规范等级,(52)参见张辉:《国际法效力等级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不能为环境保护必然优于贸易规则的立场提供一个规范依据。(53)参见许楚敬:《跨WTO体制的规则冲突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冲突条款”的发展并未有效澄清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关系及效力等级。虽然少数RTAs明确规定MEAs项下环境义务优先于RTAs项下贸易义务,(54)如CPTPP第29.1.2条。但大多数RTAs既未明确成员已签署的MEAs项下环境义务是否优先于RTAs项下贸易义务,也未澄清成员未来批准的MEAs在现有RTAs框架下居于何种法律地位。
以CPTPP为例,CPTPP对MEAs项下缔约方现有义务的处理因MEAs不同而异。CPTPP第20.4条规定,缔约方确认致力于执行其加入的MEAs,承认这些协定在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在谈判和执行MEAs方面合作的重要性。第20.5条“臭氧层保护”并没有向缔约方强加任何实质性或可强制执行的义务,只是要求缔约方采取措施控制《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未来修正案规定的物质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以下简称CITES),其遵约制度是基于缔约方的自我报告,每个CPTPP缔约方都被要求履行其CITES项下的义务,并有效执行其法律和法规。(55)CPTPP第20.17(2)条。否则,CPTPP其他缔约方就可以利用CPTPP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尽管首先鼓励缔约方通过CITES下的磋商或其他程序解决任何相关争端。(56)CPTPP第20.17(2)条脚注23、24。CPTPP争端解决条款中的附加条款旨在尽量减少CITES和CPTPP之间法理冲突的可能性。要证明某一缔约方违反了本款项下义务,另一缔约方不仅必须证明该缔约方未能采取、维持或执行法律、法规或其他措施以履行其在CITES项下的义务,且须证明这种做法影响了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当然,CPTPP包括打击非法获取的来自于CPTPP缔约方的野生动植物和鱼类贸易的条款,无论它们是否受到CITES的保护。因此,CPTPP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保护超越了CITES的规定。(57)Alberto do Amaral Júnior &Alebe Linhares Mesquita, The New Rules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Linkage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Revista de Direito Internacional, Brasília, Vol. 14, No. 2, 2017, pp. 388-411.关于《蒙特利尔议定书》和《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以下简称MARPOL),(58)CPTPP第20.5(1)条脚注3、4,CPTPP第20.6(1)条脚注6、7。CPTPP仅在第20章脚注中提及,要求每一缔约方“维持”现有的国内政策,这些政策具体列在协定附件中,履行缔约方在这两项协定下的义务。CPTPP不提供执行CPTPP缔约方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和MARPOL义务的独立机制,但提供了执行这些义务的间接机制,前提是CPTPP缔约方未能履行其《蒙特利尔议定书》和MARPOL义务,而这些不履行影响了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或投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CPTPP第20.1条“环境法”包括“缔约方为履行其基于多边环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而制定的法律法规”,通过将环境法定义为包括实施MEAs的法律,CPTPP的环境条款实质上纳入了缔约方缔结的任何MEAs,(59)Paul Nunez,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Vol.48 No.2, 2016, pp.266-267.而不仅仅是其第20章环境条款明确提及的那三个MEAs。CPTPP通过包含一系列强制执行MEAs项下的义务,挑战了以主权为基础的、创始成员国和潜在未来成员国制定条约的国家主权自主性(sovereignty-based autonomy)。(60)See generally Ching-Wen Hsueh, A Greener Trade Agreement: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Asian Journal of WTO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Policy, Vol.8 No.2, 2013.对于未来的CPTPP成员而言,批准上述三个MEAs是加入CPTPP的有效前提。这意味着,CPTPP剥夺了非MEAs缔约国独立行使其自主决定是否加入MEAs的主权权利。
(二)“不减损条款”及“有效执行条款”可能导致主权侵蚀风险
国家主权有时被认为是国际环境法最大的障碍,特别是在应对国际环境威胁方面。(61)Brian F. Fitzgerald, Trade-based Constitutionalism: The Framework For Universalizing Substantive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 Vol. 5 Issue 1, 1997.MEAs为了将尽可能多的参与者纳入其保护伞下,通常采取多边“框架+协定”的立法模式,各缔约国保留了很大的主权回旋余地。21世纪前20年见证了国际贸易法体系下RTAs环境条款的异彩纷呈,也引发了RTAs管辖权与缔约国国家主权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以USMCA、CPTPP等为代表的21世纪高标准的RTAs环境章节,其“不减损条款”和“有效执行条款”可能进一步侵蚀缔约国国家主权的环境政策空间。
由于环境问题无国界,而环境保护责任有国界。国家基于其主权,既要对主权管辖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负有责任,同时又要对共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承担责任,至少是不损害主权管辖范围外的局部或全部区域,如公海、南极及外层空间。简言之,在人类共同利益本位下,国家在环境领域肩负双重责任。(62)参见王明远:《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困境与出路:自治还是他治?》,载《清华法治论衡》第1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如CPTPP毫不例外地坚守国家利益本位和国家主权原则,即缔约方在CPTPP项下义务让位于“国内环境保护水平和环境保护优先事项”,让各国自由处理各自的环境问题。但CPTPP环境章节又设置了禁止性义务,从而为一缔约方针对另一缔约方国内主权的行使强加干涉埋下了伏笔。
(三)RTAs“环境争端解决条款”效力有待实践检验
国际争端解决较之以往更加频繁、深刻地侵蚀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力,尤其立法权,这促使主权国家不仅从法律层面,也必然要从政治层面思考主权问题。(63)参见蔡从燕:《风险社会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解构与重构》,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争端解决机制是检验RTAs环境条款有效性的试金石,也是确保环境义务履行并避免单边贸易制裁的条约法保障。近年来不仅有更多实质性的、全面的环境条款纳入RTAs法律框架,尤其CETA、CPTPP出现了更具法律拘束力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但其制度化程度较低,通过诉诸这些机制而正式启动的RTAs项下环境争端少之又少。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实际效力如何,尚无定论。为什么FTAs环境条款蔚然成风,但FTAs环境争端如凤毛麟角?
首先,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更多是起到了威慑和保障程序公正的作用。2009年生效的美国-秘鲁FTA中的环境条款史无前例,其争端解决章节适用于无法通过环境协商解决的环境争端,意味着包括CITES在内的MEAs的实施,首次受到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式约束。但是,有美国学者根据研究提出质疑,没有任何案例表明争端解决程序实际上被用于执行美国缔结的贸易协定中的环境义务。(64)Chris Wold, Empty Promises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An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 Chapter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2016.研究美国缔结的FTAs环境条款表明,围绕环境条款的贸易争端解决程序很少甚至从未启用。(65)NAFTA及NAAEC项下未发生任何环境仲裁案件,几起代表性案件有:1995年濒危物种法案案(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Case), 1995年国家森林采伐案(The National Forest Logging Case)和1996年墨西哥科苏美尔港码头案(The Cozumel Pier Case),启动了NAFTA及NAAEC项下环境争端解决程序,有学者评价这些案件揭示了NAFTA及NAAEC环境争端解决的公开通知程序和提高缔约方环境意识是成功的,但各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解决方案,因此该协议未能充分解决环境问题,是“纸老虎”。See Angela D. Da Silva, NAFTA and the Environmental Side Agreement: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Cozumel Port Terminal Controversy, Environs, Vol.21 No.1, 1998, pp.43-62; Michael J. Kelly, Bringing a Complaint Under the NAFTA Environmental Side Accord: Difficult Steps Under a Procedural Paper Tiger, But Movemen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Pepperdine Law Review, Vol. 24, No. 71, 1996, pp.91-97.
更重要的是,RTAs成员更倾向诉诸于WTO争端解决机制。WTO比新的和未经测试的RTAs环境争端解决条款在经验和合法性方面更胜一筹。WTO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DSM),且存在上诉审查,确保了判例的可预测性。(66)P. Van den Bossche and M. Lewis, "What to Do When Disagreement Strikes? The Complexity of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rade Agreements" in S. Frankel and M. Lewis (eds.) Trade Agreements at the Crossroads, Routledge, 2014, p.9.国际法是国家意志协调一致的产物,WTO相对于RTAs而言,代表着更大多数国家更协调一致的意思表示,DSM提供了更有可能被各方接受和遵守的裁决结果,未来针对MEAs施加或要求的贸易限制的争端被提交WTO专家组是理所当然。(67)Joost Pauwelyn, WTO Compassion or Superiority Complex? What to Make of the WTO Waiver for ‘Conflict Diamond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4, Issue.4, 2003, p.906.
四、应对RTAs环境条款变迁的中国方案
三十年来,中国对外缔结的RTAs环境条款主要集中于RTAs2.0和RTAs3.0阶段。迄今中国对外签署并实施了19个FTAs,包含环境条款的有10个,2008年中-新加坡FTA、2008年中-新西兰FTA、2014年中-瑞FTA、2015年中-韩FTA、2018年中-格鲁吉亚FTAs这5个FTAs甚至包括独立的环境章节,中-新加坡FTA则包含单独的环境合作协定。(68)迄今中国FTAs纳入环境条款的有:2006年中-智利FTA、2008年中-新加坡FTA、2008年中-新西兰FTA、2009年中-巴基斯坦FTA、2010年中-秘鲁FTA、2014年中-冰岛FTA、2014年中-瑞士FTA、2015年中-韩FTA、2018年中-格鲁吉亚FTA,占中国对外签署的FTAs33%,其中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4国为CPTPP缔约国。详见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我国FTAs环境条款多为框架性内容,以环境合作为主,且针对不同贸易伙伴设计个性化(case-by-case)的FTAs环境条款。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中国将要求在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方面提供更多条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重点将放在联合研究和协调环境标准上。(69)Henry Gao,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and Labour Provis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ugust 2017,http://e15initiative.org/blogs/chinas-evolving-approach-to-environmental-and-labour-provisions-in-regional-trade-agreements/.这种个性化FTAs环境条款模式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合作伙伴的不同偏好,但另一方面导致在所有中国对外缔结的FTAs实质性环境条款方面存在高度差异。而且目前中国缔结的所有FTAs项下环境争端均不适用FTAs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亦必将成为FTAs设置环境章节的主旋律。(70)参见林灿铃、魏林耀:《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环境义务及其应对》,载《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为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71)参见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大潮下,我国应秉承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确处理MEAs与RTAs之间的条约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稳步推进FTAs环境条款的“中国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环境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与一些发达国家在斗争中求合作,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RTAs环境条款范式,从而为中国参与国际法治、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一)正确处理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关系
正确处理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关系,主要是正确处理已对我国生效并具有贸易因素的MEAs与我国缔结的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关系。首先,我国应接受全面的环境承诺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执行的条约法义务,并拟定贸易、投资相关的FTAs环境条款的“中国升级版”。尽管我国是诸多MEAs的缔约国,(72)中国自1979年起先后签署了CITES、UNFCCC、《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MEAs,这些大多数都具有贸易因素。但我国对外缔结的FTAs并不包含任何MEAs的具体承诺,仅仅重申将利用国内立法有效履行其对双方或各方均为成员的MEAs的现有承诺。(73)如2015年中-韩FTA第16.4(3)条和2018年中-格FTA第9.3条。就我国加入的MEAs而言,我国接受了其中所包含的贸易限制义务。(74)如2014年中国-瑞士FTA第12.2条规定:“多边环境条约和环境原则1.缔约方重申致力于在其法律和实践中有效执行其作为缔约国的多边环境条约,以及第12.1条所述国际文书所反映的环境原则和义务”。我国在RTAs中明确规定MEAs的优先适用原则,可以有效解决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冲突。当然,也应该明确适用MEAs的前提条件,在此可以借鉴欧盟提出的原则:(1)MEAs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谈判达成;(2)谈判对所有国家开放;(3)执行和实施这种MEAs对所有RTAs成员都同等便利;(4)双边的或区域性环境协定不具有贸易法上的域外效力。
其次,我国应以切实履行MEAs为支点,团结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75)“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由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埃及、玻利维亚等18个发展中国家组成,是气候多边进程中一支重要谈判力量。坚持和维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国家自主贡献原则及预防原则,秉持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相互支持的政策目标,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RTAs环境条款规则体系。在未来RTAs中,首先重申并承诺履行我国加入和批准的MEAs项下义务,特别是一些MEAs规定了关于环境法律和事项的透明度和信息获取的承诺,公众对环境事务的参与,如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合作活动,违反国内环境法时诉诸法律和程序保障。然后通过国内环境法的制定和执行来履行MEAs涵盖的义务,包括关于MEAs的对话与合作,与MEAs有关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MEAs项下的贸易措施应与积极的激励措施同时适用,如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76)Margareta Timbu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nd the Trade Measures Contained in These Agreements,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Vol.4, Issue2, 2012, p.258.
(二)通过“一带一路”稳步推进RTAs环境条款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在当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面临新挑战和以CPTPP为代表的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促进我国加大全面改革开放和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意义重大而深远。(77)参见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载《法学》2016年第5期。应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自固有的监管权,并保留各国在确定环境立法和环境监管优先事项、保障公共福利目标方面的灵活性,如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可用尽生物或非生物自然资源的保护,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效环境执法等措施促进形成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支持的贸易和环境政策与实践,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来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在RCEP框架内达成软磋商性质的包括环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诸边协定,建立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机制。(78)参见王彦志:《RCEP投资章节:亚洲特色与全球意蕴》,载《当代法学》2021年第2期。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应强烈反对肆意将贸易与劳工或环境标准挂钩从而对他国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早在1992年东盟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反对在贸易和发展合作中利用人权,特别是环境问题作为“条件”的呼声最为明确。在联合公报中,外长们坚持认为,环境和人权问题不应该成为经济和发展合作的条件。(79)Se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25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Manila, July 21-22, 1992, para 18.2014年中-瑞FTA“缔约双方同意环保标准不得用于贸易保护主义之目的”这种禁止性条款可推广作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相关的FTAs环境条款的“中国升级版”模板。
(三)灵活运用RTAs、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环境争端
虽然目前尚无根据MEAs或RTAs环境条款针对我国提起的争端,但我国应未雨绸缪。应强烈反对他国以环保为借口利用RTAs环境条款在其管辖范围以外对我国采取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的行为,反对域外环境立法及实践的单方面行为。这些行为通过制定国内立法,单方面定义我国可能尚未接受的环境议题,将他国环境标准强加给我国,从而对我国实施贸易禁运或特别关税及配额,其歧视性、非法性显而易见。
首先,我国应将协商和对话作为启动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手段。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原则上应旨在促进成员遵守RTAs环境条款,而不应以制裁为目的。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可取决于RTAs的具体环境条款以及争端的性质。有一系列程序可供考虑,其中包括斡旋、调解、调停、情况调查委员会、争端解决小组、仲裁以及争端所涉当事方之间达成的任何其他可能的司法路径。
其次,在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下,增补完善RCEP环境争端解决机制。RCEP第19章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也极具创新性地规定了对于最不发达缔约国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可在RTAs环境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采纳。
最后,WTO争端解决机制代表国际争端解决的模范国际法,应成为RTAs项下环境争端解决的最佳选择。虽然鲍威林教授指出,WTO专家组对于非WTO规则的违反诉求也不具有管辖权,这些规则包括诸如环境和人权条约以及一般国际法,(80)参见[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03页。但是RTAs环境条款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产品贸易与环境服务贸易自由化、低碳技术转让及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如涉及WTO非歧视原则、GATT第20条、GATS第14条、SCM协定等,仍应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日益复杂的环境争端。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涉及碳边界调节机制、碳标签等气候变化诉讼时,未来无论在WTO还是RTAs,其裁决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预见性等方面情况不容乐观。从环境争端解决的角度来看,新近生效的如CPTPP、CETA在准司法甚至司法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普遍变得更加注重程序法规则。CETA的规制合作在文本内容上完成了换代转变,通过灵活开放的条款设计,在尊重国家规制主权以及条约体系性约束的基础上,尽可能满足经贸活动的规制合作需要。(81)参见张亮:《规制合作的CETA范式:生成逻辑、文本内容与实践进展》,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年第4期。巨型RTAs缔约方用来解决这些环境及气候变化问题的规则路径及未来实践,将深刻影响未来RTAs环境条款的发展面向,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
五、结语
从三十年前颇有争议发展到今天不容回避,将环境条款纳入贸易协定已成为贸易协定谈判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RTAs环境条款近三十年的变迁充分表明,由于在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方面具有体制性优势,RTAs不仅推动了各国政府在国际条约项下达成共同意志,制定严格的环境法律法规并有效执行,而且也促进了国际经贸协定的革命性变革,即贸易协定项下环境规则的趋同化,环境义务的硬法化。RTAs环境条款范围在不断扩大,并得到更广泛的遵守和执行,但这种变迁不得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得违反不干涉原则。新一代FTAs开启了国际贸易法治的新纪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贸易协定、国家主权和环境监管自主权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