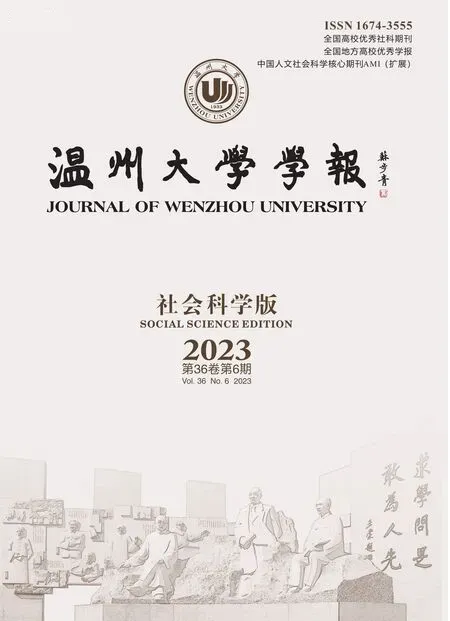从绝响到转型:近现代“文法”概念与“文法学”
谢文惠
(广州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文法”的“文章学”概念至宋元时期基本定型,明清“文法”概念虽偶有新变,但大致袭故蹈常,直至晚清古文谢幕,“文法”概念才开始了近现代的转型。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论的诸多术语和观念(包括“文法”),皆经历了渐变至激变的过程,但当今学界对近现代文论的研究往往偏向于一种割裂的状态。其一是文学运动阶段上的割裂。“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为实现彻底的反传统,与古代文论呈决裂的姿态,导致了晚清到“五四”这一阶段文论的“断层”情况。这误导了一大批学者直接遗略晚清至“五四”这一阶段的历史链条,割裂了晚清文学革命、民初文学革新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其二是文学时代分期上的割裂。对于中国文学的近代、现代分期,众家聚讼不已。中国近现代的过渡时期是中国整个文学乃至文化的转型期,是中学和西学相互碰撞的整合期,是文学创作及理论与政治经济等多种思潮共同化育的自我进化期。过分强调近现代的分期往往会疏于对过渡时期文学的考量,从而导致古今文论的长期疏离,这不利于对古今文学的嬗变进行整体观照。其三是中西文学要素的断裂。中国文论诸多术语和观念的转型,是在西方文论大量输入的语境中完成的,但若过于重视西学思想而忽视了众多本土化元素,误认为大多术语是外来“引进品”,甚至将西方的整个文学话语体系照搬于中国,那么中国本土文学要素就变成了“革命”对象,这就会直接导致中西方文论的不可调和。而“文法”概念便是这三种割裂状态下的文学“牺牲品”:“国语文法”的迅速普及,使“文法”概念剥离了古代文章学含义,仅属于语言学范畴;在西学的猛烈冲击下,本于中国传统的“文法”概念,却被改造成“舶来品”。研究“文法”概念的近现代转型,不拘于某一重大文学或政治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走向,有利于还原“文法”的本土内涵,从而突出“文法”概念的民族特性;辨析“文法”概念的古与今、中与西,进而连接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通“近代”与“现代”的文学进程,打破断代文学论,避免学科分化带来的学术弊端。
一、传统文法概念至明清的余绪
传统“文法”概念主要关涉到哲学、律法学、训诂学、文章学几个方面,分别指向“文法自然”“礼文法度”“语词句法”“作文法度”,其中“文法”的“文章学”概念至宋元趋于定型。简而言之,宋元时期的“文法”涵盖了学文法、读文法、作文法、评文法,同时围绕着“文”的“有法”与“无法”、“定法”与“活法”等辨证内容展开,明清的“文法”基本不出苑囿。较之于宋元,明清“文法”概念在继承中发展,更为清晰和系统,尤其体现在对文法的归纳和反思上。
随着辩体意识越来越强烈,古文的独尊地位愈来愈突出,“文”的文体不断细分,“诗”与“文”两种文体严格区别,“诗法”与“文法”也成为因文体不同而相对的两个概念。元代揭傒斯《诗法正宗》曰:“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难以艺,无不有法。”[1]参见:揭傒斯.诗法指南[G]//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69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23。这里“文法”特指文章之法,与“诗法”区分开来。作者旨在说明“诗”与“文”各有体、各有法,也强调了“有法”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明代储巏也说:“诗文字画,皆有典则。”[2]参见:储巏.柴墟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357。自此,“文法”更倾向于指文章之法,尤其是古文之法。唐顺之分析了各时代文法的总体特征和规律:“汉以前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者严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3]参见: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G]// 纪昀.四库全书:第1455 册.影印文渊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28。唐顺之是古文大家,他所说的文法主要针对古文而言,文法出乎自然以至于“不可易”“不容异”,一方面重申并回应了“文法”的自然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体现了明代文法的严谨。
文章之法的要求愈加细化及高度概括化,重点体现在文章作法上。明代李腾芳《文字法三十五则》用极为简练的三十五字,如“抢”“款”“度”“翻”“脱”“垫”“擒纵”“逗”等,总结了诸多文字之法,“文法”概念更为形象化[4]参见: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491-2508。明末清初唐彪的《读书作文谱》释“文法”也是如此,他摘取约十来种文章作法,并提炼出“开阖”“宾主”“推原”“遥接”“抑扬”等文法术语进行论述,简明意达[4]3480-3493。方东树《昭昧詹言》列举了二十余种文章技法,“文法”包括“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倒挽”“不许一笔挨平”“入不言,出不辞”“离合虚实,参差伸缩”等,其将“文法”具体细化为多种不同的文章技法,与“选字”“章法”“起法”“转接”“束法”等文章作法并列,“文法”的范围似乎缩小了,其实不然。方氏说:“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语不接而意接。”[5]参见: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8在方氏看来,“文法”是文章作法的统称。清代曾国藩提倡“间架说”:“作文宜摹仿古人间架。”[6]参见: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赵焕祯,校注.武汉:崇文书局,2012:86。他师古人文重“间架”,向后学昭示学文路径,是对宋元“文法”概念偏于“学文法”含义的延续。关于“学文法”,清代章学诚、徐时栋亦有对学前人文法的论述,尤其推崇史著文法,与宋元“文法”的崇尚对象和审美要求同出一辙。章学诚《文史通义·论课蒙学文法》云:“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而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7]参见: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05《文史通义·文理》云:“学文之事,可以授受者规矩方圆,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7]83徐时栋批评列国、两汉史事演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8]参见: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岀版社,2003:424。。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也明确表示古人之文只有“法”可以学习,认为“古人文字最不可攀处,只是文法高妙而已”,“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但学其法,“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9]参见: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这又回归到宋元“死法”和“活法”的议题了。同“死法”与“活法”一样,至明清,关于古文“有无定法”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云:“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不能为文,则有法如无法。”[10]参见:袁枚.袁枚文选[M].高路明,选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36。姚鼐在《与张阮林书》中说:“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11]参见:姚鼐.惜抱轩尺牍[M].卢坡,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49-50。方东树说:“古人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无定而有定,不可执著,不可告语,妙运从心,随手多变,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5]28他们强调的都是“文法”的变通性和灵活性。
鉴于宋元之际文之“法”过度浸淫渐渍于“理”,明清文论者反思“文法”,试图再次给“文法”下定义,其间不仅表明了对文章创作技法的认识,更包含了“文法”的内涵指向和法理意义。明末清初侯方域《倪涵谷文序》曰:“能扶质而御气者,才也;而气之达于理而无杂糅之病,质之任乎自然而无缘逝之迹者,法也。”[12]参见:王树林.侯方域集校笺:上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51。在侯方域看来,文法就是集气与质、理与自然于一体的概念:“法”贯之于“理”,并任乎自然,是“扶质而御气”的手段。清代廖燕《复翁源张泰亭明府书》所谓“文莫不以理为主,理是矣;然后措于词,词是矣;又必准之于起伏、段落、呼应、结构之法”[13]参见:廖燕.廖燕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8。,不仅将“文法”分解为各种类型的文章章法,更将其与“文理”的区隔表达得更为明晰。清人魏禧将“文法”譬之为“工师规矩”“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法”就是诸规矩,“不可叛也”,更不可“分寸态意而出之”[14]参见:魏禧.魏叔子文集[M].胡守人,姚品文,王能宪,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428。,这既迎合了“文法”固有的法律学含义,又将“文法”在文章创作过程中的地位抬高到一个明显的高度。方苞始则倡“义法”,以《春秋》尚简之笔法为据,以前人“文法”过于注重“律”与“技”为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5]参见:方苞.方望溪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29。在方苞看来,“义法”指作文之法,可以弥补宋元文法偏“理”“技”而疏于“义”的短板,“义”与“法”同等重要。后学钱大昕《与友人书》提出:“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16]参见:钱大昕.潜研堂集[M].吕友仁,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07。他认为“法”较之于“义”更为重要,其观点彰显了“文法”的优越性。李兆洛《答高雨农书》则认为“义充则法自具,不当歧而二之”[17]参见:李兆洛.养一斋文集[G]//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3。,可谓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修正。但无论重“义”还是重“法”,皆是对宋元“文法”重议论、重技法的反思和补充,是宋元“文法”文章学概念在明清时期之余音的反映,奠定了桐城派古文文法理论的主要基调。
二、晚清古文谢幕与古代“文法”概念的绝响
郭绍虞曾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18]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545。清代古文创作以桐城派为主,虽景象繁荣,但比起唐宋,总体水平不高。尤其在姚鼐因汉宋之争而告退后,桐城古文逐渐消沉衰亡,其间虽有方东树等人欲振其风,但因面临家国种族之难,他们力求寻找文章的治国救民之道,故而过于推崇经世之术,终究未能将其“家法”发扬光大。晚清至“五四”,经史时务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林纾等人作为桐城派的最后收官者,纵使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也仍旧无法扭转古文摇摇欲坠的局面,古代“文法”概念至此时也成为最后一发绝响。
晚清至“五四”之际,科举废除消亡,文言文法已不再适应新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晚清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新文体和文界革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19]参见: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G]// 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4:82。,直接拉下了古文的帷幕。白话文倡导者声势盛大,古文阵营黯然而熠,为延续古文岌岌可危的颠坠命运,桐城派殿军林纾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在古文理论方面尤其针对古文文法,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文法”概念基本上沿袭了清代侧重指文章技法的内涵,但更为系统和全面。他在《春觉斋论文》中提出“应知八则”“用笔八则”“用字四法”等,并翔实阐扬了多种古文技法,将之总结为“笔法论”,主张用起笔、伏笔、顿笔、顶笔、插笔、省笔、绕笔、收笔间架文章[4]6365-6433。较先前的“文法”,林纾“笔法”更为简单,但并非平铺罗列,林纾旨在明乎后学取经之道,每论一则“笔法”时都从“作用”“用法”“注意”三个角度阐发。除了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外,其他古文家在文法理论方面也作出了不菲成绩,相关论述细致翔实,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切实的指导意义。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谈了“作文之法”[20]参见:吴曾祺.涵芬楼文谈[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全书举凡明法、命意、修辞、练字、运笔、仿古、设喻、省文等写作要则,全面丰富。再如,王葆心《古文辞通义》中,《识涂篇》就古文的“读法”“讲法”“作法”“格法”作了细说[4]7221,《解蔽篇》分析了古文的常见弊病,并给出其解蔽之方[4]7060,《义例篇》则介绍了古文写作中引书、称谓、标题等具体元素以及编辑别集总集的简要方法[4]8042,这些“文法”观念与其他篇章组成一个完备的系统。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是“国文”范本,用“贯通”来求古今文法之通则。“经纬”为作文法则、法度之义[4]8248。全书以文章作法为经,列四十四文法,如局部整齐法、辘轳旋转法、鹰隼盘空法、奇峰突起法等,辅以篇章分析,文法名目鞭辟入里,极易于读者从中习得书写文章之法。
面对古文岌岌可危的境况,古文家们十分注重总结,其笔下的“文法”极具概括性,言简意赅又体大虑周。但桐城派外,“文法”论述荦荦大端者不多,唯来裕询的《汉文典·文章典》可圈可点。该书论及70 余种文章技法,将之分为章法和篇法两类,其中章法又分为起法、承法、转法和结法,篇法分为“完全之篇法”和“偏阙之篇法”,各法类别下又细分[4]8564-8573。其条分缕析之细致,非前人“文法”可及;且前人多针对理论,来氏则对每种“文法”先下“定义”,后援实例证之,实践操作性很强。在分类列法上,唐恩溥《文章学》下卷“学文绪论”述有为文之字法、句法、篇法[4]8729,胡怀琛《文则》涉有储才之法、摹神之法、取势之法等[4]9613-9615。此时有关“文法”的论述大部分沿袭前人经典的“文法”论题,如唐恩溥《文章学》“为文宜先知法度”[4]8730、胡怀琛《文则·循法第八》“作文之有法,犹制器之有规矩也”[4]9616。尽管古文“文法”概念在一系列的古文文法理论的提出下得到巩固和完善,并被囊于文章学范畴,但随着新文化运动浩浩汤汤地进行,古文暂退历史舞台,“文法”的对象发生了巨变,“文法”的内涵走向历史训诂学的范畴。
鸦片战争后,封建阶级为自救发起洋务运动,改良派掀起戊戌变法,国内外矛盾尖锐。帝国主义应侵略和传教的需要,向中国输入印欧语言,西洋科学文化由此大量涌入中国。洋务派“左翼”马建忠言:“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21]参见: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故其作《马氏文通》(1898年),学希腊、拉丁之文法,以实现“大群”的政治理想。梁启超评之曰:“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22]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6:93。《马氏文通》是“文法”专书,其“文法”不再指向宏大的文章学,而专指语言学概念,偏指西方语言之法。自《马氏文通》后,“文法”概念向狭义的方向发展,此后的汉语文法著作皆因袭《马氏文通》的体系和观点,如章士钊《中等国文典》(1907 年)等。对拉丁文法的生搬硬套,造成马氏及后来模仿者的著作存在硬伤,真正将中西化合的要数王国维。他融会话语生成的西方哲学基础,对文法的理解呈现出超越古今、新旧之争的特点。他批评时人习希腊拉丁之文法,认为这是“学者之通病”,“彼等蠢愚之根本实存于此”[23]参见:王国维.静庵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62。他认为希腊所谓“七术”(包括文法)“遗世祖”,“皆形下之学”[23]112。他将西方术语与中国术语作对比,分析“名学”与文法的区别:“至Conception 之为概念,苟用中国古语,则谓之共名亦可。(《荀子·正名篇》)然一为名学上之语,一为文法上之语,苟混此二者,此灭名学与文法之区别也。”[23]118王国维继承唐宋以来“文法”的传统概念,又吸收西方文艺美学思想,对“文法”概念的内涵进行完善和深化,其中对“名学”与“文法”的区分,实际上是参照西方文艺学而进行的,其中贯通了儒、道文化精神和康德、叔本华美学。刘师培也兼取中西“文法”概念,其笔下的“文法”不仅指汉语语法结构,也指文章作法,如其在书中就明言:“中国文学教科书,计编十册。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24]参见: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2117关于“何谓文法”,刘师培作了明确的回答:“文法者,文章之规则也。不知文法,则差误必多。”至于“通文法从何入手”,其答曰:“以分析字类为入手。”[25]参见: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M].万仕国,辑校.扬州:广陵书社,2008:74。因此其《国文典问答》一书,上卷分析字类,下卷专论国文作法。刘师培将文法与文体并举,认为述文体之作是“文学之津筏”,辩论文法之作乃是“学文之阶梯”[24]700。刘师培批评墨守桐城派者“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24]1648,认为此乃文章之桎梏,欲摆脱这种桎梏,需要识得“规矩方圆”,即“文法”。
综合来看,晚清至“五四”之际,“文法”二字兼有文字语法及作文方法之意,但更倾向于汉语语言学层面的意思,近现代“文法”概念开始转型。其间也有反对文学革命模仿西洋文法者,如周钟游、刘师培。周钟游宣扬古文义法:“彼步趋外人撰为文典,盖亦未厌人意。”[26]参见:周钟游.文学津梁[M].上海:有正书局,1916:1。刘师培则予日本以正面还击:“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24]1648纵使如此,也无法延续古文“文法”概念的生命,在近现代“文法”著作中,古代“文法”概念也丝毫不见复位的迹象。
三、“五四”思潮冲击下近现代“文法”概念的生成
“西学的输入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文化语境,这种改变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新文化语境与新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西化’与‘化西’的过程,最终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出来的。”[27]参见:付建舟,黄念然,刘再华.近现代中国文论的转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对于传统学术而言,西方学说相当于异质文化,加快了“文法”概念的转型步伐。“五四”思潮下对西方新术语的主动引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更是直接促发了“西文法”的定型。
关于西方“文法”概念的译介源头,较早见于《马氏文通》“文法乃是葛郎玛译介”一说。这一说法完全将“文法”概念的起源归之于西学,否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法”概念。据此,“五四”时期的众多学人皆认为中国无“文法”。早期王国维说:“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23]118他认为,“名学”“文法”属于抽象与分类的学术,皆是中国学者不擅长之处,导致中国学术未达到自觉的地步。俞平伯指出:“中国本没有文法书,那些主词客词谓词的位置更没有规定,我们很可以利用他,把句子造成很变化很活泼。那章法的错综也是一样的道理。”[28]参见: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M]//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3 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514。孙中山也研究起文法问题来,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欲知文者之所当然,则必自文法之学始?即西人之‘葛郎玛’也,教人分字类词,联词造句,以成言而达意志也”,“中国向来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知有是学”[29]参见: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1。。看来,中国本无文法、文法源自西学、中国文法自《马氏文通》始……这些说法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因此,作为革命派的新文学运动者们,开始意识到了建立“本国文法”的重要性。
钱玄同斥桐城义法为“谬种”,贬骈偶选学为“妖孽”,批评古代“文法”云:“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30]参见:钱玄同.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J].新青年,1918(4):350-356。因此他主张:“国语的文法书,的确很重要。现在北京大学的国文研究所,正在那里着手做这件事。”[31]参见:潘公展,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J].新青年,1919(6):638-64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也明确提出要“讲求文法之结构”[32]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1-11。。在胡适的倡导下,很多学者都认为“欲建设新文学,文法是不可少的”[33]参见:朱经农,胡适.革新文学与改良文字[J].新青年,1918(2):174-178。。胡适告知读者现在大学里许多教授在编写国语文法书,并向大家征求参考资料。胡适提倡学习文法的目的在于采用一种规定的符号,以求白话文文法的明显易解,主要是因为白话文文法“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34]参见: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66。。针对如何作白话文,傅斯年较为具体地提出了可行的方案:“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35]参见: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J].新潮,1919(2):171-181。他认为古代文法无精神、无体式:“魏晋持论,固多精审,然以视西土逻辑家言,尚嫌牵滞句文,差有浮词。其达情之文,专尚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以视西土表象写实之文,更觉折本务莫,不切群情。故论其精神,则‘意度格力,固无取焉’。论其体式,则‘简慢舒徐,斯为病矣’。”[36]参见: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J].新青年,1918(1):62-70。于是,他重点引介“高等凭借物”—西洋文法,主张将文法全盘西化。“五四”思潮下,“文法”书的编纂迫在眉睫。潘公展致信《新青年》热切要求撰写“文法教科书”,他说“中国向来没有文法,教授上狠感困难;现在既然要建设新文学,示人以‘规矩准绳’,那么文法的书一定要赶紧编好”[31]。周作人也说“中国向来没有文法,不但八股文章没有文法,就是说话也没有文法”[37]参见:陈子善,张铁荣.周作人集外文[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562。,并言明自己喜读文法书:“读文法书,是一种思维的训练。”[38]参见:周作人.平民的文学[J].每周评论,1919(5):2-3。在新文化运动者的倡导下,“五四”前后涌现了许多“文法”书,诸如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和《比较文法》、陈浚介的《白话文文法纲要》、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和《国文作法》、叶圣陶的《作文论》等,皆指向了新时代的“文法”,将“文法”概念的转型推向了高潮,使近现代“文法”概念趋于定型。“五四”思潮冲击下的“文法”概念是全新的:其对象是白话文,而非古文;其内涵指汉语语法,而非文章作法;其立足于西文,而非中文。
面对西学的强制输入,新文化倡导者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吸收;并非一味囫囵吞枣,而是辩证对待。“五四”时期的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西学的外域性,开始结合本国文学、文字加以改造,食而再化。陈独秀首次提出中西文法的不同:“所谓文法之结构者,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r,未免画蛇添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39]参见:胡适,陈独秀.通信[J].新青年,1916(2):1-7。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认为,“讲文法”是“文字”与“文学”的分歧所在,“文字为无精神之物,文学为有精神之物”[40]参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3):1-13。。任鸿隽说:“我们晓得学文学的,未做文章以前,须要先学文字和文法;因为文字和文法,是表示思想的一种器具。”[41]参见:任鸿隽.何谓科学家?[J].新青年,1919(3):247-253。西文文法尤重语言文字,不重文学,十分客观冷静;中国文字本身就是歧义的表意文字,且古代往往将“文法”概念诉诸大文学背景下,夹杂着复杂的文化语境和历史环境,主要指作文之法;而近现代的国文文法学习西文,指的是文字。这便是中西文法、古今文法的异同。杨树达较为清晰细致地分析了古今“文法”之异:“吾国旧时所谓文法,其所讲述,有所谓起承转合,谋篇布局之法者,或应为今修辞学之所研究,有所谓神韵气味者,则神秘之谈。若夫分析词类,辨别词位,如今之所谓文法学者,在周代已有其萌芽,观孔子所记之《春秋》及《公羊》《谷梁》二传之所解说,可以证也。”[42]参见:杨树达.高等国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周祜讨论文法问题,从国情出发,他说:“东西各国的文学,莫不都有一定的文法,文理极为清楚句子极为明白;依法去做,也是极容易。”[43]参见:周祜.文学革命与文法[J].新青年,1919(2):226-231。过于强调文法,往往会限制文学创作的自由性,于是康白情率先痛切地指出“打倒文法偶像”,他说:“本来中国文里,也不宜过拘。在散文里要顾忌文法,我已觉得怪腻烦的;作诗又要奉戴一个偶像,更嫌没有自由了。”[44]参见:康白情.新诗底我见[J].少年中国,1920(9):1-14。这从侧面反映了近现代“文法”的辐射范围较广,既有新诗,又有散文。吴芳吉也喊出了反对讲求文法的口号:“自此论倡,于是趋时之辈,著为文法语法之书颇众。文法语法之论愈多,文学亦愈机械而无生气……西洋文法最擅分析之事。分析愈细密,则形容愈深刻。形容愈深刻,其于文章乃大伤纤巧。”[45]参见: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J].学衡,1923(21):1-29。刘半农从不同的角度对文法进行具体分类,将之分为“语体文法”“国语文法”“方言文法”[46]参见:刘复.中国文法通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1。79,此是从语言学出发,而非文章学。鲁迅则较为客观折衷地分析了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的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47]参见: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20他主张欧化的精密可为中国文字作新的参考和改观:“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47]382近现代“文法”一词由兼及晚清的文章学概念与语言学概念过渡到“五四”后的纯粹的语言学概念,脱离了作文之法的含义,只指汉语语言文字之法,即现在极为通行的“语法”,实际上这是“文法”概念向训诂学的回归,只不过其法之对象不再是经学,而是白话文。
四、“文法学”:近现代汉语文法学科的确立
“五四”以后,“文法”的语言学指向基本定型,国文文法提倡者奠定了后世“文法学”的基础,关于建立汉语文法学体系,不少学者提出了众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了“文法学科”的建立问题。
早期任鸿隽将文法比附科学:“文法者,依历久之习惯而著为遣词置字之定律也。及其既成,则不可背。习之者辨其字句之关系,与几何之证形体盖相类。故西方学者皆谓文法属于科学,不属于文学。吾人则谓其为文词字不中律令者,其人心中必无条理。故文法之不可不讲,亦正以其为思理训练上之一事耳。”[48]参见:任鸿隽.科学与教育[M]//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春,选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66。从中可见,他肯定了中国文法理论的遣词置字之定律,认为辨析字句关系的文法更注重思辨与文理,即语言文字等的组织规律,以此为文法学科的建立大造舆论。“五四”以后,国文文白相间、时而夹杂欧化词语和句式、拉丁化字母的推行,使汉语文法不伦不类,严重妨碍了汉语的规范性。人们力图摆脱旧文法体系、建立新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刘半农《中国文法通论》谈及“文法是一种具体的科学”,他说文法必有其相关的科学:“文法的主要的关系科学,是文学,文字学(内包形体、音韵、训诂三项),国语学,方言学四种,而重要的外国文字的文法状况,和言语学上的主要条件,也是研究时常常要参酌到的。”[46]79
除“五四”前后编写的众多文法书外,文法革新者对汉语文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36年王力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涉及“比较语言学与中国文法”“西洋文法与中国文法”“死文法与活文法”“古文法与今文法”“中国的文法成分”等[49]参见: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M]// 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4-374。,吹响了文法革新的号角。以此为节点,汉语文法研究迈入了一个新时期。同年,陈望道等人掀起文法革新大讨论的浪潮,提出“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50]参见: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M]// 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65。,把文法研究推向前进。其中,傅东华《一个国文法体系的提议》、方光焘《体系与方法》、许杰《中国文法革新泛论》等深入地探讨了文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在陈氏的鼓动下,文法革新派纷纷著书立说,在建立具有汉语特色的文法新体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容《中国文法论》、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等。此外,还有一批以中小学生为受众的普及性文法代表作相继问世,如曹伯韩《中国文法初阶》、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张粒民《小学作文科教材和教法》等,在普及文法学教育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总体而言,19 世纪30 年代至40 年代,文法研究者们不仅在文法体系的建立方面颇有建树,在文法专题方面也做了不少扎实的工作,如“文法学的研究对象”“文法中词法与句法的关系”“如何划分词类和析句”等。
19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随着一批苏联汉学家的文法著作被译介至国内,中国文法研究者开始积极借鉴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理论,全面系统地阐释文法理论知识。此时文法学科侧重于对语言文字的探讨,进而发展出汉语语法学,黎锦熙的《汉语语法教材》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而“文法”关于文章写法的内涵,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乃是写作学,朱德熙的《作文指导》即是对文章的静态探讨。1960 年,陈望道等人联名发表《“语法”“文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以“文法”为正名,但是其内涵指的就是“语法”,与作文法无涉。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上海市语文学会组织了“文法学科定名问题”讨论,“语法”“文法”术语之争十分激烈,多数观点主张用“语法”定名,最具代表者如陈炳迢《语法学科定名渐趋统一的缘由和用词的社会性》,这使“语法”这一术语逐渐占得优势地位。1970 年代,学界展开文章学大讨论,语法学建设再次被提上日程,著述有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写作学著作也相继涌现,如李景隆的《作文法概要》、朱伯石的《现代写作学》等。时至今日,“文法学”研究进入多元阶段,“文法”的文章学内涵和语言学内涵界限十分明显:语言学上的“文法”即纯粹的“语法”;文章学里的“文法”,则分解在众多的写作教材中,如应试教育作文书、高等院校写作教科书、学术论文、应用文写作指导书等。因此,“语法”是“文法”概念近现代转型的主要指向,“写作学”是“文法”之文章作法含义的延续,它们皆归属于现在所谓的“语文”学科。
五、结 语
“文法”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文法”概念从古代传统的文章作法内涵演变至近现代的语法内涵,无不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社会危机、西学东渐、文体变革等相关。晚清古文大家的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古文的谢幕,但始终无法挽回古文文法退隐的局面。西学的冲击更是加速了近现代“文法”概念的转型,直至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成为“国语”,“文法”指向语法的内涵才趋于定型,并进而引导了汉语文法学科的确立。可以说,近现代的“文法”概念实则借鉴了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纯“语言”上的概念,这使“文法”回归到最原始的文学(广义)属性,即经学、训诂学下的语词文法含义。这样的回归不能说是历史的倒退,而是文学内外部因素交互的结果,是语词演变他律性和自律性合一的体现。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近现代转型下的“文法”消解了古今“文法”、中西“文法”在文章学、语言学层面上的区别,因此,追随中国古代至近现代“文法”的发生、发展和转型轨迹,对于把握“文法”之文章技法、语词文法的双重内涵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