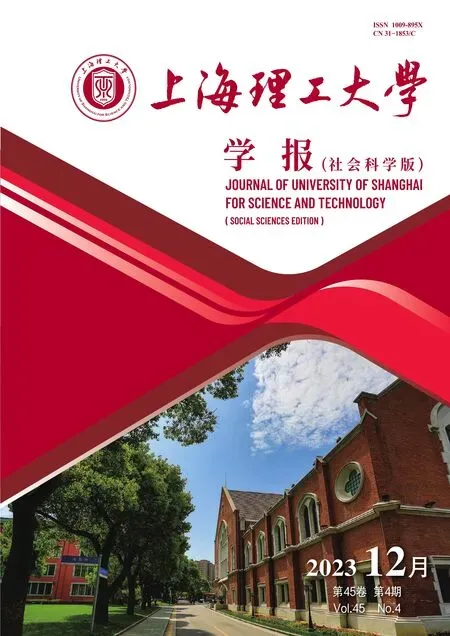伍尔夫的生命空间
——家宅内的“我” “他”与“我们”
张雯茜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在《班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与《现代小说》等文中,伍尔夫阐发了她的小说创作观,指出精神主义和物质主义两种主流小说存在的问题,寻找克服二者局限性的创作方式。她认为生命的本质蕴藏于心灵和精神深处,因此把握内在真实,才能表现真正的生命。“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在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杂质’的前提下表现‘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1]为了深刻把握人物灵魂,伍尔夫着力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在外部行动上过多着墨。对于何为真实的理解,如何挖掘人物内心真实的问题,伍尔夫诉诸追寻主观真实的路径,使人物的意识活动似白日梦般梦呓,在内心深处梦与想象亦是生命之真。
一、伍尔夫的内在真实观与巴什拉的诗意空间
伍尔夫的作品空间意象繁复,空间批评崛起给伍尔夫研究带来了经典再阐释的新视角。然而对伍尔夫的空间研究多集中于外部空间,涉及空间地理学、性别与阶级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对内部空间研究相对不足,且结合内部家庭空间研究的结论往往落脚社会与意识形态批评。如希亚将关注点放在被忽略的家庭内部空间“domestic interior”,指出伍尔夫的房间是构成记忆的空间,个体获得身份认同、一致性与安全感的核心所在[2]。辛克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房间与现代性空间》中围绕伍尔夫作品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房间,充分肯定了伍尔夫的房间在物理空间、文本空间与隐喻空间之间转换的多样性[3]。以上内部空间研究缺乏现象学分析的解读视角,与文本的“诗性”渐行渐远,正如高文婧指出空间批评实践的困境在于“出于空间批评重视社会、文化语境的倾向,使得文学本身的审美维度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4]。在当前批评界重审陷入重重话语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提倡回归“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 的背景之下,关注现象学以感性直接感知理解的内心空间无失为一种避开空间理论工具化倾向,返璞归真的阅读方式。
伍尔夫的两部代表作《达洛维夫人》与《到灯塔去》中除伦敦街道与海边为代表的外部空间外,主要集中于家宅的内部空间。家宅中,房子的构件,包括房间、门与窗,都是生命存在状态的隐喻,亦是生命的表达。巴什拉的诗意空间同样承载着居住者的灵魂,带有生命的温度,是人内心世界的延展。如此巴什拉与伍尔夫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巴什拉背离遵循传统哲学逻辑的研究方法,诉诸想象的现象学,以本质直观的方式体验原初的空间,意在“确定所拥有空间的人性价值”,“抵御”工具理性和实证思维下“敌对力量的空间”[5]27。依循巴什拉的思路,家宅应该超越描述层面以非对象化的方式把握,家居空间超越物质容器成为人类意识的居所,揭示了文学作品包含的主体间性。梅洛·庞蒂曾说:“空间是存在的,存在也是空间的”[6],因而空间与人的存在具有直接的联系。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不仅将注意力放在空间中人的存在,从微观、静态的视角审视主体间性,还把焦点投向具体的人生活的家宅,住宅与物件因投射了人对空间的感知与想象,成为生命存在状态的隐喻,借之我们可以挖掘存在的内在本真。本文拟借巴什拉的现象学空间视角出发审视通常易被忽视的生命空间,但并不限于巴什拉的理论框架。巴什拉的家宅诗学总体上是去他者化的,而缺乏伍尔夫作品中空间所蕴含的更具整体性的“我”-“他”的伦理意义。而这一点正是伍尔夫超越巴什拉之处,因此二者可以互为参照,伍尔夫的生命空间书写补充了巴什拉理论的不足。
二、家宅的生命空间
(一)“我”与“他”的房间
伍尔夫笔下的房间像有生命的身体而不是砖石结构建成的房屋,是包孕内心世界的容器。房间即是生命的载体和生命空间的表达,流露生命的情感与智性。塞克曾对伍尔夫笔下的房间展开精彩论述,与外部空间的“移动感,历史,去成为”状态相对,房间意味着“地点,存在或居所”[7]。与之相似,在巴什拉意义上作为人自我生成的原初宇宙,家宅乃是生命展开的生命空间,它“首先是‘健康’的白日梦,给人以安详、宁静、安全感、休憩与紧密感”[8]。巴什拉提出鸟巢和贝壳的诗学,把家宅喻作鸟巢和贝壳,其中藏有一个个让居住者休憩和自由想象的宇宙,家宅最宝贵的益处在于它“庇佑着梦想”“保护着梦想者”[5]5。因此在现象学意义上二者都将家宅视为生命存在的一部分,是生命的附着根基。不同之处在于巴什拉只关注积极的空间意向,忽略消极的空间,这构成他理论的某种缺陷[9];伍尔夫则二者兼顾。伍尔夫的生命空间并非巴什拉完全积极意义上承载美好梦想的诗意空间,她笔下的家宅凸显了生命之真。人物家宅中的梦想可能因无法与外界现实共存或自我封闭境遇的瞬间发现伴随痛苦的觉醒,进而发现生命的非本真性与个体的局限性,如此引出通往他者的必要性。另外巴什拉的空间根本上是去他者化的,“他者缺失”这一问题也遭批评者诟病[9];伍尔夫则关注到个体与他者和群体的通达,沟通了个体与群体心灵。
《达洛维夫人》的家宅构成了克拉丽莎的主要活动空间。房间是克拉丽莎的庇护所,在房间的沙发上就像一只鸟依偎在巢穴中安详休憩,让她在宁静的心绪中打开回忆的匣子细数往事。克拉丽莎的梦想是通过举办一场宴会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到灯塔去》聚焦家庭生活场景,物理空间更是集中在一所房屋以及周边的花园海滩,相较《达洛维夫人》少有空旷的外部空间,《达洛维夫人》个体在内外空间不断游移变动,而《到灯塔去》的人物在固定的物理和精神空间深入,在巴什拉意义上“内心的居所”向内生长。拉姆齐夫人倾心构筑了温馨丰盈的家庭巢穴,不论是客厅,厨房还是育儿室,她“使宅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充满勃勃生机”[10]206。她不仅给予丈夫同情和尊敬,让孩子们快乐地成长,还为家庭之外的莉莉,卡迈克尔和斯坦利等客人给予母性的温暖和安慰,将他们纳入幸福的天地。
巴什拉眼中的家宅“与人内心空间的内在与外在相系”[5]238,家宅空间直接呈现了居住者包括自我感知,反映人物的内在生命状态。房间首先是主体“我”生命的展现,作为自我感知和意识的承载容器,赋予居住者自主性。当她亲自打点房间内的物件时、整理餐具、安排仆人筹备晚宴和缝补衣裙的过程中,这些在房间内的活动让她之前的焦虑退却,心境逐渐平静。当克拉丽莎作为住宅的女主人她获得充分的掌控权,迷失的自我再次一点点重新聚合起来。
拉姆齐夫人的房间则更加安全和稳定,她在自己的房间安然独处,向内寻找生命之光,平静自然,不为生活琐事所占据,在这里她“怀着庄严缩回自我”[10]228,似乎成为了某种超越表象和有限性的原初存在,在无边的世界中直接面对生命的“楔形内核”,在敞开的个人生命空间一切聚合在“和平”“安息”与“永恒”中,充分享受精神的自由[10]229。
然而承载了自我感知的房间并非完全自主和自足的容器,也可能成为幽闭的囚笼,包含了人无法走出生命困境的无奈,而后者更接近《达洛维夫人》中人物的生命样态。克拉丽莎的存在危机在房间得以表达,让她看清自己的生存境况。房间能够使她充满自我的存在,而自我的房间同时遭受来自非我力量的挤压。从街道回到家的克拉丽莎发现桌上留言簿里写有丈夫理查德应邀参加布鲁顿夫人的宴会,自己却没有受到邀请时,她的自我安慰难掩内心经历的剧烈震动,客厅门外她“感到一种极度的不安”。当她走上楼进入更私密的生活空间,“好像她关上了门走到外面独自站着,形单影只地面对恐怖的黑夜”[10]27,退回阁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没有感到放松、自由,反而在一片空虚中产生束缚感,床单紧绷,“床会越来越窄”[10]28。此时的房间接近于她身体的化身,而不是外在于己的空间,在这里她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倍感生命萎缩的恐惧与焦虑。另一处克拉丽莎想象如果当年与彼得结婚的另一种可能性时,她仿佛被关入高塔的阁楼,独上塔顶”,“床单紧绷,床很窄”“门已关闭”,成为被弃绝的孤独存在,如同身处“杂乱的鸟窝间”[10]42。在房间里空间的紧缩带来的恐惧与压迫感一并袭来,内心经历着难以回到的过去与现在境况之间加剧的冲突。如乔安·斯普林格所言,过去的她更加开放、充满活力,与女友莉莉和恋人彼得年轻时在伯顿的回忆开放的空间相应的是她开放的个性。而现在作为一名家庭主妇,每天重复着一成不变的中产阶级生活,与当下生活和丈夫理查德相联系的多为封闭的束缚空间和庇护所。于是家宅闭锁的空间变为限制自由的鸟巢,其间的克拉丽莎无法迈出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生活的桎梏[11]。
对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塞普蒂莫斯而言,他的房间同样是自我生命的表达,与克拉丽莎一样他面对紧缩受压迫的空间,然而他的自我支离破碎,难以整合为完整的自我感知。伍尔夫通过这一边缘存在者形象展示了精神分裂者视角的生命景象:他的身体是房间的一部分,内在与外部视阈融合在一起,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视像淹没,常人的情感感受在塞普蒂莫斯内心都会加倍放大,并对他造成强烈冲击。家宅之于塞普蒂莫斯不是宁静的栖居,房间对他主体性构成的威胁超出了克拉丽莎来自社会规约与自我限制的束缚,也无法承载他的生命,可以随时被穿透。在房间里他处于瘫痪状态,往往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或沙发上,内心却感到失控的坠落与冲击。在他自杀前生命的最后时刻危机感达到临界点,本应是梦想的庇护所的房间俨然是孤立静止的空间,塞普蒂莫斯孤独无助,惊恐万分,房间内的物件也处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幻象与现实驳杂难分。在他曾经看到“山脉”“人的面孔”“美”的地方过去有序而富有生气的世界被空洞的物体——煤桶和餐具柜环绕,如同虚无的黑洞,横亘一面象征阻隔的屏风,意味着他无法融入生活。房间宣判他将“永远孤独”[10]130,他的生命也在一点点被吞噬。最终随着霍尔莫斯大夫冲上楼梯闯入充斥原本已因紧张、威胁、阻隔而绷紧的生命空间里,不堪重负的塞普蒂莫斯被逼至房间尽头的窗户一跃而下,标志着他生命空间的终结。塞普蒂莫斯的悲剧直接表现了无法与他者通约的自我在隔绝、紧张的生命空间面临的危机。
房间不只是自我内在生命展开的容器,也是借之反思和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介质,在这里个体找到自我与他者的共在联系,在“我”与“他”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拉姆齐夫人不仅在自己的房间完成个人生命的超越,还通达与他者的普遍联系。一方面,她与万物圆融地联系在一起,凝视物体时她“变成了她在凝视着的东西”[10]228。她感到“树木、溪流、鲜花“表达了你,感到它们成了你,感到它们懂得你,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你”[10]229。另一方面,在他人的房间她建立起孤立个体之间联系的纽带,拉姆齐夫人曾通过房间想象,似乎连墙壁也变得越来越薄,“一切都在同一条溪流之中,椅子、桌子、地图,是她的,是他们的,是谁的都没关系”[10]273。房间同他人的共通感相联系,化为一股溪流,裹挟了房间的一切,汇入她子女的存在并在她死后延续下去,汇合为一。伍尔夫进一步通过墙壁变薄甚至消失的隐喻表现人与人距离的拉近与隔阂的消失,“仿佛分隔他们的墙已经变得如此之薄”[10]273。后一章中拉姆齐夫妇彼此相隔的物理与心理距离越来越近,直至二人并肩紧挨,墙壁也因“他们之间的亲密而变得朦胧”[10]281。拉姆齐夫人借助家宅中墙壁为代表的建筑空间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了她“对共同体、延续性与包含性的愿望”[12]。
而另一种突破一时一地主体性的神秘联系更具有超越性。像房间内拉姆齐夫人感到与万物相融,互为表达的瞬间一样,达洛维夫人“变成了一种超越所有时间和物理边界的意识,通过她的想象融合在一起”[13]。在房间沙发上她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神秘的共在,窗前也多次心生与对面房间的老妇人和素未谋面的塞普蒂莫斯之间莫名的相似性共鸣,与他们的神秘联系都超越了房间之内物理空间的区隔。
“我”与“他”的联系还表现为房间内对共同物件的分享,当物品“承担起各种感觉和感情”,共享构筑了人与人同在的诗意栖居的共通空间[14]。拉姆齐夫人客厅里举行的第一次晚宴上每个人都躲在各自紧锁的心门背后,缺乏真诚的深入交流,标志着初次集体沟通失败。第二次的晚宴众人进入了一个多重维度的时空——桌上宾客共享的法式炖牛肉和一盘水果似乎成为一个如同博尔赫斯的阿莱夫般的微缩宇宙,肩负联通的使命,“把他们安全地结合在一起”。拉姆齐夫人感到“这儿就是事物核心处的静谧空间”[10]265。那一刻众人仿佛置身于神秘小岛的洞穴,共同对抗外面流动的世界。他们穿越亘古时间与希腊众神一道纵情享受令人迷狂的酒宴,在座的人们终于一同站在同样的视点观看,每个人呈现通透敞开的内心,“一切结合成一个整体”[10]267。晚宴上除共同的观看之外还有共同的聆听,拉姆齐先生朗读诗句的声音不只属于他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所有在场者,“好像没有人说词句就自己出现了似的”[10]270,不仅说出了拉姆齐夫人内心的话,也是他们所有人自己的声音。这段晚宴描写提供了“表现自我与他者的真实交融可能性的例证,这种交融也暗示了更大规模互相联系的共同体意识”[15]。
当房间空无一物或被居住者抛弃时,家宅就成了干瘪的生命空间,里面是放逐的灵魂,无处安放。理查德和彼得都是无家者的代表。理查德眼中的房间“看上去空落落的”[10]106,“根本不知道房间应该布置成什么样子”[10]107,他回到家与妻子简短寒暄后便匆匆离开家去工作,对家宅之外街道途径场所的关注远大于自己的家,家宅并非他幸福的栖所。而彼得同样否定了家,他从印度回到伦敦,在这里并没有家,他自诩“孤独的旅人”[10]52,视自己为在街道游荡的“冒险者”和“浪漫的海盗”[10]48,不愿他人限制自己的自由。在本雅明意义上开放的都市空间,人可以以闲逛的方式想象新的自我,实现个体的身份突破。彼得蔑视体面得体的秩序礼节,突破了其他人物难以逾越的阶级身份限定,诚然伦敦街道的漫步对于彼得来说是解放性的自由旅行,但是他的自由以无家为代价,没有家宅意味着他没有安放生命的空间。他拒斥家宅内的空间,在梦境中抗议“不要回到客厅之中,再也不要读完我那本书”[10]51。彼得的伦敦漫步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一个无家灵魂的放逐。无怪他从梦中醒来惊呼“灵魂死了”[10]52。在暂居的旅馆,房间的家具整洁却处处透出冷漠,眼前无家感的陌生化房间促使彼得重新反思克拉丽莎对于自己的意义。最后他方才意识到“她比他认识的任何人对他的影响都要大”,不仅是过去的恋人,更重要的是他生命中了解他,与他灵魂相系的知己[10]137。他决定去参加她举办的晚宴,用行动对这段迷惘的关系做出回应。
而克拉丽莎在家宅之外的的伦敦漫游漫无目的,接近放空自己的漂流,没有目标,不知所向。拉松指出,相较彼得她不是漫游,而是在焦虑不安中迂回绕行[16],街道上她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穿过门只是从一种不确定性迈向另一种不确定性。克拉丽莎不确定的矛盾状态在一开始就通过一段在街道的内心独白告诉了我们,“她现在常常感到她这个躯体似乎变得不存在了”,“自己是个隐身人,无人能见,无人能知”;“有的只是和街上的人群一起”[10]10。她想改变自己的境遇,却难以突破。家宅之外的克拉丽莎如同抛弃了真正安定的生存空间,没有安放自我的坚实根基,被非存在感包围 。相似之处在于二人都希望在家宅之外找到生命的依附点,最终发现他们依然离不开家,家才是让他们灵魂休憩的港湾与本真自我表达的场所。区别在于彼得试图忘却、抛弃的家正是他生命缺失的一环,对家的拒斥保全了他自由的天性,但代价是让他失去了安全感。克拉丽莎发现自己离不开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庇护,在家之外鲜有自我实现的方式。
《达洛维夫人》中的人物在家宅之外的空间游移不定,没有居所,在家宅之内因受挤压而无处可遁。家宅之内克拉丽莎属于自我的生命本真时刻为数不多,在那里她同样受到外部社会规约的无形压力,戴上面具按照中产阶级得体的方式生活。她始终受制于他人对她的期望,总是希望给其他人留下好印象,如她自己所说“一半的时候她做事不只是为了去做这些事,而是为了让别人这样或那样想”[10]10。归根结底她无法放弃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社交和物质保障,也深感这种重复空虚的生活带来婚姻爱情与生命意义无着落的困扰,结尾的宴会场景克拉丽莎在名流权贵面前的轻松自然姿态与她内心非本真状态之间的悖论将她的自我欺骗展露无遗,也是克拉丽莎自我异化与伦敦上层社会疏离状态的缩影。
在《到灯塔去》“时间流逝”一章,拉姆齐一家的家宅十年无人居住可视作伍尔夫对无家的极致表达,摹画了人无家之后无处庇荫的破碎现实。“房子空了,门锁上了”[10]286,蜷缩在家宅贝壳与鸟巢的诗与梦不再,屋子“像被遗弃在沙丘上的一个贝壳,当生命离开了以后,只能听任干盐粒灌入其中”[10]294。空荡荡的房屋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不在家的人们仿佛失却了家宅的庇护,被外界力量侵蚀。无边的暗夜笼罩下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和战争的动荡之下令人猝不及防的死亡接踵而至,拉姆齐夫人、安德鲁和明塔相继去世,曾经的温馨家庭图景亦不复存在。
(二)跨越之门
门是任何住宅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两部作品中均有大量与之相关的细节,门就其物理意义上的功能来说:“是通向场合的场所”[17]103,往往构成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通道和枢纽。巴什拉呈现了门的丰富意蕴:“犹豫,试探,欲望,安全感,随便进入,尊重”[5]288,门包孕的具体情感和情境可能浓缩了人一生的经历。
巴什拉提出有关门的核心问题是门的朝向,“门向哪里,对着谁打开?”[5]290门通向的空间就被分为两种,一种退回个体孤独的内心世界,潜入自我的深处的内在生命,另一种向与他者共在的世界敞开。
就门的基本存在形态而言有两种,打开的门和关上的门。关闭的门会成为拒绝联系或沟通失效的障碍。理查德离开克拉丽莎的房间关上门时,门代表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沟通鸿沟,克拉丽莎无法与丈夫分享交流举办晚宴的想法,而理查德直到离开房间之前也没能说出他对妻子爱的表达,于是关闭的房门可以视作他们婚姻关系的注脚。《到灯塔去》的贾斯珀不小心撞到了父亲,冒犯了易怒的拉姆齐先生,后者“砰地一声”“关上了属于他个人的那扇门”以示不满和愤怒[10]196。
打开的门则使敞开与接纳成为可能。门既能区隔空间,又能建立空间之间的联系,具有 “在联系中隔断”和 “在隔断中联系”的双重属性[18]。巴什拉说门是一个半开放的宇宙,门可能是虚掩着的,每一扇掩上的门都有企图“打开存在心底的企图,征服所有矜持存在的欲望”[5]288,门后涌动着打破封闭状态的潜流。门本身 “意味着分隔与联系不过是同一种行为的两个方面”[18]。因此预示着连通的机缘,包孕着打通墙壁所分隔空间的可能性。在《达洛维夫人》中尽管门与窗意味着界限与区隔,集体的压迫性以及个体之间的沟通失效依然存在,但是基于上文房间克拉丽莎为代表的人物与他者共通联系的可能,“起封锁、保护和标识作用的物理墙壁必将消融”[12],这一壁垒的突破到《到灯塔去》才真正完成,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实现开放式沟通与敞开的理解。
拉姆齐夫人坚持打破壁垒,推开一扇扇门进入一个个房间,连通各个物理屏障分隔的空间,把所到之处孤立的客人与家庭成员联结在一起。她打开门进入孩子们的房间为他们讲故事,进入丈夫的房间给予他同情理解,带着她的美和无私的帮助“如同一个火炬,她举着它进入每一个房间”,使人们获得安慰[10]210。门潜在的阻隔因此被缩减至最小,拉姆齐夫人能感到“与别人之间的感情上的一致”[10]273,并把共同的芬芳带给身处异质空间的人们。
与门相关的门坎则强调跨越的动作和转变的即时性。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中“门坎”“是危机和生活转折的时空体。”门坎一词的隐喻意义包括“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是危机、堕落、复活、更新、彻悟、左右人整个一生的决定等事件发生的场所”[19]。越过门坎象征生命重大时刻发生的改变。米勒指出跨越门坎是《达洛维夫人》中重要的核心比喻,向我们呈现了“直接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20]。开篇随着克拉丽莎打开门的一瞬间,标志着她同时向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敞开。她拥抱六月清晨的伦敦,从大本钟的钟声到街道来往穿梭的车辆行人,从盛开的鲜花到上下翻飞的白嘴鸥,从商店橱窗琳琅满目的商品、色彩、声音与气味,无一不与她联系在一起;随缤纷世界涌现的一连串过去岁月的记忆交错其间,在尘封的记忆中她找回与彼得和莉莉的联系。
门坎台阶前拉姆齐夫人的身影予以莉莉生活与艺术的意义的启示。莉莉在最后仿佛看到虽然可能不会有伟大的启示,但是拉姆齐夫人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守护着家宅之内的幸福空间的画面代表着“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奇迹、启发”,“拉姆齐夫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10]314,她凝固了生命,使混乱的事物具备形状。将日常的瞬间化为永恒。如此莉莉找到了她的“启示”与“形式”,即用抽象的表达汇聚凝固拉姆齐夫人的遗产并将其化为永恒的艺术。莉莉也终于不再陷于孤独的思念,感到与他人共情的需要,“似乎有一样东西必须和别人分享”,对拉姆齐先生的敌对态度转化为“需要他”的渴望[10]349,在海面上寻找拉姆齐先生的身影。门坎的跨越性于莉莉意味着她最终重拾自信,找到她所寻求的艺术表达——兼具柔软明丽丰盈的表面与坚实的内核。随跨越而明朗的的还有她困顿的内心,莉莉明确可以保留对拉姆齐夫人的向往,接过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使命,同时保有自我艺术家与独立女性的身份,让自己是其所是。
随着晚宴成功将众人真正聚集在一起,并促成一对年轻人迈入婚姻殿堂,拉姆齐夫人跨越标志着生命的更新的门坎,因为她还要继续“把所有的事情都向前推进一步”[10]271,继续把人们引向人与人“相即”的时空。对比之下克拉丽莎跨过门坎的转变并不彻底,一天游荡之后依然回到了门坎后的房间,迷失在无法与之释怀的回忆与社会规约的双重束缚中。
(三)相系之窗
魏斯顿说窗是“‘建筑的眼睛’,为我们框架出更宽广的世界。窗或许比其他建筑元素更能为建筑物赋予个性。”[16]68一方面,窗户依然是自我表达的心灵之眼,映照出人的心境。另一方面,与门相似,通透的建筑之眼窗户构建了可望的联系通路。如果门因其打开后他人侵入的可能性会对门后人的个体空间造成一定的威胁,窗则以一定的距离感让人以更放松的姿态相系,在不侵犯主体空间的前提下敞开生命的空间。随着窗户打开的空间目光越过此端看到彼端的风景,窗户让人物超越固定有限的自我,打开超越所处空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反复强调“关上门,打开窗”[10]186,确保视线的通达与分隔空间之间的联系。小说充满与窗有关的场景,窗是人物从此处望向彼处的视点,看与被看的所在。莉莉隔窗望着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隔窗凝视海与灯塔,拉姆齐先生望向拉姆齐夫人和儿子,望而不得的焦虑最终得以抚慰。
拉姆齐夫人从窗户远端的灯塔,给予拉姆齐夫人生命的自我表达,灯塔的光束就是她的光,在与灯塔的体认中,她体验着生命的狂喜、满足,个体生命空间向纵深处延展[10]228。晚宴时分随光波流动的窗户与拉姆齐夫人“带有永恒色彩的欢乐”相呼应[10]256,将外部变动的世界隔绝在外,窗内是拉姆齐夫人构筑的达成沟通与联结的自足世界,窗户见证了拉姆齐夫人守护的永恒时刻。当拉姆齐夫人完成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使命,向窗外望去,因她带来的稳定、庄严、一致与秩序,连窗外普通的榆树也变得“威严”起来,成为一道“壮丽”的风景[10]273,连同窗外的金色的满月,或许暗示对给予生活滋养的拉姆齐夫人来说,至此她的生命已经圆满,她可以面带微笑地看着自己倾心维系的共同体即使在她死后也能继续包容支持每个人。同时窗户也让她在个体空间自我感知的同时,保持与外部相系的敞开,与万物相系。
来自窗户之外的联系让克拉丽莎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克拉丽莎经常在透过窗观察周围的世界,包括街道的商店橱窗和房间卧室的窗户,尽管故事中克拉丽莎与塞普蒂莫斯二人从未真正相遇,但是两个灵魂的相知相遇通过结尾一处细节暗示——塞普蒂莫斯自杀的消息到来之前,克拉丽莎房间窗前的窗帘随风微扬,“仿佛有许多翅膀飞进了房间”[10]150,似乎塞普蒂莫斯的灵魂在此短暂停留,克拉丽莎产生与这个陌生死者经历与感受的强烈认同。
框定世界的窗户呈现的一幅幅风景画对不同人物意义殊异。画家莉莉在窗前远望予以她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以及整合的归属感。她看到窗前姆齐一家在窗口,映衬着飘动的白云和摇曳的树枝,感到生活不再是分散的碎片,而是“变成卷在一起的整体”[10]215。而当莉莉望着坐在客厅窗口的扶手椅里的拉姆齐夫人时,画面不仅带给她母亲般的安慰,还帮助莉莉克服了缺乏与他人情感联系的焦虑,也构成了她追寻艺术形式的灵感源泉。在莉莉将丰满细节构筑、充满活力的生活图景转化为抽象的艺术表达的过程中,窗成为她化生活经验创生为永恒的艺术图景的桥梁。对拉姆齐先生而言,窗维系与真实生活和他人之间联系的画面,平衡抽象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
因此人物通过窗户的相遇与相系体现了伯曼提出的“全新的伦理遭遇”,她认为伍尔夫“以美学构建了一种潜在于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伦理向度”[21]。透过窗人物超离自身所处的有限境遇,发现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进而说明自我与他者以及与一个更开阔的整体相通的必要性。
然而窗的开放性又是相对有限的,不像门可以赋予即时的行动从中直接穿越,人只能在窗前远望而不能迈出窗框定的世界,意味着视线的阻隔和通约的限制。《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透过窗户看到总是在房间内来回踱步而未走出房间的老妇人,几乎是克拉丽莎的镜像式存在。文中一句对老妇人此举的嘲讽“她看得见自己吗?”或实为对克拉丽莎看不清自我生存境况的讽喻[10]166。同样在窗前冥冥之中克拉丽莎“看到”了塞普蒂莫斯,他死亡的讯息是对她的惩罚。当一个年轻的生命陨落,被黑暗吞噬,她却虚伪地举办着一场意在把客人们联系起来而实际上人与人貌合神离的晚宴,肯定他死亡的意义却选择继续回到过去自己被框定的生活,这是何等讽刺。而窗外的景致是惨白、压抑地令人窒息的天空,也呼应她困于当前生活的境遇以及与他者不可通约的黯淡。
塞普蒂莫斯自杀时从窗子一跃而下,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人在窗前止于被动观看而无法行动的限定,然而他绝望而决绝的存在主义式反抗浸漫着无尽悲凉,结尾处他死后微微拂动的窗帘暗示他的灵魂被克拉丽莎在窗前象征性接纳。这种以隐晦方式实现的不可能之可能亦令人唏嘘。
综上,窗户为房间内的人提供向外敞开的通路,让人窥见超越孤立主体局限性的可能,同时赋予生命向内反思与观照的入口,然而内外的通达与遮蔽的局限并存。《达洛维夫人》中从窗户投出的视线是望向内部的,揭示自我生命空间向内萎缩与无法通约的困境。而《到灯塔去》的窗户呈现内与外,此与彼的和谐,孤立的自我实现与他者和集体联通的圆融整一。
三、结语
《达洛维夫人》紧张、压抑的时间步步紧逼,在大本钟荡开的离散时间中,与之相应的空间中人物往往表现为迷惘与疏离,在公共空间游移不定,不知所向,在私人空间感到逼仄阴郁,无处可遁;《到灯塔去》则表现为延展、敞开的时间,起到整合,凝固的作用,暗合众人在同一空间实现的和谐与永恒。但是最终两部作品的空间都凸显了敞开一个望向彼端、与他人共在空间的重要性,
聚焦住宅和其间的核心空间意象门与窗,透视伍尔夫笔下人物的生命空间,与巴什拉的诗意空间相呼应,家宅首先是揭示人生命存在的容身之所,然而两部作品的生命空间不尽相同。《达洛维夫人》主要呈现了无家与非本真的个体,家宅失落的梦想与生命空间凋敝的诗学。而《到灯塔去》的家宅空间则更加通透,自我感知的个人房间与他人共在的开放空间可以共存,拉姆齐夫人的母性光辉维系孤立的个体,弥合分歧,指向超越区隔的壁垒,走向与他者共在共通的集体存在身份的“我们”。
伍尔夫通过住宅空间的生命书写探索生命的本真,寄寓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全新想象:从自我感知出发,到理解他者再到人与人共情与共通的联系,表达了她消解主体之间的固化边界,追求相通相系共同体的理想。同时她的生命空间因对消极意象与他者的关注,亦超越了乌托邦化的理想空间。
——《日用家当》中“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