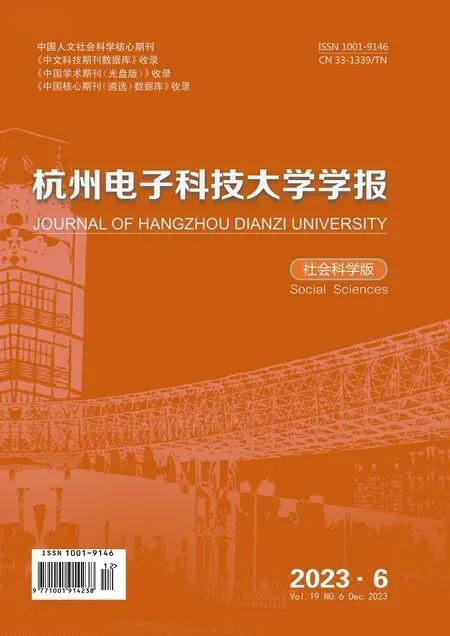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
——身体-国家话语的两条路径
王晓雄,杨妤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近些年来,“身体”已逐渐成为人文学科文化、文学批评的关键词[1]1。这一研究视域下的“身体”并非生理性的肉体,而是梅洛-庞蒂所说的“有生命的身体”;这一“身体”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包含着不确定性[2]。身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导致其成为话语汇聚的焦点,它既以自身构想和塑造政治、经济等文化因素,同时自身又被这些文化因素所构想和塑造。其中,身体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塑造颇受学者们关注。因为当身体被置于复杂的历史场域中时,个人的身体就不再是“一己之身”,而是构成“国体”的基本单位[1]6。个体通过自我身体的存在,感知政治/国家的形态,进而在政治/国家的意志或权力话语中发现或协调对自我身体的塑造。因此,针对展现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身体-国家话语的研究,就包含两条路径:其一,隐喻式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话语,即以个人的身体构想国家,将国家想象成一个有机的身体;其二,权力式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话语,即以国家的身体构想个体,用国家、社会的逻辑系统来约束、塑造个人的身体[3]。这两条研究路径广泛存在于国内的文化、文学研究中,但部分研究者对两个术语——“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的运用较为混乱,缺乏一定的辨析。并且,两条路径的研究都在探寻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内里存在着连续的逻辑链条,可形成相互映射的闭环。因此,本文将综述西方的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话语史,在辨析两者概念的同时,探究两者在身体-国家话语范畴中的逻辑关系,试图为国内的身体-国家话语研究提供一份文献基础。
一、西方的政治身体话语
政治身体(body politic),也译为“政治机体”或“政体”。它是“针对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机体论术语”[4],也就是将国家、社会隐喻式地看作一个有生命的身体,并依此展开对国家、社会的理解和剖析。穆索尔夫(Andreas Musolff)指出,西方文化中的这种身体-国家隐喻大致有三个源头,分别是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伊索寓言》和圣经传统[5]。第一个源头可以柏拉图为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言道,一个管理得好的城邦或国家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这个人的手指受伤了,那么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就是整个身体都会感到痛苦[6]197。因此,城邦中的居民好比身体的各个部位,是“苦乐同感,息息相关”[6]200的,他们理应彼此协助,共同为城邦的安定、发展做出贡献。在论及城邦的问题时,柏拉图同样延续了身体的隐喻。出问题的城邦好比不健康的身体,遇到外邪就生病,有时甚至没有外邪也会自己生出病来,就好像各党引进盟友,挑起内战,有时没有外人插手城邦也会发生党争;不良的政客及其党羽出现在城邦里,就像人体里的粘液和胆液造成混乱一样;因而城邦需要一个好的统治者来充当其医生[6]193,331,342。该种视城邦为身体的类比,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流传较广。第二个源头则多指《伊索寓言》中的“肚子寓言”:身体的其他器官认为肚子只知道吃喝,什么活都不干,于是决定罢工;结果过了一两天,器官们发现自己没有了力气,才知道往常一声不吭的肚子也在承担着重要的工作;大伙儿应当齐心协力,否则身体就会垮掉[7]。这一寓言被李维、普鲁塔克等人广泛重述,并在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该剧中,元老米尼涅斯将罗马的元老们比作肚子,而作乱的民众则是反抗肚子的器官,民众对元老们的反抗将招致整个政治身体的紊乱和衰亡。在第三个源头——圣经传统中,《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都曾提到,教会就是一具身体,耶稣便是教会的“头”。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指出各个肢体只有互相照应才能组成一具完整的身体,正如教会中的人员只有各司其职并通力合作才能获得上天的恩赐。可以说,上述三个源头建立了人体和城邦、教会的类比,构成了政治身体话语的基础。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政治身体话语在诞生之初就有着“明显的等级性”[8],它在要求合作、协调的同时也强调部分人(其他器官)对另一部分人(肚子、头)的服从;这一服从也可转化为部分群体的利益需求对城邦或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服从。第二,柏拉图的“粘液”“胆液”等提法以当时的气质体液说为基础,将政治身体话语与医学、生理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此后,政治身体话语传统不断地与医学、生理学相呼应,借由人类对自我身体认识的进步来更新对国家政治的洞察。上述两点也正对应政治身体话语的两极:前者为政治,关乎人们的政治理念;后者为身体,关乎人们的医学理念。考察西方政治身体话语的发展,也正是在考察西方政治话语和医学话语的互动关系。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身体话语就鲜明地体现出上述特点。12世纪的英格兰教士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如此描述他设想的政治身体:首脑之位,由一位服从上帝的君主担任;国家的心脏由元老院占据,耳、眼、口的职能由法官和行省总督担任,手相当于官员和士兵……躯体的各个部分要联合起来,为同一个目标而工作[9]。约翰继承了政治身体传统对协调合作的强调,同时凸显了头(君主)的重要地位,并且君主还要受灵魂(神职人员)的控制,体现出王权背后隐伏的神权。在12世纪,无论从隐喻还是字面意义上来说,“头”的地位都没有受到很大的质疑;但是到13世纪末,“人的身体最重要的器官是头还是心脏”的问题开始引发争论;与柏拉图强调头部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是最重要的器官[10]。14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理观点,认为身体中心脏首先形成,且心脏比其他部位更高贵和完美,随后,其他部位再渐渐形成。马西略将城市或国家的建立和动物的身体类比:市民的联合好比灵魂,在这灵魂里诞生了最完美的心脏,即元首制,心脏带有的热力和能量即是执政权力和法律,执政者及各级官员必须在法律的约束下履行职责[11]。马西略将元首、官员作为政体的中心,以使各个阶层各司其职来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同时不同于约翰,马西略将政治和宗教分离,主张教会应关注信仰之事,无须插手世俗政治。15世纪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则将教会重新纳入政治身体。尼古拉的构想以古罗马时期医师盖伦的医学理论为基础。盖伦认为人体包含三个主要的“运作”系统:其一,大脑和神经系统,负责感官和思维;其二,心脏和动脉系统,负责提供维持生命的能量;其三,肝脏和静脉系统,负责营养和生产[12]。学者指出,尼古拉在教会和帝国的两极关系中加入了以教会会议为代表的教会联合体,形成了三角结构;其中帝国是神经系统(帝王是大脑,帝国法是神经),同理,教会是动脉系统(圣灵和自然法是心脏,神圣法是生命之气),教会联合体是静脉系统(教会会议是肝脏,教会法是静脉);教会作为动脉系统,构成了教会联合体和帝国的基础,上帝的灵性为国家输送了赖以生存的能量;在教会的供给下,教会联合体才能发挥静脉作用,维持、恢复国家的元气,此后,帝国才能发挥感觉和行动的能力,使政令推行,机构运转[10]。从政治理念来说,约翰强调了王权背后隐伏的神权,马西略排除了神职人员对政治的影响,尼古拉则重新将基督教视作整个政治身体运作的生命源头;从生理学角度来说,约翰袭用了柏拉图的头部说,马西略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心脏说,尼古拉则以盖伦的生理学为基础。有学者总结道,以上三种政治身体话语都建基于各自时代流行的医学知识,并掺入自己的政治理解,这表明政治身体话语受政治和生理两种语境的影响和塑造[10]。
中世纪及之前的政治身体话语倾向于以身体来构想整个政治世界,其政治身体想象较为全面、整一。穆索尔夫认为,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此种政治身体的概念渐渐不再成为政治世界观的基础,但是,在政治、文学话语中运用身体、生命等“源概念”对社会进行“概念化描述”的风潮仍然十分活跃,并一直延续至今[13]。换句话说,尽管在启蒙之后,人们对整个政治体的认知渐渐从有机体论转为机械论或抽象化的认识,但在局部或单一的话题上,与身体相关的隐喻仍然持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体液隐喻和疾病隐喻,以下将作分别概述。
哈维在17世纪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心脏是一块中空的肌肉,通过收缩和舒张使血液在血管中运动,为身体提供养料[14]。于是,血液循环的概念被用于描述国家的交易、货币和信贷。作者们将大都市看作国家的心脏,认为货币流通、信贷对经济来说极为必要,可促成国家的财富分配,并带来源源不断的增长[15]。除却经济相关的话语,启蒙时代以后,可溯源至柏拉图的疾病相关的政治身体话语也被运用得越来越多,甚至已进入语言的隐喻结构,成为当代政治身体话语的主流。
苏珊·桑塔格详细讨论了作为政治身体话语一部分的疾病话语。她指出流行病常常被用来描绘社会混乱,比如波德莱尔视共和精神为国家的梅毒,雨果将隐修的生活方式看作社会的结核病,在二十世纪的话语中贫穷被认为是国家的癌症;人们已习惯用疾病来谴责社会中的某种习俗或现状,并以此呼吁一种新的政治秩序[16]。疾病天然地引起人们的厌恶与恐惧,当政治话语与疾病联姻时,话语的运用者便能将公众的厌恶和恐惧导向其谴责对象,并达成其政治目的。比如欧洲、美国针对外来移民主题的政治用语就颇能体现上述特质。帕普罗茨基(Maciej Paprocki)指出,人体的疾病起源于身体外部的医学认识影响了近代欧洲的政治话语,他们将外来的移民、未规范化的少数族裔看作侵入政治身体、引发社会混乱的传染病微粒[17]。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政客则借用消化不良的隐喻强化自己的反移民主张。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到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案》签署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客将美国比作一个进食的政治身体,移民造成了它的消化不良[18]。传染病微粒隐喻和消化隐喻都借用日常的身体类比促使民众进入传统修辞式的国家想象,成功地推进反移民和本土主义的政治主张。毕竟,身体是个体面向世界的首要依托,以身体展开修辞对人们来说是最亲切也是收效最为显著的。政治身体话语传统能够源远流长并影响人们的政治、文化思维,也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上的。近现代政客虽不再以身体整全地阐释政治体,但仍然沿袭部分身体话语,唤起民众对疾病、亚健康的本能厌恶,修辞式地加固其政治立场。
疾病话语提醒民众以一具庞大的身体去想象国家政治,具象地理解国家及相应的政策,但同时,该话语也促使民众反观自身,以相应的标准和同样的逻辑衡量自身。比如在消化隐喻的传播中,民众形象地认识到国家因移民的增多而出现社会结构的失调,因此在国家层面应限制移民流入。但该话语不仅转变了人们对移民的看法,同时也转变了人们对消化和身体的看法:既然移民是难以消化,具有威胁性的,那么其外来的食物也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对消化系统有害的,理应拒绝[18]。因此,疾病话语从国家落实到个体时,它可能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为规范,比如消化隐喻最终导致人们通过饮食选择来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其基本的思维逻辑在于,当人们把政治体构想为一个有机身体时,该身体的各个部位必然要相互协调才能保证整个机体的和谐;但同时个体也是政治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以政治身体的视角来衡量自身,以达到作为政治身体中的一员的要求。这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身体政治的范畴,亦即人作为政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政体的标准、逻辑来规限自身的行为,这将是本文下一节的主题。
二、西方的身体政治话语
基兰·莱尔德(Kieran Laird)在论述“政治身体”时,认为政治中的身体概念经历了一次转变——从把身体看作“国家政治实体的隐喻”转变为将身体视为“行为本身的重要政治场所”[19]。虽然莱尔德没有使用“身体政治”一词,但其描述的正是从政治身体话语到身体政治话语的转变。那么何谓“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呢?有学者在解释该词时这样描述道:身体是不同的社会结构映射到人类的场所;将身体置于系统的制度之下是确保身体按照社会和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行事的一种手段[20]。身体政治可以笼统地理解为从国家、政治的隐喻身体角度观照个人的身体,将国家的运作体系和制度具体化至个体,进而教化、规训个体的方方面面。因此,身体政治的探讨必然涉及(政治、社会的)权力问题。权力对个体的影响甚至辐射到“我们的坐姿、微笑、占据空间、凝视、歪头”等生活细节,而这些按南希·亨里(Nancy Henley)所说都是身体政治的范畴[21]。
要讨论身体政治,必然离不开福柯的相关论述。但在讨论福柯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的观点。埃利亚斯认为,西方的文明化有三个阶段:中世纪城堡的“礼貌”,绝对主义宫廷的“教养”,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文明化的阶段都与礼仪即自我控制身体的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家正是借助人们对身体的控制而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会控制机制,因此,文明化进程也可谓对身体加以理性化控制的过程[22]。毛斯提出的“身体技术”概念则与埃利亚斯的论述有些近似。该种传统的身体技术行为是为了某种“社会权威”,并被权威置入个体之中,它表明“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受到控制的”[23]。换言之,人的身体在规则框架下模仿、训练各种行为,并最终将身体技术内化于自身。
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的一系列探索,深化了身体政治的意义。他指出,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型基督教寄宿学校、大型工厂等,在这些场所发展出了一整套驯服人类的技巧[24]30。这是在18世纪新出现的权力的变化。在此之前,权力无法对社会机体进行个人化的详尽分析,但到了18世纪,经济变化要求权力在更具有连续性的微观渠道也能流通,能够直接贯彻到个人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24]154。于是,身体成为“可利用”和“可驯服”的,并直接被卷入了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干预身体,给身体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发出某些信号[25]27。随后,福柯将政治身体与身体政治两种话语联结了起来。他指出,我们关注的“政治身体”相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其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知识和权力关系服务,而这种知识和权力关系则把个人的身体变为认识对象,进而干预、征服个人身体[25]30。因此在福柯看来,身体政治即政治身体的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他似乎更强调身体在权力或政治身体中所处的被动地位和消极状态。
埃利亚斯、毛斯和福柯的论述构建了身体政治话语的整体性视野,并厘清了其中蕴含的基本思维逻辑。当我们顺着该逻辑将身体政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时,涉及的话题就会变得极为纷繁,因此择取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身体政治话语——饮食话语和性(别)话语来作个体化的分析。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指出,从禁欲角度来看,食色都是粗俗的,并且放纵的食欲也会促进性欲,因此西方文明的理性话语对饮食和性欲采取相似的限制措施;社会的稳定在于精神理性利用家庭、教会等机构使欲望处于从属地位,于是新教成功地将修道院克制的行为准则移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26]。特纳强调了社会权力在食色方面自上而下的规训力量,但很多时候,身体政治的作用方式并非完全单向或者僵化的,个体可通过自身的努力与规约进行对话、协商甚至反抗,寻求一种可接受的身体状态。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就暗含了对身体政治进行反抗性对话的可能。她从扮装表演入手,认为这隐晦地透露了社会性别本身的模仿性结构及其历史偶然性。由此出发,巴特勒认为性别是重复表演的效果,是对身体进行不断的“风格化”,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为”,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固化”,才成为了“暂时”的性别[27]46,184。而这种操演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主体或本体论的身份,有的只是各种不同的行动和外现;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操演都是对性别规范或规范性指令的重新演绎[27]178,183,193。虽然巴特勒不承认主体的存在,并认为每一次的性别操演都是对规范的重复,但是每一次的重复都会带来对规范的偏移。因为重复过程中同样会出现缺口和裂缝,成为建构的不稳定成分,这些成分会逃脱规范,对稳定化了的性别进行消解[28]。正是在操演的这些狭小缝隙里,个体能够凭借自身的行动产生差异性的结果,暗中对抗性别的政治。这一反抗的可能性可以推广到身体政治的其他领域。无论个体是否拥有本体论的身份,他都可凭借行动、操演与权力形成对话。于是,在身体政治领域,个体可以“通过反对为身体赋予意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混淆支配话语”[20],进而达成对自我身体的重新定义。
三、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的认知逻辑
前两节回溯了西方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的话语史,表明这两种话语是政治身体和个人身体进行相互映射和塑造的结果。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将之总结为“正如我们以自己的身体构想社会一样,我们同样以社会构想自己的身体”[29]。我们可借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对右手现象的阐释来把握两种话语交互的认知逻辑。
赫尔兹指出我们的左右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不平等:与右手相联系的通常是荣誉和特权,我们习惯用右手执行动作,相反,左手总是被厌弃,处于从属的辅助地位。有学者用人体的生理差异解释这种右手优先现象,比如因为人的左脑比右脑发达,而左脑又控制着人体右侧的肌肉运用,所以人类更习惯使用右手。赫尔兹则认为不能单从生理差异角度来解释,还得加上外在的社会、宇宙因素。他提醒我们,原始人的思维中普遍存在神圣和世俗的二元对立,人体也不能逃脱这两极性的法则[30]98,102。于是,左右手被纳入这一对立,右手(右侧)是神圣、创造性的代表,左手(左侧)则是世俗、破坏性的代表。那么为何右手会被纳入神圣一极呢?此时赫尔兹又回到了生理差异,正是右手在生理上的微弱优势使得它在集体意识的定性区分上为自己赢得了一次机会[30]114。于是,我们可以总结道:在赫尔兹看来,人体即是微观的世界,两者遵循相同的两极法则;人们通过左右手的细微差异建立起右手神圣、左手世俗的二元对立;左右手的二元对立推广并强化了人们附加于(宇宙、社会的)左、右的价值判断。在这一条思维逻辑中,人们认可人体和世界(社会)的相似性,先以世界的两极性想象人体,将两极性与左右手相联系,再以左右手的两极性想象世界,赋予左和右世俗和神圣的涵义,世界或社会的左、右涵义反过来又会加强人体左右手的二元对立。因此,右手现象表明人类身体话语和世界(社会)话语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和塑造。
对右手现象的阐释体现了个人身体和更大的有机体(宇宙、社会、国家)之间的互动。该互动的思维基础是“人类神话思维时代的一种类比联想观念”“将宇宙视为一个放大的身体,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二者之间遥相对应”[31]。由于身体是人类面对世界的首要工具,因此人类总是倾向于首先从自我的身体出发,以此丈量外部的世界,又由于两者的类同性,再把外部世界的特性向自我的身体投射。萧延中在剖析中国政治思想的建构时,运用了身体、社会、宇宙的简易模型。他指出:人们以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为基础,从自己的身体获得一套关于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根据这种认识,使用关于身体的知识去概括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结构;随后用有关社会组织结构的知识赋予宇宙以“有机体”的意义;同时,一旦宇宙模型被建构起来,由于它具有直观的自然性、必然性和客观性,因此反过来对人们解释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作用;而社会政治组织的功能再以此为理由约束个人的思维和行为[32]。显然西方的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话语也基本遵循萧延中所说的思想模型。因为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中,人的身体就是宇宙的缩影和摹本,政治身体则是人体和宇宙的中间体,同时也是人体的摹本[33]。只不过在西方的身体-国家话语中,宇宙这一环节作为背景隐藏了起来,身体和国家(政治)成为凸显的一对因素:以个人身体的生理认知构想政治身体的结构,同时又把个人身体看作政治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整个政治身体的协调运作来要求个人身体,并通过对以上两项的重复达成个人身体和政治身体的不断相互映射。
讨论至此,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身体-国家话语既关乎个体对国家的想象和理解,也关乎国家结构为个体创造的生存空间。本文综述西方的政治身体和身体政治话语史,对两者进行了概念上的辨析,并厘清了两种话语互相建构的认知基础,希望能为国内的身体-国家话语研究提供借鉴。针对身体-国家话语做文化上的研究,即在特定语境下剖析政治共同体的修辞生成。这有助于我们在话语层面理解国家认同的生产和个体生存空间的再制造,对当今社会来说一定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