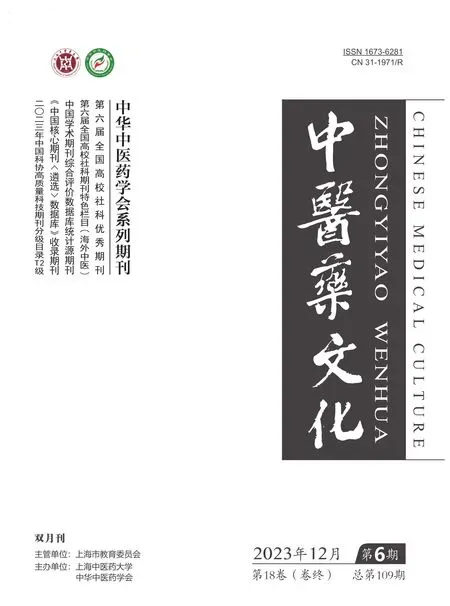从《中西医药》看民国时期中医语境和发展境遇
章 林,段逸山,任宏丽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尤其是民国时期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在国家医药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当权政府的西医话语权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医处境岌岌可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备尝羞辱,国势颓废……海内有识之士,亟图兴教育、崇科技以图自强,而长期以来形成的惟西学是尚的崇洋媚外者,视中华民族传统优良道德与文化艺术不顾,且欲消灭而后快,中医学也曾多番面临灭绝之灾。”[1]6中医界有识之士认为,创办学术期刊是关乎祖国传统医药生死存亡的得力举措。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创办中医学术期刊460 余种[2]137。众多中医学术期刊中,宋大仁等创办的《中西医药》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尝试对《中西医药》进行研究,结合当下中医传承创新发展历程,重点关注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问题,以期从期刊学术语境考察中医发展境遇。因期刊文章内容多,且主题、观点重复性大,故并未一一赘述,仅以内容最多、总体水平较高的首期为例,尝试见微知著,鉴往知来。
一、《中西医药》办刊历程及其社会影响
1935 年4 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第233 号训令批准中西医药研究社成立[3]。研究社成立后开展了大量与医药相关的工作,其中之一则是创办《中西医药》期刊。该社核心创办人是宋大仁。宋氏声望卓著,在中西医界均有较大影响。1948 年,时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施今墨、上海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丁济万等号召中医界全力推举宋氏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4]。
(一)办刊历程
研究社宗旨为“集中国内医药人才,研究中西医药,以期中国医药学术之改进。以科学方法研究医药学术,完全以真理为标的,摒除各种派别上之私见。努力灌输民众医药卫生知识,以期恢复中华民族固有健康之精神”[3]。创办经过大致如下[3]:
1932 年春—1934 年11 月为孕育发起期。1932 年春,由宋大仁、徐元甫、钟之英、褚民谊、沈乾一、万竹友、梁心、丁福保8 人发起组织,相关费用及筹办场所均由宋大仁负责。1934 年9 月20 日召开会议,宋氏提议研究社为“研究学术机构”,并拟向党政机关申请备案。宋大仁、沈警凡、范行准等7 人为备案筹备委员。9 月21 日宋氏联合党政军医界30 人,联名发起,并于10 月2 日呈请上海市党部备案,并请颁发许可证书。11 月17 日,上海市党部执字2308 号批示备案通过。时隔两年多,在1934 年11 月20 日领取许可证书。
1934 年11 月—1935 年1 月为筹备期。1934 年11 月成立筹备委员并召开筹备会议,宋大仁等29 人当选为委员,其中宋大仁、范行准、沈警凡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2 月6 日将各类章程草案邮寄各地委员以征求意见,并及时进行修订。12 月10 日呈请上海市教育局备案,同时又为筹备会成立一事呈请上海市党部备案,12 日获教育局批准,随后按照教育局“民众团体组织方案”和“上海市监督文化团体规则”等要求,办理筹备各项规则和程序。1935 年1 月15 日召开筹备会议,商讨重要文案,并决定于1 月26日召开成立大会。
1935 年1—4 月为完成期。1935 年1 月26 日召开成立大会,公推宋大仁担任主席。1 月28 日召开第一届理事会。3 月19 日上海市教育局正式发文,成立经过准予备案。上海市党部于4 月2 日上午派员视察。4 月9 日召开第二届理事会。4 月20 日上海市党部证书发文准予办法健全训令。4 月27 日呈请主管机关教育局立案并获允。
(二)出版发行情况
为做好期刊的出版发行并确保质量,知己知彼,研究社于1935 年初对全国医药期刊数量及栏目开展了一次非常详细的调查。“为欲明了医药界之真实情况,以为改良之张本,特制调查表多种,征求医药界同道填写。”[5]调查结果:“本社调查刊物,得悉总数约计三百五十种,其中业已停刊者,一百三十二种,现仍发行者,一百八十三种。发行最早者,为光绪八年,美人嘉约翰所主办之西医新报。历时最久者,为博医会报,自光绪十四年,至民国廿一年九月,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计历时四十七年之久,且从未间断,尤为难得。发行医药杂志省份以江苏省发行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又次之。”[3]此次调查统计是该社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工作,赢得行业好评。研究社掌握基本情况后,经反复商讨才确定各项细节,以避免一般性学术刊物对中西医问题的简单探讨,希望能给国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中西医药》(Journal of the Medical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为全国性学术期刊的月刊,由研究社出版部编辑股编辑、出版部发行股发行,大方印务局印刷。受时局影响,没有按月刊计划出版。出版情况为:1935 年4 期,1936 年12 期,1937 年6 期,1946 年3 期,1947 年8 期,共33 期。受日本侵略影响,1937 年8 月停刊,1946 年10 月复刊。作为出版物,期刊必被赋予特定使命。据发刊词介绍,该刊旨在呼吁摒除主观臆断中西医孰优孰劣,聚焦最新医药学术前沿,促进国家医药发展。按照宋大仁的本意,医药作为科学并无中西、国界之分,冠以“中西”两字,并非指在学术上有区分,中西两字只是从时间和空间上予以界定。“中西”医学均有可取之长,应该消除纠纷和隔阂,当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对中西医,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研究[3]。
1937 年停刊前,其学术栏目相对固定,主要包括言论、文献的研究、新知的介绍、调查与统计、国外通讯等。“言论”主要刊登有关医药革命、抨击医学上的偏激行为等文章;“文献的研究”侧重对古代医学著作的研究考证;“新知的介绍”主要刊登中西医领域最新动态,如关于鼠疫、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的治疗预防;“调查与统计”偏重对全国医药学校社团期刊等进行调研;“国外通讯”以介绍世界各国最新医学研究动态和医学事件为主。概括而言,一部分栏目“努力介绍欧西新医学说,以救济一般思想顽固之国民,使其了解医学的真相,则从前之迷茫,不攻自破”,另一部分则“努力研究中国以往医学之经验,如本草及验方等,皆予以科学的整理与发扬,及纠正以抱残守缺,不如彻底研究原因之惰性”[6]。期刊栏目特色明显,尤以“文献的研究”为要,“足以夸耀于当世”,当时的医药刊物里唯独《中西医药》有该栏目的设置[7],作者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随着研究社和期刊的发展,栏目也有变化发展,对文章的质量要求也进一步严格。例如,1936 年增设药物经验和信箱栏。为防止凭空捏造、鱼目混珠、剽窃僻方现象的出现,规定投稿时需要对所投稿件进行详细介绍,如表明药名及处方、配制及用法、适用病证、试验经过、禁忌、药理等;另外,还请郭琦元、林椿年、章次公、叶橘泉分别负责中西药单方审查工作。1937 年新增本草研究、书报评论、诊疗谈片、医药漫画等栏目。此后,栏目几无变动。1946 年复刊后,栏目和质量有所减少和下降,远逊于早期[8]35。期刊稿件来源方面,除了研究社社员,还向社会广泛征稿。作者身份包括中医、西医、军政要员、文化学者、媒体编辑、国外医药学家等,其中不乏医学博士等专家。学术栏目之外,每期也刊登以西药为主的广告,赚取盈利。例如,1935 年第1 期共刊登11 则广告(咳净、可拉明、治百咳、依拉纯、脑肾丁、药的能、心胃气痛丸、霍去病、赐保命、福斯补而命、百乃定)。
(三)特定时代的社会影响
《中西医药》的社会影响主要来源于学术和政界两个层面。学术方面,归功于社员(多为学术栏目撰文者、负责人)文章的见解具有独到性;政界方面,得益于众多政府官员的认可和支持。
《中西医药》期刊发行负责单位——中西医研究社,将其成员分为基本社员、社员和赞助社员,对所有成员都有相当的要求。基本社员:“凡对于中西医药却有根袛,而曾有有价值之著作发表者。并由社员二人介绍,经理事会通过,方为合格。”社员:“凡医药界同志,能接受本社宗旨者,皆可入社。但入社时,须提出论文两篇,经本社理事会审查通过,方为正式社员,否则视为社友。”赞助社员:“凡同情本社宗旨而肯予以实际上之助力者,得声请本社理事会,经理事会通过,方为本社赞助社员。”[9]从其社员构成情况来看,基本都具有医学专业背景,且在医学领域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的初衷更多是出于发展国家医药事业,但其言论一旦通过期刊公诸于世,就必然会产生社会效应。由于该刊的影响力,1935 年10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第414 号令要求全国学术机关、团体、学校、图书馆一致订阅,一时震惊医坛[8]34。
政界方面的支持,从当时为该刊题词的人物情况就可见一斑。“刊首语”中登载了政界、军界、教育界、文化界、商界、宗教界以及医药界名人赠送的题词,共152 件。他们中有“国府主席各院院长及各部部长各省主席厅长市长局长校长与社会名人”[5]。以排名前30 位题词人为例,便可看出该刊影响力之深远,他们依次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尚友文艺金石书画合作社主干许震、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院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江苏财政厅厅长赵棣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司法院副院长覃振、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江苏民政厅厅长余井塘、河南教育厅厅长齐真如、江西民政厅厅长吕咸、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国立暨南大学教务长李熙谋、陆军上将李宗仁、驻鄂特派绥靖主任何成濬、河南省主席刘峙、监察院秘书长王陆一、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立夫、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国立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10]。国民党内一部分深受孙中山影响的政要,一方面源自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情感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对中国贫穷落后缺医少药有着深刻认识,能够在中医事业发展方向上保持正确态度,这一价值取向从他们的题词内容可以确认。
二、《中西医药》视野下中医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医界在学术、政治和文化层面始终面临着如何发展中医的困境。在中西医长期论争的背景下,尽管学术探讨和研究根本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但透过争论可以让问题更为具体清楚。研读《中西医药》首期文章发现,作者通常以具体问题为视角,分析中医发展所面临的桎梏。与此同时,论述过程中也存有轻视、忽视中医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和心态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冲突导致医药观念存在分歧
“发刊词”最能反映期刊宗旨和远见。《中西医药》发刊词中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国社会在如何看待医药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且都不科学的观念,“一是大多数人以广大基层民众为主,坚持中医反对西医,另一种是少数受过新文化、新知识教育的人,他们反对中医提倡新医即西医”。文章认为,混乱局面严重阻碍国家医药学术和水平发展:“我国医药现状,甚为复杂;因有中西之分,各成门户之见,彼此倾轧,互相攻讦,而各忘其更有重大研究之研究进取之责任,使中国医学,永无进步。”[5]两种观念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前者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中医历史悠久,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新医(西医)是国外学说,加上传统鄙视“夷人”的心理,根本不会虚心学习西方文化,后者尽管对西医有所了解,但对中医和国家社会缺乏缜密的调查研究。故而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能以孰优孰劣的主观臆断来看待医药,而应秉承客观、严谨和科学观念看待中西医。
晚清以来,国人关于本土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矛盾,逐渐由具体领域延升至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中西医领域的论争同样如此。在倡导以科学态度对待国家医药事业的同时,“发刊词”并未真正摆脱鄙夷中医的心态:“返观我国医学,至今仍袭用原来医学,故尚未脱离阴阳五行家之藩篱,且援此以与科学抗,虽胜负之数早已决定,无如顽固者犹以数千年久远之历史相甛,而获社会上多数守旧无识者所拥护,故虽败而其气未少馁,悍然自愿孤立于全世界进化之范围以外,遂形成今日新旧交争出奴入主之混乱状态。”[5]言语之中表达了对中医因循守旧的不满,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故而寄希望于发扬学术、尊崇科学。在操作层面提到两个步骤:“其一,努力介绍欧西新医学说,以救济一般思想顽固之国民,使其了解医学的真相,则从前之迷惘,不攻自破。其二,即努力研究中国已往医学之经验,如本草及验方等,皆予以科学的整理与发放,及纠正以往抱残守缺,不知彻底研究原因之惰性。”此观念在当时中国医学界并无特别新意,共同目标都是“树我国医药上之大业,无使永久停滞于混乱状态中”[8]6。语言逻辑上具有发展眼光,内容上却含有贬低中医的情绪,这与市党部代表毛云的态度如出一辙。
在《市党部代表训词》中,毛云一面提到自己在医药领域虽不是内行,一面却直言:“我觉得一种学术,单说历史长久以为他一定有用,那也恐怕不见得,因为判别学术的优劣是在他的内容,而不是在他的形式,譬如中医学理,数千年来,都蒙了阴阳五行的毒,这种历史,纵使他再展长五千年以致一万年,也不见得他有怎样好处。”[11]作为市党部代表,身份地位不同一般,关于中医的偏激态度无疑会影响一般民众的认知。相较于毛云,市教育局代表聂海帆的态度比较温和,提出对待中西医应以科学为唯一原则,具体而言,“一、不要守旧。二、不要盲从。三、要适宜中国环境”[12]。讲话本身没有得罪中西医任何一方,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除了中医界,很少有人公开表态中医是科学的。
为什么在期刊首期开篇讨论国民医药观念这一问题?沈警凡在《本社学术部计划之管见》一文中给出了答案,认为如果该混乱、畸形状态长期持续,任其炫人耳目,必将导致“政府民众苦于无所适从,长此以往于国家社会百姓有害”。“我国医药,现呈中西对峙之局,医药学说,亦混乱无分……认此问题,是我国医药界最大而急需解决之严重问题,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欲望我国医药卫生之进展,是犹缘木求鱼也。”[13]郭琦元《在新旧医学交替中之期望》一文分析了畸形心态的具体表现:“虽然尚有多数之迷古者,战战焉怵于腐说之将覆,借保存国粹之美名,以提倡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方士邪说,而与世界科学家所公认之医学为敌。其狡猾者,则往往以新知附会旧说,以冀一遇,遂以为医学之能事已尽于此。探其衷情,其欲保存旧说则一也。更有一般知识浅薄国民,复惑于如簧之舌,益失其辨别真伪之力,于是我国医学,不仅未见进步,反而骈生许多无谓搅扰之空气,以窒息其生命!”[14]分析虽合情理,但却同时反应了轻视中医的态度。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艾伟博士《中西医药之我见》一文认为,这种不良心态,不仅存在于普通百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同样具有,此心态体现于日常文化行为、心理反映和生活常识,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是不加思考,全凭经验臆断,当遇见被西医医治无效致死的情况时,“遂以为一般西医皆不可恃”,相反,当其家人或朋友因中医而得救时,“遂以为一般中医皆有回生之术”[15]。作为丁福保(丁仲祜)先生的高第,著作等身的沈乾一在《希望健全之医药》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一不正常现象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医药组织不健全,数量和质量落后,中医也被视为违背科学的存在:“惟我国各地,尚多行不健全之医药,殊有悖于进化之理。识者忧之!盖医药有关乎疾病之安危,实较任何事项为重要。今我国以多数人之生命,操之于不健全医药之手,其危险也孰甚!而全国现有之健全医师,据最近卫生署之统计,只有六千余人。”[16]
(二)医学教育制度和理念的混乱致使中医教育失去方向
中医古代医学(中医)教育大致可分为官办学校教育和师承教育。进入20 世纪,随着西医话语权的强势盛行,中医教育处处碰壁,中医处境岌岌可危。“现今中医之处何时乎,非风雨飘摇之时乎,外习欧化之攻击,内受当局之摧残,亟亟遑遑,未恐不速其亡。”[17]随着官办教育的衰落,中医私立学校教育逐渐兴起。中医界有识之士认为,开展中医教育是关乎祖国传统医药生死存亡的得力举措。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中医办学机构有200 余所,但中医学校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得不到国民政府教育备案许可。这些中医办学机构尽管很多办学时间不长,规模不一,且几乎均为民办性质,但却不乏一些非常成功、影响深远的中医学校,它们在办学规模、办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呈现了承前启后、改革创新、汇通中西的鲜明特点,开创了一条中医办教育的自信自强之路。例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上海中国医学院[18]、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等。
研究社社员代表、期刊主力干将江晦鸣长期关注国内医学教育事业,在各类期刊发表很多关于医学教育的论述。在《怎么改进我们中国的医学教育》一文中,他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医学发展为例,认定我国近代以来的中西医药之争以及医药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医学教育的落后,改进医学教育是消除中西医隔膜、促进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出路。“我们知道近四十年来,中国的中西医药之争,迄未消弭,原因安在?依我看来,实受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影响。我们且拿日本做例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何以他们的医学会蒸蒸日上?原因虽不单纯,要以医学教育发达,居功最多。鉴往知来,我以为要想中国医学发达,中西医药之争消弭,以改进我们中国的医学教育为唯一的出路!”[20]
为了更为清楚地证实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中西医药研究社的支持下,江晦鸣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医学教育进行了详细调查。江氏对当时中国医学教学的现状、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文中特别强调中国医药学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医学教育制度的混乱,医学教育完全处于畸形状态。文章结合《新唐书百官志》《宋史选举志》《元史百官志》《明史职官志》《大清会典》等,对中国的医学教育沿革进行考证,并提出核心观点,即中国古代有医无育:“我国数千年虽有考医之举,但目的仅在采风问俗,而历朝的太医院,又不过供皇室贵胄的使唤,不足以言医学教育。”尽管其观点值得商榷,但却因此得出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实属不该。这是当时取消、反对中医的典型观点之一。江氏认为在新旧交替时期,应该大举科学旗帜,而中医是“玄学的产物,和卜筮式的无稽学说,该埋没在这时代的巨轮下,没有骈存于世界的可能了。可是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头脑,还不了解什么叫科学”。他还对很多中医前驱呕心沥血创办学校的贡献加以否认:“终至造成今日这个畸形的现象,我们还可以看见许多旧医学校林立在中国的通都大邑。”并称:“检讨过去中国医学教育所以不能进步的因果,上面所说的畸形医学教育的发展,便是一大阻力。”文中,江氏还对中国的西医教育、西医学校历史进行了梳理,并附以“民国纪元前所成立医学校之沿革表”“全国医学校的调查”“中国各级医学校之沿革”等调查数据[21]。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还专门回顾了当局政府对待中西医教育的立场,文章最后的态度也都是关于如何发展西医教育以救国救民,对中医教育只字不提。
(三)守旧封闭观念造成中医科学研究落后淘汰
沈警凡曾以应用统计学整理国药知名于世。他在《中西医药》首期撰文《我们怎样提倡药学革命》,呼吁变革长期以来的守旧观念,加强药物的研究,若非如此,必将被世界淘汰。中医的发展离不开中药,中药的种植、加工、生产,关乎国家经济和百姓生存。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心态,沈氏以中药改良创新为例,认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故步自封的思想迟早会断送中国医药的优势,一旦被世界遏制,国民健康、民族发展前途堪忧。“近年来,东西各国,争先研究中国药物,已被发明为灵药的,有麻黄精、防己精及当归精等,正须提倡,国产药物推销于国外;如脑中存着这种思想的人,他的观察一定是错误了。要知,发现上述数药有效成分的人,都非国人,并且药物有效成分的方程式,一经明了以后,可用人工合成法制造,毋须再用该项生药为原料,如麻黄樟脑已有人造品了,并且其功效反较以天然原料制成的为佳,其副作用反较以天然原料制成的为少,由此看来,人造品优于天然品了;衡以优胜劣败之理,将来制造药化学进步以后,天然药品殆在淘汰之列,若想欲以中国生药,推销于国外,以为已尽提倡国药之能事,则其思想是幼稚的,错误的,盖外国因科学进步,药用植物的品种,栽培法施肥及收获等等,皆极考究,而国人则品种不知选择,栽培不得其法,施肥之种类及收获之时期,皆不知考究;所产生药,品种杂乱,有效成分多寡不一,制药者多费时间金钱,甚不经济,用之亦不准确……我国生药,若不改良,不但不能推销于国外,恐不数年,我国之市场,反被外药占领矣。”[22]
毕业于浙江省医药专门学校的夏苍霖《麻黄素与Ephedrin》一文以麻黄发明应用为例,断言若不加强对国药的研究和重视,中药产业将为世界所控制。文中指出,中医药延续至今,极端依赖中药。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国人长期以来对药性、药物成分毫不了解,甚至反对、鄙弃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麻黄的发现和应用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麻黄是一味重要的药材,中医历来认为麻黄多为发汗及镇咳药,“尤以喘息赏用……如对于感冒时用为发汗药之葛根汤……喘息及气管枝加答儿时,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其他如麻黄汤、甘草麻黄汤、麻黄醇酒汤、大青龙汤、越婢汤、越婢加术汤、越婢加半夏汤、牡蛎汤、小青龙汤、乌头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等,均应用麻黄,其目的以麻黄为能开皮肤之气孔,去水气,治咳喘,去浮肿,消疼痛;故常以皮肤排泄障碍水毒停滞之目标下,广为应用”。尽管麻黄广为应用,沿袭数千年,但有效成分却是在1887 年由日本药学博士长井长义发现的。麻黄的主要成分为Ephedin,随后更有日本人发现其化学分子式及药理等。直至1924 年我国药理学家陈克恢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它的真正价值进一步引起世人关注。经研究,麻黄能够对以下症状有作用,“张力减衰症——眼,喘息,枯草感冒,荨麻疹,血清发疹,慢性气管枝炎,气肿,月经困难,湿疹”。其中,麻黄对喘息与其他药物相比更具优势。后经进一步研究,麻黄的副作用及如何用于中药煎剂更有相当改进。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麻黄已发展为欧美国家的人工合成品,且功效不减,这对国人而言是极大刺激。夏氏告诫国人,麻黄只不过为无数中药之一,对其功效的研究曾领先于世界,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民健康曾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能对更多中药进行科学研究,必将进一步发扬传统医药的价值。言下之意,中医药必须科学化研究,只有科学研究才能真正保持优势,盲目乐观必有被淘汰的危险:“我国新医药学者,苟能努力研究,将国药生产,一一发明其主要成分,不难与各国争雄,造成强有力之国家;否则良药遍地,宝藏满蕴,只待他人之开掘,而大好国粹,欲保存而无法保存,不亦哀哉!”[23]
(四)轻视基础文献研究影响中医学术发展
医药文献卷帙繁多,但很少有人注重研究,对医学文献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到位。专攻于医史文献研究的范行准感叹,这一陋习阻碍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他在《研究我国医药文献的方法》一文中强调,正因为研究重视程度低,导致研究方法落后、相互剽窃严重等不良现象。“数年来因为没有良师胜侣,对于此道,依然是暗中摸索,没有寻到正确的途径。”[24]为此,他根据多年的研究经历,从材料选择、文献分类、具体路径等方面提出建议。
前文已述,关于医史文献的研究是《中西医药》期刊的特色。例如,范行准《古代中西药之关系》一文从中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角度进行了系统性溯源,将医药历史与地理、文化等融合考证,得出结论:“吾国医药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未与西方发生关系,盖以其尚缺乏发生关系之主要条件——文化未有接触也。”范氏另一篇文章《中国经络学之剖视》从秦汉以来的文献(史家和医家记载)以及历代名医(扁鹊、华佗、太仓公、皇甫谧、张仲景、王叔和、郭玉、徐大椿、张三锡等)的实践进行考证,着重对“经络之生成与分布”“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经脉循行的起讫”“经脉循行的方向”“经脉循行的支别”“静脉的离合”“经脉经过的所在”“井荥俞原经合”“经穴”“经脉与络脉”“经脉与筋经”等进行研究,肯定了经络学说的科学性[25]。日本医学家富士川游《医籍考解题》一文对《医籍考》的成书过程和大致内容做了介绍,为中国医学的研究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26]。日本江户末期医学考证派学者时代汉方医学家丹波元胤所撰《医籍考》当时在国内还缺少系统的介绍,更无可查阅的影印版本,中西药研究室图书馆购买并影印,以供读者付费预约阅读。夏以煌《华佗医术传自外国考》一文针对华佗的医术传自国外一说,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考证,认为华佗医术确实融合了印度、埃及、希腊等国医术。探讨医学起源等关键问题对于中医学术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该妄自菲薄,借此否定中医价值的倾向不宜提倡。例如,《华佗医术传自外国考》一文的结论之一是,我们所保存发扬的国粹,并非真正的国粹,既非正宗,便无发扬之说。“总之,吾国之医术,自古已非纯粹之国粹也。中经溶杂,业已与埃及希腊同化之印度医术,国粹云何哉!方今西医东来,不数世后,则金针开内障法之外,又附益以水晶体摘出法,亦何尝非国粹也!国粹云何哉!由此种溶杂之机会,同化之现象。而后产生华佗之神技,及历代不少之名医,此为进步自然之趋向;今而高唱保存国粹,则名既不正,抑亦示人以自责也。乌呼可!”[27]
除了强调重视医史文献研究以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黄雯还在《我国固有医药可供科学研究者之我见》一文中重点阐述了如何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告诉读者从哪些方面研究中医。作为留洋归国的西医博士,其身份和地位迥异于中医,他所倡导的观点富有新意,也具有引导性,在指出我国医药存在固有弊端的同时,肯定了也有值得研究之处:“荒谬之玄说虽多,而数千年来之经验,间亦可取而研究之地……对于我国固有医学,宜先加研究,不可轻于剔弃。”黄氏认为,在面对外族入侵之际,医药卫生事业至为重要,要想自救还得要大力发挥中医的作用,否则很可能坐而待亡。对于如何研究,提出5 个建议,即要以科学方法整理固有医药书籍;要注重研究民间单方;研究针灸;研究患者食物之宜忌;研究癌肿(恶瘤)[28]。万竹友《如何领导中医入科学正途》一文同样就如何加强中医科学化研究进行探讨,此文体现了中西医合作的理念,从当局行政管理、教育制度和体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习交流方式、规范化操作等层面提出具体建议[29]。
(五)文化本位心态阻碍中医传承创新
宋大仁《建设本位的文化与中国医学问题》一文从当时甚为流行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视角探讨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宋氏认为“中体西用”观念对中医影响极大,面对西方科技,中医一方面露出保守和卑怯心理,另一方面因此误入歧途。其认为“中体西用”的心态由来已久,但很多人不明白两者是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表象,没有体的用只是空虚,没有用的体不能存在”。在中医科学化的道路上,很多人误解甚至故意曲解这一文化现象。“人家发明了X 光,他便回到故纸堆中,去找他的‘真理’,幸而有些偶合的地方,于是大呼小叫起来:我们也有X 光了,我们的扁鹊洞见垣一方人,尽见五脏症结,这不是X 光是什么?在这样附会和抄袭‘西学为用’之下,遂产生了唐容川中西医学汇通,以及现在的什么《今释》《辑义按》之类,此种谬误的保守的凑合,其流毒深中于一般人的脑际,尤以青年们所受的影响最大,至今不易涤除。”宋氏还认为中医表面上提倡“融汇中西”,实际上仍是以“发皇古义”为主体。此外,还特别强调中医的思维和理念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例如:“封建制度盖成立于周初……周朝的制度是封建的,是建筑在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一种阶级隶属关系之上,国医的学说里有‘脾土为主’的崇拜土地的观念,也就是这种制度思想的遗痕。”认为封建小农经济造成了国民“安分、知足、寡欲、摄生”思想,这种心理“现在还可在古代的医籍中找出这类思想的影子,自《内经》以下直至汪忍庵的医书都是很好的社会史医学史的材料”[30]。作为研究社和《中西医药》期刊的核心创办人,他的观念具有代表性。
宋氏道出了中医思想和实践中的不合理成分,与其观点类似,萧叔轩《独裁政治与医学建设》一文将中国医学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归结于国家政治腐败、政府混乱和传统文化束缚。长期以来,内忧外患的形势阻碍国家发展。萧氏援引苏联、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历史,认为国家富强需要“铁腕政治”,对于医学而言同样需要“铁腕”,正因为没有政治、文化上的“铁腕”,导致“根深蒂固的旧医学仍是不能根除源绝的。充其量也不过走到折中调和的路上去”。究其真实想法,仍是要废除中医,杜绝“草根树皮和化学药品并陈于马路的树窗里,20 世纪的新医学得与死去的岐黄尸体并行而不悖,从挑痧以至于行盐水注射,从采阴补阳,服童子精以致施用动物内分泌制剂”等现象。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是整个国家未能脱胎换骨,“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要彻底取消中医,走向所谓的科学医,就应该走当时流行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路径,以科学的朝气和毅然决然的手段打倒以中医为代表的“古旧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惰性与暮气”[31]。
总体而言,《中西医药》期刊对中医文化、教育、学术、科研等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学者们在探讨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时,难免受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的冲击,故而以问题和实践为导向的特征格外明显;另一方面,基于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以及中医群体毫无政治优势的客观现实而言,很容易造成整个行业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医药发展问题,即使这种批判是建设性的。《中西医药》关于中医药发展问题的评述具有典型的时代性、批判性和前瞻性,反映了该时期众多中医学术期刊的中医学术语境和当时的中医发展境遇。
中医究竟如何实现科学化、现代化的问题一直存在纷争,民国时期尤其如此,这一纷争在当时的众多报刊、期刊等媒介中得以深刻体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医群体的抗争,南京国民政府一定程度采取扶持中医政策,明确了中医法律地位,一度给中医界带来期待,也为团结支持抗战增添了医药保障[32]。但是,从医学、文化层面反对中医的声音从未停止,中医界精英试图通过成立社团、兴办教育、出版刊物等手段,加强团结整合,扩大社会影响。
关于中医发展的时评成为当时一道重要社会景观,医药期刊则是这一过程发生的重要场域。中医界强调中医药乃国粹,医国医民,国难当前,如若丢弃必将离亡国灭种的危境更近;祖国医药传承数千年,确有与时代不合之处,需要加强整理研究,探医药之真谛,保民族之健康;须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进而实现现代化;中医发展受阻、乱象频出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独立行政管理权。反对者虽肯定中医的历史贡献,但却以非此即彼的极端态度,对数以百万计中医师的利益缺乏尊重。通过对《中西医药》首期文章观点及其内容的分析发现,中医发展的确面临着迫切问题,这一点在当时的众多期刊都有反映。但这些问题不能成为反对、忽视中医的绝对理由,更何况这些问题并非停留于医学层面,还涉及政治、文化、习俗等等。批评的出发点应该是改良、进步,而不是简单的取消,更何况是在民族危亡、中医药发挥重要抗战作用的抗日战争时期。
传播文化、启人心智、充实民众生活、挽救垂危之中国为当时众多期刊所标榜。20 世纪30 年代孕育而生的《中西医药》与众多期刊的学术语境相似,在对中医发展问题进行论述时,对如何发展中医提出了中肯意见,具有客观性,甚至为解决整个国家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靶向目标。但在关注其崇尚科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满纸充斥的“旧医”“陋习”“遗毒”等话语。围绕社会热点开展的探索与争鸣,是民国学术期刊的最大特色。学者应当秉承科学精神,倡导言论自由,但必须结合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从国家大局、民族大义、文化前途去评述现实问题和未来走向。尽管本文从特定时代环境下的一本刊物出发,论述不甚全面,但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正因为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性,才更需要反思过去与现在,进而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发展提供参考。通过反思,才能更深刻地领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和未来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