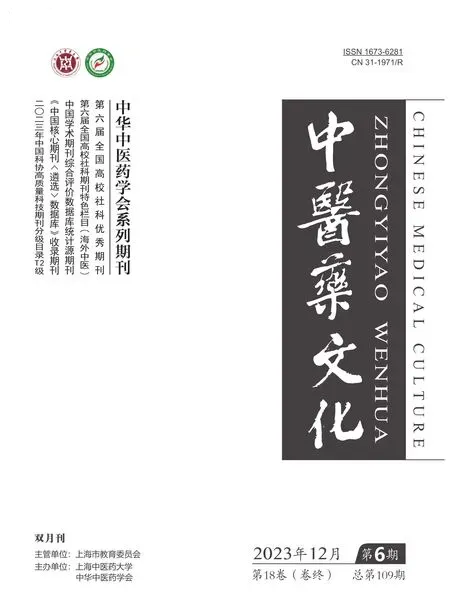明清小说中喜脉诊断的叙事伦理困境
李远达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
明清小说中存在大量具身性医学情境,与同时代医案医话中的情景往往能够形成照应或产生互补,其中的“喜脉”诊断特别值得关注。喜脉虽然命名中带有“喜”字,然而在文学文本所折射出的医学实践过程中却往往成为导致医患冲突的焦点,容易造成医患双输的局面。故此,喜脉常被明清医家称“关系最重”“必须留心”“切切不可直口说出”[1]152。关于明清小说叙事伦理,其本质与伦理叙事有别。叙事伦理的中心词是伦理,伦理行为发生在叙事主体、文本与接受等叙事全过程中,而伦理叙事则主要关注叙事文本中涉及伦理的部分。明清小说中的叙事伦理问题,由于在学理上存在回归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保守倾向,学界重视不足。单篇论文方面,仅有江守义、朱锐泉、李建军、宗城、张桢、阴姣、卢智琳等研究者有所涉猎,主要是就一部古典小说的叙事伦理进行探讨,在撰写体例上又多是学位论文①期刊论文参见江守义的《中西小说叙事伦理研究路径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9 年第2 期,第1-8 页)、朱锐泉的《论世情题材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困境”》(《明清小说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39-49 页)、李建军的《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以宋代小说为考察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9 的第7 期,第134-145,72,160 页)、宗城的《从叙事伦理看中国古典小说》(《书屋》,2019 年第11 期,第68-71 页);学位论文有张桢的《〈梼杌闲评〉叙事伦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0 年)、阴姣的《〈水浒传〉的叙事伦理研究》(喀什大学,2021 年)、卢智琳的《李渔短篇白话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 年)。。学术专著方面,江守义等学者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一书中对叙事主体、叙事文本、叙事接受三个层面与伦理的具体关联与互动做了系统性探讨[2],但在医学叙事方面仍有深入细化研究的空间。
喜脉诊断叙事是探究传统医学叙事伦理困境的上佳个案。究其原因,喜脉诊断恰好囊括了医术、叙事、宗族和伦理四位一体,因而明清小说及医案医话中所呈现出的伦理困境也尤为突出。
一、明清小说具身性伦理困境与经典医学伦理指南的裂隙
传统医学文献中对于医学伦理向来不缺乏经典性论述,但细究起来,它们往往呈现出指南化倾向。最具代表性的是《素问》《灵枢》中关于医学伦理的重要表述。例如《灵枢·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3]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还强调医者在面对患者之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4]1,如此方可为大医。如此种种,皆已成为历代医家的信条,乃是传统医学的无上准则。
然而问题便在于,上述经典中的准则所提供医患沟通伦理指南,从表面上看是原则清晰而又面面俱到的。但在不同时代、不同疾病、不同地位医患之间的具体伦理情境,又非“指南”所能涵盖,会遇到许多伦理难题。医者在面对不同身世、性别、年龄、地位、性格、修养以及病情的患者时,几乎不可能做到“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4]1。每一对医患之间所建构起的主体间性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往往受到时空限制,是不可逆的,互信一旦失去,医患关系也大多宣告终结。伦理困境的解决能力时刻拷问着医者的仁心与智慧,尤其是遭遇喜脉一类关系宗族延续的重要节点之时,医生与患者(家属)、医生与自己、医生与同事、医生与社会的关系都面临着考验。如何应对,恐怕仅凭借古典医学早期文本中的若干原则显然难以应付。明清时期的小说与医案医话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鲜活文本,便于当下的医者探索,可代入每个医学情境之中,揣摩渐染,修习提升,进而迁移实践,解决现实临床中的叙事伦理困境。
二、明清小说喜脉诊断的伦理困境
明清小说中的喜脉诊断叙事,医者往往表现出两难处境。他们依据患者有限的身心信息,综合病家氛围,谨慎小心做出判断,但时常会误判,轻则遭到病家嘲讽羞辱,医名受损,重则生命受到威胁,可以从医术因素、宗族因素、同行评议因素和社会舆论因素四个方面展开明清小说喜脉诊断的伦理困境。
(一)早期判定:喜脉诊断的医术难题
传统医学中的喜脉诊断,按照王叔和《脉经》所述之法,应当遵循以下准则:“妊娠初时,寸微小,呼吸五至。三月而尺数也。脉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脉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5]胎儿律动有一个由隐到显,逐步清晰的变化过程。在传统医学认识体系中,孕早期判定女性怀孕,并非易事。
明清小说中也有相应地体现喜脉诊断难度的情节。例如,晚明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叙刘元普为人“广行善事,仗义疏财”,因此其妻王夫人到了40 岁时,忽然喜食咸酸,伴有呕吐。前来看诊的医生大多诊断不明,只有个别医术高明的医生判断为“像是有喜的脉气”[6]。一个“像”字,表明了医生心中的忐忑,也说明喜脉诊断,并不容易。
无独有偶,清道光年间的小说《风月梦》第十四回描述常熟人陆书与进玉楼的月香缠绵,偶然发现月香“头眩目胀,身体发寒”“作恶心要吐”“四肢无力”。陆书连忙请来医生诊治,先后请来了任万林、明驰远两位扬州本地名医,都无法准确判断月香的病证。前者的诊断是:“今日寒暑稍解,有点积滞未清。再净饿一日,有了大解就没事了。若说是喜脉,尚在数十日之间,此时脉尚未现。我兄弟学浅,不敢妄拟,另请高明斟酌。”相较之下,后者的诊断则透露出更多民间的喜脉知识:“贵相知的寒暑表邪已解,任敝友用的药并不错。若说是恭喜,但凡妇人受胎,一月如滴露,二月似桃花,三月分男女,总要交到三个月,那脉象才分得清白。贵相知尚在四五十日之间,脉尚未现,总宜寒暑自知,饮食均匀,那劳力之事,谅来他是不做的,一切小心要紧。”[7]102-104明驰远的诊断自然是为小说叙事服务,喜脉确诊之难恰好表露出陆书对月香之深情。然而从医学角度看,也能折射出在现代检查设备尚未齐备的传统社会,完全依靠脉诊有限的信息量,想要较早确定怀孕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一般的社会认知并不完全认可这件事。有的小说将喜脉确诊困难归咎于医生“脉理平常,模棱不决”。清初小说《女仙外史》第二回叙述女主人公唐赛儿的降世。小说叙述其母亲怀孕时,“饮食咽酸,兀兀欲吐,像个有孕的光景”。请来的医生因医术不精,无法判定,便说道:“《脉诀》有云:受胎五个月,脉上方能显出。”家中有一位名叫老梅的老婢恰好路过,应声讽刺道:“若到五个月上,我也看得出,不消烦动先生了。”[8]小说借老梅之口,讽刺医生无能,反过来也表明在明清时代社会大众认知里的喜脉诊断,已与当时一般医生的实际能力产生了一定差距,这种差距也是医患隔膜乃至冲突的重要起点。
(二)医患隔膜:宗族礼法与祖宗颜面
绵延子嗣是传统社会宗族延续的目标,患者在小说叙事中处于失语状态,病家尤其是男性亲属的态度决定了医患沟通的效果乃至对医生的评价。如果患者是未婚或丧偶女性,那么医者直白地道出诊断结果为喜脉便是得罪病家的取祸之道。明清小说与医案医话共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反映出医患因宗族礼法与祖宗颜面而产生的隔膜甚至尖锐对立。
清中叶乾隆朝江南文士杜纲所编《娱目醒心编》卷十五《堕奸谋险遭屠割,感梦兆巧脱网罗》开篇有一则入话:小说描绘了宦家招赘婿,“尚未成婚”,女儿生病,被误诊为怀孕。听闻未过门妻子有喜,准女婿“勃然大怒”“定要退婚”。宦家为证清白,亲自登门说服女婿,设计再次哄骗医生前来,让女婿躲在帐中,待医生复诊完,女婿跳出道:“我是男子,说我有孕生下相公!怪道人家闺女也说他有了身孕!扯你当官去讲!”医生的反应则是“羞得满面通红,拖到厅上跪下磕头请罪”[9]。准女婿用男儿岂能有孕的常识责骂并殴打了医生,最终达到“塞住医生的口”的目的。
晚清陆以湉《冷庐医话》卷一记载了一则情节近乎一致的故事[10]8,小说与医案的主要情节都围绕医生判断“这不是病,是有孕的喜脉”。所不同的是,《娱目醒心编》故事的核心矛盾是宦家为了证明家门严谨,主动设计陷害医生,而《冷庐医话》所记的苏州曹医生,则是因为“仆素憎曹”,遭到仆人信息误导而误诊喜脉。两者都说明了医生在面临诊断喜脉问题时候存在伦理困境:一方面是检查手段有限,判定不易;另一方面是谨防患方为了自家的礼法与颜面,主动诱导医生犯错,损失名节。
(三)同行评议的窘境:“那众位耽搁了”
如果说明清小说中所反映的医患沟通伦理困境是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龃龉的话,那么诊疗场景中被评议的同行则更将医生置于温柔敦厚的儒家伦理与取信于病家的伦理窘迫之中。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批评为医者“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的行为,认为这种行径是“医人之膏肓也”[4]2,孙思邈的主张伴随着这篇医学伦理名文影响深远。宋以后儒医地位提升,儒家的忠恕之道更成为医生心中的道德律条。《红楼梦》第十回那位被请进宁国府为秦可卿诊病的张友士就以儒医自居,处处谨守礼仪,断不敢收下贾珍送去的名帖。然而,在诊疗场景中,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对同行评议的尴尬境地。贾府人中一再当面强调“先生说的如神”“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儒医张友士也只好淡淡回应道:“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11]147-148“不敢从其教”“那众位耽搁了”已经是张友士能够使用的最委婉的词语,与小说第六十九回无名太医评价胡君荣的“擅用虎狼之剂”[11]959一类表达相比,可以看出张友士的修养与身份。
剥离开《红楼梦》塑造的典型儒医形象,明清小说中更多见的是继承自戏曲“斗医”传统的医生相互苛评。《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中何老人评议同行赵龙岗称:“此人东门外有名的赵捣鬼,专一在街上卖杖摇铃,哄过往之人,他那里晓的甚脉息病源!”[12]这一类对同行医术与医德全面否定的现象,在明清小说中屡见不鲜。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清咸丰时期通俗小说《忠烈全传》第三十五回提到的顾孝威为孙兰娘请来诊脉的黄医官。他的一番自我表白如果与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对读,颇有一番及讽意味:
二夫人两手脉都看了,没有甚事,恭喜只是喜脉。学生有秘制保胎无忧丹,可转女成男,安宁坐草……虽然离不得望闻问切,至于敝道中有得到人家,以八面风儿话相探,人以为他识证,岂不知套人口气,总是入门之谈,学生最恨。不是学生夸口,说二夫人若是请敝道中人来看,未必看得出是喜脉,不知说些甚的呢。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学生诊了脉,问了病源,看了气色,心下就明白得紧。到家查了古方,参以己见,把那热者凉之,虚者补之,停停当当,不消三四回药儿,登时好了。后来又觉有些不快,又请我去。学生一看说是喜脉,代她安了胎,后来平平安安生下大头大脸一个公子。那吏部公也感小的得紧,不论尺头银两加礼送来。那夫人又有梯已谢礼,吏部公又将公子拜我为继父。后来又送学生一个匾儿,鼓乐喧天送到家来。匾上写道“儒医活世”四个大字。近日也有几个善书的朋友,看见说道:“写的是甚么体?一个个飞得起的。况学生幼年曾读数行书,因为家事消乏,就去学那歧黄之术。真正那儒医二字一发道的着哩。”[13]
在喋喋不休的自述中,黄医官除了表露自己对于“套人口气”的敝道中人的深恶痛绝,就是吹嘘自己为高官夫人明白、安胎妥当、收到谢礼等事。讽刺的是,这位黄医官吹嘘的归结点仍在“儒医”上面。如果我们将这位“儒医”与《红楼梦》中的张友士相比,高下立判,很大程度取决于二人对于同道截然相反的态度。
(四)社会舆论的压力:“如何要的”与“声望顿衰”
误诊喜脉对于传统社会的医生而言,后果是严重的。在明清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诊断失误的医生轻则面临“庸医”的恶名,信誉扫地,重则甚至会因此断了生计,威胁身家性命。
前述《红楼梦》中的胡君荣因将尤二姐男胎打落而害怕报复,“早已卷包逃走”[11]959,就已表征出喜脉诊断错误的严重后果。《娱目醒心编》卷十五的医生误将室女诊为有孕,遭受到的是“满满的一桶臭粪,便向他头上一淋,竟像珠冠络索一般”的羞辱;相比之下,《冷庐医话》中所记的苏州曹某似乎更惨一些,他被“叱仆殴之,并饮之以粪,跪泣求免,乃剃其髯,以粉笔涂其面,纵之去。归家谢客,半载不出,声望顿衰”[10]8。“如何要的”“声望顿衰”一类评价,对于医生而言,无异于终结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明清时代的喜脉诊断伦理困境逐渐成了一种社会舆论,许多医生即便诊断准确也有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惊吓。最为可怖的是《风月梦》中的那位扬州名医明驰远。在进玉楼老鸨口中,明驰远的医名却是由这样一则血腥故事成就的:
去年,南京不晓得什么武职大官,有位小姐得了膨胀,不知多少医生未曾医治得好。差了四个带白顶的委员,坐了一只大船到了扬州,将明先生请到南京。到了衙门,这面隔着帐幔代小姐诊了脉,请到厅上来开药方。明先生向那武官说:“小姐不是蛊胀,是恭喜了,是个男胎,已有七个月了。”遂开了一个保胎药方。那武官听了不动声色,请官亲、师爷陪着明先生在书房饮宴。那武官拿了一把宝剑走到小姐房里,不问清白,用剑将小姐肚腹剖开,果然有个四肢长全的男孩。那武官到书房向明先生道:“先生高明之至,拜服,拜服。”便将剖腹见胎之事告知,明先生唬得魂不附体。那武官道:“先生不必惊慌。”遂喊家人拿了五百银子出来相谢,仍差那四个委员坐船将明先生送回扬州。[7]103
清中后期的“委员”还没有今天广为人知的意思,指的是官宦因为专门之事委派的专员。这位明驰远从扬州远赴南京,为武官小姐诊断出喜脉,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武官不动声色地剖开女儿之腹,用一尸两命的惨痛代价验证了明驰远名医的声名。这则残酷的故事固然代入了老鸨这类市井小人的叙事视角,然而恰好印证了清代中后期就已广为流传的剖腹验脉故事模型。故事主人公可以是扬州医生明驰远,更为著名的也可以是乾隆朝名医黄元御,然而故事核心都围绕着诊脉或诊断准确,掌握权力的主人杀害亲人,验证诊断。在这则故事中,值得玩味的是,武官为何一定要“剖腹见胎”,显然不是为了成就明驰远的医名,而且也不大可能只是因为匹夫之勇,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小姐未婚先孕。这也是明驰远“唬得魂不附体”的根源。他一定十分后怕:万一诊断失误,面对如此残暴的患者家属,丧命的恐怕就是自己了。
明清小说中的喜脉诊断伦理困境十分丰富,它们是明清社会医学场景的真实缩影。清代医家郑钦安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在《医法圆通》中对此进行了清晰而全面的剖析:“按闭经一证,关系最重,诊视探问,必须留心。如诊得六脉迟涩不利者,乃闭之证。”他不仅归纳了喜脉诊断伦理困境的现象,更将笔墨集中于讨论造成喜脉诊断伦理困境的原因及解决方案。归结起来,“自古圣贤,无非在人情天理上,体会轻重而已”[1]152。我们据此展开后续讨论。
三、误诊喜脉的伦理困境归因
从《红楼梦》《女仙外史》《娱目醒心编》《风月梦》等一批明清小说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喜脉诊断伦理困境可知,喜脉诊断的困境大多因误诊而来。因此,我们应先来分析一下同样是文学文本中的脉诊,为何传统医学对于喜脉如此容易误诊。
(一)误诊喜脉归因之一:四诊不全,信息误导
喜脉误诊首先应当归咎于四诊不全与信息误导,四诊不全又是误诊的首要原因。所谓望、闻、问、切之四诊本就是中医最大限度掌握患者信息量的诊断手法,然而传统社会的礼法秩序却往往在患者与医生之间建立起一道道鸿沟。明清时代女性就医规约十分严苛。明洪武六年颁布的《祖训录》曾规定:“后妃、女孩儿等病者,轻则于乾清宫诊脉,如果并重者,方许白昼就房看视,不许夜唤医士进宫,违者,并唤医者皆斩。”可能仍担心男女大防,到洪武二十八年重新修订《皇明祖训》时,此条已被删除。明初宫中女性求医的规范为:“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14]明代医家徐春甫的《妇科心镜》针对这一社会习俗进行过批驳:“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帏幔之内,复以绵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四者有二缺焉。”[15]如此浅白明了的道理,难道传统社会的礼仪之家能够以女性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礼制的维护么?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也是令人失望的。《红楼梦》中秦可卿、晴雯、尤二姐等青年女性见外来的医生,都是严守礼制的,提供的信息量实际上非常有限,全书只有贾母请王太医诊脉,主动提出“不必进帐子去”①参见《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贾母所说:“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还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这样瞧罢。”[11]562。清代其他小说也有此类礼俗的体现,颇为显豁的一例是许仲元在《三异笔谈》卷四中讲述的医者陈君为仪郡王格格诊治产后病的故事:
陈君吴江人,以誊录生议叙州佐,知医。一日在寓,见蓝翎人牵马来邀,问何所,但云府中。陈不敢辞,随之往。至一处,入门数重,有内监出引之,朱门绮户,愈进愈邃。至一室,则绣帐双垂,于帐缝中出一手诊之。左右递诊毕,问卧者何人,宦者即叱曰:“请君诊脉,何问为?”乃易词以探,曰:“曾服过药否?”曰服,有单可查。即请单验之,宦曰可,然此单无验,不足效也,阅单,略得大概,病者幼妇,症似产后,约略定方而出。明日,蓝翎人复来,且云“今日王爷在府,恐传见”,乃盛服以往。仪郡王坐炕上,以总裁故,识之。见客入,为起立,命移一椅赏坐。云:“病者乃格格,年十六,去年已下降,今春妊,以少年不慎,半产。昨晚先生药大好。幸终疗之。”且谓左右宦者曰:“传语格格。医须望问,不必避面。”乃复入诊,格格出见,秾桃艳李,真天人也。陈已得解,乃大用芎归,数剂而愈。再入再见,以大缎一卷,荷包两对,银四十两酬之,曰:“曹地山师父荐汝高明,洵不诬也。今而后,吾府中仗君为司命矣。”拜谢而出,转计可一不可再,托词授馆泺阳,遁去。[16]
清代笔记小说中的这段描绘一波三折,从“但云府中”的疑惑,到“于帐缝中出一手诊之”的隐晦,再到“请君诊脉,何问为”的蛮横,被请来作为医生的吴江陈君内心一定是惧怕的。好在根据药单推测出了较多信息,得以初步准确开方下药。如此诊疗,最终使得被仪郡王寄予“吾府中仗君为司命矣”厚望的陈君不得不“托词授馆泺阳”,弃官南逃了。实际上,平心而论,陈君能够在四诊不全的情况下准确下药,除去临危不乱地索得药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运气,因此他最终选择逃走,也与医患关系不平等,获取诊疗信息艰难有着直接关系。
更有甚者,患者为了己方利益有意误导,使得本就四诊不全的医生,更易陷入误诊的泥潭之中。当然,即便是同一个故事,其具体误诊归因也存在有趣的差异:例如,前述《冷庐医话》将医生误诊喜脉归因于仆人对医生“声价自高”的憎恶,偏重于医德层面;而《娱目醒心编》的叙事重点则在保全闺女体面和家族声望,偏重于社会伦理层面。两相参看,恰可作为对此喜脉误诊故事较为全面的归因理解。
(二)误诊喜脉归因之二:叙事能力不足,医患互信缺乏
喜脉误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生的叙事能力不足,医患缺乏互信。传统医学根植于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医生的叙事能力,清代名医吴鞠通在《增订医医病书》中强调医生叙事对于塑造医患关系的重要性:“详告以病所由来,使病人知之而勿敢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危言以悚惧之,必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17]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中则具体分析几种不能直接说出喜脉结论的原因:如“先要问明何人,看丈夫在家否?如丈夫在家,称云敝内,他先请问,方可言说是喜,不是经闭”。除此而外,还有非医学情境如“设或言寡居,或方言丈夫出外,数载未归”“设或言室女年已过大,尚未出阁”“虽具喜脉,切切不可说出,但云经闭”[1]152。误诊喜脉之所以能够构成伦理困境,其主因是涉及家族颜面和声誉,因此医生需要考虑各种情况,综合医学知识进行判断。
细读《红楼梦》等小说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叙事能力越好的医生,往往在文本中医术越高明,越遵守礼仪规范,叙述者似乎有意在这三者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系,这反映出传统社会的一套基本价值理念。在明清小说的世界里,要想成为一个有效避免伦理困境的好医生,既需要避免《忠烈全传》黄医官式的自吹自擂,也应避免《初刻拍案惊奇》中为王夫人诊病医生的犹疑不决,值得学习的榜样是《红楼梦》中张友士的儒医风度,既不刻意贬低同道,又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捍卫医者身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中庸医胡君荣的行为。
(三)误诊喜脉归因之三:医德败坏,草菅人命
误诊喜脉如果只是医术不精或者叙事不明而导致的,最多不过是被羞辱一顿,但如果像《红楼梦》第六十九回中庸医胡君荣那般,医德败坏,心术不正,乃至于草菅人命,那带来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了:
小厮们走去,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名叫君荣。进来诊脉看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贾琏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们请出手来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从帐内伸出手来。胡君荣又诊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贾琏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一时掩了帐子,贾琏就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迂血凝结。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经脉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贾琏命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琏闻知,大骂胡君荣。一面再遣人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11]959
分析《红楼梦》第六十九回胡君荣的行止,有一处颇有争议,便是如何理解“魂飞天外,一无所知”的寓意?传统的看法认为胡君荣好色,被尤二姐的美貌所刺激,“通身麻木,一无所知”,进而误诊。然而细读文本可知,胡君荣并不是贾府中时常走动的太医,而是贾琏因尤二姐不适而命小厮另请来的医生。他并不是贾府所熟悉的王太医,身份底细也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胡君荣一开始认为尤二姐所患为“经水不调”,治疗方案是“全要大补”,继而再次诊脉,又看了尤二姐面色,得出的结论变成了“迂血凝结”,给出的相应治疗方案变为“下迂血通经脉”。从“补”到“通”,胡君荣的方案在调整,关键在于他看到尤二姐面庞那一刻内心究竟在思考什么?根据后文他卷包逃走以及尤二姐堕胎后王熙凤成为最大受益者等信息推断,此处胡君荣很可能发现了尤二姐怀有男胎,兹事体大,内心挣扎,然而受命于王熙凤的暗害活动,才导致他“魂飞天外”。如果此种推论成立,胡君荣的误诊喜脉则极有可能是医德败坏、草菅人命的恶劣行径。
归结起来,明清小说中误诊喜脉可以大致归结于患者信息不全面、医患地位悬殊、医生叙事能力差和医德丧失等缘由。这些方面的文学呈现丝毫不亚于医学文本,也为进一步探索破解喜脉诊断伦理困境之法提供了启示。
四、破解喜脉诊断伦理困境的方法
如何破解喜脉诊断的伦理困境,明清医家也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如前述《医法圆通》曰:“如在三两月内,不妨于药中多加破血耗胎之品,使胎不成,亦可以曲全两家祖宗脸面,亦是阴德。即服药不效,而胎成者,是恶积之不可掩,而罪大之不可解也。倘一朝遇此,主家向医说明,又当暗地设法,曲为保全,不露主角,其功更大。设或室女,于归期促,不得不从权以堕之。不堕则女子之终身无依,丑声扬,则两家之面目何存?舍此全彼,虽在罪例,情有可原。”[1]152增强叙事、曲为保全和挑战禁忌,这三种破局之法,明清小说都有着具身化的叙事探讨,先来看看《红楼梦》提出的解决方案。
(一)“省病诊疾,至意深心”:扩充信息,加强叙事,建立互信
秦可卿是金陵十二钗中最神秘的一位,也是第一个离世的。关于她的患病与死亡,在小说文本内外都曾是争论的焦点。如果我们聚焦于今天能看到的《红楼梦》文本来讨论秦可卿之病:她究竟是不是怀孕了呢?且看儒医张友士给出的回答:
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必然肋下疼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11]147
应该注意到,《红楼梦》继承了前代世情小说以脉象暗示人物性格、命运的表现手法。换言之,此处大段关于秦可卿病证的描摹绝非叙述者随意点染,而是有着深刻的叙事用意。如果我们以叙事医学的视角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张友士大段向患者家属陈述患者脉象绝非背医书、炫学问,而是在向有一定医学知识的贵族子弟秦可卿的丈夫贾蓉详解秦可卿的症状与医理之间的关系。秦可卿病证复杂,甚至最终张友士也没有为她的疾病命名,以至于后世研究者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张友士的一番分析获得了小说人物贾蓉和秦可卿贴身婆子的认可:“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得到如此肯定,张友士此番叙事效果就达到了,那就是建立起了坚实的医患互信。张友士的例子启示我们,在医患沟通中不一定需要全用口语解释复杂的病理现象,如果患者或家属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医学修养,可以“临症问所便”,建立个体化而非模式化的良性医患关系。
《红楼梦》在破解医患伦理困境方面做了坚实探索,它的续书作品同样也有可喜的尝试。例如,嘉庆元年(1796)前后已问世的第一部红楼续书《后红楼梦》,这部书的第十五回叙述薛宝钗生子,补叙了荣国府安胎之法,特别指出:“大凡太太们怀了孕,便静静的一个人养着,也不乱服药。只到临产的前一个月,每清晨将大桂圆二十元,带了壳用小银簪戳遍,配二钱老苏梗浓煎服下,晚上只服人参养荣丸三钱,到了临盆无不顺利。所以宝钗身子甚健,连小孩儿下地声气也高。随有王太医进来看过脉息,说道:‘恭喜恭喜,康健得很,通不用服一帖药儿,只是益母膏一样便够。干净了,单把养荣丸熬做膏子儿服下更好。’”[18]荣国府太太的安胎之法很可能反映出王太医的诊脉理念与用药习惯,与《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王太医辨证准确、用药善做减法的明医形象保持一致。由《红楼梦》等小说可知,喜脉相关诊断首要因素还是综合研判,讲脉清晰,然后才是善于沟通,获得信任。
(二)“曲全两家祖宗脸面”:利用病耻隐喻,积累阴德
传统医学对于医生职业素养的要求是全面而深入的。医生不能仅仅是解决病痛,更重要的是调治身心,全活人命、顾全体面。同时,传统社会对于行医者的潜在界定就包括了积累阴德。这类劝善故事在明清小说中不胜枚举,形成了一种社会潜意识,反过来纾解了传统社会医生的职业倦怠,提振了他们的从医信心。具体到伦理困境比较突出的喜脉诊断场景,传统社会的医者特别长于创设隐喻,至少是利用了民间约定俗成的某些隐喻,消除病耻感,曲为保全,实现医患双赢共生。这类隐喻中最具有民间信仰色彩的就是将那些非正常喜脉归结为“鬼胎”,再用一套言行去妥善处置“鬼胎”。将鬼胎与孕联系起来,宋代洪迈的《夷坚志·癸志》卷八就已出现:
饶州黥卒杨道珍,本系建康兵籍,以罪配隶,因徙家定居,且称道人。素善医,而尤工针灸……一官人宠妾,怀妊八阅月,朝夕恹恹,困卧乏力,饮食不下咽,自不能言其痛挠处。杨为诊脉而曰:“此非好孕,正恐是鬼胎耳。”其家皆哗怒不平,出语诃责。杨曰:“何必尔,他日当知之。吾今不敢用药,但且如常时服安胎药,壮脾圆散可也。”自此稍能餐粥,后两月就蓐。其腹自受孕即皤然与常异,及是乃产一物,小如拳,状类水蛙。始信为鬼胎不疑。[19]
故事中的杨道珍是一位“以罪配隶,因徙家定居”的社会边缘人。他为官吏的宠妾诊脉,冲口而出的是“此非好孕,正恐是鬼胎耳”,惹怒了官吏阖家老小,然而他依然直率而谈,下定了鬼胎的论断。果然两月后生下一个“状类水蛙”的肉球,这家人方才信任他。可见,小说叙述者是将杨道珍当作驱魔师而非医生进行描摹的,他作为医生的形象还未见丰满。
耐人寻味的是,显然带有浓厚民间想象色彩的“鬼胎”到了明清时代,在传统医学知识领域发生了道德化、伦理性转变。明清之际的傅山在《傅青主女科》里就有对鬼胎的病因解释:
室女鬼胎(十四)女子有在家未嫁,月经忽断,腹大如妊,面色乍赤乍白,六脉乍大乍小。人以为血结经闭也,谁知是灵鬼凭身乎!夫人之身正,则诸邪不敢侵;其身不正,则诸邪来犯。或精神恍惚而梦里求亲,或眼目昏花而对面相狎,或假托亲属而暗处贪欢,可明言仙人而静地取乐,其始则惊诧为奇遇而不肯告人,其后则羞赧为淫亵而不敢告人。日久年深,腹大如斗,有如怀妊之状。一身之精血,仅足以供腹中之邪,则邪日旺而正日衰,势必至经闭而血枯。后欲导其经,而邪据其腹,则经亦难通。欲生其血而邪食其精,则血实难长。医以为胎,而实非真胎。又以为瘕,而亦非瘕病。往往因循等待,不重可悲哉!治法似宜补正以祛邪,然邪不先祛,补正亦无益也。必须先祛邪而后补正,斯为得之。方用荡邪散(此方阴骘大矣。见有因此病羞愤而蹈于非命,劳疲而丧于妙年,深为可悯。若服此方不应,宜服桂香平胃散,无不见效。愈后宜调养气血,节饮食)。[20]
傅山的叙述令人震撼,在这位明清之际大医眼中,真的存在所谓“鬼胎”吗?俗语中的“心怀鬼胎”源于当时错误的医学知识。更进一步说,傅山还罗列出怀上鬼胎的几种可能:“或精神恍惚而梦里求亲,或眼目昏花而对面相狎,或假托亲属而暗处贪欢,可明言仙人而静地取乐。”上述种种表现,与传统社会偷情的障眼法极为类似。而傅山作为女科圣手,指出“荡邪散”,还自称“此方阴骘大矣”,似乎也明确指示了曲为保全的医者仁心。在明清时代的森严礼法之下,引起傅山怜悯的应当是一个个被礼法所束缚的追求爱恋的灵魂。他选择为她们打掉“鬼胎”,也算是传统社会一位忠厚医者的仁爱之术了。
(三)“坦陈己见”:挑战禁忌,设法突破伦理困境
通过《医法圆通》的辨析与明清小说的呈现,可以知道,喜脉诊断的叙事伦理困境是普遍存在,而且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很难突破困境,实现医患双赢。清代许恩普的《许氏医案》提供了一种较为有特色的可能——故意挑战禁忌,直口说破“不合时宜”的喜脉。当然,这是建立在医生充分熟悉患方并已建立互信基础上的一种努力:
兵部王铁珊夫人胎中漏血,向言无孕。余以诊脉流利不绝,认定为孕,以安胎养血之品治之。迨四个月后胎动,夫人犹曰无孕。王怒曰:“私子也,何讳为?”夫人亦恚其言秽。余劝曰:“夫妇均年不惑无子,设他医误以病治奈何?此情急之言,毋足怪。”夫妇转怒为喜。后举一子,亲朋贺筵。余曰:“私子也。”众询颠末,具以告,咸大笑。[21]
这条材料有趣而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两次重复出现的“私子也”。第一次王铁珊说出“私子也”,是在情急之下表达了对妻子坚称“无孕”的气话。许医生看出了夫妻感情深厚,丈夫这样说只是情急口角。加之他与王铁珊夫妇关系很熟,因势利导,巧妙化解了夫妻矛盾。第二次说出“私子也”的是许恩普医生,场合在孩子的庆贺宴上。这次他公然再提“私子”典故,宾客不仅没有丝毫尴尬,反而宾主和睦,大笑起来。这则医案中,王铁珊夫妻之所以会产生对怀孕与否的认知差异,主要原因是王妻“胎中漏血”且“年逾不惑”,增加了判断难度。根据《景岳全书》卷三十八:“凡妇人怀孕者,血留气聚,胞宫内实,故脉必滑数倍常,此当然也。然有中年受胎,及气血羸弱之妇,则脉见细小不数者亦有之,但于微弱之中,亦必有隐隐滑动之象,此正阴搏阳别之谓,是即妊娠之脉。”[22]许医生的诊断是比较有把握的。王铁珊夫妇中年得孕事可对今天的医生有所启示,即对于一些患者的避讳与禁忌,在诊断准确和医患彼此了解的基础上,甚至可以主动突破禁忌,坦陈己见,反而会取得较好的医患关系。《红楼梦》中的王济仁、王一贴应该也属于这类熟悉患方内情并敢于适时坦陈己见的好医生。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描摹了众多医患告知的伦理困境,其中喜脉诊断是颇为特殊的一类,它不仅关涉患者身体因素,而且将患方宗族延续、祖宗颜面、社会伦常规范置于医患沟通具身化场景中。喜脉诊断叙事激发出中国传统医学叙事模式的新可能,从而超越了《素问》《灵枢》等早期经典医学文本所提供的叙事伦理指南,进入到人性化、个体化医患沟通模式的探索之中。明清小说的喜脉诊断伦理困境呈现出医术因素、宗族因素、同行评议因素和社会舆论因素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同时,误诊喜脉可以归因于信息掌握不全面、医患地位不平等、医生叙事能力差和医德缺位等缘由;更进一步讲,突破喜脉诊断伦理困境的方式可以包括增强叙事、曲为保全与挑战禁忌三种途径。归结起来,是“自古圣贤,无非在人情天理上,体会轻重而已”。明清小说与医案医话对于叙事伦理困境的探索尽管缺乏系统性,然而却因其具身化与场景性而具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这些文本中的叙事伦理困境之理论思考与实践呈现对于当代叙事医学中国化路径而言,具有借鉴意义。现代中国的诊疗模式与医患关系虽然已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但古代文本对具体医疗伦理困境的深细描摹与曲折表达依然提供了丰富国人的心理样本,为叙事医学中国化实践烛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