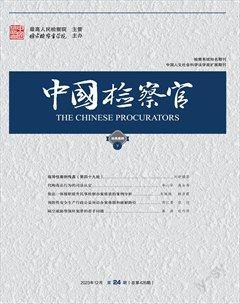利用棋牌类软件开设“云赌场”问题探析
何磊 常靖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至2022年5月间,郭某某通过微信组织李某某等20余名参赌人员,多次在“心悦麻将”游戏平台其创建的虚拟“房间”内,以天津麻将“刮大风”玩法计算输赢的方式进行赌博。其间,郭某某利用事先购买的“房卡”在上述游戏平台建立游戏“房间”,将房间号码通过微信群发送给参赌人员,由参赌人员进入“房间”赌博,郭某某每日通过游戏平台查看该房间内的输赢情况,按一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兑换一积分的比例,使用4个微信账号分别向赢家和输家结算赌资,并按每局每人2至3元的价格获取好处费(其中,2021年10月,郭某某每局从中收取2元;2021年11月至案发前,每局从中收取3元)。经查,涉案赌资累计506133.1元,郭某某从中非法获利58829元。
二、分歧意见
对于案件中郭某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郭某某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郭某某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但不属于网上开设赌场行为。其以庄家的身份设定赌博规则、提供网络赌博场所,并利用微信群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他人参与网络赌博活动,这种行为并不属于“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规定网上开设赌场的四种形式,且与传统有形的开设赌场罪并无本质差异,因此认定开设赌场罪,并按照实体赌场的标准量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郭某某的行为构成网上开设赌场犯罪。无论是利用赌博网站赌博还是利用手机游戏APP等媒介赌博,均具有互联网的虚拟特性,应当参照适用《意见》第1条关于“建立赌博网站”的相关条款,并依法认定“情节严重”进行量刑。
第四种意见认为,郭某某的行为构成网上开设赌场犯罪,但量刑上不应升档处理。“赌场是一个有着特定空间的可以供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赌博活动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解释为一个网站,也可以解释为一个微信群,当然还可以解释成其他网络虚拟空间里可以供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赌博的网络平台。”[1]但网上开设赌场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过低,从罪责刑相适应角度,不应使用该认定标准。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利用手机软件进行赌博活动,属于“网上开设赌场”
首先,从开设赌场罪的立法沿革看,《意见》中对于开设赌场的四种行为模式的规定是提示性规定而非法律拟制,并不排除四种行为模式之外的网上开设赌场行为。开设赌场是古今中外为大众普遍熟知的一种行为,因此,该行为入罪后,刑法没有对罪状作具体描述。1997年刑法第三百零三条原文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规定了赌博罪的三种行为方式: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入罪数额标准。但是,赌博罪作为行为犯,如何与治安违法行为相区分,造成了实践中的一定困扰。因此,“两高”《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了聚众赌博的入罪标准,第2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刑法第303条规定的‘开设赌场”。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并非要对“聚众赌博”或“开设赌场”作一定义,而是对于民众普遍认知意义下的赌博行为之外的赌博模式的补充规定,因此从性质上说,属于提示性规定而非法律拟制。之后,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独立为该条第2款,原文为“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样也没有具体描述何为“开设赌场”,也没有规定开设赌场的入罪及量刑升档的数额标准。至此,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中,只有聚众赌博有入罪标准,以赌博为业和开设赌场仍属行为犯。在此背景下,《意见》第1条规定了网上开设赌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其中第1款将上述《解释》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具体细化为四种行为,第2款规定了“情节严重”即网上开设赌场的量刑升档标准,形成了线下开设赌场和网上开设赌场的入罪均为行为犯,网上开设赌场的量刑升档有具体数额和情节标准、线下开设赌场没有升档标准的模式。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意见》是在《解釋》的基础上对于与赌博网站有关的开设赌场行为的细化,是基于当时司法实践的一种提示性规定,并非对其他模式的网上开设赌场行为的一概否定。比如,“两高一部”《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第2款又列举了五种“利用信息网络、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视频、数据,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跨境赌博活动”的开设赌场行为,但是没有再冠以“网上开设赌场”的描述。
本文认为,在未对网络赌场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限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不能将其他行为排除在开设赌场罪之外。利用手机软件进行赌博活动,虽不属于《意见》规定的“建立赌博网站或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型的“网上开设赌场”,但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网上开设赌场”。即使在没有上述司法解释的前提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当某种行为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时,仍然可以依照刑法第303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但该条款对于网上开设赌场的认定无疑过于简单。
本案中,郭某某利用“心悦麻将”游戏平台开设赌场,不属于《意见》规定的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或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以及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的“网上开设赌场犯罪”行为,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虚拟网络空间的不断延展,利用网络游戏平台、手机APP等乃至于更新类型的依附于网络空间而诞生的产物,进而开设赌场的行为,应属于“网络赌场”范畴,而不仅仅局限于“赌博网站”。最高法105号和106号指导案例[2]将赌博网站的外延扩展适用于赌博微信群即体现了这一点。
(二)本案不应适用或参照《意见》中“情节严重”的标准
如前所述,《意见》是对“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的网上开设赌场行为的具体规定,因此其第1条第2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只适用于这种与赌博网站有关的开设赌场行为。该规定之外的网上开设赌场行为,即使认定为网络赌场,是否应认定“情节严重”存在新的问题。若依据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不适用网络赌场“情节严重”的规定,则会导致无论行为人网上开设赌场获利多少、侵害社会管理秩序程度如何,均只能适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显然是不合理的。
若适用,则存在于法无据或上述认定标准过低的问题。在《意见》运行的十余年间,网络让金钱变成数字,降低了剁手痛感,导致实践中涉案金额屡创新高。网上开设赌场犯罪已远远超出当年立法所能涵盖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提高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但认定“情节严重”标准不变,单单提高法定刑的做法,是否会走向量刑畸重的极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意见》规定的赌资数额、抽头渔利、违法所得的计算为例,存在如下具体问题:
1. 抽头渔利数额认定。抽头渔利,一般指开设赌场者,按一定比例从赌局中攫取的回扣。有观点认为,抽头渔利还包括组织者从上级手里提取的佣金和红利[3],也有观点认为收取的赌场“场地费”也包含在内。两种观点均属于对抽头渔利进行的扩大解释。《意见》规定了情节严重情形,但并未对抽头渔利的定义进行明确。但《解释》规定了日常生活中的棋牌室如果只是收取座位费或者场所费等,进行较小金额的棋牌娱乐活动,不以犯罪论处。因此,将抽头渔利数额作为“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时应作严格解释不能随意扩大。结合本案,郭某某按每局每人2至3元人民币的价格抽取好处费的行为,类似于线下棋牌室座位费或场地费,不应认定为抽头渔利。
2. 赌资数额计算。对于线下实体赌场的赌资计算,以所有参赌人员的现金和有价证券等的总和确定,而非投注金额。本文认为,赌资即用于赌博活动的全部资金,计算赌资应从整体把握,包括参赌人员换取虚拟代币的全部款物,以及通过赌博赢得的全部款物。根据李某某等23名参赌人员与郭某某4个微信账户转账记录统计计算,本案赌资为累计506133.1元。当然该种方法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赌客流动性大,查实人数较为有限,因此如何更为全面、高效、精准计算赌资数额,仍需进一步探索。
在认定其属于网上开设赌场行为的前提下,按照《意见》规定,赌资数额累计已超30万元,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显然,一是2010年《解释》的标准,无法与当今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相匹配,从30万元到上亿元的赌资并不鲜见,量刑幅度差别有限,无疑是鼓励更高金额的赌博;二是反映出的社会危害性,无法与多人、跨省、跨境、分级代理、团队运维等网上开设赌场行为同日而语。如吴某等63人开设赌场系列案,涉案赌资达2.5亿元,11名骨干成员被判处3年至6年不等的刑罚。[4]若郭某某适用“情节严重”标准,无疑产生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结果。
3. 违法所得计算。《意见》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涉及违法所得数额的有两款,包括建立赌博网站供赌博使用、参与赌博网站利润分成作为前提条件。因此对于本案中利用棋牌类软件开设赌场的行为,并不符合该规定。但实践中违法所得的计算,有助于退赃退赔的实现。对于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学界存在净利原则[5]、总额原则[6]、相对总额原则[7]的不同观点。尽管后两种观点的打击力度更大,并不扣除网上开设赌场中所支出的人员、管理及第三方服务等费用,但存在累计计算的弊端。因此,本案中,根据银行流水及郭某某微信账单计算,其支付心悦麻将网站总金额÷每张房卡金额=购买房卡总数,除去剩余未使用数量,得出实际使用房间数。房间数*每间人数*收取参赌人员房费=总计收取房费金额,减去购买房卡的支出外,得出实际获利58829元。郭某某在审判阶段已全部退赃。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局牌结束时赌客退出的情况,游戏平台会少扣除房卡,同时购买房卡初期,平台赠送了少量房卡,因此出现无法除尽的结果,但该种计算方式已然是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前提下计算方式的最优解。
因此,本案中,郭某某利用不带赌博结算功能的棋牌类手机软件,帮助参赌者开设游戏“房间”进行赌博,再利用游戏自带的数据统计功能统计输赢情况,在线下分别与参赌者结算赌资,这种开设赌场的模式实际是将线下利用普通棋牌室开设赌场的模式转移到了线上,其盈利模式主要是按照赌博的局数收取固定的房费,而非传统开设赌场或者利用赌博网站开设赌场的抽头渔利模式,其特点是参赌人数、赌资规模都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但是盈利数额远远低于上述两种模式。因此,基于《意见》距今已有十余年,其规定的数额标准已远不能适应如今的司法实际,再加上本案的模式与利用赌博网站的开设赌场模式有明显区别,更贴近于线下开设赌场,故也不能参照《意见》的量刑升档规定。
(三)新型网上开设赌场案件如何适用《意见》的量刑升档规定
基于立法及司法实务中的诸多问题,在办理网上开设赌场案件时,往往采用“实体赌场虚拟化”的思路,将线上赌场视为线下赌场的网络化形式进行定性,再比照线下实体赌场的量刑标准,采用“网络赌场实体化”方法进行量刑;广东佛山为了统一量刑尺度,将绝大部分代理均认定为从犯,避免部分案件粗暴认定 “情节严重”后带来的量刑档次提升[8];个别地区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明确网络开设赌场范围及“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但无论何种措施,并未实质上解决问题。
“网络赌场”并非法外之地。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网络开设赌场势必将成为未来开设赌场的主要犯罪方式之一。尽管立法者在尽力对赌博犯罪量刑的参考项进行细化,但网络赌场区别于线下赌场设定更多更为复杂的规则,使得传统定罪量刑标准并非当然适用于网上开设赌场行为。当法律已表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态势时,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而应不断探索完善路径,赋予利用手机端棋牌类软件等依托互聯网、移动通讯终端的新型网上开设赌场行为以应有的法律地位。
事实上,网络开设赌场虽有其特殊性,但其本质上只是开设赌场罪的一种形式,不应割裂线上与线下开设赌场行为,亦不应不加区分地同等评价。
一是应准确界定“网络赌场”,强调赌博活动的聚集可能性,严格把握其开放性、组织性、经营性等特征,不宜局限于《意见》规定的四种情形。
二是对于《意见》的量刑升档规定是否参照适用,应根据案件的行为模式与该规定是否具有同质性予以判断。第一,如果行为模式近似,如虽然没有开设或利用赌博网站,但是利用本身具有赌博功能的电脑软件、手机软件及其他通信终端的,与赌博网站功能相同,均具有赌博网站下注、资金结算等功能,应参照《意见》的升档规定。第二,对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如实践中常见的行为人依靠其获取的赌博网站账号,召集人员在线下场所内,在其账号内投注,但对于是否属于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情况存在争议的,应当属于网上开设赌场,同样参照《意见》的量刑升档规定。第三,新型开设赌场模式,如本案,没有利用具有赌博功能的网站、软件、通讯群组,而是利用网络的联系便利性、隐蔽性,在网上进行赌资流转、参赌人员管理等非关键环节的,更类似于线下棋牌室,放任参赌人员在棋牌室内赌博,不参与抽水而仅收取房费,所获利金额远远低于抽水的,应参照线下开设赌场的规定处罚。
三是完善法律规制,统一“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如上述“棋牌软件型”开设赌场与“赌博网站型”开设赌场存在明显不同,应当综合考虑行为客观方面诸要素,包括累计和日均的抽头渔利数额、赌资数额、参赌人数、经营时长和社会影响等。针对个案的差异化量刑是必然的,但统一“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无疑是罪刑法定、禁止类推原则以及发挥刑法指引作用的必然要求。亟待由立法机关根据充分的调研,形成全国性的统一规定,以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2022年7月,公安机关以郭某某涉嫌开设赌场罪移送审查起诉;同年10月,检察机关以开设赌场罪对郭某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于2022年10月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决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