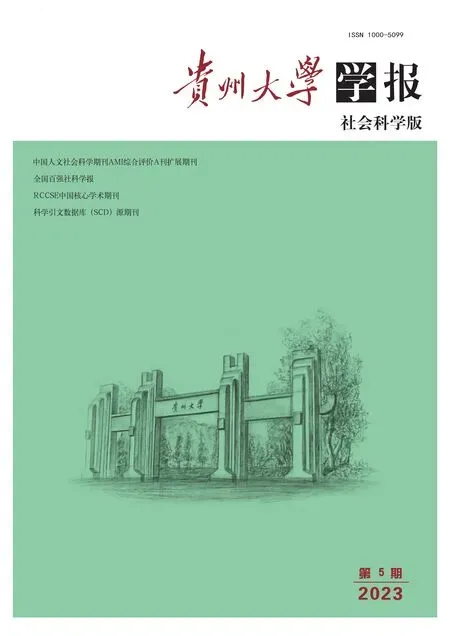康德历史哲学的思维方法
刘凤娟
(华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一种学说能够称得上“哲学”,必然具有某种普遍方法论或思维方式做指引。成熟的思维方法是使思想成为哲学、使思想史成为哲学史的东西。在康德历史哲学中,其思维方式使之区别于经验视域下的一切历史研究,也使其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历史哲学,甚至区别于其自身体系中的其他思想部门。虽然国外学界已然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如杜普瑞(Louis Dupré,1998)、戈尔德(Anderson-Gold,2001)、盖耶尔(Paul Guyer,2009)等关于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克莱因盖尔德(Pauline Kleingeld,1999)、赫西(Henrik Hdez-Villaescusa Hirsch,2010)等对其历史哲学中道德公平等难题的考察;阿利森(Henry E.Allison,2009)、伍德(Allen Wood,2009)、克莱因(Joel Thiago Klein,2013)等关于康德普遍历史理念的定位问题的争论;施奈文(J.B.Schneewind,2009)、施韦特(Kristi E.Sweet,2013)等关于非社会的社会性概念的解读,但国内的康德历史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方法论上的自觉,这一点与国外的研究构成鲜明对照。邓晓芒(1986、2003)、李秋零(2011)、丁三东(2005)等学者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921)、何兆武(1990、2005)关于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或“第四批判”论点的反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康德历史哲学思维方法的讨论。
邓晓芒认为,康德(Immanuel Kant,1784)有关历史方面的思想“是从他的自然目的论思想引申出来的,因此要理解康德的这些思想,首先必须了解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方法论原则”[1]。甚至直到晚年时期,他也“没有完全脱离‘反思判断力’的类比原理”[2]4,“因而最终尚未真正进入到历史理性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领域”[2]4。李秋零指出:“历史理性作为一种理性能力,无论是作为认识理性还是行动理性,都不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可以和前三者并列的理性能力。人为地为康德批判哲学体系划出一个‘第四批判’,实际上已违背了逻辑的划分规则。尤其是在现代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理性批判,更是已经包含在康德的‘第一批判’之中了。”[3]丁三东有类似观点:“康德并没有所谓的‘第四批判’的思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已经为历史学确立了基础。”[4]本文将在诸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尽管历史哲学的思想内容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部门,并服务于道德形而上学,但其思维方法或方法论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文本中得到了奠基。因此,不可能存在一种独立于三大批判的各种先天能力的历史理性。具体地说,历史哲学的思维方法是以合目的性原则为主领、以隐秘的历史辩证法为辅助和手段的复合方法论。本文将以此为主题展开论述,评价康德的如此这般方法论在其自身体系和近代历史哲学沿革中的地位、贡献、局限性。
一、历史哲学的合目的性思维方法
康德对合目的性观念的重视及其与机械的运动规律的分殊,早在前批判时期就有所体现。对于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他指出:“如果秩序井然且美好的世界结构只是服从其普遍运动规律的物质的一种结果,如果各种自然力量的盲目机械性能从混沌中如此美妙地发展出来,并自动地达到如此的完善性,那么,人们在观察世界大厦之美时所得出的神性创造者的证明就完全失效了……人们已经习惯于发现和强调大自然中的和谐、美、目的以及手段和目的的完善关系。”[5]康德在前批判时期还未摆脱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超自然影响的独断思想。世界的完美秩序不是仅仅靠机械规律就能解释得清楚的,而是需要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完善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最高根据就是作为神圣创造者的上帝,整个世界在康德看来是毋庸置疑地符合于上帝的创世意图。这是合目的性观念的较早表达方式。这种观念虽然被看作是与机械规律同样的客观有效,但似乎还没有被康德明确地当作是一种普遍方法论。随着《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其独断思想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但基于上帝概念的合目的性观念却以调节性原则的方式得到了普遍方法论的提升。
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明确揭示了纯粹理性的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在他看来,“理性真正说来只把知性及其合目的性的职能当作对象……因为它为知性行动的目的设立了某种集合的统一性”[6]386。理性的这种合目的的系统联结功能甚至是人类一切先天认识能力中最源始的能力。在时间秩序上,人的认识能力的运作开始于感性,然后是知性,最后是理性。而按照所有认识能力的逻辑秩序,理性首先“按照理念来考虑自己的对象并据此来规定知性,然后知性就对自己的……概念作一种经验性的运用”[6]337。理性寻求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的这一法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统一性就不会有任何理性,而没有理性就不会有知性的任何连贯的运用,并且在缺乏这种连贯运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经验性真理的任何充分的标志了,所以我们必须就这种标志而言把自然的系统统一性绝对地预设为客观上有效的和必然的”[6]390。在康德这里,自然的系统统一性就是一种合目的的统一性,并对应于知性运用的合目的的统一性;换言之,人类认识能力中知性对理性的合目的性,与自然现象的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是相对应的。前者就是后者被称为一种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验认识条件。
理性所寻求的知识的系统化,实际上就是“知识出自一个原则的关联”,而“这种理性统一性任何时候都是以一个理念为前提的”[6]387。理念为知识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在逻辑上先于知识中的分殊的各个部分,并对各个部分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诸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结予以先天的规定。在康德哲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往往是在一种合目的的系统论中得到阐述。在知识的系统整体问题上,知性的分殊性知识就是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因果联结的诸要素(或部分),由此联结成的则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系统整体;该系统整体本身对于诸知识要素来说也是一个目的。而能够提供知识的最大整体或目的的理念,是上帝。上帝理念所提供的是一种“完备的合目的性的统一性”,即绝对的完善性或“合目的性的最大统一性”[6]411-412。因为在康德看来,尽管人们不能独断地论证上帝的客观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经验的对象仿佛是从这个作为其根据或是原因的想象出来的理念对象中推导出来。这样一来例如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必须被看作好像是从一个最高的理智那里获得其存有似的”[6]400。因此,理性对知性及其分殊性知识的最大的系统把握,是一种出自原则的、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这种原则需要预设上帝理念。上帝理念为理性的源始的和必然的统一性提供了整体性和最高目的的图型,“知性概念在理性图型上的应用……是一切知性运用的系统统一的一条规则或原则”[6]397。
按照理性的这种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一切自然现象在遵循机械法则的同时必须被看作是合目的性的,由此联结成自然科学知识的系统整体。历史哲学以描述人类经验性行动为使命,而行动也是一种现象。就此而言,人类行动也必须被设想为、被描述为按照理性的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能够联结成一个系统整体,这就是康德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普遍历史理念。普遍历史或者人类社会的历史整体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的目的系统的一部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虽然将世界的合目的性观念提升为理性的普遍的合目的性原则,并由此为历史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明确而成熟地将历史性意识融入合目的性原则的是《判断力批判》这一著作。我们可以说,“第一批判”仅仅只是奠定了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未给予充分阐述。我们只是从理性的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和自然现象的合目的的系统联结中,推论出普遍历史中人类行动的合目的的系统联结。
合目的性原则与历史哲学在“第一批判”中的关系是隐秘的,而在“第三批判”中则是明确的。这是因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赋予系统哲学或目的论明显的时间或历史性维度。首先,具有内在合目的性并被叫作自然目的的有机物,“必须自己与自己处于交互作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中”[7]169。这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目的和手段的因果关系。按照这种目的论的因果秩序被思考的有机物,其各部分只有通过与整体的关系才可能,并且各部分在交互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中产生出整体。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同样将“整体的理念”看作是“作评判的人对包含在给予质料中的一切杂多东西的形式和关联的系统统一进行认识的根据”[7]170。但他继续强调:“一个这样的产品作为有组织和自组织的存在者,才能被称之为自然目的。”[7]171一个自组织的存在者就是按照部分与整体的系统结构在时间中“自己产生出自己”[7]168的自然物。康德在差不多同时期(1788年)的《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一文中,也曾明确将有机生物看作是“属于自然历史”[8]的。这区别于那种只是有组织,但不能够自组织的机械物(如一只钟表),后者不具有在时间和历史中的自我生产性和发展性。
其次,康德以有机物的自组织的合目的性为跳板将全部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发展着的系统整体。自然界作为一个目的系统整体是从诸存在物的存有及其外在合目的性来看的,而能够作为自然的最后目的的东西是人的法制文化。康德指出:只有在法制状态中,“自然素质的最大发展才可能进行”[7]221。康德将全部人类历史看作是向着一种世界公民整体行进的合目的性过程,人自身的各种自然素质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但由于人类历史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合目的性表现为一种手段和目的的等级性的系统整体,因而包含的是一种外在的合目的性,这就需要一个超越于自然之外的终极目的作为其目的链条上的最高根据。而“一个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即创造本身的终极目的”[7]222。这里的创造本身可以理解为上帝的创世活动,上帝创造世界的意图是包含在世界的终极目的概念之中。整个世界包括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上帝的创世意图中预先地被规定好了。
康德在合目的性原则中隐秘地包含了传统理性神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所不同的是,他将这种合目的性原则看作是调节性的。“第三批判”与“第一批判”在合目的性原则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将该原则看作是“自然科学的内部原则”[7]177,并且是调节性原则;其差异在于,“第三批判”不再将其看作是理性的本土原则,而是婉转地将其视为“反思性的判断力的一条由理性托付给它的准则”[7]192。康德借此凸显了反思性判断力在知性和理性之间的联结和中介作用,但并未消减理性在诸认识能力中的源始地位。康德历史哲学的主要方法论就是这种在“第一批判”中得到奠基、在“第三批判”中得到清晰阐述的先验合目的性原则。虽然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不是历史性的,但却可以容纳历史性维度。由此,历史哲学得以确立。
二、历史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
康德有关人类历史的宏观架构是在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之下得以论述,但为了充分解释现实世界中诸多矛盾、冲突与最后的完善目的的统一性,他还引入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并不是作为普遍方法论,而是作为合目的性原则的辅助手段,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类社会内部的对立统一格局被类比于自然界中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描述了自然事物的合目的性的系统统一性,但按照机械原则来看,物质之间具有吸引力和排斥力。他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指出:“排斥力与吸引力一样都属于物质的本质,而且在物质的概念中哪一方都不能与另一方分离开来。”[9]523康德在“第三批判”的“目的论判断力的辩证论”部分,揭示了机械规律与目的因规律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以机械规律从属于目的因的规律(即合目的性原则)而可能。这实际上对应于“第一批判”中知性原理对理性原则的从属性。在历史哲学中,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被描述为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人们进入社会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却与不断威胁要分裂这个社会的一种普遍对抗结合在一起。”[10]27社会化的倾向是使人趋向于形成社会、相互合作的偏好,而分裂社会的那种倾向则是使人个别化、孤立化的偏好。康德将这两者共同包含在一个概念中,即“非社会的社会性”[10]27。这一概念本身就揭示了人的本性的内在矛盾和对立。而人性内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矛盾关系同样从属于那种合目的性的原则,并充当其辅助手段。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康德在物质实体和人类社会之间设置了这种类比,但他并没有同等看待物质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确切地说,康德并没有在自然事物的矛盾关系和合目的性关系中安置一种自然的辩证法,而只是在人类社会中描述了一种历史的辩证法(1)这里使用的两个“辩证法”只是一种概念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说,康德哲学中已经有作为明确的方法论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就在于,人性基于其内在矛盾和对立,可以被看作是自我驱动和自我完善的。这就在普遍历史的宏观视域中为人性赋予了一定程度的主导性。人类的一切经验性行动并不只是单纯地被设想为上帝隐秘计划操控着的对象,而是在相互矛盾和普遍对抗中促进着自身禀赋的发展。尽管在历史中被成就的人性并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2)历史的真正主体是先验理性或先验的反思性判断力,历史是在人类先验认识能力的合目的性原则之下才呈现为一个发展着的系统整体。,但他能够将其辩证发展过程统摄在先验合目的性原则之下,这已经是一种进步。
具体地看,康德历史哲学中的辩证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是在人性内部对立着的,而不是一种外在对立;完善的法制社会秩序被看作是基于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对立而被驱动并促成的。这构成近代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的较早表现形式。
康德在1784年的《普遍历史》中表达了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对立思想,这种思想在1794年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下简称为《宗教》)中演变为恶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的共存的观念。他指出:“非社会的社会性……这方面的禀赋显然蕴涵在人性之中……他在自身中也发现了非社会的属性。”[10]27-28人性内部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对立是可以从个体角度去思考。每个人都必须“在他的那些他无法忍受,但也不能离开的同伙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10]28。康德强调了“忍受”和“离开”这两个词语,就如同他强调每个人在拥有一种社会化偏好之时,也同时具有孤立化的偏好那样。人的本性就在于“兼具”两种倾向。在《宗教》中,他对社会性与非社会性进行了更清晰的界定,对两者共存的方式也做了详细解释。社会性被看作是向善的原初禀赋,并被区分为三种:无须理性参与并作为动物性禀赋的社会本能、基于理性并作为人性禀赋的比较而言的自爱、基于纯粹理性并作为人格性禀赋的道德情感。非社会性被看作是趋恶的倾向,并同样被区分为三种:人的本性的脆弱、人的心灵的不纯正、人心的恶劣。康德在《宗教》中将人的本性中善恶两种原则看作是任性的属性,它存在于准则对道德法则的采纳或是违背的主观根据中,而这种主观根据自身又是一个准则。由于准则不同于作为现象的外在行动,所以,人性的内在矛盾不仅意味着在每一个个体内部存在着善恶两种原则(社会性与非社会性),还意味着善恶原则是在人心中、在准则中的对立。这种内在对立造成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外在的普遍对抗。这种由内而外的研究视角也区别于他对自然中物质实体的考察。诸物质实体之间的吸引和排斥不是由于其内部规定,而是由于它们都占据着空间中的特定部分。物质就是占据空间的事物,只具有外部规定性,“没有绝对内部的规定”[9]559。这一点区别于康德前批判时期(3)参阅康德的《形而上学认识各首要原则的新说明》(1755年)。的物质实体观念。康德在批判时期仅保留了人性的内部规定,而放弃了对物质实体内部规定的立场;这一点也对应并解释了他唯独在人类历史中而不是在普遍的自然历史中设置辩证思维方式的做法。真正的辩证思维应该奠定在存在者的内部矛盾上,而不只是诸事物间的外在对立上。
康德在《宗教》中进一步描述了善恶两种原则共居于人性的方式。这两种原则虽然共同存在于人性内部,但并不具有同等价值权重。康德在多部著作和文本中始终将善看作是人性的应然的走向,这一点对于任何熟悉其道德思想的人都是不陌生的。但恶则是对善的原则乃至普遍道德法则的背离。康德使用了两个巧妙的词语:嫁接、附着。他指出,在动物性禀赋之上,“可以嫁接各种各样的恶习”[11]25,在比较而言的自爱之上“可以嫁接这样一些极大的恶习,即对所有被我们视为异己的人持有隐秘的和公开的敌意”[11]26。这些恶习都不是从善的本性中自动滋长出来的,而是在人性中另外具有一种最高的主观根据,即“准则背离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主观根据”或“趋恶的自然倾向”[11]28。并且即便是这种趋恶的倾向也“只能附着于任性的道德能力”[11]30之上。所以,在康德这里,无论是内在的趋恶倾向(恶的原则)还是表现出来的种种恶习(恶的行动),都不具有与善的原则同等的地位。虽然善恶原则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但他在两者之间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就为它们在普遍历史中的统一性确立了方向:善恶两种原则或者社会性与非社会性,必然以前者战胜后者的方式而达到统一。而这种历史性的统一的驱动力不是别的,就是善恶之间的内在对立。
康德对人性自我驱动的描述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对人性自我驱动的宏观景象的描述。“每个人在提出自己自私的非分要求时必然遇到的对抗,就是产生自非社会性……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人的一切力量……这时,就迈出了从野蛮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真正说来就在于人的社会价值;于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得到发展……就这样使形成一个社会的那种病理学上被迫的协调最终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10]28换言之,“一切装扮人的文化和艺术及最美好的社会秩序,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10]29。社会性与非社会性不仅在人性内部互相对立着,也在历史进程中走向统一。这个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人格性禀赋中的善的原则最终战胜恶的原则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从社会本能逐渐过渡到在纯粹理性基础上自由自主自觉自愿地构建道德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社会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上的普遍对抗,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因此,完美的社会秩序看起来恰恰是非社会性的结果。非社会性“被自身所逼迫而管束自己”[10]29,人类追求自我利益的活动反而造成对自我利益的规制和约束。
第二种是康德对战争与和平法制关系的描述。《论永久和平》揭示了“从自然状态的战争状态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状态”[12]382。《判断力批判》则更明确地指出:“尽管战争是人类的一种(由于不受约束的情欲的激发)无意的尝试,但却是深深隐藏着的、也许是无上智慧有意的尝试,即借助于各个国家的自由,即使不是造成了、但毕竟是准备了各国的一个建立在道德之上的系统的合法性……战争更多的却是一种动机……要把服务于文化的一切才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7]221战争对和平的驱动力最鲜明地体现在其自我否定上,战争是以对战争的否定而实现和平的。
第三种是在信仰历史或教会历史中启示信仰对纯粹信仰的驱动作用。康德在《宗教》中“关于在地上逐步建立善的原则的统治的历史观念”一章指出,教会历史“从它的最初的开端,就包含着趋向真正的、普遍的宗教信仰的客观统一的种子和原则,它在逐步地接近这样的宗教信仰”[11]127。而这种发展过程是以如下方式呈现的:“一种历史性的信仰作为引导性的手段,刺激了纯粹的宗教,但却是借助于这样的意识,即它仅仅是这样一种引导性的手段。而历史性的信仰作为教会信仰包含着一种原则,即不断地迫近纯粹的宗教信仰,以便最终能够省去那种引导性的手段。”[11]116这里的历史性信仰就是启示信仰,而且需要借助经验证明或感性方式来把握的东西。人类信仰观念的变迁史与人性的完善、道德的进步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对启示信仰的依赖是人性尚未达到其最完善程度的具体表现。在宗教领域,启示信仰也是以自我否定的方式逐渐促进纯粹信仰的确立。
康德对战争、启示信仰、非社会性、趋恶的倾向的态度本身包含着辩证因素。他一方面批判其道德缺陷,另一方面又肯定其道德驱动作用;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评价只有在一种历史的和辩证的视域中考察才是合理的。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方式并非已经就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人们最多只能说,康德在其历史哲学中已经触及历史辩证法,但只是将其作为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的辅助手段。合目的性原则呈现了普遍历史的宏观整体性,历史的辩证法(一个权宜的概念)则有助于人们理解普遍历史的具体演进方式。合目的性原则对辩证思维方式的这种涵摄,符合康德哲学整体的先验逻辑方法论。辩证思维是作为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的手段、内容而被统一在历史哲学中。人类行动全都趋向于一种道德上的形而上学目的,但诸行动间的协作、对立,甚至对抗等复杂关系需要在一种辩证思维之下,才能被合理地理解为符合该目的。
三、康德历史哲学方法论的贡献与局限性
康德这种以合目的性原则为主领、以隐秘的历史辩证法为辅助和手段的复合方法论:一方面超越了经验历史观和神学历史观,使历史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历史哲学成为科学的思想门类;另一方面引领了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为之后黑格尔(G.W.F.Hegel)、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等人的辩证历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德哲学深受休谟(David Hume)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上同样如此。他继承了两者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在历史哲学中构想了一种人性自我驱动、自我完善的观念。但康德有自身的独创性。具体而言,他超越了休谟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观念和卢梭的依赖于外部因素和趋向堕落的人性观。休谟指出:“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历史的主要功用只在于给我们发现出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来。”[13]托马斯·斯图尔姆(Thomas Sturm)指出:“至少到1775—1776年,康德也接受人性是恒常的这种本体论论点,甚至将其与自己的人类学概念联系在一起。”[14]而在1784年的《普遍历史》中,康德则明确将人性看作是可变的:“一种造物的所有自然禀赋都注定有朝一日完全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展开。”[10]25这种可变的人性观实际上是对卢梭的某种继承。众所周知,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描述了具有原始同情心的人类如何逐渐被败坏的过程。并且,人性的堕落是“通过一系列可能不会发生的外部偶然因素”[15]才可能。但与卢梭不同的是,康德不仅构想了人类从原始的善中堕入罪恶的过程,同时构想了人类基于其本性的内在对立而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从善到恶又复归于善的完整历史进程体现了人性自身的主体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恰恰是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得到描述。
当然,康德的历史观也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目的论的影响。他将人类历史看作是按照神意的隐秘计划展开的完整过程:“人们在宏观上可以把人类的历史视为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10]34这种历史观与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论点一脉相承,后者在《上帝之城》中“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人类戏剧的浮沉……这出戏剧和世界历史是同一的……从起源到终结,整个世界是以建立一个神圣社会作为唯一目标的,而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一切事物,甚至连宇宙本身才被创造出来”[16]。但有所不同的是,康德并不把人类历史合乎神意的目的论描述看作是独断的,他在历史哲学中的合目的性原则不是人类理性对历史事实和人类行动的独断规定,而毋宁是理性对认识能力自身的反思性原则。他的目的是使人权宜地理解历史的整体性和完备性。所以,这种合目的性原则不是像知性法则那样的构成性原则,而是一种调节性原则。
康德借助于这种调节性的合目的性原则及其附属的辩证思维方式,使经验性的人类行动被统摄为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系统整体,从而也使历史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历史哲学在其科学的哲学体系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一种哲学的理论形态不是仅仅建立在某些新观点之上,更需要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在近代,维科(Giambattista Vico)以“论题法”开展历史研究,并区别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批判法”视域下的自然科学研究。这构成了历史哲学的发端。康德则以合目的性原则与辩证思维的复合方法论奠定了德国古典时期历史哲学的研究基调。
黑格尔虽然对康德的先验逻辑有诸多批判,但其历史哲学中的“理性的狡计”和辩证发展观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历史哲学的继承。李秋零教授将“从康德的‘自然意图’到黑格尔的‘理性狡计’”当作是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一条重要线索,并充分肯定了两者的内在联系[17]。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形态都是对传统神学目的论的改造,因而自身都带有合目的性的思维方式。但他们又都在这种目的论思维框架内嵌入了历史的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同样不是某种外部偶然因素,而是“自由的观念”和“人类的热情”[18]23,“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18]23,而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工具和手段。人们在追逐私人利益、特殊目的甚至由此相互对抗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着精神的自由本性。这与康德从非社会性中产生社会性的思路具有某种相似性。对此而言,康德的神意并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而只是一种调节性观念;黑格尔的理性及其自由观念则是在历史背后起支配作用,但自身并不参与到社会普遍对抗的隐秘主体。
康德的历史辩证法毕竟是非常不彻底的、带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自然和自由的二元论上。康德一方面截然区分了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想要通过一种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将二者联结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理论上的断层,好像人类生存的整个图景就是由自然、自由以及两者之间的普遍历史对接起来的拼图一般。这种理论困境是康德的复合方法论所无法解决的。这一点可以在其“正义元首”论题上体现出来。
普遍历史是以描述人类经验性行动为内容,但历史是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目的。人性在历史中的自我完善对应于“一个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10]29,这是大自然或神要求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而一个普遍管理法权的社会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能够和谐共处的社会,因为“普遍的法权法则”就在于,“如此外在地行动,使你的任性的自由应用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19]。但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和谐共处的共同体需要一个“自身公正的公共正义的元首”[10]30。康德将这种元首描述为:“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并具有“善良意志”的人。而结合这一时期他对善良意志的理解,这就是一种在内在意念上达到动机的纯粹性的理性存在者[10]31。但他紧接着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困难:“从造就出人的如此弯曲的木头中,不可能加工出任何完全直的东西。”[10]30人性中具有非社会性的倾向,每个个体都不可能自身实现道德的完善。而没有这种正直公正的元首,和谐的共同体也难以维系。个体层面上自然本性与自由的无法统一的难题,必然造成整个共同体层面自然和自由难以统一的困境。
其实,康德在历史哲学中所提出的这种困难由来已久。在二元论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Plato)那里,那种拥有智慧和完满德性的哲学王就是康德的具有善良意志和丰富经验的正义元首的原型。柏拉图用亲身实践证明了其实现的艰难,康德对此不可能没有自知之明。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就做了适度让步,不再执着于元首的内在道德良善,而是退而求其次,将其描述为一种“道德的政治家”[12]378。他遵循的原则是,“要这样行动,使你能够想要你的准则应当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不管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12]382。换言之,元首无须在内在意念上具有完全纯粹的动机和目的,只要其外在行动能够符合普遍法则就是称职的。不幸的是,这种适度妥协似乎为康德普遍历史向道德自由的平稳过渡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但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人类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这些有理性的存在者全都将死亡,其类却是不死的”[10]27。但自由却具有超感性、超时间的理智层面的意义,自由的真正实现在历史内部是无法指望的。
所以,人们能够在其历史哲学中看到的一切辩证的和积极的因素最终都被裹挟在其二元论的牢笼中,无法大放光彩。康德的复合的方法论就体现了他在思维方式上的拖泥带水。历史的辩证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隐秘地统摄在其先验原则之下,因而,其历史哲学的真正主体只能是提出先验合目的性原则的纯粹理性,即一种认识能力,而不是具有历史性维度的人性。自我驱动的人性最多只是在纯粹理性的先验原则之下呈现出来的“次生”主体。康德之后,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是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等,都摒除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将辩证的、历史性的哲学精神发展到极致。我们可以说,康德的思维方式是近代哲学与现当代哲学之间的过渡者。这种过渡性质在其历史哲学的复合方法论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四、结论
康德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在于,以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为主导,以辩证思维为辅助的方法论整体。他的批判哲学,尤其是“第一批判”和“第三批判”已经为这种方法论奠定了基础。所以,在方法论或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历史哲学隶属于批判哲学。而在思想内容上,普遍历史的合目的性整体建立在道德的形而上学目的之上,并为该目的在时间进程和人类社会中的实现准备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所以,从思想特质来说,历史哲学又是附属于形而上学。
合目的性的思维方式既是对之前机械思维的超越,也是对古希腊以来独断的神学目的论的扬弃。在康德历史哲学中,有关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神意等描述并不意味着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神圣存在者(上帝),而是人类理性为把握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悬拟的概念。所以,历史哲学中的合目的性原则是一种调节性原则。康德历史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人性基于其内部矛盾而自我驱动、自我完善、自我成就。这种辩证思维在之后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逐渐突破先验哲学的束缚,演变为独当一面的普遍方法论,并对现当代存在哲学、诠释学等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德国古典时期到现当代是一个历史意识逐渐变得强烈,辩证思维逐渐摆脱各种先验预设和绝对主体的思想进程。